- +1
宅的终极奥义:居家隔离才不配叫做“宅”

▲电影《镜子》剧照。
▲主播/夏忆,配乐/ 牛尾憲輔《 reflexion,allegretto,you》,程璧 《我的心里是满的》。
撰文|祝羽捷、于是
设计 | 97

祝羽捷,作家、策展人
宅女于是:
你好哇宅女于是,你今天好吗?你宅的心情还算不错吗?
上周上海书展,我全勤出门,颠簸得乒乓作响,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特别是辞职以后,宅着的时间比出门多。但这一周,每天披星戴月地回家,倍感疲倦,讲话多了脑仁疼,性子有点躁,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是脑震荡呢。都如此疲倦了,竟然还失眠,辗转反侧,开始怀疑人生。

▲上周顶着40多度高温和暴雨天气出门看展,朋友们说我是艺术壮士。
我常常在外出和宅之间激荡挣扎,生出双重性格,一重性格渴望敞开,接收外界的信息,也表达自己,骚动不安;而另一重性格是封闭的,建立一种内循环,像是个在蓄能的铅块电池。总保持一种状态的话我会疯掉,在两种状态中摇摆,很难摆平,反而对生活保持了敏感和热情。
记得过去我们说到“宅男”这个词,心头还会闪过一丝贬义,心里想的是那些不出户,对外界不关心,只关注自我和小世界的人。普遍认为这个概念起源于日本,有种说法:很多日本年轻人丧失对外界的好奇,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在家宅着玩游戏、追星、支持偶像养成,如果自己不想去拼搏,把欲望投影在某个年轻偶像身上,看她/他去选秀、竞争、出道也是一种快乐。关于宅的极端案例有很多,我读过一则报道,日本有位宅男,职业是汽车生产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色情杂志,失踪六个月,被房东发现他在家被书架上的杂志翻落时给砸死,他生前搜集了整整六吨杂志。
说不定日本人不同意他们是宅的始祖,因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就发明了“沙发土豆”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拿着遥控器,蜷在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干,只会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说美国人是始祖,金庸先生也不干,他创作了武功高强的东方不败,不想着一统江湖,反而躲在深山老林绣起了花。说东方不败是始祖,康德先生还不干,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家乡,按着极其精准的作息生活,用东方不败的绣花精神搞创作。

▲电影《镜子》剧照。
过去的宅很容易炮制疯人,大家达成共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非疯即傻,例如“阁楼上的疯女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疯再宅,还是宅了才疯,不得而知。但大家普遍相信,与外界不交流的人必耳目闭塞,过分关注自己,跟不上时代变化,顽固不化。如今完全无须有这种担忧,一上网就什么都知道了,甚至比外面的人更能掌握国际动态、社会时事,谁家的狗失踪了,谁家在打离婚官司……这是真正的足不出户,坐拥天下。我听过戴锦华老师一个演讲,中间讲到:“两岸三地的年轻人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大突破的时代到来,但是这个文明大突破的时代未必施惠于年轻人。所以,年轻人都在经历着从小确幸到小确丧的一种生命经验,这样的一种宅生存可以成为某种保有自由和获取自由的选择,但是另一边是你已经被劳动力结构整体排斥的一种结果,你只能打点零工或者在家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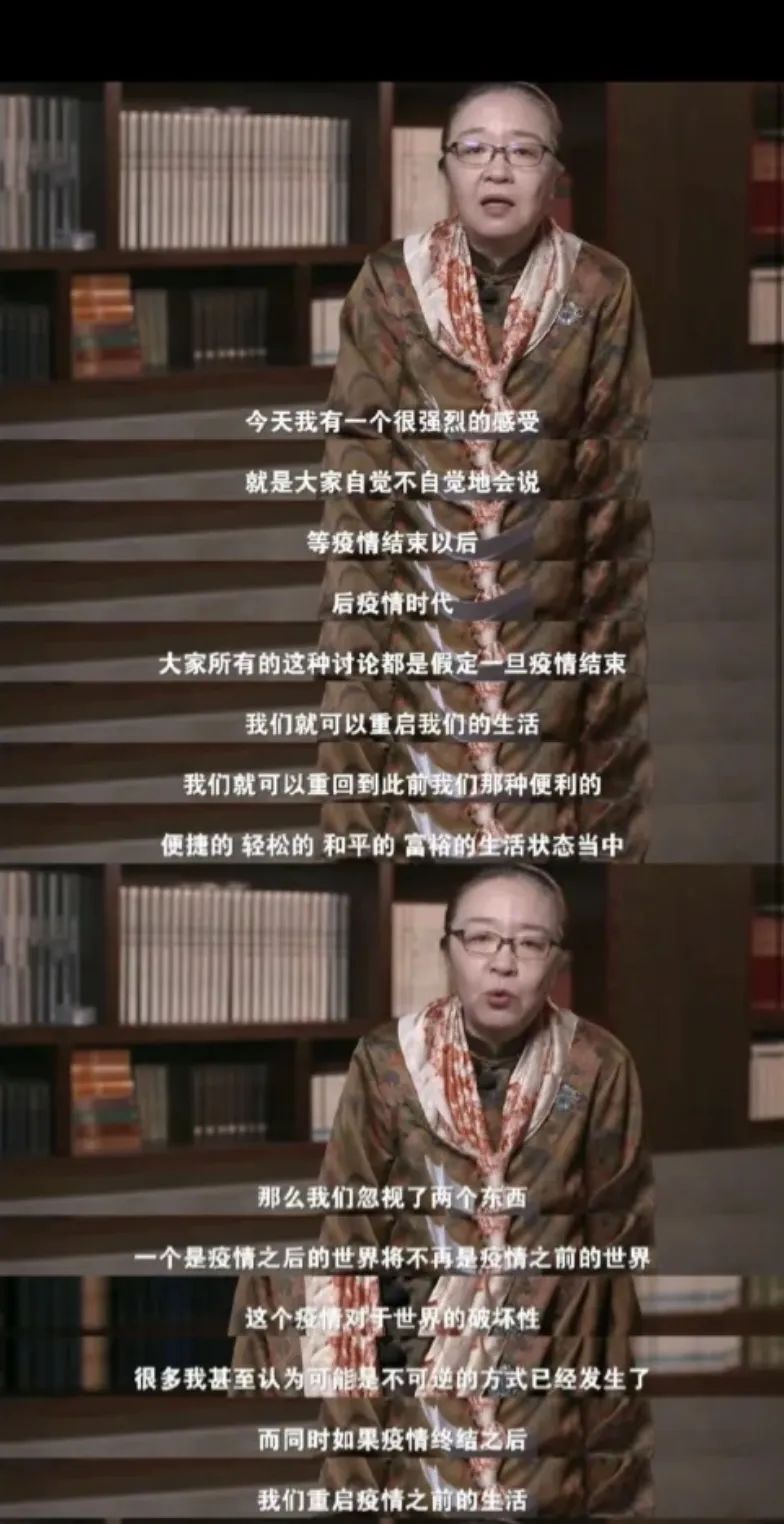
▲戴锦华老师说: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不再是疫情之前的世界,疫情对于世界的破坏性,是不可逆的。
今日的语境之下,“宅男”“宅女”有了新解,我理解的是虽赶不上康德先生这般伟人的定力,但也说明内心丰富,一个人也能待得住,不用因烦躁撕扯自己的头皮,不用拿脑袋撞墙,自洽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觉得无聊,搞不好还能在某个领域作出一番事业。宅并非意味着出家遁世,深居简出完全不会与外界阻断。宅也从一种带着悲观色彩的亚文化成了一种大众文化,不少人写宅家做饭、宅家追剧的攻略,还有不少人喜欢拍宅家vlog,分享如何宅得更动人,宅得更有仪式感。宅还成了消费主义的新形式,博主们会推荐宅家好物,从家用电器到吃鸡神器、香薰、蜡烛、睡衣、泡泡浴,宅家健身需要的跑步机、哑铃、家用动感单车,为了宅得舒服还可以买护眼台灯、平板电脑、手机支架,懒人沙发、符合人体力学的靠枕、座椅,记忆床垫。如果事业心不忘,在家soho的人还可以开一家云公司,云打卡、云报表、云会议。如果预算充足,你也可以付钱找人跑腿,再也不用像神农一样跋山涉水尝百草了。
在我看来,密密匝匝地奔波过,才真的能体会回家宅着的意义。宅自有裨益:宅着不用打车,不用受交通堵塞的罪,不用呼吸汽车尾气,还可以少花钱。更何况,出门会遇到伤害,遇到失望,遇到不理解,有时伤害别人,有时伤害自己。像我这种常常多做多错,好心也会办坏事的人,减少出门就是减少犯错的机会。唯有宅在家里,心里窃喜:真好呀,折腾了一大圈,搞砸了许多事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边界是什么,有多少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有多少不能降格的事情。该死心的死心,喜欢的人也换了一波,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多欲望和兴趣了,再也不用为不甘寂寞痛苦了。
东方不败为什么不肯出山,也许是觉得万物皆空,生命虚无。跟他不一样的是,我是处处碰壁所以退回来,带着负气,东方不败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觉得一切不过一场梦。为什么会想到东方不败,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过日子,并非无力回应大千世界,他们是发现浮华不过都是过眼云烟,索性在后方操演着沙盘,尚不输真实世界里的热闹,目光更加明鉴。如果世界是一个圆形的罗马剧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一把舒适的座椅,坐在其中,既能一起百感交集,也能独享怡然自得。我相信不少宅的人并非厌世,而是活得足够通透,他们不在乎身在何处,不在乎空间的大小和形状。

▲电影《镜子》剧照。
刚工作的那几年,我把家当酒店睡,门口放着不同尺寸的旅行箱,每个月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鞋子在门口架子上横七竖八。我见到日子过得有模有样的人,既惭愧又羡慕。其实,随意讨论宅的好处难免太过“悬浮”,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奔波在外忙于生计,回家倒头就睡,连家都不能好好看上几眼——宅也是一种特权。
我有个朋友当了母亲后,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盘腿打坐,约法三章,打坐期间不可有人来打扰。现在我懂了,那是她在自我被挤压的空间里,划出了一个独处的领域,人无论处于人生何种阶段,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里,都需要有自留地,可以看作一叶孤舟,也可以看作是伍尔夫口中的“一个人的房间”。我小时候,吃完晚饭就回自己的房间写作业,现在回忆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明知道父母不会随意越界,但总要把自己的房间反锁,写完作业写日记,日记本也是带锁的,封面画着田园风光和建在斜坡上的小木屋,颇有瓦尔登湖的味道。
有次听到许倬云老师说,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我立刻泪目。如果我能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宅”这个词对我来说程度太深了,充其量是需要一定质量的独处状态,那种状态仿佛一只潜水艇深入海洋,看到不为人知的深海景观。那些独处的时刻仿佛我那本上了锁的日记本,独自体会那些不必示人的心情和回忆。

▲许倬云老师在《十三邀》里的话。
我喜欢的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有首诗里写道:我独自一人,对自己的灵魂,满怀着巨大的爱情。
祝羽捷

于是,作家、译者
著有《六翼天使》《事后》《一只黑猫的自闭症》《慌城孤读》等小说、散文集。译有《时间之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杜马岛》《长眠医生》《黑暗塔VII》、《比虚构更离奇》、《穷途·墨路》、《失落的秘符》等二十余部英美文学作品。
祝老师:
见信好!你全勤出席书展?也太厉害了吧!我上一次一连七天出门已是去年5月旅行时的事……不知不觉已经宅了十几个月了。再仔细回想,事实上,我已经宅了足有二十年了吧。
前几天见面时,你说起《野生作家访谈录》里的片段让你感动,这反倒让我很惭愧,说到底,不会赚钱、只会宅家、很少社交的人永远是疑似loser的少数派,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宅故我在,仅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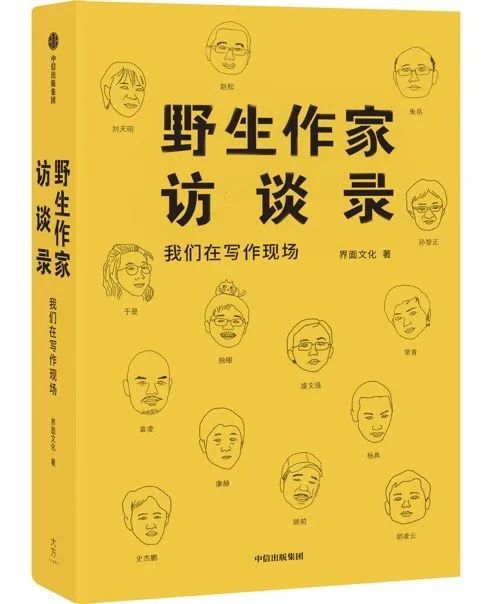
©️《野生作家访谈录》,界面文化著
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那年租房独居是1998年。但记得很清楚是天山路水城路的一室户,五楼,朝南,冬天阳光特别好,把床摆在窗前,晒着太阳读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记忆里,情节都模糊了,那片缓慢移动的梯形阳光痕迹却还很鲜明。自从有了一间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房间”,我每次出门基本上都有明确的目的,能让我立刻出门的人一定都很重要。但是,曾在番禺路租屋里创下的28天不出门纪录已在2020年疫情期间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居家煮饭喂养自己的纪录……总之,在家是很忙的。严格来说,我不是御宅族,这个古老的名词早已消失在瞬息万变、每天出新梗的网络历史里了。但当年的御宅族现在怎样了?要是有人做个追踪报道应该很有意思。

▲电影《镜子》剧照。
我不沉迷于追剧和打游戏,也没有社恐,徒有宅人的美名。我也不是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关注自我和小世界的人”。我关注很多事情(甚至可能太多了),因为我总觉得世界在以几何倍数扩增——比如中老年人不知道的年轻人的世界,比如女性不知道的男性的世界,比如loser不知道的人生赢家的世界,比如南亚人不知道的中欧人的世界——通过书籍、影视、音乐、新闻、网络乃至坊间谣言,我假装知道了一些,并且对这种假装的实质保持警惕(真的有人完全地、透彻地、感同身受地知道所有的事吗?)网络促成了同类相聚,也导致了高度同质化,社会学家已定论,这很可能催生阶级固化、极端主义等退步状况。宅人都必须挂在网上,对这一点要有自知之明。
我记不清有多久没像“沙发土豆”那样懒着了。我有自己的房间,但没有伍尔夫500英镑的年收入(以零售价格推算,1930年的500英镑相当于今天年薪4万美元;以收入推算,则相当于今天年薪12.3万美元)。工作时间表就像紧箍咒,限定了我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这恐怕要归功于二十年来催稿的编辑们。他们给了我一个确定的deadline,我就能细化出每天的时间表。我相信,你提到的那些宅家的博主们也会深深感受到时间规划的重要性。当然,执行规划更重要。在家开云端公司的人,我觉得不是宅,只是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根据我多年来的经验,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应该分开,否则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都会受影响——幸好我们的工作只需一台破电脑就可以了。

▲ 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
讲到底,宅是很人工的。衣食住行,工作娱乐,都建立在现成的社会化标准服务上,从属于消费社会。很难说宅是不是更环保,因人而异吧。至于我,每天收快递时会觉得很浪费,但也无计可施。宅的代价很昂贵,所有必需品都让别人送到家门口。
现代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在N种糟糕的选项里做出相对而言更适合自己的选择,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绝非最好的选择。但你说得没错,交通是噩梦,污染是噩梦,有时候,交际也会像噩梦。现代人花费在交际上的精力和时间是巨大的浪费,所以聪明人都会做减法,做取舍,而且多半都会首先舍弃没有营养的社交。不过,这种取舍的前提是已经粗略地看过世界,换句话说,没有闯荡过江湖,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宅心。
谁不想在瓦尔登湖畔当梭罗呢,更何况,他的避世一方面贴近自然,一方面距离热闹的社交中心也不远。是左右逢源,而非左右为难。梭罗的《瓦尔登湖》第一章讲明了经济的幻觉,第二章就开始呼吁我们回归现实。
梭罗不是极端自然主义者,而是向往着希腊式的人性觉醒。事实上,在湖边的农作物种植项目因为严寒而失败后,他又写了著名的《抵抗公民政府》,提出了“个人高于国家”的观点。
那是1846年。所以,一百多年后,只记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当代人多少是误解了他,把他当作避世隐居的榜样更是错得离谱。人家明明很有入世的觉悟,贴近土地绝非创造自然生活方式那么简单,湖畔小屋既是他的创作基地,甚至还是废奴者学会的年会举办地。湖畔生活让他越来越明白,个人的良知是政治生活的基础,而且,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集体生活,人类生活终究都不是大自然中最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已。人的局限性不能被忽视、被低估。
你不要负气了才回家宅着,这样对家不公平,对自己也不宽容。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安顿自己。我有朋友把独居的空间装饰得美轮美奂,沉溺于独享一切。相比而言,我的狗窝毫无风格,几近简陋,四面墙都被书堆满了,有喜欢的画也没地方挂,偶尔想买束花,坦白说,也没地方摆。花和画,和人一样,特别需要自己的空间。我把它们的空间都霸占了。
于斯曼有本书叫《逆天》(上海译文版译为《逆流》),我很喜欢,当年奥斯卡·王尔德也很喜欢,还称其为“毒书”。主人公烦透了巴黎的虚伪和浮夸,决定离群索居,闭门不出,完全依照自己的品位打造避世豪宅,对宝石、绘画、花卉、香氛、植物、古书的评论,足以见得他对世俗潮流是多么不屑。迷人的,总是这样的避世美学,看起来既沉沦又高昂。但冷静下来想,吸引我的并不是这种贵族式的避世方法,而是用自然主义的研究精神研究文学、绘画、音乐及奢侈品对精神的意义,这种写小说的方法让我觉得很有趣。事实上,从物指向精神的路径是很容易走偏的,阶级意识、物质主义、时代趋势都可能把创作者带上歧路。不说创作者,就连生活者本人也会有所迷失。

©️《逆天》,(法)乔里-卡尔·于斯曼 著
在我想来,甘愿避世的人总有沉迷的对象,必须有,无论电玩或宝石,还是书籍或影视,甚或囤积癖者的囤积物,精神总归要有聚焦的重点。既然如此,为自己好好挑选精神落脚处就是最重要的事。精神上保持审美的自由,甚至道德的自由,才是宅的终极意义;否则,就只是身体和行动的物理性局限,是逼仄空间里的蹉跎和堕落,是表演性的放弃,是假的宅人,真的囚犯。
顺祝夏凉(我快热疯了)。
于是

本文配图部分来源于《镜子》剧照,部分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虚度书店
原标题:《宅的终极奥义:居家隔离才不配叫做“宅”》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