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叶攀︱波兰民族主义的转变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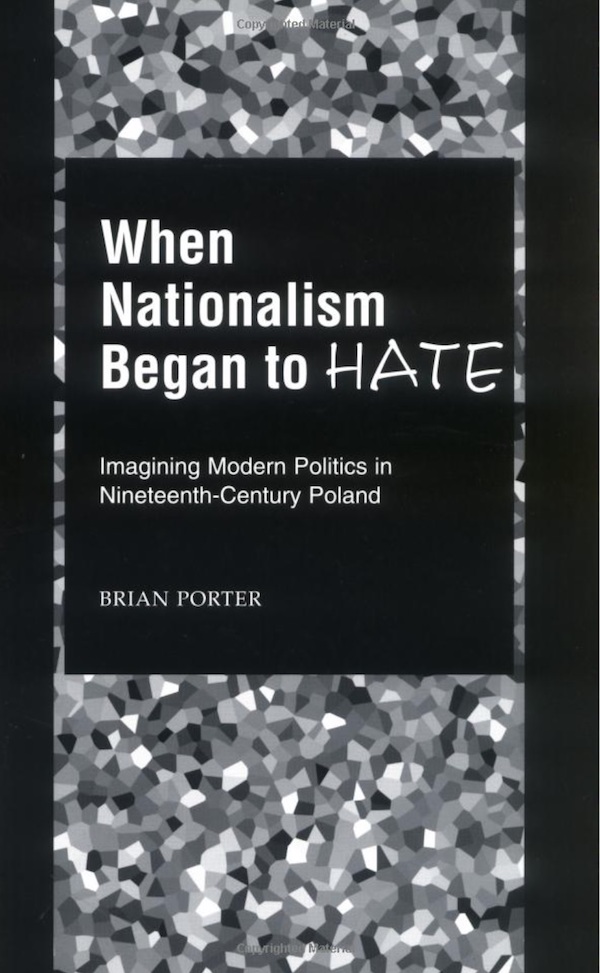
波兰是东欧重镇。近代以来,波兰可谓群星璀璨,涌现出了无数风流人物,肖邦、密茨凯维奇、居里夫人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波兰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也是风起云涌,1830年和1863年的两次波兰起义的影响力遍及欧洲,也是众多国内外学者探讨的对象。布莱安·波特(Brian Porter)的《当民族主义开始仇恨》(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就探讨了波兰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转变历程。
的确,从十九世纪初期到1863年起义的波兰民族主义是解放性的。东布罗夫斯基、符卢勃列夫斯基、科希秋什科等人们熟知的人物都活跃在这个时期。相应地,这个时代的波兰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普遍性”,是普遍的解放。正因为这种解放性,波兰民族主义在这个时代鼓吹的解放并不是针对俄国这个“民族”,而是针对的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波兰民族主义并不把整个俄国“民族”视为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口号是“为了我们的自由,也为了你们的自由”。因此,这个时代的波兰民族主义强调的是社会革命,这个革命针对的不仅是沙俄统治者,还有波兰本国的贵族等上层统治者。毫不奇怪,这个时期的波兰贵族不仅不热心支持波兰民族主义,事实上这些贵族恰恰是反对波兰独立(和革命)的,比如奥匈帝国占领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的波兰贵族就接受了并认同奥匈帝国的统治。这些贵族要求的只是奥匈帝国统治下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自治”权利。在这个时期,保守派和波兰民族主义者也就成了反义词。不过,这个时期波兰的革命者主要从哲学和文学角度谈论波兰的革命,他们探讨的波兰“民族”与其说是现实中的波兰人或者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精神”。这些革命者和波兰国内的联系不多,受到他们影响的波兰群众也为数甚少,他们的活动在多数时候是知识分子的密谋。国内一些学者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叙事就止步于此,似乎解放性是波兰民族主义与生俱来,并且永远持续的特质,1863年之后波兰民族主义也因此沿着解放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直到1918年波兰获得独立,甚至延续到了波兰独立之后。但是,正如本书指出的,这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波兰民族主义从十九世纪初中期知识分子的密谋,向社会运动转变的过程中,其言辞和实践也日益倾向威权主义。那么,我们就来具体追寻一下波兰民族主义的变化历程。
1863年起义失败之后,波兰出现了一股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社会运动的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波兰的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吸收的不是法国的孔德一系思想,而是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巴克尔(Buckle)这一系思想。众所周知,斯宾塞的思想强调的是“生存斗争”和社会进化。这一点被他的波兰追随者全部接受了。但是和斯宾塞的主张不同,波兰的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并不强调物质层面的“生存斗争”——因为这必然意味着他们反对的政治行动,也不适应他们的“文明”胃口。在这个方面,奥若什科娃(Orzeskowa,《涅曼河畔》的作者)等波兰实证主义者们对斯宾塞理论进行了改造,他们吸收了巴克尔的思想,亦即“文明”之间的竞争结果不是由力量决定,“适者生存”的最后胜利者必然是最文明的也是最自由化的那一个。他们的观点是,因为波兰的经济社会比沙俄发达,“文明”程度更高,更加“欧洲”,因此根据(实证主义揭橥的)历史规律,波兰必然战胜“落后”的沙俄,获得独立。那么如何达致彼岸呢?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开出了“工作”这个药方,而反对早期波兰革命者的“行动”,换言之,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者们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代替革命性的政治行动。斯维托霍夫斯基(Swietochowski)对这一点的鼓吹尤其着力,维斯利茨基(Wislicki)甚至主张创造一个资产阶级出来。大家都知道,实证主义对于抽象的哲学和“精神”不感兴趣,与之相应,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概念也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不再以前述波兰革命者们主张的抽象的“民族精神”,或者人类解放作为波兰民族的标志,而是把波兰人构成的“共同体”设定为波兰民族。也就是说,这股思潮已经放弃了早期波兰民族主义者们追求的普遍性。当然,这股思潮既然强调“工作”,而且是当时波兰的法律和规范边界内的工作,那么这股思潮的追随者也就从他们的保守派对手那里引入了等级、权威等范畴。这样做的涵义不言而喻。一言以蔽之,波兰的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主张的是:只要波兰人努力工作,发展资本主义,波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就能超过沙俄等东欧落后的邻居,波兰独立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是,到了1878年,一位驻波兰的沙俄官员把俄属波兰称为“(沙俄)帝国内最安宁的地方”。

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上述主张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政治结果,波兰的安宁也没有持续太久,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波兰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前述的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地位很快动摇了。被称为“叛逆者”(niepokorni, the defiant ones)的新一代波兰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呼声》(Glos, The Voice)和《社会主义评论》(Prezglad Spoleczny, The Socialist Review)杂志周围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这个时代的波兰革命者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沙俄上大学或者进行其它活动,他们也就通过各个渠道受到了来自俄国革命者,具体地说就是俄国民粹派的影响——这或许是某些国内学者忽视这个时期的波兰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对于这一代波兰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波兰一月起义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他们生活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是他们的切身体验。这一代波兰青年知识分子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基辅等地的革命行动,以及阅读诸如“土地和自由社”(Zemlia i Volya)这样的俄国民粹派组织的小册子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活动中,也有不少波兰革命者投身于其中。反过来,也有很多俄国革命者支持波兰独立,甚至羡慕波兰的起义传统。相应地,“叛逆者”也在挑战前述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者对俄国的“东方”划分。早期“叛逆者”坚持了他们的先辈的社会解放路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毕苏茨基则是受到俄国革命者影响较小的那一系。当然,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比同期的沙俄高得多,波兰革命者不像俄国民粹派那样抗拒历史和社会的进步,波兰也没有沙俄那样发达的农村公社。因此,这个时期的波兰革命者并不像俄国民粹派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在波兰是可以避免的。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更多地表现在他们的波兰“人民”概念上。
不用说,“叛逆者”不会认同前述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者对工作的强调,以及对历史自动进步的信仰。事实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叛逆者”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者的反叛。“叛逆者”强调的是革命性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求通过革命性的政治活动实现历史进步。十九世纪初期中期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们把民族设定为“行动”,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叛逆者”回到了这个传统中。人们不难发现,“叛逆者”们也受到了强调直接行动的俄国民粹派的影响。不过,由于波兰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个时代的波兰革命者们不再像他们的十九世纪初期前辈们那样从哲学角度谈论民族主义和人类解放,开始具体地谈论他们的诉求对象,亦即波兰“人民”的实际构成。一开始的时候,社会解放和民族独立也像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那样协调,波兰的解放不仅意味着沙俄统治被推翻,也意味着从波兰社会上层的统治中解放。不过,十九世纪后期的波兰社会,已经比十九世纪初期的波兰社会复杂得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的社会阶级分化也和其它国家一样日益明显。这就使得波兰民族主义者追求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性越来越受到挑战。这也就埋下了波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的伏笔。

“叛逆者”活动初期,他们对波兰民族问题采取了两种态度。利马诺夫斯基(Limanowski)等未来的波兰社会主义者认为,波兰独立之后,波兰无产阶级才是波兰民族的真正代表;只有消灭了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波兰民族才能出现在现实中。《呼声》集团的波普瓦夫斯基(Poplawski)在这个时期的观点也相当类似。与之相反,波兰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波兰民族是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的。因此,波兰民族包括了波兰的所有阶级。波兰人民(这个概念是从俄国民粹派那里移植过来的)也包括了波兰的所有被压迫者。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呼声》集团成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统一战线。
不过,这个统一战线并未维持太久。十九世纪后期的波兰,其经济比沙俄本部更加发达,工业化程度也更高。这个时期波兰相当数量的工农也接受了初步的文化教育,有能力阅读各种文化产品。因此,这个时期波兰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都开始发展了。到了1905年,波兰农民也摆脱了长期的冷漠。诸如克齐维茨基(Krzywicki),凯列斯-克劳兹(Kelles-Krauz)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活动的。他们强调的当然是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他们也力图把波兰的独立、解放和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随着波兰社会的发展,他们也开始更加强调社会主义。1889年,克齐维茨基对波兰民族主义中日益增长的保守倾向做出了批判。1892年,波兰社会党在巴黎建立。同年,民族主义的波兰民族联盟(National League)也建立了。这两个组织之间很快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898年12月沙俄当局建造的密茨凯维奇雕像落成的时候,波兰民族联盟主张参与沙俄统治当局主持的雕像揭幕仪式,并通过这个仪式对波兰工农进行民族主义教育,而波兰社会党主张对之进行抗议。结果,到了雕像揭幕的时候,波兰民族联盟的领袖们和忠于沙俄的波兰人以及沙俄人士站在一起参加仪式,而波兰社会主义者们在障碍的另一边被捕。1899年,波兰社会党禁止其党员同时加入波兰民族联盟。1905年6月波兰罗兹工人运动期间,支持这一运动的波兰社会党和反对这一运动的波兰国家民主党组织发生了流血冲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波普瓦夫斯基也放弃了原先的“理想”。有趣的是,波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最终分道扬镳也有来自俄国的因素:这个时期正是俄国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并最终决裂的时期,也就是俄国的“民族道路”被马克思主义者放弃的时期。由于前述的波兰社会经济和沙俄的差异,波兰的争论也就不围绕着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而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和社会解放之间的关系而展开。波兰民族问题不再能够被推到遥远的未来。同时,这个时期历史进步的观念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波兰也不例外,维茨科夫斯基(Wieckowski)甚至像索列尔(Georges Sorel)那样彻底否定社会进步理论,波兰的斗争也因此失去了解放涵义。“人民”的定义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这个时候的“叛逆者”放弃了阶级斗争观念,他们的“人民”也就把波兰社会上层包括了进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毕苏茨基虽然还在波兰社会党内活动,但是他已经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完成波兰民族主义事业。
在波兰民族主义者方面,率先发难,试图切断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之间联系的是瓦林斯基(Warynski)与德乌斯基(Dluski)。他们组织的集团把民族视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没有差异,也不会发生冲突。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也不再是历史进步的载体。显而易见,他们的民族概念已经是压迫性的了。不奇怪,马克思本人对瓦林斯基做出了尖锐批评。瓦林斯基对马克思的回答则是:“以波兰的名义召集起来的运动,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必须是反动的。”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波兰又一次迎来了社会运动的高潮,这次社会运动中,波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再携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德莫夫斯基(Dmowski)、巴利茨基(Balicki)等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逐渐浮出了水面。这也是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新兴右翼崭露头角的时期。他们建立了“国家民主党”——波兰重新独立后于1919年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这个党获得了最多席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党也是波兰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919年6月28日,代表波兰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正是德莫夫斯基,他也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右翼的领袖与偶像之一——1925年,德莫夫斯基和西科尔斯基(Sikorski)是波兰右翼期望的、以意大利法西斯为模板的政变的两名潜在领袖。目前,德莫夫斯基是波兰“法律和公正党”的英雄之一。波兰国家民主党不仅反对任何民族问题上的“多元”,而且干脆禁止在其出版物上探讨阶级斗争——有趣的是,剧变后的波兰也有这个禁忌,当然其结果,正如戴维·奥斯特(David Ost)指出的,大同小异。不用说,国家民主党对社会革命不会感兴趣的,他们的“人民”当然是包括波兰的资本家、地主在内的。这个时期波兰日益发展的社会运动也被国家民主党的人士们解释为“外国煽动者”的阴谋。到了最后,连“人民”本身都成了与“整体”对立的“部分”利益,成了民族团结的绊脚石(该党1903年的纲领)。米科夫斯基(Milkowski)甚至提出要对人民进行“启蒙”,以使他们能够完成“民族防御”。这样一种论调我们似曾相识。波兰国家民主党支持的“民主”,也成了寡头政治的同义词。不过,波兰国家民主党并不支持自由放任经济。从理论上说,十九世纪末期,贡普洛维茨(Gumplowicz)试图锻造一种把自由主义和生存斗争熔于一炉的社会学。这个学说也成了从那之后的波兰民族主义的理论支撑之一。德莫夫斯基也早早就“论证”了暴力和敌对的永恒。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和谁更接近,笔者以为不难看出。
波兰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如此程度之后,对其它民族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首当其冲的是犹太人问题。如前所述,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波兰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解放和社会革命,而不是波兰的民族身份和族群特质。自然,对于这个时期的波兰民族主义来说,犹太人的解放和波兰的独立是同时的、同步的。二者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冲突。倒是一些亲沙俄的保守派,例如杰伦斯基(Jelenski)鼓吹反犹主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这个状况发生了逆转。从1888年奥尔丁斯基(Ordynski)的文章起,《呼声》集团日益滑向反犹主义。通过这样一种反犹主义,前述贡普洛维茨鼓吹的那种永恒的、西西弗斯式的暴力“斗争”进入了波兰民族主义叙事。波兰国家民主党的历史叙事里,犹太人成了寄生虫,而且还是波兰国家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敌人”的象征与标志,以及阴谋的主角。这些叙事让我们不禁有似曾相识之感。
在波兰国家民主党的历史叙事中,波兰的独立也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解放。如前所述,早期波兰民族主义的解放叙事中,波兰的解放不仅意味着自身的解放,也意味帮助沙俄人民获得解放,或者说互相支持。这也意味着承认乌克兰、立陶宛和罗塞尼亚等地人民的自决权利。德莫夫斯基等人则相反,他们采纳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解释成两个民族之间的“生存空间”竞争——也就是斯宾塞式的“适者生存”,这样一种竞争当然无所谓善恶,也无所谓解放和奴役。与之相应,1892年,德莫夫斯基发表文章为殖民主义辩护。在德莫夫斯基的叙事中,波兰不再是早期波兰革命者观念中的受害者,他们为独立后的波兰要求的,也不再是波兰人居住的地方,而包括了乌克兰、立陶宛和罗塞尼亚(Ruthenia)。这些主张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大家都知道,波兰刚刚在1918年重新独立,就占领了立陶宛的一块地方并与立陶宛开战;随后波兰入侵了乌克兰,并和新生的苏俄发生了战争。1938年,波兰和纳粹以及霍尔蒂统治的匈牙利达成协议,接着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切欣(Cieszyn)地区。

波兰国家民主党的人士把这种民族主义叙事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其中之一是巴利茨基提出的“民族利己主义”(national egoism)思想,其要义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设想的“民族”有权强行贯彻同一性,创造一个种族-语言共同体。对于德莫夫斯基等人来说,波兰并不是受害者,也不需要诉诸任何崇高的事业或者伦理标准来证明自身(而这正是十九世纪初中期波兰民族主义的主张)。在他们鼓吹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里,任何波兰民族征途上的绊脚石都是他们的敌人,都必须被击败,而且必须被摧毁。他们叙事里的波兰民族,也是一个把原子化、碎片化了的波兰人连结起来的有机共同体。
大家都知道,在波兰民族主义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波兰仍然被沙俄、普鲁士德国和奥匈帝国瓜分。为了避免他们这些为殖民主义和征服辩解的主张反噬自身,这些人士可谓费尽心机,波普瓦夫斯基提出了一种既针对德国和俄国保持波兰特性,又维持波兰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野心的主张。巴利茨基则提出,只要意图良好,征服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么一来,波兰民族主义者们就可以既批判沙俄和德国(还有奥匈),又推行自己对东欧其它地区的野心。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是无穷无尽、永远存在的,而不是历史性的。这就是前述贡普洛维茨理论中的西西弗斯式冲突。不用说,这样一种民族主义也是不择手段的。1899年沙俄发生饥荒,一些波兰人试图组织援救行动,这些人受到了国家民主党的严厉批评。后者也就彻底放弃了十九世纪初中期波兰革命者的口号:“为了我们的自由,也为了你们的自由。”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叙事中,波兰之外的其它“民族”也就成了一个无分化的,因而和波兰“民族”全面敌对的整体。这样的民族主义叙事也不再区分诸如沙俄驻波兰的官员、推行俄国化政策的人士与普通俄国人,更不用说俄国革命者。德莫夫斯基甚至以这个为标准对沙俄政府针对波兰实施的“俄罗斯化”政策进行辩解,其潜台词显而易见。对于波兰国家民主党的人士来说,欣赏俄国文学艺术也成了不可接受的行为。不用说,这些人对德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排斥态 度。换言之,波兰国家民主党的这种民族主义排斥一切“非波兰”的行为。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旅程,波兰民族主义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国家民主党锻造的这种叙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波兰消失:剧变之后的波兰,当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了禁忌之后,社会不平等与分化也被一些人视为“非波兰”的行为。
虽然本书的讨论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但是德莫夫斯基及其代表的那一种民族主义在那之后并未退居幕后,而是一如既往地活跃在波兰政坛。因此笔者有必要多耗费点笔墨。如前所述,1918年波兰独立之后,德莫夫斯基仍然是波兰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以及右翼的领袖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莫夫斯基指控犹太人策划了全球经济危机,并且从中获利;他还公开仰慕意大利法西斯。在一战后的岁月里,德莫夫斯基以及波兰国家民主党越来越倾向于天主教,他甚至认为,天主教和波兰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939年1月,在纳粹入侵波兰之前八个月,德莫夫斯基病死于沃姆察(Lomza)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时期的波兰民族主义也在那之后不久告一段落了。不过,从2001年起,新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在剧变后的波兰又再次进入政坛,并且登堂入室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