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思诚与见独之间,他说惟期暗夜承薪火,不因微薄忘古今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学系男神老师”
“北大十佳教师”
“当代真正的儒者”
“北大哲学系杨立华老师是个怎样的人?”问题在知乎上获50w+浏览量,回答者众多,“杨立华老师是本科期间最喜欢也是最敬佩的老师之一了。”“总能感觉到他的博学和深度,上课的时候常常有顿悟的感觉。”“站在讲台上,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北大最帅,没有之一。”可以说,杨立华是一位兼具学识、气质和品格的老师、学者。

他的庄子哲学课一经b站播出,便吸引众多校内外学子观看,弹幕满屏。杨老师之所以带领大家阅读经典著作《庄子》,是因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甚至变化越来越显著、剧烈的时代,我们需要经典的恒久的力量,来支撑我们前行。
《庄子》的阅读曾经改变了他的一生,使得他转向了哲学,并走出了“无法忍受的穷极无聊,懈怠,没有方向,迷茫”的状态,他也希望将这种力量带给青年学子,同时将经典转化为我们同时代的思想。
当学生回忆起杨老师,都是深深的敬佩。“印象最深的就是有次他重感冒,约莫还发烧,但是仍然脊背挺直地坚持给我们上了一整天的课,因为不能耽误我们的学习。下课的时候发现他的衬衫背后都被汗水打湿,他一句抱怨也没有,依旧慷慨激昂地说着他的孟子。”

如此博学、出众、广受赞誉的老师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跨界经历和心路历程。
他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对于专业他本人并没有那么专注和喜爱,反而常常感到闷闷不乐和迷茫无助。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蔡志忠的漫说《庄子说》,因为感到有所启发,继而就找来《庄子》的原著细细阅读。由此,打开了杨立华通往哲学之路的大门。
从工程热物理学到哲学,杨立华的人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也许正是由于这段跨学科的人生经历,杨立华的学问和日后的讲课不仅为哲学专业的同学所推崇,在深受非专业人士的喜爱,将哲学的道理和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不是成为束之高阁的学问。
有人这样评价,“就他在非专业同学中为中哲带来的影响来说可以说‘人能弘道’。帅和风度是很多人去听课的最简单的驱动力,风趣是他留住学生听众注意力的外在特点,而他也确实以容易接受的方式将儒家的光芒展现给大众。”
他不仅将知识学进入了,还真正践行于己身,有着由内而外的儒者气度。
有学生赞许地说:“简单来说我觉得杨立华老师,是一个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儒者。他学儒家、讲儒家,行事作风也也按儒家的精神标准来要求自己。杨老师的思想和上课讲的内容都是非常正能量的东西,努力给大家展示世界上积极的光明的道理。杨老师身上为人处事有原则、心中有力量、知识渊博、有责任感、才华横溢等等的性格特点,完全展现了儒家精神的人格典范。”
杨立华老师的新作《思诚与见独之间:中国哲学论集》最新出炉啦,这无疑是本非常独特的书,收入其中的文字,时间跨度整整二十年,字字皆出于他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阐释心得。
还记得2000年春季学期,杨立华老师为北大哲学系98级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结课的当晚次陆象山《鹅湖诗》韵,撰有一首七言近体,表明了他的生活方式和治学态度:
道崇自然德崇钦,竹林伊洛两关心;每寻嵇阮狷狂迹,更慕程朱德业岑;无意埃尘纷起落,有心名相任浮沉;惟期暗夜承薪火,不因微薄忘古今。
今天,小北就带领大家一起领略《思诚与见独之间》的洞见,走进杨立华老师的世界,一个点亮的哲学世界:
01
儒学复兴与宋学的禁欲取向
以韩愈为宋学的远源,这已经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界的通识。
儒学复兴的首要工作当然是重塑儒学的身份认同,即确立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据,而这一目的,韩愈是通过“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来达到的。由此可见,韩愈对儒学的提倡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工具性的立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何以韩愈并不格外地关注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宋学的主题似乎仍在延续中唐儒学复兴时面临的问题。如何在政俗两面摆脱宗教迷狂仍是士绅阶层最为关注的关乎国家命运的大课题。
要完成在政俗两面摆脱宗教迷狂和重建儒学身份认同这两个互为表里的任务,各种基本的理论形态所指向的实践的方向虽有种种微细的不同,但究其实质,则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诉诸刑政的措施,如韩愈提倡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另一种则是在世俗生活层面,以一种根本性的伦理精神形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宋代儒者普遍认识到从刑政手段上禁绝佛老的影响既难奏效,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如何重建由一种根本性的伦理精神贯注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修养手段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由这一根本的伦理精神统贯起来的道德秩序,便成为北宋儒者最为核心的关注。
如果将洛学与我们前面通过演绎法推导出的、围绕在政俗两面摆脱宗教迷狂和重塑儒学身份认同这一核心问题的几种理论形态相对照,我们便会发现,洛学最接近于我们所说的“稳态结构”。
这一情况使得洛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渐渐成为一般思想界的普遍共识,这种普遍共识深刻地影响着宋代儒学的总体取向,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最终“真理”判准的构成,当这种普遍共识成为一切思想表达的潜在前提时,程朱理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真理”。
02
以无为用和天地之心
近代以来,在几乎所有的哲学史阐发中,“用”都在体用的对举中被范畴化了。将中国哲学当成一种概念化的思考方式,其正当性何在?难道概念化的思考方式不是柏拉图以来的古希腊传统所独有的吗?将中国哲学“提升”为一种概念化的思考方式,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文化身份的自我沦丧呢?具体到此处的讨论,范畴化的方式在一种表面性的提升中,错失了对“用”的原本的根源性的把握。
事实上,“用”才在王弼的思里有其突显的地位,“用”还贯穿王弼的思的所有事相。所有的“用”都是恰当的吗?如何才是恰当的、合乎道的“用”呢?答曰:以无为用。
“穷力举重,不能为用。”如以锤子锤打东西,当然是要锤子重些效果才好,然而如果锤子重到了要勉力才提得起来的地步,就反而不能发挥锤子的作用了。因此,“用”要以适手为度。“常”就是适手性。
而“以无为用”,首先就是适手之用。在适手之用中,物之物性、用具之有用性达到了完足。在适手之用中,使用者与用具浑然一体。用具在其有用性之充极中隐身于无。在这种充极性的隐身中,使用者与用具切身地相遇了。
在用中,或者说向着用,天、地、天地之间的万物以及人(王)敞开、相遇。相遇即敞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敞开不是空间性的,相反,空间性倒是以敞开和相遇为根基的。空间性植根于从可用转为在用的过程中某种必须不断地去除的东西。
“用”扭结起了人与万物的相遇。在这一相遇中,既不是万物向着作为主体的人摆置,也不是人向着用具存在,而是共同向着“用”本身摆置,向着由“以无为用”而开敞的“天地之心”摆置。万物与人在这一根源性的敞开之域中相遇。
03
魏晋时代、王弼化与玄学话语
我们要确立一个时代的专题研究,首先要建构的是一个研究的对象域。对象域的建立,取决于诸多边界条件的确立。首先是构成对象域的历史时段的起点和终点的确定。我们注意到,在既有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构成断代研究的时代划分往往与朝代史有关。
就魏晋这个个案而言,汉魏之际的转折具有根本的意义。某种断裂的楔入,是有关魏晋这个时代的专题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
其次,在一个封闭性的历史时段里,必须看到藉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某种统一的精神气质。这一精神气质也就是汤用彤所说的“普通思想”或“一般思潮”及其得以形成的一致的眼光和方法。换言之,建构出时代内部的一致性特征和某种同质的连续性,是对象域能否成立的关键。
如果说魏晋玄学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中具有某种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首先要归因于其对象域的成功建构。
我们还能否在“玄学”之外,找到走近魏晋思想的新的视野呢?这里,“玄学之外”这一提法本身就包含着颠覆的企图,但这里的颠覆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颠覆意味着在某种公认的完成之上找寻重新开始的可能。颠覆是对魏晋玄学研究的某种终结可能性的觉察和拒绝。
使玄学成为可能的细化格栅源出于对王弼思想的框架化表述。事实上,魏晋玄学几乎就是王弼化的魏晋思想。
“玄学之外”绝不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改变,换言之,我们并不是要在玄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作任何平面的拓展,或将目光放在各种各样琐屑的、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相反,“玄学之外”正是要在玄学范式关注的对象上挣脱玄学话语的束缚,从而更深入地把握魏晋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

04
郭象与政治哲学
在郭象的政治哲学里,理想的统治者是圣人。作为道家和儒家共同追求的人格典范,圣人成为一个契合点,使得郭象可以自如地将儒家的种种政治理念纳入他对《庄子》的阐发和解释当中。在《庄子序》中,郭象明确将“内圣外王之道”标举为《庄子》一书的基本宗旨之一。而正是这一“内圣外王”的圣人形象,为解决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历史和现实中真实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张提供了基础。
郭象的理想治世其实只能在有圣人维持的偶然的历史瞬间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一实现了的理想治世,最终又必然会在后人对“无为之迹”和“仁义之迹”的仿效中,渐渐地失落。
经由郭象的努力,道家的无为之政的外延被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在他的《庄子注》当中,无为不再是对古代圣王的理想治世的某种诗意的乡愁,而是变成了极富现实可能性的政治进路。
这里,“迹”与“所以迹”这一重要的创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他可以毫无障碍地将历史上的各种治迹通通纳入无为的政治范畴当中。
当然这样做也有从根本上消泯不同政治取向之间的限界的危险。而实际上,他的思想中也确有这样的倾向:“尧桀将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辩哉!”(《骈拇》篇注)而且,既然“迹”只是圣人对变化中的时世的顺应,那么,一切暴政也都可以以此为借口,为自己找到正当性的基础。
以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来理解郭象的政治哲学,认为郭象的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进而认为郭象要在儒道之间进行折衷和调和,这是一直以来魏晋玄学研究的根本误区。事实上,这一问题意识本身就建立在对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的误读和夸大之上。从我们前面的细致梳理可以看到,郭象的政治哲学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调和主义的产物,而应被看作在现实的历史处境当中,道家思想的某种自我发展和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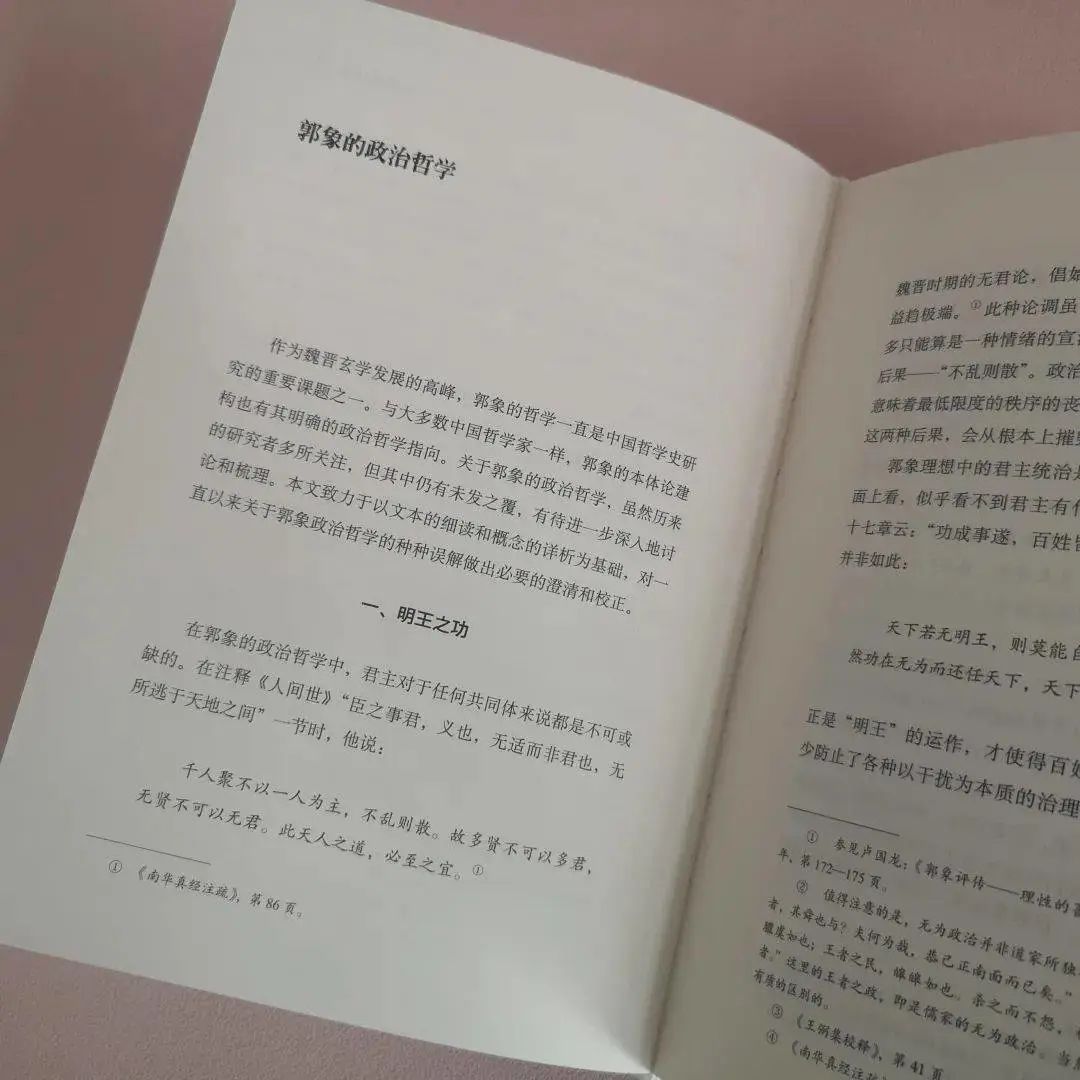
05
孝的心性基础:孔子之“敬”与孟子之“慕”
《论语》中关于孝的论述,引出了“礼”和“敬”这两个关键词。实际上,“礼”和“敬”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说的孝是以敬为根本的。
而孟子关于孝的论述,触及几种与孝有关的情感。孟子将重心放在了“慕”上。他将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关切和欲求,统一放置到了“慕”这一情感之下。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孝应该有从孩童时期延续下来的对父母的依恋为内在的基础。对父母之“慕”应该超越各年龄阶段其他的关切和欲求,成为人生始终不变的重心。尽管孟子并没有将“慕”作为孝的一般标准,但“慕”的引入本身,已经与孔子关于孝的论述形成了差异。
以“敬”为情感基础的孝,首先指向的是个人的成德。宋明理学的修养工夫中,敬字始终处在核心的位置。对于任何个体,敬都意味着收敛凝聚。朱子在解释敬字的时候说道:“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此种收敛凝聚,既有助于个体边界的建立,也有助于对个人分限的清醒认识。
正是通过敬,个体明确了自己在自然-社会-历史中的特定位置,也明确了这个特定位置的责任和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敬是一个人能够做到“克己复礼”的前提。
“慕”则与此不同,作为一种向外的关切和欲求,更多地指向了对个体界限的超逾和忽视。从孟子所说的“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这样的表达看,“慕”显然是某种接近异性之间的思恋的情感。
当然,从孟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成长阶段“慕”的内涵不同,比如“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所以,不能说孟子因此混同了五伦之间的差别。但从“大孝终身慕父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延续年少时对父母的依恋的倾向。此种倾向,至少会有削弱人的精神自立的危险,从而延阻人的成长和成熟。
究竟以什么样的情感底色为基础,来确立现代社会的伦理准则,恐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许在孔子的“敬”与孟子的“慕”之间,我们可以找到更契合时代的孝的情感基础。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