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群居是人类本性吗?
2006年,我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刚刚开始,《秩序、失序与战争》英文版出版了。这本书的灵感来自我早期的田野调查:首先,我在就读博士期间研究了欧洲农村的社会变革;其次,我在澳大利亚了解狩猎采集者如何调整他们的社会策略,以便适应环境。然而,2005-2017年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4-2016年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合作进行的中国研究,帮助我更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理论,思考是什么让乡村生活中的互助合作持续下去。
我非常感谢魏澜提议将《秩序、失序与战争》翻译成中文,感谢纳日碧力戈教授接受她的提议,合作翻译这本书;也感谢魏澜在自己的博士研究中运用这本书的一些思想,研究一个华南村庄的社会变迁。
《秩序、失序与战争》研究位于家户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本项研究以欧洲哲学家提出的看法为出发点:群居是人类本性吗?或者独居才是人类本性(除非被某种压倒性力量捆绑在一起)?
英国内战(1642-1651)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挑战了据称国王拥有所谓神圣统治权的欧洲封建专制国家。哲学家们开始自问,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怎样的。有些人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回答这个问题,把已知的人类状况与其相反状况对立起来,假设人类天生是独居的,并推测是何种可能的条件让人们聚到一起。在生物学理论中,达尔文把个体作为自然选择发生作用的单位,这一观点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是可以被观察到的经验,而且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在社会理论中,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并不那么富有成效,至今还不存在由独居个体构成人群的已知个案。即使是狩猎采集者也会建立社交网络,以便获得他们可以依赖的朋友和亲戚的帮忙。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论认为,若没有统治者,人们的生活将陷入“孤独、贫穷、肮脏、野蛮与短暂”之中,尽管右翼评论员将继续引用这个观点,但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证明,他们对冲突的解释是值得怀疑的。
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们是理性人,人的自然状况是群居。正如弗格森在1767年写道:“人以群聚,维系生存”。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类始终是理性的社会存在。事实上,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现存物种[例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比如纳粹集中营,人们也会试图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法国大革命
这本书的第二个灵感来自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引发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制度理性安排的类似辩论。西方右翼评论员声称,资本主义是建立稳定社会制度的唯一基础。一些人,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甚至认为,只有当社会开始告别自在习俗的传统形式,接触到市场交换理性的时候,理性思维才可能出现。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了法国地区具有数百年传统的生产合作社和村社土地集体管理制度,我对其稳定性的亲身体验,否定了只有自由市场和个人财产所有权才能带来社会稳定的那种说法。
从关于社会秩序的广义哲学命题出发,进入可检验的理论,我综合运用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尝试解释存在于家户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变迁性。我必须强调,在借鉴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时,我不为人类社会行为生物决定论辩护,而是将这两个方面并置起来:一方面是人类能动性的合理使用可以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达尔文主义进化过程中随机遗传变异的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已经有大量研究。
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论点是,种群的不同个体为了实现生存目标,会采用略有不同的办法;在种群的生存条件下,那些策略最成功的个体将生育更有生命力的后代。几代人之后,最成功的策略将在种群中取得优势。然而,没有任何一种适应是完美的,每种策略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当下的环境和条件;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另一种策略可能会更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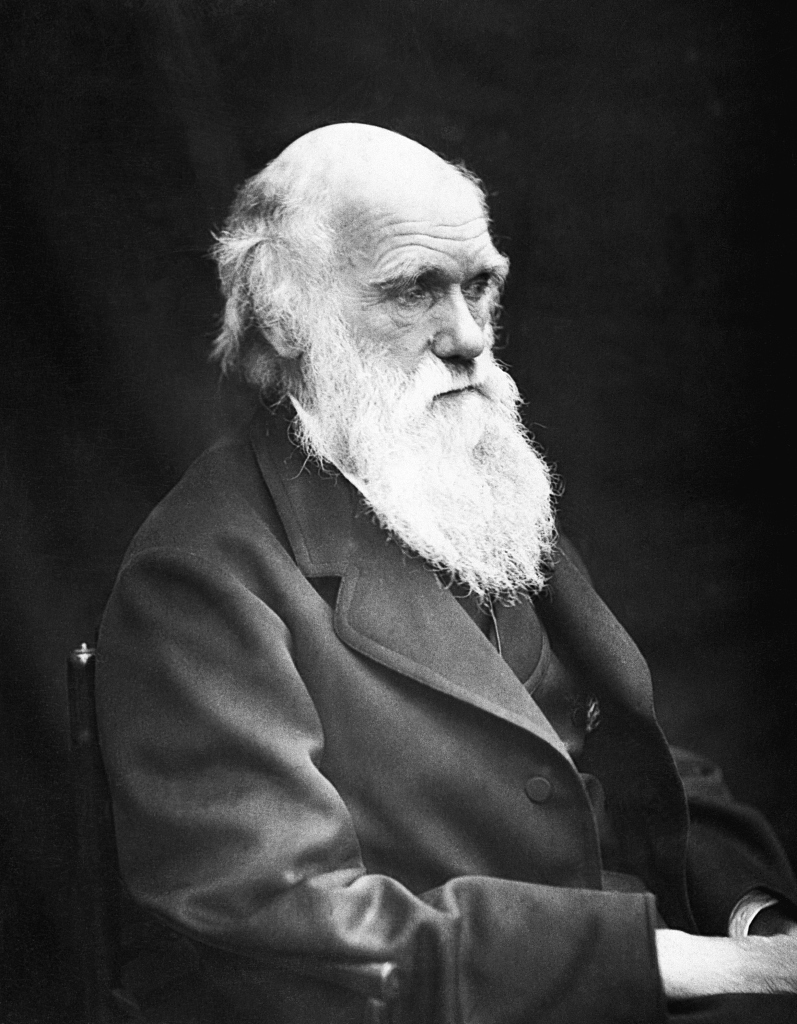
达尔文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H. M. S. Beagle)上航行时遇到的例证之一,对他的理论发展特别有影响。1835年,达尔文在厄瓜多尔海岸外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了几种生活在不同岛屿上的雀鸟。有的雀鸟的喙又宽又结实,可以打开种子;有的雀鸟的喙则又窄又精细,可以用来捕捉昆虫;还有许多雀鸟的喙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状。达尔文的结论是,尽管每个物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它们已经适应了岛屿栖息地上的主要食物来源。因为岛屿的生态环境不同,所以最常见的食物来源也不同。当所有的雀鸟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时,那些喙的形状最适合岛上可获食物的个体,生命力旺盛,比其他个体可以繁衍更多的后代。1976年当某个岛屿发生旱灾时,他的假设得到了证明。动物学家彼得(Peter)和罗斯玛丽·格兰特(Rosemary Grant)发现,拥有最坚硬的种子的植物存活得最好,而喙较大的食籽雀的个体数量增加,与此同时,以较小而精的种子为食的雀鸟因进化出喙较小,个体数量则减少了(en.wikipedia.org/Peter_and_Rosemary_Grant,访问日期:2021年1月30日)。

尽管达尔文很清楚许多动物物种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但他的理论认为,最密切相关的个体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将是最激烈的,这一理论阻碍了他去解释社会生活是如何进化的。这是达尔文最靠谱的一次解释:他在孩子们的帮助下,研究房后野地里的蜜蜂和花。田野里有两种活跃的蜂:小蜜蜂(honey bee)和大黄蜂(bumble bee)。孩子们帮助他找到蜂群,他们发现小蜜蜂会到一种三叶草中采蜜,而大黄蜂到另一种三叶草中采蜜。当达尔文仔细观察时,他发现每一种蜂都会选择那些最适合它们的口器采蜜的花。达尔文推断,对蜂最有吸引力的花会更频繁地被授粉,繁殖成功率最高;口器最有效的蜂收集的营养最多,繁殖也更有效。“因此,”他写道,“我能理解一朵花和一只蜜蜂是如何以最完美的方式,同时或相继慢慢地发生变异并互相适应”[《物种起源》(第6版)第75页]。这个过程现在被称为协同进化。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的协同进化案例都是建立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的。对红桃皇后假说(van Valen,1973)追根溯源,在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桃皇后对爱丽丝说:“在这里,你想要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必须跑。”它解释了捕食者与猎物的协同进化,有更多马克思主义色彩。红桃皇后假说模拟了捕食者和猎物的协同进化:在任何同代中,只有速度更快的猎豹可以捕捉到足够的瞪羚来喂养自己的幼崽;同时,也只有速度更快的瞪羚可以逃脱追捕,喂养自己的幼崽,这样就形成了越来越特化的螺旋性适应。
协同进化为社会进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起点,潜在地促成了达尔文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社会进化理论模型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双向传输。在生物学中,达尔文和范·瓦伦(van Valen)确定的物种个体组合之间的相互作用类型,被概括为“适应度景观”的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种群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相施加选择压力。“适应度景观”的概念最初是由生物学家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于1932年提出(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gress of Genetics,1:356-366),并于1982年由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应用于经济学。另一方面,博弈论最初由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于1953年在经济学领域提出,1982年由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转用于生物学。
社会理论
达尔文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对物种中的有机体个体之间的变异感兴趣,而马克思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集体过程感兴趣。尽管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有效性只能根据有机体的特定环境来判断,但马克思坚持19世纪标准的进化观,认为进化是一种进步的力量,从简单走向复杂。然而,马克思是第一个确定社会动力学的人,这种动力实际上导致了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国富论》(1776)成书时工业革命即将开始,但它研究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斯密认为,在曾经的市场上,人们可以专门生产最符合自己才艺的商品,社会关系是通过交换产生的。尽管斯密也承认金钱使人拥有购买他人劳动的权力(1976年再版的第47页),但他仍然认为,“在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中,获得商品的欲望带来惠及下层民众的普遍富裕”(第22页)。斯密有句名言:“我们不能期待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出于仁慈为我们提供晚餐,而只能期待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为我们提供晚餐”(第27页)。换句话说,他们用自己制作的东西换取他们需要的其他商品,而我们作为其他商品的生产者都能从中受益。
2005年,当我开始在山东研究传统艺术时,我非常惊喜地发现,一些特定的村庄专门从事特定工艺品的制作,比如木刻画、玩偶制作或葬礼模型等。专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声誉提高了,买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想要购买的工艺品。我还发现,因为男人一生都待在他们出生的村庄里,所以男人的艺术成为某些村庄的特色。妇女把她们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技能,如棉织或剪纸,带到她们丈夫的村庄,使妇女的艺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后来,当我进行背景阅读时,我从甘博(Sidney Gamble)1954年的研究《定县:华北乡村社区》(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中了解到,我所看到的模式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个较复杂系统的遗绪。甘博的表32(1954:97)列出了1928年一个县中,他和中国合作研究人员统计列出的所有家庭产业。各个村庄专门从事例如制作盒子、扫帚、水桶、鞭炮、香肠肠衣、鞋子、肥皂或甜品,当地市场平均每天接待2000至3000名游客。在此之前,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亚当·斯密对传统社会的研究是基于他自己的想象(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但甘博证明,生产者之间的交流可以大规模进行。
马克思在斯密之后一个世纪著书立说,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当·斯密75年前预言的普遍富裕并没有惠及最低阶层的人。相反,英国的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贫穷和困苦。城市贫民区一个房间里住着十个甚至更多的人,八岁的孩子在工厂里工作,一天的工作时间在十到十五个小时之间。马克思很清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交换,一种是斯密的例子中所描述的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生产者把他们生产的商品以货币交换给想要它们的人;另一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交换的商品的性质不感兴趣,资本家只想牟利,把商品的价格卖得比购入时的更高。机器可以比工匠更廉价、更大量地生产商品,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致使手工业者失业,迫使他们把劳动力卖给拥有工厂的资本家。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84:173)改述了马克思的解释,他写道,没有他人的帮助,人们很难实现自己的目标,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既制约互动,也促成互动。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稳定系统的模型(斯密:人们只生产够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和一个不稳定系统的模型(马克思:资本家被牟利的机会所驱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动态作了精彩的描述,他明白其他社会形态会有不同的互动态势,但他对其他类型的社会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勾勒出它们可能存在的互动态势。所以这就不奇怪,他未能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互动态势作出同样有见地的解释。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原始人类状态”的例子,一种几乎不需要解释的自然状态。因此,令人兴奋的是,发现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者的策略,实际上是对他们生活的特定环境的巧妙的社会适应。其中有些策略也存在于农民社会。
20世纪初,生产合作社在中国很流行。1934年6月,定县共有22个合作社(Gamble,1954:271)。1936年,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见他的《江村经济》,1983)选择了华南村庄进行实地考察,因为他的姐姐正在那个村庄帮助当地农民经营一家合作制缫丝厂。这样的合作社一直持续到1956年左右。我们采访过的一些乡村艺术家认为,振兴合作社是有益的,这样,社员们就可以联合起来批量购买原材料,直接与他们的作品的使用者谈判销售。对于集体所有或集体管理资源可以取得成功的具体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理解,这肯定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使用诸如“适应度景观”之类的概念,以及在博弈论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可以让我们对社会的稳定与不稳定有更细致的理解,我将在本书中使用这些概念。
本文为《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中文版前言,该书作者罗伯特·莱顿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杜伦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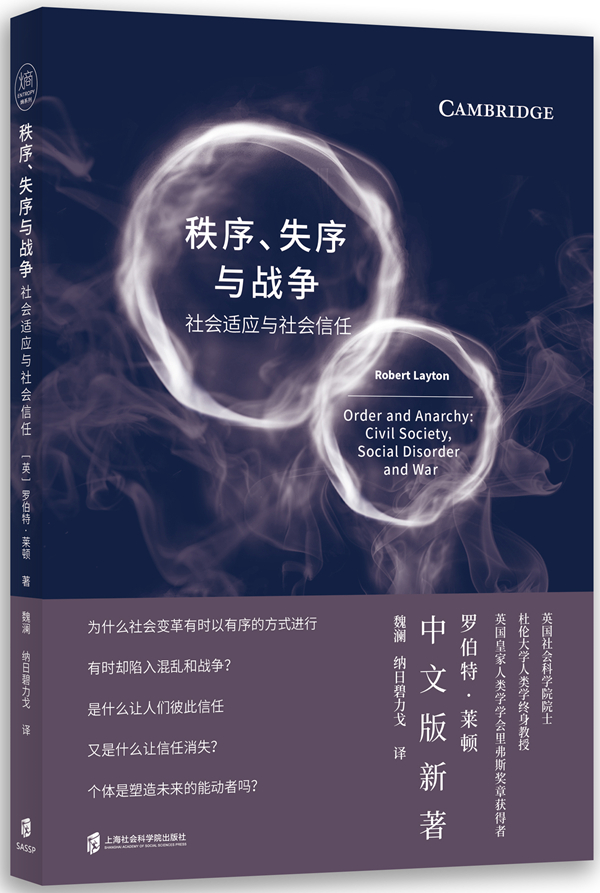
《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英】罗伯特·莱顿/著 魏澜、纳日碧力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2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