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从书稿到印行的幕后故事
无论采用怎样的标准,《在中国发现历史》甫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好评如潮,两度被译成中文,兼有日文、韩文版本,北美、欧洲、东亚中国历史系学生人手一本。美国图书馆协会书评期刊《选择》(Choice)将其评为1984-1985年度“杰出学术书籍”。它的教学价值广受赞誉,康奈尔大学高家龙(Sherman Cochran)评价该书为“优美的教材”。1986年秋天,高家龙写信给我,说他用《在中国发现历史》做研究生史学研究课的最后大作业,“要求学生根据本学期的阅读材料撰写这本书的书评,然后在最后一节课前互读书评,课上讨论。我教讨论课以来,那次是最好的收尾——多亏了你的书”。

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最能彰显《在中国发现历史》在北美中国研究界特殊地位的是,2014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75年会组织了一场特别圆桌论坛,纪念此书出版三十周年。据我所知,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历史上,这样的活动绝无仅有。近些年来,这本书在中国史学家中的影响力也非比寻常。2014年圆桌讨论嘉宾李怀印说,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1986年到1999年《在中国发现历史》被116篇中文期刊论文引用,平均每年8篇;2000年至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774篇,每年大约55篇。引用数量井喷的部分原因是中国互联网数字化兴起,但李怀印同时指出,20、21世纪之交,革命范式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愈加对地方、区域社会文化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一转向与《在中国发现历史》终章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有深切共鸣,引用数量暴增绝不仅仅是巧合。
卢汉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精彩点评也提及此书对中国历史学家的影响。但若不是三十多年前我与林同奇的神奇相遇,这一影响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至少不会那么快出现。1985年初,林同奇刚从中国来到哈佛,踏进费正清中心我的办公室时,我并不认识他。他说自己读过《在中国发现历史》,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看到这本书。他在中国人脉深厚,已与著名出版社、有意出版中译本的中华书局有书信往来。林同奇英语精湛,来美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数十载,他说愿意亲自翻译。一开始我对这个提议并没有严肃对待,因为80年代中期鲜有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术著作被译成中文。但林同奇志在必得,于是我们拍马上阵。
当时计算机远没有现在普及。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的工作流程相当原始。林同奇用老式中文原稿纸手写译稿,每译好一章就交给我,我对照原文检查。我列一份清单,标明修改意见、问题、建议措辞等,然后我们见面长谈几个小时,讨论清单上每一项问题,然后他再提供那一章的修改稿。对我来说,这真是段长见识的经历!这本书出版后,无数中国同事告诉我,有林同奇这位翻译,我是三生有幸。我想说的是,这份神兵天降的经历,例证了后文“无法预知结果”(outcome blindness)的说法,对于这本原意是写给西方人,尤其是美国读者的书来说,它的历史进程被大大地改变了。1989年7月,中译本出版。
待到此时,中美历史关系研究学者之间互通有无势头良好,我的好朋友、复旦大学的汪熙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版尚未发行就已备受瞩目。1986年5月,汪熙写信给我,说已有书评见刊,戏称自己觉得中国史学界是通过我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书“发现”了我。林同奇当时正在翻译此书,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英文书评,特地取名“在美国发现历史学”。我给林同奇看了汪熙信中不谋而合的部分,他觉得十分好笑。

柯文与林同奇,摄于2008年
付梓前传
如果世界是完美的话,刚才描述的这本书,出版社一定乐意发行。但当时此书大获全胜的结果远无人预见,世界也远非完美。1981年初,书稿已经完成。我的前两本书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颇受好评,所以我就把这部书稿又给了哈佛。但这个决定的结果十分惨痛,留下的创伤不小。1981年3月,我见了哈佛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艾达·唐纳德(Aida Donald)。哈佛把书稿寄给两位外审,6月初收到外审报告后,我写信给唐纳德回复外审意见,内容大致如下:出版社收到书稿的两份报告:一份激烈负面,认为我的研究并无裨益;另一份却大加赞赏,不少建设性建议可供提升书稿质量。仅就两份报告的行文来说,假如两份报告说的是同一本书、同一位作者,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蘧蘧然若庄周。庄周是中国哲学家,梦为蝴蝶,醒来不知自己是周之梦为蝴蝶,还是蝴蝶之梦为周。
客观冷静看待那份负面报告实属不易。那份报告中满是情绪用词,完全不符合学术评价严格的实证标准,让人心生疑窦。考虑到其观点极为负面,所以用词奇异、主观片面或许也属正常。报告作者对自己的论辩力度自视甚低,抑或过分高看了我,不信的话无须再进一步探究,只需看报告的意见信,里面说虽然“意见非常负面”,坚决反对出版,但“我相信柯文教授的书会出版,可能经哈佛大学出版社”……
我认为关键是负面报告的作者一直没有理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若是另一位出版社外审以及受我邀请看过书稿的六七位学者同事,都不懂这本书的内容的话,我自然提心吊胆。此书不是全面研究中国历史学这门学科,而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厘清、分析、批判美国历史学研究普遍存在的假设”……
说我的分析“薄弱”“有气无力”的攻击,我不知如何应答,因为给出意见的这位作者又一次没从文中找出任何支撑自己言论的实质证据。他认为第二章是“书中最薄弱的”,论证“模糊、令人面赤”,但另一位审稿人却评价其为“历史学研究的优秀的入门介绍”;他甚至不吝赞美,说我对约瑟夫·列文森的分析“力透纸背”。对列文森的分析,约占第二章一半内容。
负面报告的作者认为具体指出书中的“偏漏错误”纯属浪费他的时间,因为如果我有能力改正的话,绝不会写出这种书。对此我唯一能说的就是,现在我能理解50年代被抓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人的心情了。
写到这里,我的幽默感所剩无几。这位作者扣的另一顶帽子倒值得简评。他说这本书充满了“哈佛中心、小团体中心、美国中心”的狭隘偏见。我不知道他说的“哈佛中心”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我博士是在哈佛念的,是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有两本书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我认罪。如果是说书中一半以上的学者,职业生涯的一些阶段与哈佛紧密相关,我再次认罪。但我要马上反驳。其一,截至1981年我提交书稿时,哈佛……尤其是在费正清(的指导下),战后培养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数目远超美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评价这些年美国的中国历史学,不可能不深刻反映哈佛的影响。其二,书中分析的哈佛学者在意识形态、治学路径上千差万别。其三,书中深刻、尖锐批评了不少哈佛人,如费正清、芮玛丽,尤其是列文森。这本书可能简言之是以哈佛为中心的,但绝对不是要为并不存在的“哈佛学派”向人们道歉。
至于“小团体中心”,应该是指作者说的“一小撮儿狐朋狗友”,作者说我只讨论了这些人,尤其是只赞赏了这些人。恐怕在这里,这位作者是在扮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我一向敬重费正清、芮玛丽、列文森,一向视费正清先生为朋友、同事、导师。但如前所述,这三位在我的研究书稿中都有批判。另外,我并无相与的伯克利毕业生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以及耶鲁出身、我几乎没打过交道的高家龙,都对此书深表赞赏。
狭隘偏见中的美国中心,我猜是指偏重了美国的历史学(为什么这样侧重前面已经讲过)……
现在简要说说第二份报告,感觉像宇航员环绕太空许多天后,终于回到了地球。不是因为这份报告里有一些溢美之词——当然看到这样的评价令人心满意足,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每位学者都希望看到的严肃、负责、明辨、具有建设性的审读。我这里不就每点建议都做评析,只想说每个点都深刻异常,我会在终稿中多加完善,大量采纳……
在这封信中我花了大量笔墨反驳第一份报告的意见,没有细致回应第二份的建议。这深属遗憾,但恐怕也不可避免。我最想做的是向你们说明这次的负面意见是个意外。这份意见都算不上意见,完全误解了整本书,其中的攻击全盘负面,没有任何实证支撑,更无法分析其优点。更可气的是,(这份意见的)作者写完这些还自鸣得意,说这本书出版之时,他会把这份意见“几乎一字不改”,发做书评。我只能说,我的理由有千万条,但也希望他得偿所愿,越快越好!
我之后获悉,哈佛大学出版社治理委员会收到我对外审意见的回复后左右为难,决定让其中一位委员,也是一位社会科学学者读完书稿,在下次开会时给出意见。听小道消息说这位委员的意见趋近于负面,我听从艾达·唐纳德的建议撤回了书稿。
下一站是耶鲁。我之前认识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查尔斯·格伦奇(Charles Grench)。查尔斯知道我当时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商讨进展不顺,鼓励我如果哈佛不成,不如转投耶鲁。我没有正式投稿,而是问他能不能先看一下书稿,听听他的意见。电话初步交谈了之后,我在1981年7月10日写信给他,说已经另外寄了两份书稿,信中我试着说明此书的特别之处:
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专著,而是战后至今美国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史,因此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位历史学家看待这个领域过去和未来的观点,而且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我确实说明了自己的学术倾向,也努力客观看待与我路子不同的研究范式。这样的书该领域前所未有。我认为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西方之外历史的学者,会发现这份付出有益、重要。
信中我提到了看过书稿人士的正面反应,并提及尽管没有人认为结构上需要大改,但也给出了一些改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被采纳。“至于本书的潜在读者,”我在信中或许太过乐观地说,“我想应该是中国研究领域刚入门的人——本科主修生和低年级研究生。”
查尔斯浏览了一遍书稿,说很喜欢。“关键是最终成品能不能达到出版的水平”,他咨询几位同事后写信给我。他的同事说我探讨的这些议题,面向主要读者的最好方式是写成期刊论文。他补充的一句话尤其发人深思:“历史学的问题很难回答,主要人物还健在,还有一些伤疤隐隐作痛。你扮演了法官的角色,但我们担心,表层下涌动的暗流其实还有很多,现在解决可能价值有限,会触及私人关系。”我回信给查尔斯说没能由耶鲁出版很是遗憾,并感谢他非比寻常的回复速度和坦率的态度。
此时是1981年夏天,我面前的拦路虎愈加分明。一是哈佛暗示、耶鲁明示的,这本书关于历史学,许多出版社一向不愿触碰这个话题。二是尤其鉴于这本书中分析的历史学家,除了列文森外都健在,仍活跃在学界。学术期刊书评里可以对当世学者进行批判,可即便如此,一般也建议没拿到终身教职的年轻同事谨慎行事(当然我已经获得终身教职),可写书不一样。另一个困难是,至少对于哈佛大学出版社来说,我在第一章大费笔墨,指出以费正清为首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的弱点。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否说明了表面下暗藏的玄机呢?此外,费先生一向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关系甚好、互相成就,若真的发行我这本书的话,出版社很可能会难堪。
我必须马上指出,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费先生的所做所想。多年前,费先生读过收录在詹姆斯·克劳利(James Crowley)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中的我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的初步批判,还发给我手写的便条(没有日期,用费式简写写的):“你那篇收录在克劳利论文集中的文章非常好,见解高超,中国重心向内,外国影响接触远属边缘偶发因素,外国人不可想。李约瑟收集资料来说明‘西学中源’。世界史的思考方法日新月异。”

柯文在上海演讲,右为复旦大学经济史家汪熙,摄于2003年11月
师与生:无法被超越的费正清
此处最适合按下出书之事不表,转而说说费正清先生最大的特点:他的为师之道。前文已经提及,无论何时我把自己的文章寄给费先生,永远能很快收到他的详细点评,且一般是令人如沐春风的鼓励。几周、几个月甚至数年后,我往往会收到他给别人信函的复印件,他在信中仍不吝溢美之词,盛赞我的文章,提醒别人去读。这些信是鼓舞人心、彰显巧思的写作模板,反映了真心以学生成就为荣、慷慨大度的导师精神。所以对我来说,导师费先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包容所有异于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他也是个固执的人,不会轻易改弦易辙,觉得愚蠢无知的学术想法,他能在纸上将其批得体无完肤。费先生明白,就算在学术殿堂,也一定会有前浪后浪。“不站在前人肩膀上,踩在前人脸上,人类怎能进步?”他有次用费式简明扼要的风格写道。但如果学生不理解的话,他从来不会停止倾听,放弃这位学生,不与他讲话,或者不再去函。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费先生也与严厉批评他长达数年的人保持频繁交流。
另外一个说明费先生慷慨大度的例子是,我的书在耶鲁大学出版社遭到冷遇之后,经过很久的内心挣扎,我决定在找下一家出版社时,不如完全避开大学出版社。马上映入脑海的是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自由出版社的专长是出版严肃非虚构作品,而且当时正在策划出版由西北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薛立敦(James Sheridan)主编的“转型中的现代中国”丛书。我致信薛立敦,大概介绍了我书稿的内容,另外给他寄去序言、绪论和目录。11月初,他打电话说很欣赏已经收到的部分,希望阅读全文。我随即寄给他全稿。12月初,薛立敦打电话,说这本书“十分精彩”,论证清晰有力,纸质版一旦出版,一定大卖,并适合作为课程书目。他还说不觉得我对书中涉及的学者有狭隘偏见。他已与自由出版社商讨,提供了外审推荐名单,出版社会把书稿交给其中的一位。
此时是1981年底,很久之前我已把书稿给费先生看过,跟他讲了寻求出版过程中的艰难险阻。费先生在圣诞节前主动给薛立敦写信,把信的复印件也寄给了我。他写道:我现在才看完柯文的“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历史学”书稿,我认为这本书极为精彩——分析脉络清晰,风格审慎中立。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应把书稿中提及的书目悉数研读,学生也会对大部分内容感兴趣。关键是柯文把所有书纳入一个框架,除去自陈观点之时,其余不含任何偏见,这使读者能迅速了解历史分析的三大学说;而且翔实程度无人能比。这本书说的是史学实质,是现代中国史领域的历史,是其中每位成员都需要的自我认同。
换言之,这部书稿展现了几大学说之间的互相补充,提升了我们历史学家的成熟度。对于老一辈,这是个看待这些学说问题更清晰、更坚定的机会。而对于年轻一辈,这本书弥补了近世史研究的盲点。近世史太近,难以以历史手法记录,又离年轻人个人经历太远,难以回忆。这本书使新老几代都能受益良多,深受启发,从而找到自己的定位。信末,费先生说希望自由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为丛书中的一本出版;还说到当时他正和费维恺合编《剑桥中国史》第13卷,在该书导论中,他们“希望引用这本书”。
《剑桥中国史》第13卷即《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1986年出版。费先生提到的导论是《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由费先生、费维恺、独立学者冉玫铄合写。费先生一诺千金,1984年3月,《在中国发现历史》终于出版后,他特意写信给我,说因为最终有太多人参与写作上述导论,他们很难写就所有人都同意的文本。“很明显我们需要求助一位‘史学大师’,”他在信中说,“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帮忙。请帮我们看一下。我们感激不尽。”仔细审读了这篇导论后,我写信给费先生说,这篇文章“有所有类似超级导论的共性……超出了导论的范畴,加入的新材料、新观点太多,侵占了该卷的后续内容。这篇导论写得确实非常好,可问题是怎样连贯起来。”他对我这一封长长的建议信表示真挚感谢。
费先生还有两次求助于我。1981年12月费先生致信薛立敦几天后,邀请我去他家共进午餐。他和赖肖尔这两位著名两卷本教科书《东亚文明史》(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58、1960)的作者,感到该书大体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需要更新重写。他想知道我愿不愿意参与他负责的明朝以来这部分章节的写作。初步计划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重写原书日本的部分,当时在耶鲁执教的余英时(是我1962年到1963年在密大的同事)重写远古到明朝部分。我对此有所保留,自觉不擅长写教科书,而且70年代我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同石约翰(John Schrecker)合编的19世纪改革工作坊丛书,因此急切想回归基础科研。同时,对重写他人著作的想法我也十分抗拒。在我表达自己的矛盾心情之后,费先生说不用马上做决定,可以多花时间考虑一下。深深纠结近三个月后,我最终决定不参与,并在1982年3月20日写信给费先生告知他。一周后收到他的便条:“我能理解。我们会想念你,但你做得对。”我不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重写《东亚文明史》教科书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费先生最后自己写了一本。
说到第二次,那是1991年5月20日清晨,费先生84岁寿辰来临之际,他往我家中打电话,说他正在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医院(Mount Auburn Hospital)治疗,心悸越来越严重,自己“一向持重”,如果病情恶化,希望有人接管他的《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的成书、出版工作。我已经受他邀请审阅过两次书稿——上次是这次打电话前几个月以信件回复的——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问我愿不愿意接管这件事,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提到自己也年近60(当时是马上57岁),因此也有些焦虑,尽管现在记不起是为什么而焦虑了。费先生叹气,感慨地反驳多愿自己也才60岁。这声长叹起了作用,过去我几次回绝,这次我带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对他说“好”。

费正清
这次的惶惶不安不是由于背后需要负担的工作。虽然我一向秉承他在六十大寿时对承恩蒙泽的学生立下的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但这次有更加直接表示感激的机会,我很高兴。然而我不安的是,自己之前公开表示对他的一些立场持保留意见,结果却要在书中披上他的外衣,采取与自己大相径庭的立场。结果我的烦恼是杞人忧天。费先生又坚持数月,即使住院在床,依然继续修改、草拟书稿的尾声部分,充实文中欠缺的内容,还指挥在我看来是一支小型正规军的学者团队,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此书撰写。1991年9月12日,他和妻子费慰梅去哈佛大学出版社递交《中国新史》完整打印本,几小时后心脏病发作,两天后离世。他逝世第二天,慰梅打电话给我,说费先生的死于他是幸事(指他在心力衰竭前努力写完书稿,这对他来说压力过大),但“于我们是坏事”,感叹他时间卡得正好。
从5月电话到9月他逝世之间的几个月,费先生和我一直就此书事宜频繁联系。有时他会打电话谈谈自己最近读的书,想听听我的看法(他读书比我快得多,一般我都无从发言),也分享自己的想法。有时我会告诉他自己在读什么,推荐他也看看。下次聊天时,他不仅已经精读了这本书,如果作者观点有说服力,他还会努力把这本书塞进自己的书稿。
费先生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前几天,我午饭后去办公室拜访他,想告诉他自己关于书稿最新一版问题突出的一章的想法。(结果他已经又拟了一版,问题已被有效解决了,无须我的点评。)他着急的时候,一定要快点儿看才能跟上。他办公室的门半掩着,我敲门时一开始无人应答,然后听到他的声音:“进来。”原来是我打搅了费先生无人不知的饭后午睡。他马上坐起身开始讨论书稿,好像刚才一直躺着在思考这本书,抑或是在梦中思考?他说几周后书稿就要交付清样了,他担心不能纳入“17本新书”的成果,而这17本书在递交清样和书出版之间一定会问世的。我的思绪回到这么多年,听闻费先生耍各种把戏,从不情不愿的作者手中夺来他们书稿的故事。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就开始按费先生的风格教育费先生,苦口婆心说新书永远都会有,而学者的著作里纳入尚未出版的书不现实,所以要知道何时收手停止修改,接受业已完成的事实,等等。他笑了,笑容一如往常讳莫如深。他知道我说得对,但他也知道,归根结底,他说得也对,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本书,书问世时,他很可能就不在了。他真的很想确保一切无虞,才能放心离去。
在费先生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除了与他频繁交流之外,我还应哈佛大学出版社时任助理社长、总编辑艾达·唐纳德邀请,担任书稿外审。费先生去世后,我积极参与了此书出版需要的编辑工作,就著作里的插图材料咨询了慰梅,并仔细审阅了清样,尽力将成书错误降到最低。我甚至重写了关于晚清农业经济人多地少问题影响的一段。最后能参与成书我很高兴,这是对这位自己亏欠良多的人明确表达我深切的感激之情。
仍须努力
结果我的书在自由出版社也是功败垂成。大概是费先生给薛立敦写信的时候(1981年12月),薛立敦给我写了一封思虑缜密的批评长信,指出一些他认为书中需要加强的薄弱之处。他的一些观点我认同,回信说一定修改。我不知道外审的意见是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外审。1982年2月我接到自由出版社历史编辑乔伊斯·塞尔泽(Joyce Seltzer)的电话,被告知出版社将不予考虑此书,理由是这本书不符合“大规模作为教材”使用的设想。她说我的文笔很好,然而——多么似曾相识的说法!——历史学著作一般只有其他历史学家感兴趣,由大学出版社接手更好。她在随后的简短信件中重申,对于自由出版社来说,这本书“读者应该不多,商业价值低”。几天后,薛立敦打来电话,表示自己对出版社的决定愤懑不已,并依然坚持认为这是本好书,会极力出言支持出版。
书稿自首次交给出版社已经一整年,结果离被接受还长路漫漫。我依然坚信这本书的价值,认为它对北美中国历史学界是有益的贡献。但让我费解的是,虽然有许多支持这本书的声音,两家大学出版社和一家以出版学术作品见长的商业出版社却都泼了冷水。这是我出版前两本书时完全没有经历的,那两本都是提交哈佛大学出版社几个月后就立项了。若说就此绝望跳下布鲁克林大桥倒还不至于,但我确实很受伤。
另外还有一家商业出版社我觉得可能值得联系,那就是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 Books)。这家出版社一直对亚洲相关的图书青睐有加,尤其是那些批判思考美国对亚洲看法的类型。我的书虽然只关注亚洲的一个区域,但显然也属于批判思考的类型。我跟万神殿亚洲书籍主编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打过交道,于是1982年8月给他写了封信,附上书稿序言、绪论和目录。之后我收到他的简短回复,说只凭绪论无法决定,需要看完全稿。当时他明确说,从绪论来看,“感觉这本书更适合大学出版社,不太适合万神殿这种商业出版社”。此时看来,投万神殿明显不太可能成功。我回信感谢他愿意浏览全稿,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他们社出版,但我感觉如他所言,找大学出版社前景更加光明一些,我想再试试这条路。
这时是1982年9月末,没有更努力去敲开万神殿大门的原因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不相干的事情,最终解决了问题。关键人物是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她写有多本研究美国东亚关系的重要著作,包括《美国和远东危机,1933-1938年》(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3-1938,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并凭此书获得1965年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研究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博格博士20世纪40年代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美国分会会员,在中国生活过两年。几年后,太平洋国际学会被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组织的人士攻击,称要为“把中国输给了”共产党负责,她暂停学术生涯几年,帮助维护备受攻击的欧文·拉铁摩尔等同事。
我结识博格是在1982年夏天,当时她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我的朋友、中国政治学者沙乐思(Lawrence Sullivan)刚搬到纽约附近,他熟悉我这本书,知道我还在找出版社,就向博格提及了书稿。博格此前正在整理思路,筹备一本讲美国的中国史、东亚史研究的短篇论文集,于是7月给我打了电话。接下来的长谈我觉得有一个多小时,可以想象,我很紧张,又有防备,但感到这其实是一次面试。听到她做记录的铅笔沙沙作响,想到自己在接受面试,我还是感到很荣幸的。博格之后很快要北上波士顿开会,我们8月6日共进了时长不短的午餐,当天晚些时候我把书稿交给她,加了一张便条,说可以给她在哥大的同事、中国政治研究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看看,他应该感兴趣。
8月末我收到多萝西(午餐后我们就互称名字了)的信,笔道瘦削,如同打印字体,她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她在信中提及这部书稿令她“非常不安”,因为她想写的这里很多都写了,若是从出版的书第一次看到,“一定是平地惊雷”。她深深感谢了我处理这种情况“非常友善、大度的方式”,说这对她“意味深重”。我当然马上回信,让她放心,虽然我和她或许大致观点相近,可我一定写不出她那种作品——她的目标读者是美国研究学者,我的不是;她关注的是美国东亚关系史,我在书稿中并没有涉及。
回到纽约后,多萝西把书稿给了黎安友,他9月末给我寄来评点的长信。黎安友几年前受托写过20世纪中国政治研究综述,所以对这方面的挑战心知肚明。“所有这些问题,”他有些自嘲地说,“你做出了超凡回答而且行文如此优雅,也只有我这样真正努力过但失败了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成就的巨大意义。”他对书稿有两个主要的担心,一是现在熟知的读者群体问题。有多少人会买、会读?他说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任何考虑出版这本书的公司一定会就此辗转反侧,请求外审决断”。他然后就如何既不改变全书主旨,又能提升吸引力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第二个担心的是公允问题。我为支撑自己的论点,是不是对费正清、列文森的分析过于浮皮潦草?这里他的观点尤为深刻,也十分有说服力,促使我重写了序言部分的内容。这部分现在是这样的:
公允问题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撰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做出判断时,我力求不偏不倚,在指出一位学者的著作、一个大的学术取向的不足时,我尽量说清批评的前提依据。但用别人的著作印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难免有一定程度的歪曲。人们的观点随时间起伏变化,势必有所流失;学者的著作总是纷繁复杂,其中融洽对位的主题、主题的限定条件,甚至亦有可取之处的些许矛盾,都会从视野之中消失。因此,我把费正清、列文森当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历史学主要取向的代表人物时,很容易忽视费先生学术生涯悠悠五十余载,治学中国有多个角度,但他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忽略过异于自己学说的学术论文,反而是张开双臂。列文森虽然1969年不幸去世,无法回应当时渐次出现的新学说,但他目光如炬、思路精细,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任何学说的框架之中。

柯文在纽约与四位子女参加庆祝他姐姐芭芭拉九十大寿的聚会,摄于2017年9月
意想不到
说回黎安友的信之前,我想在此补充几句关于约瑟夫·列文森的话。1969年4月6日,列文森在加利福尼亚州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因划艇事故溺亡。我大约在他逝世六七年前认识他,十分敬服他为学、为人的风度。他去世时,我深受打击。在我的脑海中,他的死也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紧密相连。1969年4月初,我收到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于当年3月29日发出的信,邀请我为他编辑的东亚论文集写一篇文章。文集最终定名为《世界的一半:中日历史文化》(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格拉斯哥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推荐了我。我深感荣耀,写信给汤因比博士说撰写此章是我的荣幸,章题为《欧游东方:西方对中国、日本的第一次冲击》(Europe Goes East: The First Impact of the West on China and Japan)。我在4月8日的信中陈述了一些自己倾向于如何着手的细节,汤因比5月14日回复说收到回信很高兴,我怎样诠释都可以。他认为我提到的观点对那一章来说,可以“大大增加其价值、意义”。他随信附上了文集的作者名单,还提到列文森英年早逝的消息,问我除了负责那章之外,能不能考虑写本来由列文森撰写的“西方的第二次冲击”那章。我5月21日回信说当时忙于完成《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亦有其他事由,恕难从命。我冒昧推荐了几位我相信能写好列文森那章的学者。6月2日,汤因比回信说完全理解,并感谢我推荐人选。
哥大喜讯
1982年9月底,黎安友在信中还指出了一些小的缺点,建议我多加考虑,之后表示乐意与多萝西·博格一起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荐此书,希望他们能“审慎、惜才”。他也表示出版社做决定前应该会请一位外审。我回信感谢安友对书稿的评价,也感谢他帮忙与出版社沟通。同时,多萝西已经把书稿寄给哥大出版社执行编辑伯纳德·格罗纳特(Bernard Gronert),10月6日格罗纳特打电话,说刚花了一个小时浏览书稿,很欣赏我的文笔和直接介绍此书、融入个人立场的方式。他提到哥大出版社即将出一本致敬多萝西·博格的历史学文集,由孔华润(Warren Cohen)主编,他认为跟我这本书很适合作为一套。他问我既然前两本书都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何这本书遭到冷遇。我和盘托出,猜测说是因外审报告观点极为相左,哈佛又与费先生有密切的联系,管理层可能因此决定放弃。格罗纳特说会马上把书稿交给外审。
此时多萝西·博格已然放下之前任何个人利益,愿意为我的书稿出版贡献所有力量。除了书稿交到出版社时写的赞扬信之外,11月初她给我写便条,说一旦知道消息马上告诉她。“我感觉一定一切顺利,”她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充满鼓励,“也希望一切尽快。”
感恩节那个周末,多萝西非常有心,在家给我打了个电话,兴奋地给我读她已经收到但我还未收到的外审报告的片段。一两天后,我也收到了报告全文和格罗纳特的手写便条,他说这本书“如若有光”。“有了外审的报告以及安友、多萝西的支持信,”他说,“12月15日我把这个项目在院系出版会上提出,一定会一呼百应。”
外审报告开篇就解决了各家出版社最关心的问题:这本书谁会看?报告作者(后来我发现是易社强)说:
有人会问,这本书“对中国研究学者来说是必读书吗?”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字:是!这本书会是学术研讨会、历史学课程、高水平中国“近世史”研究综述的起点,柯文之后,谁人敢言“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历史”课第一节讲座的题目会是“‘现代中国’概念问题所在”,只需总结柯文此书观点即可。研究生资格口试这本书一定是必读书目,就算整场资格考不是“柯文式”的,教授们也一定会问学生许多“柯文式”的问题。
报告随后点出书稿需要修改的地方,尤其是题目,不过前几年已经改过十几次:
柯文行文流畅明晰,对分析有绝佳的帮助,但题目却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已经驳斥了“现代中国”这个术语不能深刻描述背后的现实,他就不能把书名定作“美国历史学家与现代中国”了。《美国近世中国史历史著作》这个题目(当时发给外审的题目)像躺在碗里的麦片,被动吸收牛奶,一点儿都不出彩、响亮、悦耳。不过,目前的书名确实说明了此书的内容,应该作为副标题保留。正标题应根据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来拟。
我采纳了外审意见的前一部分,没采纳后一部分。修改后成书的正标题,当时就觉得恰到好处,三十年后的今天依觉如此——《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是对黑格尔观点——“我们面前最古老的国度没有过去……这个国度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因此中国没有历史”——最机智的反驳。
书稿很快就被出版社接受。多萝西下一个跟这本书有关的便条写于1984年4月,书刚出版之后。她祝一切顺利:“祝愿这本书一帆风顺,书评佳,销量佳,心想事成。”然后感谢我在序言中对她的致谢。“我总觉得,自己最喜欢读的,是人们在致谢中表达的那最真挚、纯粹的感情。”她写道。回望当时在书中我感谢多萝西的用词,真的不过是寻常语句。但有时,深刻的感情藏在普通语句之下。我从多萝西的回应中明白,她知道我有多感激,同样重要的是,她知道我懂得她一开始支持此书时的内心况味。
回首与多萝西·博格非比寻常的友谊,我总会想起她为这本书所做的一切。别人面对类似的情况,会遮遮掩掩、有所保留,她找到我时,我也是如此。多萝西下意识的反应是放下个人情感,拥抱自己认同的观点,沒有停留在小我的自矜、自尊上。这不是说她完全无私,她风趣幽默,不屑于自私无私。但她是少有的心胸开阔的人,过人之处不止这一点,能做她的朋友,我三生有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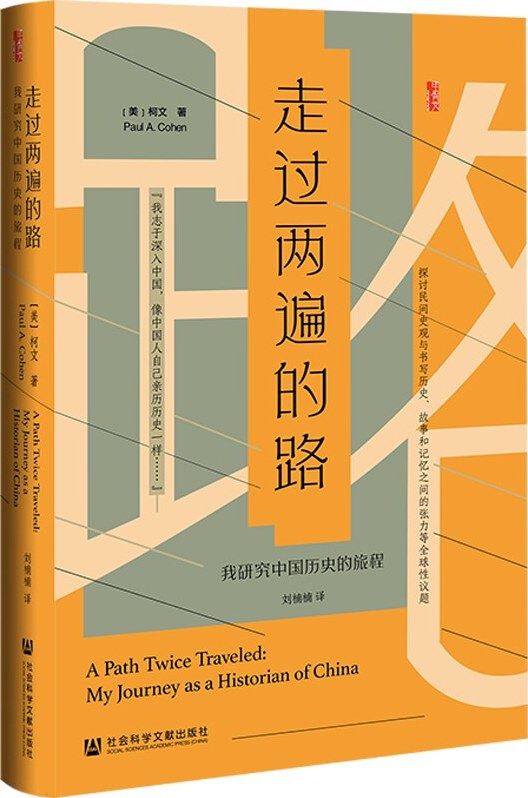
(本文摘自柯文(Paul A. Cohen)著《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的旅程》,刘楠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