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黑格尔和谢林论中国在“普遍历史”中的地位

提要
黑格尔和谢林的历史哲学体系继承了康德的“普遍历史”思想。在这两位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构想里,中国都占据着一个确定的地位。然而对于这个地位的深入分析表明,黑格尔是把中国看作普遍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而谢林则是强调中国游离于普遍历史进程之外的独特性。相关分析既让我们认识到了黑格尔和谢林的历史哲学的分野,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中国精神的特性,以及它在历史中的真正地位。
如今,通过日益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都登上了同一条船,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这个事实,各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不绝于耳。但令人遗憾的是,不少学者想当然地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这必然会激起我们的深思和反对。因为,严格说来,“全球化”只是一个空泛的形式,其相应的内容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人们从不同视角的出发为“全球化”给出不同的定义,但这个概念本身仍然仅仅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理念。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全球化的统一性原则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界定。也就是说,如果不可避免的全球化首要意味着全部国家和民族的统一,那么人们必须追问,这个统一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以及,它依靠着怎样的指引,将在未来走向何方?有些人可以完全从经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但哲学家对这种做法不可能感到满意。换言之,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历史哲学,它把“全球化”的本质还原为一种“普遍历史”,将当前现实看作是普遍历史的一个环节,并从根本上出发对这一现象给出澄清和解释。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关于历史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诸位大师无疑给出了许多光辉的范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其《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1784)中指出,整个人类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亦即建立起一个无论内外都达到完满的国家体制(Staatsverfassung)。(AA VIII, 27)[1]康德在这里或其他一些地方经常提到的“自然”,其实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或理性化的自然,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理性本身。在康德的历史哲学里,理性保障并引导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此而言,一切在历史之内发生的东西,至少就历史的主流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后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827)的序言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TW 7, 24)[2]这也是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发挥了康德的思想。也就是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合乎理性”,这成了衡量人类历史发展的尺度标准。
与此同时,康德也意识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在最后阶段才能都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普通的人总是离不开一个师长或指引者,那么“人”这个物种同样也需要一个遴选出来的领导民族。(AA VIII, 23)然而,哪个民族有能力去扮演这样一个卓越的角色呢?在这里,康德不无谨慎但又充满自豪地宣称:
“……我们确实可以自夸道,相对于邻近的各个民族而言,我们德意志民族有权在这个世界舞台上争取一个杰出的地位。”(AA VIII, 23)而在另一个地方,康德又说道:“……我们这个国家未来将很有可能为所有别的国家立法。”(AA VIII, 29)
这些话表明,在康德看来,假若德意志民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这至少在原则是可能的,于情理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可见,康德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但他仍然没有摆脱那种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所以他认为,在古代,只有希腊历史才是可信的历史,而其他民族的历史只能从它们与希腊历史相遇的那个时间开始算起。康德同意休谟的那个说法,即“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的第一页是全部真实历史的唯一开端。”(AA VIII, 29)这句话也表明,中国对康德而言始终是一个“未知的领域”(terra incognita)。至于康德在课堂上关于中国的那些带有猎奇意味的少许讲述,更像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3]
但我们知道,近代欧洲并不是向来就如此忽视中国的。实际上,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中央帝国(中国)及其文化的赞叹在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是颇有影响的,而且沃尔夫甚至因为过于夸奖中国文化而触怒了基督教会和政府,因此被剥夺了教授职位。恰恰是在康德那个时代,中国的正面光辉形象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对于中国的推崇让位给浪漫派和宗教蒙昧主义对于中国的贬斥:人们或者是像康德那样忽视中国,或者是像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那样近乎丧心病狂地对中国进行恶意诋毁,说什么中国故意“向欧洲大量输入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4]除此之外,最初兴起于德国浪漫派,后来在叔本华那里达到顶峰的对于印度文化的偏爱,也大大分散了人们对于中国的兴趣。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
即便如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射到谢林和黑格尔身上,看看他们对于中国的关注和论述,就会立即获得迥然不同的感受。无疑,在整个西方思想史里,没有任何人比谢林和黑格尔更深刻地反思到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全面深入地发挥了“普遍历史”的思想。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质的哲学”(geschichtliche Philosophie)。所谓“历史的-批判的”(historisch-kritisch)方法,是谢林和黑格尔给后来的人类精神活动打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诚然,两位哲学家都不是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和了解——特别是关于东方国家的文化——基本上都得依靠其他专门学者提供的素材(翻译、报道、研究等等)。关于中国,当时那些学者所提供的信息,不管是赞美还是贬斥,不管是真实的记载还是带着偏见的描述,都反映出了一些鲜明的共同特点,引起谢林和黑格尔的注意,并将其整合到他们各自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去。当然,从今天的西方“汉学”的发展水平来看,谢林和黑格尔对中国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谬见甚多,正如按照现代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自然思辨中也充满了错误。但是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毋宁在于去考察,如果谢林和黑格尔那个时代所理解的中国毕竟是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在当今西方世界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理解下的“中国”在这两位哲学家对于整个历史的把握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有着怎样的意义?
如果我们分别考察一下黑格尔和谢林各自的论述,那么首先可以发现,他们在如下一些认识上是一致的:
1、中国是一个极为古老,甚至最为古老的国家;
2、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孔教”不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佛教和道教并没有被看作属于原生的“中国”精神);
3、中国的国家体制、伦理和世俗生活在漫长的数千年里维持不变;
4、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王权社会。
但是,这些认识本身还不能说明任何东西,而且同样的观察并不一定会导致同样的结论和评价。恰好是在这里,关于中国在历史中的地位,黑格尔和谢林作出了不同的判断,而这又是因为,黑格尔和谢林各自的历史哲学构思有着迥然不同的根源。如今,通过对比并分析这两位哲学家的“中国观”的异同,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两个伟大的历史哲学体系在原则和方法上的分野。对于我们中国学者而言,这样的工作应该能引起特别的兴趣。

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约瑟夫·谢林(1775-1854)
首先我们知道,“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黑格尔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在《精神现象学》中已有所反映,但尚未清楚地表述出来。在后来的《哲学全书》里,黑格尔才明确提出:
“我们看到,逻辑理念的不同层次在哲学史里表现为相继而起的哲学体系……较早的哲学体系与较后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就是逻辑理念的较早层次与较后层次之间的关系。”(TW 8, 184)
同样,他在《哲学史演讲录》中也说道:
“单就逻辑的进程自身而言,按照其主要阶段,人们在其中也就掌握了历史现象的进程。”(TW 20, 478)
在黑格尔哲学里,逻辑理念是一个无限地走向对立的进程,既然其开端在于“存在”和“无”的单纯对立,那么现实的历史的开端也应该是这两个原初规定性的最真切的表现。当然,要认定这个表现——确切地说是对于这个表现之最初的意识——是出现于中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了。
实际上,当黑格尔具体地考察“历史”的时候,已经把纯粹的逻辑学规定性转化为理性的自由意识问题。对此黑格尔自己的态度很明确,他在《历史哲学讲授录》中宣称:“历史必须以中国为开端。”(TW 12, 143 u. 147)表面上看来,这里的依据似乎很简单,即中国是有记述以来最古老的国家(按黑格尔的了解是至少可以推算到公元前3000多年)。也许有些民族可以吹嘘他们有“更悠久”的历史,甚至虚构出一些空洞的年代数字。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当然要更久远得多,至于精神本身的存在更是时间所无法估量的,但黑格尔心目中的历史首要地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亦即可以作为哲学的对象的历史,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哲学的意思不是别的,无非就是在思想中进行的历史观察。”(TW 12, 20)历史哲学坚持的是“唯一的”一个思想,即“理性”的思想:“理性统治着世界,世界史里的进程也是合乎理性的。”(ebd.)历史哲学中的思辨认识应该表明:
“理性……既是实体也是无穷的力量,它本身既是所有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无穷的质料,也是无穷的形式,是它这些内容的实现。”(TW 12, 20-21)
对于哲学的初学者,或者说对于尚未具备这样认识的人,黑格尔建议(但并不强求)他们抱着信任的态度来观察历史——不仅是对理性的信任,而且也是对黑格尔本人的信任,因为上述深刻认识毋宁说是在历史观察的最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这是一个我知道的结果,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了整体。”(TW 12, 22)除了这部《历史哲学讲授录》之外,在黑格尔的其他著述里,很少见到他如此露骨地表露出这一坚定的自信。但是,虽说理性统治着世界,一切存在都符合理性的法则,但并不是任何存在都对此有所意识,比如太阳和行星虽然也是遵循永恒的理性法则而运行,但它们不可能意识到此。就此而言,上述自然活动不能归属到历史的范围。真正的历史只能从理性的意识开始,而理性的意识就是对于“自由”的意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世界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发展过程。”(TW 12, 32)按照这个尺度,黑格尔得出了他的那个著名的断言:
“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则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所有人在其自身就是自由的,即人作为人就是自由的。”(ebd.)

世界史的阶段和过程同样按照这个尺度而被划分。
因此,当黑格尔以中国作为历史的开端,这与其说是一种赏赐给中国的“荣幸”,不如说首要地是因为黑格尔判断,理性的意识在中国还处于最低级的阶段,只有皇帝“一个人”意识到了自由。但这个判断是不充分的,如果只是就中国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王权专制社会而言,其说服力也是不够的。西方从希腊和罗马开始,同样不乏僭主、暴君,同样存在着专制甚至独裁统治,为什么不说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在黑格尔那里,印度也被认为是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但那里却并不存在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统治。实际上,用是否专制或专制的程度作为尺度标准来衡量社会的“先进”还是“落后”,是很不靠谱的事情,因为黑格尔本人最信赖的理性并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呈现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完整的文化中:国家体制、伦理规范、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发展,乃至生活习俗等等。因此,当黑格尔把中国定位于历史的初级阶段,他必须论证道,理性在中国的上述各个方面——至少是在最基础的哲学、宗教和艺术等纯精神性的领域——都处于最低限度发展的阶段。诚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美学讲演录》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但这些论述很难说是有力地支持了他在《历史哲学讲授录》中的相关论断。在《历史哲学讲授录》里谈到中国的地方,黑格尔基本上是简要转述了中国自伏羲以来的历史过程,然后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始终保持不变的国家体制的精神”上面。(TW 12, 152)在他看来,这个精神即“家庭精神”,是“实体性精神与个体的直接统一”。(ebd.)其特点在于,个体意志与吞噬它的实体之间的对立还没有返回到自身内,个体意志还没有把实体的势力设定为他自己的本质性,还不知道他只有在这个本质性中才是自由的,等等。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单纯对立表现为前者对于后者的无反思的、无自我的服从,否则便会遭到惩罚;又因个体意志和普遍意志在这里都没有通过一种中介活动而返回到自身内,所以无论服从还是惩罚都是“外在的”。从这些观点出发,黑格尔津津乐道于中国的三纲五常的一些细节规定,并谈论了中央帝国的政府管理和法制,其中特别提到:
“因为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所以专制的统治方式是必然的结果。”(TW 12, 157)
这里所说的“平等”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的意思,而是所有的人(从平民到最高官员)都得同样服从皇帝的权威,而唯一的“不平等”,就是皇帝和所有其他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从黑格尔的这些描述中,倒看不出他对于中国有多少明显的贬损语气。

就宗教的方面来看,正如黑格尔正确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宗教”和西方人的宗教(Religion,原意为“对神的敬畏”)是两回事,只不过他在这里得出的是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对我们来说,宗教是精神在自身内的一种内在性,因为精神是在自身内想象着它的最内在的本质。”(ebd.)由于中国人在黑格尔心目中始终处于“单纯对立”或“尚未经过中介活动而返回到自身内”的阶段,所以他也否认了中国人在宗教生活中的“内在性”、“独立性”、“精神性”等等,甚至认为这同样也是“中国科学”的缺陷,即“缺乏真正的科学兴趣和理论研究”。(TW 12, 168-169)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把中国的书写文字看作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我们知道,在哲学的领域里,黑格尔和不少德国哲学家(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自己的母语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也许他们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必须把中国的语言文字当作与此相对立的一个反面。无独有偶,早在《逻辑学》里,黑格尔就已经指出,一门适合哲学的语言应该拥有丰富的逻辑表达式,特别是一些独特的、独立的表达式,来表现思维的规定性,尽可能地把思维的规定性提炼为一些名词和动词,赋予其对象化的形式;而作为一个反例,他断言:“中国的语言在其构造中完全没有,或者只是很贫乏地做到了这一点”。(TW 5, 20)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黑格尔是对的,但是像他这样在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情况下轻率地贬斥中文,却是可笑的做法。类似的更可笑的情形是,赫尔德这位满腔道德和宗教的热情,但是思维简单的思想家,针对中国语言超过八万的汉字数目和众多字体,宣称道:“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但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5]这让我们想起莱布尼茨说过的一句话:
“我发现,绝大多数学派在他们肯定主张某些东西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但在他们否定某些东西的时候则不那么在理。”[6]
实际上,黑格尔真正能列举出的中国语言的“缺点”只不过是,相比中文,西方人的书写语言很容易学习,因为他们把语音分为25个左右的单音(字母),只需要记住这些字母及其组合就行了,而中国人则必须至少学习数千个字符。上个世纪初,我国那些曾经主张汉字完全拼音化的人大概也是这个思路,据说这样就不必去记繁多复杂的汉字了,可以降低学习中文的难度,减少文盲的人数。现在看来,这想法实在简单而至于幼稚了。因为,本身说来,任何正常情况下的母语学习都不是“困难”的,或者是同等难度的;至于文盲的多少,与其说取决于语言本身,不如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义务教育制度更为合适。
鉴于思想和语言的密切关系,可以说黑格尔对于中国语言的无知已经决定了他对于“中国思想”的理解只能流于肤浅的表面。如果说他在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还能看到一些要点的话,那么他在哲学、宗教和艺术等领域的评价基本上是完全隔膜的。他的整个《美学讲演录》只在少数几个地方提到中国,即使提到基本上也是毫无根据的贬斥,比如:
“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在他们的艺术形象、神像和偶像那里还停留在无形式的,或糟糕的、不具有真正的规定性的形式的阶段,他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美。”(TW 13, 105)
这不过是武断地重复赫尔德的错误论调。在宗教领域,当黑格尔把宗教划分为自然宗教、自由宗教、绝对宗教三大阶段,中国的宗教同样被置于其中的最低阶段,在自然宗教里只比巫术高一个层次。按照黑格尔一贯的看法,这里仍然是实体性的存在与特殊个别的精神之间的单纯对立,前者被看作是普遍的、吞噬一切的力量。中国宗教被称作是“法度的宗教”,这里的“法度”(Maß)与《逻辑学》里所说的作为质与量的统一的“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所有本质性存在和理性法则的统称,但还处于抽象、空洞的阶段。法度的一个表现是“天”,但这个概念
“所指的是一种完全无规定的、抽象的普遍性,是所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关联的一个完全无规定的总体……中国人的‘天’是某种完全空洞的东西。”(TW 13, 320)
除此之外,“‘天’仅仅意味着‘自然’。”(TW 12, 166)法度的另一个表现是“道”,但黑格尔在其中看到的只有诸如“存在和非存在”(即老子所说的“有”和“无”)、“一和二”等极为简单的范畴,以及“许多特殊规定性和特殊法则的堆积”。(TW 13, 323)至于孔子,他在黑格尔心目中的地位很低很低,其任务主要是把对天的祭祀(这是皇帝的专门工作)转化为一种对官员和其他人们都适用的道德生活,给出各种义务的情况和规定,仅此而已。对于孔子在莱布尼茨时代的欧洲赢得的卓越声誉,黑格尔表现得十分不屑一顾,他认为孔子的《论语》中“没有任何卓越的东西”,甚至宣称西塞罗的一部《论义务》要比孔子的全部书籍给予我们更多的教益。(TW 18, 142)而对于具有浓厚形而上学意味的《易经》和《道德经》,黑格尔也只是给出了最简单的一些皮毛的描述,认为它们和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具有同样的渊源(TW, 12, 171)——这些在他看来就是“中国哲学”的全部。我们看到,黑格尔甚至不太情愿承认中国有“哲学”这个东西,而只愿承认这是“一种与哲学很接近的宗教世界观。”(TW 18, 138)。同样,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提到了“所谓的东方哲学”,并将它与“真正的哲学”区别开来。(ebd.)归根结底,黑格尔的那个评判尺度始终是所谓的“主体性”(离开自身而后又返回到自身),而中国的精神在他看来还一直没有返回到自身内,没有达到“内在性”,没有个体的人格,没有自觉的意识,等等。这些导致黑格尔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民族的性格的标志在于,“远离所有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道德、伦理、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TW 12, 174)

但是黑格尔的论断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一方面在于他对于自己论述的对象缺乏全面的、真正的了解,更主要地是在于他虚构了一个世界精神由东往西漫游,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步发展的模式,而中国恰好不幸处于“最东方”的位置,因而被强制设定在最低级、最落后的阶段。理性应该在历史的发展中日益达到更高的自我意识,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戴着那个“精神漫游”的偏见的眼镜,就不仅不能正确评估理性在古代中国达到的高度,也看不到理性在中国精神中的持久推进,最重要的是,看不到中国在世界史里独一无二的地位。
恰好是在这个问题上,谢林提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观点。从很多方面来看,谢林是黑格尔最为密切的同道者,同时也是其最强大的竞争敌手。谢林的基本思想也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尽管他没有建立起一个黑格尔式的逻辑学体系),其思辨能力和历史性思维与黑格尔相比毫不逊色。在其22岁时写下的《历史哲学是否可能》(1797)一文中,谢林思索了“历史”的范围,以及历史哲学总的指导方针:“只有当存在着一个理想,而具体事物以无穷杂多的方式偏移这个理想,但在整体上又与这个理想完全契合,这才有历史可言。”(I, 469)[7]从这个原则出发,谢林在后来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里把哲学看作是
“自我意识的前进发展史。要准确并且完整地描绘这个历史,主要的关键在于,不仅要准确地区分出这个历史的具体分期以及每个分期下面的具体阶段,而且要在一个顺序中来思想它们……”(III, 331)
这个方法也被黑格尔采纳,但毕竟是谢林最先提出的。正因如此,谢林在晚年多次强调道:
“早在我最初的步伐里,哲学已经显露出‘历史’的趋势,至少是以一种意识到自身的,返回自身的自我的形式……这个方法正是我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天然的东西。尽管我不能夸耀说这个方法是一个绝对的发明,但是同样地我绝对不能让人把它从我这里抢夺过去,或者承认另外一个人[黑格尔]的吹嘘,说是他发明了这个方法。”(X, 94, 96)
但另一方面,在谢林的整个前期哲学里,他对于“历史”的考察主要还是限定在先验哲学的层面,并没有进入到现实的世界史。后来的“世界时代哲学”尽管勾勒出了一幅宏大的历史哲学图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但谢林也只是论述了其中前面的三分之一部分,亦即“过去”,而这个“过去”部分考察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史前”(Vorgeschichte)更为合适。从谢林和黑格尔共同的“理想”来看,他们是高度一致的,即历史是世界精神(或称作“上帝”、“理性”或别的什么)四处漫游并最终回归自身的过程。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何设定这个漫游的开端?谢林在各个民族的神话(Mythologie)和神秘学(Mysterien)中寻找历史的开端,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开始就把这些内容摒弃在“历史”的范畴之外:“历史是散文式的,而[诗歌形式的]神话还没有包含历史在内。”(TW 12, 142)黑格尔在去世之前,曾经就格雷斯(J. J. von Görres)的《世界史的基础、结构和时间顺序》(1831)一书写了一篇书评,针对格雷斯在一些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基督教天启之间建立联系的企图,黑格尔挖苦道,这不过是一种充满幻想、空洞的类比游戏和盲目激情的无用之举。(TW 11, 487 ff.)这等于也是对于谢林的一个间接批评。当然,格雷斯的思想怎么能与谢林相提并论,所以谢林并不认可黑格尔一概而论地蔑视甚至排斥神话的做法。在谢林的后期哲学里,不存在一种孤立的“历史哲学”,它应该由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以及作为其导论的世界时代哲学组成。和黑格尔相反,谢林在《天启哲学原稿》(1830/31)中宣称,神话和神秘学的内容不是别的,“恰恰是宗教意识的历史本身,是上帝的历史本身。”[8]世界史必须回溯到精神的最初源头,“如果没有神话哲学,历史哲学就既不能捍卫其概念,也不能找到历史真正的开端。因此很明显,在神话哲学成立之前,‘历史哲学’只是作为一个名称而存在。”[9]从这个原则出发,谢林论述了绝对者(上帝)如何从原初的一分化为二和多,并最终回到自身,成为一个绝对统一体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在人类史前意识中的反映:神话和神秘学,前者是一种公开的故事,后者是一种秘传的教义,但本质上反映的是同样的思想和历史进程。

按照谢林的历史图式,世界精神从埃及出发,经过印度而回到希腊,并为基督教的天启作好准备。在这篇论文里,我们最感兴趣的自然是谢林怎么看待中国的问题。很明显,当谢林勾勒的世界精神的漫游路线时,并没有在其中给予中国一个位置,这与黑格尔把中国放在世界精神的起点和最低阶段成为鲜明的对比。是谢林遗忘了中国?当然不是。因为,恰恰是“中国”构成了谢林的神话哲学乃至历史哲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难题,促使谢林思考中国的独特地位和意义。
正如谢林看到的,中国与其他那些民族的神话毫无关系。埃及、印度和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和相似结构,比如提丰之于梵天和乌兰诺斯,奥西里斯之于湿婆和克罗诺斯,霍罗斯之于毗湿奴和宙斯。但是在中国的远古传说中,却找不到类似的痕迹。因此,对于谢林哲学的神话进程来说,中国民族是“一个绝对非神话的民族”,就此而言,可以说构成了世界史的“唯一的一个例外”。(XII, 521)诚然,人们会反驳道,中国自古以来拥有大量的神话、仙话、鬼话、民间传说等等,[10]怎么会是一个“非神话的民族”呢?但关键在于,谢林所理解的“神话”特指的是一种“诸神的生成史”或“诸神的谱系学”,而这是中国的神话传说所全然缺乏的东西。尽管如此,谢林并不想因为中国就推翻他自己的神话哲学或放弃神话哲学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原初的那个排他的统一体必须让位于后起的一个分化原则,以便达到最后的统一。在谢林看来,在那个原初统一体退隐的关口,有一个“大分化”(Krisis),这不仅是各个民族的分化,也是各种神话、语言的分化——这些都是在一瞬间同时发生的,或在超越时间的一个层面上发生的。没有那个民族是没有神话的,正如没有哪个民族会没有语言。在这阵子情况下,如果谢林判定中国缺乏他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神话”,那么就只能说,中国不是芸芸众多的民族之一,不可与其他民族混为一谈。谢林大胆地提出,“中国民族(das chinesische Volk)”这个提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是纯粹的‘人’,正如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众多民族之一,而是自认为是与所有民族不同的真正的‘人’(Menschheit)。”(XII, 522)
因此,谢林倾向于使用“中国人”(das chinesische Wesen, die Chinesen)”而不是“中国民族”的提法,尽管他偶尔还是会习惯性地说到“中国民族”。
也就是说,中国精神并没有经历那个从一到多的过渡,而是从始至终地将那个原初的统一体保留下来,所以中国人是“绝对的史前人类的保存下来的一部分。”(Ebd.)就此而言,“中国始终是独一无二的。”(XII, 526)原初统一体的意识在中国意识那里拒绝了宗教-神谱学的进程,所以中国完全置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神话活动之外,没有参与进去。在某种程度上,谢林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灾难”:“本来‘二’应该取代迄今的统一性的位置,但是中国意识反抗这个‘二’,它到现在都还坚持在那个最初原则的排他性上面。”(XII, 528)
尽管如此,谢林在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中央帝国是一个“历史的奇观”:
“中央帝国是世界上所有帝国里面最古老的,它持久独立地保持着自身,展示出自身内的一个不可征服的生命原则。”(XII, 529)
蒙古人和满族的统治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中央帝国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从内在来看,这个国家到今天都还完全具有和四千年前一样的面貌,持久地立足于它在起源时就以之为基础的同一个原则上面。”(Ebd.)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帝制只是从公元前200多年(秦帝国)才开始,但谢林和黑格尔一样,都认为帝制至少应该从尧的时代算起,而秦始皇不过是恢复了中国更早的、甚至可以说最古老的那个秩序。(Ebd.)谢林认为:
“这个不受限制的、绝对的帝制的理念和中国民族一样古老,它不是在时间中产生出来,而是从民族的起源以来就一直彰显着的一个理念。”(XII, 530)
很多学者把中国民族的精神归结为祖先崇拜和家族谱系,谢林固然承认这些东西的巨大影响,但是他追问的问题更深,即祖先崇拜原则为什么能拥有这样长久深远的影响呢?答案的关键还是那个“灾难”:一不曾过渡到二(多)。原初的统一体作为一个排斥意识——因为意识总是已经意味着二分——的原则,在中国意识里没有转变成一个相对的单一体(就像在所有其他神话民族那里一样),而是转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且外在的单一体。这个原则体现为“天”,并进一步应用到国家上面,皇帝作为“天子”掌管着“天”的一切权力。这个绝对原则在对内和对外方面都发挥巨大影响。“中国确实是变得可见的‘天’,因为它从不改变,就像天体一样静止不动。”(XII, 534)那么,中国精神是怎么把天的权力与世俗的统治者(他们经常会犯错误,有各种缺点)结合起来的呢?谢林又提醒我们回忆起那个“灾难”,并认为它表现在中国帝国的普遍象征——“强大而聪明的龙”(XII, 537)上面,龙是从“纯粹的天”到“世俗的天”的过渡,是二者的一个中介。

既然分化从未发生,也就谈不上有对于重新统一的追求,因此中国意识也缺乏“救世主”的观念,而这是狄奥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以及耶稣在基督教天启里扮演的角色。中国意识省却了一个漫长的痛苦挣扎过程,
“通过宗教原则的那个绝对的转向和世间化,中国意识完全省却了宗教进程,它几乎原初地就达到了那个纯粹合理性(reine Vernünftigkeit)的立场,而其他民族只有通过一个神话进程才达到这个立场。”(XII, 540)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族是一个彻底非宗教的民族,他们获得了一种摆脱神话和神谱学进程的自由,但代价却是成为完全的无神论——这里的“无神论”不是指积极肯定地拒绝或否定上帝,毋宁说对中国人而言,上帝根本就不是一个讨论的对象,甚至根本就没有作为一个对象出现在某种直接的意识中。(Ebd.)
除了那个神奇的统一性原则之外,谢林还看到了中国人展示出的另外一个谜,即他们的语言。对西方人来说,独特的中国语言仿佛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但谢林指出,中国语言根本就不是“一种”语言,而是“语言”本身,是“原初语言”的遗迹,正如中国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人类本身。中国语言完全是中国意识的反应:
“确切地说,在中国语言里,似乎也蕴含着‘天’的完整力量,那种原初就管理着一切、绝对地统治着每个个体、并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力量。”(XII, 541)
在谢林看来,中国语言的特点在于其单音节的特性,每个词都是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组成,而没有西方语言中辅音与元音的自由组合。在中国语言里,甚至外来语都必须服从它的这个特性,比如“Christus”一词就被翻译为“Ji-li-si-du”这四个词。中国语言缺乏语法和语法形式,其根源在于,单个的词不能脱离整体的联系,
“每个词既可以是名词和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和副词,而正因为它可以是一切,所以实际上它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在孤立的、单独的或抽象出来的情况下,什么都不是。”(XII, 544)
所以,中国语言的内部包含着一种暴力,“彻底地剥夺了每个词之独立的形成……整体在部分面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XII, 545-546)另一方面,中国语言在语音上的贫乏与它的无比庞大的文字系统对应(谢林那个时代已经知道中文至少有八万多汉字),这是因为语音的稀少不足以指呼事物,所以中国语言的文字就起着“呈现对象自身”(XII, 551)的作用。与此同时,谢林认为汉字与埃及的象形文字根本不是一个起源,后者的贫乏(不超过800个)毋宁说是字母文字的前身。在对中国语言的评价上,尽管谢林和黑格尔看到的是同样的情形,但和黑格尔的妄自菲薄做法不同,谢林不但深入剖析了中国语言的特性,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学者(黑格尔自然也在其内)将中国语言的特性归结为“幼稚”或“落后”的看法。因为,中国不是仿佛从一个野蛮的状态逐渐进步到现在的样子,而是通过远古的一个“不可追思的事件”(XII, 549)从起源到现在都是这样样子,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绝不是幼稚落后的东西,而是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精神的成果。谢林自少年起即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古典语言的素养(包括对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掌握),使得他在评价中国语言时的高度远远超过了黑格尔。实际上,不仅中国语言不是什么幼稚未成熟的东西,可以说任何民族的语言都不是幼稚的。按照谢林的神话哲学思想,凡是史前人类保存下来的一切精神现象的遗迹,哪怕是某些看起来“稚嫩”的东西,都已经是一种高度成熟和发展的表现,是精神在无时间的永恒循环中逐渐孕育出来的成果。我们动辄就说古人低级和落后,不过是站在当前立场的的自以为是,以及对古人的真实情况不够了解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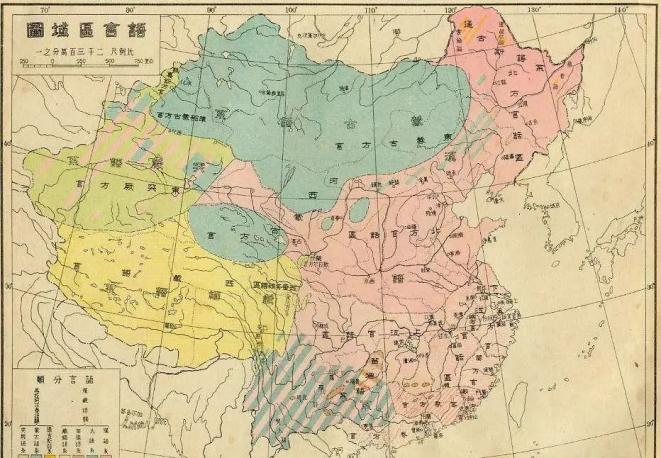
总之,谢林深深惊叹于中国之作为地球上完全独立的一个部分(尽管其时他知道中国已经遭到了英国和俄国的侵略),感叹中国是“另一种或第二种人类”。(XII, 555)在其他民族那里,总的趋势是不断分裂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小的民族,惟独中国体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性。
“中国是从历史的本原和开始就已孤立出来的一部分人类,正因如此,它自古以来就占据着它现在的领地,几乎摆脱了任何震荡和推动其他人类的那个进程。”(XII, 556)
所以中国人有理由宣称,历史是随着他们的国家一起开始的,因为他们的国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在历史的开端就已经存在。谢林同意这种说法。但另一方面,谢林并不因此而过高评价中国在世界史里的意义,更不认为其他民族的历史或整个世界史是以中国为开端,因为,“中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是位于所有历史的开端,即它拒绝了任何运动。”(XII, 557)当其他民族被卷入普遍历史的洪流和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时,中国岿然不动,这一方面是一种超然卓绝的表现,但另一方面,说得难听点,“中国意识并不是那个史前状态自身,而是那个状态的一个僵死模型或干尸。”(ebd.)在这个意义上,既可以说中国是最古老的民族,也可以说它不是,因为,一种脱离了时间和进程的古老,实质上是对于自身的否定,而真正的、活生生的“最古老者”,只有作为一个进程的开端才有意义——就此而言,巴比伦民族才是“最古老的”民族。相比于谢林的观点,其实黑格尔也注意到了,中国既可以说是历史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在历史的进程之外:
“中国和印度仿佛置身于世界史之外,作为后来各个阶段的前提而存在着,但这些阶段的联合才构成世界史的一个活生生的进程。”(TW 12, 147)
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与谢林的观点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但在对于中国的观察上,黑格尔没有得出一个启发性的结论。
尽管不承认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宗教,但谢林在中国仍然区分出三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这里我们仅仅简单提及前者。在谢林看来,孔子不是某种哲学或宗教的创始人,而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一个极为动荡的环节,在一个古代原则变得动摇的年代,将这些原则重新固定到了它们的远古根基上面。”(XII, 560)
这个评价可以说真正触及到了孔子的历史使命和根本意义,比黑格尔那种拿西塞罗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做法不啻高明百倍。谢林认为,孔子是中国民族的精神代表和表现,他的学说没有任何个人的、专属于他的东西,他是通过他的民族的本质来说话。这个本质认为国家就是一切,所以孔子也不承认国家之外的任何宗教、科学和伦理学说。在孔子的精神里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那个“原初统一原则”,该原则之绝对的外在化和世间化(国家)诚然也承认上帝(“天”),但这里所谓的上帝仅仅意味一种法则和世界秩序,意味着一个治理和统筹着一切的理性,至于其人格性却是无所谓的,因为“天”的人格性(假若有这个东西的话)不会带来任何影响。就此而言,孔子精神的后果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丝毫不逊色于近代那些哲学家和启蒙主义者”。(XII, 562)这时我们再来看看黑格尔将中国列为理性的最低级蒙昧阶段的做法,相比之下,谢林的认识无疑要深刻得多。

不管怎样,其实在今天看来,无论黑格尔还是谢林对于中国的认识了解都不是充分全面的,然而当这些认识被整合进他们的历史哲学之后,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赫尔德-黑格尔式的中国偏见在今天的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仍然颇有市场。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一个“汉学”问题。黑格尔和谢林所分别诠释的中国模式,对于我们始终有着重要的警醒和启发的意义,不管他们强调的是中国的“落后性”还是“独特性”。反映到当前现实,一个基本问题的即,我们中国是应该作为一个所谓的“落后的东方国家”去追随“先进发展”的西方国家的步伐,融入其“普遍历史”的进程呢(实则是甘当其垫脚石),还是应该坚持自己在世界史里绝对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完整地保守中国精神数千年来独具的文明内容。如果将黑格尔和谢林的相关思想作一个比较,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谢林更有助于让我们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树立起巨大的自信心,而只有具备这种自信心,我们才可能公正地反思中国历史,思索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在整个人类中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使命。近世中国学者里,钱穆先生可谓这方面的一个典范,虽然他很有可能根本不了解谢林的哲学及相关观点。同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精神从古至今始终是一个充满无穷活力的整体,而不是谢林所错误断言的那种“干尸”。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中真正的“逻辑”是什么?在当前全球化或“普遍历史”看似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向来特立独行的中国精神能否(以及如何)很好地融入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精神应该在全球文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将要面对的中心问题。
注 释
[1] AA = Kants Werke. Akademische Textausgabe. Berlin, 1968.
[2]本文引据黑格尔依据的是20卷本的《黑格尔全集》(G.. W. 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Theorie-Werkausgabe. Redaktion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 Frankfurt am Main, 1970),缩写为“TW”;“TW”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指卷册,再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指该卷页码。以下同。
[3]参阅《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7
原标题:《黑格尔和谢林论中国在“普遍历史”中的地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