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双相患者在健身房有过的小小努力,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见证过 | 三明治
原创 安心 三明治


作者|安心
编辑|邱不苑

我睁开眼睛,已经是下午了,身体和床铺都脏兮兮的,房间里也充斥着一股不新鲜的泡面味道。我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两周了,除了吃东西上厕所和偶尔一次的清洗身体,我都一动不动。
自从不久前抑郁症再一次发作,我就没有去上班了,也不再接听电话,接电话对我来说是一种酷刑,任何形式的与外界的交流都让我痛苦不已。我想关机或者开启飞行模式,但又怕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万一有人上门来找我呢?这个房间是公司给我租的,他们知道地址,我无比害怕这种可能性。
但不幸的是,在这两周里我的手机不停的响起,理由显而易见,没人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从工作岗位上失踪了,我的物品原封不动的放在工位上,逐渐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开始需要找我,我毕竟是一个管理材料的秘书。上司发来一次又一次的语音邀请,后来是无奈的语音消息:“你至少得接听我的电话,然后我们才能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职和不负责任,我深深知道这一点,但无法控制自己想要逃避一切的,越来越低落的心情,不管是自己当下的样子还是可能给周围造成的麻烦,甚至是潜在的他人对我的看法,一层一层像黑色的浓烟将我包裹在内。但只要我闭上眼睛,坚决拒绝这一切叨扰,拒绝面对生活的话,仿佛还可以坚持下去。
唯一还有些交流的人是妈妈,我用微信打字给她:“我今天想洗澡,但是我动不了”。
“没关系,先吃点东西,等有力气了再洗,不洗也没关系”,妈妈每天最担心的是我有没有好好吃饭,因为抑郁发作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不吃饭,这五年来,我在自己学习工作的每个地方都有发病,北京、俄罗斯、比利时、老家,这回是南京,她也变得有经验了。
不过我确实没有好好吃饭,每次答应她吃饭以后都是糊弄糊弄,抑郁的时候任何饭菜都无法给我带来快乐,只要能有东西给我填饱肚子,不至于因为腹中空空而情绪更加低落就可以。
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又发微信给妈妈:“我要不要现在去洗澡?”
“鼓鼓劲,一鼓作气,就完成了”,她很有耐心地鼓励我。
又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走出浴室,把衣服塞进洗衣机。
“我洗好了。我还洗了衣服。”
“真棒!妈妈为你骄傲!”
如果有人以为抑郁症患者不能行动期间,会舒舒服服躺在床上连续睡很多天的话,那只对了一半。我的体验是,虽然真的很疲倦,每天有十几个小时昏睡不醒,但醒着的时候十分空虚煎熬,而且仍旧疲惫不堪。时间会把自己拆解为一分钟又一分钟,排着队来和你认识,我跟他们讨论不同的话题。“你好吗,这一分钟?我刚刚和上一分钟讨论了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失眠的问题吧……”
这种煎熬逐渐让我难以忍受。我躺在床上,看着每天正午窗户透进的阳光,天气这么好,我的心灵却像一座空壳,每天除了昏睡、哭泣,什么都做不了。有一天我的自我痛恨就这么达到了极点,我在手机软件上做了预约,去了步行100米远的健身房。

当我乘电梯下到一楼,走在好久不见的马路上时,有种身体不太受控制的感觉,眼睛也不舒服极了。毕竟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活动过身体,且一直在吃不健康的食物。那家健身房新开不久,我上班的时候每天会路过。进入的时候我很忐忑,因为我从没健身过,这次冒险只是因为在网上看到锻炼身体对抑郁症有奇效。
这是家包月会员制健身房,教练几乎没有怎么使用销售技巧我便接受了条款,成为了他手下身体最弱的会员。教练安排我隔天去锻炼一小时,我很满意,因为这会成为我接下来为之努力的全部生活内容,其他时间我可以在家恢复元气。
一开始的几次我十分寡言少语,我不想和教练有过多交流,不想他知道任何关于我的事情,在一对一的教室里我每次都保持一言不发的上完课然后回家,躺下。教练是个年轻小伙子,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口和他讲话,是因为实在吃不消运动的强度了。
“教练,我觉得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太大了。”
“这算什么啊,强度太小没效果,只有一点一点加强度才能进步啊,况且我已经给你放了很多水了。”
“不是,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吧,这个强度我真的吃不消,我不是想要偷懒。”
实际上身体太疲劳的时候,情绪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天感到不舒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想要改善身体的初衷就不成立了。但我一开始就决定不给没什么关系的人知道我的病。可此时此刻……
“教练,我有抑郁症。”我无奈地看着他,“如果运动强度我接受不了的话,会造成病情恶化的。”
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健身房的大家都知道我有抑郁症这件事了。主要是教练和老板,他们喜欢在我组间休息的时候好奇地问我有关抑郁症的事情。
不得不说,躺尸之余能有人沟通沟通感觉还不错。我跟他们解释我来锻炼就是因为抑郁症,这种病需要看大夫吃药,我已经吃了五年了,但是每年换季的时候都容易反复发作。今年就是这样,本来春夏的时候都控制的很好,现在看来工作也要丢了。
但比起工作,那段时间我几乎寄全部的希望在运动上了。我对心理层面上还有药物的治疗有些失望,他们这些年根本没有治好我,我怀疑抑郁情绪肯定是因为自己从不运动导致没有健硕的躯体而趁虚而入的。在健身房的所有会员中,据教练说我是最弱的一个,我当然相信,每次我上跑步机5分钟内就会汗流浃背。另一个也这样的人,离奇的是个教练,那就是老梁。
一开始我完全没猜到老梁在这间健身房里是做什么的,我以为他是个钟点工。枯瘦的身材,常年打工带来的一点含胸驼背,一身黑色劣质运动服从没换过。他基本没在休息的,要么是倒垃圾收快递,要么和教练说着什么,有时候也看到别的教练带着他训练。但作为一个20多岁几乎只对帅哥感兴趣的肤浅女性,我对这位过于平平无奇的路人甲大叔是一点了解的欲望都没有。
自从健身房的人(也无非是老板、我的教练和老梁)都知道了我的事以后,我被动的开始和大家熟络起来,组间休息的时候教练都会和我聊两句。有一天我实在没什么话题可说才问教练:“那个大叔今天没来吗?”
“你说梁教练吗?那个年龄大一点的?”
对“梁教练”这个称呼不得不说,我震惊了一秒。他居然是个教练吗?
“他今天参加入职培训去了,他也是刚来应聘做教练的,之前是搞骑行的。”教练说。
我对这位“梁教练”有点改观了,或许他精瘦的身材是骑行这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带来的,而黢黑的肌肤来源于高原上的紫外线,他可能比我想的要酷得多!
下一次去锻炼的时候梁教练又在了,我得知他平时就住在健身房。平时他对待人有些刻意讨好,会主动给我倒好温水,然后侧着身用双手将杯子放在我面前(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如果我回应他和教练间的话题,他会高兴的不行,然后用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跟我们聊下去。知道我身体弱,他也讲起自己身体曾经有多么差,后来多跑跑就好些了。老梁看上去确实像个得过什么大病又恢复的人。
“老梁刚来的时候确实气色很差,我们都不知道他打哪来的,穿一身花花绿绿的球衣,头发也很长”,教练打趣道,“他就那么推门进来,说看到门口写着招人,他想应聘。所以当天就面试了,就在这里呆下了。”
老梁不好意思的笑,按理说既然通过了应聘,就得称为“梁教练”,但大家都只管他叫老梁。

翘班在家躺了一个月左右,我一个人去了南京脑科医院。每次发病,我都是在前一段状态积累下的极度疲累和焦虑中突然“宕机”,几乎不吃不喝只流眼泪的躺半个月到一个月后,自己会爬起来到处去求医问药。每个患者的临床反应和应对方法都不一样,总之当我对大夫描述了我这些年来的病情后,他意味不明的微笑了一下:“就是说这些年来你什么都没耽误?”
我一时语塞,好像确实是这样的。虽然这几年我生活的过程充满了这样那样的痛苦,也因为发病差点因为没法参加期末考试而延毕,但因为一直有好好治疗,所以每当病情好转的时候我都能处理好自己的学业和生活,所以不仅没有延毕,最后还高分拿到了硕士学位。在医生的眼里,可能我病的程度很轻吧。精神科里有许多更严重的住院病人,我听说过,去医院的时候在门诊大厅也见过。不像能在网络上为自己发声的年轻人,有很多患者是看上去就很贫苦,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手里拿的那几盒药带来的经济负担,会不会很快使他们的家人失去耐心从而放弃对他们的照料。但在此刻被医生提醒起我的幸运,我该开心吗?
这位大夫很友好地接受了我想要换药吃的请求。抑郁症患者如果对自己服用的药物种类不满意,是可以和大夫商量的。这次发作我的典型症状是焦虑,当时极度的焦虑整夜整夜的缠着我。每天只要我的大脑醒着,都在担忧身边的人是不是想害我,我没了工作是不是很快就会饿死,我是不是没有明天了,或者生活就永远这么空虚无聊吗?……等等负面思想不断地搅和进我头脑的一口大锅里,让我胸闷气短,随时落泪,夜夜梦魇。他开了我没吃过的抗抑郁药“帕罗西汀”给我,我没想到他设下了一个“小把戏”在里面。
付了款去药房取药的时候,药剂师疑惑地问我:“你要不要再找大夫确认一下有没有写错,这个剂量有点大吧。”我告诉她没事的不会开错。有些抑郁症患者尤其是家属非常忌讳精神药品,但我习惯了,并且十分寄希望于一剂猛药可以将我从精神的极度痛苦中解脱出来。
一般精神药物会在服用两周后起效,由于新药的用量几乎是我从前稳定用药剂量的两倍,我的精神很快有好转的势头,教练也称赞我比刚来时的精神状态好多了。但很快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一改之前的颓唐,我开始讨厌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越来越亢奋激动,有时候彻夜不眠的思考,一天可以发七八条朋友圈;教练震惊于我的双臂哑铃划船从一边4kg直接跃升到8kg,连连称赞我是增肌奇才;周末我的一位老同学约我剧本杀,在全是陌生人的十人本里我几乎化身一位神秘古代领袖轻而易举的hold住全场。
周一是我每次复诊的日子,医生听完我对最近情况的描述后告诉我,我转躁了。
我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大夫给我的大剂量药物让我真正的病情显露出来。双相情感障碍又称为躁郁症,和一般的抑郁症不同,患者的状态不仅有抑郁,还会有躁狂,一般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可以简单理解为帮助人情绪变好,但是用药多的话,如果是双相患者便会转为躁狂发作,也就是转躁。躁狂期常见的反应是睡眠减少、思维和话语奔逸、行为增多、性欲亢进等。在过去的几年我一直被当作普通抑郁症来治疗,因为我的躁狂情绪出现的极少甚至没有,一般容易被误诊为普通抑郁,是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二型。
我其实没有多惊讶,因为这些年我也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双相,只是非常不愿意接受这种可能,因为相比一般的抑郁症,这种重性精神疾病更难治疗,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只能控制。但既然这一次事实摆在了面前,我也只好接受之前的误诊,重新接受针对双相的药物治疗,毕竟,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这种疾病会像近视一样不断的加深。
让我开心的是终于可以换药吃了,大夫开了碳酸锂和丙戊酸镁给我,这俩都是针对双相的心境稳定剂。过去一个月帕罗西汀让我感到十分的恐惧,我只想赶紧摆脱它。抗抑郁药是有非常多副作用的,很为人熟知的一项就是性功能障碍,但我之前服用过的各种药物都没有帕罗西汀在这方面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深重。几乎是服用它的第一天开始,我的生殖器就麻木了,这就好像你的一部分感觉能力被拿走了,比如失去味觉嗅觉什么的。我感觉自己变得不完整,这种不完整带来的无能感可能就像女性在更年期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一样。总之它意味着你毫无办法的失去了原先那个姣好的自己,而你并没做错什么。即使花好几个小时在脑海里想要唤醒自己曾经具备的一种能力或者说感觉,用手抚摸自己的胸部和大腿,最后都还是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的半个夜晚我会停不下来的在网上浏览同病相怜的人们互相交流自己的经验。
这错误的举动会使得你的后半夜更加心惊肉跳,头疼脑胀,辗转反侧,因为不只你自己,大家都怕极了,纷纷分享自己的经验。近年来随着吃药治疗的人逐渐增多,pssd群体数量也在上升,这是个对老患者我来说也新鲜的词,Post-SSRI Sexual Dysfunction,就是在使用抗抑郁药后长期存在的甚至不可逆的性功能障碍,外网上对此现象的研究论文在逐渐增多。
可在属于我的白天的现实中,一切都温和而光明。当我和大夫讲接受不了帕罗西汀的副作用时,他问道:“你结婚了吗”,我回答没有,他又困惑的追问:“那你担心这干嘛?”在在场的实习大夫友好目光的洗礼下,我一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不过当老大夫确信的说:“这种药物是会造成高潮困难,不过是可逆的,停药就好了”,我才不至于困窘的要死。
从医院回家后我开始换药吃,抑郁症药物是需要逐步增减剂量来用药和停药的。帕罗西汀的停用在我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戒断反应,好几天来我的心率一直保持在120以上;成宿的做梦,梦中离奇的景象极为生动,我全记得住;还有暴饮暴食,强烈的食欲驱使我每天叫四次外卖,感谢那些工作到十点后的餐厅,方便我不费力气便能大快朵颐。这些反应持续纠缠了我两个月之久。

我没有跟健身房的人讲自己确诊双相的事,和不了解这种病的人解释自己的病情毕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不过我的“抑郁症”仍是我在健身房时大家聊的主要话题之一,出于好奇也出于想宽慰我的好意。
当时我已经一个多月没上班了,还住在那间独立的公司给租的宿舍里,我的生活僵持着,总有一天,可能是几天后,也可能更久,我得去公司打包行李,办理一些把自己清除出去的手续,结束这种尴尬的状态。但是我没有力气,不管是做决定的意志力还是搬运一件东西的体力,我仍然需要妈妈给我鼓励才能起床去洗澡,每天去健身房和下楼取外卖就是我能做的极限了。空虚无聊的时候,我开始赖在健身房不走,那里生意很差,总是只有我和教练还有老梁。
教练是一个20出头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起聊天的时候,老梁总开玩笑吐槽他“什么都不懂”。这指的是教练很单纯,是那种多少可以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小孩。
有一天带我做俯卧撑的时候,他注意到我指甲上有一些残存的指甲油,就问我:“你这个涂了多久了?还没掉啊?”
我说:“好久了。你看这长出来的全被我剪掉了。”
他兴奋地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指甲和头发都是从根部开始生长的,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们是从末端开始长的。”
“一万个人里面也不会有一个人会有这种想法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也挺优秀的”,我笑他说。
再说老梁。老梁在健身房工作两个月了,看上去健壮多了,也不再驼背了,以前他看上去瘦弱地像刚做过肿瘤手术似的。和老梁的交谈中,我知道他原来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专业骑行选手,而是骑着三轮车从东北老家出发,向西绕了半个中国最后来到这里。而他选择骑行的契机和我来到这里开始健身是一样的:身体太差每天只能躺着,感觉再这样下去真的会死掉了。老梁说,有一天骷髅一样的他从床上爬起来,卷起铺盖放到三轮车上,第一天就骑了20公里,晚上他把车停下,一头栽倒在路边昏睡了过去。就这样骑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他适应了路上的风霜,身体也好起来了。
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离开家,骑行。我们每次聊天都是只言片语的。按理说一个人的故事不该这么不符合常理,一般人都能说明白自己从哪来到哪去。
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是一个读完书刚出社会的人,现阶段我的任务是工作和恋爱。哪怕从十年前开始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就常常使我的生活变得有些困难,但我从未脱轨,即使在每一次想要自杀的边缘,我都在努力挣扎着自救,求医,最终使生活往“正确”的轨道上回转。我不理解40多岁的老梁为什么不是待在家里,考虑着父母的抚养、子女的教育、自己的养老保险金和纳税之类的问题,而像一个吉普赛人似的“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球衣”来应聘健身教练。何况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健身教练。
教练有时候背地里跟我说:“老梁年纪大了,带他练总是记不住动作,挺费劲的。”
确实,虽然一开始常见他积极跟着教练学,没有学员的时候就出去发宣传单,挺积极的,但时间久了感觉水平完全没提高,要是我的话,应该也不会选老梁作自己的教练,哪怕只是辅助——这里的月费挺贵的呢。
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聊天,那应该是老梁不告而别的前一周吧,我一直的困惑终于得到了解答。那天我们聊到精神病院,老梁突然说他去过,准确的说是进去过,然后和我们讲起里面的各种“人才”。这些人物的事迹我一个也记不清了,因为老梁本身就是一个夸大其词的,缺乏细节的叙述者,我只记得老梁说自己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他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还用一两分钟科普了一下症状。
“躁郁症就是你躁狂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跟发疯了一样就只想打人,拦都拦不住,但是过了以后又会很抑郁,好几个月都不想动。”
我嘴上哦哦着,没缓过来自己的惊讶,怎么遍地都是双相患者呢?还好我之前没自曝,不然显得矫情了。
“躁郁分两种的,有一种是躁狂为主,这是一型,还有一种以抑郁为主,是二型。我是一型。”老梁继续说道,教练聚精会神的听着,我想老梁也是拿定这家伙听不明白才说这些的吧。
“这是背景哈。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把警察给打了,厉不厉害?”老梁讲到这里还有点得意的神色,教练津津有味地听着。“当时我在街上感觉实在控制不住了,我心里又怕伤人,只想谁给我拉住,这时候我看那边正好一个交警,就冲过去,说了一句,对不住了兄弟,然后一拳过去……然后就让警车给我拉走了。之后他们给我安排入院了,我在那住了一年多。”
我明白老梁为什么老大不小的离家出走了。

那段时间在健身房的“虚度”给了我不少的慰藉,有时候我会在那里一直待到他们下班,和大家一起打扫卫生,有时候跟着他们去周边社区发传单,这些事情多少能让我的大脑不被各种焦虑恐惧的念头占据。我运动也很勤奋,一方面是想通过肉体的疼痛驱散精神的折磨,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当前生活中唯一可以投入的内容。
在我生病的这些年里,自己一直都挺擅长“灾后重建工作”的。在抑郁症面前,我的求生欲非常强,朋友们甚至爸妈都佩服我。记得在俄罗斯读研的时候一次发作,我预感到自己精神上最后一根弦要断了,快要失态倒在回家的公交上了,那种感觉就好像肠胃炎发作的人想要忍住呕吐。但我还是用最后的意志力把自己拖回家去,告诉室友自己可能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麻烦她之后两周带些饮用水和食物给我。在比利时交换的时候再次发作,倒下前给辅导员写了邮件安排好了关于课程的一切,还去申请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基金,积极治疗到基本可以生活自理。双相情感障碍的确诊,对我来说有一个意义在于,作为六大重性精神疾病之一,他大概率真的无法治愈,这样的话,我的生活像水坝上裂开了一个缺口,或者土豆上长出一颗嫩芽。
但比起患者老梁,患者小安之前的人生可真是太幸运了。出生在体制内小康之家,上着全市最好的学校,自小聪明又漂亮,毕业于名牌大学,一直都在社会认为的正轨上骄傲前行。在被狡猾的抑郁症一脚绊倒之前,哪里想得到会有老梁这样的人物来陪她聊天、宽慰她?老梁已经被故乡踢出这种“正常的”生活轨道了,因为自己的异于常人,他大约只是骑着三轮车,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到处寻觅一个可以接纳自己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所以一开始她没法参透这个人从哪来,到哪去。
这天晚上,老梁又在侃侃而谈了:“我以前有个朋友是个大老板,很有钱,也有老婆孩子。但他就是不想活了,找我喝酒,跟我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要我陪他去海边,我们一路没停的去了,我看着他一步一步往海里走。后来我自己回去了。”
“你不救他吗?”
“没用的,下定决心了,救也没用,还是会死。”
是啊,哪怕我之前一直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合意的工作、男友,或者有了健壮的体魄,抑郁就会好了,也不过是一种人们常有的自我欺骗罢了。即使一切都顺利,难道一个人就不会突然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吗?抑郁症的缘由不只是挫折和童年伤痛的。
从健身房离开,老梁送我到楼下,挥手说:“常来坐啊,一起聊聊天。”

隔天上午再去的时候,训练间隙教练说:“老梁的快递没拿。”
“怎么了?”我说。
“你没发现吗?老梁这两天都不在。他走了,去上海了。”
“培训吗?”我以为跟上次一样。
“他不干了,行李都拿走了,骑去上海了,说是那边有朋友,能找到事做。”
“怎么这么突然?前天还跟我说让我常来的。”这时候我觉得十分惊讶了,平时真没遇到过这种戛然而止的剧情。
“就前天你走了以后,突然跟我说要走,连夜就走了。虽然以前也有些迹象吧,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走。”教练说那天我走了以后,有学员来锻炼,他顾不过来的时候让老梁去辅助一下,但是老梁教的不对,被学员说了。之后情绪就不太对劲,晚上的时候和教练单独聊了聊,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就走了。
“他需要些耐心吧,健身确实需要时间的。”我说,虽然也觉得老梁不适合干这个。
“之前我们出去发传单的时候,也有人嘲笑过他”,教练说,“但是我没想到他一直放在心上,那天情绪有点激动,我看着像快哭了。”
这就是老梁的不告而别,我也没有过他的微信,也不知道他的全名。在这间小小健身房有过的努力,全世界只有教练和我见证过。
如果从一点点的偏离正轨开始,有一天我会不会也像老梁一样被排除在主流生活之外呢?有时在知乎上浏览到不要和抑郁症尤其是双相患者恋爱的建议,诚诚恳恳,我自己也觉得人家说的对,别人也只有一次的人生需要慎重对待的呀。找工作呢,要是这种事情不隐瞒,怎么可能有工作的机会,但不隐瞒,就像在健身房破功的经历一样,谁知道自己吃不吃得消。
爸妈那边比我还要矛盾,一会像是忘记我有病一样,盼望我能尽快经济独立和结婚,一会又安慰我说:“没关系,爸妈努力赚钱给你养老,你只要开心地活着就行。”
我好像活在一个前后矛盾的世界。
自打老梁尝试做健身教练未果,仓皇逃走以后,我对自己的未来更焦虑了,时不时的需要服用减缓焦虑的药物。老梁的例子让我感到害怕:我还年轻,履历完美,但这种像癌细胞一样的精神疾病会逐渐在我的体内增殖,让我的生活开始接二连三的失败,最后由内部坍塌吗?
在《鼠疫》里面,对里厄医生来说,瘟疫意味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因为人类在疾病面前可以做的太少了,而世界上的疾病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可能很多年后我会告诉别人接下来我是怎么做的,但现在仿佛自己也接过了一辆三轮车,上面是我的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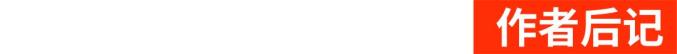
老梁走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公司的最后通牒,要我在月底前搬走。客观来看,我的逃跑比老梁的还出人意料,而且更不负责任。以前我可以通过补考来修满学分成功毕业,能够看起来“什么都没耽误”,但工作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为团队创造价值,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接下来的人生我肯定还是要工作的吧,但是必须要小心翼翼的活着,也要做好随时失败逃跑的准备,做好面对接下来“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的准备。
一年又一年,我发现父母对我的态度也逐渐温和下去,不只是我,他们也被这个疾病磨平了。妈妈有时候会和我说一些特别可爱的话,她说:“你要不要学习缝纫开个裁缝店啊,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娃娃缝衣服。”我有点感谢躁郁症能让父母,以及我自己停下来,重新透过岁月的稜镜去审视生活,去回想起我们一开始对于幸福生活的设想。
从这份工作中失败逃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我的生活迟迟不能重启。家人们言语中都担心我的身体,却也希望我能回归社会,我明白他们也和我一样需要从心态上去适应这份挫折。治疗了半年后我终于不是三天两头情绪失控了,只是还害怕人群,对周遭的看法敏感,还不能回归职场。
这半年里试着去谈恋爱,对方被我的病吓跑了。想想看还是得佛系一些,即使我能找到合适的人,他也有一半的概率放弃我。因为病的原因,再喜欢我的男孩子也没勇气对我作出长择的决定。以前有过一个男生,在我抑郁的时候对我很好,几乎是一手将我拖出火坑,我们正常的交往在某个母亲节他回家吃晚饭那天戛然而止。那是我第一次毫无征兆的被男生拉黑删除,应该是父母的期盼让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和我扯上麻烦。
骑着我自己的“三轮车”,接下来往哪去我并没有什么头绪。我想起来老梁说起他出发时的样子,在路上没什么可怕,一两个月就适应了。我现在感觉良好,相比很多病人的真实经历,我只是受了一点点挫折。
原标题:《双相患者在健身房有过的小小努力,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见证过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