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吉尔·德勒兹:在遭遇普鲁斯特之后,布列兹用自己的音乐,创造了一组基础的哲学概念|纯粹阅读
、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18-1995.11.4)
无需计算的占据:布列兹、普鲁斯特和时间
文 / 吉尔·德勒兹 译 / 蓝江
布列兹经常会提出他与作家和诗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米肖、夏尔、马拉美……如果剪辑不是连续性的对立面的话,如果连续性是由剪辑来界定的话,那么就会同样建立文学文本和音乐文本之间的连续性,并在它们之间置入一个剪辑。并没有一般性的解决方案:每一次,都必须按照不断变化的,通常是不规则的尺度来进行衡量各种关系。不过,现在布列兹与普鲁斯特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并不是更深刻的关系,而是一种不同本质的关系,一种缄默的,隐晦的关系(即便他经常在著作引用普鲁斯特)。仿佛他与普鲁斯特“心有戚戚”,机缘巧合,意气相投,布列兹定义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要么计算着占据时空,要么无需计算地占据[1]。尺度用来产生关系,或者实现一种没有尺度的关系。难道他与普鲁斯特关系不正好是第二种吗?魂系梦绕或被魂系梦绕的关系(“你想从我这里要些什么?”),没有计算,没有尺度的占据或被占据的关系。

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3.26-2016.1.6),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
在普鲁斯特那里,布列兹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声音和噪音如何远离那些特征、场所和名称。他们一开始接触这些特征、场所、名称,是为了创作独立的“主题”,这些“主题”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增多或萎缩,减少或增加,加快速度或变慢下来。主旨首先与一道风景,或像路标一样的特征相关联,但随后它变成了孤独变化的风景,或孤独变化的特征。普鲁斯特必然会引出一个分节,梵泰蒂尔(Vinteuil)为炼金术而做的音乐,出现在整篇《追忆逝水年华》中,并向瓦格纳献上敬意(即便人们认为梵泰蒂尔不同于瓦格纳)。布列兹反过来向普鲁斯特献上敬意,认为普鲁斯特已经十分深刻地理解瓦格纳主题的独立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它经历了速度变化,向着自由改变而运动,进入了连续不断的变奏当中,而这些变奏预设了属于“音乐存在”的新时间形式[2]。普鲁斯特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写成的:连续的爱、嫉恨、蛰伏等等,所有这些都脱离了人物,以致于它们自己就变成了无限变化的角色,没有身份的个性化,嫉恨1,嫉恨2,嫉恨3……在独立的时间维度上,这种可变的发展类型被称为“时间模块”,“无穷无尽变化的声音模块”。这个独立的,并非预先存在的维度,这种与模块的变奏并存的东西被称之为斜列(diagonal)。斜列表明,它不可能被还原为和弦的垂直轴,也不可能还原为充当有旋律的水平轴,将它们作为预先设定的坐标系[3]。对于布列兹来说,音乐创作的缩影就在于斜列,每一次都处在不同的条件下,从多声部结合,通过贝多芬的抉择,在瓦格纳那里融合了和弦和旋律,直到韦伯恩摒弃了垂直轴和水平轴的边界,形成了序列中新的模块,让它们按照斜列运动,仿佛分配整个作品的时间功能[4]。每一次,斜列都像是一个和弦和旋律的矢量-模块,这是一种时间化的功能。按照普鲁斯特的说法,《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音乐创作似乎是一样的:以变化的速度和自由的改编,不断地依照斜列来改变时间模块,斜列构成了作品的唯一统一,它贯穿着所有部分。旅行的统一,并不是在风景的垂直的马路上行进,这就像和弦的切入,也不是在路线上的旋律线上前进。它在斜列上前进,“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让看到的景观连续起来,让视角运动起来,并合并成一个变化和时间的模块[5]。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7.10-1922.11.18)
不过,由于时间模块囊括了高速和低速,增大和减少,附录和结论而运行,那么它与距离关系和计时关系密不可分,这些关系界定了可分割性、可容纳性、比例性:“脉冲”是最小公倍数(或者单倍数),“节拍”就是对特定时间下的统一体的数量的刻画。正在这样条理化的时空中,脉冲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其剪切是可以被确定的,成为一种理性的类型(连续统的第一方面)和有尺度的。无论其尺度是否规范,它都可以被确定为各个剪切之间的尺寸。所以,时间模块遵循着条理化的时空秩序,在那里,它们按照脉冲的速度和尺度的变量来寻找其斜列。然而,一个光滑或非脉冲的时空反过来不同于这种条理化的时空。它只在整体上来计时:其切口是不确定的,或毋宁是一种非理性的类型,距离和临近关系取代了尺度,距离和临近关系不能被打破,它们表达了出现在那里的命运或稀缺性(事件的统计学的分配)。占据的标准取代了速度的标准[6]。直觉是没有计算的占据,而不是用计算来占据。对于这种新颖的绵延模块的形象,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布列兹的“时间气泡”(bulles de temps)一词?数量不会消失,但这种数量会变得不依赖于尺度和时间尺度关系,它们变成了数字,数数的数字,游牧或马拉美式的数字,音乐上的律动,而不是尺度。这绝不是按照组成模块的各个元素来区分一个封闭的时空,相反,它们在一个开放时空的气泡中配置着各个元素。从一种时间划分方式到另一种时间划分方式的过渡:不再是时间的大写序列(Série),而是时间的大写次序(Ordre)。布列兹在条理化和光滑之间的区分,与其说是分隔(séparation),不如说是持续的沟通(perpétuel communication)。两种时空是相互轮换和重叠的,在两种时间划分方式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交换,即便这种交换仅仅在如下意义上成立,即在条理化时间中的同质性划分,给出了光滑时间的印象,而在光滑时间中的不平均的分配,引入了一些方向,这些方向通过相邻性的凝练或积聚,产生了条理化时间。

追忆似水年华(全新修订)
作者: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李恒基 等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06
如果我们列举出普鲁斯特描述的梵泰蒂尔的奏鸣曲与七重奏之间的所有区别,那么就会某种东西区别出一个封闭的平面和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闭锁模块和一个气泡(沐浴在紫罗兰色的迷雾下的七重奏创造了一个整体音符,仿佛“在猫眼石中一般”),也会有某种东西将奏鸣曲的小段与速度标记(indication)衔接起来,而奏鸣曲的小段所指的是占据的标记。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追忆似水年华》在体系上按照双重揭示来安排每一个主题,每一个人物:一个是“盒子”中的揭示,在“盒子”中,速度的各种变奏和性质上的改变都依赖于节段和时间(计时学),另一个则是星云或多样性。它只是按照统计上的分配(两条“道路”,即梅塞格丽斯(Méséglise)的道路和盖尔芒特(Guermantes)的道路,被展现为两种统计的方向)来记录浓度或稀缺的值。阿尔贝蒂娜兼有二者,有时候是条理化的,有时候是光滑的,有时候是变化的模块,有时候则是扩散的星云,尽管她都依照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划分。整本《追忆似水年华》都必须读解为光滑和条理化的时间:这就是按照布列兹的区分来进行双重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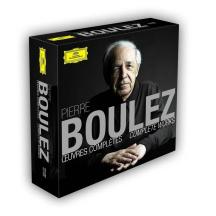
布列兹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合唱团、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DG4794261 <10CD>)
相对于这个更深层的主旨,记忆问题似乎十分次要。布列兹借用了斯特拉文斯基和德索米耶尔(Désormière)的“我憎恨记忆”的表述,提出了“赞美遗忘”的主题,而从未停止过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普鲁斯特。对于普鲁斯特而言,即便不由自主的记忆也会占据一个有限的区域,艺术从各个方向在这个区域中流溢,它只能充当一个诱导剂。艺术的问题,创造的关联性问题,是感知问题,而不是记忆问题:音乐是纯粹的出场,将感知延伸到宇宙的极限处。延伸感知就是艺术的目的(或者说是柏格森式哲学的目的)。唯有当感知打破记忆所绑定在其身上的同一性之后,我们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音乐总是拥有这样一个对象:没有同一性的个体化,它组成了“音乐存在物”。毫无疑问,调性语言恢复了与第一个八度音和和音的同一性原则。但模块和气泡体系导致了在界定它们的变奏和分配中,对同一性原则的普遍拒绝[7]。那么,感知问题变得更为强烈:我们如何感知这样的个别对象,它们的变奏是常量,我们无法分析它们的速度,甚至这些个别对象在光滑的环境下逃逸了所有的尺度?[8]数字或数数的数字,同时避免了脉冲关系和尺度关系,并没有在声音现象中像这样表象出来,即便它们创造了一种真正的现象,但恰恰没有同一性。是否这些无法感知的东西,感知上的黑洞可以用写作来填补,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充当“记忆”功能的阅读之眼,来让耳朵起作用?
在哲学与艺术之间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刘汉全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04
不过,这些问题发生了转向,即我们何以感知认为写作,“没有去理解写作的义务”?布列兹在界定第三种写作,即毗邻于光滑和条理化时空的第三种时空时,找到了答案,第三种时空理所当然是一种感知性写作:大定在的宇宙(l’univers des Fixes)。宇宙是通过不可思议的简化来起作用的,正如在瓦格纳和韦伯恩的三个声图一样,或者像贝尔格(Alban Berg)的十二音技法中的悬置一样,或者韦伯恩的异常重音一样,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自我呈现,如同一个与正式结构保持齐平的姿态,或者分离出一个基本元素的群组的包络(enveloppe)。它们之间的包络关系创造了感知的丰富性,并对感觉(sensibilité)和记忆保持警惕[9]。在梵泰蒂尔的乐章中,高音符保持了两个尺度,“就像一个声音的帘幕,隐藏了它潜伏的奥秘”,这就是大定在的例子。至于七重奏,梵泰蒂尔小姐的朋友需要写下这部作品的固定的标记。这就是普鲁斯特不由自主的角色,创造了定在的包络。
这绝不意味着不由自主的记忆,或定在,重构了同一性原则。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和福克纳一样,他们在文学中都消解了同一性原则的存在。即便在重复时,定在也不是由重复元素的同一性,而是由诸多元素的性质上的的共性来界定的,没有这种共性,就不能重复(例如,两个片段之间的著名的品味共性,或者在音乐中共同的音高……)。定在不是同一性,它并不能通过变奏之下的同一性来揭示。反过来才是对的。它容许了各个变奏之间的同一化,或者成为了没有同一性的个别化。这就是它如何拓展了感知:在条理化环境下,它让变奏变得可感,在光滑环境下分配了这些变奏。这并不是将差异带入到同一性之中,它只是让像这样的差异可以被同一化。于是,在普鲁斯特那里,作为两个片段之间的性质共性的品味认为贡布雷总是与自己相异。在音乐和文学里,重复与差异的功能性作用取代了同一性和变奏的有机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定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感知到的变奏或散播能持久永存,而是昙花一现。这些包络本身也不断地在单一的作品中,或在一个模块中,或一个气泡中让它们自己之间保持“运动的关系”。
康德的批判哲学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夏莹 牛子牛 译 吴子枫 校
出版社: 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12
拓展的感知意味着创造出力量,这些理论通常是感知不到的可感物,共鸣(或可见物)。当然,这些力量不一定是时间,但是这些力量会与时间的力量混杂并结合在一起。“时间并不总是可见的……”,我们很容易,通常也十分痛苦地在时间中感知事物。我们也感知到计时学的形式、单位和关系,但并没有将时间感知为一种力量,或感知到时间本身,感知不到“最纯粹形式下的时间”。以声音为媒介,可以让时间变得可感,让时间的数量变得可感,用物质材料来把握时间的力量,让时间的力量变成声音:这就是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计划。布列兹在新的条件(尤其是序列)推进了他的计划。但对于布列兹来说,音乐条件以一定的方式反映了普鲁斯特的文学条件:让时间的默然的力量发出声音。在进一步发展了在声音材料中运作的时间划分功能之后,音乐家把握了时间的力量,并让之变得可感。时间的力量和时间划分的功能一并形成了关联性时间(temps impliqué)的诸多方面。对于布列兹和普鲁斯特来说,这些方面是多,可以简单还原为“逝去-发现”(perdu-retrouvé)。这是逝去的时间,逝去的时间不是一个否定,而是时间的圆满的功能。对布列兹而言,声音的碎片化或者消逝是一个音色事件,音色的消逝,在这个意义上,音色就像爱一样,重复了它的结局,而不是它的起源。那么,有一个“重新-追寻的时间”,即绵延模块的形成,它们按照斜列运动:它们并不是(和谐)的和音,而是真正的贴身肉搏,通常是带有韵律的肉搏,声音或嗓音所垂青的是摔角手战胜对手,或被对手战胜的地方,就像在梵泰蒂尔的音乐中一样。这既是时间的条理化的力量。那么,有一种“重新获得”的时间,一种被识别的时间,但只有一刹那。这就是时间的“姿态”或定在的包络。最后是“乌托邦时间”,正如布列兹在向梅西安致敬时所说的那样:在穿透了数字,穿透了时间那魂系梦绕的巨大气泡的,面对光滑之后,再一次发现自己——按照普鲁斯特的分析,发现了人类“在时间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在空间汇总为他们保留的太过局促的位置”。或者毋宁是,当他们开始计算“一个没有尺度,反而延长的位置”[10]时,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在遭遇了普鲁斯特之后,布列兹创造了一组基础的哲学概念,这些概念都来自于他自己的音乐作品。
差异与重复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安靖 张子岳 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06
注 释
[1]Penser la musique aujourd'hui(PM), Ed. Gonthier, p. 107.
[2]Points de repère(PR), Ed. du Seuil-Bourgois, «le temps re-cherché », p. 236257.
[3]对于斜列和模块,可以参看Relevés d'apprenti (RA), Ed. du Seuil articles « Contrepoint» et «Webern ». Et PM, p. 137,59.
[4]Sur Wagner, PR, p. 243-246. Sur Webern, RA, p. 372, 376-377.
[5]参看La Pléiade, l,p. 655 (l'unité de la Recherche est toujours présentée comme une diagonale).
[6]对于切口、条理和光滑,可以参看《思考今天的音乐》(Penser la musique aujourd'hui)。似乎对我来说,戴德金(Dedekind)在非理性切口和理性切口之间的区分,已经罗素在距离和尺寸之间做出的区分,都对应于布列兹提出的光滑和条理化之间的区分。
[7]《思考今天的音乐》第48页:“另一方面,在序列体系中,没有函项(fonction)将自己表现为从一个序列到另一个序列的同一项……通过它们的位置关系的变化发展,由同一绝对元素组成的对象可以得出发散的函项”。
[8]《思考今天的音乐》第44页:“当到处都出现了切口,耳朵就会迷失所有的方向,对于间歇也没有任何知识,就像眼睛必须要在理想状态下的光滑表面上来判断距离一样”。
[9]参看这篇主要论文《音乐家的写作:聋子的目光?》(L'Ecriture du musicien: le regard du sourd?),载于《批判》(Critique)杂志n°408, 1981年5月号。论瓦格纳的标线,第249页(“固定元素”)。
[10]La Pléiade, III, p.1048. 普鲁斯特在时间的这个侧面和重新获得的时间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重新获得的时间是一个不同的侧面(论“乌托邦”,梅西安和布列兹)。
延伸阅读
德勒兹与音乐
文 / 薛 亮
在德勒兹看来, 音乐是最不受形式限制的艺术。德勒兹这样评价音乐, “音乐总能播放出逃亡的路线, 如同许多‘变化性繁殖’一样,甚至推翻给音乐以结构并使其块茎化的那些符码; 音乐形式, 乃至其断裂和多产之所以可以比作一棵野草、一个块茎, 其原因就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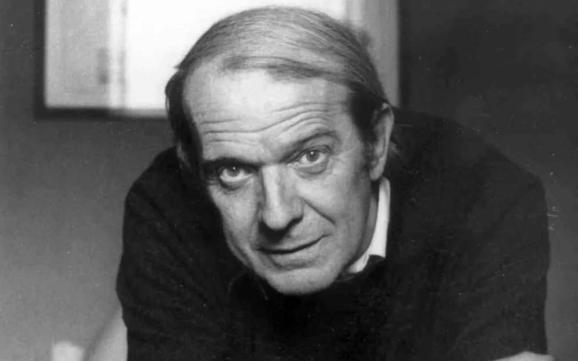
吉尔·德勒兹
吉尔·德勒兹, 一个法国人, 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当代哲学家。他从不忌讳称自己是哲学家, 在他眼中, 哲学永远是创造概念的。他说: “我从不曾关注形而上学的超越或哲学的死亡。哲学具有永远保持现实性、永远创造概念的功用。这一点是无可取代的。”即使在哲学史的研究方面, 他的态度也是那样鲜明: “哲学史不应该重复一个哲学家所说的, 而应该说出一个哲学家有必要省略的东西, 说出他没有说出却存在于他的言语之中的东西。”
德勒兹的著述看起来几乎都是一个片断一个片断的, 由分散在全书各个部分的、非连续性的精神闪光点构成。德勒兹的著述非常难读, 也非常耐读。很难说在读过几遍之后我们究竟读懂了多少, 残留在记忆中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 只言片语, 却似乎又胜于千言万语。德勒兹的哲学之于传统哲学, 正好像无调性音乐之于调性音乐一样。德勒兹注意到了奥地利的十二音位主义者们对音乐再现的解域。同样,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德勒兹对哲学传统的解域。也许德勒兹哲学给人启发的地方更多的在于一些细节, 而他对音乐的论述也散落在各个段落。
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杨洁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9
除了电影、文学之外, 音乐是德勒兹讨论得最多的艺术形式了。德勒兹在一次访谈中表达了哲学与音乐的某种联系: “音乐是否也是这样: 以哲学家为友呢? 我认为这是肯定的: 哲学是一首真正的无声的歌, 它没有歌的声响, 但是有着与音乐相同的运动感。”
1995年11月4日, 饱受病痛折磨的德勒兹从巴黎十七区的家里跳楼自杀。或许对于他来说,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等待死亡。有意思的是, 在致敬的送葬队伍中, 竟有一支先锋摇滚音乐人的小分队, 而两张向德勒兹致敬的CD合辑则预示着福柯所说的“德勒兹的时代”首先在音乐领域中到来。
音乐厂牌Sub Rosa首先推出了仅有五首作品的合辑Folds & Rhizomes: In Memoriam Gilles Deleuze。紧接着先锋德国实验/电子音乐厂牌Mille Plateaux (这个厂牌的得名直接来自于德勒兹的“千层高原”) 推出了集结了更多先锋音乐人的双CD合辑In Memoriam Gilles Deleuze。这一事件使德勒兹的哲学一下子成了先锋艺术领域新的应用哲学, 这显然得益于德勒兹与加塔里合作的《反俄狄浦斯》和《千层高原》的哲学文本充满着艺术各领域的启示性话语。

《褶子和块茎,纪念德勒兹》唱片封面
德勒兹和摇滚的结缘并不是摇滚音乐人的一厢情愿。作为哲学家, 德勒兹并不像阿多诺那样, 视野中只有古典音乐。我们惊奇地发现德勒兹有可能是位摇滚乐迷, 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到美国摇滚歌手帕蒂·史密斯 (Patti Smith)。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 德勒兹甚至这样诙谐地说: “讲课是一种‘诵唱’, 较之戏剧它更贴近音乐。或者说, 讲课有点像摇滚音乐会。”
福柯 褶子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于奇智 杨洁 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09
黑格尔的《美学》中有很大的篇幅论及音乐, 可他还是谦虚地把话说在前面, 表明自己对“声音的长短高低轻重的关系以及不同的乐器, 音质, 音阶等等之间的差别”不太熟悉, 所以“只能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观点和个别的看法”。同样, 德勒兹也只是作为一个音乐的聆听者。我们不能指望从德勒兹的音乐美学理论当中获得诸如《企鹅激光唱片指南》等等类似的实际指导意义, 但是, 一个哲学家的聆听必然有其独特处, 尤其是一个当代哲学家。我们可以注意到, 德勒兹对二十世纪音乐中的先锋派一直极为关注,行文中布列兹(Pierre Boulez)、约翰·凯奇、斯托克豪森等现代音乐代表人物出现频率很高。德勒兹要探究音乐的本质, 以及先锋派创作实践的意义, 歌颂音乐中的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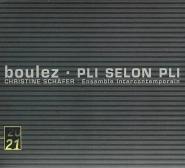
布列兹《重重皱褶》唱片封面
德勒兹关于音乐的论述主要见于《千层高原》和后来的《褶子》当中。《千层高原》中第十一高原“叠歌 (Of the Refrain)”是献给音乐的, 第十高原“生成强度, 生成动物, 生成无感知”也有相当大的篇幅论及音乐。德勒兹对叠歌的注意延续了其早年著作《差异与重复》中重复的概念。《差异与重复》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否定句, “重复不是一般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先锋派音乐家约翰·凯奇的一句话的类似性, “重复也是变化的一种形式”。在《千层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不把音乐按时间顺序分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个时代, 而试图按顺序将音乐分成混沌的力、大地的力和宇宙的力。而在《褶子》中, 德勒兹对照莱布尼茨以两个时钟的一致比较各种不同的灵魂与形体的概念 (或者是流数、或者是偶因、或者是和谐), 又将音乐分为三个“年龄段”, 即无伴奏齐唱阶段、复调或对位法阶段、呈和弦的和谐阶段 (巴洛克阶段)。德勒兹在一次访谈中一定程度地解释了这种变化:情感、感知和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三种力量, 他们从艺术走向哲学, 从哲学走向艺术。最困难的显然是音乐, 在《千层高原》中对此有初步分析: 间奏导致这三种力量。我们试图使间奏成为我们的主要概念之一, 有小间奏和大间奏, 这同领土与地球相称。总之所有三个阶段都在连绵延伸, 相互混合, 在现在这本关于莱布尼茨或者关于褶皱的著作(即《褶子》)中, 我对此看得更加清楚。
什么是哲学?
作者: 吉尔·德勒兹 菲力克斯·迦塔利 著 张祖建 译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07
的确, 相对于《千层高原》的不确定性,《褶子》较为系统地论及了巴洛克音乐。德勒兹指出莱布尼茨和巴洛克音乐同时将和谐变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在十八世纪上半叶音乐美学中以“激情论”为代表的他律美学盛行时, 莱布尼茨从构成音乐的形式角度探讨了音乐的本质, 把数学和音乐的本质和内容联系起来。他指出, “音乐, 就它的基础来说, 是数学的; 就它的表现来说, 是直觉的”, 他更进一步地提出, “音乐是心灵的算术练习, 心灵在听音乐时计算着自己而不自知”。这种自律美学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斯宾诺莎在其《知性改进论》中提到: “……刺激听觉的东西, 我们则说它产生噪音、乐音或和声, 和声特别使人入迷到相信神也喜欢它。甚至还有些哲学家居然确信天体的运动组成了一种和声。这一切都充分表明, 每一个人都是凭自己的头脑结构来判断事物, 也可以说都是把想象力的感受当作事物。”这段话里讽刺的“有些哲学家”就是指毕达哥拉斯学派。奇怪的是, 德勒兹同时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推崇备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巴罗克音乐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考量, 我想德勒兹除了对现代音乐保持关注之外, 一定也为以巴赫为代表的巴罗克音乐所吸引。很明显, 作为创造概念的大师 ,德勒兹的哲学史研究视野里不会少了经常制造奇特概念的莱布尼茨。德勒兹注意到莱布尼茨和巴罗克音乐的某种联系, 一种基于数学对音乐、建筑的审视。相对于在《千层高原》音乐论述的零散和对先锋音乐创作的关注, 在《褶子》中德勒兹将视野转向历史, 更多考虑到的是音乐中的一种和谐。
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董强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1-07
德勒兹在《根茎》中称颂“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威廉·巴罗斯 (William Burrough) 的艺术美学——切碎和拼贴, 指出: “把一个文本叠在另一个文本之上, 构成了繁殖的、甚至是偶生的根, 这是对所论文本的根的一个补充。在这个折叠的补充维度里, 整体继续从事精神的劳作。” 威廉·巴罗斯的切碎和拼贴最早被其用于小说创作, 后来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被先锋音乐创作所吸收, 成为现代电子音乐创作最常用的手段。威廉·巴罗斯曾经鼓吹过如下宣言式的口号, “任何人, 只要有一把剪刀就能成为诗人”。对于音乐这种形式就是一切的艺术类型而言, 切碎和拼贴也许最为合适。被音乐家运用得越来越娴熟的采样和混音推动着电子音乐的发展, 从Brain Eno提出的Ambient音乐概念到纽约Dj Spooky的病场 (Illbient) 音乐的反拨。Dj Spooky在做音乐之前的专业是法国文学和哲学, 其音乐实践理论很明显地延续了威廉·巴罗斯和德勒兹开辟的道路, 他甚至在其专辑内写道: “混音: 不同意义的交融, 其以前的涵义被圈进了一个空间, 在其中它们被予以处理, 让其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的不同在电子拓扑存在的当下界域之中消逝。”
德勒兹指出钢琴家古尔德 (Glenn Gould) 演奏时的加快速度, 并非仅仅在炫技, 而是在把音乐的点变成线, 达到无限的繁殖。音乐的演绎是重要的, 躺在乐谱上并不是音乐本身。在记录某些现代音乐时, 传统记谱法已经完全失效, 只能直接纪录在磁带上。演绎之所以重要, 我想它代表着一种复活机制。在这一点,我们似乎又可以回到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论述上去了。德勒兹注意到极简派音乐 (Minimal Music), “形式被纯粹的速度变化取代了”, 这也是一种创造。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摇滚乐中, 金属乐乐器演奏速度的越来越快, 直接导致了激流金属和死亡金属乐派的诞生。纯粹的技术主义也可以催生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艺术摇滚中的激进主义流派E.L.P.乐队在现场就曾把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上的图画》完整地用电声乐器演奏了一遍, 这同样也是一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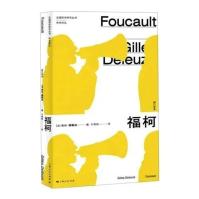
福柯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于奇智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3
在德勒兹看来, 音乐是最不受形式限制的艺术。德勒兹这样评价音乐: “音乐总能播放出逃亡的路线, 如同许多‘变化性繁殖’一样, 甚至推翻给音乐以结构并使其块茎化的那些符码; 音乐形式, 乃至其断裂和多产之所以可以比作一棵野草、一个块茎, 其原因就在于此。”德勒兹敏锐地察觉到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突破的无限可能性。无须多言, 我们可以目睹在二十世纪调性音乐的瓦解, 音乐流派的无限膨胀。
在德勒兹的哲学文本中, 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对布列兹 (Pierre Boulez) 现代音乐美学的引用也很频繁。许多人在听无调性音乐时, 觉得每首都大同小异, 布列兹在一次访谈中做出了回应, 他引述了俄国五人团代表人物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Rimsky Korsakov) 的一句话: “习惯了就好。”德勒兹认为, “音乐家最有资格说: ‘我痛恨记忆功能, 我痛恨记忆。’”那是因为音乐家承认了生成的力量。

布列兹带领声学与音乐研究所(IRCAM)团队参加计算机音乐课
布列兹在科隆有过类似的一长段话:
传统的确存在, 你接受传统教育之后, 我喜欢这样来比喻, 连你的基因都会变得“很传统”, 但千万不要让你成为一座图书馆, 更不要让这座图书馆来瓦解你。因此你与传统应保持的关系是充满弹性与活力, 而不是沉闷、死板的。我们身前是座收藏雄伟庞大的图书馆, 一座资源丰富的音乐图书馆, 从中我们得以了解自十三世纪迄今的音乐。其实这是一种负担, 当吸收太多、模仿太多时, 你就很难再做自己。 因为你脑子里容着的都是别人的东西, 因此我们的不时去“烧毁”这些东西, 好比凤凰鸟浴火重生一般, 让自己不带记忆的再生一次。我认为克利 (Klee) 他就做得到, 克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哪天生下来可以没有知识束缚该多棒!”。这里“没有知识的束缚”, 我指的是“没有过去经验的记忆包袱”, 但问题就在这, 当你每天尝试着去改变既有的世界时, 你什么事也没有完成, 因为你所做的, 前人早就做好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除了要意识过去的存在外, 同时又要不受过去的束缚而失去自由。
德勒兹论福柯
作者: [法]吉尔·德勒兹 著 杨凯麟 译
出版社: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03
也许, 说来说去, 德勒兹思考得最多的还是音乐的本质。德勒兹在看德彪西的《佩里亚斯和梅丽桑德》时, 注意到了“作为一个孩子——女人, 一个秘密, 梅丽桑德死了两次”。德彪西的《佩里亚斯和梅丽桑德》改编自象征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的作品。我们在看《佩里亚斯和梅丽桑德》这部歌剧时, 很容易联想到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梅丽桑德和伊索尔德这两个女人的死法反映了德彪西和瓦格纳旨趣相异的美学追求。死了两次的梅丽桑德使这出戏剧少了瓦格纳歌剧那种矫揉造作的悲剧性。所以德勒兹认为: “音乐从来就不是悲剧性的; 音乐是欢乐。但是, 有时候, 它必然要使我们体会到死亡; 体会到湮灭, 因此不是欢乐之死的那种幸福。”德勒兹在叠歌中找到音乐之根的一种形式。一个孩子在黑暗中为了安抚恐惧的心灵, 唱出令人心安的调子, 也许这就是最初的音乐。我到现在还记得, 高中时偶尔在杂志上翻到一个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小女孩的诗Slow Dance中的一句话, “Hear the Music before the song is over.”。德勒兹在解读尼采时说, “实际上虚无主义是被击败了, 但是被它自身击败的。”我想音乐也许是作为对抗虚无主义而存在的, 可它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
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2016),法国著名现代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以善于准确清晰地诠释20世纪音乐而著称,较为出名的作品包括:《没有主人的琴锤》(Le Marteau sans Maitre)(1955年),《爆炸-固定》(Explosantel-fixe)(1973年)。和《仪式》(1975年)等先锋音乐。。布列兹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拜梅西安为师学习和声,随莱博维茨学十二音技法,随奥涅格的妻子沃拉布尔学对位。布列兹在指挥中强调节奏的魅力,强调现代作品在节奏中呈现的色彩感,也强调音响效果。他演绎的他自己的作品、梅西安、巴托克、贝尔格的作品,都堪称为权威。而他最辉煌的成就,应该说是1976年在拜罗伊特指挥《尼伯龙根的指环》百年纪念演出,对这部宏大史诗给予了全新的现代性解释。1995年,他被任命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家,曾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和柏林交响乐团等世界著名交响乐团合作。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u, 1925.1.18-1995.11.4),20世纪60年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的哲学围绕一系列以“差异”为基调、蕴涵原创性的概念、充满思想的多样性。他所涉猎与影响的领域遍及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精神分析、语言学习及电影评论、绘画和戏剧,代表作有《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反俄狄浦斯》《何谓哲学》等。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