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迈克尔·罗兰:世界文化图景下的物质性、博物馆与人类学
访谈+撰文 _ 张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罗攀(中国民族博物馆)

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
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是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与物质文化系的荣休教授,以及《物质文化研究》《人类学评论》的编委。2006年以来,他多次赴北京、泉州、成都、贵阳、大理等地举办讲座,参加会议。2016年,他的14篇讲座与访谈结集为《历史、物质性与遗产》一书,以中文出版。罗兰教授一直关注中国的博物馆与遗产现象,并就中国的遗产观念及民间博物馆实践发表过文章论述。此次对话从人类学学科与博物馆的渊源展开,继而探讨人类学视角能为我们思考博物馆带来怎样的启迪。
您认为,当前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如何看待人类学与博物馆在中国的关系?
迈克尔 · 罗兰:在中国,人类学和博物馆的关系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我认为这与其在欧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二者的重点似乎都可以被视为保护物质知识(material knowledge),而不仅仅是收藏物品本身。
管理和保存正在消失的物质知识非常重要,这种抢救式的民族学工作似乎是中国的博物馆与人类学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博物馆繁荣之前便是如此。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曾经参与培训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第一批从业者。实际上,这并不是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时学到的东西。我想,对他而言,这延续的是欧洲民族志收藏的一个普遍原则,他会特别关注来自欧洲的经验,也许特别是德语传统中 volkskunde 与 volkenkunde,即“民俗学”与“民族学”的区分。
人类学有责任来管理和保存边缘或濒危的文化和物质知识,而这与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的使命是一致的。我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人类学从未离开过民族志收藏,而这些民族志藏品对博物馆极其重要。

历史、物质性与遗产
[英]迈克尔·罗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博物馆热潮?人类学能如何参与其中?
迈克尔 · 罗兰:你们一定比我更清楚。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21年蔡元培的一篇演讲,这个想法后来在中国的人类学界深深扎根。而在欧洲,人类学与博物馆经历了长期的分离,直到最近它们才开始重新走到一起。我认为这是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当前中国博物馆的蓬勃发展确实对人类学提出了挑战。因为眼下的繁荣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国家主导的博物馆建设。因此,对于人类学者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人类学如何保持对地方、遗产和博物馆的关注。
在国家主导博物馆建设的时代,人类学要发挥作用,必须首先认清自己在当下情况中的定位。目前,当任何地方需要筹建一个重要的博物馆时,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说,“我们必须和人类学家谈谈”,或者“必须有一个人类学家参与”。他们更有可能谈到需要一个设计师,或向营销和旅游方面的专家咨询。
那么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如何为自己申辩,让人们理解人类学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强调人类学与文化营销、旅游不同,它侧重于通过对某个地方的历史与地方性知识的把握,赋予博物馆以意义。
我认为有必要问:当提到人类学时,公众会有怎样的期待?中国对于人类学的普遍观感(popular perception)是怎样的?人类学是什么,能做什么?人们对其了解多少?人类学是对异域或民族风情的研究,还是关于地方的、草根的身份和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是研究域外文明的吗?可以让我们了解非洲、欧洲或太平洋地区吗?
我们可能要跳出中国的视野,看到如今的人类学博物馆已经基本完成了向“世界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转型。这是一种全球观念,我指的并不是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全球化,而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全球观念,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都处于 “世界文化”这个概念中的不同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贡献。
您曾长期在非洲进行博物馆及文化遗产研究,能否谈谈其与今天中国的博物馆建设之间的共性和区别?
迈克尔 · 罗兰:在过去的几年里,非洲的确也出现了博物馆热潮,但主要围绕藏品归还和赔偿问题。在非洲,博物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去殖民化,即与殖民历史撇清关系。这就涉及如何处理殖民时代欧洲人在非洲留下的博物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殖民者在此建造博物馆,为的是在殖民主义终结以后能够留下一些东西。因此,非洲正在经历的博物馆热潮,关键在于“立新”。在非洲,人类学尚未像在中国一样形成一种本土的学术语言和传统,而仍然与欧洲殖民主义直接挂钩,因此处境更为艰难。现在,非洲博物馆的任务是让欧洲的博物馆将那些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收集的藏品归还给非洲,以“重建”非洲文化。围绕欧洲博物馆与这些新的非洲博物馆究竟该如何合作,双方正争论不休。

大英博物馆非洲展厅。图源:大英博物馆官网
回到刚才说到的全球或世界文化概念,我认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如今都需要将自己视为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人类学在博物馆中的作用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一种全球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现象。任何地区或国家彼此都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非洲与中国如此不同,因为中国博物馆有自己的历史,而非洲博物馆需要与欧洲博物馆建立或保持一种关系。对中国来讲,更关键的可能是延续“天下”的视野,比如中国的博物馆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博物馆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何共同点和差异?我们该如何从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文化概念的框架中去理解这种关系?
您怎么看人类学的“物质转向”以及跨物种的民族志?在某种意义上,您认为人类学在博物馆的复兴与上述转向有关吗?这可能给我们理解人类学博物馆与民族志收藏带来什么启发?
迈克尔 · 罗兰:是的,这个被称为“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的思潮一直围绕着解决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作为一个理论领域发祥于20世纪80年代,与布鲁诺 · 拉图尔(Bruno Latour)代表的新唯物主义思想几乎同时出现,二者都关注物质的能动性以及客体如何建构主体,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或人去创造物或者使用物,而是实际的物质世界和物质文化塑造主体(即人)。80年代以来,物质文化研究开始对人类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人类学家总是将自己视为主体,然后另有一个民族志对象,而新唯物主义和物质文化研究则关注物体如何构建主体,或物质如何塑造主体及其身份。这也使人类学对待博物馆和收藏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过去,人类学家面对博物馆中大量的物质文化收藏而无从下手。我们是否只能去做更多的田野调查?还是可以反过来,从藏品本身的物质性着手,了解它们如何能够构建人?换言之,我们可以思考:这些物,即便作为陈旧的藏品,对现在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就如同我们说遗产可以创造现在或者未来,当人们走进博物馆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眼前所见所感的那种物质体验所塑造的?
博物馆和物质体验如何塑造观众?我们如何理解博物馆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可以塑造其主体(即观众)?是因为这个博物馆及其藏品存在,它的观众才存在。过去,博物馆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总是围绕如何征藏、如何阐释、藏品如何登账保存,都是关于人对物做了什么,藏品变成了需要处理与保存的“死物”。而今,博物馆本身的意义也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博物馆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的力量。因为博物馆本身创造了一个世界,观众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艺术博物馆,有人可能认为,不了解艺术家,就无法了解艺术品。我想,其实未必。艺术品本身会让人们去观看,并做出反应。倘若没有在艺术博物馆里看到那件作品,观者便无法获得这些体验。

大英博物馆藏品伊夫头像(The Ife Head),尼日利亚,非洲,14 - 15世纪。图源:大英博物馆官网
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博物馆也可以算是一种艺术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两个概念不断相互影响。哈尔 · 福斯特(Hal Foster)在他的名篇《作为民族志学者的艺术家》中提出,当代艺术界出现了“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同样,人类学博物馆越是用接近于艺术博物馆的方式进行陈列,观众的反响似乎越强烈。这意味着物质文化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显然对人类学产生了影响。不过当然,物质文化转向并非人类学所独有,美学、艺术、文化研究等领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讨论,并聚焦于物如何构建不同的主体、身份及世界。这是一个广泛而影响深远的现象,而人类学可以借此重新思考物品、收藏及博物馆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人类学正因此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同样,其他社会科学也需要回应这种针对物质性的态度的转变,将物质(substance)或事物(thing)放在人与非人,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看待,这跟所谓“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所处理的文化—自然二分关系也息息相关。
您提到了博物馆观众与艺术品之间主客体视角的转换,物的能动性这种视角如何启发当前的人类学博物馆实践?
迈克尔 · 罗兰:一直以来,展示民族志藏品是为了传达关于某个族群或某种文化的人类学知识。人类学家通过陈列服饰或日常用品来展示和解读某种生活方式,这种解读完全建立在人类学家的主体性之上:“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族群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吧,因为这些是他们代表性的物品。”观众立刻就睡着了。
如果反过来,将这些藏品的美学、色彩、意象以及物质性和图像学特征等一股脑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单纯的审美体验会带给他们一种强烈的震撼。好的艺术家都是这么做的:让观众在艺术品面前大吃一惊,不知所措,进而思考“我在看什么?我该如何理解眼前这些不同的媒介、形式和材料的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观众被这样一次审美经验塑造了。参观结束以后,他们也许感觉受到触动,情绪起伏,但不太确定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这里,主客体之间的整个关系真的有可能翻转。很明显,这些物体和它们的形式具有不同寻常的创造力。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不能一起工作,一起创作,人类学博物馆也的确可以变得更接近艺术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艺术品生命之树(Tree of Life),莫桑比克,2004年,由莫桑比克内战后上缴的枪支雕塑而成。图源:大英博物馆官网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必须区分艺术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将纯粹的人类学博物馆概念融入一个更广泛的、美学意义上的博物馆语境中,因为民族学藏品本身就足以给人以触动与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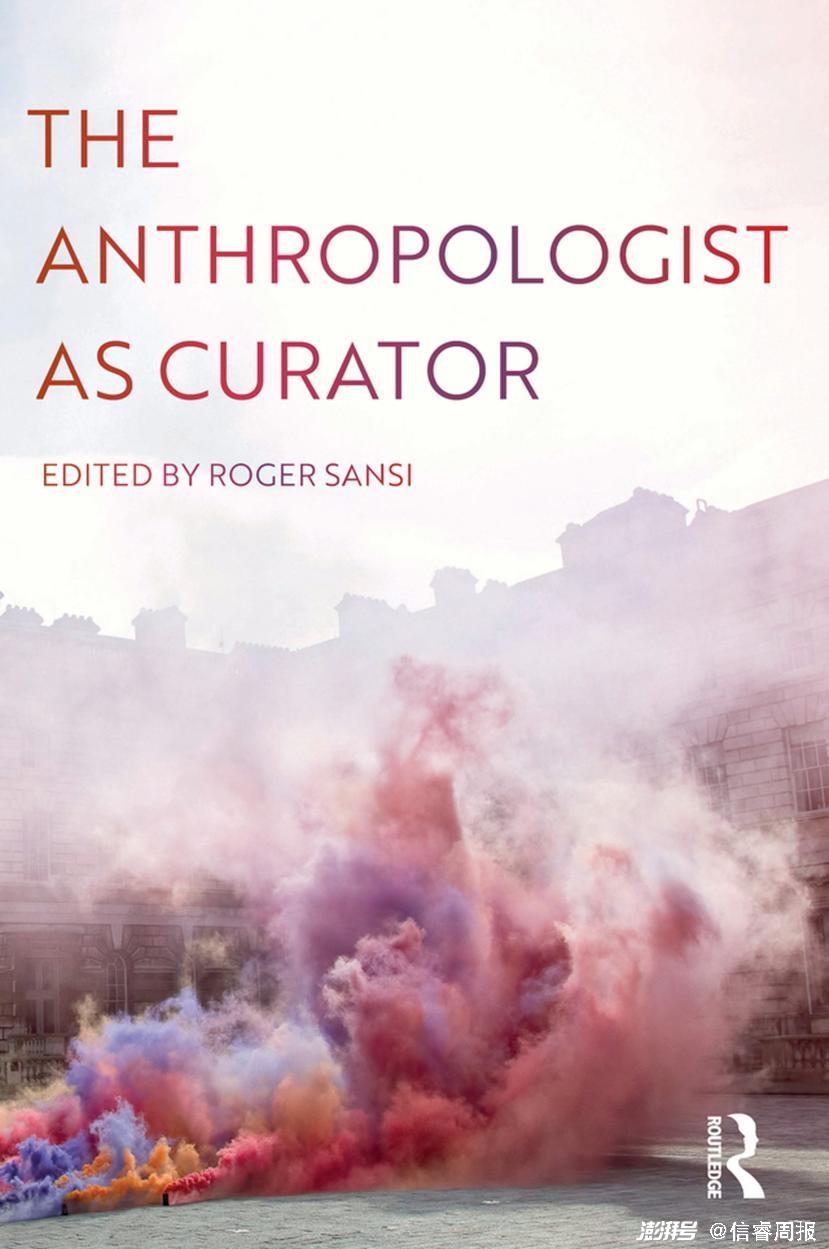
The Anthropologist as Curator
Roger Sansi (ed.)
Routledge
有趣的是,人类学家的博物馆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储藏室,一个资料库,一个满是东西的房间,只有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够进去使用那些材料。后来,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需要将藏品通过一种通俗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展览,让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也能理解。这便是叙事的作用。清晰、线性的叙事线,往往传达着简单明了的信息。而您提到的艺术博物馆所做的,恰恰是让艺术品或藏品摆脱这种目的性的叙事,从而将其本身呈现给观众。有意思的是,对我来说,这似乎回归了人类学家博物馆的原型,一个充满物的房间。
迈克尔 · 罗兰:这就类似于在英国,很多人喜欢牛津大学的皮特里斯博物馆(Pitt-Rivers Museum),因为那里完整地保留了19 世纪最初创建时的陈列。在早期的人类学理念之下,所有的藏品都被杂乱地摆放在玻璃柜中,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在那里,你能看到食人族的物件、人头骨、有毒的箭头以及各种恐怖的面具等。而当我去大英博物馆时,展览井井有条,清楚地告诉我我应获得的信息是什么。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叙事,一个故事,我是在接受教育,就像在学校里上课一样。


牛津大学皮特里斯博物馆(Pitt-Rivers Museum)。图源:皮特里斯博物馆官网
但若你问我最喜欢大英博物馆还是皮特里斯博物馆,我选择后者。我想很多人会认同,因为皮特里斯博物馆给我的冲击更大。当然,皮特里斯博物馆也会定期举办小的临时展览,带有明确的结构和叙事,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某些特定的议题,但皮特里斯博物馆的其他部分对我来说更令人兴奋。
这里隐含着一种矛盾。19世纪,欧洲很多博物馆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把荒蛮之地的物件带回欧洲。人类学家去非洲寻找野生动物、野蛮人,把他们带到欧洲,进行展览。就像毕加索,当他被问到是否想了解启发自己灵感的那些非洲面具都有何含义时,他拒绝了:不,我对理解语境毫无兴趣,我只是对面具感兴趣,对这些充满暴力的形象感兴趣,然后将其融入我自己的创作。一次参观艺术品的震撼和冲击,如何能使人脱离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让人通过接触艺术,产生一些新问题和新的思考,这正是艺术家所期望的。
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涉及博物馆的功能问题。博物馆拥有文化遗产和收藏品,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存在那里。而博物馆只是不停地用它们讲故事,试图教育人们,但观众也许并不想听。如果反过来,去关注这些物体如何能真正给人们带来冲击和思考,也许情况会不一样。
那些民族志藏品本身就很有力量。它们通常是静默的,而如果展览布置恰当,就可以相当令人震撼。比如那些面具、仪式用品,那些我们并不熟识的生产生活用具,注视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如此大的冲击力。即便最简单的锅具都有物质性。事实上,物质本身塑造了你的手指、双手,让它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比如制陶者,他们的手、手指、使用手臂的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再比如音乐家,音乐会完全改变人,人们经年累月地学习长笛,演奏行为也完全改变了人们。

大英博物馆与乌昆 · 万安比(Wukun Wanambi)合作展览。图源:大英博物馆官网
或许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博物馆可以将藏品交给如格雷森 · 佩里(Grayson Perry)这样的艺术家,邀请他们利用藏品进行任意创作,结果往往会以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打动观众。大英博物馆也与像乌昆 · 万安比(Wukun Wanambi)这样的当代艺术家合作过。在非洲、大洋洲展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与过去的民族志藏品一同陈列。不过问题又来了。这样的合作似乎仅限于非洲和大洋洲,其他古文明(比如埃及、中国、印度等)则不行,因为这些文明太严肃和重要了,决不允许这样“乱来”。我倒认为,与当代艺术并置是对民族志藏品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人类学博物馆这个概念的一种解放,或许展示古代文明正需要一点这样的天马行空。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4期,原标题为《世界文化图景下的物质性、博物馆与人类学——专访迈克尔·罗兰》)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