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54岁中国迪斯科女皇,嗲炸
原创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张蔷今年54岁,是3个孩子的妈妈,
但疫情这两年,也完全没有歇着,
出了11张新专辑,上新潮的音乐节,
1年跑了9个城市唱livehouse现场,
今年还参加了《乘风破浪》第三季,
斩获不少00后的粉丝:
“想不到音乐最潮的是年纪最大的蔷姐姐。”
用网友的话说,她的履历是“嗲炸天”的:
17岁,成为全中国最红的女歌星;
19岁,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20岁,正当大红大紫时,
她却突然不玩了,选择出国留学;
回来后又结婚生子,退出歌坛;
2013年,在退出歌坛20多年后,
又重新杀回音乐圈,
以迪斯科女王的身份火出圈。
今年6月的上旬,
她仍然住在浪姐的宿舍里,
身上还别着麦克风,准备着第二天的比赛,
在睡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她的声音听上去并不疲惫,
反而很chill(放松),
“自己要开心,才能给大家带去美好的东西。
快乐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
自述:张蔷
编辑:陈星
责编:倪楚娇


▲
在浪姐舞台上的张蔷
之前只是在网上看到浪姐的片段,没有整一季看,因为我不是太懂真人秀。
浪姐第二季邀请了我,但是到第三季,我们感受到诚意,才来参加。
过去我跟我的家里人和团队全员,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
我录了两首歌就可以睡觉休息,演出上台呈现就完了,有时候,连走路都不用我操心,他们都让我不操心不受累,事事安排得很周到。
我们团队的人每天哄我,跟上学下学一样,特别好玩。
我怀着一种上完舞台就走的心态,但是不行,在浪姐的节目组里,有1200多个工作人员,人家是真人秀。
我肯定是感受到压力了,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集体生活,要跟姐姐们一起住宿舍。比如要早起,还要冷不丁地跟小学生一样训练,每天还得练跳舞,还不让睡觉(笑)。
每次公演的那天是最遭罪的,前一天只睡3个小时。回到宿舍,洗漱之后倒头就睡了。我们起得很早,8点就要化好妆准备出发了。
我上浪姐,第一首歌就选的是《630 Affection in my eyes》。这首歌出自2020年出的《我是张蔷 My name is rose》专辑。
630,是重庆的18:30新闻。在重庆,所有人都会看那档新闻,我写词的时候,就把重庆的夜景写进去了。
大家下班了,城市的灯火都亮了起来,就像天使降临了一样。
每个人在夜色里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他们认为此刻的自己是谁?
浪姐的舞台对于电子音乐,是比较陌生的,我觉得这首歌能抓住人的心,因为它的节奏很强,萨克斯表现力很强。

▲
张蔷与组员在后台训练,她直言“瘦了一圈”
我刚“浪”起来的时候,都像减肥了,我瘦了一圈。
但现在慢慢习惯了。我觉得我能搞定,我的舞台没有问题。
我是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个姐姐,但是她们没拿我当年龄大的人,我也没拿她们当年龄小的人,因为我的样子不像老气横秋的上一代。
我第一眼看唐诗逸,就觉得眼缘特别好,我女儿也喜欢她。如果我再选,我会选唐来做队长,她给人感觉特别温和,会照顾大家的情绪。
像是齐溪,就是我寝室的邻居,我们常在院里聚会,我们还约好了之后在北京见面。
对于会不会赢,我是走一步说一步,对未来没有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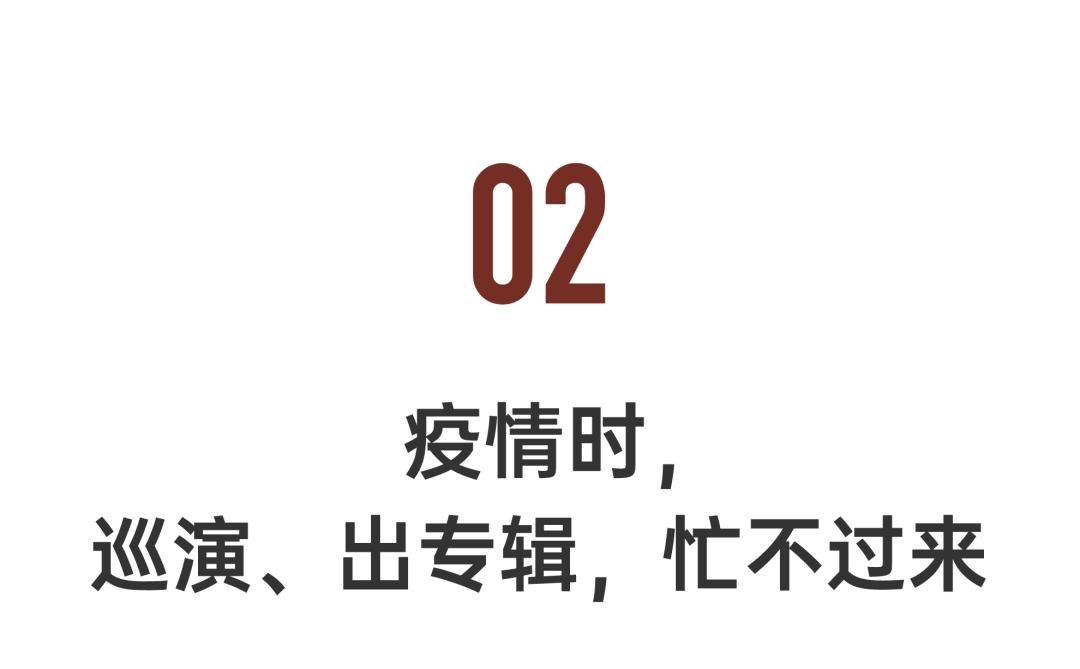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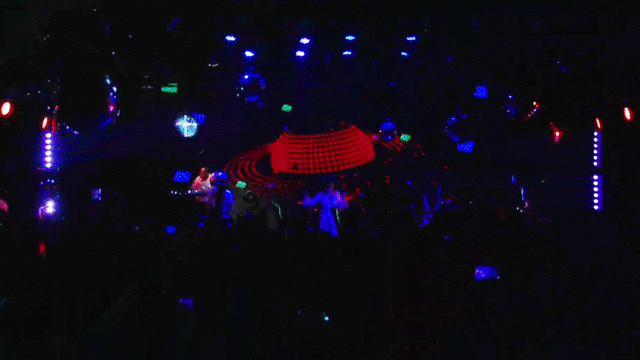

▲
去年,张蔷参加9个城市巡演,都完美避过疫情
我在中国流行歌坛比较早出道。80年代发了很多专辑,基本上全中国,除了广东,都在流行着我发的磁带。
我今年54岁,3个孩子的妈,还在唱呢。疫情期间,出专辑、巡演,我都忙不过来。
去年一年,我跑了9个城市,一站接一站地巡演,都完美避过疫情,现在想起来挺神奇的。
印象很深是在特热的青岛,现场特别热闹,让我感觉乐手的汗,都能甩到我的手臂上。
2019年到2022年,我出了11张专辑,有一半都是我自己原创的。新写的音乐风格是电子音乐和爵士黑炮儿风格。
黑炮风格,是我早年就喜欢的,它是有旋律性的音乐,不喜欢自己哼哼唧唧那种,光有节奏的。我觉得有旋律才属于中国人的情感。
2020年的《我是张蔷 My name is rose》专辑,是我近年最喜欢的一张。我把自己的经历都写进歌里。
《肆两is it time to say goodnight》是写给我妈的。我很想念她,“春天有了旋律,夏天写给你,秋天有了旋律,冬天写给你”,有一种后置的悲伤。我写完之后,我的吉他手很感动,就哭了。
《不能停止的爱I can’t stop》这首歌,节奏特有劲,滴滴答答的。这种劲儿是来自于爱情,让心底里特别有力量的感觉。旋律能让我爱上一个人,所以我写了歌词,爱是不会停止的。
《过石门River of Jialing》写的是重庆的石门大桥。我经过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钓鱼,小船漂浮。阴雨天的时候,涨潮落潮,能看到江边的大磐石。我就想象自己是一个鸟,飞在桥上,飞到云上。
我一直很喜欢写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坐在我自己的一个屋里,没有任何人打扰,我大概15分钟就能写出来。
这3年,我在思考一个事情,怎么才能让中国的流行音乐跟世界接轨。过去外国人听我们中国歌手的歌,都听不懂。我给他们听过,他们就说像印度歌,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很好听,但你不会经常去听。
现在世界都是相通的,让新一代人欣赏你,必须有一些新的元素进来。
于是有2张专辑,我跟国外的音乐人合作,一张是跟瑞士的摇滚乐队Stevans,一张是跟英国的混音师合作。他们给了我许多新的想法,有些迪斯科音乐,混合踢踏舞风格,还有电子乐,都加进来了。
过去我经常唱高音,大家说我的声音像唢呐,现在我用低音唱歌,就像交响乐里的竖琴。我觉得人处于开放的状态,做出来的歌才好听。


▲
张蔷和母亲
我出生在北京,妈妈是一个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
父母在我6岁时分开了,我就跟妈妈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宿舍里住。
妈妈一直都是最新潮的。小学时候我敢穿睡衣去上学,我妈给我做了一身都是绒的衣服,全是古代铜钱的布料,穿起来像睡衣一样。
头发也用火钳卷起来,有点像外国人一样。
当时乐团宿舍,整栋楼里住的都是新潮的年轻人,一起床,就能听到吹拉弹唱。
我就跟着他们,从小接触西方音乐,从俄罗斯音乐到歌剧等等。

▲
张蔷的卷发是母亲烫的
小学五年级,开始真正接触流行音乐。西方的像约翰·丹佛、迈克尔·杰克逊,虽然不明白在唱什么,但就觉得好听,就老听。
有年冬天放学回家,我听到一首贝斯开头的歌,那旋律太好听了,直接脱下毛衣在家跳起舞来。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比莉·珍》(Billie Jean)。
后来,邓丽君、张帝的歌进来了,以前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流行歌,开始被接纳。
那会儿我已经是海淀区的中学生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成了中国第一批迷流行音乐的人。那时特别喜欢凤飞飞,还有欧阳菲菲。

▲
80年代的张蔷,已经非常新潮
我的人生路线,原本是从职高毕业后,做一名幼教。
但后来我在唱歌中找到了一种快乐,有了做歌手的想法,就找各种机会去试。
那时东方歌舞团最火,但得有关系才能进,没去成。后来参加过海淀区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也去过“走穴”演出。
80年代时,中国老百姓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那种大杂拌表演形式。
走穴一般是上东北,我还跟刘晓庆去过武汉,那时还常碰到蒋大为、孙国庆、丁武……
路上就坐绿皮火车去,记得我有次穿了双黑色的丝袜,同车厢的大爷问,你穿的是什么,像一腿的毛。
那时常唱的有《伤心的电影》、《请到天涯海角来》,台下得有上千人,年轻人都喜欢。
最后一场是在石家庄体育馆,等我唱的那天,晚上的时候不是有迪斯科球吗,还有蓝色的光,折射出来满场都是星星点点,特别漂亮,又挺浪漫的。
好多观众就把钱币拿出来这样弹,整个场上银亮亮的,就跟下的银色的雨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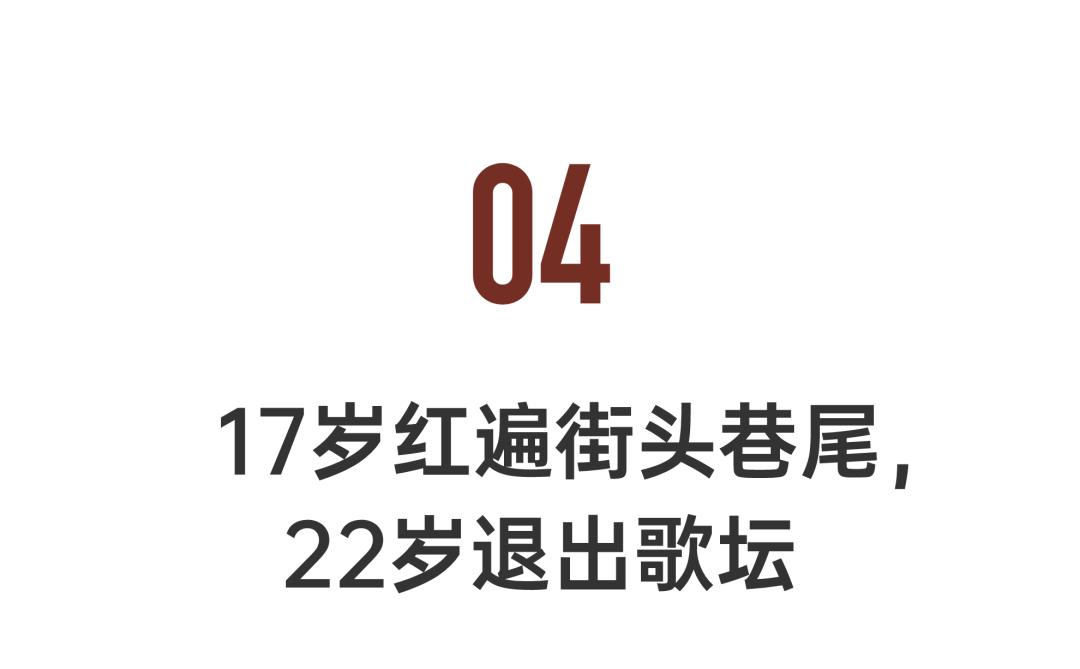

▲
18岁的张蔷已红遍中国
17岁时,我差点成了当时的“万元户”。
1984年,那会儿云南声像来北京挑歌手,我清唱了一首《伤心的电影》寄过去,第三天对方就来信了,让我准备过去录音。
当时我觉得学校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就主动辍学了,去云南。
在那待了半个月,录了两张专辑。一个《东京之夜》,还有一个是《害羞的女孩》。
那时候都还没有版权意识,就是翻唱,谁都可以唱谁的歌,我就争取自己来选曲目。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最新的多轨录音棚,录音还把整个中央歌舞团的电子乐队都拉过去了。
先录鼓然后再进键盘,然后再进号,然后吉他、贝斯,最后都合成完了,我进去再唱。
发行量当时我是绝对不知道的。

▲
张蔷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
后来听人说,《东京之夜》起初是60万张,后来加印到250万张,很多经销商直接拿着现金在印厂门口等。
录之前,我跟云南音像的老板谈好是一张唱片分我1400块钱。等我唱完,他说再多录一张,两张一共给我9000块。那会儿不是万元户是最受人崇拜的吗?
当时好多外国媒体过来采访我,最早有一个《南华早报》的记者,之后就不断地有什么《时代》周刊,意大利共产党报,包括还有什么《太阳报》。
他们通常会问你,一张专辑能挣多少钱?你现在为什么还住在这样的地方,跟大家用一个公共厕所?

▲
张蔷登上《时代》周刊
当时我的价钱不断攀升,我其实知道自己挺红的,但确实没什么感觉。
我挺平静地待在家里,周围的邻居就跟什么没有发生过一样。那时也没有粉丝或媒体像现在似的,这样追捧一个明星。
80年代,人相对是简单重感情的。我唱歌就是唱得直接,快乐。
1987年的4月,我出国去了澳洲。离开的时候,应该是最红的时候,也是最烦恼的时候。

▲
2年间,张蔷发行了19张专辑
1985、1986年那2年里,我发了19张专辑。当时的状态,不忙碌,就是闲散,还有烦。
那会在国家大剧院的录音室,我一个月包4张专辑,最不满意的就那四个,拿出去瑕疵太多了。编曲不能做到你的心里,编曲糟糕,我唱得也会糟糕。
当时给我制作的人都是搞民乐的。我说,你这是迪斯科吗?怎么唱得那么别扭?我说太难听了你编的。

▲
张蔷在录音室

▲
张蔷在澳洲留学
我从小听海量的外国歌曲,经常买打口带。还有国外的亲戚和朋友,或者我妈妈乐团那些乐手,他们会提供给我很多外界接触不到的东西,我有自己对音乐的审美。
不了解流行音乐的人,不懂迪斯科的人,在那重新演绎迪斯科是另一种感觉。
于是,我自己交学费,自己担保,去了澳大利亚的珀斯。
平时除了上课,就继续通过电台,听所有的世界上新推出来的流行音乐。
1988年就回来了。回国之后我就结婚、生了孩子,基本上退出歌坛。


▲
张蔷作为迪斯科女王,强势回归
迪斯科是快乐的,有一天乐一天那种心态,我也属于这样。
平时我不喜欢化妆,几乎都是素颜。但一上舞台,复古迪斯科风就都回来了。
2013年我就签约了摩登天空,我非常喜欢这张《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唱过这么多歌,最满意、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这张专辑里的《Bye Bye Disco》(最后的迪斯科女孩)。
那种律动里有一种浪漫的感觉,有快乐,有忧伤全在里边。

▲
张蔷与新裤子乐队同台演出
2017年的《北京女孩》,2013年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这两张专辑都是和新裤子乐队合作的。
我心灵里有一种,怎么说呢,特别乐观的情绪。所以很多悲伤的歌,都被我唱成轻快的节奏了。
我想每个人也都需要美好的情感,也想我唱歌可以带给人这样的感受。
我的星座月亮是巨蟹,敏感脆弱,但是我的太阳又是射手,很奔放的。
我真的不在乎别人的说法。
沉淀一下,然后再绽放,这个也挺符合我的名字,蔷啊,蔷薇花的蔷。
2020年的专辑《我是张蔷 My name is rose》里《花园路号探测器My name is rose》那首歌,写的就是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花园路上,那条路上没有一朵花,只有我的名字像一种花,算是一种对童年的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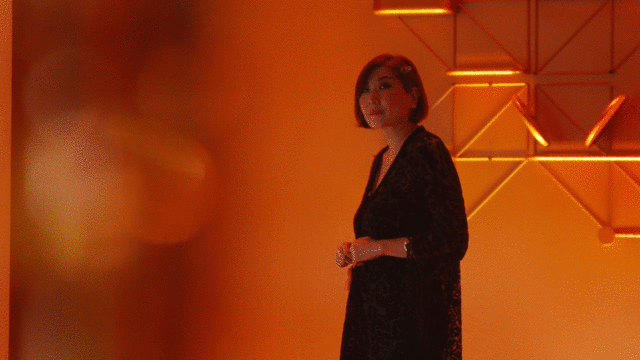
▲
54岁的张蔷,沉淀后,再绽放
我不唱的那几年,总是有媒体问我是不是被封杀了?
我不是还在唱吗?没有。一切不唱全是我自个选择的,因为我需要照顾孩子,那会儿我没心情唱。
我喜欢结婚,我想自己有家。
因为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我希望我的家庭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很不幸,我这第一次还是离了。但是我们是朋友,我们不是仇人。
完后我还是渴望美好的婚姻生活,大概单身了九年,重新第二次再结婚,一直到现在。

▲
张蔷和女儿
两个人在一起永远都有伴、有孩子,我喜欢那样的生活。
日常的我,比较轻松,就是每天给家里人做饭。我最拿手的是湖北的腊鱼,和五花肉一起做的。我老公会给我打下手。
还喜欢网购,有些演出服我都从网上买,回来自己手工改造。我在节目里提到的亮晶晶的发卡,就是我女儿给我做的。

▲
张蔷说:“快乐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
今年,我还要新发8张专辑。之后,我希望能继续做一些更多元的音乐,唱一些以前的好听的被人遗忘的音乐。
图片、影像资料提供:张蔷工作室
图片摄影:吕海强、WATiETC_等等
▼

原标题:《54岁中国迪斯科女皇,嗲炸》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