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伍斌评《美国的分裂》︱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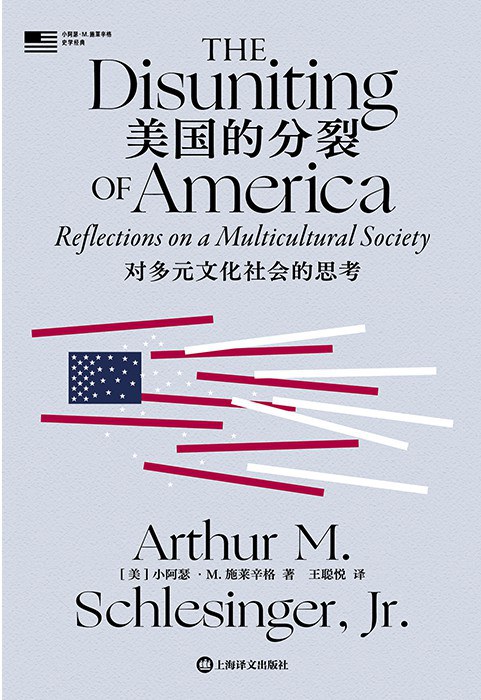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美]小阿瑟·M. 施莱辛格著,王聪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224页,65.00元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是二十世纪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年少成名,不到三十岁时即凭借《杰克逊时代》一书斩获1946年普利策奖,从而确立了其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此后于1958年获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并在1966年再度获得普利策奖。他一生笔耕不辍,出版著作达三十余部,发表各类文章两百多篇。与同期史学家相比,施莱辛格对政治颇为热衷,曾长期深度参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似乎并不囿于“历史学家应与其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的行规。1961年至1963年间,施莱辛格担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这一身份有助于他获得一般史家所不能触及的信息和材料,促使其研究与美国的时局关联愈加紧密。施莱辛格的经历及其研究旨趣和明显的个人特征,也使他成为一位颇具争议的史家。
思想和观念的争论往往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无疑是美国社会和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其基本内涵早就有学者提及。1915年,美国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提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旨在批评当时颇为盛行的“熔炉论”(melting-pot),认为虽然“熔炉论”的愿景非常诱人,但只不过是虚幻的空中楼阁,并不符合当时美国社会文化多元的实际。不过,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彼时美国民族主义兴盛的年代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兴起民权运动,唤醒了不同少数族群的权利意识。联合国也于1965年率先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呼吁各国明确“一切基于种族优越或仇恨的思想传播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惩罚”。美国各少数族群试图维持本族群的传统文化,并希望获得主流社会尊重与平等发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美国历史上针对移民族群的排斥和同化等处理方式逐渐失去了市场,而美国持续保持其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则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此同时,霍勒斯·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理念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政治色彩更浓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取代。前者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的共存,后者则更注重文化在共存基础之上的平等,同时为少数群体维系其传统文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少数族群大多热烈拥抱多元文化主义,保守主义者和狭隘的美利坚民族主义者则对之持批评态度。最初的文化多元主义旨在给予少数群体文化必要的尊重,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即便是那些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者,也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社会文化多样的现实。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黑人并未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第二,非欧洲移民,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数量和影响力激增。其结果是,美国族群同化的理想渐行渐远,而美国社会也更像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所说的“我们现在都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发展,致使部分多元文化主义者走向了偏激。他们甚至无视历史事实,将自己所属族群的文化置于美国历史的中心,从而导致美国历史书写的碎化、失真及美国社会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对美国历史有着强烈一致性认同的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91年出版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以下简称《分裂》)一书,对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及其理念进行了抨击,表达了对美国社会因“族群中心主义”而走向分裂的担忧。由于本书自出版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关于该书及其作者的各种评论也非常丰富,笔者不再赘述,在此仅对其予以简单推介评述,敬期读者诸君指正。
施莱辛格的《分裂》是一部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著作。该书的副标题为“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能看出施莱辛格旨在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尤其是“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撕裂。他对“非洲中心主义”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逐一批驳。
非洲中心主义要求美国学校的历史教育重视对黑人儿童自我价值的培育,因为以往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忽视了非白人的历史,这对非白人儿童的价值和自尊都造成打击,导致黑人学生成绩不佳,进而厌学,对黑人学生的心理造成了伤害。施莱辛格认为,这种论断夸大了白人中心主义教育的不利影响,并没有证据证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会破坏少数儿童的心理”(64页)。施莱辛格认为这种种族决定心理的观点不过是种族主义的老调重弹,同时他对黑人援引这种观点来表达自身的诉求感到十分惊讶。在施莱辛格看来,美国的非洲中心论确实是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谓“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者强调非洲文化和非洲认同事实上是颇为虚伪的。他援引著名社会学家、“和平队”(Peace Corps)顾问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观察认为,“在非洲服务的黑人‘和平队’志愿者们在从祖籍重返‘现实’家园后往往对他们‘根深蒂固的美国人特性’产生了新的共鸣。他们终究还是美国文化而非非洲文化的子孙、贡献者乃至牺牲者”(60页)。易言之,虽然这些非洲中心主义者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宣扬非洲文化与非洲认同,争取在美国的历史教学中增添尽可能多的非洲因素,然而他们自身却已然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而非欧洲文化的代表,也无法适应非洲的文化与价值。施莱辛格指责非洲中心主义的教育是比白人中心主义教育更为“摧残心灵”的教育。他对非洲中心主义强调非洲文化、语言、习俗等在美国教育中的参与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些偏执的人并非“多元文化主义者”,而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非洲中心主义者”。施莱辛格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种族狂热,特别是非洲中心论的种种运动,对美国的教育及少数族裔的未来而言都不是什么好兆头”(51页)。
施莱辛格还以犹太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为例,认为这两个群体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成功,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歧视和排斥,美国的课程体系设置也鲜有关于两个群体历史文化的介绍,但他们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反而在二战之后通过自身努力,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深度互动中,获得了经济和阶级等方面的提升。施莱辛格试图以此证明,少数族群在美国获得成功与其传统文化和历史在美国教育中受重视的程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不过,施莱辛格似乎忽视了亚裔和犹太裔在美国获得成功所遭遇的阻力,他们付出的努力恐非主流美国人所能想象。更何况这两个群体,尤其是亚裔并没有美国主流认知中的那般成功,其内部的多样性也远非任何一种刻板印象所能概括。
施莱辛格并不反对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中增加黑人史、亚裔史、女性史等内容,但前提是要将其作为实实在在的历史来客观讲述,而不是当成某种意识形态或者虔诚的信仰予以教授。在施莱辛格看来,“历史的功能并非促进族群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更好的理解世界、理解过去;冷静地分析、判断和展望;尊重不同文化和传统,并毫不畏惧地捍卫那些使历史研究自由成为可能的普世价值,诸如宽容、民主和人权思想,等等”(75页)。从某种意义上,施莱辛格也理解那些在美国历史记忆中失语的少数族裔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以及他们加强自我群体声音的举措,“但是制度化的分离主义则不然,它只会凸显种族差异、加剧种族关系紧张”(76页)。施莱辛格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偏激要求,如将本族群在美国历史的地位提升到同白人相当的地位、双语教学等,都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曾发出警告:“毫无疑问能置这个国家于死地、使之绝无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继续维系下去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任它沦为诸多心存芥蒂的族群之间的角力场。”(95页)施莱辛格尤其不理解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背景下,少数族裔仍争取学习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更何况,“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异质的国家,共同的语言堪称必要的黏合剂”(86页)。
施莱辛格在批判族群中心主义导致美国分裂的同时,也对美国的主流文化、共同理想及价值理念充满信心,认为种族中心主义者导致美国分裂的诸种举措终将失败。施莱辛格指出,“美国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有能力把种族、宗教、族群背景迥异的人们聚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112-113页)。施莱辛格也承认,美国的认同不会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它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美国人口结构的微弱变化也在改变着其国家精神。但他强调,无论是美国的认同还是气质的改变,“不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11页)。施莱辛格同时指出,维系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的纽带不应遭到破坏,“这些纽带包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运”(118页)。有意思的是,且不说多元文化主义者,即便是施莱辛格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者,或者偏激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似乎也没有否认上述价值观念和维系美国社会统一的“纽带”。事实上,美国各民族群体之间在基本价值观上有较高程度的共识。
从《分裂》一书中能明显感觉到施莱辛格对美国社会同一性逐渐丧失的焦虑。他的焦虑与美国社会种族构成变化有关,也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关于“谁是美国人”的焦虑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焦虑感导致施莱辛格在《分裂》一书的论述与分析中,多少缺乏学者应有的冷静、中立和客观。
施莱辛格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对多样性的追求,是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而美国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也是来自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然而,对多样性的追求并不仅是族群中心主义者的追求,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诉求,旨在扭转或弥补美国社会以往对少数族群的忽视、歧视,乃至奴役。在课程改革方面,少数族群坚持认为,美国和美国历史都不是单一族群所建构和书写的,而是各族群共同贡献的结果,每个族群都应该在美国的历史书写中占据应有的合理位置。争夺历史的书写,事实上也是某种形式的权力争夺。历史记忆对未来是有指导意义的。谁来书写历史,什么应该被书写,与各个群体在美国的当时处境以及未来地位休戚相关。施莱辛格对多样性追求的反对,无疑也是对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念的否定。施莱辛格似乎有意忽视多元文化主义的诸多正当诉求,将之同族群中心主义相提并论。
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误解颇深。他认为,“反对‘熔炉论’的族群起义,至少在言辞上(尽管我认为在现实中并非如此)达到了否定共同文化和单一社会的理念的目的。如果大量民众果真接受这一点,共和国无疑会陷入很大的麻烦”(111页)。这里的论述未免有失偏颇,前文已提及,几乎没有族群否定美国共同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者也并不否认欧洲文化对美国文化的意义,没有忽视白人对美国历史所做出的贡献,更无意否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奠基之功。
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不仅招致少数族群的回击,很多学者也认为他走得太远。美国日裔学者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就明确指出,美国不是非要在“多元文化主义”与同一性文化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甚至觉得在教学中教给学生不同观点和相关争论,对摆脱历史相对主义和获取真知甚为重要。更有学者批评施莱辛格“对美国学界汗牛充栋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梳理”。甚至有读者指出,严格来说《分裂》其实不是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的著述,而是关于施莱辛格所设想的非洲中心主义的书籍。施莱辛格通过一种带有想象色彩的极端非洲中心主义,并将其描述为“种族崇拜”,贴上“生物决定论”的标签,进而对之加以批判。简言之,施莱辛格是基于某种对非洲中心主义和美国分裂的危机想象,来建构《分裂》一书的基本逻辑。施莱辛格不但混用“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也没有区分“文化”与“社会”两个概念,导致其将少数族群的文化认同视为对美国社会的撕裂。同时,施莱辛格可能也忽视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所提出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社会出现的严重分裂,文化多元主义既不是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二战后的美苏冷战是当时世界格局的最显著特征,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和军事等层面的激烈竞争,掩盖了美国内部很多矛盾。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之久的美苏冷战也就此结束。美国的种族、阶级等社会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并随着两大党对选民的争夺而有激化之势。这与当时美国历史学的碎片化及反碎片化趋势桴鼓相应。当然,美国社会分裂最为根本的原因仍是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居住隔离、种族仇视等。
施莱辛格虽然也承认美国历史上白人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少数族群所造成的伤害,但他似乎忽略了二者对少数族群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他对争取黑人权利的人士缺乏理解,批评“黑人的事儿只是被害妄想情结中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即他们时常感到有人想要伤害自己,几乎所有少数族裔都会时不时被这种情结俘获”(88页)。不难看出,施莱辛格所责备的是抛弃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非裔美国人。施莱辛格难免避重就轻之嫌,他所说的“非洲中心主义”,更多的不过是对白人奴役黑人历史的纠正。
施莱辛格或许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或者白人中心论者,但他表现出的西方优越感仍是显而易见的。他强调西方文化是一种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文化,虽然有不堪的过往,但愿意积极克服,而其他文化则并非如此。施莱辛格指出,西方传统同其他文化传统存在本质性差别,“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传统包含着对理想状态的构想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揭露出自己的罪行且持续进行自我批判。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把自我批评作为其存在的基础”(103-104页)。他甚至为西方的殖民主义找到了道德合法性,指出是法国人将阿尔巴尼亚妇女从必须佩戴面纱的习俗中拯救出来,是英国人废除了印度的殉夫之俗,“是西方而不是非西方文化开启了废除奴隶制的改革运动”(106页)。
施莱辛格并不孤独,同时代的学者形成了一股保守的潮流,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展开反思、批评,甚至反扑,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大卫·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以及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人,但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激烈的。很少有学者如施莱辛格在《分裂》一书中那样,行文分析超出理性中立,充满了焦虑情绪乃至偏见。从这个意义上,很难将《分裂》一书归为公正、严肃、严谨的学术研究,说其是一种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时评或许更为恰当。
总体而言,《分裂》一书是美国当时多元文化纵深发展,部分多元文化主义者走向族群中心主义,并触及到美国同一性可能丧失的某种反弹。其中不乏对多元文化主义反思的真知灼见,对理解今日的美国也多有助益。但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或者他所声称的“族群中心主义”的批评,很容易使读者回想起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在大规模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移民抵美后,美国社会所展现出的焦虑,进而催生了一系列排外言行,美国社会也因之分裂为“我者”和“他者”、“美国人”和“异族”(aliens)。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