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孟子论“义战”与更易之道
孟子支持正义的战争,其所言“义战”于《孟子》一书可分两类考论。一是以“汤武革命”为例,揭明正义的战争乃除暴安民,推翻暴君的战争就是“义战”,必定受民众欢迎。二是就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论,“义战”指“解民于倒悬”而受民众欢迎的战争。“汤武革命”一说,见于《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所言“革命”乃指有德者顺应历史发展之规律(此谓“顺乎天”,故以“天地革而四时成”譬喻之)推翻暴政,“解民于倒悬”(此谓“应乎人”)。孟子对《革卦》所言“革命”之义(“顺乎天而应乎人”)有更深刻的申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明文指出“汤武革命”的对象乃“贼仁者”“贼义者”。齐宣王以“汤放桀,武王伐纣”,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另,孟子明确表示,“汤武革命”的目的在行“尧舜之道”。《孟子·万章章句上》记载孟子述说“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以尧舜之道”,“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又,孟子述说武王伐殷: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依以上所引,孟子述说汤“伐夏救民”、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大悦”。孟子虽未有用“汤武革命”一词,然我们仍可据之申论孟子政治哲学中表明的政权更易之道。依孟子所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所显示之“革命”,包含了政权更易之道的根本要素:革命之合法性和正义性在其“依仁义而行”,而革命之对象是“贼仁者”“贼义者”。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而建立新政权,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不必讳言,除“汤武革命”之外,中国历史上未有过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甚至可以说,世界史上也未出现过这种革命。据此,我们可以说,孟子依汤武而论“革命”之为政权更易之道,乃是政道之最高原型。我们必须将孟子此言“革命”与近世以来依西方种种“革命”理论而立之“革命主张”区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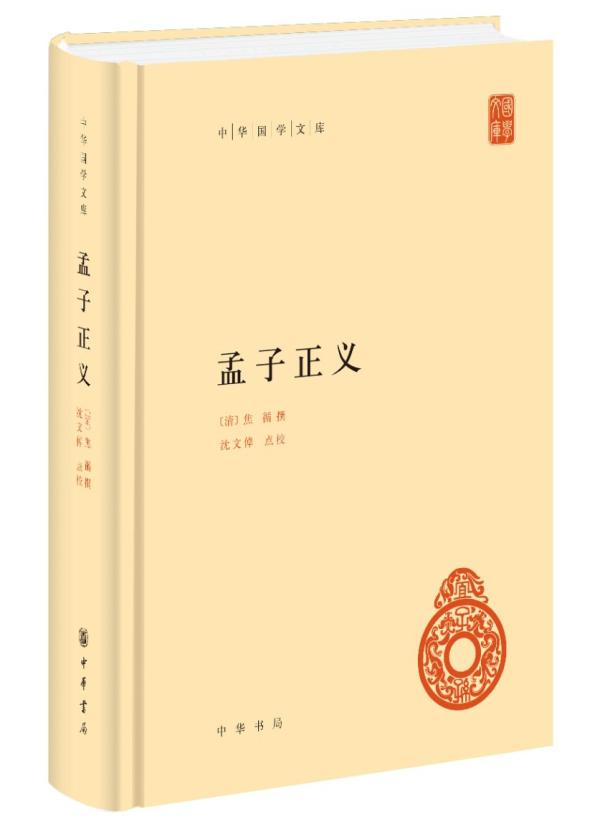
《孟子正义》
俗语有云“打天下”,牟先生说:“此种打散腐败势力之胶固之战争,在中国以前即曰‘革命’,或曰‘马上得天下’。此亦即俗语所谓‘打天下’也。”此所云“打天下”可说是在君主专制时代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唯一形态,这种行为一般被称为“革命”,其实根本与孟子依“汤武革命”所言之“革命”不同。又,如牟先生说:“革命者,变更其所受于天之命也。”不过,必须注意,并非一切“打天下”,夺取政权,都能称之为“革命”,一般所谓“打天下”,虽然大多都自称“替天行道”,但实质上只不过是政权之易手。依孟子所论,唯独仁者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以建立施仁政、行王道的新政权,始得谓之“受于天之命”,而堪称“革命”。依此义,孟子所言“革命”甚至不能与人类历史上种种经济形态的革命(如工业革命)、社会与思想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政治制度的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混为一谈。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章句下》)何谓“义战”?孟子言“义战”,可见于其述说汤之征葛。《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载: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葛伯“放纵无道,不祀先祖”,“与饷者为仇”,(《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六)武王征葛,“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孟子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章句下》)朱子注:“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汤征葛,“义战”也。“义战”之根本义是以仁义之师征讨残暴者,“救民于水火之中”也。以上所记述天子征讨无道之诸侯,属于“义战”。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霸主施仁政、行王道,并有主张行仁政之诸侯攻打施暴政者,以实现统一天下而行王道之理想。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译注》
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载,孟子对齐宣王说:“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齐宣王不行仁政,令燕民失望,孟子进言:“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齐宣王不听。齐宣王之攻打燕,只为争城掠地,致使生灵涂炭,此即孟子说的“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并说争霸者是“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主张“义战”,但反对诸侯之间相互攻伐,用朱子的话说,“论征伐则必称汤武”,“行师不法汤武,则是为乱”。(《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二)孟子明确反对任何“敌百姓”的战争,严斥诸侯争城掠地之战,夺民财、为争地而杀人是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章句上》),其罪之大,虽死亦不足以容之。
孟子重视人的生存权利,一再强调“民”之生命高于“君”之利益。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他严词警告诸侯杀人盈野、盈城之暴行,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子·尽心章句下》)又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孟子严斥梁惠王“不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又,《孟子·告子章句下》记载:“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孟子正告慎子: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指出,鲁国吞并小国,乃仁者所不为,何况以战争强夺?故责备慎子应“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并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依孟子所论,唯独仁者之师推翻暴政以施仁政、行王道,始谓之“革命”。若就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论,只有“解民于倒悬”,民心所归向者始谓之“义战”。此即孟子说:“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一般所谓“打天下”,只不过是政权之易手﹐即孟子所言“亦运而已矣”。就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时期只通过“打天下”改朝换代之事实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非理性的,中国历来并无政道,但并不能据此断言中国政治思想中无关于政道之学说。如我们已论明,孟子所言“王道”就标明了理性的、包含着政道的政治原型。
析疑与辩难
问:《论语·八佾第三》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有学者据之以为孟子对于战争的态度不同于孔子。
答:孟子赞“汤放桀,武王伐纣”,在于其除暴君以行王道。而孔子慨叹周武王的乐舞“尽美矣,未尽善也”,非不赞同“汤武革命”,而在于表示战争毕竟未能尽善。征于孟子之言论,也能见出他慎言“战”,对于战争的态度与孔子并无不同。孟子说:“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章句下》)《书·周书·武成》叙周武王伐纣,有云“血流漂杵”。孟子质疑,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同前)又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同前)孟子对齐宣王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战争之发动与否,依据于“民悦”或“民不悦”。依以上所述可见,孟子所主张的战争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所以说“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无不仁者陷民于水火中,则不必有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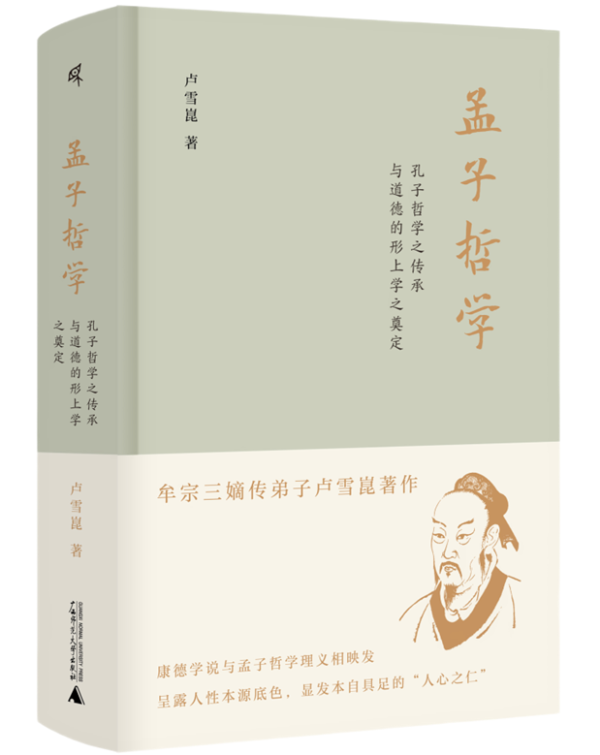
本文选自《孟子哲学:孔子哲学之传承与道德的形上学之奠定》(卢雪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2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