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斯威夫特笔下的民众与贵族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Jonathan Swift by Charles Jervas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文 | 刘火,作者授权发布
斯威夫特,准确地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谁,如果不是读书人,大约是不知道或知之甚少。如果说《格列佛游记》(或小人国或大人国的故事),大约知道的人就会多一些。斯威夫特不仅是通俗作家,事实上,斯威夫特是十七世纪后期十八世纪前期最重要的政论家或者激进的后进分子。何谓“激进的后进分子”?即向后(古代)看齐的激进分子。刘小枫依据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近代西方历史和前人的研究,认为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到十六世纪)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中间,有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即源自法英两国的“古今之争”。
所谓“古今之争”,就是:“崇古派”的一方认为只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及风俗,都没有过时,依然影响着后代与当下。“尚今派”(或“崇今派”)的一派认为,通过文艺复兴,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由科学、民主、自由替代旧文化旧制度的时代已经来临。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人坦普尔(Sir.William Temple,1628-1699)、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后者的代表沃顿(Willian Wotton,1666-1727)和稍后的集大成者的伏尔泰(Voltaire 1694- 1778 )。斯威夫特自大学毕业21岁(1688)做了坦普尔私人秘书。当英国的“崇古派”旗手坦普尔倒在了十八世纪门槛前即1699年时,32岁的斯威夫特接过了坦普尔的“崇古”大旗继续战斗。1701匿名发表的《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与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维基百科”译作《关于雅典、罗马时期分歧、斗争的论述》,下简称“论雅典罗马”。收于中译本《图书馆里的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5年,2020,精装),虽然不及同一作者的《一只桶的故事》(1704)、《格列佛游记》(1726)等著名,但作为一篇崇古的名篇,却是一篇今天看来也极难得的关于古(主要是古)今政治体制论述的重要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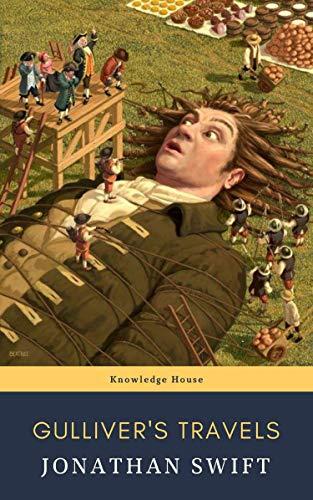
这篇文章一开头便写道:“人们公认,在所有政体中,都有一个绝对无限的权力,无论由哪个部门来执行,这种权力从历史起源和自然法上讲似乎都被赋予给了全体国民”。显然,写这段话的时候,斯威夫特是看过洛克的《政府论》(1689。中译本,1964,商务印书馆)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作为近代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其主要业绩在于在社会契约论上所做出的划时代的贡献。洛克认为:政府须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由被统治者授权,而且政府须保障被统治者即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政府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另外,洛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是后来西方政体三权分立的基础。不过,斯威夫特似乎并不完全认同洛克的观点。“论雅典罗马”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弄清楚权力均衡的真正含义最好先考察均衡的本质是什么。”接着,斯威夫特说“均衡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承托点和托住它的手,其次是两个托盘和要放在到其中的重物。”这一比喻,即天秤的比喻。从这个比喻看,在前提上就基本否定了洛克的社会契约,也就是肯定了由社会契约替代之前的君主制(洛克有语,一切君王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暴君”)。
当然,在一个已经实行了400多年的《大宪章》(1215)的英国,再回到君王独尊的时代,显然是不合适宜的复辟(也非作者斯威夫特的本意)。因此,对于tyranny(“tyranny”中文可译,“专制”、“独裁”、“威权”等),斯威夫特自然不会去赞扬,但斯威夫特说:“一旦由于疏忽、蠢行、维持平衡之手软弱无力或强者倒向某一方,力量在其余双方之间不会长久平分下去,支重新恢复平衡之前,将完全集中到一方。这是‘专制’一词在最古老的希腊名著最准确的解释。”说完,斯威夫特又说:“与许多浅薄之士的严重谬论相反,它不是指某个人攫取了绝对权力,而是指任何一方打破平衡,让权力全部放在一个托盘里。”这话,显然有所指(是否指洛克的《政府论》待考),也就是对新兴的“崇今派”社会契约论中的政府权力须民众授权才正当与合法的质疑。事实上,“论雅典罗马”就是这种质疑的产物。
“论雅典罗马”就是雅典和罗马两种不同的权力结构里得出:无论是“雅典民主”还是“罗马君主”(或“罗马贵族”),都有他们优势同时也有他们的缺陷。斯威夫特在论及“雅典民主”时,“论雅典罗马”说“希腊强大的共和国,自梭伦建制,经过多次大衰退,被草率、嫉妒和变化无常的民众彻底葬送。”我们知道,希腊的“城邦制”(公元前九世纪始),是以公民及代表公民组成的群体。这种群体即一种政治共同体,它以城市为单位形成自治国家。即所谓的“共和”。今天英文的“Republic”(此词即含“人民”的意思)就是从希腊文“城邦(poleis)”一词来的。柏拉图最重要的著作《理想国》(中译本,1986,商务印书馆)的英文书名即“poleis”。“论雅典罗马”还进一步说,这种以“民主”,“容不得将军胜利,也容不得将军不幸”,而且“公民大会一直错误地审判和报答那些最有助于他们的人”。于是,“论雅典罗马”批评当时“崇今派”的观点:“人们信誓旦旦地宣称,雅典民众的这种权力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坚持认为,它是雅典公民无可置疑的特权。事实上,这种权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猖狂的权力侵犯,是对梭伦建制最严重的背叛”。由此,“论雅典罗马”说,“民众利用弹劾的手段控告某个人,结果使雅典遭受了灭顶之灾。”借这一说法,表明今天人们借鉴的古代,如果是这样的就会大错特错的。所以“论雅典罗马”说:“从古至今,国内外的重大议事机构有时抛出无知、鲁莽、错误的决议,常用让我感到诧异。这使我意识到,民众的议会也会犯个人所能犯的所有问题、蠢事和邪恶”。这才是这位“崇古派”的真实意图:借古讽今。而伏尔泰则说“在艺术和错误的摇篮——希腊,人类精神的伟大和愚蠢都被发展到了极致”(伏尔泰《哲学通信/第十三封/谈洛克》,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显然,斯威夫特不看好洛克们的社会契约里的民众授权论。因为在“论雅典罗马”看来,民众是“草率、嫉妒和变化无常的”。那么,与希腊不一样的罗马在斯威夫特的眼里,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罗马由国王统治,由贵族选出的一百人元老院选举产生。这保证了罗马300年的兴盛。当民众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时,便寻求权力。“论雅典罗马”指出“公民大会甚至可以把选举国王的权力从贵族的手中夺过来”。斯威夫特说“这一步变化巨大,造成国内局势动荡,争斗频繁”,而且“国将不国”。虽然后来由于执政官制度的兴起,才又达成了“贵族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均衡”。显然,从斯威夫特的这些论述里,他对所谓的“民众授权”一论是反对的。“论雅典罗马”说:“民众比较擅长破坏和建设而不善于保持已有的东西;民众喜欢攫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更喜欢把它拱手让人,并把自己搭进去。”写道这里,作者不无幽默地讲“人以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可见作者对民众的态度。斯威夫特作为一位“崇古派”的后起之秀,运用他的博识,表明他所崇古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衰亡都与民众的“不是”有关。甚至罗马后来的那些执政官的“暴政”(tyranny),都与民众相关。下面这说话最为惊世骇俗:
渥大维胜利后,必然推行最为邪恶的独裁,历史上怒气冲冲的上帝给予堕落恶毒的民众最为严酷的惩罚也莫过于此。
也就是说,独裁是由民众所引发的。
关于罗马的衰落,后人有无数个理由。据“维基百科”说,1984年德国人亚历山大·德曼特出版的专著《罗马的沦陷》(Der Fall Roms)中列举了前人给罗马衰亡的210种解释,显然有比斯威夫特的这一种解读更为周全。至少,罗马的衰落决非如“论雅典罗马”所说,是因为民众打破了托盘的平衡所至。可见著者崇古的观点,很多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只为当是的论争的“负气”之论。不过有一点,著者的话倒是引人发省的: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他们先是迎来了民众的专制,然后是个人的专制”。这话即是对希腊城邦衰落原因的指正,更是对罗马衰落的指正。这让笔者想起房龙(1882-1944)《宽容》(中译本,1985,三联书店)一书中所叙,当某一新的宗教还处在比它早的宗教时,新的宗教(因为它可能是异教)呼吁宽容和争取权力,但一旦新的这一宗教获得权力之后,就开始了打压比它新的宗教(新的异教)。
历史上这种恶恶相因恶恶为果的事,真是屡见不鲜的。
《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与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一文从表到今天,已过了300多年。显然,历史并没有按照“崇古派”的理论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而是朝着沃顿、洛克、蒙田、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崇今派”启蒙先贤大致辟开的路前行。“古今之争”并非如刘小枫所说是一僵局。事实上,这种古今之争,已在早期的英法、后来的北美和整个欧洲定出了胜负。不过,当我们重新来读一下这篇“崇古派”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政体中关于民众与贵族(“共和”和“专制”),或者关于“民主”与“君主”关系的文章,也许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
原标题:《斯威夫特笔下的民众与贵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