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
在校园开枪的杀手们害怕什么?被忘记姓名
原创 游识猷 果壳
本文将不会出现任何一个枪手的名字。
5月24日,美国德州罗布小学发生了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个孩子,和2个教师。

紧急救援人员聚集在枪击现场附近。|DARIO LOPEZ-MILLS/ASSOCIATED PRESS
令人震惊的悲剧发生后,关于控枪的争论又一次开始。
的确,枪支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枪支易得,人均拥有的枪支数量全世界最多。而研究显示,人均拥枪量越高,公共场所大规模枪杀案件就越多。
在美国,校园枪手大多是合法获得武器的。虽然很多枪手有精神和心理病史,但这些病史并不会让他们在美国买不到枪支。
一个建议是,如果一个人曾经表达过对杀人、自杀、大规模枪击案感兴趣,这个人就不该被允许合法拥枪。
然而,枪支的问题在美国实在是历史悠久而纠葛太多,很多研究者不得不转向另一个方向——
如何减少校园枪击案。

警察在发生枪击事件的罗布小学外巡逻| DARIO LOPEZ-MILLS/ASSOCIATED PRESS
通向校园杀手的“五阶段”和“五条件”
每一个校园枪击悲剧,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
有研究总结出这些校园杀手的形成之路——
一、慢性压力阶段:在童年或青春期经历一些长期的伤害或挫折,导致孤单,
二、无法控制压力阶段:由于孤单、社会隔离,导致了缺乏“亲社会的支持系统”,于是压力累积而无法消除,
三、急性压力阶段:发生短期的负面事件(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想象),对个人来说特别具有破坏性,心理健康急剧恶化,
四、计划阶段:急迫地想恢复控制感,开始幻想大屠杀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和出路,开始行动,为屠杀做准备,
五、大屠杀阶段:使用枪支,在校园等公共场合大屠杀。
这五个阶段连续发展,每个阶段都增大了风险。
此外,校园枪手大多符合五个条件——
①认为自己在社会里处于极端边缘的地位,
②有社会心理问题,例如精神疾病、严重抑郁或反社会精神变态等,放大了个人感受到的社会排斥
③自己思考出了解决方法——武器攻击,以改变自己的声名,从一个失败者,变成一个恶名远扬者,
④执法和治安系统失灵,即使枪手发出了一些信号,但没有被监测到
⑤获得了枪支、炸药或其他武器。
但仅仅是根据这些条件,或者任何一个“枪手特征清单”,都不足以找出所有的枪手。
还需要别的预防和阻止办法。

枪手特征清单还不够,需要有别的预防和阻止方法|Unsplash
不能靠预测,要靠举报
美国特情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研究都认为——要“事先认出谁会去大规模枪击”,是很难或者基本不可能的。
去学校等公共场所开枪的人的确有些特点,比如枪手大多是男性——但绝大多数男性绝不会犯下这种罪行;枪手大多有精神健康问题——但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也是非暴力的。即使将搜索范围缩小到最高危的人群,这种搜索也远远不够精确,很可能会给一大堆守法公民找了麻烦,却遗漏了真正的杀手。
不过,有个办法可以找到真正的枪手——他会自己说出来。
枪手其实大多难以抑制自己吹嘘的冲动。研究发现,校园枪手大多会事先“泄露”(leakage),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吹嘘、暗示、威胁、表达自己的暴力态度、描写自己的暴力幻想、预言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发出最后通牒。越是年轻的枪手,越可能泄露。
2014年加州伊斯拉维斯塔的枪手,不仅在网上发布了《惩戒日》视频,还给亲友、老师和心理医生发了一篇又臭又长的10万字自传体宣言《我扭曲的世界》。
他们忍不住。

枪手很难忍住吹嘘的冲动|Unsplash
另外,枪手们有时还会对他们认可的人发出警告,比如劝朋友在某天不要去上学,或者不要去学校的咖啡厅——因为那是他将要杀人的时间地点。
美国特勤局的研究发现,在81% 的案例中,“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袭击者正在考虑或计划袭击学校”;在59% 的案例中,甚至不止一个人知道。FBI在2018年的一个研究显示,56%的人在攻击前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暴力想法和意图。
问题在于,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人,经常不愿意报告执法部门。原因有许多:一,他们会觉得那是开玩笑,识别不出真正的危机,二,担心主动举报后,自己会被枪手盯上,惹祸上身;三,觉得别人会举报,自己无需做;四,如果枪手是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举报似乎就是在“背叛”;五,举报了,可能也没有用。
FBI的研究显示,举报有时真的没有用。2000~2013年美国发生的枪击案里,有41%的枪手曾经被举报“行为令人担忧”,但并没有被阻止,枪击案依然发生了。
为什么执法部门没能认出枪手?因为这类枪手和其他罪犯不太一样。
枪手大多是“独狼”,他们身边都是普通人,和其他罪犯没有关联,在枪击之前,他们也往往没有暴力罪的案底。这就让他们很容易躲过执法部门的盘查。
1999年的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里,一个罪犯在网上写,“我很快就会去找每个人,我会全副武装,我会开枪杀了你们…… 我只想杀伤你们,越多越好。”
另一个罪犯在作业里写了个虚构故事,讲一个私立中学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文章结尾是“我理解他的行为”。
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的罪犯,曾经多次被举报到校警那里,因为他跟踪女学生,在课堂上惹麻烦,还发表自杀言论。但校警没有收到一条关键信息——枪手在写作作业里,说同学是“卑鄙的人类,人类的耻辱”,希望同学们都“下地狱”,他还写了个故事,故事主角策划一场校园大规模枪击,“杀死这个该死的学校里的每一个该死的人”。
每个玩笑,每个虚构的故事,都有一些真心的成分。
唯有广泛地培训公众,让每个人都知道,哪些言论可能预兆着极端暴力风险,应该被报告给执法部门。
有了这些枪手自爆的“泄露”信息,执法部门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糟糕的案例,模仿的阈值
在美国,1999年的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范例”。
社会学家拉尔夫•拉金(Ralph Larkin)认为,哥伦拜恩枪击案里的两个枪手,为后来的许多起枪击案写下了“文化脚本”。
后来的研究显示,哥伦拜恩枪手里的其中一人,是典型的精神变态和反社会者。他缺乏同情心而擅于操纵别人,他前科累累,他用德语写“我是上帝”,他的日记里满是关于强暴和残害的幻想,他想毁灭全世界,为此他花了整整一年去策划,拍下说明自己动机的录像,写下了长长的宣言。
此后8年里,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里,有8起枪手明确提到了哥伦拜恩案,有6起简直就是哥伦拜恩的翻版。

哥伦拜恩枪击案里的两个枪手,为后来的许多起枪击案写下了“文化脚本”|Unsplash
在马里兰的购物中心,一个枪手穿上和哥伦拜恩枪手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背包,拿着一样的武器,他甚至躲在商场的更衣室里等到了同样的时间——上午11:14。然后他出来,枪杀了两个人,然后自杀。
在西雅图太平洋大学校园,一个枪手枪击了三人,他被警方逮捕后同样提到了哥伦拜恩枪手的“指导”,称其是“所有枪手的导师”。
在哥伦拜恩案后,枪击案变得越来越“仪式化”,越来越像一场关于自我的演出。
哥伦拜恩枪手自拍的录像成为后续枪手模仿的样本,后来的枪手们拍的镜头殊途同归——先用枪指着摄像机,然后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接着两手各拿一把枪,张开双臂;特写镜头;最后挥手告别。
尽管“演出”越来越类似。但随着枪击案的增多,枪手们的个人特征变得越来越多样。他们似乎并不是一类人。
如何解释这种“枪手的多元化”?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曾经提出一个“暴乱的阈值模型”。他的观点是,在暴乱中,其实发生了某些类似“滚雪球”一样的事情。

看到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会让本来作恶门槛较高的人,也加入作恶|Unsplash
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天生的恶徒,他作恶的门槛为“零”,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商店扔石头。
然后是作恶门槛为“一”的人,他自己一个人不会主动扔石头砸玻璃,但看到一个其他人在这么做,就会跟着做。
接着是作恶门槛为“二”的人,他看到两个人在砸玻璃,才会跟着模仿……
以此类推,直到一个在99%的情况下都很正直善良的人,除非他身边每个人都在砸商店玻璃,直接抢走物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忍不住动摇,从已经被砸的商店里顺手带走一两样东西。
格兰诺维特说,“大多数人并不想犯罪,但群体互动是这样的,由于大胆的男性行为会带来身份和地位,一旦其他人在偷车,而你不加入,你就要承担被贴上‘胆小鬼娘娘腔’标签的高昂代价。”
看到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会让本来作恶门槛较高的人,也加入作恶。
这正是校园枪击案传播开后,所发生的事情。
留下不朽的恶名
校园大规模枪击案犯罪者的一大动机,是追求“不朽的恶名”。
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宁可整个世界记住我的恶名,也不要默默无闻地被忽视。
美国人非常渴望和崇拜名声,也有着强烈的“追求个人成功”的自恋文化。这种文化激励出了强烈的竞争心态,成功者拥有了全世界,但失败者就要承受严重的失望、沮丧和愤怒。
很多枪手正是一个愤怒的失败者,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过上更好的生活,有资格获得更大的成功,但某些因素阻碍了他们获得成功——阻碍可能是周围的亲人或者同学,可能是“不识好歹”的金发美女,可能是“娇纵任性”的富N代……总之,这个世界辜负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应得的成功”。但通过杀害无辜的人,媒体可能会来争相报道他们,于是他们终于收获了本该有的“名气和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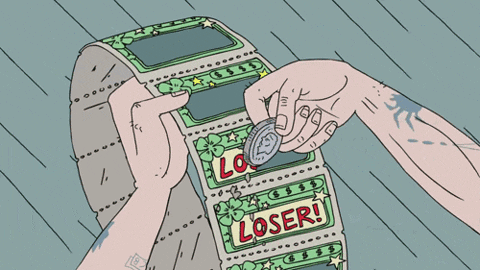
很多枪手正是一个愤怒的失败者|Giphy
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在接受采访时就精准地说出了枪手们的心声:“如果你认为你的生命毫无价值,你是个无名小卒,你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你想做一些事情来保证你的名字会被全国人讨论,你有什么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很多无辜的人。”
1999年哥伦拜恩的枪手录下视频,预言自己将被载入史册。2014年加州伊斯拉维斯塔的枪手则写,“耻辱总比默默无闻好。”
这种思想,培育出了很多枪手的“不公的收集者心态”(injustice collector)和“战士心态”(warrior mentality)。首先,他们一笔笔记下世界对自己的不公平——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他们扭曲的幻想。然后,他们通过充斥着暴力的自恋妄想,去弥补自己现实里的无能和挫败感,还切实地行动起来,为犯罪做计划和准备。
忘却他姓名
正因为枪手的一大动机是追求身后的“恶名”,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新闻报道和社交网络上的讨论,如果增强了枪手的声名,让枪手获得大量关注,成为反社会的“明星”……那么,其实就是在助长下一次枪击案。
校园枪击是一场枪手的表演,但这场表演需要观众和媒体的配合。
正因如此,这几年出现了“反恶名”(No Notoriety)和“不写他姓名”(Don’t Name Them)的运动。这些运动号召:
除非枪手还在逃,需要追捕,否则不必长篇累牍地报道枪手的名字、照片、人生。这些交由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来研究。如果需要报道,可以用代词或者简写。
报道整个社区的悲恸和坚韧。报道那些受害者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他们被夺走的人生。报道那些挺身而出、阻止枪手的英雄,让英雄们的名字和照片广泛传播。
不要让潜在的枪手升起对媒体报道和关注的渴望。

擦去他的姓名|Unsplash
虽然枪手们总是把自己不如意的生活全部归咎于外部世界,但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知道自己也负有部分责任。但他们的自我狂妄自大同时又脆弱无比,他们无法承受自责,无法承受自我怀疑和那种自己毫无价值的感受。
于是他们每天说服自己,自己没有错,自己比其他人更优越,自己本来就值得更好的生活……而世界辜负了自己,所以,就算杀掉无辜的人,也只是世界对自己的应有补偿。他们幻想着,通过大屠杀,他们眼中的“压迫者”付出了代价,整个世界将战栗着承认,他们是最强大、最聪明、最优越的。
而证明他们错了的一个办法就是——
让枪手生前和死后,都默默无闻。
参考文献
[1]Allely, C. S. (2020). The psychology of extreme violence: a case study approach to serial homicide, mass shooting, school shooting and lone-actor terrorism. Routledge.
[2]Lankford, A. (2016). Fame-seeking rampage shooters: initial findings and empirical prediction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7, 122–129.
[3]Lankford, A. (2018). Identifying potential mass shooters and suicide terrorists with warning signs of suicide, perceived victimization, and desires for attention or fa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00(5), 471–482.
[4]Lankford, A. & Madfis, E. (2018). Don’t name them, don’t show them, but report everything else: A pragmatic proposal for denying mass killers the attention they seek and deterring future offender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2(2), 260–279.
[5]Lankford, A., Adkins, K. G. & Madfis, E. (2019). Are the Deadliest Mass Shootings Preventable? An Assessment of Leakage, Information Reported to Law Enforcement, and Fire- arms Acquisition Prior to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1043986219840231.
[6]Vossekuil, B., Fein, R. A., Reddy, M., Borum, R. & Modzeleski, W. (2002). The final report and findings of the Safe School Initiativ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chool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Secret Service and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7]O’Toole, M. E. (2000). The school shooter: A threat assessment perspectiv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8]Meloy, J. R., Hempel, A. G., Gray, B. T., Mohandie, K., Shiva, A. & Richards, T. C. (200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orth American adolescent and adult mass murderer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22(3), 291–309.
[9]Levin, J. & Madfis, E. (2009). Mass murder at school and cumulative strain: A sequential mode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2(9), 1227–1245.
Murray, J. L. (2017a). The transcendent fantasy in mass killers. Deviant Behavior, 38(10), 1172–1185.
[10]NOVA (21 December 2012). Can science predict mass murder? www.pbs.org/wgbh/nova/body/mass-murder.html
[11]Nast, C. (2015). How School Shootings Spread. New York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10/19/thresholds-of-violence
作者:游识猷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花样年华》25年后重映
- 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发表致辞
- 吴敬平社媒炮轰国球被资本裹挟

- 字节CEO梁汝波:抖音和今日头条要打击无底线搏流量的行为
- 美媒:台积电可能接手英特尔芯片制造业务

- 世界陆地表面的最低点
- 中国古代记录日期的一种方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