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傅正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宫崎史学的背面

今年8月,期待已久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亚洲史论考》)中译本终于问世。据马云超教授披露,这部译作历经曲折,其过程前后近十年。译者用心之深,真可谓“字字看来皆有意,十年辛苦不寻常” (马云超:《写火星人都能看懂的历史:宫崎市定与他的〈亚洲史论考〉》,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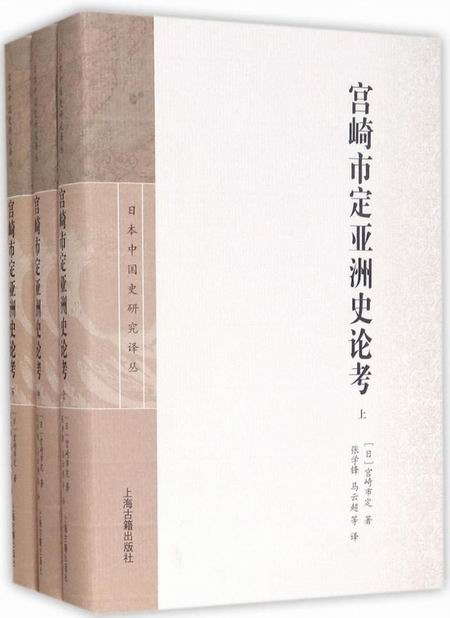
宫崎市定作为京都学派第二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早已享誉海内学林,其《九品官人法研究》直至今日仍是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早在196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的中译本,次年又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订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足见其重要性。然而以往的译本要么是单部著作,要么是由中文译者取舍选编,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难窥宫崎史学之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的《亚洲史论考》乃是日本学者编次,并经由宫崎本人审订,意义正在于为我们展现了其史学思想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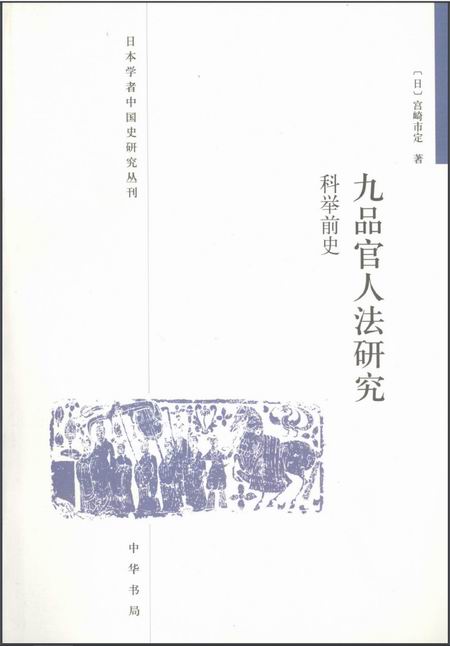

如实观察历史的史学家?
不用说正文,即便上、中、下三卷的“前言”就十分值得玩味。例如宫崎市定在“上卷前言”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史学立场:“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当今流行的理论历史学,如果试图在我的著作中寻求这方面的东西的话,那就完全是找错门了。”什么是“流行的理论历史学”?宫崎回忆了几个典型,比如“文学部的西田几多郎博士”“经济学部的河上肇博士”,“他们的讲课在当时全校中是最有人气的”(《亚洲史论考》“上卷前言”,15页)。
众所周知,河上肇博士的《经济学大纲》深刻地影响了其时的许多革命家。宫崎坦承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河上肇,乃是因为他“曾经利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说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在对河上的“奴隶社会”做了一番让人云山雾罩的批驳后,宫崎更直指彼辈推崇的桑巴特:“他的历史分期学说,仅止于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事实在看,并在其上再赋予理论,因此他的重点在于理论的构建。这一点,我们实在无法遵从。稍微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作为由个人建立起来的某种理论体系,其精密程度无论有多高,其实都是有限的,一定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破绽。”(《亚洲史论考》“上卷前言”,16页)
与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截然不同,宫崎市定主张,“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应该通过史实去观察整个历史,将观察的结果就此记录”(《亚洲史论考》“上卷前言”,16页)。想必宫崎市定这寥寥数语会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
但我们不应忽略,他之所以劈头就龂龂争辩于“流行的理论历史学”,是有其学派之争背景的。日本第一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创设于1870年代,不仅教学体制完全效法欧洲,尤其是德国,甚至大量聘用西方人充任教员,例如其史学科便是由德国人李斯一手培育。有日本论者谓,该校“流行的是追求洋气十足的西洋学问”([日]户川芳郎:《汉学·支那学·中国研究》,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四),1990年,转引自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52页)。
东大对于建立日本现代学术之功绩,固然不遑多论,但其缺陷也毋庸讳言。尤其自189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主义”呼声高涨,于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等人的鼓呼之下,在关西建立一所不同于东大学风的京都大学,就势在必行。支持者中就包括宫崎市定的恩师内藤湖南。两校学风一重西洋一主东洋,交相辉映,史学研究自不能外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白鸟库吉、加藤繁等人便揪住内藤湖南“中国历史分期法”过重于文化而很少涉及经济层面这一点不放,连续展开批判。比如加藤繁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概说》一书中就提出了与内藤不一样的历史分期法。他指出,“隋唐以前,中国是大官僚豪族的大土地占有制,在这种土地上耕作的是奴隶,直到唐中期均田制崩溃以后,奴隶从事农耕的现象才渐趋衰退,代之以佃户耕作,至宋代成为显著的特点”。按照“奴隶耕作”这个标准,“中国在隋唐以前均为古代社会,宋以后才进入中世社会”(陈金凤:《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日本研究》,2010年第四期)。
这一番关于隋唐奴隶社会的论断在我们看来实在太过奇诡,诚若其论,是否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南部一下子就从上古跳到近世?
重要的是,加藤繁的学说在战后居然借着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势头,一下子普及开来。1946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派学者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派”)。“社会五阶段论”便是历研派的重要主张之一。加藤繁关于“隋唐奴隶耕作”的判断,正好能套入五阶段论。他的学生前田直典就据此而对内藤史学大张挞伐。
在1948年发表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一文中,前田直典便指名道姓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人统称为京都学派,并依据乃师之论激烈批判之。有趣的是,前田的批判虽然猛烈,但仍然预设了“唐宋变革”,只不过分别换了两个阶段的称呼。内藤湖南称魏晋隋唐为“贵族时代”,前田直典就称之为“奴隶社会”;内藤湖南称宋代为“平民时代”,前田直典就称之为“封建社会”,真可谓一样的“唐宋变革”,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参见陈金凤前揭文)。

这样的批判当然引发宫崎市定的强烈不满。他甚至连加藤繁做笔记、抄卡片、编索引都要刻意挖苦一番,称其“即使不读书也可以研究学问”(《东洋史学的研究方法》,《亚洲史论考》下卷,1382页)。《亚洲史论考》中卷重点讨论“中国中世”,在该卷前言中,宫崎就做出了回应,指出对方全然误解了唐代的部曲。“我认为与其将部曲比对为奴隶,不如将之比对为农奴,这样更符合其上层贱民的身份。如此一来,部曲无疑就是具有中世纪特征的隶民。”(《亚洲史论考》“中卷前言”,520页)
不惟如此,他还时而嘲笑日本“唯物主义史学家”是“禁欲史学”:“使用无人能懂的术语,借助无人能懂的逻辑展开议论,时而分析,时而综合,最终得出一个无人能懂的结论。”又时而挖苦其为“兴奋史学”,“借助来历不明的资金参加反体制运动,不知何时就会被那只无形的手所操纵而越陷越深,最终身心失去自主,连灵魂也出卖给了别人”(《亚洲史论考》“中卷前言”,521-522页)。对于这样无情的奚落,我们不必要耿耿于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远较前田直典等人成熟,至少不会如彼辈般将隋唐时代生搬硬套进“奴隶社会”。宫崎市定的结论在许多地方反而更接近于我们史学界的判断。
然而宫崎市定的反驳固然有理,仍不妨碍我们严肃思考,他真的如自己标榜的那样,只是一个实事求是而不掺杂理论预设的史料派学者吗?
并非中国的“中国史分期”
值得注意,宫崎市定的结论是“部曲无疑就是具有中世纪特征的隶民”。这里的“中世纪”显然是指日耳曼封建社会。他与加藤繁、前田直典辈不同之处,恐怕不在于一者重史料,一者套理论,而在于双方的参照系不同。加藤繁以奴隶社会套嵌魏晋隋唐史事,宫崎市定则以日耳曼封建社会套嵌魏晋隋唐史事,一样都预设了西方框架。
东京大学那一派不遑赘论,这里且看宫崎市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已论定,中国为地主封建制,欧洲为领主封建制,二者不必十分对应。但宫崎市定研究中古史的方法,正在于找出欧洲封建社会的特点,再一一裁剪中国。平心而论,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魏晋隋唐的豪族虽然有浓厚的封建烙印,但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却远不是西欧那种封君-封臣关系,这点怎么解释?宫崎市定说道:
当时最基层的乡里的豪族代表构成了县政府,县一级的豪族构成了州政府,州一级的豪族进入中央,构成了中央政府。地方长官虽然由中央政府推戴的军阀天子来任命,但这些长官依然是豪族的代表,豪族之间彼此承认既得权益,努力保全自己的阶级利益。纵然没有采用封建制的形式,但却因为采用了封建性的身份制度,地方豪族不仅可以将财产传给子孙,还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给子孙,实现世系。从背面看豪族是地方上的土豪,从正面看却是官僚性贵族,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东洋的近世》,《亚洲史论考》上卷,189页)
这是一段深奥到令人费解的文字。宫崎市定一方面说,从州县到中央的各级行政官员都由天子任命,多少承认了当时中国已然实现职业官僚制度;另一方面他又说,当时中国“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所谓“从背面看豪族是地方上的土豪,从正面看却是官僚性贵族”,但“贵族”与“官僚性”岂非矛盾?一个事物何以既是“A”又是“非A”呢?
再者,“官僚性”十分明显,“贵族性”又体现在哪里?宫崎说,“地方豪族不仅可以将财产传给子孙,还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给子孙,实现世系”。原来所谓“贵族性”“封建性”竟是财产爵位继承权!今天的英国仍有上议院,它岂不尚停留在封建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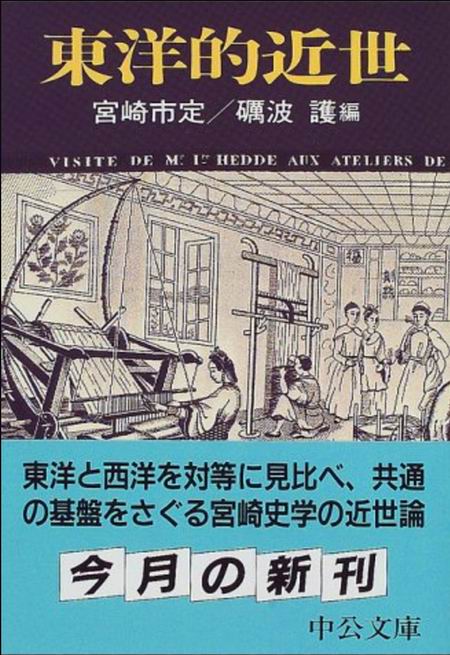
宫崎市定说的“纵然没有采用封建制的形式,但却采用了封建性的身份制度”,实在是一遁词。在这里,宫崎遇到了麻烦。在他看来,西方历史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世纪—民族国家体系这几个阶段,那么中国历史也必须完全套进这几个阶段里去。春秋战国自然对应古希腊城邦;秦汉对应罗马帝国。用他的话说,“在中国,可以说大体上也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从商代到春秋时期,大体上是都市国家(Polis,即城邦)对立的时代,统一了战国七雄的秦、汉,则相当于古代帝国”(《中国古代史概论》,《亚洲史论考》上卷,137页)。这样编排历史当然十分简单方便,然而罗马帝国有编户齐民否?能统一文字、度量衡否?
当然,出于维护其史学体系计,魏晋隋唐时代肯定要对应日耳曼封建社会。确切地说,隋唐天子对应欧洲之封君,豪族对应欧洲之封臣。但是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不是更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君与封臣吗?
宫崎市定答道:“周王统治的本国与诸侯们统治的分国之间,难道真存在着后世所想象的那种君臣关系吗?我觉得他们之间恐怕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同盟关系而已。……西周的所谓封建制度,从一开始就是虽有若无的东西罢了。”(《中国古代史概论》,《亚洲史论考》上卷,143页)这又是一番遁词。欧洲中世纪之君臣难道就不是“一种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了吗?试问神圣罗马帝国又是怎么分崩离析的呢?
宫崎市定在论证魏晋隋唐“豪族封建”时,似乎有了一种战胜马克思的感觉。但他可能不知道,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秉持过“五阶段论”。马克思确实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3页)但是“亚细亚”“古代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封建”三种社会形态并不简单地是线性时间上的前后相续关系,它们倒毋宁是平行并列关系,其中只有日耳曼封建社会能自发地生成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姑且不论马克思的观点是不是种西方中心论,但最起码他很睿智地察觉到,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欧洲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不能笼统地涵盖于一部民族历史。秦汉、魏晋果如是乎?
“物质的传播史”
宫崎市定的问题不应该归罪于他的老师内藤湖南。尽管宫崎一生都在维护乃师的“中国历史分期法”,但二者的学理依据却很不一样。如林晓光便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果说宫崎史学的基本立足点是‘地域’,其主脉在于‘交通’,那么内藤史学的基本立足点便是‘民族’,而根底在于‘文化’。”诚哉斯言!

内藤湖南更像斯宾格勒,他认定各个文明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生命循环周期,其发展各自依据于它自己的幼年、成年、老年,“世界历史就有如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而不是统一的进化脉络。宫崎市定大不相同,“由于基本要素(如铁与马等)向全世界进度不一地扩散,世界历史最终会依循着同样的道路发展起来,只是速度快慢不一而已”([日]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者序”,第6-7页)。内藤湖南在划分中国历史时,更多地考虑中国社会自身的逻辑;宫崎市定在维护师说时,却要以西方裁削中国。
这个差异反映了宫崎市定与内藤湖南根本不同的文明定义。在内藤湖南、三宅雪岭等辈日本政教社成员看来,东西文明存在竞争关系。内藤治汉学,是要将东洋文明擦垢磨光,“以崭新的笔锋叙述之、描写之、批判之、探究之,则其于世界之勋业,庶几可尽‘真’之道”(三宅雪岭口述,内藤湖南、长泽说代笔:《真善美日本人》之第三章“日本人之任务一”,载《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三集“思想篇”,日本评论社,1967年,转引自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35页)。其志在对抗西方物质文明,光大东洋。如他所言:“像世人对欧洲,尤其像是对美国那样顶礼膜拜,在我是办不到的。毋宁说正是因为到了欧洲,我才意识到,所谓东洋文化,乃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存在。”“单单从国家文明设施之类的标准来评判民族文化是行不通的。”(内藤湖南:《论民族文化与文明》,《东洋文化史研究》,133、136页)
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
然而这种“以物质发达评判民族文化”的“行不通的”方法,却是宫崎市定所依据的方法。比如谈到“武王伐纣”,宫崎市定就说,“周人东侵殷商,最终灭亡商朝,其最直接的动机是对解州盐池的占有欲”。比如谈到秦国伐魏,他又称:“秦进取中原最大的目的,依然是魏国境内的解州盐池。”(《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亚洲史论考》上卷,32、44页)
当然,中国历史也不只是解州盐池的历史,它也部分地是战马的历史。如宫崎所说,“由于步兵方阵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行动迟缓,在战斗中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到了战国中期,开始出现了骑兵战术”,“骑马作战,除了马匹的调教以外,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技术条件,这就是护蹄马掌的使用”(《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亚洲史论考》上卷,45页)。于是,一部战国史更像是秦人“为盐而攻伐,因马而取胜”的历史。
不用说,这样的公式不惟于理难通,亦多违拗史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战马运用不输于秦,为何只见秦军为解州而东向,不闻燕赵因盐池而南下呢?宫崎市定反复申说“护蹄马铁”,殊不知骑兵要发挥威力更有待于马鞍马镫,后者的普及至少要等到两汉时期。《亚洲史论考》结集之时,秦陵兵马俑刚被发现。宫崎市定不知秦军方阵的构成,此不足为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把复杂的文明历程化约为一两种物品的传播推广,这本身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宫崎认定,“青铜器和铁都是西亚人发现的,然后再从这里向四处传播,使各地相继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古代史概论》,《亚洲史论考》上卷,137页)。东洋文明也如青铜器和铁器的传播路径一样,是从西亚迁徙过来的。大概西亚人一路东向找盐而至解州,遂有中原文明。这番论调岂不是与法国人拉克伯里那早已过气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如出一辙?
宫崎市定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不忘强调一下,“拉氏的假设,根本就是非常牵强的”,自己则是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起源于西方这一观点”(《中国古代史概论》,《亚洲史论考》上卷,140页)。遗憾的是,通观全篇,我们不惟不知二者的差别何在,更会感到宫崎市定更像是给拉氏辩护。
姑且不论西亚人是怎么找到解州盐池的,单说战国后期东边的齐燕已经逐渐普及了铁器,而西边的秦国却仍以青铜器为主。设若铁器西来,何以其先行于东而后行于西呢?
国民性视野下的日中关系
不知宫崎市定会有上述结论,是否受了巴克尔、兰普雷希特等西方早期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世人受惑于傅斯年辈,多以为兰克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但事实上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之初恰恰是反兰克学派的,这点王晴佳教授早有辩正。参见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四期)但可以肯定,宫崎之能歧出于内藤湖南,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桑原骘藏。例如他在1957年《亚洲史研究》“第一卷前言”中便坦承:“大家普遍把我看作内藤史学的继承者,但我自己绝不这么认为。……若从我试图客观地考察事实、彻底解读史料这一点来说,我的做法似是更接近桑原博士。”岛田虔次也据此认为:“内藤的影响为从,桑原的影响为主。”(宫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第一》前言,京都:同朋社,1957年,第4页;岛田虔次:《宫崎史学の系谱论》,《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页,两处皆转引自吕超:《宫崎市定东洋史观的形成——青壮年期的经历及其影响》,《国际汉学》,2017年第一期,85页)
桑原骘藏
相较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更着力于中国与西域,甚至西方的交往。例如桑原便强调:
西域本身固有的优秀文化不仅从相当古老的时代起就给东洋以影响,唐宋元明时代,西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比想象的多得多。……
我国现行的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排除西域的史实。([日]桑原骘藏:《东洋人的发明》,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14页)
一般认为,宫崎市定会强调“中西之交通”,正得益于桑原骘藏的西域史研究。但如谓桑原、内藤之别仅止于此,就大谬不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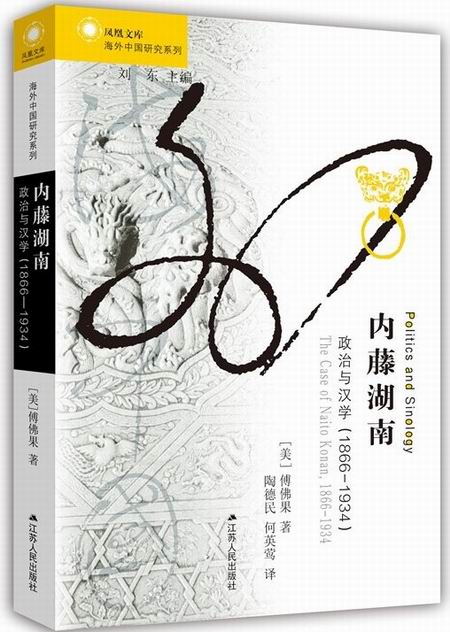
美国学者傅佛果便指出,桑原骘藏几乎是京大东洋史教师中的“一个例外”。按理说京大史学科多有东洋立场,多敬爱中国文化,桑原却“对中国人采取极其蔑视的态度,在讲课时以及著作中经常故意侮辱、嘲笑中国人”([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45、146页)。此人十分推崇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与他在东京大学的恩师白鸟库吉一样,桑原热衷于宣称中国人“天生”具有某些劣根性。比如他举例道:
中国官场有回避制度,地方官不能到本籍就任。科举考试时,若和考试官有亲属关系者,就不得不考虑是否要让他参加考试。很明显,回避的要义在于,排除官吏们因亲属或熟人而作弊的可能,以防上下的猜疑。回避制度之严密正是中国人猜疑心之深的证明。(桑原骘藏:《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东洋史说苑》,177页)
这番话荒唐至极。按照这个逻辑,西方政治更有分权原则,岂不证明西方人猜忌心重到无以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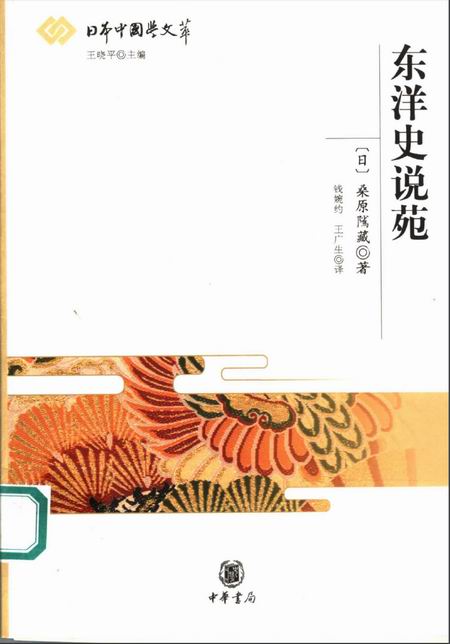
就是这样荒唐的论调,宫崎市定、贝塚茂树等人却要强为之弥缝补苴:“桑原揭示中国的阴暗面是为了让日本人更全面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让日本人从‘尊敬中国’的迷雾中走出来,看到中国的真实面貌。”正所谓“爱就是更好的理解”,桑原之所以这样挖苦中国人,实在是出于“对中国深深的热爱”(参见钱婉约:《〈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东洋史说苑》附录,283页)。
不用说,这种辩护实属强词夺理。彼时日强中弱,日人纷纷向西之不暇,何来“‘尊敬中国’的迷雾”?此公辄曰“中国人天生如何低劣”,种族歧视也是热爱与理解?正如钱婉约所言,桑原骘藏一向贬斥中国传统学术方法,除留学外,几乎没有再踏上过中国的土地,除陈垣外,也几乎不与中国同行交往,“如果硬要说他是‘热爱中国’的人,不仅难以服人,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吧”(钱婉约:《〈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东洋史说苑》附录,284页)。
这些道理,聪明如宫崎市定者又岂会不知?他之所以为乃师强辩,只怕是对此“国民性批判”有会于心吧。有时中国的“国民性”在宫崎市定那里会表述为“文明社会”。例如桑原骘藏曾说,“东洋人的通病是缺乏研究心”,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罗盘、火药,却“历经几百上千年,依然未脱旧态”,反而需要西洋人“迅速地利用或扩大其应用范围”。(桑原骘藏:《东洋人的发明》,《东洋史说苑》,13页)对此,宫崎市定便找到了“缺乏研究心”的原因。他说道:
天文学的知识发展了,但最终沦落为占星术,化学的知识增加了,又演变成畸形的炼金术,其结果,文明越进步,迷信就越盛行,迷信成为扼杀科学发展的凶手。很多人曾经将迷信误解成野蛮的原始社会的产物,但事实正好相反,文明越古老的社会积累起来的迷信就越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亚洲史论考》上卷,125页)
天文学脱胎于占星术,化学脱胎于炼金术,这是毋庸置疑、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宫崎市定为何颠倒常识,仿佛古人本有天文学、化学,到了近世文明社会反而沦落为占星术、炼金术呢?
仔细想来,日本历史远不如中国古老,中华文明已十分成熟时,彼国仍稚气未脱。如果不颠倒正常的社会发展次序,又怎么论证“朴素的”日本胜过“文明的”中国呢?如宫崎所说:“日本人的朴素主义精神,表现为谦虚天真,善恶分明,因此对西方的科学文明有着惊人的判断力。……日本与清朝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以后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亚洲史论考》上卷,126、127页)倘说朴素主义民族能征善战,尚可理解,要说它“有科学判断力”,则原始人岂不最有科学判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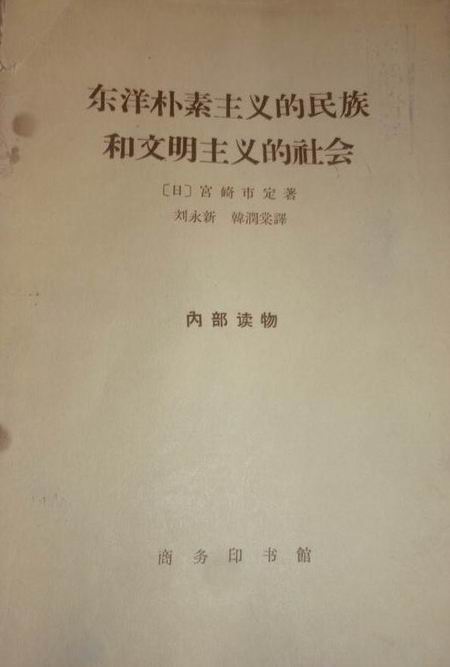
须知类似的论断绝非孤例。例如宫崎市定在1943年结集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中就说,倭寇的目的“绝不是掠夺”,“他们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参与了遭受官府迫害的中国同类的复仇运动中去而已”。“那些倭寇在中国出了一臂之力回到日本后,他们都会说‘做客回来了’,可见他们确实受到了中国同伙的热情接待。”这样的表述直教人分不清,他到底是要客观研究“倭寇”还是要回护日本侵略者?在他看来,“日本人本来就爱好和平,自始至终都只是想与中国民众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通商贸易”。“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到了中国官府与民众的争斗中去了”,其结果也终将是解放中国人民(《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亚洲史论考》上卷,445页)。
又如宫崎市定曾区分了所谓“中国式体制”与“日本式体制”。他指出,“西方人和中国人动辄认为日本因靠近中国而被包含在中国式体制之中,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所谓“中国式体制”当然是那高高在上,无知且自大的朝贡体系。“所谓外交上的日本式体制,就是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对方的体制,在对等的礼节下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举凡外交模式,必居二者之一,概莫能外。他接着指出,“虽然东亚范围内有时也有国家向中国要求平等,但都早已灭亡,只剩下日本数千年来始终维持着平等的精神,这就是日本式体制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亚洲史论考》上卷,445、508页)。其言之凿凿,仿佛欧洲人经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民族国家体系,只是在步日本人的后尘,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只是“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平等外交关系”。
吊诡之处在于,发明了“互利互惠的平等外交关系”的日本却要欧美列强打开国门,教其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不争史实又如何解释呢?
宫崎市定痛心道:“这(指闭关锁国政策)绝非日本肇国以来的国策,不如说是与传统的日本式体制格格不入的政策。”万幸的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回到了原有的立场,在怂恿朝鲜门户开放的同时,也开始向清朝申请基于平等礼节的国家外交”,“如果这种体制(中国式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那么,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东洋各民族,也许就能品尝到数倍的幸福”(《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亚洲史论考》上卷,508、510、515页)。看起来中国与朝鲜还要感谢日本呢!大和民族不怕牺牲帮助中国人解放自己,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拒斥呢?
“救世主”与“终点站”
人们也许会说,宫崎市定之所以如此,实在是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毕竟此公在1925、1932、1945年数次服役于日本陆军。确实,宫崎在战后开始清算军国主义了。例如他撰写《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一文,便直指分别掌握日本陆海军的长州、萨摩两藩。

宫崎揭露长、萨二藩本是幕府锁国政策的寄生虫。美国佩里舰队迫使日本放弃“锁国政策”,致使萨长武装走私集团无利可图。彼辈遂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希望日本重新闭关锁国,“其实是想维护自身的走私利益”(《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亚洲史论考》下卷,1318页)。其结果呢?
萨长终于得到了天下,锁国也好,攘夷也好,自然是不可能的,明治元年即发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宣言。对照此前的所作所为,这简直就是在愚弄人。这时,他们就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皇室,仗着这是天皇对天地神明的誓言,绝不可违背,从而把过去的事情全都一笔勾销了。从整个经过来看,最了解开国益处的本来就是萨长二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愿意把开国获利这样的好事交给幕府来做,而必须要在自己的统治下亲自决定开国。不拘任何主义,根据现实需要转风使舵,这就是萨长政治家们的绝活。(《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亚洲史论考》下卷,1323页)
“转风使舵”一说,可谓入木三分!然而对比战前宫崎市定大肆颂扬彼辈“尊王攘夷”论者,谓其促使日本回归“肇国以来的国策”,真令人感到反讽。
宫崎市定对于长萨二藩和德川幕府的评价可以随势而变,然其对中日文明地位的论定却始终不变。宫崎在战时撰写的《中国的开放与日本》一文中曾说:
在欧美的压迫下,东洋各国或被征服,或沦为半殖民地,唯有日本不纠缠于应对的方式,只要无碍大局,就可以听该听之言,斥该斥之物,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日本式体制的基础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亚洲史论考》上卷,516页)
此乃将日本打造成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而到了1958年的《东洋史上的日本》,救世主日本就改头换面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点站”。
日本的古代文化,从性质上说来,可以把它叫作“终点站文化”。……
……从遥远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出发的卡车部队,到达了终点日本,在这里卸下了车上的货物。(《东洋史上的日本》,《亚洲史论考》下卷, 1334、1336页)
至此宫崎市定终于说出了他“世界史研究”的实相。对此,王广生先生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坚持世界文明起源一元论即西亚文明历史先进论,客观上也就否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立性,逻辑上也为其日本文化作为近代史上汲取东西文化之精华而成为后发而起的‘结晶文化’做了铺垫。”(王广生:《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国际汉学》,2015年第三期,110页)所谓“解州盐池”“西亚铁器”,还是“宋代近世”往往都以此为线索,贯穿而成。
准此而论,上述种种结论正根植于宫崎市定的史学理论。不知宫崎市定是否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殊途同归了:他们都以某种国家形式为人类历史的终点和文明等级的顶端。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世界精神的最终承载者是日耳曼,到了宫崎市定这里就变成了日本。

谷川道雄先生在《“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总序》中善意地提醒我们:日本第二代中国史学者多成熟于1930年代,他们的研究不可能不带有这一时期的烙印(参见[日]谷川道雄:《“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总序》,《亚洲史论考》上卷,序言第2-3页)。他的提醒,发人深省。宫崎史学之广博深邃当然是不容否定的,许多成果必不因立场而丧失其价值。这里之所以集矢于宫崎市定的史观,并不是否定他的成就,而是要通过这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一窥近代日本学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十分感谢张学锋、马云超等教授学者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能翻译出版这部巨著。他们的努力使我们有机会知晓宫崎市定的思想内核。相信这套书的意义远不限于国外某同行的研究,它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不只史学史研究者需要认真对待此书,近代政治史的研究者同样值得认真研读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