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答辩·《中国剧团在东南亚》︱作为跨地域历史线索的戏剧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张倍瑜与四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1900-1970年代》(Chinese Theatre Troupes in Southeast Asia: Touring Diaspora, 1900s-1970s)。本文为评论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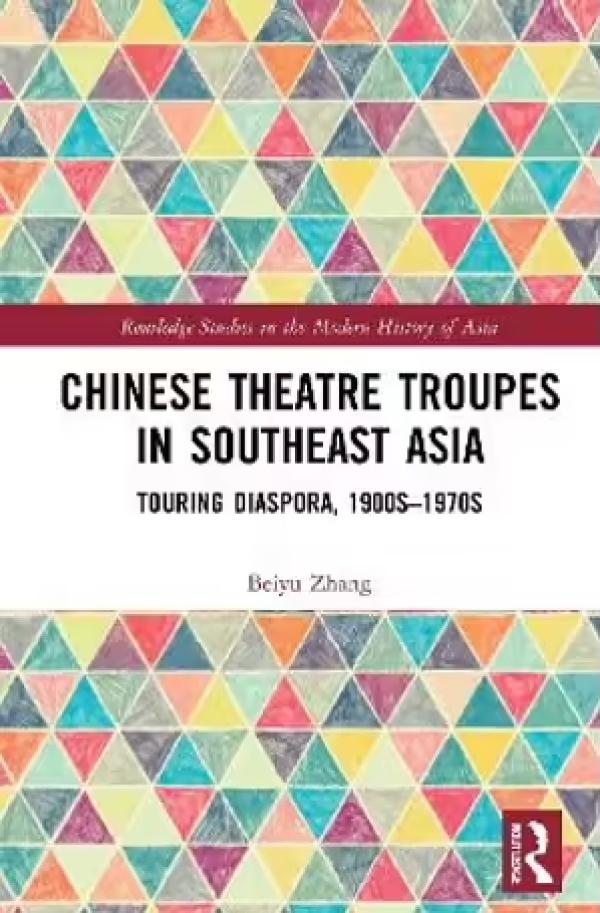
张倍瑜著,《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1900-1970年代》( Chinese Theatre Troupes in Southeast Asia: Touring Diaspora, 1900s-1970s)
在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历史联系的讨论中,海洋贸易、人口迁移、宗教信仰常是绕不开的关键词。但是,与上述移民、信仰、商业伴随始终的地方戏曲,却常常被划入戏剧学者的领域,而鲜少为历史学者重视。开拓此一领域的新著《中国剧团在东南亚:离散地的巡回表演,1900-1970年代》,以张倍瑜博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位论文为基础,经过作者在澳门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扩写,最终成书。该书以戏剧为题,所讲述的历史却大大超出了戏剧史所涵盖的范围。与其说是戏剧史,说该书是一部以戏剧为线索的跨国史、离散史研究或更确切一些。
《中国剧团在东南亚》一书依据讨论的时间分为两部分,大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构成第一部分的前四章,分别就移民网络的形成和其中的流动性的相关议题展开探讨。内容涵盖了早期移民社区中戏剧空间的形成、潮剧团的跨国演出、上海中国歌舞团的南洋巡演和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的筹款演出。第二部分的三章则前后相续,对冷战之下潮剧团、潮剧电影在香港和东南亚的传播和适应策略进行分析,并考察香港演出团体在新、马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章从早期依附于神庙的戏台和戏棚出发,追索自庙宇剧场、戏园到近代剧院和游乐场的发展历程。远自马六甲青云亭的设立始,庙宇便成为移民社区进行自治的重要场域。用于娱神、酬神的戏剧,也在社区中心的庙宇进行展演,在服务于精神信仰的同时,也以神明之名满足早期华人移民的娱乐需求。随着华侨社区的壮大,与华人财力的积累同步,上述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早期简陋的戏棚,得以在庙宇的兴修过程中演化为固定的戏台,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庙以外,另一个得以观赏戏剧的传统空间是戏园。自19世纪末,服务于不同方言戏曲的中国戏园在海峡殖民地纷纷涌现。他们作为娱乐业的一部分,起初与妓院和赌馆比邻,因不洁的名声而成为殖民当局后期整治的对象。在丽春园等传统戏园接受新式改造后,一批以“舞台”“戏院”为名的新式剧院开始登场,但仍为管治者眼中缺乏秩序的空间。待到20世纪20年代,以邵氏为代表的娱乐业巨头开始在南洋各埠引进已兴盛于沪港两地的新式戏剧空间——游乐场。游乐场的跨国运营既依托于已有的商业网络,同时也强化了这一网络内的流动性。作者用以例举的邵氏便通过集团内的资源共享,逐步打造出一个涵盖了电影制作在内的娱乐帝国。通过对戏剧空间载体演进过程的研究,该章阐述了海峡殖民地的剧场地景如何随着殖民政策、移民建设的脚步而改变,成为后续各章中容纳剧团展演的重要空间。
接续首章对硬件设施的探讨,作者在第二章开始切入剧团这一“软件”,开启了对本书中心议题的论述。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对潮剧和潮汕移民群体的关注,是本书区别于过往研究的亮点之一。作者利用第二章简要介绍了潮人下南洋的历史路径并深入梳理了传统潮剧戏班的海外发展史。经过清中叶的大规模移民和海洋贸易,潮汕人在东南亚各地建立起社区,尤集中于暹罗。潮剧戏班的运作与移民社区密切互动,因与赌业等传统娱乐业相混杂,早期戏班常需借助秘密会社的力量以与海外接触,将戏路延伸至移民社区,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和更响亮的名声。随着海外潮剧受众和戏园的蓬勃发展,前往海外演出的戏班在通过宗族扩展支脉的同时,也试图与戏园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以使自身在竞争中更为突出。时至民国,作为戏剧艺术中心的上海对潮剧也产生了影响,通过赴沪学习和聘请沪上名家的方式,潮剧尝试了颇为新奇的改革,或将西式文明戏与潮剧相结合,或将声光电的布景搬上潮剧舞台。另外,受海派京剧启发而排演的长连戏,也在曼谷大获成功。域外的潮剧发展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原乡,如在暹罗,因法律和演员自杀的事件影响,潮剧戏班的童伶制先于潮州得到废除。该章以潮剧的赴沪演出作结,围绕此番演出的媒体报道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戏班在南洋收获的名声,展现了循商路而成的戏路如何使一个极具地方性的剧种完成跨地域的艺术交流,进而得到主流文化的认知。
在之后两章中,作者稍微转移了对潮剧的关注,将目光投向两个特殊的演出团体。以上海的中国歌舞团为主角的第三章,叙述了黎锦晖带领该团赴南洋巡演的历程。作者首先借该章对黎锦晖进行了深描,将他推进国语运动的努力与他此后鼓吹的童谣教育和流行歌曲创作相联系。黎在上海的声名鹊起,为1928年5月中国歌舞团的南洋之旅开启了门路。透过跨国唱片公司的商业网络,歌舞团南下巡演的消息在东南亚频繁见报,引起当地城市精英阶层的兴趣。不过,尽管南洋已有华文学校使用上海出版的国语教材进行教学,黎的作品也通过这些学校而得以在异国传播,离散地混杂的语言环境还是让他感到困惑。与此对应,歌舞团在演出选曲上也强调了此时盛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此种对中华民族的宣传在南洋各埠的受容度有着显著差异,于英国殖民地和暹罗未受阻碍的歌舞团,在荷属东印度却引起了殖民当局的疑虑和干涉。1929年2月,完成了在巴达维亚的演出后,黎锦晖宣告了歌舞团的解散,为这场代表非左翼五四新文化的南洋之行画上了句号。
在第四章的讨论中,作者将抗战期间的武汉合唱团作为主角。不过,该团在海峡殖民地和英属马来亚的成功巡演,还应归功于与之分量相当的配角——即以南侨总会为代表的离散地救国团体。与中国歌舞团不同,得益于南洋救国团体垂直的层级架构,武汉合唱团除在城市演出筹款外,更深入到热带乡村的矿场、种植园进行巡演。在演出中,该团还巧妙地融入了南洋特色,将《放下你的鞭子》一剧改编为“逃难”系列,根据演出地的不同而更换剧名(如《逃难到星洲》《逃难到笨珍》等),并在察觉到街头演出式的筹款环节与剧院不相适应后,及时调整策略,选择神庙前地作为演出场所。不过,合唱团的演出也同样引起了殖民当局的焦虑。虽然该团为国民党背景,但因同时期的马共同样组织起支持中国抗日的后援会,英殖当局出于防共,仍对武汉合唱团的演出进行监视。尽管如此,武汉合唱团的巡演依然募款颇丰,南洋华侨也得以通过它来对母国表达有力的支持。
第二部分的三章均在冷战阴云下展开,讨论剧团演出和戏剧电影在多方势力交织中的跨境旅行。第五、六章重回潮剧议题,由1950年代潮剧的社会主义改造谈起,叙述至改造后新潮剧在香港受到的热烈欢迎,并进一步延伸到左、右翼电影公司在港产潮剧片上的竞争。1950年代的潮剧改革在形式上要求剔除传统潮剧中的“封建主义”色彩,废除童伶制,并抛弃传统戏班资本主义式的逐利行为(如长连戏的演出)。此外,在艺术上,戏剧改革部门要求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作为指导,深入发掘角色的表达内涵。经历数年的改革后,新潮剧在广州、北京的汇报演出均得到党政官员和戏剧权威的认可,并于1960年踏上了赴港演出的旅程。这场该年5月份的演出,原定播放有关汕头社会主义建设的纪录片,但当局在考虑软化宣传的策略后,决定将之替换为由广东潮剧团担演的潮剧。更具传统色彩的潮剧在规避了政治争议的同时,也传达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有力革新民族艺术的形象。融入现代表演技巧和编排的潮剧使香港潮人眼前一亮,即使对此次演出大加抨击的右翼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剧团中姚璇秋的演出之出色。新潮剧的表演迅速在香港引发了“潮剧热”, 以长城、凤凰、新联为代表的左翼电影公司由此开始与大陆剧团合作,推出面向香港和东南亚的潮剧电影。与此同时,以邵氏和国泰为代表的右翼公司,连同东山、潮艺等“非左翼”公司,也都纷纷投入这一门利润颇丰的生意。可以想见,潮剧电影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作公司政治背景的影响,此种影响在冷战之下的东南亚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化。在奉行亲美反共路线的泰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左翼公司的潮剧电影被拒绝进入潮人云集的泰国,而香港的右翼电影公司则与泰国的潮剧演员达成了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左右的界线在新加坡则显得十分模糊,常被定义为右翼的邵氏也会接手发行来自长城的潮剧电影。类似的灵活性更大程度上出自对作品质量的认可和现实商业的考虑,譬如香港右翼潮剧团新天彩,便通过学习左翼公司制作的电影来提升演出水平;对许多声称支持右翼的非左翼公司而言,比起政治倾向,它们更多考虑的只是中国台湾和泰国的市场。通过香港的潮剧电影,中国大陆得以绕过与东南亚在冷战期间的政治隔阂,与海外华人达成文化联系,并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案例寓于其中,进行隐晦的宣传。

1961年香港新天彩《扫窗会》剧照
第七章是本书相对特殊的一章,比起前文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关注,该章将焦点放到了东南亚的区域政治上,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进程为主要背景,探讨香港的左翼剧团如何在两地(国)处理“中华性”(Chineseness)的踌躇中发挥作用。随着冷战的开展,华文学校等与中国相联系的组织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打压,但借道香港传播的左翼文化却更加受到当地反殖力量的追捧。以新加坡为例,反殖期间产生的左翼同情一直延续到了自治时期,此时的新加坡正在努力寻求多元文化的融合。作为华族文化的代表之一,由长城公司旗下六名电影明星组成的香港剧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了1959年底的国家忠诚周演出。作为服务于国族建构的活动之一,此次演出得到了李光耀的欢迎。而对中国而言,长城剧团的演出则成为展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利机会,通过戏曲和民族舞蹈的编排,此次演出通过渲染“中华性”来彰显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而后新加坡虽为求并入马来西亚而坚定了反共立场,但与左派相绑定的“中华性”仍成为人民行动党争取左倾阶层支持的工具,例如在该党支持下,新加坡仍于1962—1963年放映了中国大陆的电影《刘三姐》。虽得偿所愿并入马来西亚,但新加坡很快因为与“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不相容的多民族政治主张而于1965年被逐出。面对多元民族整合的压力,华文教育随即受到压制,但香港左翼电影明星剧团很快又于次年的8月获邀到新加坡巡演,作为严肃文化的代表,服务于当局正在推动的“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另一边,马来西亚政府同样将邀请香港剧团作为政治手段。1971年马来西亚深受洪灾之际,香港左翼剧团应邀到吉隆坡演出,得到阿都·拉萨的欢迎,并成为其外交政策转向的表征之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通过非官方渠道开展了多番接触,并最终于1972年正式建交。作为“中华性”的代表,香港的左翼剧团成为中国大陆与新、马两地维持潜在联系的桥梁,也作为政治资源为两国在国家建构和政策转向中所借用。
完成这样一部跨学科、跨区域研究的著作绝非易事,难点之一便在于面向不同专业读者的平衡讲述。研究戏曲的读者对历史背景、社会情形的了解或有欠缺,研究移民史的读者则可能在艺术知识上储备不足。本书作者在背景知识铺陈上的把握相当出色,书中不断缩进观察视角,在讨论具体问题前将全局中的要点加以点明。同时,又通过插叙将“逃难”系列和潮剧《扫窗会》的艺术分析融于对剧团行为内涵的论述。面对错综复杂的东南亚,跨区域方面的研究难点,则在于准确区分南洋各埠之间分异并结合各不相同的历史语境进行研究。无论在讨论殖民时期的英、荷政府,还是分析冷战期间的新加坡和泰国,作者都相当敏锐地关注到差异环境对当地华人社会及巡游剧团产生的重要影响。
另外,本书在跨国史层面对潮剧的关注,也为当前的潮学研究添砖加瓦。深耕潮汕史的黄挺教授,曾提出应将潮汕置于“中国”和“重洋”之间加以考察。具体到近代潮汕史中,“汕—香—暹—叻”贸易体系已成学者反复讨论和广泛接受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于近作《遥远的海岸》(Distant Shores)中,进一步将“海洋潮州”的范围描绘为从上海一直延伸至曼谷及海峡殖民地的广阔海域,这一范围恰好也覆盖了本书作者所考察的若干城市。以往的潮汕海洋史,多重对海洋贸易、沿海盗寇、侨商巨贾或宗教信仰的研究,对于戏剧艺术的传演少有深入探讨。而过往的潮剧史研究,虽也将海外的潮剧发展囊括在内,却缺少如本书对潮剧与当地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如导言和结语所强调的,相比于实实在在的演出,中国剧团在东南亚行动中的“表演性”对学术研究而言更为重要。如“中华性”等精神内涵的表达和接受,在离散地政治环境和历史进程中何以发挥作用,构成了本书讨论中的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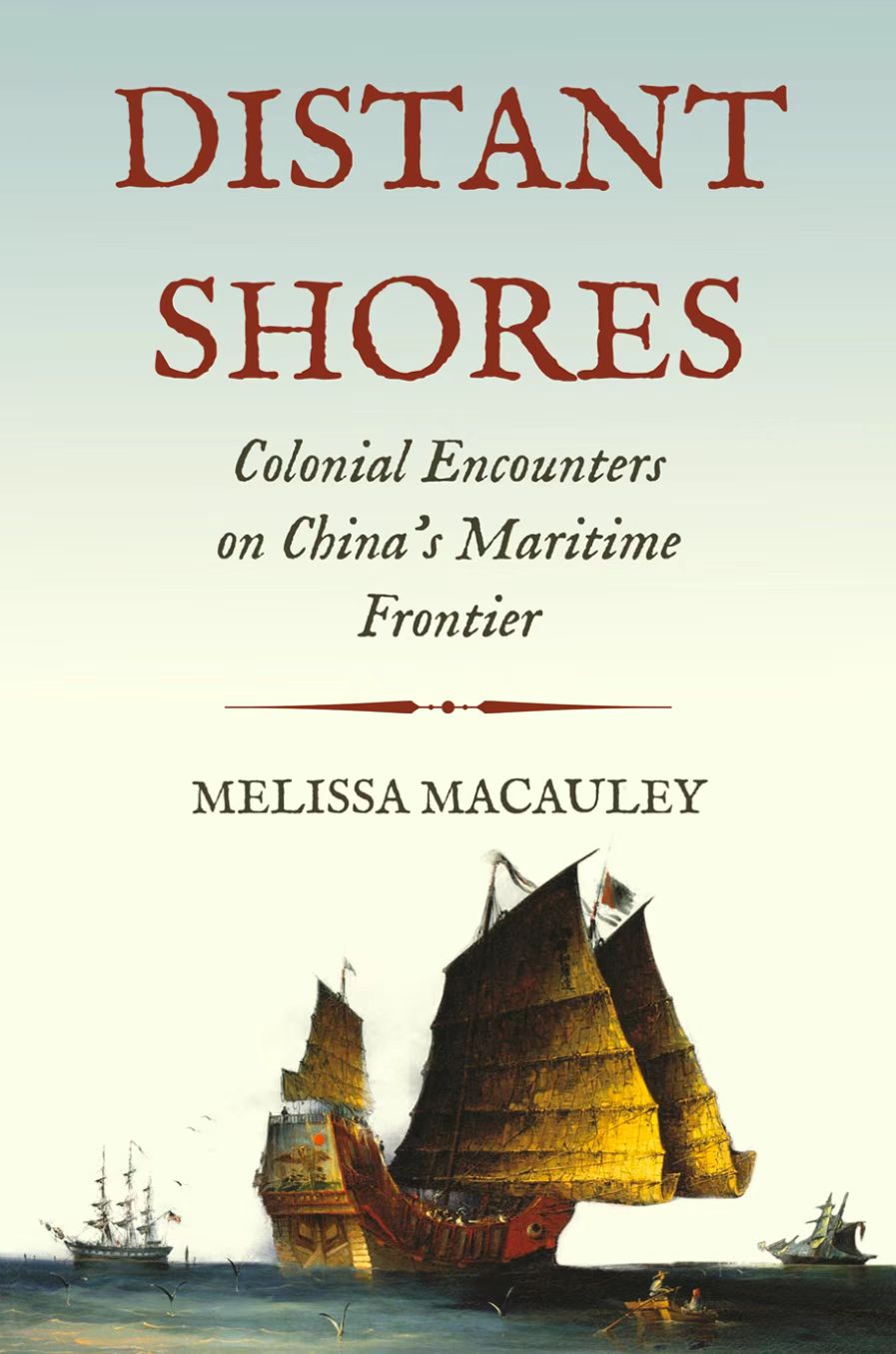
《遥远的海岸》
白璧微瑕,本书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相对于通贯的专著,本书在体例上更接近于一册主题相近的专题研究合集。各章之间虽有线索相连,但在第一部分中,无论对象差异或时间跨度都有过大之嫌,对读者而言,阅读时难免感觉跳跃过快,其间尚有不少空白不曾填补。另一方面,在史料的运用上,作者相当倚重于报纸的围绕剧团演出所作的报道。此一方法用于专门分析左、右双方立场的篇章时便恰如其分,但在用以讨论离散地受众之反应时,则难免因媒体对夸大而失之片面。
此外,在具体史事上,还有三个问题斗胆向张博士请教。第一,书中注意到了潮剧改革中对传统程式和社会主义新风的平衡对待,不过因主题要求,更多偏向于论述其中“新”的因素。事实上,在1950年代潮剧改革中,对于旧剧目的抢救和发掘也一并进行,文中重点分析的《扫窗会》便是这一工作中的典型。笔者好奇的是,改革早期的这一发现“旧”的工作,于日后对外宣传新潮剧时着意强调的“传统文化”起到何种作用?
第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改造中强调了对剧情的理解和人物的塑造,但书中在处理这一过程时较为粗放地将改革者等同于代表集体面貌的工作组,不知可否在谈谈潮剧的导演制改革及导演这一关键角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末章将大量的篇幅给予新、马两国建设历程中的政治气氛、族群关系等议题,本书主题关注的剧团巡演似乎成了片断式的陪衬角色。不知对于香港及内地,在面对演出邀请时是否也会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作出相关讨论和决策(除文中已提及的节目安排外)?过程如何?或者说,是否有史料能用以研究该问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