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孔夫子吐痰吗?民国“新生活运动”对国人素质的改造
面对西方时,近代中国人不仅感到自己国家在国力上积贫积弱,也在切实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到“文明”的焦虑。在生活方式上强调“脱亚论”的日本引入了一整套西方对身体的控制手段:军事化管理、西方礼节。面对这个迅速现代化崛起、击败自己,又继续虎视眈眈的近邻,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感到一种强烈的迫切感,试图从基本生活方式入手改造国民性,以图改变国力贫弱的颓势。
蒋介石政府于1934年推出的“新生活运动”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执行。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试图改变从育儿到就餐的一整套国民习惯。这一运动在其施行过程中——如《教养身体的政治》一书作者深町英夫所揭示的那样——混合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诉诸儒家伦理,却又另一方面时时刻刻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置于西方式的他者目光之下。1930年代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与中美,中日关系的走向决定了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足够发动民众参与。而在作者看来,这场运动背后的焦虑感和迫切感直到今天仍未结束,仍然或多或少左右着中国人对待他者,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和行为。
本文节选自《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书第一章《苹果的回味——思想》,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孙中山与“不雅”的华人
中国人之举止动作的“不美”早已为一些早期革命家所意识到。1896年,居住于日本横滨的第二代华侨冯自由(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经历了极其痛切的一次体验。他当年虚岁十四,由父亲冯镜如(后来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派往东京,和另一个中国少年一同肄业于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晓星学校。该校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学生中居住于横滨的西洋人子弟占三分之二,其余是日本人,中国人仅有他们两个。于是,西洋学生“恒歌中国人污秽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两个中国少年不得已每于休息时间藏在厕所附近的小院里,西洋学生则“扬言华人多患腹泻”。冯自由在此校学习四个月后,“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
但不敢告诉父亲实际情形,仅说不愿意学法文而已。1899年,章炳麟为了摆脱戊戌政变后的弹压而亡命日本东京,逗留在梁启超的寓所,但不了解日本习惯,“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冯自由当时亦下榻于该处,故而获悉了这一奇闻。亲身经历过以卫生为借口的种族歧视之后,又亲眼目睹了被视为祖国、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学大师”的如此举止动作,不难想象当时年轻的冯自由所受到的心理打击之大。
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逗留时,有一天与汪精卫、胡汉民、邓慕韩、张永福等一些同盟会会员聊天,谈到外国人之善于清洁。有人赞赏欧美人,有人称赞日本人,得不出结论。于是,孙中山说道:“若以清洁论,中国人亦有一部份〔分〕之人其净洁逾于其他各国,或可谓各国不能及也。......二三子不留心耳,我国好洁净之人,自成一族,不啻有数万人,汝等均所深知熟见者也。......其人迩在目前,即广州河下之蛋家是也。蛋家一族之讲求洁净,自衣服以至寝处,无不惟净惟洁,一尘不染,是其素性,为外国人所不能及。彼等虽穷无立锥,而其爱洁净之习惯并无少懈,此人所常知而彼等反忽之,此亦中国人每好舍近求远之弊。如我人能择己之长,去己所短,发扬光大之,则中国人社会乌至于停顿而不能进化也。”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举三个实例来说: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跻〔济〕跻(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倒〔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迷(excuse me)。”
上列逸事都显示出,这些早期革命家已意识到了中国人的举止动作成为外国人惊讶、困惑、蔑视的对象这一事实。但是,他们未必认为中国人在本质上劣于外国人。例如,孙中山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解释方式,即将其解释为《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被忽略的结果。他说:“象〔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然而,他通过外国人的眼光才发现了自己民族之身体的“不美”,故而提倡云:“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要按照外国的标准来注意自己身体的美观,以此改善外国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且,孙中山自己的生活习惯与章炳麟完全相反,“经月不见唾涎,不见吐痰,遇有稍咳以巾掩口,遇有嚏涕,亦以巾承拭,巾一日两换为常。”这无疑是他们海外生活经验的多寡所导致的差异,即曾在夏威夷、香港受过教育的孙中山和初次走出国门的章炳麟在经历上的不同,而与两者对中国传统学问、文化(“修身”)的了解、素养程度无关。孙中山的此种担忧和期望后来都传递给了他的继承者——蒋介石。
留日经验:蒋介石如何看待自我约束?
1906年,正值清末留日热潮的顶峰时期,年满18岁的蒋介石在负笈东瀛的船上遇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中国同学漫不经意地吐痰在船头的甲板上,其时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就走过来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扔掉。’”
蒋介石在东京清华学校学习了半年多的日语之后回国。1908年,他再赴日本进入振武学校,这是日本当局于1903年专门为了收容希望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等的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教育学校。蒋介石此时的生活状况可从该校的《斋房条规》得以了解,这份资料显示出了当年日本人试图促使中国人接受的公私生活规范。
为了维持身体的规矩和清洁,“每日设有汤【热水】浴,以备洗澡”。“学生装扮,务须齐整洁净,从起床至就寝时,必应照制装扮,为要”。学校要求学生们在满足其生理欲求时(睡眠、饮食、排泄等),也要控制住自己身体的欲望,以维持周围环境的秩序和卫生,即“每晨闻有起床号音时,急速离床,照制装扮,并将寝具,按式整顿;起床后,非有就寝号音,不得擅自就床,……不得互相搅扰安眠;每日三餐,自有号音,早餐及午餐,须以半点钟内食毕,惟晚〈餐〉准一点钟内食毕;食饭时,不妨彼此间谈,惟不得喧哗杂乱;厕房内,各须留心,不可污秽;斋内及廊下,不得吐痰,或抛弃尘芥”。
如此,振武学校的《斋房条规》所提到的范围虽局限于该校内部,并未涉及一般社会,但它明确地要求全体学生须对整个学校的规矩和清洁负责。
蒋介石于1910年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驻屯于新潟县高田的野炮兵第十九连队,实习了一年多的时间。此时,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了陆军省编纂的《军队内务书》的约束。此书详细地列举了兵营生活的规则。例如,为了维持身体的规矩、清洁,“除了规定的时间及场所之外,不许任意吃喝”;“起床后到点名为止,日夕不许躺在床上”;“纽扣、风纪扣、带扣等皆不准解开不理,穿着裤裙时尤其要注意”;“时常洗澡,洗涤头发、脸面、手脚,剪指甲,刷牙齿,全身要维持清洁”。关于周围的环境,同样需要注意秩序和卫生,即“起床后,开窗户,将毛毯及床单挥动并精心地折叠,把枕头夹在褥子和卧床中间,洗脸,擦武器,整顿衣服,照料马匹,给其喂草”、“熄灯后,不准妨碍别人的安眠”、“室内要经常维持清洁、好好整顿,物品不要乱放或带到规定以外的场所”、“不要在室内、走廊及从窗户上向外吐痰”。
为了监视各项规则的执行情况,“中队长要于每周六下午进行清洁检查,以便查看其所属物件的保存、维修状况是否良好”;“军医要时常巡视兵营内外,注意各项卫生规定是否确实得到执行,并视察士卒在练兵中的动作,注意其对健康的影响”。蒋介石又回忆云:“他们军队官长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戴〕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即是内务整洁尚未作〔做〕到实在,必须重新作〔做〕过。其次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到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求合乎规定——限定其容积总量三分之一。”
近代日本亦展开了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卫生知识的启蒙、教育。例如,森林太郎将上述的《陆军卫生教程》简化为《卫生学大意》,1891-1892年连载于《女学讲义录》上。1900年创作的《卫生唱歌》提倡云:“晚8时就寝,早7时起床,好好漱口、洗眼、擦脸、梳头。……所有食物饮料,都常吃八分饱,食后休息一会,然后开始运动。吃饭后勿立刻洗澡,洗澡时要用肥皂,好好除掉身上污垢。”由此可见,一般民众也要和军人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讲求规矩、清洁,以便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国民。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和野炮兵连队服役过程中学到的,正是明治时期日本正在引进、普及的对身体的“教养”。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不仅把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看作身体美观的条件,而且将其视为管理、锻炼身体的要点。在冬天普降大雪的新潟县高田,新兵们“每天早晨5点钟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之后,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冷水来洗脸”。蒋介石“少年时的体格就不好”,但是在高田期间,“用雪满身洗擦,或是用冷水,这样洗澡临苦锻炼,后来这身体才能够慢慢强健起来”。此外,“每人每餐规定只许吃一中碗的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饭的上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他当初“肚子里常常觉得饥饿......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来充饥”,可是“到了第三星期,虽不到酒保去购食饼干,也就不觉饥饿了”。
根据这种亲身体验,蒋介石提出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如下见解: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常常洗冰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能终年用冷水洗脸呢?普通那〔哪〕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将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普通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穷的人家,就只早晨烧一次,日中出去工作,就带一包冷饭。……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不然,打仗的时候,你要等水烧热以后来洗脸,又要等饭烧热再吃,敌人已经将你包围好,还了得吗?
这意味着,即使在进行洗脸、饮食等这种私人行为时,个人也要牺牲自己对身体舒适的追求,以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秩序、卫生的意义,在于个人通过自己身体的“禁欲”、“苦行”,由此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为集体利益贡献的潜在力量。蒋介石认为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学习的富强之源。简言之,他在日本学到了将军队式的规矩和清洁普及到全体社会,由此“教养”人民的身体、为国家动员做准备的必要性。孙中山等先行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之举止动作的美观,而蒋介石则意识到了“教养”身体的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即创造近代国民的必要性。
新生活运动的四大主轴
新生活运动企图实现、维持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由此将中国人民改造成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近代国民。此亦意味着,蒋介石要根据自己的留日经验对中国社会进行军队式的组织化整顿。
如何显示我的身体?《新生活须知》有三种版本,第一种是序章已引用的版本,即新生活运动开始时由蒋介石的心腹邓文仪起草,并由程时煃、黄光斗(亦皆为蒋介石心腹)审查的《新生活须知(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第二种是由蒋介石亲自重订后于5月15日发表在全国各大报纸上的版本。第三种是7月30日载于《中央周报》上后并未流传的版本。与仅列举95条规定的初稿不同,第二种版本是以四字一句的形式写成的《千字文》式的韵文,也明确地表示要以四维(“礼义廉耻”)为此一运动的理论根据,但其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与初稿大致相同。第三种版本的形式和性质则居于前两种之间。就围绕衣食住行之具体规定的内容而言,后两种与《初稿》几乎一致,是故笔者将对《初稿》进行分析,探讨其有关身体和举止动作之规定的含义。
《新生活须知》寻求维持、实现“规矩、清洁”的对象,可分为下列四个范畴。
(1)自己的身体
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人检点自己身体的卫生状况,这包括照顾尚未具有自我检点能力的儿童。首先,身体的各部分及整体要受到日常的、定期的净化,而且饮食清洁、接种防疫也要得到足够的注意,以防止各种异物混入身体损害健康。同时,人人要操作其身体模仿几何学图形(“行坐要正直”“眼要向前正视”),身体的外表要经常服从衣着的形状,而且衣着也要尽量保持其原来的形状、质量(“衣服要干净”、“衣服破绽要补好”)。然而,各种身体欲望(食欲、性欲、睡眠欲等)要时常抑制(“不要去嫖赌”、“不吃鸦片烟”、“早起早睡”、“不要吃零食”、“不酗酒”、“不吸烟”)。如此,新生活运动提倡每个人不断地用精神力量来管理、控制自己的身体,换言之,即把身体看作被动的客体,把精神看作主动的主体,并由精神经常对身体进行保护、规范。故此,这种管理、控制、保护、规范的标准不是自己身体内部自然产生出来的欲求,而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并由精神来规定的人为秩序,即身体美学。
(2)与别人的关系
每个人虽需要努力同亲人(“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邻人(“邻人失火要去帮助”)、友人(“对朋友要讲义气”)等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也要节制其私人交往(“无谓应酬要减少”、“婚丧喜庆要节俭”)。此外,人们不仅对熟人要有礼貌(“早晨相见要说’你早’”、“相别之时要说’再见’”、“见了长辈要敬礼”),而且对于所有的外人,与其交往时也要采取殷勤的、诚实的态度。具体而言,在见面、说话、工作等方面,都得控制自己尊重对方(“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不要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凡事要讲道理不要吵闹”、“说话态度要和气”、“走路时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做买卖必须公平”),且要为非特定多数的陌生人(尤其是遇到困难的人)着想,考虑、谅解、满足他们的感情和利益(“人有丧事勿嬉笑”、“别人打架要劝解”、“见人跌倒要扶救”、“拾到东西交还原人”、“对于妇孺要礼让”、“上下车船要帮助妇孺老弱”)。
如此,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外人看作跟自己一起构成共同体的伙伴。具体而言,他们不但要扮演亲人、邻人、友人等人际关系的具体角色,而且要作为抽象的一个个人维持并调和整个社会的秩序。换言之,每个人要把自己视为其所属社会的一个成员,需要具有公共意识。
(3)周围的环境
即使在人们满足其生理欲求时(饮食、排泄等),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举止动作,以免影响到周围环境的规矩和清洁(“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喝嚼勿出声”、“不要到处吐痰”、“不要随地小便”)。这种规矩和清洁不仅需要经常在自己的居室内(包括家具、什物等在内)得到维持(“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家具要简洁”、“居家要清静”、“被褥要常晒常洗”、“房屋要常常打扫”、“窗户要多开”、“桌椅要干净”、“厨房要干净”、“碗筷要干净”、“厕所要干净”),而且在自己住宅的外围需要同样执行(“沟渠要常常疏通”、“苍蝇要扑灭”、“蚊子要扑灭”、“老鼠要捕杀”、“垃圾倒在垃圾桶”、“字纸不丢马路上”、“晒衣服不挂在街上”、“家家天天要打扫门口的街道”)。
如此,他们不仅要维持自己身体的美观,也要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以求将周围空间的规矩和清洁优先于自己身体的生理欲求。这意味着,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周围空间的一部分,由精神(理性)管理、控制身体(欲望),思考、寻求整体环境的秩序和卫生。换言之,他们需要根据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把自己的存在相对化,使其服从于周围的空间。
(4)公共的场所
每个人利用公共场所和参加公共活动时,要节制自己的声音来维持周围环境的肃静(“开会看戏要肃静”、“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在〉饭馆茶店不可大声喊叫”),也要对其规矩和清洁负责任(“公共场所出出进进一个一个顺着走”、“爱惜公物废物利用”、“集会场所要脱帽”、“进了房屋不戴帽”、“果皮不要随地乱抛”、“广告不乱贴”、“车站码头要清洁”、“公园戏院要清洁”、“饭馆旅馆茶店要干净”、“洗澡堂理发馆要清洁”),而且移动时要以抑制自己服从公众,来维持公共交通的秩序(“走路要靠左边走”、“走路不要争先”、“走路不要吸烟”、“走路不吃东西”、“走路不要大喊”、“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上下码头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此外,人人要操作其身体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升降国旗要敬礼”、“唱党〈歌〉国歌要起立”)。
如此,每个人要由精神(理性)管理身体(欲望),控制自己的举止动作,以维持公共场所的秩序和卫生。换言之,他们把超越个人的公共观念内在化,从此把自己视为整个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这意味着,个人应该遵守的身体美学的标准,亦适应于其所属之共同体的公共意识。
这种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无疑是企图通过起源于西方各国的身体之规矩、清洁的观念来创造近代国民。然而,如上所述,蒋介石屡次强调新生活运动是源于“礼义廉耻”这种古代中国的道德理念。那么,对于来自西方的身体观、社会观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关系,这场运动是如何解释的呢?
抽象的“礼义廉耻”
阐述新生活运动之基本方针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也有三种版本,但都主张此次运动符合古代中国的道德理念。运动开始时由邓文仪起草的初稿指出:“此运动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之始。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之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做〕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整备。”
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拟定但并未流传的另一种版本引用了蒋介石的演讲,即“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又写道:“礼义廉耻的作用是在遏乱、止暴、弭贪、防滥,所以我们要使乱、暴、贪、滥的社会不致产生,就非倡导礼义廉耻不为功。以上所述的礼义廉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就是新生活的中心理论、中心信条,我们不但要认识些〔这〕这〔些〕,而且要将它们纳入实际生活之中,就是要从食、衣、住、行、待人、接物、日常生活做起。”
但是,对于抽象的道德理念和具体举止动作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版本的纲要均未加以任何解释。
蒋介石亲自重订后于5月15日发表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很详细地阐述了“礼义廉耻”的含义,并主张这些概念对国家、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定义云:“‘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些德性关系到整体国民的命运。如此,《新生活运动纲要》把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礼义廉耻”的丧失,因而倡导:只有提高人民的道德才能改良人民的生活。
据此,其对两种批判意见进行了反驳。第一种是“‘礼义廉耻’不过是一种美善的行为,但恐智识技能不若人,则德行虽美善,亦不足救国”,第二种是“‘礼义廉耻’不过是一种节文,冻馁不给,节文何用”,这些均属于物质主义性质的批判。对于前者,其反驳道:知识、技术只不过是手段,德性才是目的,即“人因求行为之完善,而后有智识技能之需要”。对于后者的反驳则是经济、物质问题需要先改善,道德、精神问题才能解决,如“盖有‘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无‘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争之盗之仍不得足,仓廪不实,为窃为乞仍不得实”。总之,其认为伦理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
然而,对于“衣食住行”之具体的、个别的行为和“礼义廉耻”这些抽象的、一般的德性之间的关系,其记述仍不明确,亦不详细。它只不过把“食衣住行之遂行”分为三个方面论述:第一,“资料之获得应合乎廉……食衣住行之资料,须以自己劳力换得,或以正当名分取予。若争夺依赖,固所不可,即施让赠与,亦所不屑”;第二,“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老者衣帛食肉,不负载于道路,宜于饱暖舒闲,而少年仅以不饥不寒为足,宜于刻苦锻炼也”;第三,“方式之运用应合乎礼……(一)须合乎自然的定律。(二)须合乎社会的规律。(三)须合乎国家的纪律”。据此,它倡导云:“如三者有一失礼、忘义于不廉之事,即成为生活污点,皆当引为耻也。”
除了这些暧昧、模糊的记述之外,其并未阐释“衣食住行”怎样做才能符合“礼义廉耻”。换言之,从几千年前的经典里如何才能得出“钮扣要扣好”“拾到东西交还原人”“不要随地吐痰”“上下码头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等规则?简言之,孔夫子曾吐痰吗?
名曰“继承传统”,其实是学习西方
对于如何操作、展示自己的身体这一问题,中国的传统思想并非缺乏这种思维,不少古典文献即对此有许多记载。因此,新生活运动屡次试图借各种典故来解释其所提倡的身体观、社会观。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民间人士进行了最全面、具体的考察,即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历史教员曾毅。他于1934年6月1日出版《新生活论证》一书,把“孔子所主张的生活”叫作“旧生活以前的古生活”,认为它和“今日西人所有的合理生活”一样,“是有意义的,是颇文明的”,而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如此堕落的原因在于传统道德观念的丧失。于是,他把《新生活须知》初稿的95条规定分为31个范畴,对各个范畴指出了与其相类似的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记载。在此列举其中的一些范畴,并检验其逻辑。
曾毅为了证明“古生活”和“新生活”的相似性而提到的许多古典文献,其中确实有与《新生活须知》的各项规定类似的一些记载。然而,大部分典故并非是所有的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普遍规定,而是以父子、君臣、师生、长幼、主客等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特殊礼节。不仅如此,他有时还会忽视原文的前后关系,任意引用各种典故,因而我们不得不认为其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之嫌。但是,这种倾向并非只限于曾毅一个人,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领导人物亦或多或少地有这种倾向。如此强调古代中国早已拥有近代西方文明的这种逻辑,或许可认为源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里将孔子描绘成一个改革者的做法。后来,孙中山主张《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权主义的滥觞,并说:“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芥〔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
此种认识可视为在不得不承认西洋文明之先进性的情况下保持、慰藉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尝试,也是使这种通过西化实现的近代化获得正当性及正统性的论述技巧。然而,这种论述具有把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转换为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危险性。换言之,这种尝试很容易陷入阻碍、回避、拒绝革新的自我欺瞒的陷阱里。
古代中国人确实早已拥有高度发达的身体美学,但其性质与起源于近代西方的生活礼仪迥然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们要于何时、在何处操作自己的身体,以显示何种形象。古代中国的礼法基本上是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非日常性仪式上相互扮演各自的具体角色之做法,而并非是抽象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非特定多数的陌生人共同构成、维持一个社会的方法。换言之,古代中国的身体美学要求人们断断续续地用自己的身体来确认、体现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故而它所追求的美感意味着人们如何操作各自的身体来显示其特殊的、个别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反,近代西方的身体美学却促使每个人持续地、不断地用其身体来表现、证明各自人格的伦理美德,因而其所追求的美感也意味着他们如何通过检点自己的身体来满足普遍的、一般性的个人责任。
对于中西、古今身体意识之间的这种差异,我们可以指出其两个来源。第一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中国的传统思想把个人看作人际关系网络的结点,社会则是各种各样的具体人际关系的积聚、总和,即如孟子所倡导的“五伦”的总和。与此相反,正如霍布斯的“利维坦”,近代西方思想则认为个人是互相独立的、等价的“原子”,社会却是包含、超越所有个人的抽象场所。第二是对身体与精神的关系的看法。正如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西方思想认为精神与身体各自根据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属于各不相同的世界,而且双方之间存在着贵贱、圣俗的对立和矛盾。然而,如朱子的理一分殊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并未把精神和身体截然分开,而是将两者视为同一原理、同一世界的两个侧面,故而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对立和矛盾。
这与其说是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垂直差距),不如说是身体观、社会观之性质的不同(水平差异)。但是,由于这些独特的性质,中国的传统思想难以产生个人把自己看成整个社会中的一分子的近代性公共意识,以及经常由精神(理性)控制、管理身体(欲望)来构成、维持社会空间的近代性身体美学。
那么,孔夫子到底是否曾经吐过痰?我们虽然对此无法做出结论,但至少可以这样解释——对于孔夫子来说,“礼”并不意味着不能在公共场所吐痰,而是意味着不能在长上面前吐痰。
小结总之,新生活运动在抽象的理念方面,是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思想,但在具体的礼仪问题上,却是要求中国人的一举一动完全仿效近代西方(及日本)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是故,中国人的举止动作是否美观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其在西方人的眼里是怎样被认识的。换言之,新生活运动要求中国人把西方人的眼光内在化,以此来管理、控制自己的举止动作,由此体现近代性身体观和社会观,此即通过身体之“教养”而实现的近代化。
总而言之,国民党政权为了“教养”中国人之身体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本质上必然地把中国人民及其生活习惯作为否定、侮蔑的对象,并对其表示出敌对态度。故此,该运动可能会引起一般人民对国家的怀疑、反感,以致削弱、破坏它的统治正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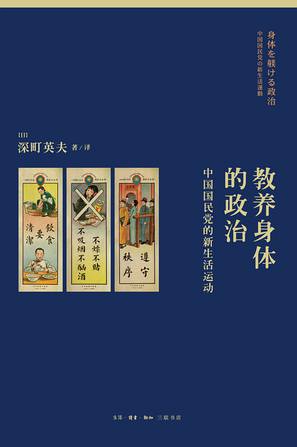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