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静|数字遗产:死后即焚与数字永生
文 _ 陈静(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年轻女孩玛莎与男友艾什准备开始甜蜜的新生活时,艾什却遭遇了车祸,不幸身亡。这给玛莎带来了巨大打击,尤其是当她发觉自己怀孕后,玛莎开启了与由艾什生前的数字足迹合成的AI“艾什”的线上联系。她宛若上瘾般地与“艾什”交谈,笑声与阳光重回生活。一次,玛莎付费升级了服务之后,一个活生生的“艾什”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一切似乎回归正常。但玛莎却在细枝末节间感受到了“刺点”:人工智能程序设定下的“艾什”无法在超出档案记录的规则之外行事,他只能根据过去来复演当下。即使如此,玛莎也无法下定决心抛弃“艾什”。此后,“艾什”仿佛幽灵般活在阁楼上,只有在像女儿生日这样的日子里,玛莎才会让女儿与之见面——作为生日礼物。
这一情节出自英剧《黑镜》(Black Mirror)第二季的第一集《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人工智能、仿生对话、人造人已是科幻故事中烂俗的情节,稍微熟悉相关理论的人,甚至还可以聊起这个故事中的若干学术梗,比如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恐怖谷等。除去科幻的部分,故事的主题其实非常传统,即痛失吾爱之后如何度过悲恸。只不过它讲述的不是传统的悼念,而更多地聚焦于主角如何受益于科技进步下的失而复得。据说编剧查理 · 布鲁克(Charlie Brooker)的灵感来自对于是否应从手机通讯录中删除已逝好友的名字,以及关于推特是否可能在用户去世后模仿其继续发布消息的思考。

《马上回来》(2013)
事实上,现实世界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尝试,比如聊天机器人Replika。2015年,《黑镜》第二季首播两年后,痛失挚友的工程师尤金妮亚 · 凯达(Eugenia Kuyda)和团队花了两年时间利用Google TensorFlow“训练”了3500万条英文文本和3000万条俄文文本,建立了两个神经网络,再利用她和逝去的朋友的几百条对话“训练”神经网络去模仿好友的口气来进行问答。尽管Replika招致争议,但凯达认为这将会打造一种新的纪念形式。其后,这个因为私人兴趣发展起来的项目成了一个面向大众的商业项目,可以开展交互和定制化的聊天。如其名所示,这个平台允许你去创造一个虚拟化身,然后通过与之对话来“告知”它你的信息,滋养其智慧,从而使其越来越“像”你自己,让你通过看到自己来进行自我反思——是不是听起来更像一个字面上的“黑镜”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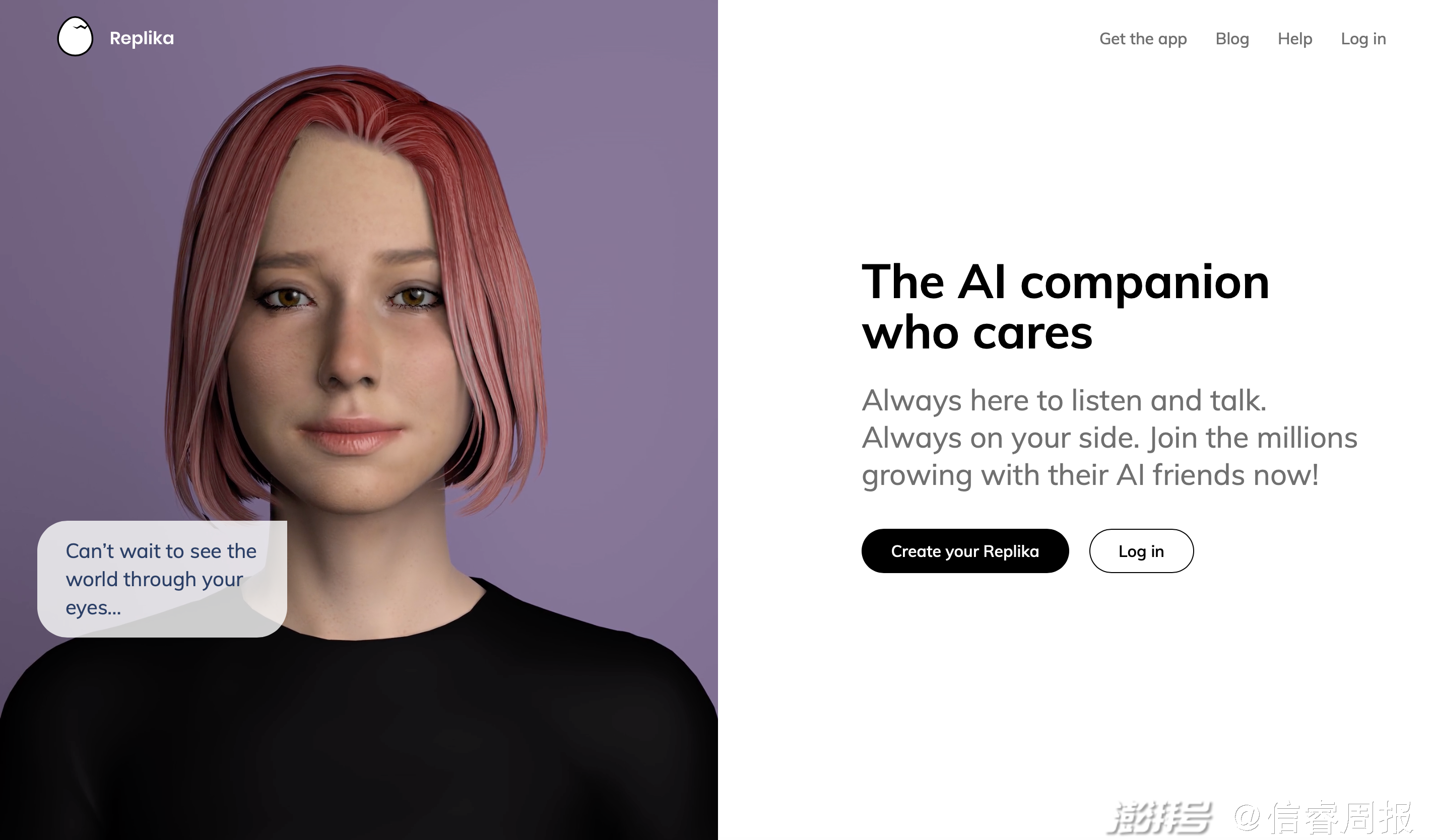
Replika官网首页
类似的故事还在继续。2019年,李杨——一位失去爱女的母亲——向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团队能根据女儿陈瑾的照片和视频制作能与她互动的软件。尽管实验室做出了这样的产品,但“专家们害怕当‘AI陈瑾’出现后,母亲李杨会因此沉迷, 从而无法真正走出丧女之痛”,决定无限期地暂缓向这位母亲交付产品。[1]
如果如Replika官网所声称的,复制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为了治愈还活着的人,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究竟在怀念什么?我们复活的又是什么?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将已逝者在世时的“数字痕迹”保存下来并在其身后再次使用的方式,是否正当且合理?是否尊重了已逝者的主观意愿与意志?这些数字内容是否与一般性资产一样具有明确归属权,可以被继承和再使用?如果是,那么谁能拥有这样的权利,是像用户这样的内容生产/提供方,抑或社交软件这样的服务商/渠道?
这一系列问题指向了同一个议题:数字遗产。尽管我国法律条款中尚未对“数字遗产”做出明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仅对可继承的遗产范围作了概括性规定,即“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2]),但实际上,数字遗产已成为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数字遗产”的英文表述通常为digital legacy或digital inheritance,可以指称个人数字资产中可由指定受益人继承的部分。广义而言,数字遗产还具有公共属性,即digital heritage,多指那些具有持久保存价值、值得为子孙后代保存的数字信息和材料[3]。在中文中,由于一律都用“数字遗产”指称,所以往往会发生混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转换关系,这部分会在后文提及。
死亡学与数字幽灵
1774年的圣诞节前夕,一个敏感、热情且才华横溢的少年开枪自杀了,他以热烈如火的感情拥抱理想,以死塑造了一个永恒美好的彼岸世界。这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经典情节,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恰逢其时地彰显了一种时代病,更在于其见证了印刷时代文字的伟大力量,灵魂的声音被封装在书本构成的永恒世界中。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将之称为“一种记忆的解放”,也是“一种记忆的终结”。当维特的烦恼被封存在书中时,维特就从歌德本人的记忆中独立出来,成了一个可以被阅读和想象的对象,并在读者的阅读快感中得到还原,虽然还原后的结果不再属于彼时被歌德书写的记忆。文字、书本成了封印记忆的容器,也成了记录死亡(同时也是解放死亡)的最好载体。维特们如幽灵般永存于字里行间,无数次地唤醒一代又一代试图进入永恒理想世界的年轻人。
而基特勒想提醒我们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媒介,诸如摩斯电码、留声机唱片和照相机,依然在扮演着禁锢“幽灵”的角色。人类的感知作为数据被存储到机器里,等待着被唤醒,从而在空气、光与电流中重新被还原为可被感知的具象。如同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的科幻小说《复活公司》(Die Resurrection Co.)中的情节,死者的亡灵成了电信网络的一部分:美国达科他州小镇纳克若波利斯墓地管理机构为了应对活埋丑闻,不惜花费75万美金成立子公司,给镇上所有的棺材都接通了电话线,确保坟墓里的居民可以接入公共电话网。基特勒曾以这篇小说为例,旨在说明留声机、电话、照相机及电影等“新媒介”所构成的媒介景观使死亡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基特勒感慨道:
如果说墓碑是树立在文化开端的象征,那么我们的媒体技术就能够召唤回所有的神灵。有关朝生暮死的古老书写哀叹——人们总是用这种短暂性去衡量书写与感官享受之间的距离——突然地陷入了沉默。在媒体景观之中,不朽再次流传于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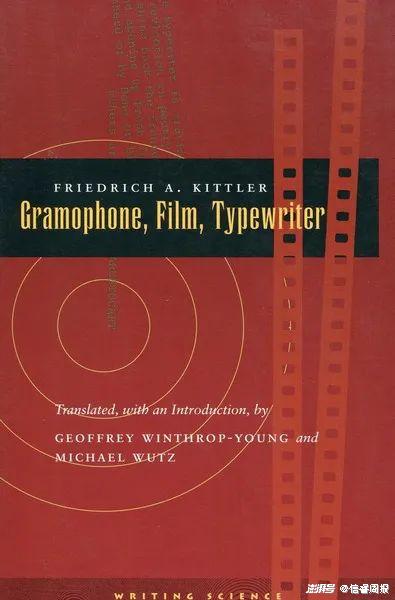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Friedrich A. Kittler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世纪,媒介景观依旧,不朽再次流传。禁锢于书籍与唱片中的幽灵如今以“数字幽灵”之名游荡在无边无际的“0-1”矩阵之中,时刻提醒着我们数字时代的死亡也是一种遗忘与唤醒的循环往复。与书籍不同的是,数字媒介提供的还原可能性越来越高。像《马上回来》中的情节那样,社交媒体能做到的对一个人的还原已经远超文字所能提供的想象。文字、声音、图像、气味甚至触感都可能被还原,可能像Replika那样纯粹虚拟,也可能如“艾什”一样现实具身化。我们在数字世界中留存的一切数字足迹,其原初或许是无意识与无目的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会随着物理主体的消亡而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留存在计算机及互联网打造的物理硬盘和虚拟空间中,构成了我们的身后遗存物,等待着被再次唤醒。
由此,死亡学(Thanatology)也被数字重塑了。死亡学从包括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精神学等多学科视角去看待死亡、损失和悲痛,其关注的人群不仅包括面临死亡的人,还有死者的亲友以及其他关心死者的人。1996年,卡拉 · 索夫卡(Carla Sofka)首创Thanatechnology (死亡技术学)一词,用以指称那些“像交互式视频光盘和计算机程序一样,用于获取信息或帮助学习死亡学主题的技术机制”。
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人们尚未形成对数字遗产的意识,也没有合适的概念去描述数字死亡,“死亡技术学”这一概念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技术对死亡的介入过程。数字死亡本身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内在机制的探寻视角。如何将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字遗产纳入死亡学的研究视野,如何考量数字资源对于人类健康、生存、死亡以及人际关系的影响,成了死亡技术学的探索主题之一。

本文选自《信睿周报》第71期
数字资产与数字死亡管理者
威廉姆 · 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在1995年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之初做出的关于虚拟社会映射现实世界而生的一系列论断已经逐一被验证。虚拟社会已不仅是现实社会的镜像和对应物,而是嵌入现实生活中,成了现实的一部分。与现实中的物品和货币一样,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创造的数字内容,包括电脑上的各种文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字信息、照片、视频,个人邮件往来,购买的各类付费服务、电子书及视频,在单机或联网游戏中的战绩与代币,在商业平台上发布的发表物及待售品,个人网站上的音乐与艺术作品等,已经成了个人资产的一部分,可流通和被交易。在此意义上,一切以数字格式存在并具有可使用性(使用权)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数字资产”。
尽管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这些数字内容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些数字内容可被算作资产,只有很少的人能意识到需要为这些资产做身后打算。由数字遗产协会(Digital Legacy Association)和美国锡耶纳学院共同开展的、基于线上问卷的《2018数字死亡报告》[5]显示,超过40%以上的被调查者知道“数字资产”“数字足迹”“数字遗产”这些词汇,但大部分人都不熟悉相关政策法规,更鲜有人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网站、博客等网络数字内容制订身后计划。尽管这个调研的样本量(300多人)非常有限,但因为此领域的调研颇为罕见,也具有管中窥豹的借鉴意义。同时,谷歌、苹果、脸书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已经开始推出数字遗产服务,但其覆盖的数字内容未包含个人数字遗产的全部,更不要说系统性地帮助其拥有者制订计划或执行其计划了。
事实上,与数字遗产相关的产业已经存在。比如,网站LegacyLocker.com能为用户提供数字资产管理服务,类似的还有Entrustet.com和DataInherit.com,可将已故用户的有关信息发送给指定继承人,确保其可以获取用户的数字资产;Bcelebrated.com和MyWonderfulLife.com等网站则能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线上纪念服务;甚至还有像DigitalEstateServices.com这样的“数字锁匠”(digital locksmith),可以帮助用户登录被锁定的计算机,并对内容进行存档。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职业—数字死亡管理者(digital death manager)。大卫 · 西斯托(Davide Sisto )在《线上身后事:数字文化中的死亡、记忆和哀悼》(Online Afterlives:Immortality, Memory, and Grief in Digital Culture)一书中借2018年《时代》(Time)杂志刊文讨论的“死亡清理”(death cleaning)话题——一个人在大限将至之时,应清除家中的非必要之物,从而使得家里更整洁有序——指出,这一点也适用于虚拟家庭。
负责管理这一事务的人即为数字死亡管理者,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整理用户已经在网上发布的数字内容,还能处理用户死后依然存在的内容(比如仍能使用的社交账号),并安排相应的哀悼活动,以及权衡这些遗产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换句话说,数字死亡管理者扮演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更要熟悉互联网规则,并根据网络行情和数字资产的重要性及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估。

Online Afterlives
Davide Sisto
The MIT Press 2020
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对数字资产进行管理的最大困难并非全然来自数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数字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也会对数字资产管理造成障碍。目前,大部分互联网服务都依赖于用户数据,而用户数据的获取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平等和潜在规则——比如,用户数据通常是在用户不知情或即使知情也要被迫服从的情况下授权给服务提供商的,用户自身并不拥有其数据。
此外,有一些数据是保存在特定的应用程序中的,导出或备份文件往往也需要同款程序或同样的运行环境。因此,这些数据即使已在本地保存或备份,也无法随意被再次打开或使用。再者,服务商提供的数据存储空间限制或服务商停止服务导致用户数据消失,也可能造成用户无法再次获取或永久保存这些数据。当然,还有大量数据因为涉及个人隐私而用户不愿意将之公布,但又不希望这些数据在自己死后以“数字僵尸”(digital zombie)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些数字内容又应如何处理?
现实中已经出现类似的纷争案例,即互联网平台拒绝将逝者在其平台上使用的邮箱账号和密码告知其亲属。在公司对数据的垄断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用户能否拥有删除数据的权利?然而从客观上来讲,无论用户有着多么强大的意愿,死后即焚都是无法实现的。鉴于设备生产商、网络运营商、软件服务商都各自拥有部分的用户数据,死后即焚绝不是单纯地将数据从设备上删除或格式化这么简单。毕竟,用户生前留下的无数的数字足迹一旦接入互联网,便将是永恒。
在大数据时代,对数字资产的价值评估和甄选也显得尤为必要。比如,什么内容值得被保留下来?该以何种方式被保留?继承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数字遗产是不可避免的。互联网使得系统地记录整个社会成为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数字网络来实现的。这种持久的在线记录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提醒着我们: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生活的痕迹却无法被真正抹去。这种悖论恰恰是数字遗产所具有的本质规定性:一个人的死亡使得其数字内容成为遗产,而数字使得死亡成为永生。在此意义上,如何在生前就甄选出需要被保存的内容,删除/焚毁不希望被保留和继承的内容,以及选择怎样的方式被继承或再利用则成了制定遗嘱或安排遗产的必要考虑。
《马上回来》中“艾什”式的虚拟永生人是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形式,即人们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保存或还原逝去的亲友,使其在互联网中永久存在。另一种形式的数字永生则是通过对个人资料和文献存档,使其成为可以被访问和再次利用的数据对象,多以个人档案和个人数据库的方式出现。笔者认为,后者在当下有关“遗产”的讨论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如前文提及,数字遗产在狭义和广义上既有区别,也有相关性。尤其是,当我们从持久保存的角度来考虑数字遗产问题时,就会发现当下以数字形式存档的大量历史文献与资料在其初始状态下也是狭义上的个人遗产,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公共性和历史性凸显,从而以公共遗产的面目出现。也即,这些遗产需要在公共财产的意义上得到认证,其继承和保存的价值才能被认可。
近年来,随着公共史学的兴起及大量口述史、个人或家族资料的出现,个人遗产(比如个人影像史、家族相册、佚名图像)也开始被作为公共遗产来讨论,或者说,个人遗产被视为潜在的公共遗产并逐渐获得重视。其中很多并不具有明确的主体拥有者,而是作为一种边缘材料被收集起来,但因其时代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数字遗产也是如此。我们对日记、笔记、手稿进行的研究,也许将在不久后变成对电子邮件、微博帖子和聊天记录的分析。然而,对后者的获取并不比前者更为容易。如何从当下出发考量未来的数字遗产,实际上是一个更为艰巨的命题,但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开示我们:做好眼下的数字资产管理,并为自己身后的数字遗产做好计划,将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历史的未来。
注释
[1] 万能编辑部. 失独母亲用AI "复活" 女儿,这能解决人类的爱之憾吗?[A/OL]. 澎湃, 2020-01-1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2562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编继承, https://www.spp.gov.cn/spp/ssmfdyflvdtpgz/202008/t20200831_478418.shtml。
[3] 参见联合国关于 "数字遗产概念" 的界定: https://en.unesco.org/themes/information-preservation/digital-heritage/concept-digital-heritage。
[4] KITTLE F.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5] 该报告的数据由 "数字遗产协会" 和锡耶纳大学共同收集并发布, 参见: https://digitallegacyassociation.org/about/reports-2/。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1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