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的中国文学翻译之路
原创 佩特雷卡 中拉智讯
智讯君按
2022年是中国与阿根廷建交五十周年,也是中阿友好合作年。50年间,有许多人为增进中阿交流和理解做出不懈努力。在此特别时刻,我们将陆续分享其中一些人的中阿故事,以资纪念,以飨读者。
一
我开始学习汉语多少有些机缘巧合:当时,我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而且想学一门具有挑战性的语言。阿根廷那时还没有开设“中国研究”这样的课程,在我就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专业中完全找不到中国文学的影子。我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均来自校外,来自我那些诗人朋友的丰富藏书,来自埃兹拉·庞德、肯尼斯·雷克思罗斯、马塞拉·德胡安和亚瑟·威利的翻译作品。早在学习汉语之前,我和几个朋友打算阅读杜甫诗歌的原文。连着数月,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在某个朋友的家中,花费无数个小时和无数个日子,试图在字典中找到诗歌里的文字。当然,我们最后以放弃告终,一句诗都没译出来,但我们乐在其中,而且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后来开始学习汉语,很大程度上跟那次失败的经历有关。
我们谁也无法得知学习一门语言会把我们带往何处,而当你学习的这门语言是汉语时,你就更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切。初学汉语时,我就没做好这种准备。如我所言,我学汉语纯属偶然,我对读诗写诗抱有兴趣,而学习汉语则是其副产品。在阿根廷文学传统中,写作是和翻译挂钩的;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学传统亦是如此。很多我崇拜的阿根廷诗人,比如博尔赫斯、阿尔贝托·吉里和米拉·罗森伯格,他们都是或者曾经是翻译家。在这种文学语境下,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为写作本身提供了一间实验室。我脑中带着这个想法开始学习汉语;但汉语显然要在我身上做些其他的施展。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2008年。那一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而我则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当时,我已经学了近四年的汉语,最初的那些计划显然已不合时宜。汉语已在我体内安营扎寨,它拥有了一种自主性,令人始料未及。那时,我仍在创作诗歌,发表诗作,也开始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我当时仍认为翻译是为我的写作事业准备的实验室。然而,我对中国的兴趣,对中国文学、汉语和文化的兴趣,已不再局限于我对诗歌和写作的兴趣,它像是获得了自主性,成为我身体的另一部分。
我至今记得,2008年8月我抵达北京两三天后,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在中国的一年已经结束了,我正要回阿根廷。也就是说,时间悄悄溜走,我要踏上阿根廷的归途,而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之所以做这种梦,是因为我当时非常害怕在中国呆了一年之后毫无改变。但是那一年,我最终还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步履不停地在北京城行走,我取了另一个名字,我开始读中国现代文学,我跑遍了中国的很多地方,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游历了一些名山,一次又一次坐上火车或大巴开启新的旅行。我还想办法结识了几位我当时正在翻译其作品的诗人。回到阿根廷后,我继续打磨译文,并与2011年出版了一部诗集,里面收录了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一百首诗作。
与英语或法语等其他语言相比,西班牙语中的汉学传统相对贫瘠。直到不久前,在西班牙语出版市场上,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间接译本仍占主导地位。这一情况在今天虽有改善,但出版社仍更喜欢采用由英语或法语译成的西班牙语版本,而不是花钱找一个合格的译者,直接从汉语翻译。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从汉语直译要比从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转译难得多,也会耗费更多时间。花三个月时间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文本,如果从汉语直译,可能要耗费一年,而后者却不见得会比前者赚得多。因此,如果一般译者已经很难用翻译来养活自己的话,那么汉语译者靠翻译养活自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幸运的是,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给翻译行业提供补贴,以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这项举措改善了译者的状况。但即便如此,情况依然堪忧,因为很多时候译者拿不到全部补贴,或者要过很久才能拿到。这就好像一些中国的出版社,很多时候它们负责对外推广作家及发放补贴的工作,却全然忽视文学翻译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或者,人们还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所谓译者,就是那些把翻译当作消遣的有钱人。于是译者就处于此等悖论中:他们一遍遍地听到文化政策的负责人哀叹译者之稀缺,在一个又一个论坛上强调翻译的重要性,实际上却对译者的真正需求回应甚少。

中国文学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翻译,他们还是法国人所称的“摆渡者”,即负责引入外国文学和文化的人。各国的出版社,阿根廷的,智利的,西班牙的,只能通过译者来了解中国文学,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让出版者确信某部作品很重要,很有必要去译介它。这些译者的工作量已经超出其他语言译者的工作量;在很多情况下,后者不过是完成交给他们的翻译任务,而中文译者除了完成翻译外,还不得不自己在出版物中寻找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寻找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反响的东西。这完全就是一项额外的工作。
另一大障碍是,我们需要在中国旅居,以便和作者进行合作,搞研究,寻找新书,和汉语接触,等等,而中国在这方面缺乏相应的项目支持。我目前旅居的法国就有一项比较好的政策,包含几个专门为外国译者提供的居住规划。这些规划给那些已与外国出版社签约的译者提供在法国短期停留(一至三个月)的经济支持。
从我们这方面来讲,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因为事实上,虽然阿根廷每年似乎都开设新的“中国研究项目”,但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贸易和外交方面,也就是说,所谓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对话是用这样一种非常局限的方式完成的。除了一些没有机构支持的孤军奋战之外,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尝试建立一个中国研究项目,也没有推动中国文学走进大学的措施。
当然了,这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就像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鲁迅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尽管困难重重,尽管缺乏支持,尽管来自出版社的、来自那些总是过度推广的不良作家们的支持或是不足或是延迟,尽管缺少时间,尽管出版市场狭小,我们作为译者,还是在继续翻译着,尝试着开辟新的道路。
二
如我之前所说,我开始学习汉语始于我对诗歌的兴趣,尤其是中国诗歌。翻译中国诗歌与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之间有一定关联:这项工作让我得到锻炼,创造出更好的诗歌。但有那么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有人问我,我写的诗歌和我作为中国诗歌译者这项事业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会说没有一点关系。这个问题看似矛盾,但也可能不那么矛盾,因为一方面翻译工作和诗歌创作之间存在关系,另一方面一个人翻译的诗歌类型跟他所创作的诗歌类型之间存在关系。于我而言,实际上我并不喜欢用西班牙语创作“中国”诗歌,我所喜欢的只是翻译诗歌这项工作本身。
尽管天天阅读中国作品,所有工作都围着翻译中国诗歌转,但在我的诗作中,看不到“中国”式的东西,至少我觉得看不到。2012年左右,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写下一首题为《山》的长诗。这首诗堪称惊喜之作,因为在诗中呈现出一种中国式情感和一系列的中国元素,而我并未刻意为之,这和我多年来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有关。下面是这首诗的节选:
(……)
但奇迹是不存在的。
比如现在,正是秋天,
几只喜鹊在树梢喳喳叫着。
天上,也在发生着一些有趣的事情,
全速行进。
或许现在是最佳的时刻
用以区分哪些事情可行,哪些不行。
林林林 树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林 林
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
一个人站在 林林林林林
树林中间的 林林人林林
一块空地上 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
一个人藏在树林中
蹲着
做着笔记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段故事的脚注。
15岁时,我将心志集中于苍山,
20岁时,我不再彷徨犹豫。
30岁时,我知晓了我的命运
且学会了保持沉默。
就好像突然置身于
一个空房间
而你却不知道是怎么到了这儿。
(……)
我一直对瓦尔特·本杰明的观点颇感兴趣。他认为,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原始语言渗入目标语言,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语言包含其他语言的一个片段。这首诗多多少少带有这么个意思,因为汉字进入了文本,和西班牙语相融合,但同时又保持着它自身的新奇。
另一方面,除了象形文字游戏,除了对《论语》著名片段(在我的诗里有所变动)的暗指,在这首诗的情绪里蕴含些许中国元素。对我来说(或许仅仅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从这首诗的标题“山”上就显露无疑。这是因为,我对山的看法与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有关,同样地,我对中国的印象也和山(或中国的山)带给我的印象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又和中国诗歌有关,“山”在中国诗歌中出现的频率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种文明的诗歌都要多。当我想到中国诗歌的时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堆以“山”为背景或以“山”为主角的诗句。我想到了王维的“空山不见人”,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还有韩愈的“黄昏到寺蝙蝠飞”。我还想到了最初读到的杜甫诗作之一《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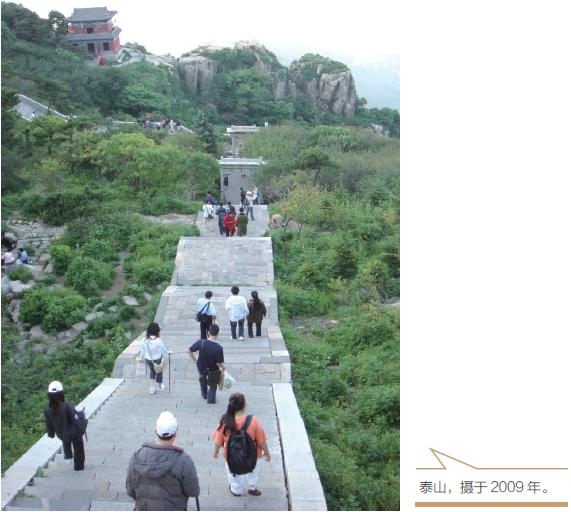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首先是因为颈联中的意象具有双层含义。在第五句诗中,“胸”既指山的胸,又指诗人的胸怀,而在第六句中,“眦”可以指诗人的眼睛,也可以指山峰的洞穴。我尤喜诗歌的结尾,杜甫在这里想象自己登上山顶,从上往下观看风景。我知道这里是一处暗指,因为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是在736年创作的这首诗,就在他第一次科举考试落榜后不久。那是他人生中两次科举落榜的第一次。于是他就去现在的山东游玩,他父亲在那里任职奉天令。面对泰山,杜甫写下了这首诗。
2009年6月,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在泰山顶上度过了三十岁生日。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杜甫的这首诗,不过有人跟我说,在三十岁前登上泰山顶的人可以长寿。那是我在中国攀登的第一座山,但并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山。比如我曾登上过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一座高山。那山位于巴里洛切附近,要先花几个小时沿着河岸长途跋涉过一片山毛榉林,然后顺着一条陡峭的螺旋式小路爬坡,最后来到冰湖边上的一处营地。在中国爬山就大不相同了。在中国,取代营地的是寺庙,不仅山顶上有寺庙,途中也有。寺庙,寺庙的废墟,有古代铭文的石碑,悠久历史的遗迹,以及居住遗址。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新鲜,也很吸引人,但是除去这一点,初登泰山的经历却有些让我失望:泰山并非王维诗中所描写的“空山”。人太多了,到处都是游客,都是相机和手机,还有来来往往运送食物的小商贩,售卖饮料、水果和纪念品的小摊,以及扬声器的噪音。登完泰山后不久,我又去了黄山。黄山让我惊喜,松树盘结扭曲,直入云霄,就像我在画中看到的那样。
三
上文提及的本杰明关于翻译的看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并非完全陌生。鲁迅就提出过类似观点,即“硬译”。鲁迅认为,译者应当尽最大可能地忠于原文,即使在语法层面也要忠于原文,哪怕是译文听上去有些“硬”,也要忠于原作。简而言之,鲁迅将翻译看作是对本国语言进行改造的一种工具。汉语的句法倾向于使用排比,也就是短句的并列,句子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联系,并且汉语对重复内容的容忍度也较高。西班牙语的句法更加复杂,继承了拉丁语的严谨逻辑性。中文短句所形成的节奏很难转移到西班牙语中。很多时候,在翻译时,有必要背叛这种节奏,然后把句子重新组织成一个更长的语段。
除了句子和节奏问题,有时我也会思考本杰明的理论,然后设想有没有可能将中文渗透到西班牙语中。对我来说,翻译的理想状态之一是将“无为”的概念应用于翻译。也就是说,不要翻译,直接从另一种语言中搬运过来一个词,将其作为一个外来的嫩枝嫁接到本土语言的土地上,让它自己去生长。如果一个译者能够用这种方式从其他语言中偷运过来一个词,不加翻译,让这个词融入到他自己的语言的词汇库中,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译者在两种语言之间搭建了一座特殊的桥梁。这类“搬运”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单词发音相关。比如,从日语翻译到西班牙语就有很多例子,如“榻榻米”,“寿司”,“武士道”,“盆景”等(不用说,这些词里面很多都源自汉语)。
而中文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中文的发音和西班牙语的发音差别较大,还有就是拼音不能直观地读出来。较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专有名词的翻译,因为读者不知道怎么去读这个名词。举个例子,我在2016年译了一本格非的小说,叫《隐身衣》,小说主人公姓“崔”(Cui),而西班牙语读者会读成“归”(Kui)。为了让读者读出这个字本该有的发音,必须舍弃拼音的用法,将其改编为这样一种形式:“Tsui”。但是在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西班牙语自身的限制性,或者说是西班牙语和汉语之间关系的限制,因为英语和法语具有可替换的改编体系,可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发音,至今仍被一些译者所采用,而在西班牙语中就没有类似的体系。西班牙语中没有可以替换拼音的东西。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汉语词汇成为了西班牙语的常用词,比如“道”,“炒饭”,“豆腐”,“功夫”,“荔枝”,等等。可能中文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尝试让新的汉语词汇在其本国语言中流通开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选择不翻译和翻译同样重要。
四
2000年初,我还没开始学习汉语,当时我有一位朋友,她是《易经》的狂热粉丝。她把这本书读了很多遍,背了书中的很多内容,还喜欢用《易经》给朋友算卦。每次去她家,或者我遇到大问题、困境待解决时,我都会让她给我算一卦。我们坐在位于阿尔玛格罗区的她家客厅里,她要我想一个问题,然后让我把几枚硬币扔上三次或几次。然后她就查阅《易经》,找到对应的卦象,根据我的问题进行解释。她的解释往往既迷人又精准,以至于时间一久,我都有点依赖了。每年年尾,我是指每个中国农历年岁末,我们都会跟这位朋友聚一聚,她会告诉我们新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关于《易经》,我的这位朋友说,这本书不是去“猜测”未来,这书仅仅是一本用来解释现在的手册,一个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指南。她这么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听着她阐释,感觉好像她真的能读出卦象中的命运。
在那之后,我到了中国,却再也没碰上过像她那样这么把《易经》当回事的人,但我经常入迷地漫步于那些在寺庙附近开设的生意摊。比如在北京的雍和宫附近,就有一些这样的生意,售卖年鉴、佛牌、神像、熏香,还有一些专门预测未来和算命的人。有一次在上海周边的七宝村,一个在桥上的男人主动要给我“读脸”。他给我说了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可能因为很多话在我听来有些荒谬。没几分钟,在我们周围就聚起了一堆人,看着我们。一个老外正在看脸算命!过了一会我站起来了,然后付钱走人。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是挺矛盾的,因为一方面,如果你去问一个中国人关于宗教的事情,他很可能会回答:“中国没有宗教”。但是另一方面,很有可能还是这个人,过会儿就去庙里烧香,或者在大街上给逝者烧纸。这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式悖论之一。

2009年回到阿根廷之后,我有三年没有再去中国,直至2012年底。我在上海呆了六个月,给一份阿根廷日报写简讯,帮阿德里安娜-伊达尔戈出版社做一本故事集。之后我与妻子回到阿根廷,但很快就赴巴黎定居,在那里我开始攻读中国文学的研究生课程。法国距离中国近多了,所以自从我们在法国定居后,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做研究、查资料、看朋友和旅游。在巴黎,我们找了很久之后,终于通过朋友的朋友租到了一所公寓。难以置信的是,公寓所在的街道名叫“中国街”……有时候,即使一个人不愿相信命运,也很难做到真的不相信命运。
作者:米格尔·安赫尔·佩特雷卡(阿根廷诗人、汉学家)
原标题:《我的中国文学翻译之路》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