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在美国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 三明治
原创 晓苏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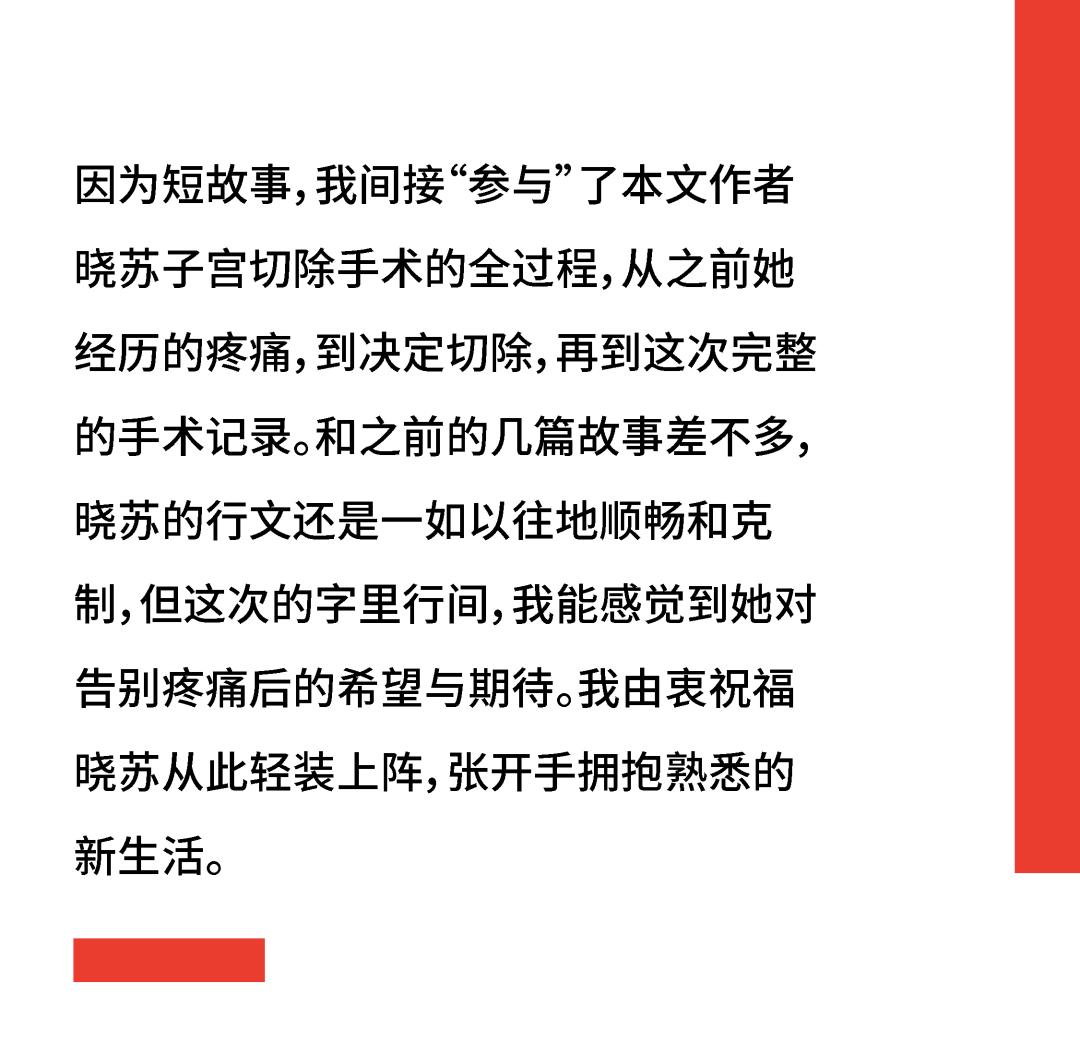
作者 | 晓苏
编辑 | 童言
二月七日,凌晨6点,我们离开宾馆,驱车前往圣安东尼医院。车程不过十分钟,路上没有人,路灯洒下的橘色光束打在潮湿的柏油路上,泛出银光。二月初的美国西北小镇,日出很晚,日落很早,天气湿冷。
“你害怕吗?”我打破沉默,问在开车的T先生。
T先生愣住,“有一点吧。你害怕吗?”
“有一点吧。”我俩都笑了。
疫情期间的手术,是不可以有人陪同的,T先生送我到手术大楼门口,看着我换上医用口罩,登记证件,然后挥挥手。
原本嘈杂、繁忙的医院大厅,现在只有我和看门登记的大爷。灯还没有完全打开,昏暗的,安静的。电梯门打开,我一个人走进去,上二楼,那里应该有在等待我的护士。

决定做子宫切除手术是在两个月前,约定好手术时间之后,新冠出现奥密克戎变种,原本有所回转的疫情瞬间又紧张了起来。一月份,我接到医院电话,说为了节省医疗资源,州里要求停止所有不必要的手术。电话里,护士详细询问了我的疼痛状况,目前吃药的副作用。
关于子宫腺肌病的疼痛和如何下定决心切除子宫,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写过。在手术之前的三四个月里,我一直在接受激素治疗,每天口服5毫克的单一孕激素。这种治疗方法可以缓解疼痛,但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例如,体重增加、掉头发、疲劳和情绪波动。孕激素增加,给身体的信号类似于怀孕,人会变得很想吃东西,不愿意运动,习惯性疲乏。我在三个月期间重了15斤,常规运动也停了,因为情绪非常低落,不想出门,不愿意见人,不想起床。在期间的写作也变得异常困难,各种感觉变得模糊,思维反应迟钝。
我在想如果要一直这样下去,我能够接受吗?在长期病痛和麻木抑郁之间,你会如何选择?好在,我决定不选了,这都是暂时的,我在等我的手术,切除子宫就好了。
于是我跟医院的护士详细讲述了我的病情和目前情绪抑郁的状况,对方表示理解和同情,会继续帮我争取按原计划手术。这样的电话我们还通过两次,每一次都说手术可能会取消,需要提交更多资料。每一次放下电话,我都会焦虑一整天,不会做不成手术了吧,那我要怎么办?

医院评估后认为我目前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手术是必要的,可以按照原计划进行。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我开始按照医生的交代,逐步进行术前准备工作。
原来在国内做手术的时候,通常是提前一天入院,然后在医院做各种检查,清肠、备皮。在美国的两次手术中,都是手术当天才去医院。需要的检查医生会让患者提前去指定的机构做,清肠、皮肤清洁这样的工作也都是发放文字说明,患者自己在家里做。开始我以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后来跟朋友聊,才知道一直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费用的问题,美国医疗成本高,住院费很贵,而作为买单方的保险公司不愿意支付这个费用,于是就有了在美国“住院难”的问题。
同样的,手术结束之后,能不住院就不住院。一年前,我做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的时候,医院就要求当天回家,这次的子宫切除手术,按理需要术后住院观察一天,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天也不让待了。而同样的手术在中国至少需要住五天医院。当然,我没觉得这是个问题,疫情下,待在医院也是自己一个人,回到家还能有家人照顾。不过后来证明,我想错了。
手术前三天要做新冠核酸检测,确保阴性后,进入居家隔离。手术前一天,做肠道准备,就是清肠。具体方法是这样的,把一大桶通肠排便的药粉(800g)分两份,倒入两桶2升装的功能饮料中(因为功能饮料中含有电解质可以防止脱水)。从上午10点开始,每三小时喝一瓶。期间不能吃任何固体食物,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结束。我拿着医生给的说明反复看,上面写着“这个清肠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不会造成腹部绞痛,同时又能把肠子里的东西清干净。”她说得对,的确没有拉肚子时候的肠绞痛,但整个过程很难说得上美妙,几乎整天都在上厕所。
晚上七点钟,我们离开家,开车去往医院旁边的宾馆。做手术的医院离家有两个小时车程,为了避免手术当天慌乱,我们决定提前过来住一晚。我要在宾馆做身体消毒,方法也很原始,就是用杀菌香皂洗澡,手术前的晚上和当天早晨各一次,穿上干净的衣服。
晚上十一点,感觉肚子是彻底空了,人也很疲乏,睡前喝了最后一口水(手术前不能再喝水了),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当天,我很早醒来,躺在床上等闹钟,闹钟设置在五点半。脑子里盘算着,一会儿要做的事情,要带的东西,就像要参加考试的学生。可这次接受考察的并不是我,没有理由紧张啊,为什么就睡不着了呢。

走出电梯,二楼大厅是家属等候区,摆着宽大的沙发和茶几,旁边有自助咖啡台。这里空空荡荡,凉飕飕的,真想喝杯热咖啡。这时,等候区对面的玻璃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护士,跟我核对了信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手环(上面有我的信息和条形码),戴在我的左手腕上,示意我跟她走。
护士带我进入一个单间病房,说,“我叫罗拉,是你今天的主管护士。”
房间不大,正中有一张医疗用床,床头两侧是各种监控仪器,显示仪跳动着数字。我换好病号服,躺在病床上。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罗拉走进来开始帮我连接监控设备,血氧仪、心电图、血压带。她很友好,问我家住在哪里,怎么过来的,谁会在外面等我。
“我们需要给你埋静脉针管,”没等我反应过来,针头就刺入了我的左臂静脉,只是一下刺痛,罗拉抽出针头,留下软管在里面,疼痛就消失了。
我从护士的一顿操作中回过神儿来,从包里摸出手机,给T先生打电话汇报了进展。一阵困意袭来,我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
切除子宫的决定做了之后,我并没有反复和动摇,而是越来越兴奋,想到以后不会再来月经,不会再痛经,能多出多少时间啊,感觉生命都被拉长了。当然,我还没有去想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做点什么好,最近一些日子想得最多的是,如果手术出了意外应该怎么办。
我写了遗嘱,跟T先生交代了一些账号密码,其他的似乎也不没什么可做的了。想到这里,我睁开眼睛,再次找出手机,打开摄像头,对着镜头说,“嗨,小爱、小森,我是妈妈,我现在在医院,我准备做手术了。很快就可以回家看你们啦。妈妈爱你们。”然后用摄像头环顾了一下四周,白墙、风景画、嗡嗡作响的医疗设备。好了,30秒,如果有什么意外,这会是孩子们能看到关于我的最后影像。
这时,另一位护士来了,她拿出一叠文件,跟我核实手术内容,确认风险。
“你知道手术要做什么吗?”她问。
“知道,子宫切除。如果发现有内膜异位病灶,也会一起切除。”我回答。
“好的,写在这里”,她指给我要填写的位置,
“不切除卵巢。”她补充。
“对,保留卵巢。”我赶紧在表格上加上了保留卵巢,这可不能弄错了。
护士还和我核对了T先生的联络方式,“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吗?”
“如果子宫切除之后,卵巢还会继续工作,排卵,对吗?那么排出来的卵子会去哪里呢?”这是我刚想到的一个问题。
护士愣了一秒钟,说,“哪里都不去,输卵管会被封住,卵子就待在里面。”
“哦。”
那这些卵细胞会死掉吗?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觉得在当下好像不太重要。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

咚咚,急促有力的两下敲门后,门被拉开了。我的主治医生C走进来,她穿着羽绒服,脸颊红扑扑的,带着室外的凉气。她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笑容依旧亲切灿烂。见到C我心里踏实很多,C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妇科疾病情况复杂、手术难度高,在医学上却不受重视,风险高又不赚钱,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做。C一直专注在内异症领域,帮助了很多病患减轻痛苦。
“你准备好了吗?紧张吗?”C问我,声音轻快。
我说自己不紧张,同时反问,“你紧张吗?”
C听了笑了笑,离开了。
房间再次安静下来,灯光昏暗,床头的监控设备时不时发出“嘀——嘀——”的声音,屏幕上显示着我的血压、心跳和心电图。突然有点想念妈妈爸爸,他们还不知道我要做手术,说了也帮不上忙,只能平添一份紧张和担忧。我盘算着,是做完手术就告诉他们呢,还是等完全康复了再告诉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国了,手术之后要回去一次,带着孩子们。这算是一个遗憾吗?还有别的吗?如果生命到今天就结束,好像也没有更多遗憾了。这样想着,心里放松了很多。
我闭上眼睛,任由思绪飘散。突然门被拉开了,灯光被推到到最亮,刺眼的白光让我睁不开眼睛。蒂娜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大夫,脚步轻快,笑容让他看上去很年轻。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关于有没有吃饭、喝水,服用什么药物,喝不喝酒之类的。然后,他拿起一个注射器,把一管药水打进了之前罗拉留的静脉管子当中。
时间停止了,记忆就停在那里。

醒来,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应该有很多张床,但我看不见。只能隐约地看到天花板和左边的监视器,监视器旁边坐着一个护士。
“我在哪里?”
“手术很顺利,你现在在监控室,需要在这里呆两个小时。”护士凑上前来问,“你需要什么吗?”
“我好困。”在麻药的作用下,我迅速回到了睡眠状态,但很快又醒了,因为想上厕所。“我想要尿尿(pee)”天哪,我竟然直接说了尿尿,而不是上洗手间(restroom)或者厕所(bathroom),这些成年人用的词汇。好像当你脱去衣服,躺在手术桌上,没有了主观能动性,丢掉了社会属性,回到了只知道吃喝拉撒的婴儿时期。从深度麻醉中苏醒,就像从海底慢慢浮到海面,先是看到一点点光,然后越来越亮,竟然有一丝幸福和欣喜。重生的感觉,很美妙。可惜我的膀胱在叫喊,让我重生得有些急促。
“再等一会儿,这里不行,等回到病房。”护士坚定地回答。
好吧,再忍一忍。我闭上眼睛,试图让麻药的残余带我进入梦乡,但没有成功。大概又过了半小时,罗拉来了。她和另一个护士一起推着我的床出了监控室。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睁开会晕,而且费劲),感受着病床的轮子哐哐作响,左拐、右拐、掉头,终于停下不动了。我回到了最初来的那个病房,属于我自己的小屋。
“我要上洗手间。”我努力地跟罗拉说。
“好的,我扶你起来。”她扶着我坐在床边,“感觉怎么样?头晕吗?可以站起来吗?”
“还好,我试试。”我把身体靠在她身上,慢慢站了起来。因为有麻药,并没有感觉疼,只是很虚弱,加上有点晕。
罗拉扶着我走到洗手间,大概五米远的样子,看着我坐在马桶上。回到病床,罗拉很开心地跟我说,“你已经完成排尿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你做得很棒。这样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你想多休息一会儿还是早点回家?”
“我想回家。”
罗拉拿来文件,记录各种数据。然后推来了一个B超仪,测量了膀胱有没有排空。最后宣布,“没问题,你可以回家了。”
罗拉拨通了T先生的电话,手机放免提,开始跟T先生和我一起交代术后注意事项。一共开了五种止疼药,从程度最轻的布洛芬到阿片类,分不同等级,按照需求来吃。手术安放的止疼泵是直通到腹腔的,疗效能持续五天,第五天的时候要把管子拔出来。
“怎么拔?自己拔吗?”T先生在电话那头透出不安。
“对,把管子从肚子里拉出来,然后消毒伤口,贴上创可贴就可以。”罗拉很轻松地说,“如果有液体流出或者疼痛,或者管子断在肚子里,就直接去急诊室,那边的护士会处理。”
“不能去医院让护士来弄吗?”从肚子上拉出管子,然后堵上洞这件事,让T先生有点惊慌。
“也可以……但是没有必要。有说明书,很容易,不要害怕,绝大多数家属都可以完成。”罗拉鼓励T先生。
释放止疼药的管子很细,直径一两毫米,左右各一根,在腹腔内的部分大概有30厘米,需要拉很长时间才能全部取出来。管子末端有三条短线,看到这个就知道管子被完整取出,没有断在里面。整个过程不怎么疼,只是有一些拉扯的感觉。
回到病房,罗拉继续说,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医生,以下几种情况除外,一旦发现直接拨打911,包括胸口疼痛、呼吸困难、强烈的腹痛,等等。
通话大概二十分钟,各种注意事项没完没了。我迷迷糊糊地听着,觉得跟我关系不大,相信T先生会认真处理。
在罗拉的帮助下,我穿好衣服,侧挎着我的止痛泵,努力地坐在轮椅上,让自己不要滑下去。罗拉拿来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我腿上,这是所有的注意事项和手术报告。我做完手术了,我还活着,而且感觉很好。

“我跟医生通过电话了,手术很顺利。子宫的形状很糟糕,她觉得切除之后应该会极大地改善疼痛情况。”T先生边开车边说,像是松了口气。后来我在医院给的文档里面,看到了子宫的照片,是正常子宫的三倍大小,膨胀成一个球形,只看了一眼我就合上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车程,我们到家了。在T先生的搀扶下,我吃力地从车库走到客厅,躺在了客厅临时搭起来的小床上。回到家的这几个台阶加十米远的距离,几乎要了我的命。我躺在床上,两眼发晕,身体轻飘飘的。庆幸我们安排了这个临时的小床,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走到二楼卧室的。
为了方便我康复,婆婆把孩子们和狗都接走了,家里清净不少。T先生拿来婆婆事先煮好的白粥和小菜,要我吃一点。手术之前已经饿了24小时,肚子咕咕作响,好想吃东西,但现在却吃不下去。我侧过头,努力地喝了几口粥,“我想睡觉。”说着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从沉睡中醒来的第一感觉很不错,我叫来T先生,让他扶着我起来,慢慢走去洗手间。
“感觉怎么样?”T先生问。
“很好,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上厕所。”T先生犹豫了一下,说,“我在门口等你。”
我上完厕所,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穿好衣服,过程不太疼。表现真不错,我心里想。
然后意识空白了,我隐约感觉自己被一股力量卷着下坠,体会到巨大的恐惧。我努力挣扎,想要回到地面,有一刹那我好像回来了,我看见了洗手间的天花板。但只有那一刹那,最终我被黑暗吸走,不见了。
下一刻,我发现自己躺在客厅地板上,似乎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氧气,我使地劲呼吸,感觉安全了。我努力想睁开眼睛,没有成功。我听见T先生在旁边和人焦急地讲着电话,救护车的声音远远地响起,越来越近。
当我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五个穿着藏蓝色制服的急救人员围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领队的是一位女士,她蹲下来问我,用电筒照我的眼睛。另一个人在帮我量血压。“血压60、30。”他们看上去很着急,相互说着话。
“我没事儿,我躺一下就好了。”我费力地说,这点儿事竟然叫了911,真是浪费资源,我心里想。
“你的晕厥是血压过低造成的,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你血压过低。”领队的女士说。
“我不想去医院。”我看着T先生说。这是真心话,我好不容易从医院回来,我想呆在家里。
“我们强烈建议你们去医院,第二辆救护车已经来了,上面有担架,你们什么都不用管。”
就这样,在手术第二天,我被911又送回了医院,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在离家十分钟的地方是我们常去的医院。急诊室医生问,为什么要跑到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医院做手术?我说那里有一个专家。又问,为什么这么大的手术不住院?我说因为新冠疫情的政策。他摇摇头,走了出去。我才意识到,住院是有必要的。
进来几个护士帮我做各种测试,输液。而我只想闭上眼睛,就好像身体能量不足以去处理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要用所有的能量确保自己不再被那个黑色漩涡吸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医生回来了。他跟我的医生C通了电话,他说,手术做得很好,没有问题。“你的手术医生非常专业,也很关心你的情况,是个负责任的好医生。”听他这么说,我松了口气,跑大老远去做手术的这个决定被医生认可了。
“只是止疼泵有一个副作用是使血压降低,我们可以用夹子减缓药物的摄入速度,应该会有帮助。其他检查都没有问题。你需要输液,让血压回到正常范围,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医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手术后因为有麻药和止疼药作用,可能并不觉得疼,但不代表身体没有问题,术后头两天要以卧床休息为主。”
我在急诊室待到晚上七点,血压终于恢复正常。在回家的路上,T先生跟我描述当时的状况,我突然晕倒,没有了呼吸,持续了快十分钟,他吓出一身冷汗。
“你是不是以为我就要这么过去了?”我跟他开玩笑。
“那倒没有,我觉得你不至于。”
这是恢复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好在有惊无险。

手术后的恢复过程很奇妙,我的意识像是一个大人,一个旁观者,看着我的身体像一个婴儿一样,从极度虚弱,什么都做不了,慢慢成长起来,变得有力气。和婴儿成长一样,她也会反复,每次感觉好一点的时候,总会因为多度乐观而受到打击,例如活动多了头晕,拎了重的东西腹部疼痛。
在手术四周左右的时候,我经历了严重的失眠。医生说,这是更年期综合征。因为手术的创伤让卵巢受到惊吓,进入休眠状态,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回复正常。
大概八周左右的时候,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只是还是会经常感到疲惫和困倦。这属于正常的术后反应,身体需要大概六个月时间来适应没有子宫的情况。医生说,最终身体会找到平衡。感叹一下我们的身体真是玄妙又伟大。
我重新开始练习瑜伽,并期待能在不久的将来回到岩馆爬墙。前几天还去了海边,最近又在安排夏天去欧洲的旅行,没有疼痛的日子真好。
过去十多年,我的生活都在围绕着疼痛,然而,她竟然真的消失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无所适从。很长时间以来,疼痛既是我的痛苦来源,也是我的避难所和平衡器。每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和困难,我都会躲进身体的疼痛之中,像是一个借口,更大的痛苦,可以遮盖其他痛苦;而当生活中出现那些美好的、幸福的、幸运的事情,我会用疼痛去平衡,因为我忍受了痛苦,那么给我点甜头也是应该的吧。
而现在,这个避难所和平衡器没有了,生活中其他的问题变得很大,甚至一些问题无中生有出来,比如,我一度担心孩子上学时候的安全问题,焦虑不已;另一方面,我也会想,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在经受苦难,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享受自己富足而安稳的生活呢?我真的配吗?我应该做点什么来回馈呢?和我的身体一样,我也需要时间去适应没有疼痛的生活。
我原本以为变化会在一瞬间发生,就像年轻时候会想,如果我能有一百万,如果我能去西藏转经,如果我能拿到某一个学位,那么我的人生就会被改变。现在我逐渐相信,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大彻大悟,也没有妙手回春的完好如初,一切都有痕迹,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好坏。

童言老师建议我写写手术及康复后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我是有抗拒的。一方面觉得生病这点事儿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了,再写显得矫情;另一方面,好不容易甩掉的疼痛,往前跑还来不及,何必回头看呢。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现在不把这篇写下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写。写下来,给关心我的人一个后续,给自己一个交代。最终我完成了这篇关于手术和康复的故事,回头再读也觉得挺有意思,感谢童言老师几个月来的关心和鼓励。
我的疼痛消失了,很快我会不再记得她来过,生活像是在画布上涂颜料,一层盖过一层,旧的颜色被遮住了而颜料的厚度还在。祝大家健康快乐!
原标题:《我在美国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