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论文 | 记忆研究的未来: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联结
记忆研究的未来: 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联结
编者按:
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作为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持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随着研究的聚焦,记忆研究也面临着诸多批评与担忧。针对此问题,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列举和分析当代记忆研究所遇到的三大瓶颈,然后重新探究记忆概念的价值,从而提出自己对记忆研究出路的看法。文章的关键在于,从意义(meanings)和时间性(temporalities)两个关键词入手,总结得出:记忆研究必须与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进行联结才能走向更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钱力成,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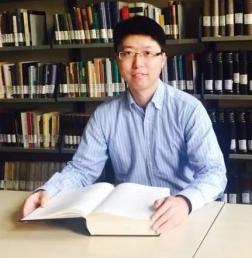
本文作者 钱力成
一、引言
“所有的都已被说过,只是尚未被所有人说到”,这是埃尔(Astrid Erll) 在《旅行记忆》一文开头引用喜剧演员瓦伦丁(Karl Valentin) 的一句话。埃尔引述这句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学界对记忆研究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记忆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只增量不增质的“添加型工作” (additive project) 。我们不仅研究和记录了法guo国的“记忆之场”,也记录了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埃及和拉丁美洲等地的记忆图景。这些记录尽管有其价值,但也不禁让人疑惑: 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再添加一个记忆案例吗?
虽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以及“记忆社会框架”的理论,但当代对记忆研究热忱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记忆潮”(memory boom) 有关。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 当“记忆潮“的高潮退去,记忆研究是否也会逐渐走向没落? 奥利克(Jeffrey Olick) 及其同事在《集体记忆读本》的前言中提出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答案当然是不会———因为研究数量多少不能作为衡量某个领域是否繁荣的标准,而人们对记忆和过去的态度远比批评者想象的更为长久、渐进和复杂。尽管如此,关于记忆研究是否已死或已走向没落的疑问确实存在,它也促使我们再一次思考: 记忆研究的未来在哪里?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列举和分析当代记忆研究所遇到的三大瓶颈,在此基础上,我将重新探究记忆概念的价值、提出我对记忆研究出路的看法。总体而言,本文认为,记忆研究的两个关键词是意义(meanings) 和时间性(temporalities) ,因此,记忆研究只有跟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进行结合才能走向更好的未来。
二、记忆研究的瓶颈
如果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潮兴起开始计算,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记忆研究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皮埃尔·诺拉主持编撰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 、阿斯曼夫妇所提出和引领的“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 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在记忆研究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该领域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的瓶颈,我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疑问: 即记忆研究是否只是一个概念游戏? 记忆研究是否就是故事会? 以及用更通俗的话来说,记忆研究是“软”还是“硬”?
1. 记忆研究是概念游戏吗?
尽管记忆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提出新概念,但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涌现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名词和概念,例如“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集合记忆”(collected memory)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 、“模仿记忆”(mimetic memory) 、“物质记忆”(material memory) 、“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 、“体化记忆”( incorporated memory) 、“刻写记忆”(inscribed memry) 等等,不一而足。在眼花缭乱的同时,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记忆研究就是一个概念游戏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在于辨别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概念。事实上,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而言,概念都是我们认识世界、形成理论的重要工具。马克思所说的阶级(class) 、韦伯所说的地位群体(status) 等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因而是不可或缺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概念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嵌入于人类知识和理论体系、能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崭新视角和重要认识论或方法论工具的概念; 另一类则是在某些具体领域或案例中抽象归纳、相对修正性或累加性的概念(和埃尔所说的“添加型工作”类似) 。尽管这两类概念对我们认识世界都有帮助(第二类概念对我们认识某个区域的特殊性可能更有帮助) ,但相较而言第一类概念对人类知识进步的帮助可能更为重要。这对记忆研究而言也是如此。
例如,“想象的共同体” 就是记忆研究领域中很重要的第一类概念。此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回应了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即民族主义究竟是古已有之还是现代性的产物? 安德森详细分析了历史上所产生的四波民族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民族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 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都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 的出现和时间观念的改变对 形 成 民 族 这 一“想 象 的 共 同 体”至 关 重要——毕竟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之大都不是人们日常接触所能感知到的,只有当本雅明意义上的空洞的、同质的时间(homogeneous empty time) 得以被体认、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报纸等媒介的出现后,人们才可以把那些远在天边的陌生人想象成为和自己同一时间和空间下的国家共同体的同胞。“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也因此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认识论维度。在上文提到的诸多“记忆”中,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首次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将记忆作为个人体验的认知,因此也为人们认识记忆和过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第二类概念是相对“累加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仍有其价值,但在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方面的作用会相对小一些。例如,在“传统的发明”概念指导下,学者们如果在世界各地寻找各种被发明出来的传统,那么这个努力虽然在认识特定区域方面有其价值,但在提供视角方面的创新性就相对有限。另一个案例是福柯的理论。福柯提出的权力毛细血管作用瑏瑡无疑颠覆了我们认识和思考权力的固有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论工具。但如果我们只是沿着福柯的思维去寻找各种权力毛细血管作用的细微机制和案例,那么这些努力虽然在认识特定案例上具有价值,但其对认识论挑战和视野重塑方面的作用无疑不如福柯来的更有价值。同样的,如果我们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框架下的工作内容只是去辨别一个又一个案例时,那这种努力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开创性价值也可能会打折扣。记忆研究究竟是否是一个概念游戏?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记忆研究和其它社科和人文研究一样,它既是又不是一个概念游戏。人们思考、说话、交流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化工作无疑都依赖于概念。但是,我们(作为学者) 提出概念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相比累加性工作的第二类概念,我们更应该探索和理论化那些深深嵌入于人类知识脉络之中并为我们提供崭新视角和重要认识论工具的概念,而这也应该是记忆研究回应和突破概念游戏这一批评的努力方向。
2. 记忆研究是故事会吗?
对记忆研究的另一疑问是: 记忆研究似乎极强依赖于叙事———当我们阅读发生在美国、德国、以色列、埃及和拉丁美洲的研究案例时,我们似乎在听一个又一个有关过去的故事。但在“听故事”之外,记忆研究是否能为我们提供其它更多的(理论) 价值呢? 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破解此质疑的一个前提假设,即故事不能作为我们理论化的工具、故事只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当然,这里又涉及到更为深层次的两个问题: 第一,描述是否可以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第二,如果我们需要理论化,“故事”如何过渡到理论?
针对第一个问题,学界其实有不同的争论。由于记忆研究是一个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对于“描述”在学科中的位置自然也有不同的判断。例如,历史学(特别是传统实证史学) 会更强调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梳理。它虽然也讲理论,但是历史学的理论往往更多的会藏在史实(或 曰“故事”) 背后。与此相对,社会学是一个更为强调理论的学科,它也希望能在故事基础上将理论以一个更为清晰的方式放在前台。当然,社会学家口中的“理论”也拥有不同内涵———社会学家阿本德(Gabriel Abend) 就曾总结过“理论”一词的七种含义,包括关于变量的一般性命题 (general proposition) 、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诠释性的理解经验、对社会学先驱经典的研究、相对整体的世界观、有价值判断的论断(比如女性主义理论) 以及关于“真实”社会建构的(哲学性) 反思等。尽管社会学家对“理论”的理解各异,但其共同的对“理论”的执着追求依旧带来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有“理论创新”,那我们现有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现有理论概念的内涵可能因此被掏空、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经验和理论上反而可能被贫困化———这也是可汗(Shamus Khan) 及其同事《少一些理论、多一些描述》一文的主要质疑和中心论点。
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在叙述和分析时一旦涉及概念,那必然涉及了抽象和一定程度的理论化,因此,所谓的“纯粹描述”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此外,如果我们希望社会学的记忆研究不局限在理解某个特定群体或区域(当然这本身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那就仍然要面对抽象化和一般化(generalization) ,进而涉及理论化的问题。当然,正如上文阿本德的文章所述,理论化的方式和路径可以多元化。这就回到了关于“故事会”的第二个问题: 记忆研究如何从故事过渡到理论。总体而言,社会学的分析中存在着解释和解读两种传统。“爱讲故事”的记忆研究是否只运用解读传统呢? 事实上,“故事”和“叙述”不仅天然地蕴含着解读,其分析视角也可以是解释性的。例如,在研究以色列对前总理拉宾的纪念活动中,研究者(Vered Vinitzky - Seroussi & Chana Teeger) 发现沉默(silence) 既可以帮助人们遗忘、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促进人们记忆; 基于此,作者区分了显性沉默(overt silence) 和隐性沉默(covert silence) ,系统地理论化了沉默对于纪念和忘却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偏向解读的。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和克雷格比较了美国 1960 年代的石墙暴动和发生在三番、洛杉矶和纽约的其他运动,指出只有石墙运动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即行动者是否认为此运动值得纪念(commemorable) 和行动者是否具有足够记忆能力(mnemonic capacity) 将事件转化为记忆载体(commemorative vehicle)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某个社会运动才会被社会记住并被构建为某群体的中心认同。”明显是解释性的(斯考切波式的宏观—因果式)的分析。由此可见,记忆研究并非局限于某一种理论化的方式,记忆研究涉及故事但也超越故事。
3. 记忆研究是“软”还是“硬”?
针对记忆研究的第三个疑问是: 鉴于记忆研究的对象常包括话语、叙述、符号、象征等内容,记忆研究是否太“软”了? 换句话说,话语、符号等内容是否只涉及社会现象的表征而不涉及问题的深层内核? 2017 年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事件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当年的 8 月 11 日和 12日,全美各地的右翼分子(包括新法西斯分子、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等群体) 纷纷聚集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城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进行了所谓的右翼联合大游行(Unite the Right Rally) 。他们游行和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夏洛茨维尔市政府之前做出的拆除罗伯特. 李将军雕像的决定。罗伯特·李将军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军的领袖之一,也被美国南方和很多白人看成是自己的英雄。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罗伯特. 李以及其他一些联邦时期的雕像也常被左翼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标志———这也是夏洛茨维尔在 2016 年投票决定拆除雕像的原因。右翼分子在 8 月 11-12 日的游行中情绪高涨,他们高喊着“这是我们的土地”的口号、高举着纳粹和南方军的旗帜并与反游行的人群发生了冲突。在12日的下午,右翼分子菲尔德(James Alex Fields) 驾驶了一辆汽车冲向了反对右翼游行的人群,并最终造成一人死亡 19 人受伤的悲剧。而菲尔德本人也在 2018 年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例子毫无疑问是围绕记忆的斗争。事件的导火索是如何处置罗伯特.李将军这一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符号; 而人们围绕象征的斗争切切实实的带来了深刻和严峻的政治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 和“真的政治”(real politics) 的界限就不存在了。当某个事物被人们认为真实和重要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真实和重要的影响力及后果。由此可见,话语、叙述、符号和象征等记忆研究的内容并不天然就是“软的”,它们可以产生十分“硬核”的后果。当然,还需澄清的是,记忆研究的内容其实并不只包含话语、符号等表征系统,记忆研究也十分关注与记忆有关的“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 。媒介发展、民族主义、社会和文化认同、纪念仪式、纪念空间构造等一系列议题都是记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换言之,记忆研究不仅涉及人们怎么说的、也涉及人们怎么做的。因此,所谓的“软”还是“硬”并不涉及记忆研究的本质,而记忆研究也无需被此问题所钳制和困扰。
三、记忆研究的意义与出路
既然记忆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概念游戏、故事会,其研究内容也不宜用软/硬的二元对立来认识,那么记忆研究的意义和出路究竟在哪里? 记忆研究如何避免成为埃尔(Astrid Erll) 所担忧的只增量不增质的“添加型工作”? 对此,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元问题上来: 即记忆研究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其实,无论是对记忆的社会框架、记忆之场、文化记忆的研究,还是对以记忆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认同、合法性建构的探究,记忆研究在本质上离不开两个关键词,那就是意义( meanings) 与时间性(temporality)。
意义不仅涉及上文所述的话语、符号、象征和叙述,也涉及更为深层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即韦伯意义上的“理解”和涂尔干意义上的“民情”与集体意识。因此,意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社会学“变量”,而是社会记忆研究的核心元素———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记忆,其核心都是人们对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解和阐释。就此而言,记忆研究自然联结到了以意义和意义实践(meaning making)为核心的文化社会学领域了。事实上,当代文化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影响; 韦伯和格尔茨对文化作为“意义之网”(web of meanings)的理解和比喻深刻影响了文化社会学的发展和轮廓。在此基础上,斯威德勒(Ann Swidler) 的“文化工具箱”理论、维西(Stephan Vaisey) 的双重动机理论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 的文化社会学强范式(strong program of cultural sociology) 等都是在不同维度上对“意义”的探寻。记忆研究也是如此。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诺拉所探讨的“记忆之场”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哈布瓦赫关于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的分析无一不涉及人们对“意义” 的理解以及围绕意义的产生、表达、接受和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因此,只有通过与文化社会学的联结,记忆研究才能摆脱“过去”的魔咒、转而迈向更深层次的意义世界———事实上,近年来有关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世界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的研究虽未言明但实际上正是往这个方向的迈进。
除了意义和意义实践,记忆研究的另一关键词即是时间性,而这也与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要素形成了天然的联结。记忆研究对时间性的强调可以体现在很多议题上———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过去决定论”和“现在决定论”的争论、记忆和忘却的关系和机制、路径依赖和过程性(process) 视角的强调等,无一不体现了记忆研究对时间的敏感。与此同时,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第三波以来的历史社会学开始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事件性和时间性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用赵鼎新的话来说,历史社会学本身就是社会学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时间序列叙事的结合。与此同时,记忆研究必须能反思性地理解自身发展蓬勃的历史时间性———1980 年代学术界对记忆研究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社科学界的文化转向、历史转向相关; 而记忆潮的出现又与冷战与后冷战、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国家从过去寻找合法性、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学者对“进步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的挑战等息息相关,这些都成为记忆研究复兴的重要条件。换言之,记忆研究在当代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关切的历史和历史社会学议题。事实上,记忆研究中的重要作品,包括《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有关犹太大屠杀的“文化创伤”等也正是回应了时代所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用奥利克的话来说,就是记忆研究对“现代性”(modernity) 本身的回应。由此可见,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对当代历史时间性的敏感、离不开与历史社会学的深度联结。
记忆研究与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联结不仅为记忆研究提供了未来,同时也为中国记忆研究提供了机遇。中国所经历的快速社会转型以及伴随这种转型而形成的“中国经验”本身就涉及了对时间性和现代性的回应,而中国人在这种转型下所形成的“中国体验” (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等) 也与“意义”和“意义实践”的问题息息相关。就此而言,与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联结也应是中国记忆研究的题中之义。
四、结语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如果把记忆研究和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联系在一起,把记忆和文化创伤、认同等议题放在一起,那么记忆一词的含义是否过于广泛? 实际上,早在1998年,奥利克和罗宾斯在梳理记忆研究谱系时就已面对过这个问题。他们引用施瓦茨和布鲁默对(Herbert Blumer) 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和操作化概念(operational concepts) 的区分观点后认为,“记忆”一词实际上是一种为人们提供启迪的“敏化概念”,因此并非如定量研究中的操作化概念那样具有严格和精确的定义; 更为重要的是,“记忆”的价值也正是在其启迪性的敏化概念维度。此外,“记忆”一词的广泛内涵实际上在社会中本身存在、并非是由记忆研究学者定义出来的; 记忆概念的延展性对记忆研究的发展本身也是有益的。本文认同此观点。用“记忆”一词来形容我们为之奋斗的这个研究领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进行某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时则需要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进行理论化,避免不假思索地进入所谓的概念游戏。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是否需要直接使用“记忆”这个概念在此意义上其实是第二位的,更为重要的则是把意义和时间性囊括进我们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在进行经验研究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记忆研究的社会意义。事实上,记忆研究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和西方在二战后对犹太大屠杀(Holocaust) 历史意义和社会正义的探究相关,学者们对线性历史观的挑战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底层和历史无声者的声音被社会听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建构、认同的维系也都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想象和建构。因此,社会记忆研究作为一项学术和公共事业的未来依旧充满希望。
转载 | 向仁雨
审核 | Anders
终审 | 李致宪
©Political理论志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标题:《论文 | 记忆研究的未来: 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联结》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