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傅月庵︱到底谁不爱台湾啊!?
1990年代初,小说家朱天心在报纸副刊写专栏,岛屿上许多读者因此认识了“学飞的盟盟”。那时代还没有“亲子教养”这种听来颇假掰的名词,大家所喜爱的,无非一个新手妈妈(那时好像也没这称呼),很用心记录下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无所谓教养,更不用以眩人,或想教人。小说家心情也许比较接近林良先生《小太阳》里写他几个女儿,或更远时候丰子恺先生画笔下的“瞻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因此认识了谢海盟,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

不停学飞的“盟盟”,后来如岛屿上千万小孩一样,进入体制,过着学校生活,身影渐形隐逝。等他再度出现于普通读者眼前,已是2015年的事了。二十九岁的他写了一本《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电影轰动,此书也不遑多让,有人称这是文学新人“最华丽的登场”,语气不无讽刺成分,更多的当系妒羡,妒他的笔,羡他有那么多“长辈”——背负着“政治不正确”的家族命运,海盟一登场,便似乎注定要被更严苛地摊开审视。——网络如箭,众犬吠声的时代里,有时想想,亚斯伯格症对他也未必不好,至少真可实践“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而非仅念来妆点门面,故作洒脱而已。

引苏东坡《定风波》词句有原因。2010年作家舒国治出版《水城台北》,海盟读后,深受启蒙,于是坚定地在台北市整整走了七年,每日至少走五小时,探访这一水泥城市里,残存的大小水路痕迹。而后化“脚到”为“手到”,写成了“未出先轰动”的这一本《舒兰河上:台北水路踏查》。——若非超乎常人的偏执与专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谁愿意这样辛苦才写出一本书呢?
说此书未出先轰动,也有梗:先是海盟曾以此书为标的,获选“台北文学奖”年金补助,得奖后,年轻评论者曾有不同意见,直指评审有护航之嫌(果然长辈惹出祸!?)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竖耳听闻的路人,谨记在心,等著书出版,一番两瞪眼看好戏;次者,《行云纪》虽也好,但如书名所言,也就一本“侧录”,报道成分居多。海盟能写,已经自证,但到底能不能驾驭更“无据”的东西,或说“创”出一个题目来“作”呢?《舒兰河上》光看写作大纲,企图强烈,计划庞大,要以一人之力完成,确实有点如梦似幻。他真的能吗?关心的人也都等着看。
终于书出了!翻读一过,关心的人已可放心;有意见的人或也应撤回意见了。台北文学年金制度那么多年,补助那么多人写出那么多作品,真正能够开拓“台北书写”疆界者实为数有限,个人很主观的看法,《舒兰河上》当是其中极出格的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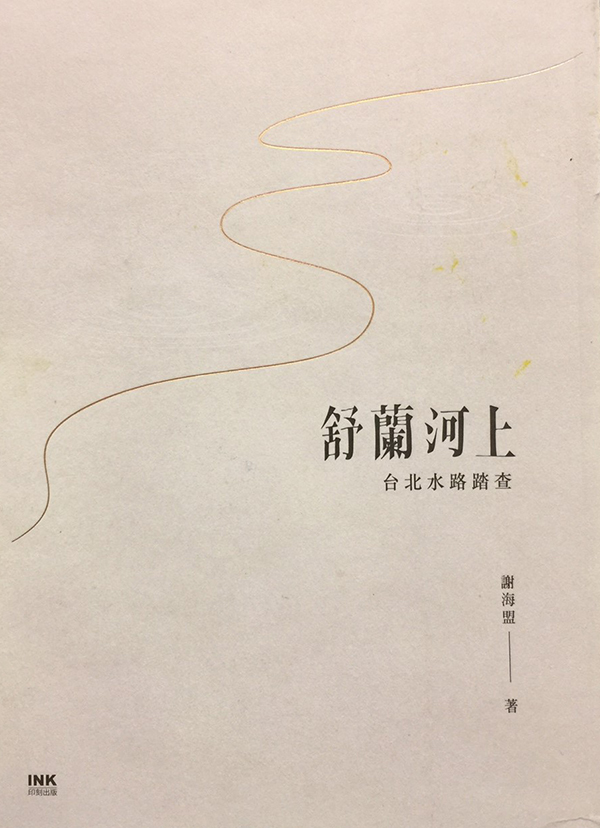
台北盆地曾经是个堰塞湖,且不只一次,这是众所周知的,几度物转星移,沧海终成桑田,盆地里却还残留许多陂塘湖泊,大小河流。数百年年前,先民到此开垦,胼手胝足,筑堤挖沟兴水利,造就了稻米水乡。一直到1960年代,盆地里务农多于工商,即使早成台湾首府,依然圳渠密布,陂塘四处可见。“四十年来台北最大的改变,我以为可得一句话:由水城变成陆城。”作家舒国治在他的名篇《水城台北》开宗明义这样说,并在《水城台北之河迹》一文中,约略描绘早被填平或加盖成路的大小圳沟可能的分布。海盟所要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整辑排比,考镜源流”,一步一脚印,将这些沟渠现貌一一找出来,其艰难可想而知。光是前置作业所用到的地图,顺手拈来就有:《台湾堡图》《瑠公水利组合区域图》《台北市市街图》“美军轰炸图”“美军空照图”……以及他生逢其时,得能随时键取的手机Google地图。要挖宝,就得有藏宝图。这些地图以及参考文献格外重要,可惜初版书后无附,再版时或可考虑。
“工程浩大,很难,不简单喔~”若仅是这样,一般受过田野调查训练的人,多点恒心毅力,倒也不难办到。真正让人惊艳的是,自言不当“女同志”,决意当“大叔”的跨性别者海盟,把这一非虚构作品写出浓浓文学味道:
水潭以中段的永安祠为界,下游水潭栖息灰黑吴郭鱼间杂着两三尾红尼罗鱼群,拦河堰上每每可见浮挂的鱼尸,然而这群鱼始终不见口数凋零;上游则是各色溪鱼,往往成群黑压压聚在平静潭面下的水急处上溯。永安祠公厕旁的山壁很有意思,小小岩洞布满起司孔般的壁面,那是海蚀洞,山中无甲子,给地壳运动抬升到深山里,也不知道多少寒暑了。
三言两语,钩勒到位,兼以着色。类似片段,书中所在多有。
此书好看!摸索沿河行,拉出一个又一个人,串成一个又一个故事,说出这本那本小说的这一那一场景,有欢乐有哀伤,无论山河故人或老去的猫狗,败废的旧村老厝,乃至缘遇的花花草草,都耐看耐嚼。或要让人有所不耐的当数“经过某某街几巷几号转入某某路几号……”段落,你若在家看,尽管跳过无妨;读后心动,竟也寻河去了,彼时即知这些段落有多好、多重要。
乍读此书,人们或要想起“杀人鲸麻麻”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的笔法,《三十三年梦》的笔调。这是明显可见的。海盟当仁不让的是,他的笔法相对层次繁复,他的笔调相对宽容温柔,两相抟糅,遂让我们想起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乃至《陶庵梦忆》的某种幽微心情——尽管同行有人,动保人、电影人、编剧、导演……所踩踏的亦是他所认定的家乡土地,我们却时时可感受到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某种悲凉,或说自伤。这到底是因接收了太多别人的记忆而铸就的老灵魂所致呢,还是根源于“生下来没有完整身体”,一辈子挣扎想要拥有而不可得的无奈呢?
有不待风吹而自行散落者,人心之花是也。忆昔伊人之深情挚语,一一了无遗忘,而其人则成路人矣!其别盖过于死别焉。
《徒然草》名句,老掉牙的东西,看完书,想起了,随手记在书后,无来由。另外一个疑惑,就藏在心里了:“到底谁不爱台湾啊!?”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