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谈|彭勇、杨海英:南明到底亡在哪里?
顾诚先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1978年,顾诚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该文钩沉史料、严密考证,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也成为其成名作。1984年,《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别开实证蹊径。1997年,被顾先生视为姊妹篇的《南明史》问世,该书在海内外均有广泛的影响力。今年是《南明史》出版25周年,读客文化对这部经典著作进行了再版。4月24日,中央民族大学的彭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海英研究员,围绕“南明到底亡在哪里”展开对谈。澎湃新闻择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活动现场
《南明史》背后的故事
彭勇:我最早报考顾诚先生的研究生是在1994年。我是1992年读硕士,1995年毕业的,所以在前一年的秋天到顾先生家里去拜访,向先生提出希望报考他的博士。顾先生当时表示欢迎,还和我说起因为《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包括河南人民出版社在内的出版机构都曾和他联系,表示想出版先生的其他书,但当时顾先生手上的《南明史》还没出版,因此写书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入学后,顾先生时不时地会给我讲到写作《南明史》时的一些故事。顾先生出版过两本专著,一本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本就是《南明史》了。《南明史》一直是到1997年才付梓,两本书间隔了10多年的时间。其实顾先生在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之后,马上就动笔写《南明史》了,但南明的历史确实很复杂;另外,先生在写作时发现明代的卫所制度太重要了,所以他就暂时搁置了《南明史》的写作。从1986年到1989年间,先生发表了4篇关于明代卫所制度的文章,如《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
顾先生的治学风格很严谨,他都是手抄史料。抄写用的纸是在印刷厂定制的专门稿纸,比我们现在的A4纸要大一号。顾先生抄史料的时候会留出1/3的空白,以便在边上作批。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明史部分有一册的题字是顾先生题的。顾先生的史料都是从图书馆里一点点抄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曾提起自己为找史料特地去昆明住了一个多月。南明永历最后那几年是在昆明活动的,顾先生住在昆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天天都在抄材料,其中不乏很多珍贵的材料。
今天很多学者,尤其是明清史学者,提倡要搜集新材料、跑田野,其实当年顾先生收集材料的那种方法,也是跑田野的一种形式(虽然顾先生天天待在图书馆,没有时间真的跑出去走走看看)。顾先生还向我说起过,《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讲的都是农民军在地方打仗的历史,因此,先生读地方志的一个方法就是随着农民战争的路线而行进,打到哪里,他就去看哪里的地方志,因此先生最终来到了昆明,并在昆明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先生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地方志一一看完的,所以很多人都用“竭泽而渔”来形容他研读材料的精神。虽说明清史的材料太过庞杂,不一定、也不太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但是这种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提起《南明史》,顾先生还说起过他之所以迟迟不愿意交付出版社,也因为他一直是手写,写着写着有新材料了,他就得改;改得乱了,他就得再抄。先生每抄一遍、改一遍要小半年时间,我们后来整理先生的手稿时,就发现有很多包稿子,先生的手稿是用旧的挂历做封面,然后拿大夹子夹上,一本一本的,现在这些手稿都捐给了北师大图书馆了。先生在《南明史》的后记里面说起自己实在是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其实这也是因为先生对学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当时有很多人来问他,说《南明史》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姐姐都已经出版10年了,怎么还不见妹妹,其实这跟顾先生的治学方式有很大关系。
杨海英:秦晖先生当时为《南明史》写过一篇书评,名为《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且顾先生自己也对这篇书评很满意。
书评提到了《南明史》的“三个超越”:一个是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一个是对改革前史学的超越,还有一个是对当时流行史学的超越。我觉得秦晖先生的总结到现在也没有过时。25年过去了,据我所知,南明史研究领域并未出现超越顾诚先生的著作。顾先生对南明历史的梳理和研究,给后学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
我其实没见过顾先生,但有书信联系,顾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回信。大概是在2000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隆武政权的文章。我是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是王锺翰先生的博士生,入学的时候王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因此他指派大师兄姚念慈老师带着我们做具体的研究工作,姚老师就对顾先生非常的敬佩,常跟我们提起顾先生是一个为学术而生的人。我是1996年毕业,毕业后就直接进了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先生当时成了我的业务指导老师。
读博期间,王锺翰先生给我指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写洪承畴,但是我摸了一段材料之后,说自己写不出来,因为当时已经有三本相关著作出版了,因而改写东南士绅了。进入历史所后,何龄修先生建议我把洪承畴的研究再捡起来。要研究洪承畴,就必须关注南明。顾先生的《南明史》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买来读了。
顾先生在《南明史》中写隆武政权,提到了黄道周,提到了隆武帝的亲征,也提到了黄斌卿在舟山的不作为,但相对是比较分散的。而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关注的是洪承畴怎么平定南明、稳定江南,因此这几个历史事件就能够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当时自己写完文章也有点兴奋,就赶紧给顾先生寄去了,后来顾先生给我回了一封信,给了我认可和鼓励。
南明的“内斗”
杨海英:顾先生有篇论文题为《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其实对于南明而言,有很多关键的时间点。隆武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西南的永历也是关键时间点,以山西姜瓖为代表的北方各省的抗清斗争又是一个关键点,可以说,南明当时的情况就等于不断失去一个个机会,没有踩准这些关键点,好好的机会一再断送。断送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斗,而并不在于清军有多强大。顾先生也提到八旗并不是天下无敌,清军将领很多都是降兵降将,包括像洪承畴。其实胜利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怎么用人、采取什么政策,跟清朝相比,南明就是因为内部斗争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失败。
彭勇:从我的理解来讲,“内斗”本身是一种比较显性的说法,很容易让读者记住。而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所谓的党争,明朝的党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所谓的东林党也只不过是一群为了谋取自己私利的一些临时组织而已,这一点已经从学术上讲得很清楚了。
所谓的党争或者说内斗,只不过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所谓明朝的复兴,只是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已。刚才杨老师特别提到了很多个关键点,从当时的实力对比上看,局面其实是有可能被扭转的。南明到了后期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了,很多人都打着南明的幌子谋求自己的私利,可以说是内斗,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大家都认为郑成功厉害、李定国厉害,但实际上,一些看上去很厉害的力量加起来以后反而弱了。
顾先生在《南明史》里多次用了“鲜廉寡耻”这个词,这个词极富感情色彩。《南明史》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因为中间出过几版,我都需要做校对,都需要从头到尾地去读,顾先生这样的词,我印象太深刻,说明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杨海英:这是《南明史》特别鲜明的一个特点。鞭辟入里、力透纸背的分析,再加上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所以读者爱读,我确实觉得读来有种章回小说的精彩。
司徒琳的《南明史》提到明代的宗室数量庞大且没有实权。但从南明的角度来看,如果那么多的宗室能够团结起来,也会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而清朝采取的政策就是把南明的宗室集中起来,然后杀掉,发现一个就杀一个,宗室的旗帜就倒下了。南明的帝王中属隆武帝最有进取心,很多都从没有定过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能过一天算一天。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他们却完全看不到,甚至是瞎指挥,葬送了很多机会。因此,《南明史》读起来确实是让人痛心疾首,尽管对手也犯了很多错误,但南明就是没有抓住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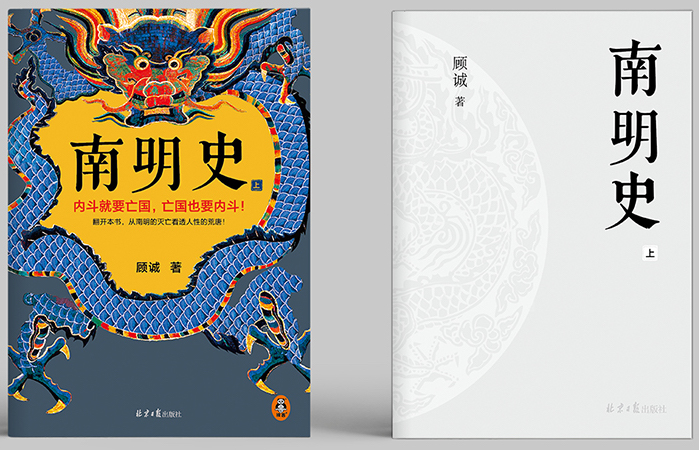
《南明史》,读客文化·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
农民军和民族问题
彭勇:《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可以对比来读,明朝末年的农民军其实是结束了一个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的明政权。明朝到了后期,这个机构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靠崇祯皇帝他自己已经解决不了了,要不然也不会有农民起义的爆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顺和大西农民政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
但到南明时期,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无论是大顺、大西,还是南明或清朝,这种逐鹿天下又是一种新的力量格局了,是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如果这个时候南明能够和大顺、大西结合起来,这股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但关键是南明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南明君臣大一统的思想里,曾经降过大顺、大西的官员都不太能被接受,更何况是要联合这些逼死崇祯皇帝的力量?恰恰相反的是,农民军意识到了要联合,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采取的一些政策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种威胁,因而开始寻求与南明的联合,这确实是一种战略眼光的问题。
杨海英:顾先生对史可法的评价不高。但何修龄先生就觉得不要那么苛刻,因为这种转变对史可法等人来说太难了,“平寇”是他们从明末起就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从敌人一下子变成战友,确实是很困难的。
彭勇: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清军入关之初犯了很多错误,刚开始,清军的进展还挺顺利的,之后就实行剃发易服,引起了强烈的抵抗,所以很快又停止了。姚念慈老师就研究过这个问题。
由于反清复明高潮的出现,多尔衮慢慢也开始改变政策,所以说各种力量其实是在博弈。顾先生在《南明史》的序言里讲到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那一段说的是非常经典的。他认为历史大体很多都是偶然性的因素构成,所谓的必然就是指历史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其中也充满了很多变数、很多偶然。
杨海英:《南明史》是以抗清斗争为主线,可以说是以明为本位的,而当时流行的是以清为本位、认为清的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观点。顾老并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当时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不容置疑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20世纪的再发明”而已,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民族矛盾。
如果清初民族问题不存在的话,那么当时不至于会出现多地多次的抗清运动。江西的、山西的、陕西的,包括南方的,短短十年之内,一处平定一处又起。就从我研究的洪承畴来说,他第一次出镇江南,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就把隆武政权和鲁监国平定了。但不久后,北方民众的抗清斗争又起来了。姜瓖这些都已经降清、接受了清朝统治的人,为什么又反了?多尔衮甚至亲征了两次,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大同被围城八个月都没有被攻下,当时姜瓖没有外援;如果有外援的话,也许就能取得胜利。清初的这种机会太多了。顺治十年洪承畴经略西南,坐镇长沙,四年多时间寸土未恢,在那里待了那么久,却不能前进一步,为什么?其实清朝力量根本不够,无法统治这么大的一块区域。但就因为孙可望跟李定国有矛盾,他们又斗起来了,才让清方有了可乘之机。其实当时洪承畴已经递了两次辞呈了,他说自己干不下去了,身体不好,请求退休。等到他的退休报告刚送出去,这边孙可望投降的人就来了,他马上想,机会来了,但报告已递出了,清廷也已经看得透透的了,所以最后也没怎么给洪承畴好脸色。
所以在一个翻天覆地、充满巨大变化的时代,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选择也不一样,结果当然也不一样。
彭勇:刚开始清朝统治者是打着“复君父仇”的幌子,并且接纳汉族官员,但过了两年就开始实行一些所谓倒行逆施的民族政策,反而使一些反清复明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了。对于后来的清朝统治者而言,满汉民族矛盾的弥合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清朝统治者自己在政策上的反复也很激烈,这其实也印证了民族关系问题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个案:柳同春与吴兴祚
彭勇:顾先生曾经跟我讲过,第一版《南明史》在印的时候,出版社曾经跟他商量说能不能放一点插图,这样可能更好看一些。顾先生还真的是选了半天,最后,他就只选了柳同春《天念录》里边的那一幅图。
柳同春这个人,并没有被列在《清史列传》的“贰臣传”和“逆臣传”里,说明他可能都不入乾隆的法眼,连名列其中的资格都没有。但柳同春本人,其实代表了明清易代时一些武臣的命运。柳同春是河南太康(属开封府)人,任繁塔千总。到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时候,明朝派他带着河南的军人到北京参加防御,那时候农民战争已经如火如荼。柳同春很会审时度势,他一想明朝已经气数已尽,就想着不如干脆就降了大顺。大顺那个时候正是势如破竹地往北京打,柳同春被安排守卫山西,负责地方治安,得了一个官。
顾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里边附了很多页的大顺派往各地的官员表,柳同春就是其中之一。柳同春降顺后不久,李自成就进了北京,且很快又被赶出来了,于是柳同春就开始彷徨。他没有跟着李自成的大军一直南下,而是继续徘徊游走,因为即便回河南,路途上也会有各种问题。当时柳同春主要靠抢劫当地百姓以养活手下的人,所以他实际上已成流寇了。犹豫了几个月之后,柳同春决定降清,清朝给他派了一个官,后来到了江西任都司。在整个南昌城重新反清复明之后,这次柳同春很坚决地不投降、不反清了,而且还冒着一家几十口被杀的危险,自己把头发剃了,扮成和尚逃出城去,把南昌被围和叛乱的消息直接送到南京。后来柳同春就以此争功,认为若不是自己去传消息、搬救兵,南昌城早就完了,甚至整个南方都完了。
柳同春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反反复复,最后却立场坚定了——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其实我也让我的研究生、本科生去做过研究,看看明清易代时有多少是投降的,多少是不投降的,有多少是被杀死的,有多少是自杀死的,又有多少是躲到山里去了。
我认为人是那个时代的一粒尘埃,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要对当时的人有太高的要求,更不要做过多的道德评价和判断。但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比如史可法、李定国,自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舍弃很多东西。而对于普通人,我认为道德上的鞭挞、标签式的评价,是没意义的。
杨海英:像郑芝龙其实很关键,隆武政权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他全心全意的支持。他有他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我也在想,如果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会怎么选择、能否看清形势走向。郑芝龙的选择是跟着清朝走,还叫他儿子郑成功也跟他走,但没想到他儿子不听他的。我想如果郑芝龙要是选择跟隆武政权合作的话,历史被改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郑成功后来还坚持了那么久,而郑芝龙却被清廷杀头。
我做过有关明末清初江南人士的研究,关注过一个吴姓的山阴世家,明朝时这个家族里最著名的就是万历九年做过蓟辽总督的兵部尚书吴兑,后来他们家族的很多人都跑到辽东去了,并在那边安家。他们家族有很多人都很有意思。清初的福建按察使吴兴祚就来自这个家族,“洪承畴以内阁经略五省、吴兴祚由知县三年升总督,皆异数。”
明末清初后金势力起来了以后,这个家族的有些人是逃走,被杀的也有很多,吴兴祚的父亲吴执忠被俘,后在代善府上做了十几年管家。到顺治初年入关后,吴执忠才开始分到各地做知县等官,吴兴祚也是在做过多任知县,后靠在东南沿海与郑成功武装抗衡、较量,立下汗马功劳而获得清廷“超擢”,从无锡知县骤升福建按察使,成为旗下新贵。
我们来看看吴兴祚的人生轨迹,这位出身于明代山阴世家的大家子弟,后成为正红旗下的包衣,之后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到了清这一面,在东南造船、组织军队,直接跟刘国轩的水师对打,后凭功劳成为新贵阶层。同样在福建前线立下大功的姚启圣也是绍兴人。这些人真的是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绑上去,姚启圣还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
所以说在面对你死我活的争夺江山之时,如果还是三心二意的话,怎么可能成功呢?一定是要把所有的身家都摆上去,所以我们重新思考郑芝龙三心二意的选择时,感慨也就更多了。
彭勇:我们经常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越是在大变革的时代,越是能够去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人的本来面目,看清在历史发展的常态之下的一种突变,往往那才是历史的真实。
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让大家很感慨的是,它本来是整个王朝更替中的其中一环,但是不一样的是,大家会去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发展的快车道了,而晚明时期出现了一些所谓叫资本主义萌芽或是近代化的一些因素,有人认为这个时期已经是世界的一体化的开端。
而进入到清朝以后,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又重新回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帝制时代,尽管后来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一看,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当我们对比1840年和1644年时常常会发现,间隔两百年,怎么我们看到的事物会别无二致,而这个症结,恰恰可以在由明到清的转变期里找,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遗民心态的问题,本来还是叫“残山剩水写荒凉”,最后架不住整个时代大势的裹挟,大家又回到了这种传统的秩序当中去。
所以到1840年中国人被迫去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社会怎么和1644年那个时候如此相似——这可能是读《南明史》会有的启发。确实,有人说这是一部“痛史”,但是同时,它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像顾诚先生说的,如果把历史的一种结论,当成是一种必然的话,那和传统王朝提倡的天命眷顾又有什么区别?如果都去拿结论去论证其必然,而没有一种批判、反思的精神,也就没有研究历史、反思历史的必要了。
(本文已经彭勇、杨海英审阅)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