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6
纪念拉兹|赵英男:约瑟夫·拉兹与法哲学的战国时代

约瑟夫·拉兹(1939-2022)
据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法学院以及“莱特播报:哲学博客”(Leiter Reports: A Philosophy Blog)消息,国际知名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于当地时间2022年5月2日在伦敦去世。
拉兹(1939-2022)自1967年以来,任教于希伯来大学哲学系及法学院、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著有《法律体系的概念》(1970)、《实践理性和规范》(1975)、《法律的权威》(1979/2009)、《自由的道德》(1986)、《公共领域的伦理学》(1994)、《迷人的理性》(1999)、《价值的实践》(2003)、《在权威与解释之间》(2009)、《从规范性到责任》(2011)、《规范性的根源》(2022)等作品。
2022年5月2日,国际著名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 1939-2022)于英国伦敦逝世。至此,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英美法哲学发展的三位重要学者——另两位是赫伯特·哈特(H. L. A. Hart, 1907-1992)与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1931-2013)——都已作古,成为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回顾哈特之后英美法哲学在形式与实质、方法与内容方面的发展,拉兹的影响力恐怕无人可与之比肩。在辉煌的学术成果之外,拉兹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至今仍活跃在国际法哲学舞台的学者,其中包括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已故,牛津大学)、莱斯利·格林(Leslie Green,荣休,牛津大学)、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康奈尔大学)、布莱恩·比克斯(Brian Bix,明尼苏达大学)、斯科特·夏皮罗(Scott Shapiro,耶鲁大学)等我们理解今时今日的法哲学发展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斯人已去,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接下他手中的长矛与肩上的行囊,遍历他来时的路途与风霜,去一窥他曾许诺的远方。不过在此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才是“法哲学”。
走近法哲学
在英美语境下,“法哲学”的常见表述有两个,一个是legal philosophy,另一个是jurisprudence,其中尤以后者常见。在中文表述中,它往往被译为“法理学”。据说这是源自穗积陈重(1855-1926)的译法,但也有学者考证指出,早在他从德国留学回日本之前,出版于1881年的《哲学字汇》中就已有“法理学”这个名称。穗积陈重将这个概念等同于“法哲学”,亦即从哲学视角出发讨论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性等一般性问题。在我国语境下,法理学的含义与此类似,但要宽泛许多。它一般是学科意义上法学二级学科“法学基础理论”的代称,包含了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个视角出发对于法律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与“法律理论”(legal theory)相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我国法理学奠基人之一沈宗灵先生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所言,我们谈起法理学,往往将之理解为法律基本理论,亦即法哲学。
将jurisprudence理解为法哲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哈特、德沃金、拉兹等人所代表的主流立场。在这一视野下,法哲学主要讨论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如哈特在《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61)开篇所言,这是一个“恼人不休的问题”,被许许多多法学家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解答。但是自哈特开始,英美语境中的法哲学尝试借助分析哲学方法,从概念层面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法律是什么”的答案,不是日常生活中哪部法典或判例,更不是买卖赠予这类法律现象,而是对于“法律”这个概念的理解。而要理解这个概念,就需要理解它与邻近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哈特指出,阐明法律的概念就是阐明法律和道德、规则以及强制力的区别与关联。
这种思考方式,使得法哲学需要面对第二个问题,也即我们“为何遵守法律”。如哈特的分析方法所表明的那样,“法律”如果是一个可以在逻辑上同道德、强制力、宗教等等事物相分离的“东西”,那么它是否也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这些事物的行动理由?更形象地说,法律向我们提出了行为要求,我们是因为“法律这么说,我就这么做”,还是因为惧怕惩罚、趋利避害或道德诫命而按照法律行事?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什么”和“为何遵守法律”这两个问题虽然不同,但却存在关联,一般被视为“法概念论”层面的两大主题。
以上都是从行为规范角度理解法律。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司法领域,关注法律作为裁判规范或依据这个主要功能,“法官如何(依法)裁判”就成为法哲学关注的第三个核心问题。现代国家与社会和法治的关联非常密切,法官依法裁判是实现法治的关键一环。法官是否依法裁判、如何才算依法裁判、如何应对新型或疑难案件等等问题,都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议题,且与我们如何理解法律、如何看待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因此,“法官如何(依法)裁判”一般被视为法哲学中与“法概念论”相对的另一个层面:“裁判理论”。
这两个层面的三个问题构成了当代英美法哲学的核心。不同于探究特定时空条件中特定法律制度的特殊法理学,这些问题研究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现象。故而学者们会认为这个理论框架也等同于“一般法哲学”(a general jurisprudence)。约瑟夫·拉兹在过去五十余年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的,尤其集中在“法律是什么”以及“为何遵守法律”这两个问题上。
竞逐圣杯的游戏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前言中,非常有趣地用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方法描述自己的这部作品。他说一方面可以将此书理解为“分析法学”著作,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视为一次“描述社会学”的尝试。无论哈特还有我们现在如何理解“社会学”这门学科,不可否认的是,哈特的理论中有许多可以和社会科学方法对接的部分。最体现这一点的,是他逐渐认为法律其实是一种社会实践抑或惯习(convention),是特定群体外在的一致性行为及内在某种态度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哈特虽然也认为理解法律就是理解法律的“概念”,而把握该概念就是把握其“性质”或“本质”,但他将法律的性质仅仅理解为法律与道德、强制力、规则之间的关联或差异。

哈特
从拉兹开始,英美法哲学对法律性质的理解就与哈特产生了微妙但却重要的不同。拉兹将法律的性质(nature of law)视为法律之为法律所必须具有的本质必然属性或特征,是有关法律必然为真的命题,法理论或法哲学就是对这种性质的探究和把握。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比如,与他年纪相仿的朱尔斯·科尔曼(Jules Coleman)、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都持此论,他的学生加德纳、马默、夏皮罗等亦复如是。在某种程度上,当代英美法哲学有关“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法律”这个“概念”之“性质”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边构建着自己的理论,一边寻找着“对手”论点中的缝隙,相互厮杀之余又会对不忠诚于这一研究路径的人展开围剿,仿佛是一群身披铠甲、自带使命来竞逐圣杯的圣殿骑士。
在这场竞逐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圣殿骑士们念兹在兹的是,我们在判定某个规范是否属于法律时,所诉诸的标准是否必然包括道德。这里的关键点是“必然”这个模态词——法律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在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根据道德标准来判定某个规范是否属于法律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形是偶然的,与具体的经验现实条件相关。简言之,相较于社会事实,道德并非决定法律的最终因素。
如此一来,法哲学中有关“法律概念”的研究,就不再如哈特隐隐约约暗示的那样,似乎既可以从哲学也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加以考察,而是如拉兹及其信众所说,只能由哲学方法加以分析,否则便无法得到必然为真的命题,也就无法认识法律之为法律所必须具有的特征。
这种独特的哲学方法,从哲学分支来说,与形而上学或元伦理学相近,它并不考虑诸如一房两卖如何确权这样具体而微的问题,而是分析法律在何种意义上得到道德或社会事实(比如,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社会成员的某种实践)的“决定”。这好像是说世界如同一块千层糕,我们需要为名为“法律”的这一层找到一个“根据”或为之“奠基”。从实际操作来看,这种独特的哲学方法主要通过梳理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法律”这个概念时涉及的直觉,来寻找它一直追求的法律本质必然属性。这与分析哲学一般意义上探究语词意义或确定其指称的工作不大相同,但也可以被宽泛地称为“概念分析”。
抛开复杂的理论争辩,根据上述勾勒,拉兹会遇到的非常直觉化的反驳就是:既然拉兹承认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为何又认为经验现象不足以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法律理论要探究法律本质必然属性,探究必然为真的命题,这种从使用概念直觉出发的方法又是否有效呢?如果说,过往五十年来拉兹所影响的法哲学发展让这种有关法律性质的研究走向极致,在今天我们不妨仔细想想这两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或许会让我们迎来法哲学的另一种样貌。
三面迎敌的出击
有关法律概念的讨论,更多体现的是拉兹在法哲学方法论层面的贡献。在实质理论层面,拉兹的突出贡献是对法律权威的解读,并在实践哲学“理由转向”的影响下,提出了“权威的服务观”。这场转变大概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的《利他主义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1970)开风气之先,该书从理由角度理解利他和自利的关系。之后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运用理由来描述人的美德,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以此来阐述契约论,达沃尔(Stephan Darwall)则以之提出“第二人称视角”的学说。不过要想了解拉兹的理论,我们还是要先回到法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首先,“法律是什么”和“为何遵守法律”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相关,与哈特的学说密不可分。哈特认为,法律究其根本是一种社会实践,特定社会中的特定成员(通常是律政官员)会有意识地参与某种一致性实践,并对违背该实践的行为报以批判性态度。这种特定形态的实践,既回答了什么是法律,也解释了人们为何会遵循法律。正如维特根斯坦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在我们回溯特定行为的理由时,会最终到达无法解释下去的一点。此时,“我们这样说,这样做,这样生活”就成为了这一切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哈特对于“为何遵守法律”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这是法律,我们就会遵守”。但在拉兹看来,这个答案难以让人满意,因为它只是解释了我们的行为,而没有对之加以证成:法律如此规定,不见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这就好比象棋规则告诉我们马走日、象飞田,但不见得我们现在就应该下象棋。
其次,把视野转向政治哲学,我们会发现理性与权威之间存在着或许难以调和的矛盾。根据通常理解,理性意味着一个人的自律(autonomy),也即我们面对现实情境根据自己的慎思判断做出选择并据此行动;权威则指的是我们放弃自律,接受他律(heteronomy),根据自我之外的某个人或组织的判断而行动。如果我们用自律或理性作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本质特征,又把向公民发号施令的权威归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个人接受国家的权威,似乎就放弃了理性;反之,则有无政府主义的隐忧。这意味着想要证成法律及国家意志对于个人行动所具有的影响,就必须消除权威和理性之间的矛盾。
最后,如果从实践哲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应该做某事”所体现的规范性理解为“我有做此事的理由”,且这个理由可以支持或证成我的行为。按照这种理解,我们遵循法律是由于我们具有支持或证成这样做的理由。那么这种理由是什么呢?它是法律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理由类型的理由吗?它是否属于道德理由?这个理由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还是通过激发我们原有的理由而产生作用?
以上三方面问题,都是拉兹试图通过讨论“法律权威”来加以解决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以一敌三”的多线作战,也正因为如此,拉兹的影响超越了法哲学与法学领域,遍及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元伦理学乃至整个哲学领域。细致分析拉兹的学说恐怕都不是一部著作可以完成的任务。不过总括来说,拉兹是通过“权威的服务观”来解决这三方面问题的。

拉兹
拉兹的权威观念包含三个要素。其一,一切权威指令应当基于这些指令所适用的对象,并与这些指令所包含的情境相关(依赖性命题);其二,承认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而言具有权威的通常和根本方式,就是表明权威适用的对象,如果承认所谓的权威指令具有权威性拘束力,并试图遵循它们而非遵循直接适用于他的理由,就能够更好地遵从适用于他的这些理由(通常证立命题);其三,权威所提供的行动理由并不是对既有行动理由的额外补充,而是对它们的替代(优先性命题)。其中前两个命题构成“权威的服务观”。
依据这种观点,权威并不是提出与行动者固有理由不同的理由,而是提出一种指引行动者如何处理自己固有理由的方案,也即“二阶理由”。行动者根据法律的命令,会放弃固有理由中的一些,同时保护或强化其中的另一些。这就使得行动者形成了基于固有理由的“新理由”,它因法律而得以生成,是对固有理由的取代。这种复杂的理由构造,一方面坚持了理性或自律的要求,也即行动者的理由都源于其自身;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权威的要求,即行动者的行动不是源于自身判断而是权威的判断。这意味着理性和权威并不必然冲突。此时,如果遵循法律能够比人们自己慎思后的行动更好地满足正当理由的要求,也即“通常证立命题”得到满足,法律便具有正当权威。理性和权威的冲突彻底得到消除。
这就意味着法律如此说,我们也有正当理由如此做——我们的行为不仅在法律内部得到解释,而且在法律所依托的道德框架内得到证成。因此,法律是否具有权威,完全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为何遵守法律”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要依靠法律推理在法律系统内部明确法律所提出的行为要求,同时还要将此要求纳入更广泛的道德推理中加以检验。如果说,拉兹在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否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关联,那么在这里他反而乐于承认两者的必然联系。这也让他和哈特的立场产生了距离:首先,法律必然与道德存在关联,法律理论就并非如哈特所说,是描述性的;其次,拉兹学说隐含了一种道德实在论立场,而哈特似乎无此主张。
正是由于这种道德实在论,强调道德是客观的“事实”,拉兹认为法律所提供的行动理由是一种“外在理由”:法律不是通过激发我们内心中的欲望、情感等因素来改变我们的慎思判断与行动,而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这是因为某种行为对某人好,并不等于存在做这件事的理由——前者是依赖于行动者本人视角的,后者则取决于客观价值。这预示了拉兹在2022年最新出版的文集《规范性的根源》(The Roots of Normativ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 5)中提出的“基于价值的理由”这个立场。根据该立场,从价值到理由再到行动构成一个序列,描述的是理由如何作用于人的慎思判断;同时拉兹从行动者本身出发,将推理实践刻画为一种解答特定问题的意向性活动,理性能力则是对事物样态以及行为适切性的认识,这描述了行动者如何能够回应理由。因此,有关规范性和理由的分析,在拉兹的学说中构成了他对于“人”这种存在及其行动的理解。如果说,人类的一切知识,不过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德尔斐神谕的辩证展开,是从自身出发再回到自身的一次旅程,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拉兹做到了这一点,这或许能稍减他的突然离去带给我们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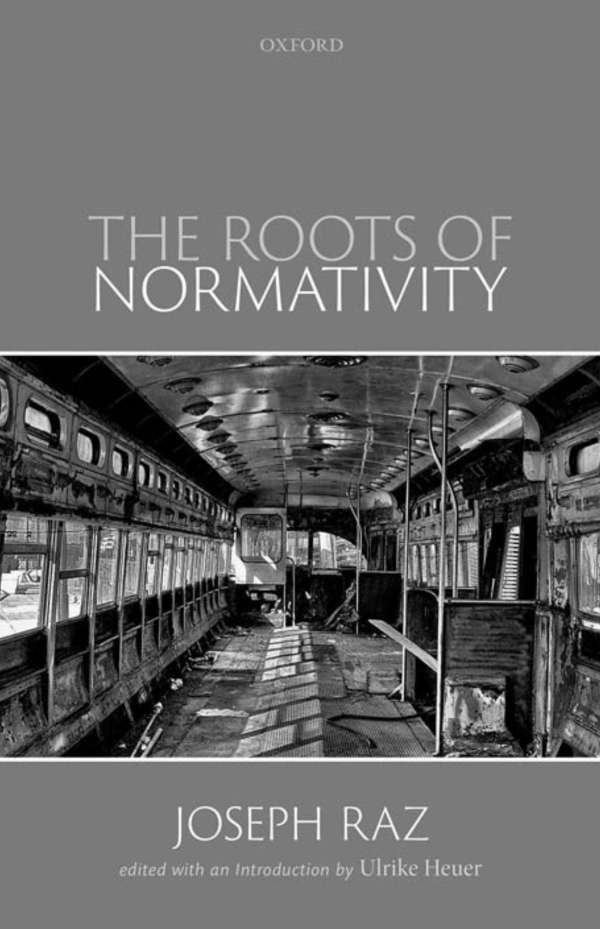
拉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规范性的根源》
是非成败
回顾拉兹依据“权威的服务观”在法哲学、政治哲学、实践哲学核心问题上的战斗,不难发现,他的作品虽然多以单篇文章或文集形式出现,初读之下难免一头雾水,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其实可以感受到,在每一个看似随意选择的讨论议题背后,拉兹都有更为宏观的立场或一以贯之的主线。他虽然没有对相关议题贡献出“鸿篇巨制”(magnum opus),却是所涉足的每个领域中不可绕过或忽视的关键性人物。这种“融贯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可以将不同领域的资源糅合为一个坚实的立场,同时回应多个理论脉络中的难题。比如,他其实是通过实践哲学的“理由论”来理解“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法律主张正当权威,而正当权威是一种“二阶理由”,它服务于更为根本的客观价值(正当理由);正是由于这种客观价值的存在,法律能够被证成具有正当权威,而权威意味着行动者要听从法律而非个人的判断,这就使得道德不能成为决定法律的因素,否则法律的要求将取决于我们个人的道德判断,法律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如此一来,看似仅仅回应“为何遵循法律”的权威理论,实际上也能够解释“法律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实质立场与哈特不一样的拉兹,似乎此时又与之拉近了距离。
当然,从具体内容和论证细节来看,拉兹的学说有许多问题。首先,比较根本的一个是,将法律的性质理解为“主张正当权威”,或许在论证上并不严密。一方面我们不一定非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法律,或许将法律理解为一种社会规划、一种社会惯习也是不错的选择,为何一定要选择这个角度,拉兹并没有做出充分论证。另一方面拉兹承认,不是所有法律最终都能够被证成具有正当权威,这似乎隐含着如下观点:有一些法律实际上在主张自己并不具有的东西。但根据他的立场,我们反而认为法律的这种“虚伪”就是其性质,这未免有些违背直觉。
其次,按照拉兹的理解,权威意味着在实践推理中排除个人的判断,但是根据“通常证立命题”的表述,行动者需要衡量法律和自己的判断相比,哪一个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正当理由/客观价值。这似乎在权威概念中悄悄引入了本该坚决排除掉的东西。如何处理这种认知上的难题,可能决定了拉兹理论的成败。
最后,拉兹预设了道德实在论或价值客观论的立场。作为事实的理由在影响我们的行动时,并不依赖我们原有的理由,也不依赖任何与情感、欲望、利益相关的因素。这种外在理由立场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从认知角度分析,如果一种事物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如何认识到它呢?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一定要同我们发生某种关联,才会产生影响。这使得拉兹的理论似乎成为了一种空中楼阁,精美却难以实现。
不过纵然有这些问题值得讨论,拉兹的理论工作为我们研究法哲学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范本。站在拉兹的延长线上,我们或许会对德沃金这位目光敏锐的哲学家的判断有所疑虑。德沃金曾在《哈特后记与政治哲学的要义》(Hart’s Postscript and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4)中指责哈特与拉兹所代表的立场会让法哲学日益与更宏大的议题和领域丧失关联,最终会变得微不足道而被人抛弃;他在《三十年来》(Thirty Years On, 2002)中更是连篇累牍援引拉兹的表述,对之做出激烈的抨击——这符合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辛辣、尖锐,甚至往往顾不上精确重构“对手”的观点。

德沃金
从法哲学整体发展来说,德沃金的判断不可谓不准确,甚至颇有先见之明。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法哲学与法学和哲学的关系,讨论法哲学一般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关联等等。但具体到拉兹本人,德沃金的指责并无道理。拉兹的理论虽然聚焦在法哲学当中少数几个问题上,甚至主要关注的只是“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性”问题,但他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和基于的问题意识却是统揽全局的。无论这个由哈特开启、拉兹修正的传统是否越走越窄(或许的确如此),拉兹本人的理论却绝非如此。他的宏大理论视野和精细的分析技术在《自由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 1986)以及《公共领域的伦理学》(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1994)中表露无疑。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德沃金的距离或许比他们彼此所认为的要更小。这种宏大与精微并举的理论风格,也提醒我们:单单阅读拉兹,并不能成为拉兹;单单阅读法哲学作品,也无法做好法哲学。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如何做好法哲学,或如何成为一名好的法哲学学者,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领域内重磅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体现着学科发展的成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门学科的混乱所带给人们的不安。2013年2月德沃金的离世,宣告着曾经主导着英美法哲学发展的哈特—德沃金论战正式落幕。其实就在两位论战正酣时,法哲学领域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和大概一致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回顾,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人物与学说可谓“主流”,但深而究之,每位法哲学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随着拉兹故去,众声喧哗与千人千面,与其说是对法哲学领域的一种夸张描述,倒不如说是一种如实相告。毕竟,那位活跃在在研讨会现场以及出现在著作正文或脚注中,接受大家从各方面开火的人,从此将永远保持沉默。不过有关哈特开创、他所修正的法哲学路径的讨论,则一直如火如荼。
近年来对此路径提出严肃挑战且声势逐渐浩大的一种立场就是“取消主义”。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它认为有些问题之所以困扰我们,是因为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或解答问题的路径误入歧途。如果可以找到症结所在,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得到了消除。这个立场是从德沃金的学说演化而来的。德沃金认为法哲学领域有关“法律是什么”的回答,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但我们要想解释法律,就需要明确道德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这样就预设了某种道德理论;反过来,如果想要阐明道德要求,就需要辨析它与法律要求之间的区别,这样就预设了某种法律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德沃金质疑在概念层面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斯科特·赫肖维茨(Scott Hershovitz)在《法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Jurisprudence, 2015)这篇文章中指出,法律的规范性就是道德的规范性,我们在进行实践推理时,并不会如拉兹所说,认为法律创设了独特的理由,且其最终证成依赖于更宏观的道德框架;恰恰相反,我们会直接认为法律提出的就是一个道德理由,我们在道德论域中权衡法律和其他道德理由的权重。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制度的行为所带给我们的道德影响力。这些观点启发我们思考,拉兹强调对法律性质的概念研究、强调法律提供独特理由的主张,是否是我们理解法哲学的唯一路径?
同时,社会法律研究,也即运用社会科学成果,回应法哲学或法理论中“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性”“法官如何裁判”等问题的思潮,从多个角度对拉兹所代表的法哲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近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有弗里德里克·肖尔(Frederick Schauer)、罗杰·科特瑞尔(Roger Cotterrell)、威廉·特维宁(William Twining)和布莱恩·塔玛纳哈(Brian Tamanaha)等等。他们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都强调不应当将jurisprudence简单等同于法哲学。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承认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比较好的法学研究方法就是从经验现实入手,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多种样态、发挥的不同功能,而非仅仅依靠基于直觉的哲学思辨。这不是否定法哲学研究的意义,而是破除这一进路在英美法律理论领域的“垄断”地位——法哲学家倾向于将任何不同于自己方法与观点的研究简单地理解为与jurisprudence无关,进而与“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性”“法官如何裁判”等问题无关。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如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所说,法哲学有点像“牛津圈”的游戏。这一方面表明法哲学家的高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的边缘和不为人所喜。当然,这不是说受欢迎的,便是好的;但只为少数几个人来写作,也未必是件值得追求的事,对于法学这门学科来说,尤为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需要思考拉兹所代表的这种精于概念、工于论证的风格,是否有一定限度,是否需要我们无条件地接受并运用到所有问题上面?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相较于亦步亦趋地追随特定人物、特定方法抑或特定观点,在这样一个法哲学的“战国时代”, 走出固有的传统,更为全面地分析自己立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工具,更为开放地看待不同取向和路径的研究,或许是一种可以尝试的选择。毕竟,在这个“失范”的领域中,同行间的交流越来越难有观点碰撞,如果不是小圈子里的相互抬爱,就是不同道路上的相互瞭望,抑或寻找彼此“把柄”的攻防演习。但其实“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理论、议题、概念、方法多元化的时代,择善固执当然可取,但也需博闻强识。
怀念,是为了忘记
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拉兹与他的学说,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被我们热烈讨论和提及?现在做出断言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位严肃的法哲学研究者,都会自觉抑或被动地站在拉兹的延长线上。尽管如韦伯所说,现代社会中的学术研究,其命运注定就是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内过时,但拉兹的名字似乎与哈特、德沃金、奥斯丁、边沁等人一样,几乎就等同于法哲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他被我们兴高采烈地提及,还是习焉不察地忘记,他都没有真正离去。不过,总有一天真正的别离会来临,但或许我们都无需悲伤,因为这一定也意味着我们的成长。


- 《花样年华》25年后重映
- 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发表致辞
- 吴敬平社媒炮轰国球被资本裹挟

- 字节CEO梁汝波:抖音和今日头条要打击无底线搏流量的行为
- 美媒:台积电可能接手英特尔芯片制造业务

- 世界陆地表面的最低点
- 中国古代记录日期的一种方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