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昝涛评《撒马尔罕》:希望枝头的一枚甜果(上)
历史上的卡亚姆
朋友啊,请听我一句忠言,
高举红酒与如花似玉的美人倾谈。
那创世的主宰非常旷达,
才不管你我的胡子是长是短。
既然你无法破解这亘古大谜,
也无从知晓智者破译的天际,
何不以美酒绿茵创造一个天堂,
那彼世的天堂可去可不去。
他以神力创造了人的躯身颜面,
但又事事把恶人照顾成全。
若说酒罐有违穆斯林之道,
酒不也盛在他创造的葫芦里面?
老天啊,可知你对世人暴虐乖戾,
你横行无忌,把世人欺凌催逼。
你让悭吝者富有,让正直人忧伤,
你不是笨伯定然是一头蠢驴。
(【波斯】奥玛·海亚姆:《鲁拜集》,张鸿年、宋丕方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第421-427页)
张鸿年、宋丕方译《鲁拜集》
据伊朗学者考证,上引的几首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四行诗(即“鲁拜”,“鲁拜”一词的波斯语本义就是“四行诗”,系伊朗古代诗歌形式,有四行,每行十一个音节,讲求押韵,类似于中国的绝句诗,同前,第3页) 皆出自中世纪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Umar Khayyām,1048-1131)之手。诗人正是这本历史小说《撒马尔罕》的主角,在中文版,他的名字被译为奥马尔·卡亚姆(为了行文的方便,后文姑且采用中文版《撒马尔罕》里的译法)。
关于笔者与这本历史小说的邂逅,还有一段往事。四年前,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邂逅了已经定居美国的同乡S。有一天下午,我在S家的地下室翻看散落得乱七八糟的书,得知我正在选修乌兹别克语后,他主动推荐并赠送给我一本他已经不需要的英文旧书,S说自己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简单翻了翻,此书对了解中亚历史可能有用。这本书就是黎巴嫩裔法国小说家、历史学家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的《撒马尔罕》(Samarkand)。S送给我的是该书1994年的英译本(Amin Maalouf, Samarkand, Translated by Russell Harris, London: Abacus, 1994) 。现在中国大陆刚又有了该书的中文版,由黄思恩、林子涵与彭广恺几位译者直接从法文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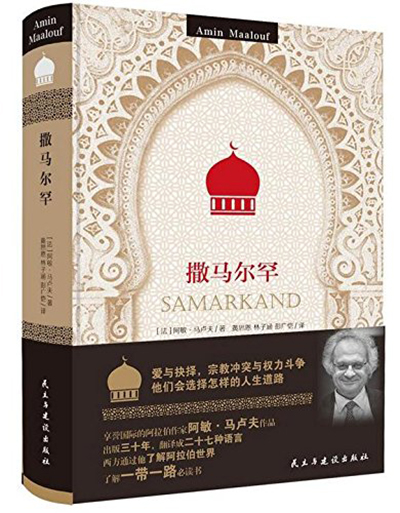
《撒马尔罕》一书叙述的诸多事情,主要发生在今天的伊朗境内,而不是在撒马尔罕。它的主要线索是围绕着十二世纪塞尔柱突厥帝国的一位思想家和学者卡亚姆的四行诗手稿的命运(创作、遗失、寻找、再现与沉睡海底)来展开,故事性比较强。在内容上时间跨度很大,前半部分集中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后半部分的叙事涵盖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书的后半部分讲的是卡亚姆及其《鲁拜集》在十九世纪西方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情节是,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虚构角色“我”——出生于1873年的法裔美国人——两度深入伊朗寻找所谓卡亚姆的鲁拜集《撒马尔罕手稿》原稿(实际上并不存在),后半部分叙事的中心是“我”的见闻以及亲身经历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伊朗的大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初的伊朗宪政革命。《撒马尔罕》一书触及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主题,比如在伊斯兰式帝国统治者与宗教精英阶层的关系,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教派政治问题,西方近代的东方学,穆斯林世界对现代性的思考、适应与变革,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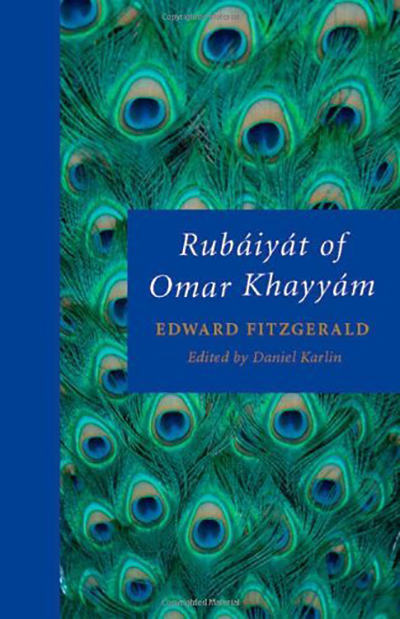
通读《鲁拜集》不难发现,诗歌的意象都来自具体的现实生活[“(《鲁拜集》)诗歌的意象是具体的,来自人类的行为、娱乐和手工制作以及社会形式:在夜晚行进的驼队,制陶人在市场上‘捶打潮湿的黏土’,一场象棋游戏,一场马球赛,一盏魔术灯,穆安津的唤礼。这不是说《鲁拜集》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说它植根于现实。”Edward FitzGerald,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ited by Daniel Kar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xxvii] ,随处可见对美酒和美人的赞颂,对教士、神学和宗教的教条与严苛戒律的怀疑、嘲讽、蔑视与否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现世幸福不加掩饰的迫求。读罢,一个及时行乐、自由不羁、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对此,苏菲(神秘主义)的解读却不一样,他们认为不能被诗歌的字面意思所蒙蔽,那些不被宗教教条所赞同的意象(尤其是饮酒)其实是讽喻性的,代表了灵魂对再次被吸纳进神圣统一体的渴望,在这种讽喻性解释的框架下,醉酒代表的是精神的沉迷,性欲代表的是渴望与神圣相结合,等等。使卡亚姆在西方家喻户晓的《鲁拜集》最早英译者、英国诗人菲茨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就反对关于卡亚姆四行诗的苏菲式解读(Edward FitzGerald,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ited by Daniel Karlin, p. xiv.)。 伊朗著名文学评论家伏鲁基认为:“那些认为海亚姆离经叛道的人没有看到,他的这种追求和探讨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一个人凭他的内心信仰和哲学理念确信创世主存在,并履行一切宗教义务……因为主的奥秘是世人无法理解的……” (转引自张鸿年、宋丕方译《鲁拜集》“译者序言”)

历史上的卡亚姆并不以诗才而闻名,他的同代人主要视其为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视卡亚姆为非欧几何的先驱,他在三次方程式、二项式定理与历法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且远早于欧洲人。早期的那些认识卡亚姆的人(包括他的学生)都没有提到过他的诗歌。直到十三世纪的时候,人们才确认卡亚姆也创作鲁拜。可能正是因为卡亚姆的哲学思想及其部分鲁拜具有前述的那种“离经叛道”的特征,后世的鲁拜集汇编者便将越来越多的此类鲁拜归到卡亚姆的名下,但权威性也就越来越低,关于某首鲁拜是不是真的出自卡亚姆之手这样的考证,至今也不可能有定论(Edward FitzGerald,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ited by Daniel Karlin, p. xiii)。 但对现代人而言,更多的人知道卡亚姆是著名的波斯哲理诗人,是《鲁拜集》的作者,甚至鲁拜这种诗歌形式已经专属卡亚姆了,很少人关注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这可能跟后世科学进步的日新月异有一定关系。卡亚姆在现当代作为诗人闻名世界,也不是靠着伊朗人的推广,而是拜欧洲人所赐。
笔者在文首引用卡亚姆的诗歌,是想让读者能够较为直观地了解这位主人公。细读诗的内容,再联系其所生活的十一、十二世纪伊朗-中亚的历史、社会、宗教背景,不难理解其字面意思上的“离经叛道”。作为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建基于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之上的思想的继承者,卡亚姆一定会在哲学上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新兴的塞尔柱突厥统治者所拥抱的那种伊斯兰正统神学格格不入。“卡亚姆智慧卓越,但有证据表明他被怀疑为自由思想家和异端。” (Edward FitzGerald,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ited by Daniel Karlin, pp. xiii-xiv)这一点在小说的开篇即已点明,当二十四岁的卡亚姆于1072年夏天来到撒马尔罕的时候,当地人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先通过引用卡亚姆的一首四行诗揶揄了他的“虔诚敬神”——
主啊,你打碎了我的酒壶,
断绝了我的享乐之路。
将猩红的酒泼洒在地,
恕我无礼,难道你也醉得一塌糊涂?
(【法】阿敏·马卢夫:《撒马尔罕》,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第6页)
这首四行诗并非小说家的杜撰,在张鸿年先生译的《鲁拜集》第411页上可以查阅到。小说中,接下来的情节是:卡亚姆深知这样的“离经叛道”在保守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知的人”)那里不受欢迎,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他的反驳方式就是否认自己是这首诗的作者。
小说开篇这样一个有火药味的“辩论”场景,实际上暗示了一个历史性的主题:“自由思想”与“宗教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说这个主题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从古至今都存在。而进入近代以后,这个主题又被简化为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问题,当然,这种简化很可能还暗含着某种现代性的短视。马卢夫根据历史资料提到卡亚姆崇拜伊本·西纳,视后者为“独一无二的大师、知识渊博的智者,对理性的倡导者”(一般认为,卡亚姆继承了伊本·西纳的唯物主义哲学观)。 伊本·西纳最器重的弟子杰伯尔因为“傲慢和直言不讳”而被责罚甚至数次入狱,此后他一蹶不振并最终发疯。卡亚姆在刚到撒马尔罕时就见到了发疯的杰伯尔,看到他被人们追打和欺负,此情此景让卡亚姆首先想到了自己——如果不够谨慎的话,自己很可能会落得同样的下场,“终有一天会被无知的大众摧毁”(第4页)。
而后面,当卡亚姆出于不可抑制的同情,奉劝被狂热冲昏头脑的民众不要再欺负杰伯尔时,一个疤痕脸的男人狠狠地说:“这个人是酒鬼,是不信教的,是哲学家!”群众附和着说:“我们撒马尔罕不需要哲学家。”随后,马卢夫写道:“对这些人而言,‘哲学’这个词代表的就是世俗亵神的希腊科学,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指那些既非宗教也非文学的东西。”“尽管年纪尚轻,奥马尔·卡亚姆却早已是闻名遐迩的哲学家,比可怜的杰伯尔更受人瞩目。”(第5页)关于“哲学家”这个主题,查阅张鸿年先生译的《鲁拜集》可以发现这么一首诗:“敌视我的人说我是哲学家,创世主晓得这是一派胡话。自从来到这浮生逆旅,我是何许人,自己也难于回答。” (第319页)如果这首诗是卡亚姆写的,那么,他看起来像是在自我辩解,也像是在自嘲。
文本一旦问世,往往就不再只属于作者本人,更属于读者。以我非常个人化的阅读体会而言,前述所谓历史性的主题其实可以被视为《撒马尔罕》整本书的主题,进一步说就是,如果说作者马卢夫有什么倾向性的话,那就是对卡亚姆所代表的精神/价值的肯定,他肯定的不是对信仰的嘲讽,而是对科学、理性和真理的追求,对这种价值的肯定又会引申出对思想自由的歌颂和主张对权力保持一定的(某种程度上也是高傲的)距离。在书中,卡亚姆的科学研究虽然离不开权力的支持和庇护,必要时他也主动寻求之,但卡亚姆又确实拒绝了直接掌握权力(无论是拒绝当情报总监,还是拒绝极端主义组织领导人的庇护)。作为科学家的卡亚姆,他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是什么呢?其实,人们不必去纠缠和考证《鲁拜集》中诗歌作者的身份问题,在卡亚姆著名的关于代数和方程式的数学论文的前言部分,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我们的时代因为缺少科学家而饱受折磨,我们仅有一个数量极少的科学家群体,但他们中不少人还陷入麻烦……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假装智者的人其实是在用谎言欺骗真理,他们不去拓展知识的边疆,宁可利用他们所知甚少的科学去追求低级的物质享受。一旦他们遇到真诚地渴望获得知识和追求真理的人、力图拒斥谎言和避免欺诈的人,他们就会取笑他和嘲弄他。所以,愿真主帮助和安慰我们。
(Omar Al-Khayyam, An Essay by the Uniquely Wise‘Abel Fath Omar Bin Al-Khayyam on Algebra and Equations,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Roshdi Khalil, Garnet Publishing, p. 1)
小说在涉及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主要讲的是伊朗人对自身腐败和落后的反思,对西式进步和现代化的追求。在这样的一个近代历史主题的框架下,一个虚构出来的西方人又两度跑到伊朗去寻找所谓卡亚姆《鲁拜集》的“撒马尔罕手稿”,似乎在暗示说伊朗人需要在现代找回他们已经失落的“卡亚姆”——甚至是在西方人的帮助下。进一步说,对现代伊朗人而言,失落的其实不是卡亚姆的手稿,而是卡亚姆的精神以及对这种精神的尊重。当然,也正是在这个部分,文学的讽刺效果出来了:在十一世纪与来自布哈拉的美丽性感的女诗人在月光下对酒当歌、缠绵悱恻的是哲学家卡亚姆,在二十世纪初,和花容月貌的波斯公主共浴爱河、一起阅读《鲁拜集》手稿的是个基本上不懂波斯文的法裔美国人……
卡亚姆生活的中亚文化繁荣时期
如前述,卡亚姆在学术上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但如果在时间上再往前追溯一点,便不难发现,卡亚姆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学术繁荣时代的后期,整个这一时期属于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比如,在这一时期生长于萨曼王朝花拉子模地区的比鲁尼(Biruni,973-1048)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巨人,他是第一位研究婆罗门教的伊斯兰学者、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大地测量学家,他早于西方的开普勒将行星轨道确定为椭圆形。前文已提及的布哈拉人伊本·西纳更是科学史上的巨匠,他的《医典》直到十八世纪都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影响巨大,他在天文学、化学、地质学、力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哲学调和了亚里士多德与新柏拉图主义,至十二世纪成为伊斯兰哲学的主流,也因此被宗教学者所敌视,伊本·西纳的形而上学还影响了著名的意大利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在卡亚姆出生之前,伊本·西纳这样的科学巨人已经去世。

弗里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将中亚历史的这一文化繁荣时期称为“启蒙”时代,他的专著《失落的启蒙:从阿拉伯征服到跛子帖木儿的中亚黄金时代》(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就是关于这一主题的,也是迄今关于这一时期中亚文化史的最好著作。对斯塔尔教授来说,他处理的中亚文化启蒙、发展的脉络时段更长,是从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到十五世纪中叶帖木儿时期,在其书中,斯塔尔教授将这段数百年的历史时期分成阿拉伯人的征服和统治、突厥人的统治、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等三个阶段,探讨了中亚文化启蒙时代的背景、多名学者的哲学和科学成就以及中亚启蒙时代衰退的原因,其中卡亚姆占据了比较重要的章节。在这本书中,斯塔尔教授为了突出这一启蒙时代的“中亚性”,非常重视该时期那些著名学者的出生地和受教育地是在中亚。但不能忽视的是,中亚实际上长期属于波斯文化圈。

如果将视野放宽至整个穆斯林世界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学术繁荣是普遍的,囊括了西起西班牙、东到中亚的广阔穆斯林地区。有一本已经译成中文的《智慧宫》(乔纳森·莱昂斯:《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刘榜离、杨宏译,新星出版社,2013) ,“智慧宫”(Bayt al-Hikmah/House of Wisdom)是中世纪阿拉伯阿巴斯王朝(Abbasid,750-1258)哈里发迈蒙(Ma’mûn,813-833在位)支持建立的综合性学术机构,为穆斯林世界的文化繁荣和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世学者将其誉为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源泉、智慧的宝库、学者的圣殿”,《智慧宫》一书讲的是在欧洲蒙昧的中世纪时期,以“智慧宫”为代表的相对先进、有创造力的阿拉伯文明翻译、保存和创造了怎样的科学与哲学成果,这些成果又如何通过征服、贸易和大量来自欧洲的“知识朝圣者”的艰苦译介引入西方,为后来欧洲的文化复兴和近代文明的崛起奠定基础,进而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形态。这本书可以作为斯塔尔教授前述著作的补充,使我们对中古时期穆斯林所创造的文明成就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从“全球史”和“大历史”的角度看,由于存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人类交流与互动,欧亚大陆可以被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甚至非洲也应该被计算在内)。学术与文化的繁荣/创新不只是需要个人的天才、统治者的赞助与安定的政治秩序,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有宽松的思想环境与持续的文化积淀、交流、互动和碰撞。创新往往是多元的产物。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的观点来说,创新需要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过于强调某些学术成就的地域性、民族性或者文明圈属性,未见得就客观和公正,毕竟,“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一直是希腊、罗马和波斯文化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继承者”(【美】简·伯班克、弗里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72页) 。
除了科学的繁荣,卡亚姆活动的时代还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伊朗文化的“复兴”,二是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及其推动中亚的突厥化,并进入伊斯兰核心地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及之后用所谓的“突厥人”来指称历史上活动于内亚和中东地区的,相当大范围内讲突厥语的不同游牧部族群体,主要是为了方便而遵从既定的叙述惯例,当然也是考虑到后世西方语言学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分类;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与“突厥”相关的指称,主要地是周边不同文明的人(汉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对相关群体的他称;在古代史上,除了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突厥”认同,包括乌古斯九姓也不自认或自称“突厥”(罗新:“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全球史评论》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81-82页)。 后来讲突厥语的不同部族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更是弱化了他们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我们所说的突厥化,是指突厥人与当地人(在中亚地区主要是印欧语人)融合,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的过程。将“突厥”认同泛用于一般的内亚历史叙述,主要是一种后人的发明,它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更日益具有政治意义,从而将只是专指的Turk一词,作为古往今来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
伊朗文化复兴
译者在前言中已经为书名《撒马尔罕》辩解,说在当时没有今天的民族国家疆界,而撒马尔罕当时属于伊朗文化圈。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仍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传说中卡亚姆创作其《鲁拜集》的那个空白小册子,就是撒马尔罕的教法官(qadi)郑重且秘密地赠送给他的,所以这部手稿在文中一直被称为“撒马尔罕手稿”。
另外,历史地看,尽管今天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但从历史的角度说,自阿拉伯人于七世纪中征服伊朗后,还有一个波斯文化复兴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波斯人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创立于中亚地区的萨曼王朝(Samanid,874-999,十世纪时萨曼王朝成为中亚军事强国之一,其领土以今乌兹别克斯坦为核心,囊括哈萨克斯坦南部、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以及伊朗大部分) ,尽管这个王朝在名义上保留了对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效忠,其统治者一直仅自称“埃米尔”,但正是在其统治时期出现了波斯文化的复兴,而萨曼王朝的活动中心就是今天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主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也就是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两年前,笔者在布哈拉考察时,特别留意参观了建于十世纪初、保存尚好的萨曼王朝陵墓。粗略来看,在该陵墓的建筑设计中可以发现琐罗亚斯德教与伊斯兰元素的并存,生动地呈现了文化发展中交融与沉淀的特征。

历史地看,七世纪中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九至十一世纪伊朗本土出现了以萨曼王朝和白益王朝为代表的地方政权,十一世纪中期后则出现了以塞尔柱王朝为代表的突厥人政权,如此来看,伊朗本地政权的起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就是多个伊朗本地穆斯林王朝相继崛起或并存,有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伊朗间奏”(Iranian Intermezzo,这个词是由Vladimir Minorsky创造的, “The Iranian Intermezzo,” in Studies in Caucasian History, London, 1953;后来著名的中东史研专家伯纳德·刘易斯采用了这种说法,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 New York, 1995),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就是带有伊斯兰形式的伊朗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复兴。
所谓伊朗文化复兴的问题,其背景是阿拉伯征服和伊斯兰化,从现代的角度看,这很符合伊朗民族主义的口味,所以,难免会出现诠释过度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公元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勃兴于阿拉伯半岛,随后开启了一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四处征服的历史时期,这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版图,且影响至今。七世纪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224-651)被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阿拉伯部落民所征服,阿拉伯人统治当地历三个世纪,伊朗文化圈开始了漫长的伊斯兰化进程。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伊斯兰征服之初,伊朗文化圈占主要地位的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祆教或拜火教),但阿拉伯人的统治也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长期掌握大权的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 自然地,阿拉伯语成为正式语言,行政、文学-学术作品以及日常文书逐渐多采用阿拉伯文。伊朗当地的宗教和语言受到冲击。在这种异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某种程度上也会出现伊朗本地人的反弹,有捍卫自身认同、保护和复兴伊朗本土文化的需求,这个问题跟近代民族主义有相似性,但仍需注意不能以近代民族主义来比附古代世界的事情,以免造成时代错位。当然,从古至今都普遍存在捍卫自身文化的现象。伊朗人在文化上一向自视很高,并不甘心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被阿拉伯的影响所排斥和削弱,也是自然的。七至十世纪,由于要与伊斯兰教对抗,琐罗亚斯德教的宣传和著述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张鸿年:《〈列王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6-67页)。
八、九世纪之交,巴格达的阿巴斯哈里发政权对伊朗的统治逐渐削弱,伊朗的地方王朝兴起,在这一时期,伊朗新的民族语言——新波斯语(即达里波斯语)开始形成,一些波斯诗人逐渐放弃将阿拉伯语作为文学书面语言,而开始用达里语创作。在地方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达里语迅速推广和传播到伊朗全境,其中主要控制了中亚和伊朗大部分地区的萨曼王朝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赞美波斯文化,倡导复兴波斯语及其文学艺术,规定波斯文是官方通行文字。达里波斯语的文学创作,兴起于东部霍拉桑(呼罗珊)地区。
“达里”意为“宫廷的”, 阿拉伯人入侵后,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至霍拉桑,在霍拉桑的宫廷即使用这种语言,因而称为达里波斯语。达里波斯语实际上是多民族混居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共同语,在字母、语法和词汇上与阿拉伯语有着深厚而广泛的联系。在历史上,达里波斯语曾通行于中亚、西亚和印度北方等广大地区,其文学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学,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波斯文明的集中体现(冀开运:“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 ,以其为载体出现了繁荣灿烂的中世纪文化和文学,从十世纪至十五世纪,波斯诗歌璀璨夺目,菲尔多西、莫拉维、萨迪、哈菲兹都是世界闻名的文学家。今天,现代的达里波斯语是伊朗、塔吉克斯坦的通用语,也是阿富汗的两种通用语之一。

在这个所谓伊朗文化复兴的进程中,最值得提及的应该是菲尔多西(940-1020)及其创作的《列王纪》,《列王纪》在后世被视为波斯民族文化复兴的代表。这部伟大的史诗成书于十世纪与十一世纪之交,正是伊朗社会的转型期,政治斗争比较激烈,民族间、宗教间的矛盾突出。伊朗学者扎毕胡拉·萨法在讨论《列王纪》产生的时代特点时指出:“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从一种信念过渡到另一种信念,从一种宗教过渡到另一种宗教,从一种传统过渡到另一种传统的过程。设想如果没有反映这种过渡的几部著作(《列王纪》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为两个时代的中介和桥梁,可能在世事错综复杂的变化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伊朗民族会完全忘记自己的古老传统。他们会与其他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民族。” (转引自张鸿年:《〈列王纪〉研究》,第67-68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伊朗学者倾向于把《列王纪》视为本民族传统的拯救、保存和传播媒介。《列王纪》是世界上由一个人创作的最长的史诗,涵盖了阿拉伯-伊斯兰征服前的伊朗全史,作品中还充斥着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张鸿年先生指出,在《列王纪》中表示“神”的用语,创世主用的是“胡达万德”(Hodavand),这是一个波斯语词,与伊朗指神的“胡大”(Hoda)同义,这个词不同于琐罗亚斯德教指“天神”的词“耶兹丹”(يزدان),也不同于伊斯兰教指真主的词“安拉”(Allah),《列王纪》第一节之外,凡指神的地方,除少数用“胡达万德”之外,一律用的是“耶兹丹”,在总共十二万行诗歌中,没有用一个“安拉”。张先生认为,在当时伊斯兰教已经传入数百年,阿拉伯语已经成为宗教和科学用语的情况下,菲尔多西不用“安拉”这一带有明显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色彩的词,显然是有意为之 (转引自张鸿年:《〈列王纪〉研究》,第68页)。
菲尔多西确实有意不用或少用阿拉伯语词汇,对早期新波斯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到二十世纪伊朗民族主义勃兴的时期,菲尔多西及其《列王纪》受到空前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1934年伊朗政府邀请世界著名学者举行菲尔多西诞生千年学术讨论会,并为菲尔多西新建了墓地,伊斯兰国王亲自为其揭幕 (转引自张鸿年:《〈列王纪〉研究》,第35页)。
与菲尔多西使用早期达里语相比,卡亚姆创作其鲁拜时使用的已经是有所发展的古典达里波斯语,在伊朗,卡亚姆的地位也远不如“民族诗人”菲尔多西那么高。卡亚姆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经西方人“发现”而暴得大名,这才反过来影响了伊朗国内,自然也免不了被“民族化”的倾向。这从受到伊朗民族主义文学观念影响较大的著名翻译家张鸿年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张先生在讨论卡亚姆的《鲁拜集》时,延续了其关于菲尔多西之《列王纪》的观点,说卡亚姆的作品“充满了伊壁鸠鲁主义哲学与拜火教哲学的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家郭沫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都曾根据英国诗人菲茨吉拉德的英译本,译过一首卡亚姆的四行诗,这首诗张鸿年先生从波斯语直接译过来是:
如若能像天神一样主宰苍天,
我就把这苍天一举掀翻。
再铸乾坤,重造天宇,
让不愿作奴隶的人称心如愿。
张先生指出,英译本忽略了波斯文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第一行中的“天神”,另一个是第四行中的“不愿作奴隶的人”。他强调,“天神”(ايزد,感谢张湛兄指教,ايزد与يزدان都是“天神”的意思,后者是前者的复数,词根来自巴列维语意指“崇拜”的动词يزد) 是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词,并不是现今常见概念里的“安拉”或“胡达”,据此,他认为,“这表明海亚姆概念里的宇宙主宰仍然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天神”。
而张先生对“不愿作奴隶的人”这个词的解释是,“向往自由的人”或“道地的纯种人”,引申义为伊朗人。张先生认为:“海亚姆使用这个词的用意非常明显,是表示要让不愿为奴的伊朗人‘称心如愿’。言外之意即公元7世纪外族入侵伊朗后,伊朗人过的是奴隶般的日子。明白了诗人用词的这些细微之处,就可以了解这首诗除了表示对人世的一般的不满之外,更体现了对入侵的外来统治者的憎恶这一深意。而这正是伊朗人的普遍心态。直到今天,伊朗人的这种心态仍然存在。” (转引自张鸿年、宋丕方译《鲁拜集》“译者序言”)
对张鸿年先生的这种倾向于“民族主义”的解释,我总感觉是受到伊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所致,当然,我对此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暂且作为一种疑虑放在这里。 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解读本身就存在各种可能性,有些东西对诗人而言可能只是某种自然情感的流露,或者受到当时的历史、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而做的正常选择,不见得就一定带有后人所赋予它的那种政治性或民族性。
比如就语言的选择来说,选择使用本地语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具有伊朗当地特色的文学形式,应该是某种自然选择,在当时的伊朗和中亚地区,大众层面普遍使用的语言就是人们一直讲的伊朗语族(伊朗语族包括约二十种语言,分布于伊朗、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中亚部分地区,主要语言有波斯语、普什图语等。伊朗语族诸语言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代伊朗语,包括两部分,一是阿维斯陀语,一是用楔形文字的古波斯语;二、公元三至十世纪的中世伊朗语,包括帕提亚语、巴列维语、大夏语、花剌子模语、粟特语、和阗塞种语;三、现代波斯语,直接来自巴列维语,吸收了一些阿拉伯语和突厥语借词——阿富汗斯坦的普什图语是现代伊朗语的东支)的不同方言。在公元一千年前后的中亚地区,“宗教继续是基于阿拉伯语的神圣经典,撒马尔罕、布哈拉与其他城镇的人们以及乡下的农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仍然是伊朗的(Iranian),尽管越来越从粟特语(Sogdian)和花拉子模语(Khwarazmian)向波斯语(Persian)转变。”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3)
就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而言,口头和书面的创作都是重要的,《列王纪》和《鲁拜集》都有口传传统,并非都是文人的创作,另外也还得考虑统治者的出身、偏好和教育背景,也就是他们是否听得懂、看得懂以及是否愿意看的问题。相对于当地人来说,作为外来统治者的阿拉伯人人口本身就很少,同化能力没那么强;在没有普及大众教育的时代,就算阿拉伯人统治的时间够长,作为外语的阿拉伯语主要还是局限于上层政治精英与受教育的文化-学术精英之间,另外,还要考虑到后来伊朗本地王朝的赞助,以及伊朗当地的语言作为一种深厚文化传统之载体的源远流长与发达程度,波斯语的长期使用自然会给当地人造成一种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并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它不一定非要跟某种民族情感挂钩,后来的突厥人和印度人也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用波斯语从事创作。强调伊朗本地的主体性不等于否认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只是波斯语言和文学的发展深受阿拉伯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学术的进步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阿拉伯语长期作为官方和学术通用语的作用,学术的交流就不会那么顺畅,各种创新成就的取得也会更加困难。诚如当代学者所言:“阿拉伯语为信仰崇拜以及求知提供的共同语言,跨越了空间与政治分歧。” (【美】简·伯班克、弗里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第73页)不必说,包括卡亚姆在内当时的很多科学家,他们的学术著作就是用阿拉伯语写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