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伪善的家庭长大,他们用“正确”扼杀了10岁的我 | 三明治
原创 嘻天真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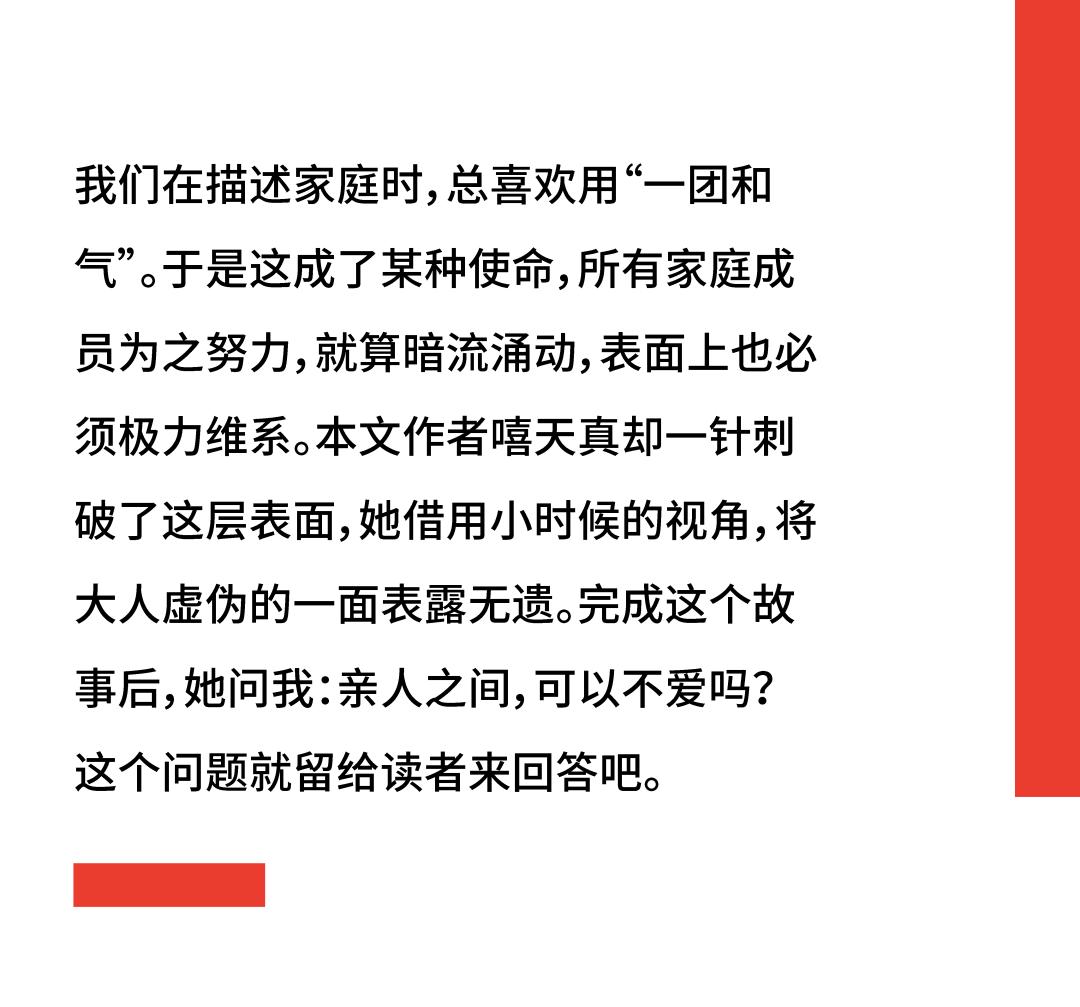
作者 | 嘻天真
编辑 | 童言
几年前的春节,妈妈和奶奶吵了一架。她们不是总吵架,相反,她们几乎没吵过架,大部分时间里,她们是母慈子孝的模样,比如这次,我们带着奶奶一起回外婆家过年,那个小城也是我们曾经生活了多年的地方,奶奶非常高兴,到处走访曾经的朋友,可在返程的路上,密封的狭小的轿车空间里,坐在后排一左一右的两个人突然吵了起来。
我戴上耳机,把音乐声音开到很大,爸爸皱着眉头开车,找不到话。高速路上车不多,这场内部斗争激烈又孤独。我很想逃,又很想说些什么,长久以来我都处于这个状态,行动上越逃越远,心理上又不接受自己的逃跑姿态。多多少少,这两个女人对我是有付出的,让我逃走也是付出,是了不起的付出。我对自己的逃跑感到愧疚。
“不要吵了!”我大喊了一声,以家庭特有的暴力式沟通。她们的争吵暂停了两秒,又立马变回之前的样子,我的声音消失得太快,快得像没发生过。
我并不感到生气,反正再过几天,我们都会以各自的方式消失。我会回到另一座城市工作,奶奶会回到另一区的养老院住,妈妈和爸爸会又把家里划成两块,除了吃饭以外,他们很享受彼此的消失。
是的,等过几天,再激烈的争吵,都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以前的我总是吵。
九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妈妈的学生,是个比我小的男孩,被安排住我的隔壁床。我和他没法玩在一起,经常吵架打架,但妈妈对他非常好,他写作业写睡着时妈妈笑得眼泪花都出来了,要是换做是我,就会变成一场严厉的苛责。在那时,妈妈对我和他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对我严苛,对他宽松,他总能轻易得到妈妈的夸赞和笑脸,我则相反,天天都是费力不讨好。
爸爸常年在外,妈妈的爱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没法看着它落到别的小孩身上。哭闹是我索爱的方式,但得到的回答总是,“你是亲生的,妈妈肯是爱你的呀”,像教科书一样不可反驳,可我心中却是另一个答案。
一年后爷爷去世,我们去爸爸的老家奔丧。在商量奶奶的去处时我参与了小孩们的争夺战,说要奶奶跟我们住,妈妈是不愿意的,我不理解,奶奶来家里不是很好吗?多一个亲人在身边,就能多一份爱。我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奶奶来家里后,我不光能得到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的奶奶的宠爱,而且,我再也不用为妈妈那点零星的可怜的爱感到伤心。
最终奶奶跟我们坐上了回家的车。尽管之前只见过她一面,但我相信她就是结束我的母爱争夺战的英雄。在近一天的车程里,我挨着她坐,拉着她,生怕她反悔。那竟然成了最后一次我想靠近她,后来的二十年里,我都忍不住想离她远远的。我也想离这个坐在前排的妈妈远远的,那天,她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奶奶来家后不久,爸爸离开了家去工作,剩下我、妈妈、奶奶、那个男孩。奶奶接受了买菜做饭的工作,住进了我和那个男孩的卧室,并充当起这间卧室的主管,她不许我们躺在床上时讲话,也不喜欢我那些墙上的贴纸,信基督教的她认为那是魔鬼,把我心爱的美少女贴纸一张张撕掉了。除此之外,我总感觉自己被奶奶盯着,一言一行都可能被纠正,连入厕时间也在监管之列。
一切似乎并没有往我想象的方向发展,可我没法跟人说,奶奶是我要来的,她看我,是爱我,是为了我好。至今,我们家仍是爸爸那边的家人眼里的完美模样,妈妈是好儿媳、好老师,奶奶是好婆婆、好长辈,而我,以前成绩好,现在工作好,在至亲的爱的怀抱中长大,“像公主一样”。爸爸那边的家人把他们很爱的老人给了我,而我,怎么可以不快乐?
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堵着,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它怎么和老师教的不一样,怎么和家人们说的不一样,我告诉自己,我肯定是被爱着的,至于感受不到,就像他们说的,是我的问题。

“我们是家人不是敌人。”这是妈妈教育我的口头禅,她总觉得我把他们当敌人,什么都不说,什么要防着他们,她的声音从说变成吼,眼泪又要飙出来了。她说的是事实,以前我闭口不谈学校和工作里的事,现在,我连住家地址也拒绝告知,不回家,不单独联系,只在家族微信群里说话,有其他人看着,我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很多年前我就成了“敌人”。妈妈对奶奶客客气气,微笑着,在饭桌上努力找话,可她越来越多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说一句话。我也好想把自己关起来,那个可以从房间内上锁的小阳台,曾经是我的特别领地,现在却成了奶奶的地盘,她拿着《圣经》在那里读,有时候敞着门,有时候也会上锁。
我没处可躲,我忍不住恨她。有时候用眼神,有时候用言语,有时候用哭闹,就像对那个男孩一样,我觉得她的出现也破坏了我和妈妈的关系,妈妈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我忍不住想要这两个人都快快离开,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妈妈。把我的家还给我,把我的爱还给我。我想要一切都回到以前的样子,可以自由自在的样子。
离开的不是他们,是我。后来的我一直在离开。初中时离家住校,接着转学,离开那座小城,高中时要求住校,尽管当时的家就在学校旁边。大学选择了离家很远的城市,再之后,辗转于几座城市,没再回去。妈妈每次叫我回家,都让我想离开得更远、更远,不想和任何亲人扯上关系。爸爸开玩笑说养了个白眼狼,但被我听得认真,我感到愧疚,一想起家,我就觉得自己不该存在,如果我不存在,他们会过得很好吧?
小时候也想过自己不要存在。有段时间,会在阳台上往楼下看,五楼之下的水泥地上有一堵围墙,如果我落下,是在墙内还是墙外,又会不会落在哪家的雨棚上捡回命,像电视里一样。有天我抬起了一只腿,那是在一次争吵之后,眼里的眼泪流不出了,我踮了踮另一只脚。背后的客厅传来了奶奶的声音:"你摔死了还好,你要是没摔死,以后就恼火了。"
她的语气像是在看电视剧,我却觉得这怎么和电视里演的不一样。她说得很对,后来我没再尝试那个姿势,但我无法感谢她。我也无法感谢我的妈妈,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避开了这个小孩的“把戏”。在那天,过了个把钟头吧,家里又有了读书声,是妈妈在辅导那个男孩写作业,男孩的读书声难得的清脆,我好像也开始相信什么也没有发生。

总是在做关于逃跑的梦。在梦里,我在不同楼栋的楼梯间和房间窜逃,急中生智和拼尽全力,被什么东西追着,来不及感到恐惧。梦的结局都是失败,在那最后时刻,我惊醒过来。
逃跑是我的人生主线。能逃,是我选择一切的首要条件。不要事业单位,不要婚姻、生子,拒绝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不停地换工作,搬家,每搬到新的住处,会忍不住计划逃跑路线,要是有歹徒进来,我躲在哪,要从哪里逃。在朋友们眼中,我自由、潇洒,在家人眼里,我不懂事,是“白眼狼”,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逃,我很累。
小时候也不总是那么绝望,我最喜欢和妈妈单独相处的福利时光。有时晚上妈妈会在洗衣台那搓洗内裤,奶奶和那个男孩都睡觉了,我找借口讨论功课,想在妈妈旁边多留一会儿。这时妈妈会压低声音,一边搓着手上的内裤,一边跟我讲些只有我才可以听的悄悄话。那都是些对奶奶的看法,有时说奶奶挪用了买菜的公款,有时说奶奶生活习惯不好,有时说奶奶的教会朋友层次低。她皱着眉头喋喋不休,和白天的天使模样截然相反。可我更喜欢这个怨声载道的她,我觉得这个她更真实,而且,是我独享的。
我对奶奶的攻击越来越明目张胆,那些晚上的悄悄话像是古装剧里皇上的密赐令牌,我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到了不得不做的正义。我常常瞪着她,眼神里塞满了恨意,她要是敢纠正我的什么行为,我就大喊大叫,反抗到底。奶奶被我气得不得了,她抓住我的手使劲摇,问我为什么这么恨她,可我什么也不说,打死也不说,我有我要保护的正义。
正义没有胜利,我成了家里的坏小孩。塞满恨意的眼神有天落在了我身上,来自我的妈妈,我最心爱的妈妈,她的眼睛是刀子做的吗?我好像被杀死了一样。她说,“对奶奶要尊敬”。这句话后来像是传遍了整个家庭,每一个家人都来对我说一遍,语重心长的、轻描淡写的、温柔的、严厉的,他们朗读着他们的课本,和听的人界限分明。
战争还在继续,尽管我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有次期末,学校发了家庭调查表,里面有“尊敬老人”一栏需要打分。作为教师子女的我当然知道,这项评分直接关乎到我是否能得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这是以前我都能得到的,要是这次没被评上的话……不行,我必须得到那张奖状,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坏小孩,我还想当那个人人羡慕的公主。我恳求妈妈、奶奶给我一个“优”,向所有大人保证会对奶奶尊敬、对她好,还有爸爸,天哪他们告诉了爸爸,他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唯一我能想象的爱我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爸爸的爱。我哭着恳求着大人们,忍着心里深深的羞耻。
妈妈笑了一下,换了支铅笔,写下了一个什么。

后来我没再对奶奶有任何攻击,对她客气、尊敬,叫一声奶奶,上一丝微笑,已至我的极限。对我来说,奶奶成了家里的另一个小孩,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孩,享受着全世界的保护和照顾,后来的十几年里,她也都牵动着爸爸妈妈的注意力,不必取得好成绩,不必藏起自己的情绪,不必看谁的脸色,她轻易就能得到无条件的温柔和爱,那是我不松懈努力才能得到一点儿的东西。
我不爱她,是的,我良心不安。她对我有付出,给未成年的我做过饭,过年时给过我压岁钱,后来也接受了我在家里的冷漠模样。我对她的付出感到愧疚,至今害怕见到她,害怕走进她的房间,害怕看见和她有关的一切,她的《圣经》,她的相册,她的水杯,她洗澡用的香皂,她入厕需要的辅助椅。我们之间隔着的沉重的空气,是我不爱她的铁证。
妈妈仍在对我说着悄悄话,她仍是所有人面前的天使,唯独对我恶语相加。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份悄悄话有不同的样子,只是主角早已变成了我,那些恶毒的话被她灌进我的耳朵,说是为我好,就好像我还是那个很坏的小孩,需要她的狠狠教育。我很伤心,又舍不得拒绝,说悄悄话的妈妈有着珍贵的真实,不那么追求正确了。
妈妈到快退休时才不那么追求正确。几年前,有天爸爸跟我打电话,说奶奶搬去养老院去住了。那时奶奶快九十岁了,身体还算健康,除了日常服用药物外,不需要人特别照顾。爸爸叹了声气,说是妈妈要奶奶搬走的,奶奶倒是乐意。他在期待我说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妈妈也什么也没有说,我们静悄悄的,就像无事发生。
其实妈妈和奶奶后来关系不错。小时候的我成了坏小孩后,妈妈和奶奶联手了,她们熟练的扮演起某种角色,你唱我和着,齐了心让我改邪归正。见到要问候、要微笑,拍合照时要站在一起,最好要挽着手,尤其注意面对外人时,要露出幸福的样子,不知道怎么答,就跟妈妈一样微笑着点头。否则,就会“告诉爸爸”。
我机械地操作着新的规章,就是越来越不想在家里呆。这样一阵子后,有天中午吃饭,那个男孩在餐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筷子。家里响起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声,是两个女人的笑声,她们哈哈哈地笑,笑了好久好久,笑得前仰后合,笑得鼻涕眼泪都出来了。我低头吃饭,一直在犹豫自己是否应该跟着笑起来。应该?还是不应该?应该?还是不应该?
应该。我应该去奶奶的养老院看望她,我应该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我应该体恤那几年爸爸妈妈的不容易,我应该是一个好女儿,和父母、家人无话不谈,我应该对得起家人的付出。而那一刻,我应该为家庭的欢声笑语作出贡献。
我感到愧疚。人之初,性本恶。我应该下地狱。
那天的饭桌上,眼泪和米饭一起被我咽进身体里,我成了一颗大大张开翅膀的蒲公英,要是有一丝风,我就愿意拼尽全力飞走。离开、远离,远离我的罪恶,远离我的地狱。我不在乎要飞去哪里,这是一次没有目的地的逃离。
我成了自己的禁地。

车里的争吵还在继续。我打开地图,看着坐标一点一点移向目的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是三房两厅,彼此讨厌的人必须同行,进入同一部电梯,进入同一个门,拐进各自的房间,用各自的方式消除记忆。只有倒霉蛋才继续生气。
一会儿以后,我们又要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了。饭桌旁的墙上有一张写着繁体的“爱”字的海报,大大的红色的爱字占了五分之四,剩下的五分之一是已过期的日历。这张海报是奶奶从基督教会拿回来的,它被贴在墙上,被妈妈允许存在。一年又一年里,“爱”字看着这个家,也看着我们四口人。
被告知妈妈要奶奶去住养老院时,我好像看到了小时候关于“该不该笑”的问题的答案。答案当然是应该,可妈妈选了不该,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选择,作为人民教师的她,明知故犯。她成了爸爸口中不可理喻的女人,我该支持她吗?应该,还是不应该?
小时候的那张我没拿到的奖状,后来,被妈妈拿了十几年。奶奶夸她是好媳妇,爸爸的家人也夸她,妈妈的家人也夸她,认识我们一家的人都夸她,夸她孝顺、好心、明理,在那些很像表彰大会的家人饭局上,他们使出了他们最大的声音朗读。妈妈微笑着回应,爸爸也陪着笑脸,我又不知道该不该笑了,我真是个倒霉蛋。
奶奶越老越爱笑了,不知道是不是她反复读《圣经》的原因,《圣经》教人要爱啊,她常常笑着,像一个真正慈祥的老太。我从爸爸嘴里收集着她的健康动态,还是什么也不说,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小时候到现在,我们搬了很多个房子了,奶奶在很多个家里读着《圣经》。有个场景总是发生,一般在吃完饭的午后,在爸爸妈妈午睡时,在我独自在客厅享受难得的自在的时候,她小声读唱着《圣经》,发出一声巨大的叹息:“我怎么还死不到哦!”
我没法忽略这个音量,又想往外逃了。我穿上鞋,打开门,大步走向电梯,下楼出门,直到看到小区里的光景依旧一如既往。
今天无事发生。幸好。

这是一个迟到20年的故事,是我人生最大的秘密,直到20年后的现在,我还是不太敢把它讲出来。在此特别感谢童言老师和我发小的支撑,天哪,我能讲出来真的太不容易了。其实我们全家都是好人,也许是真的太好,他们用“正确”狠狠杀死了那个10岁的的,在我心里种下了羞耻,让我从此不会攻击,没有了“皮肤”,我以为自己必须为任何关系、任何人负责。
20年来,因为无法回应长辈的索取、无法使家庭关系亲密,我一直感到羞愧,也为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羞愧。此刻,我本来想把矛头指向“正确”,指向父辈的成长环境的生存必须,但我不想那么正确的。
原标题:《在伪善的家庭长大,他们用“正确”扼杀了10岁的我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