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十而惑,我愿经常与93岁的姥姥聊聊天 | 三明治
原创 Yanzi韬韬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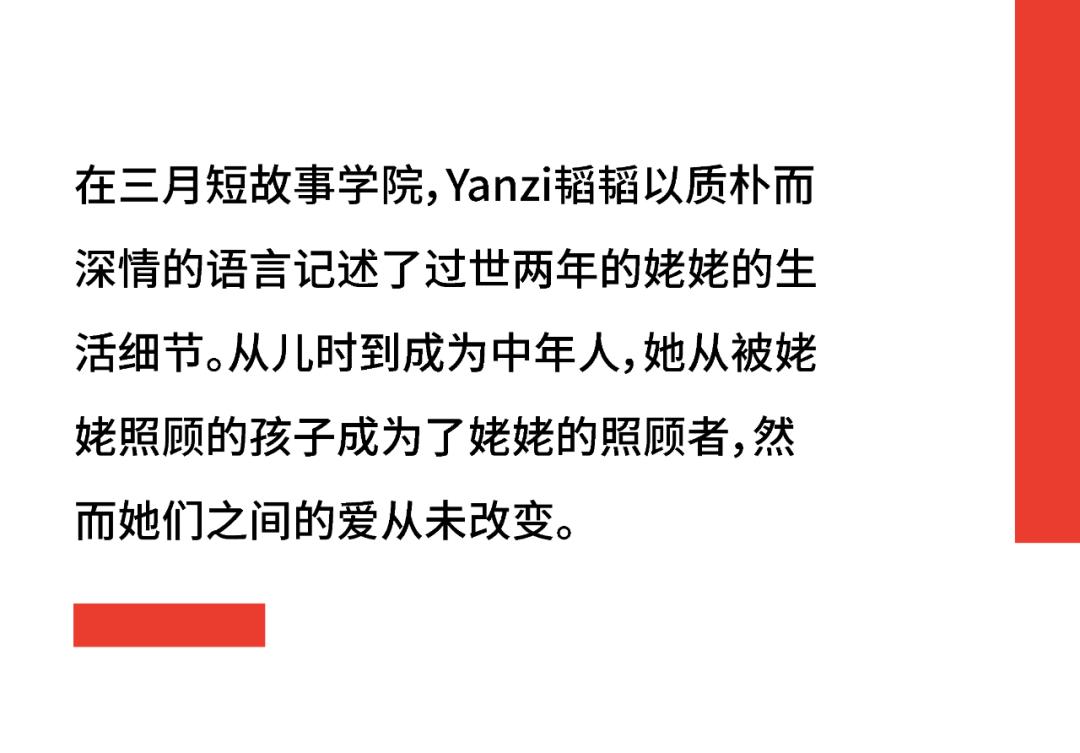
作者|Yanzi韬韬
编辑|恕行
夜晚,关上灯,孩子睡了,我闭着眼睛,在脑海中默默想念去世的姥姥。
曾经的生活单纯快乐。家里是四世同堂,上有90多岁的姥姥,让我总感觉自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四十岁这年,姥姥离开了我,我似乎才第一次感觉到,生命里真的有很多苦呢。孔子所谓“四十不惑”,怎么我却是“四十而惑”呢?

姥姥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我知道她可能要离开我们了。周末我回去看她,要过海底隧道开车一个半小时。
她躺在炕上,头朝外,脚朝内。孩子们在屋外门口嬉笑打闹,我坐在炕沿上,静静地陪着姥姥坐着,手拉着她的手,帮她按揉手指头。
姥姥手背上的皮肤看上去有点发亮,有一丝丝的干皮均匀地分布在手背上,让我想起来家里老二出生后一段时间,身上总是有一层层均匀密布的干皮,就像是鱼鳞一样,那是未曾褪去的新生的痕迹,而姥姥手上,竟然也出现了这样密布的干皮。右手靠近手腕的地方一团黑紫色,那是之前感冒打吊瓶留下的痕迹,好久都没有消除。
我在松松垮垮的手背轻轻捏起一层皮,这层皮形成了一个竖墙,站立在手背上,久久不肯平铺下去,我赶紧把它捋平。翻过手来,手心的皮肤格外的白皙透明,毛细血管清晰可见,手一按,就有一个小窝出现,跟手背上的皮墙不肯落下去相反,这个小肉窝倔强地不肯鼓起来!我轻轻揉着,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地捋过去,从指根往上推,推到指尖。我不敢太用力,怕姥姥疼,推到中指更不能用力,因为她中指第一个骨节处突然有一个差不多四十度的弯,总是这样弯着。以前姥姥总是自己开玩笑说,看这个破手,还弯弯着,不知道什么毛病。我知道那是常年干活不自觉形成的习惯,骨头已经长弯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炕在里屋,照不到阳光,一扇大玻璃窗在中间,窗台上有个花瓶。姥姥喜欢花,我每次回来都会给她带一束花。她最喜欢我家门口的那棵月季花,花能开到比张开的手掌还大。花是黄色、橘色渐变,到花瓣边缘上,一圈橘红色煞是好看。每每在花开得最好的时候,我都拿剪刀剪下来,给姥姥拿到炕前,插在花瓶里。
这次回来还不到月季花季,我从花店买了玫瑰,给姥姥放在鼻子前闻,她说香。我安静地揉着手,姥姥闭着眼睛。大部分时间她都闭着眼睛,眼角有黄色的分泌物,我刚拿温水毛巾给她擦干净。
我说:“姥姥,你别害怕呀!”
她还是闭着眼睛,嘴角微微一动:“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我不再说话,好像有很多话,但是又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的我,真是幼稚可笑呀。时光飞逝,现在的我为在她病榻前说的那些安慰的话感到惭愧,我为没有再多陪她一分钟而感到内疚。那时候的我是那么的自不量力,自以为是。
四十岁的我,在九十三岁的姥姥面前,安慰她不要怕呀,不要怕什么呢?难道我当时是安慰她不要害怕死亡吗?该害怕的不是走的人,而是留下来的人啊!
姥姥说她不怕,是真的已经不害怕了吗?我已经不能再去跟她寻求答案,反而是她老人家,留给我这样一个大大的疑问: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该如何去活?

有时候姥姥盘腿坐在炕上,手边会有一些孩子们拿回来的商场的广告纸、或者半岛都市报什么的。她经常煞有其事地翻看,翻着翻着,就开始折纸,手捋过去,把纸左一下右一下,简单地折起来,好像就是为了拿手捋那个边边。她就那样安静坐着不说话,捋过来捋过去,好像那就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她兴致高了,会折一下再拿出剪刀来剪一下,再展开就是一串可爱的手拉手的小人,或者光头的男孩,或者扎俩小辫的女孩,一大串,剪完随手扔在炕上,我看见了就过去拿着玩。
姥姥说:“这个字是兰,这个字是刘。”
我凑过去一看,果然是。我在报纸上再找几个简单的字,说:“姥,你看,这个不是大嘛,这个小,不认识?”
她笑着说:“不认识!”
我转过头跟孩子说:“姥姥的名字叫刘瑞兰,知道了?”
姥姥认识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基本上都不认识。
姥姥生于1929年10月。姥爷与姥姥同年,比姥姥小两个月,姥爷走的时候我还在初中。在失去伴侣之后,姥姥一个人生活了26年。
大舅和小舅两家紧邻着,姥姥后来几年都是一家一个月的住。在小舅家的时候,炕是在外间,窗外就是院子,经常有阳光照在炕上。
在家上学那些年,我一般晚上吃完饭都会从自己家溜达到姥姥家,坐在她炕上跟她聊天。炕上经常有很多村里的邻居,坐在一起喝茶、拉呱、吃点瓜子花生什么的,往往我都是最后一个走的。我出了门,回头看玻璃窗户里,灯光格外亮,姥姥开始收拾褥子,脱衣服、准备关灯睡觉,一个人的身影单薄也安稳。
有时候我去得晚,天黑了,外面黑黑的。姥姥大部分时间都不开灯,只开着那个32寸的老式电视机。她盘腿坐着,胳膊压在膝盖上,电视机的光影映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的。电视里经常放着的是西游记或是咿咿呀呀唱戏的。
上炕我是完全不会盘腿的,一般会伸直着腿歪着身子倚着靠着的。有时候姥姥看我坐久了,就会把她的枕头扔给我,说:“要不你坐这个吧。”
我哪能坐她的枕头,还是躺着歪着的,不太那么雅观。姥姥盘腿盘得可好了,两腿完全平行搭在一起,盘腿后上面的脚完全搭在大腿根处。夏天的时候她穿着肉色的袜子,是妈妈买的厚实的尼龙袜子,但是因为脚太小了,袜子又大又松,袜口提到脚踝很高处。
姥姥的脚很特别。有一次我拿出手机想给她的脚拍照,她不让我拍,说:“你拍这干啥,你看难看的样儿!”
她的脚一直在我脑海里,模样清晰。大拇指伸在前面,其他的脚指头都弯曲着折叠到脚底下,小拇指直接在脚心下面的位置,整个脚成一个小巧的三角形,大约就我的手掌大小,足弓高高拱起,有几双鞋子都是特制的尖形小鞋子,其他的鞋子都是买最小的尺码。
因为常年的摩擦,弯折后的脚指头关节处都有一层厚厚的茧,每个脚趾头的指甲都特别坚硬,长长了的时候像鹰爪一样。趾甲太硬太厚,用普通的剪刀根本剪不动,更别说指甲刀了,指甲刀缝都塞不进去。后来妈妈终于想到了好办法,找人借了一把修剪树枝的大剪刀,终于能好好地剪剪姥姥的脚指甲了,但是又不敢太用力,怕剪到肉。
因为脚是“三寸金莲”,所以我总感觉姥姥走路小心翼翼、颤颤巍巍的,用脚后跟在一步一挪地往前。前几年我俩经常在家门口的胡同里溜达,从姥姥家溜达到我家吃饭,吃饭饭再溜达回去。因为姥姥的小脚,我们走得很慢。姥姥的胳膊从我的胳膊内侧伸进来,我弯着手臂,手心向上,她的手正好放在我的手心里。我托着她的手,一步一步的,碰到邻居就聊两句,看到花开就停下来摸摸,或者望着路上人家新修的房子说说。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有一次姥姥终于跟我说了她缠脚的故事:“我12岁开始裹脚,那时候觉得脚小好看啊,看人家裹脚馋得要命,所以到了可以裹脚的时候赶紧裹起来。”
我问姥姥:“那小姥姥怎么是大脚啊?”
小姥姥是姥姥的妹妹,比姥姥小三岁。“你小姥姥鬼儿啊,白天大人看着的时候缠起来,晚上没人的时候就偷偷解开,我呐,白天晚上的都缠着,就想要一个那样好看的小脚,缠了没几年,解放了,好了,人家不用缠了,解开了,脚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这不行了,解开也已经定型了。”
“那你裹着脚的时候不疼吗?”
“不疼啊,谁记得这些,可能不疼吧。”
“你是不是光顾着好看去了根本不记得疼了呀。”我取笑姥姥,姥姥也笑了,她这是伤疤没好,疼也早忘了呀!
“再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吧!”我缠着姥姥问。

那几年,我每次回家都想着能多跟姥姥聊一聊,想多知道一些她以前的事,她跟我说的,我都赶紧拿笔记下来。我担心她年纪大了,担心时间久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忘记了她。
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感觉,矛盾地挣扎着。我一直在跟姥姥默默告别,做跟姥姥告别的心理建设,尤其是有几次在她生病之后。
有一次姥姥可能感冒了,妹妹给我发信息说姥姥好像不大好。我拼车赶回家,姥姥还是在炕上躺着,头朝外,呼吸有点喘。我低头喊她:“姥,姥……”
她睁开眼,歪过头来,嘴唇咕噜含糊地叫着我的乳名:“艳……艳……”
弟弟说,姥姥已经两天不认识人了,叫她也不答应,俺大姐姐回来就认识俺大姐姐了。
姥姥手上打着吊瓶,我们陪着她坐在周围,晚上妈妈炕上陪着。我到十点多回家去,早上六点多再过去。姥姥逐渐消喘,我把她扶起来坐一会,姥姥逐渐又跟我说话了:“你这生完孩子要注意好好歇着,别累出毛病来。”
“那你呢,姥姥,你生这四个孩子那时候什么样子?”
“俺们那时候生孩子,哪像现在这样,生完你小舅,坐月子里就去推磨,我想喝个粘粥,嫩姥爷是什么都不会做,那也是什么都没有啊,就自己煮了一锅地瓜蔓汤喝了。”
姥姥堂屋中间有一口井,这些年总是盖着盖,我小时候也看过里面确实有水呢。
“那口井啊,嫩姥爷挖那口井可是费了劲了,挖了以后拿石头垒边,藏满了地瓜白菜啥的,怕打仗还能有地方藏身啊!”
“年轻的时候还看过枪毙人呢,枪毙的都是地主,一下枪毙七八个,在村口那个地方。”
姥姥坐不了太久,我给姥姥煮了一碗面条,但是她吃不下,全都剩在碗里了。
我给姥姥揉腿,我说:“姥,你这腿脚动不了这是老年病,人老了要是没点毛病那成老妖怪了!你没有大毛病,就是有点感冒,你别害怕啊!”
看看我之前不止一次跟姥姥说要她不要害怕,是因为我心里害怕吗?
“我不怕,怕什么,我都90多了!”
“活到100岁还不行?”
姥姥因为发烧脸一直有点红,眼睛有点肿,眼神有点漂移,但是耳朵好使,思路清晰。那么,是身体先背叛了灵魂?她自己说,就是腿脚不好使,发麻,不会动,其他没有什么。我手放在她的手腕处,偷偷地数她的脉搏,一分钟91下。我仔细该观察她的呼吸,顺畅有力,没有任何痛苦的样子,那么,是她的身体也在支撑着精神?我不知道。
我扶着姥姥躺下,跟她开玩笑说,我觉得她能活到100岁。
街坊邻居的知道姥姥病了,一阵一阵的有人来看她,姥姥眯着眼睛都能认出人家来,脑子真的是一点都不糊涂。

春夏秋冬,只要是天气好的时候,没事的早晨和傍晚,姥姥门口永远是热闹的一片。
前屋胡同里的嗓子如公鸭的邢姥姥,隔着一个街东边胡同里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的李姥姥,后屋路口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收养了姐姐孩子的二姥姥,隔着一条大马路村后头的开始是拄着拐杖后来推着三轮小车跨走路的外号叫“罐鼻子”的姥姥,得了健忘症每次看见我都问我一百遍你是谁家大闺女的舅姥姥……这些姥姥,几乎每个晴天甚至小雨天,没事的早晨或是下午,都集中在姥姥门前。这时候舅舅家的各种马扎子、破板凳、矮腿椅子、甚至破纸壳子,立刻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板凳不够用了,就拿个纸壳折一下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有时候一个人刚抬起屁股回家去了,另一个人又来了接着坐下。
早些年的时候,姥姥一般坐在一个比膝盖高点的带椅背的马扎上,再后来坐得矮了不舒服,妈妈给姥姥弄了一个大大的椅子,大家围坐成一片,聊天,拉呱。十点多妈妈从菜园里回来,大家就开始一起帮忙择韭菜、摘果子(花生)、择苔菜、削土豆……各种忙乎,旁边就是孩子们的乐园了。大舅特意趁村子里修马路的时候推了一三轮车的沙子回来,堆在门口,孩子们挖沙子的挖沙子,用一个大盆子接一盆水,放一堆玩具在里面玩,或者骑着自行车、滑板车来回疯跑......有时候同村的人路过门口,有人打声招呼过去了,有人没事就停下来,我赶紧让出板凳,来人坐着继续聊一会,一会站起来走了……一直到中午吃饭的点,大人小孩各自散去,妈妈骑自行车回家去先给我做饭,我等到最后人都走光了扶姥姥进屋去吃饭,我回家,下午睡醒午觉,大家再聚,次日再聚……
大舅小舅门口的每日聚会就像电视里的快镜头一样在我脑海闪过,刷刷刷,人来来往,唯一不变的是贴着红色春联的半掩着的木门,门口小菜园里面沙堆压倒几棵小葱和辣椒,门口斑驳的水泥路面,前屋自家二层楼后垒起的可以直接坐人的台阶。这些物件不动,人来人往,如动画人物一样登登登走来又走远,那几个姥姥是一个一个地减少。
屋后自己独居的二姥姥,因为哥哥跟养女争房产被气病了好久之后走了;健忘的舅姥姥摔了一跤再也没出门,也去世了;满头白发的李姥姥住院了,虽然后来出院但是儿媳妇再也不允许她出来遛弯了;推着小车来找姥姥玩的“罐鼻子”姥姥,因为大闺女与儿子因养老闹到法院自己没地方去,住到邻村的小女儿家里去了......镜头逐渐慢下来,我抱着刚出生的老大靠在姥姥旁边,给她看孩子胖嘟嘟的脚丫,我把老二放在姥姥怀里让她抱着我给他俩拍照片......人来人往,姥姥总是坐在门口阳光最亮的地方,就算是最后自己不能走动了,我也拿轮椅把她推到门口,让阳光能够照到她的身上,晒晒太阳。姥姥的发量逐渐稀少,不是银白,是灰白。
阳光太耀眼我就把她轮椅转过去,背对着太阳。阳光照在灰白的头发上,我看得晃眼。风轻轻吹起齐耳的碎发,一层头皮屑落在后肩膀上,我听见姥姥说:“你来,看!”
“什么?”我轻轻拂去姥姥肩膀的头皮屑,转到前面去。姥姥掀起上衣的下摆,我一看,是一只毛茸茸的黄毛的小鸡。这只小鸡是我在城里给孩子买了玩的,买了两只,已经被孩子养死了一只,剩下一只又瘦又小,感觉也快活不成了。我把它拿回舅舅家放在院子里,院子里有一个大鸡笼子,里面养了八九只母鸡。
“姥姥,你怎么把小鸡放在肚子里呀!”
“我怕它冷,冻得直哆嗦,还怕那些大鸡欺负它。”姥姥摸着小鸡说,“晚上我还想搂着它睡呢,别叫猫叼去。”
我看着小鸡,真是只幸福的小鸡啊,被姥姥这样挂念着。后来那只小鸡终于长大了,因为到家的晚,长成了鸡群里最瘦小的那一只,但是却是我眼里最美的一只小鸡。

我是家里的老大姐,弟弟妹妹一大堆,但是从小我就像那只小鸡一样,被姥姥小心呵护全心爱护着。
小学时,上下学经过姥姥家门口,必然是先进姥姥家吃上点的。上初中以后,骑自行车放学,进了村里的那条主干道以后,往左走是回我家,往右走是去姥姥家,我必然会先往右一拐去姥姥家,姥姥也必然是做好了饭等着我。
姥姥用的是大锅,过堂里烧锅台大锅,一进屋满屋子热腾腾的蒸汽,我的眼镜霎时间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但是鼻子却开始贪婪地猛吸一口热气,闻到发面馒头的麦香味。姥姥坐在门口烧火,往灶头里面塞上一堆木头,火舌舔着木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火光照着姥姥的脸,红通通的:“洗洗手到炕上等着吃饭。”我颠颠地坐到炕头上,饱饱地美餐一顿。
后来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每次离家的时候,都会先去姥姥家跟她聊一会,陪她坐一会,等到再不走赶不上车了,我才离开。我往外走,姥姥手背在身后,小脚颤悠悠地跟着我身后,直到走到胡同路口的马路上,靠在路边,歪着头看着我将要走的路。
我说:“姥,你回去吧,我走啦啊!”她嘴上说着“好,你看着车啊!”可是每次无论我走多远,只要我回头,姥姥总是在路口那个胡同看着我,直到我转过弯,再也看不见姥姥。
我每年寒假暑假才回家,后来参加工作了,一个月能回家一次。每次我回家,姥姥都会从她炕头的油纸袋子里,摸摸索索地拿出另一个袋子,打开里面的袋子,有时候拿出来几颗糖,有时候拿出来一个梨,十一假期回去会拿出来八月十五给我留的月饼.......糖果有点化了软了,梨有时候会有一边已经有点烂的圈圈了,八月十五的月饼我一点都不爱吃,夹着姜丝有点辣,冰糖又太硬吃了还长肉......但是姥姥炕头的油纸袋子里,仿佛永远都有为我准备的她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每每我回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进门,总是有留给我的好吃的。
有一次姥姥刚要拿出来,屋外妗子打开大门快要进来了,姥姥迅速把袋子往身后一藏,若无其事地跟我聊起天来。等过了一会,姥姥回头看看妗子进屋去了,这才又转身,拿出她身后的袋子,拿出几个半指长的大枣来:“给,看看这个枣,长这么大!”

然而,姥姥这样好脾气的老人家却是在儿媳妇手下艰难讨生活的。姥姥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二舅当年在招工人的时候去了南方,前几年还经常回来,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就很少回来了。
对远方的孩子,姥姥说的最多的一句是,我不挂挂(挂念)他,他爱好不好。我在她那些牵强的嘴角、躲闪的眼神中看到做母亲的不易。
在姥姥这样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小脚老太太来说,母亲对远方孩子的挂念,在岁月的长河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又厚重如山,我能做的,就是经常给她和二舅连个视频聊聊天。聊天也就重复的那几句,“我挺好的,不用挂挂我”……远方的孩子就像长长的线扯着的风筝,恨不能拉一拉、再拉一拉,把他拉得近一些,再近一些。身边的孩子呢,有时候却像过年了还欠着地主家二吊钱的长工一样,就差一脚给踢出门外了。
大舅和小舅住的房子都是姥爷留下的宅基地,分给两人,前几年互相帮衬着盖起了二层楼房,为了养姥姥,每家都在一楼留了一间房间算作是姥姥的房间,每家一个月轮流住。关于每家一月轮流这事,还是我从姥姥最忠诚的“小伙伴”“罐鼻子”姥姥嘴里听到的完整版本。
前几年姥姥爱喝几口小酒,一次喝醉不小心从炕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在小舅那边住了好久没去过大舅那边。眼看着小妗子(舅妈)的脸色越来越冰,大妗子避而不见,两个从小玩到白头的“老姐妹”聊天之后,“罐鼻子”姥姥给我姥姥出了个主意。
就在一个下午,“双簧”计谋上演了。“罐鼻子”姥姥去大妗子家玩,在炕上跟大妗子聊天呢,突然问道:“咦,那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有人敲门?”
“没有啊,没有人!”
“不是耗子吧,是嫩里屋那边的声音。”
“罐鼻子”姥姥跟在大妗子后面,有点“害怕”莫名其妙的声音的样子,循着声音找过去,找到了大舅小舅两家之间间隔着的门。大妗子拉开门的插销——
“哎呀老姐姐,你怎么在这地上爬着呀!”“罐鼻子”姥姥发出惊讶的叫声。大妗子看着外人吃惊的样子,很不情愿地扶起腿还没好利索的姥姥,扶到了大舅这边,姥姥就这样又在大舅家过这个月。
姥姥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轻描淡写的,还笑“罐鼻子”姥姥真是想了个好办法,让大妗子在外人面前不能表现得太凶,不能不接受她,不得不把她接到里屋抗上去。但是姥姥用的那个“爬”字却深深地刺激了我。
那时候姥姥的腿没有完全好利索,根本不能自己走到那扇门那里。我仿佛看着她,先一点一点挪动自己有点肥胖的上半身,到了炕沿上,半腰高的炕,她让自己先“掉”在旁边的椅子上,再“掉”在地上,她“哎”地轻哼一声,摔得有一点疼,还能忍受,手揉一揉摔疼的大腿,顾不上原本受伤的小腿的疼痛,上身在地上,手脚并用,爬过炉子,爬过餐桌,爬到两家间隔的门前,使劲地敲起那扇背面锁着的门……
那时候大约是姥姥七十多岁吧,说话间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吗?我完全不知道姥姥跟她的老姐妹还有这一样一出“自导自演”的戏码。
后来,姥姥基本上不能下炕了,我回家那次,给她煮一碗面条,没想到老人家连烂面条吃起来都那么费劲,吃两口就吃不下了。我把面条碗放在桌子沿上,还是在炕上陪着她聊天,接着小妗子下班回来了。
“弄点面条不知道吃了它,剩下个碗里浪费粮食!”
“我姥姥吃不下,吃了一口吃不下了!”
“吃不下别吃,吃不了别做,做了不吃放那占着个碗!”
姥姥躺在炕上,灰白的头发因为长时间枕着枕头很是凌乱,眼睛灰暗无神,但是她看着我,努力地在摇头。
“别惹她。”她用极轻的声音说着,她也没有太大的力气跟我说了。
小妗子呼呼走过来,哐当一声门被关上,又突然猛地被打开。小妗子拿起桌子上的半碗面条,几乎是冲出门去,手一甩,面条被倒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她再次冲进来,穿过我姥姥的炕前,进到里屋的厨房,水龙头哗哗打开刷碗,碗被咣当一声仍在一摞碗里,离破碎只有一线距离的碰撞声。
我气不过,穿上鞋下炕,大喊:“剩点面条怎么了,我姥还没吃完呢!她吃不下我等再给她再热热吃就是了!”
我真想跟她大喊,你是人吗?你怎么这么坏!但是我咽下这些话,不敢喊。我一会就要走了,回城里上班,姥姥还要在这生活!我不敢惹她!
我的眼泪冲出眼眶,哽咽地喊不出来话:“我姥还能吃你几天饭,她能浪费你几天粮食!”
“我姥姥就要死了!你就不能对她好点!她要死了!”
小妗子对我的哭诉恳求没有任何反应,还在喊着浪费粮食伤天理。我哭着去看姥姥,她眼神昏暗,对着我摇头。弟弟过去把小妗子拉到一边去,大声训斥她。可是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预约的出租车已经到屋后的路口等我了。
我抹掉眼泪过去跟姥姥说:“我得走了姥姥!”她点点头,我哭着出门,在院子里回头看我姥姥。姥姥歪着头,努力地仰着头歪过来头来,看着外面的我。她一句话不说,就是那样努力的歪着头看着我,就像以前以前的每一次,我出门她送我到路口的眼神一模一样。她已经“自身难保”,但是满眼都是对我的挂念和关切。
我哭着走了,哭了一路,哭到了城里,出租车司机听了我一路嚎啕大哭。
路上我给小妗子转了两千块钱,给她发信息,我说拜托她不用特别好好照顾姥姥,对她说话声音小一点就行,缺钱的话跟我要就行,我别的帮不上出点钱尽尽心,希望她能收下。我哭到眼睛看不清楚给她发的什么内容,哭到心碎,哭人老了的凄凉与无奈。我哭因为我知道她可能时日不多了,我心疼她,我为她辛苦一生最后换来儿媳妇这样的对待感到不公感到愤怒!但是我的姥姥,她自己却似乎总是把这些看做简单的事来面对。

最后的日子,姥姥睡睡醒醒。
谁又不是睡睡醒醒?
睡睡醒醒之间,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到底该对亲人做些什么?
离家上学、上班、成家以后,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回家一次。但是每次回家,在我妈家里,就是孩子们陪着姥爷看会电视,吃吃姥姥做的饭。离开家时间久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家串门,除了大舅小舅家门口玩玩。
有时候觉得,这每个月里某个周末,奔波在路上四个多小时回去换的一天时间,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而姥姥的存在让我告诉我,有意思,有意义!就在我回家陪爸爸看电视的时光里,就在孩子们在姥姥门口疯跑的日子里,就在放弃了减肥计划大口大口地扒嘴里妈妈炒的菜煮的肉里,就在我坐在大舅小舅门口闲得百无聊赖给姥姥剪剪指甲抠抠耳朵的日子里,在我从QQ音乐里给姥姥播放的咿咿呀呀的听不懂的《杨三姐告状》和《天仙配》里……这些陪伴家人的时光本身,就是回家的意义。
2020年初的疫情前,我留出了五天年假,要等春节回家去多陪姥姥几天。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的计划。
在过了高速重重防疫检查关卡后我回家了一趟,匆匆忙忙看姥姥一眼。她在炕上没起来,我戴着口罩姥姥马上就认出了我,我在她耳朵边大喊:“现在有传染病,我没法回来!”
其实姥姥一点都不聋,耳朵一直很好用,好像我只有喊出来才能表达我不能回去陪她的遗憾和纠结,我还要回去照顾两个孩子。疫情不明朗甚至很恐怖,家里爸爸妈妈也不敢让我久待,我喊着告诉她我不能回来陪她还要一会马上就要走的原因。
“那是还没有好药!”姥姥依然明白。
再次回去就是疫情后两个月了。姥姥瘦了一点,下巴尖了。她认识我,还能跟我聊天,她跟我说她自己看自己出殡都看了好几回了,看见已经走了的舅姥姥回来跟她说话好几次了。我不敢接话,把她扶起来坐一会,给她挠挠后背,拿水湿了毛巾给她擦擦眼角擦擦脸。她很安静,像个小孩子一样安静地被我照顾,就像小时候,她照顾我一样。
生命就像花儿一样会开放会凋零,就像大自然中的一切,会出现会消失。家门口的月季花,败了旧的,生出新的,我把开的最好的花都剪下来,带着去看姥姥。
我在她的坟前哭,看坟后的柳枝随风飞舞,看蓝天空旷无边,看脚下的泥土里小蚯蚓钻下去,西瓜虫翻滚,小蜘蛛急匆匆的逃走,有时候还听到青蛙呱呱的叫声,我猜想着是姥姥派它们来跟我打招呼,也默默希望它们带去我给姥姥的问候。
四十二岁的我,为姥姥哭过的眼睛变得有点肿胀,似乎样貌也有了些许的改变。四十岁因为姥姥的离去,我才开始对人生产生种种疑惑,失去姥姥爱护的我似乎与这个年龄该有的成熟格格不入。
我的疑惑依然没有解开。我时时去翻看姥姥的照片,默默念叨她对我的好。我默默思考,她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我们,从不争辩,从不埋怨。她是在用她的生命告诉我,生命是苦,但是我们可以往甜里过啊!
再后来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楼下看到一位老奶奶经过,戴一个大红色的羊绒帽子,穿一件酒红色的羊绒半长款大衣,皮肤白白的,脸上有一些皱纹。老奶奶看了我一眼,轻轻笑着,走过去了。我忍不住回头看她,笔直的腰杆,鲜艳但不失典雅的衣服。我想,如果我姥姥现在能像她这样,可以独自散步,可以经常跟我聊聊天,该多好啊。

我姥姥的故事,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是她给予我的,让我在没有她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回忆,细细汲取,获得对生活无量坚强的力量,去爱与被爱。
生命的相遇,对每一个人都值得。
用写作来记录身边的故事,是我从小的梦想,但是几十年都没有实际行动起来,感谢三明治的编辑们,尤其是不苑老师、依蔓老师、恕行老师,在我人生中最迷惑的时间与你们相遇,给我指引,让我终于有力量推开那扇门,称之为写作的“理想之门”!我知道我还很幼稚,就算步履蹒跚,只要静下来,开始写,我已经赢了一半,接下来,交给时间!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原标题:《四十而惑,我愿经常与93岁的姥姥聊聊天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