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还在给鹿道森写信的人
原创 小昼 极昼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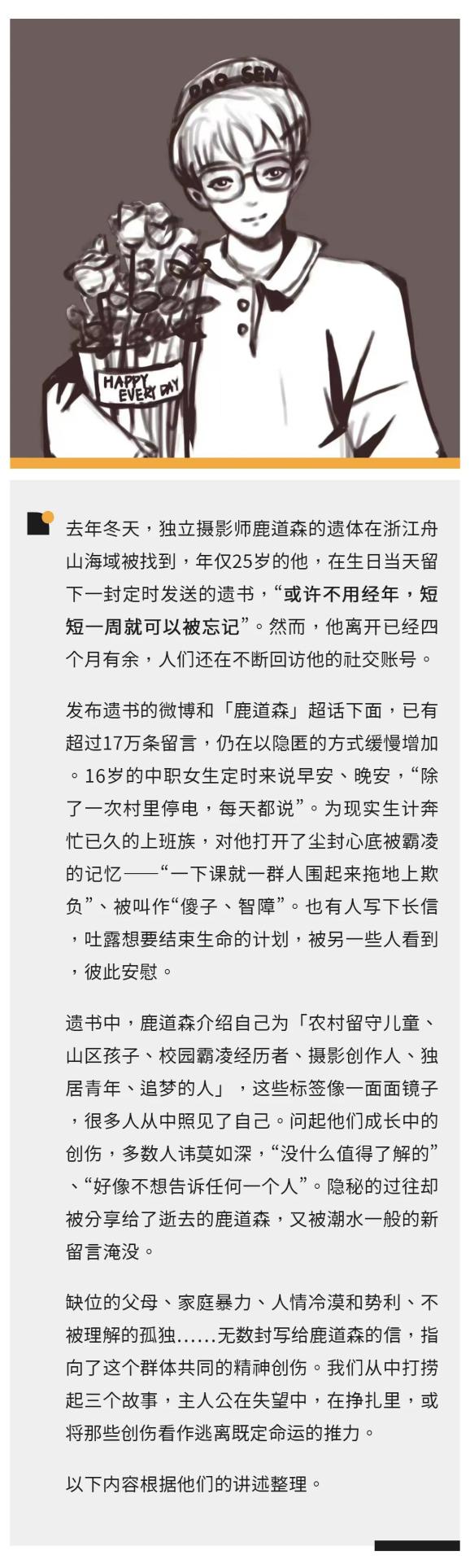
文 | 姜婉茹
编辑 | 陶若谷
“他们永远只在乎金钱,名利,地位,没有人关心你是否幸福,快乐,我感觉压力好大。没有爱,没有钱,没有生活的动力,没有未来。/
而现在我自己苦苦追求的艺术,现在看来倒是一个笑话,要是我能够靠作品多赚点钱,或许能够改变生活吧,但是很抱歉,我没有,没能够改变。”
(节选自鹿道森的遗书)
致鹿道森:
可是我真的不快乐,死亡对我来说是解脱。
希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孩子。
—— 黎舒,25岁,做剪辑师的农村姑娘
刷到小鹿新闻的那天,我窝在沙发上看他的遗书,哭了起来。我的猫从没见过我这样,它看得呆住了。后来每当我感觉“快要死了”的时候,就会去小鹿的微博,“认识”他之前,这些话都憋在心里,怕被怜悯、怕被安慰、也怕被人说矫情。我不敢把留言同步到自己主页,不想被正在读研的表姐看到。有的陌生人会安慰我说什么“世界美好”,我觉得那些话很空。
我今年25岁,是小鹿离开这个世界的年纪。可能原生家庭的伤害会在这个年龄段凸显出来,贫穷、缺爱、学历低、事业不顺、被逼婚……都是环环相扣的。但是小鹿上过大学,起点比我高,如果我是他,也许会再坚持一下。
我出生于96年,父亲是一名英语老师,母亲是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妈妈打扮时髦,不甘于一辈子在农村,想要城市户口。她的工资比我爸还高,脾气却很温和。他俩是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当时爷爷的农田要被没收,妈妈嫁过去就能保留,男方催着匆忙把婚结了。我今年还跟姥姥感叹,“为了一块地,就嫁给他了”。
结婚第二年就生下了我。那年工厂大量裁员,妈妈也没了工作,可能还有产后抑郁的原因,她像变了一个人。爷爷奶奶会用难听的话骂她,父亲也开始对她家暴。小姨跟我说,见过父亲把妈妈从三轮车上拽下来,当着全村人狠打。还有一次,小姨透过门缝看见,妈妈躲在堂屋里面烧婚纱照。
99年,他们离婚了,妈妈什么都没要,只要我。可是她很快又再婚了,我想按她的性格,应该是不愿意的,但是在农村,好像女人不能不结婚。她搬去了很远的地方住,我跟着姥姥生活。
我对妈妈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一次是在舅舅家,她追着喂我饭吃;一次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突然从藏身的角落出现,送给我一个橘子。我把它吃了,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直到2005年的冬天,那年我9岁,姥姥说很久没见过我妈了,买了东西去探望她,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找了个邻居把门撞开,姥姥看见我妈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再婚的丈夫出门打工了,没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她对这个世界、对我,都没有留下一句话。
小学的日子过得还行,我文科成绩好,还在一个全国的作文比赛拿过奖。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家的事,只是每次申请贫困补助,表格上别人会填爸爸是谁,妈妈是谁,我不知道该填谁,有时填父亲陌生的名字,有时填舅舅,尽力糊弄过去。
每天上下学,要经过村里的“CBD”,总有一群大妈以为我走远了,就在背后指点比划,“这个小姑娘没妈了”,我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觉得很自卑,尽可能绕着那条路走。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真正的噩梦从12岁那年开始。父亲偶尔会来学校,送些棉手套之类的小玩意,一天下午,他直接来我班里,把我抱到面包车上,我很害怕,但是没有说话,知道无法挣脱。
那天姥姥去学校找过我,得知被父亲接走了,说“那就跟他吧”。姥姥家特别穷,种玉米和小麦,一年差不多卖一千块钱,三餐只能吃一些粥,没有肉。她当年为了吃饱饭才嫁给姥爷,结果姥爷经商被骗,跳井死了,后来妈妈又去世了。我不忍心她一个人,总想回到她身边。
父亲后来说,他是不想付每天8块钱的抚养费了,才把我接回去。他的新妻子是个厉害的女人,嫁之前就说,“我可不像你大媳妇,拿个软柿子捏”。我父亲怕她。那天我哭了整个晚上,心里始终觉得,不跟我商量就强行“偷走”,很不尊重我,也因此不肯按父亲的意愿,叫那个女人一声“妈”。
有天父亲让我背《卜算子·咏梅》,我不肯,他抓住我的头发,把头摁在冰凉的地上打。后来我尽量不跟父亲同处一室,躲着他走,不跟他说话。每天三更半夜,我都会看看大门有没有落锁,想顺着记忆里的路,逃回姥姥家。没事做的时候,我拿着小刀去划院子里的大杨树,一刀一刀,那棵树最后死掉了。因为“太过叛逆”,后妈把我撵去了奶奶家。
我的整个人生,都捆绑在亲人的利益里,他们眼里只有钱。我的出生跟“一块地”有关;为了省掉抚养费,被强行拖到父亲身边;又是因为钱不给上学,改变了命运的轨迹。
中考张榜的时候,我考上了高中,跟父亲说我要上学,学费3000块。钱都在后妈手里,他说“你连妈都不喊一声,还指望人家给你钱”。我姨跟我姑商量,一家出一半学费,姑姑说,谁让她上学谁出钱。奶奶也说,女孩子不要上学了。没人觉得应该帮我这一步。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升学。之后父亲带我去办了一张身份证,为了不被计划生育政策罚款,家庭住址栏上,填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我去了外地打工,在东莞电子厂当仓储员,后来又去餐馆端盘子。打工的日子,我跟周围喜欢聊家长里短的阿姨、等着结婚生娃的同龄人格格不入,隐隐觉得有自己的事要做。小时候喜欢一个歌手,因为他和对文字的天然亲近感,想要进入传媒业,接近那道星光。
我用打工赚的钱买了台电脑,先是学设计,又自学了一点剪辑,然后去了郑州,给新媒体公司剪短视频,按条计费,没签合同。
甲方很挑剔,一组素材大约剪10条1分多的视频,要求在2-3天内剪完,修改意见多了就意味着重剪,经常熬夜。流量好的片子,也从来没人夸是剪辑的创意好,彷佛只是被雇佣的工具人。但我是公司里剪片最多的,活儿来了就上,多急多累都顶下来了,我没有生活,只有工作。

●鹿道森的个人网站,图源自网络。
后来公司倒闭,我又换了几个城市,但一份长久的、签合同的工作很难找,我的学历(硬伤)始终摆在眼前,无法逾越。
姥姥和舅舅都不支持我做剪辑,觉得学美容美发实在。村里的姑娘,大多在22岁前就结婚了,为了躲催婚,我过年不敢回家。姥姥觉得找个县里有车有房的人,对我好就行。但我想攒钱买房子,留在城市里。
心里好像有一个很大缺口,想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需要房子、车子、票子带来的安全感。从小到大,所有亲情都离不开钱,感觉以钱为基础的关系会很结实。别人都是两个人结婚一起还贷买房,我从没想过可以依靠别人。
我只爱传媒业,视频发布的那一刻会有成就感,但是它给不了我要的安全感,也许会有一天,像小鹿跟摄影说再见一样,我要跟喜欢过的剪辑道别。
前两年我填了人体器官捐献的表格,也搜索过怎样自杀不痛苦。我很抗拒这样的命运,总觉得应该能考上一个本科,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到像字节跳动那种。听说那里压力大,但我“想被压榨还压榨不了呢”。
已经十多年没见过父亲了,前几年联系过一次,他说起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学习不好,“当时还不如让你上学”,这话听着恶心。但我不再恨他了,希望他注意血压,早点把房贷还上,这辈子就当没有缘分吧。
“很抱歉,我的生命,好像就是一直在逃离。/
很多事情文字的表述都显得苍白无力,即使你亲身体会恐怕也未必知道我是怎样的感受。冰冻三尺,又岂是一日之寒呢。/
压垮我的不是一根稻草,是无数的沙粒,我走一步都是像背着大山走。”
(节选自鹿道森的遗书)
致鹿道森:
如果活着太累太可怕,我不会劝你。
—— 莫非,40岁+,把哥哥埋在芦苇荡边河床上
到了四十几岁,渐渐过上了曾经向往的生活,很少会再坐下来,揭开伤疤,细数童年的创痛。鹿道森的“遗书”让我突然又陷入过往,记忆里已经暗淡的场景,再度被照亮。
年轻的摄影师有条不紊地退租、送出摄影器材、寄送随身物品,安排好身后事,然后冷静地赴死,这绝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就像我大哥当年一样。
那是九几年的时候,21岁的哥哥策划了自己的“人生谢幕旅行”。他提前半年开始建立信任,每月帮不当班的工友代领工资。直到最后一次,一次性拿走了10名工友的工资,不辞而别。揣着几百块“巨款”,他去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把向往的江南城市走过一遍,然后掐算着端午的时间,回到了最疼爱他的外婆坟前。
舅舅去扫墓时,从哥哥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两毛钱,还有一些火车、景点的票根,拼凑出他人生最后的踪迹。一张手写的遗言纸条上,写着“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是当时热映的台湾电影插曲,也是一张控诉书,没有一字提到父亲,满纸却都在骂他。
我比哥哥小3岁,与他共同生活了12年,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互相分享好玩的东西,他会揍欺负我的孩子,有时也打我。当时我们耻于表露软弱的情感,哪怕父亲的巴掌落下来,都不肯掉一滴眼泪。我和哥哥很少正经地聊一聊成长中的噩梦,没有彼此安慰过。倔强、敏感、自卑,是我们共同的性格基调,我受过的伤害,哥哥或多或少都遭遇过。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我出生6个月就断了奶,被寄养在城里的祖父母家,跟爸妈和3个哥哥姐姐分离。家乡有一句谚语,叫“宁跟讨饭的娘,也不跟做官的爹”。但是在我3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哥哥和两个姐姐在农村长大,他们常在不通电、没有灯光的乡下黑夜里找父亲,大的孩子哭,小的叫嚷着跟在后面跑,而爸爸不知道正在哪家喝酒。
7岁时,爸爸回到城里住。在外人眼里,父亲是最底层的市民阶层出身,没什么文化,被分配去做重体力劳动,拖着板车挨家挨户送蜂窝煤。不喝酒的时候,他是个“老实人”,沉默寡言,没什么存在感,在哪里都没人在乎他的意见。
父亲的人生过得并不如意,也遇到了那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只有面对更为弱势的小孩时,他才抬得起头,有机会宣泄压力和苦闷,也许打小孩,就是他的解压方式。
打人的时候,他把我们拎进房间,门锁上,捆住人,用皮带带铁的那头抽,抽一下身上就紫一道,皮肤肿起来。有时候用皮鞋直接踹背,狠狠踢上一脚,小孩像个木偶,“啪”地就扑在地上。醉酒时下手更没有轻重,我有时候会想,他要是把我打死了,也就解脱了。
有时邻居过来敲门,被父亲一声“我打自己的小孩,关你屁事”就吼走了。没有挨打的哥哥姐姐在旁边站着,噤若寒蝉,没人敢阻拦,大姐劝过我“不要忤逆父亲”。
好在邻居家其他小孩也挨揍,虽然没我家打得狠。当他们嘲笑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也有机会嘲笑他们的伤口,有种报仇的快意。
直到高一我窜了个子,比父亲更高,可以单手抓住他的拳头,他知道自己老了,不是我的对手了。
父亲对我们的成长不闻不问,养育弟妹的负担落到了大姐身上。她十三四岁就去服装厂做缝纫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份工一直做到退休。每学期开学,三个弟妹都要交学费,拿不出钱,就商量谁先交,谁拖一两个月再交。
少年时我营养不良,体格瘦弱,头发偏黄,常穿打补丁的衣服。有个老师用阴阳怪气的口吻,讲我家里的私事,给我取外号,同学跟着一起叫我“黄毛”,还有人喊“娘娘腔”——实际我没有柔和的气质,他们只是觉得这是个脏词,攻击起来有足够的杀伤力。
校园霸凌未必都是加诸在身上的拳脚,还有不被允许参与集体汇演,体育活动无人互动。交朋友总怕得罪了人,用一种巴结的心态,仿佛同学跟我玩是一种“恩赐”。
哥哥交到了“朋友”,他15岁辍学,还未成年就被父亲推进了社会,跟几个社会上的“弟兄”住在一起,大多是家里不幸福的孩子。他蹬三轮送货,去发廊做小工,在医院做护工,去纺织厂做翻砂工,能做的尽量都做,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显得心事重重,没有年轻人的朝气。父亲会找他要钱,有钱时哥哥塞一些给他,没钱时还会偷拿家里的粮票、布票。无论父亲怎么骂他、打他,他都一声不吭,安静地捱着。
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是个闷热的夏天。他坐在床边喊我过去,好像想说点什么。等我站过去,他沉默了一会儿,却什么都没说。可能在他眼里,我还是个孩子。
那时我的心思不在哥哥身上,一心想着最好一夜长大,逃离这个家。哥哥姐姐们可能也这么想,每个人自顾不暇,都在一滩自己的泥沼中挣扎。
等到我的年龄渐渐超过了哥哥,不断回想最后的一面,如果那天使劲儿追问,好好劝劝,他可以不走这条极端的路吗?被社会捶打多年之后,我想,在哥哥万全而周密的计划面前,我的劝慰可能苍白得像一张纸。一个铁了心告别世界的人,根本不会来抓我伸出的手。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小时候每当父亲把我的衣服扔出家门,让我滚蛋,我想着滚就滚,转身就去投奔呵护过我的姑妈,总还有个去处。新华书店里淘到的旧杂志,小说和诗歌,也给过我慰藉,指引了方向。而疼爱哥哥的外婆很早就过世了,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在乎他的人。
舅舅发电报给父亲,让他带哥哥的骨灰回家。父亲不愿意花几十块钱买骨灰盒,直接用一个口袋把哥哥装了回来,塞到我床底下。过了几天,一个月光清冷的夜里,我找了一片芦苇荡,把哥哥埋在了河床上,不远处葬着母亲。
父亲跟平时一样,雷打不动地喝得烂醉。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喝酒,微薄的工资,一直被优先用来抽烟喝酒,从早到晚,一天三顿。他曾经醉酒掉进河里,也摔过当时珍贵的自行车。醉后出尽洋相,彻夜不息地胡言乱语。所以我一辈子不沾烟酒,仿佛在用一生的时间,清除父亲的影响。
15岁高中毕业,我念了技术学校、做过机械工人、读过大专夜校、在宾馆打过工、报名高自考,最后拿到本科文凭。在地理上,我从长江边的南方小镇、那个30多平方米的筒子楼,一路逃到省城、逃到北京,北漂十五年后,又逃出国,被一个声音驱赶着,“快跑,越远越好”,就像一个逃犯。
童年幸福的人,可以躲到童年里去寻找精神上的力量支撑,而我们是无处可退的人。
后来父亲因为抽烟酗酒,得病去世了。姐姐买了一块墓地,想把爸妈和哥哥合葬在一起。但是母亲和哥哥的骨灰早已无迹可寻,连哥哥的一件衣服、一张照片也找不到,做不了衣冠冢。只是在当年埋骨的地方,抓了一把土放进墓中。
「若是我们还能够拥有时间,若能再次回到血缘的起点,我只想彼此怜悯,珍视,依偎,谅解。把缺失的感情修复完整,让心里的爱简单如初。但是,时间犹如水滴,不再会回到我们的手中。世间的感情多是如此,无论我们是否甘愿,生命里的遗憾总是和怀念一样地坚韧。」(莫非纪念亲人的文字《缝补》,写于2012年。)

●网友纪念鹿道森的画。图/鹿狮子Lion (已获授权)

●网友为纪念鹿道森创作的插画。图/梁望(已获授权)
“有人说为啥总感觉你不够自信,从小就生活在责备的环境里,我很自卑。我也只是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想要被爱,可为什么就这么艰难呢。”
我疲惫不堪,重组千万次,破碎千万次。
(节选自鹿道森的遗书)
致鹿道森:
人生不过大梦一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
—— 陈默,28岁,群众演员
在鹿道森的的超话里,有很多抑郁的人留言,我会去安慰那些想自杀的人,就像在鼓励我自己,但其实没什么用。很多人还在抑郁焦虑、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里,我好像已经到了下一阶段,规划好了一整年要做的事情——练出胸肌腹肌倒三角、一次性考过ACE健身私教证书、学习摄影,强迫自己“变好”,不要死。
这是一个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缠斗、跟世界拉扯的过程。但可能会因为突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开始消沉。最近得知姥姥去世了,疫情原因无法回乡送终,我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黑暗里听歌、发呆、打游戏、暴饮暴食,拼命吃甜的,胖了5斤。
已经两年没喝酒了,这几天喝了许多。姥姥去世了,去年姥爷也去世了,大前年爷爷也去世了,奶奶30年前就去世了。我又少了一个亲人,虽然他们不是很疼我,可我还是很难过。可能两三个星期后,会再度收拾情绪去健身,捡起“变好”的计划。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朋友的,翻翻通讯录,没有一个可以通话的人。
原生家庭的创伤一直跟随着我。我爷爷之前有一些地,父亲是最受宠的小儿子,村里人叫他“三少爷”。后来家道中落,父亲被惯坏了,喜欢在街上跟人喝酒,三天一大场,两天一小场,从街头喝到街尾,不肯出去工作。后来他的亲哥,我大伯混得不错,在村里一大片泥房子中间,给父亲盖了石头房子。
我妈是十里八村出名的美女,相亲相了一两百个,她都看不上。相到我爸的时候,看他人长得不错,整个村又只有这么一座醒目的新房子,恰逢家里当时老给她气受,赌气一样赶紧嫁了。后来我妈被我爸打得受不了,逃回娘家,想要离婚的时候,外公嫌丢人,把母亲撵回了家。
当年妇女地位很低,妈妈很难靠劳动获得收入,家里一直靠大伯接济。印象里有次全班都交了学费,只有我没交,妈妈去找外婆借,外婆也没有钱,现把豆子卖了。但是爸爸很爱他自己,想吃肉就买一份自己吃,我和妈妈、姐姐只能捡他剩下的。
亲戚都瞧不起我家,姑姑来串门,只带些卖不出去的烂苹果,说“反正你们连这也买不起”。姐姐会指使我找爷爷要钱,让我抱着他的腿打滚儿,爷爷没办法了,就给我一毛钱。但是大伯家的孩子来,爷爷会给一块钱。那时候一毛钱能买一片辣条,或者一袋汽水,一两块糖,吃上一次特别奢侈。
小时候转到县里上中学,我一天没洗头,两天没洗澡,就担心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甚至于别人看我一眼,都怀疑是瞧不起我。我总是下意识去讨好别人,有次给同学买吃的,怕其他人看见不舒服,就给在场的都买一份,我自己不吃,明明是很想吃的。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因为自卑,我一直不太敢跟别人说话,特别是跟女孩说话会脸红。虽然我长得比较好看,个头也高,小时候被选入了校国旗队。有个姑娘下课总喜欢黏着我,在身后一声声地叫,哥。但我沉默寡言,这种自卑被同学解读为“装酷”。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被人喜欢过。
回到家就只有无止境的争吵,父亲经常打人。姐姐比我大一岁,为了少挨打,有时会嫁祸给我。她摁坏了电视,把遥控器往我身上一扔,就去喊父亲:“弟弟把电视弄坏了”。有时她纯粹想看我挨打取乐。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每次都叫我让着姐姐,我体谅你,所以不说话,可是谁关心过我呢?母亲很意外,她说,你老实,你乖,你姐总是乱嚎,我只想让她停下,别打扰他人。
还有一次,二大爷带了一些火腿肠,我分了几根给小伙伴吃。第二天父亲说,因为这几根肠他和二大爷打了一架。我在被窝里哭得好伤心,那天才明白我爸的亲哥,也不能算是我的亲人。
只有表姐偏疼我,她只给我一个人买吃的。有一次看见她,我太激动了,直接从楼上滚了下来,现在鼻子还有一点弯弯的。还有同桌喜欢买菠萝味的软糖,会分给我一块,这件事温暖了我好多年。
缺爱的人往往得不到爱,不是因为长得帅就能免于受伤。我从来不敢主动开启一场恋爱,觉得配不上喜欢的人。被人“追到”又想把一切好东西都给对方,没什么钱也去买迪奥、香奈儿的口红。女朋友生气,我要发几百条信息去哄,最后都是她们离开我。
在和抑郁对抗的时候,爱情曾是“武器”,是活着的意义。后来一个女孩教我,恋爱是有套路的,要先嘘寒问暖献殷勤,再忽冷忽热,欲擒故纵,“让对方心里想的都是你”。我认真做了笔记,还没实践过。
我想不幸的原生家庭,父母多半不会教孩子人情世故,我还是按照内心的标尺在生活。有时也会想,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合群的人,按“套路”来的话,就会有钱、有人爱吧?
之前在北京做过一阵儿信用卡推广,如果在转化率上作假,一天能挣很多钱,克扣是行业的潜规则。只有一次交不上房租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赚了几千块钱——这钱太好挣了,但后来我再也没拿过这个钱,过不了心里的坎儿。
特别痛苦的时候,会选择逃避。之前逃到部队当兵,我体能很差,晚睡早起地加练。别人做常规训练,我会主动跟指导员说,加练负重10公里跑。实在跑不动也不会停下,一边跑一边哭。累到脑子“死机了”,走路都能撞柱子上,就没时间产生负面情绪了。
现在我又“逃”进了影视城当群演,最多一两句台词,角色连名字都没有。教表演的老师说,演戏就是说谎,人人从小就会。没人教过我,我是班上的“问题学生”,学得很慢。
最近读了一些书,找寻活下去的理由,毕竟“来都来了”。我没勇气去恨别人,只当是还了上辈子的债。现在想尽可能去遗忘不好的回忆,去学滑板,买一辆摩托,去玩,去吃好吃的……还是要努力生活,好好爱自己。

●鹿道森发布遗书的账号截图。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头图为网友为纪念鹿道森创作的插画,作者难梦星河,已获授权。)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 END -

原标题:《还在给鹿道森写信的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