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周书记︱他把“放弃犹太身份”看作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对中国读者来说,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喇卫国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一书中的有些议题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从大的方面来看,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他们在近现代世界政治中的遭遇,以及以色列这一国家建立的过程,都充满了复杂性,各种历史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建构、演变,容易在人们头脑中积淀着各种固化的认识;从本书的写作方式来看,作者把犹太历史研究与对以色列现实政治的分析思考及个人成长经历、所见所闻和身份认同的认识变化结合起来,围绕着个人放弃犹太人身份的原因展开一种思想录式的对话与追问,如果对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与现实以及作者的生活语境没有相当的认识,恐怕很难完全理解书中论述的很多议题。但是,由于现代政治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历史叙事反思、个人政治伦理与道德立场等议题都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桑德这部著作对中国读者而言的可读性及深刻意义都无庸置疑。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出版的犹太研究著作主要是以犹太思想与文化研究为起点,以译介的方式为主,如顾晓鸣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上海三联书店)、徐新、凌继尧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傅有德主编的“汉译犹太文化丛书”(山东大学出版社)等,均有广泛影响。专题研究论文则较为集中于在华犹太人的史料整理与历史研究,也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就开始关注犹太复国主义与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关系。八十年代国内的文化研究热一般都带有从传统文化转型以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时代特征,而犹太文化往往被认为是成功融“犹太性”和“现代性”于一体的文化转型,美国犹太文化的独特性也引起学界关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则显示出与七十年代末中国对以外交口径的变化相同的转变轨迹,1992年中以建交更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研究增添了正面色彩。甚至也有中国学者提出“谁是‘犹太人’”的问题,试图从文献研究入手澄清“犹太人”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这些出版物足以使普通读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接受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宣传中转变过来,但是如果没有对今天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犹太人”概念的基本认识,仍然很难明白当代语境中的“犹太人”问题、巴以冲突及其解决前景等问题的真实性质。

施罗默·桑德于1946年出生在奥地利林茨一个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家庭。作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的“虚构三部曲”(《虚构的犹太民族》《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虚构的以色列地》)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与争议。在《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岽兴 、张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中,桑德追溯并剖析了犹太人的所谓“民族”历史,指出历史上的所谓“犹太人”根本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所谓古已有之、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史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建构和塑造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认为虽然该书运用的史料和提出的观点并不新鲜,但是该书在普及性和对建立犹太国的合法性的批判等方面的贡献仍然使它有很大价值。朱特还提到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知道历史真相的“我们”实际上非常有限,在美国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仍然相信官方所虚构和宣传的犹太历史,因此桑德这部著作颇有意义(《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附录二,“关于桑德和以色列”)。那么,针对犹太民族叙事的虚构性、刻意把犹太人历史苦难崇高化、以色列国家政治中愈演愈烈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以色列政府强加给自己的犹太“民族”属性等等问题,桑德在《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这部著作中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作为一个以色列国民而生活。他在破除犹太民族的神话之后,以个人身份的改变及其论述,呼吁人们反对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他把放弃犹太身份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责任。
为什么曾经坚持做犹太人而现在要放弃做犹太人?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及道义原则不可分割。桑德在书中讲述了2011年在特拉维夫机场过安检时发生的一幕情景:一个头裹传统围巾的女人被两个以色列安全警察押着离开了等候安检的队伍,他马上猜到她是“非犹太”以色列人;这是司空见惯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总是要接受特别的询问和检查。“我感到很不自在,向她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她用疑问的眼神默默地看了我一下。她的眼神并不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样,但道出了恐惧和哀怨。她向我微笑了一下并做了一个宿命的表示。几分钟后,我毫无困难地穿过了安检台。我简直感到羞愧而且不敢朝她的方向转过头去,只能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补偿。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我确信:在以色列,最要紧的是做一个‘犹太人’而不做阿拉伯人。”(95-96页)桑德的复杂感受(从不自在到羞愧)以及从对方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感情可能会刺痛以色列某些读者,甚至可能还会改写文本,虚构出这样一幕:“我”走到安检台前要求安全警察也把他带去做特别检查,警察以为听错了,“我”重复了一遍,对方惊讶得瞪大眼睛,马上用对讲机喊来……;最后桑德被喝斥着、推搡着回到正常过安检的队伍,几天后他任教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收到安全部门的通报……有理由认为,在反恐的名义下不断推行种族主义的以色列政治语境中,这种虚构正是对桑德内心感受的准确诠释。其实,从桑德作为波兰犹太人后裔的身份来看,他对于受害人遭遇及身份的自我认同也是有传统的。犹太人在波兰曾经有过长期的辉煌历史,但是纳粹德国占领时期整个族群几乎被彻底灭绝,而且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也不仅仅来自德国纳粹。1944年波兰犹太诗人朱利安·杜维姆在他的悲情诗《我们,波兰的犹太人……》中表达了因为遭受迫害反而要坚持波兰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的强烈感情,桑德说他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悲情诗,从而加强了他的犹太人意识;他还提到伊利亚·爱伦堡的一个观点:这个星球上只要还有一个反犹分子,他就要作为犹太人而存在。但是以色列越来越极端的种族主义政策使他的身份自信不断受到伤害(70页)。那么,对非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自然会使他走向放弃犹太人身份。如果从自觉“站队”的角度来看,从杜维姆、爱伦堡到桑德都有一种共同的“站队观”:世界上只要存在不公不义的迫害,我们就是那些受迫害的人。
实施种族主义政策无疑是现代文明国家的耻辱,因拥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选举制度而被看作中东地区唯一民主国家的以色列实施种族歧视政策,更使桑德感到无法容忍。在以色列,非犹太人的以色列国民在成为政府雇员、购买土地、竞选国家公职等方面均无法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以色列国民中的阿拉伯人更被视为危险人群,上述安检时要接受特殊检查的实例已是一种常态。在以色列的法律、教育和媒体中充斥着种族主义的思想,桑德时刻感到自己“生活在西方世界最为种族主义的一个社会中”。因此,他把反对种族主义政策与促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紧密联系起来,呼吁国家的立法者必须把国家机构看作全体以色列公民的民主权力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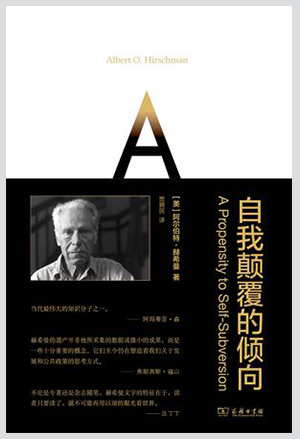
“放弃”是桑德这部书的两个核心概念之一,读者可能更为关注的是“放弃”的具体原因,这当然也是桑德在书中反复强调和从各个方面论述的问题,但是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放弃”作为个人的一种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应有机制、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以及在历史变革进程中的呼吁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第一章的题目是“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在某种角度来看,正可以看作桑德的“放弃”论更具现实意义的诠释。赫希曼这一章的主题是,在东德的变革历史进程中,“退出”与“呼吁”机制是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通过观察和分析这幕壮观的历史史诗中的微观细节,他提出了几个充满思想魅力和现实经验洞见的议题:一、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称作“精神离境”(23页),这是“退出”也是“放弃”;二、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相继出现的口号是“我们要出去”、“我们一直留在这里”和“我们是人民” (35页),这些戏剧般变化的口号正是对从“退出”到“呼吁”的最好诠释,也可以看作桑德的“放弃”之后的一种延伸的必然性:通过宣告放弃而呼吁抗争;三、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问题是:“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45页)他说的“公共因素”指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对个人动机和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结论是“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51页)这也正是桑德对历史所抱有的信念。
桑德公开宣布放弃犹太人身份,因此很容易被打上反犹主义者和颠覆国家的标签,然而他真正热爱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他谈到希特勒的种族主义阴魂不散,“其邪恶的意识形态又沉渣泛起,流毒难尽,以至于今天更以一种强劲的、惊人的、可怕的速率传播开来”(7页)。而在全书的最后,他说:“我对这片土地的挚爱总是激起我对它的悲观情绪。所以,我常常沉浸在忧伤之中,为现在感到痛心,为未来感到焦虑。我累了,觉得我们的政治行动之树上最后的理性之叶已经落下,使我们赤裸地面对部落里那些昏聩巫师们的任性。”(119页)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变为彻底的历史宿命论者,他仍然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因此他宣称无论他的诽谤者说或写些什么,他会继续写类似《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这样的书。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