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欣开九秩的国际东方学大家茨默教授:一个晚辈的印象记
今天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熟知的德国学者茨默教授八十寿辰。作为跟从茨默先生读书问学的晚辈,本人在过去三十年中受教于先生良多。谨草此文,略述师尊的德业成就与国际学术因缘,浅学如我,不敢奢望能测前辈学问之深,不全不确之处,尚望同人学友匡补。谨以区区小文,在万维网中为先生寿!

茨默教授接受《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专访时的画像(蒋立冬绘)

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学讲学(2014年)
青年茨默的成长期
茨默(Peter Zieme),德国人,1942年4月19日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家境小康。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留在了故乡也就是东柏林的茨默一家,随着体制的变化,身份由店主变成售货员。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按照当时的政策,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背景的茨默申请就读大学的过程也颇为艰难,所幸成绩优秀、表现良好,他终获录取,成为东德第一高校洪堡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大学时代的茨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年轻人,对学习各种语言非常着迷,显露出语言天赋。他在一家夜校(Abendschule)学阿拉伯语,任课教师是当时在洪堡大学读博士的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1935-2012)。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对语言天赋异禀,学生觉得老师满腹经纶,两人一见如故,就此开始了五十年的事业合作与毕生友谊。这是一段“德国东方学双子星座”的佳话,且待另表。
在宗德曼的建议下,茨默转了专业,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入洪堡大学的伊朗学研究所,当时的主任教授是荣克(Heinrich Junker,1889-1970),他是老派德国学者,做伊朗学,搞印欧研究,思想旧,学问好,是宗德曼的导师。茨默主修伊朗学,但半路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1963年洪堡大学聘请匈牙利学者哈匝伊(Hazai György,1932-2016)加盟,这是一位主攻突厥语方言的中生代学者,成为茨默走上突厥学道路的引路人,两人也是毕生的挚友。哈匝伊教授在洪堡任教二十年,与茨默合作,以吐鲁番文书研究推进了东德东方学研究的国际交往,特别是与日本学界的合作:从1966年开始,以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领衔的日本学者团队先后多次访问柏林科学院,阅读吐鲁番文书,开展编目合作,邀请东德学者访日。西德学者从七十年代开始也频频访问位于东柏林中区的吐鲁番研究组。
1965年毕业于洪堡大学之后,茨默进入民主德国国家科学院,以吐鲁番文书为研究对象攻读博士学位,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茨默是一个“大器早成”的研究者,他博士论文完成之时年方二十七岁,论文是一个七百页的大部头:Untersuchungen zur Schrift und Sprache der manichä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吐鲁番出土的以摩尼字母书写的突厥语文书之文字学与语言学研究》)。以这个年纪戴上博士帽,在国外古典研究领域是偏早的。正常的博士论文写作周期是“八年抗战”,一般情况下,戴帽之年罕有在而立之前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并没有注册作博士生这一项硬性制度规定,博士候选人只要出具有关学历证明,报出一个像样的博士论文选题计划,获得导师(Doktorvater/-mutter)的认可,就可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可以为了一些优惠政策注册当博士生,也可以从事任何其他职业,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论文完成没有时间限定。是否到学校听课,属于与导师的约定加自愿选择,一切都非常宽松。但是最后一关很严,就是论文答辩前的审读、修改,答辩的场面也严肃庄重,历经几个小时,完毕之时,考生罕有依旧神闲气定、毫无挫折感的。宣布答辩通过后,女秘书端来香槟酒,“嘭”的一响,大家举杯,笑逐颜开。我还记得,当年本人的答辩过后,茨默先生对我说:“我们现在是同事了(Jetzt sind wir Kollegen)。另外,要考虑一下下一步的题目。”这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1969年,茨默博士正式入职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一直供职到两德统一,科学院按照联邦制,改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学者茨默
茨默先生以解读文本闻名,学界有“最高法院”之称,指的是他的学问渊深广博,对突厥学的全局有发言权,判断公正,终审结论难于翻案。有关突厥学的历史经纬源流,郑诗亮先生曾与茨默先生做过一次深入、精彩的访谈(《上海书评》,2019年8月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76792)。严格、客观、有权威性,这是对他治学的最好总结。说他著作等身,不是虚语,文末附录简历所列的著作,只是茨默先生专著的几分之一。须知古代语言释读工作类似于文科中的理科,没有看懂谈不上正确的释读,随意乱猜(guess-work),即使不一定被同行公开撰文批评、改正,也一定无人引用,终将自生自灭。茨默先生的释读是突厥学的楷模之作,虽然我也听他自己说过,某一篇论文恐怕不成立,不要用了,也不要翻译了。这正体现了一位严谨学者的科学精神和谦逊态度。
在科学院工作之初,年轻的茨默就在哈匝伊教授的支持下,做成一件大事:创立“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丛刊”(Berliner Turfantexte,简称BTT),由东德科学院附属的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e Verlag)出版,第一种为哈匝伊、茨默合作的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 nebst einem Anhang von Taijun Inokuchi(《梁朝傅大士金刚经颂的回鹘语残篇》),书后附有日本学者井之口泰淳的专题论文,显示了这个东德学术新丛书的开放姿态。到1990年两德统一,BTT共出版了十七种。而曾经拥有国际声望的科学院出版社随政治变局进入了颠簸期,在短短几年内数次改易东家,其人文部分先后由巴伐利亚的奥尔登堡出版社(R. Oldenbourg Verlag)、科奈尔森(Cornelsen Verlag)出版社收购,目前归入总部设在柏林的德古伊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从第十八种开始,茨默将BTT转到荷兰的学术大社布雷珀尔斯(Brepols)接续出版,该社于1996年以他的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Edi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utra(《金光明经序与第一卷的突厥语译本》)重张BTT系列。于今二十余年过去,目前出到第四十七册,也是茨默的作品:Uigurorum veterum fragmenta minora(《回鹘文书丛残》,2020年)。
东德科学院的吐鲁番学研究具有国际声誉,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德国西域探险队四次到新疆南北多个地区,发掘、采集、收购的古代遗物甚多,文书(写本、印本)就有四万件之数,涉及的语言文字超过二十种,当中包含已经失传的“死语言”(如吐火罗语、于阗语、“据史德语”、西夏文、契丹文等)和沉湮千年的古代宗教经典与教史记录(最突出的是德藏数千件摩尼教写本,为举世最丰富的收藏),东西方科研文化大国的学者历来非常重视,前往调查、研究,掌握一手信息。作为这批宝藏的主要收藏单位,柏林科学院自然成了朝圣参拜之地,它在西域语文、历史研究方面的悠久、优秀传统,虽经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才损失、流失而不坠,是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恒宁(W.B. Henning)、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另一个中国名字是冯加班)几位“吐鲁番人”(Turfaner,科学院同事对从事吐鲁番写本研究的学者的谑称),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米维礼(F.W.K. Müller)、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柏林大学的威利・邦(Willy Bang)、哥廷根大学的安德雷亚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为吐鲁番文书的解读打开了局面,而后由第二代鲍伊斯(Mary Boyce)、宗德曼、茨默接续传统,并发扬光大,使世人知晓这些哪怕只有几个字的小残片中包含的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珍贵信息,令“六经皆史”“四库皆史”在非汉语文献中获得了适用性(参见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前言)。
其二,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各国学者乐于前往的学术胜地,宗德曼、茨默分别为吐鲁番特藏的伊朗语、突厥回鹘语两大语系文献整理研究的掌门人。我在柏林读书、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有几年经常去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得以亲眼目睹这里之为国际吐鲁番学研究重镇的鼎盛气象。所里常川有外地、外国来访客人,Livshitz、Hazai、Kara、McKenzie、Emmerick、Tezcan、Röhrborn、Erdal、Maue、Weber、Gnoli、Morano、Sims-Williams、Sam Lieu、Laut、Hartmann、Wille、Dietz、庄垣内正弘、小田寿典、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吉田丰、北村高、西胁常记等东西各国的学者都是常客,年轻一代的有松井太、笠井幸代、Pavel Lurje、Ilya Yakubovitch等。中国学者中,有张广达、耿世民、吴玉贵、晁华山、荣新江、段晴、李肖、朱玉麒、阿不都热西提、阿不来提、刘屹、余欣、潘华琼等师友到访,其时我也曾有机会问学、请教,起到一些陪同、介绍安排阅览的作用。2002年茨默先生在所长任上,与印度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高昌再探——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会议代表有一百二十之数,提交论文七十二篇,其中应邀赴会的中国代表有十三人。
茨默与中国及国际学术界
因为时代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世界隔绝了一些年,彼此来往甚少,信息不通,了解的途径只能靠出版物。这里举一个例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文弼先生所著《吐鲁番考古记》出版。早在二十年代,黄先生曾作为中方代表,跟随中国和瑞典的考察团远赴西域考察,发现了许多文物,包括大批古代写本文书。新中国成立之初,黄先生的研究陆续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吐鲁番考古记》是其中一种,收录了他在吐鲁番地区的一些发现,公布了一批材料,除了汉文的,也有非汉文的,有一些是梵语的佛教写本,还有一些不清楚是什么语言,黄文弼先生很谨慎,以图版予以公布。茨默在东柏林读到了这本书,发现内有回鹘语写本,内容有摩尼教的线索,尽管照片既不清晰又不完整,他还是把握住了一些关键语句、字眼,从上下文推求,于1970年写成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Manichäismus bei den Türken(《论突厥人摩尼教的几个问题》,在第十三届国际阿尔泰常设会议上发表,会议论文集Traditions religieuses et para-religieuses des peuples altaïques 出版于1972年),大胆提出这是一份摩尼教文书,记录了重要摩尼教史史料。论文发表,可谓石破天惊,引起轰动。其时《吐鲁番考古记》出版已经将近二十年。七十年代后期,耿世民先生了解到这篇论文,遂前往收藏黄文弼文书的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调阅全宗文书,做了通篇释读,确认了茨默的猜想是正确的。耿先生的长篇论文《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四期。后来森安孝夫又在此基础上重做此题,深入开掘,为此既前往历博阅读原件,确认释读疑点,又远涉天山,前往吐鲁番实地踏勘当年出土遗址,完成了一篇《回鹘摩尼教史研究》(《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 1991年),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也因此奠定了他在国际摩尼教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该书于2004年出版德文译本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Forschungen zu manichäischen Quellen und 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Übersetzt von Christian Steineck, Harrassowitz Verlag)。德文是国际东方学和摩尼教研究的重要工作语言,英文著述远不及德文,至今仍然如此。
还有一件事情,是茨默教授带着我做的:释读1981年吐鲁番文物管理所在柏孜克里克发掘出土的摩尼教文书。大部分发现品陆续发表,但留下一些老大难残片,有条件看到这批文书的各家一时束手。2009年秋天,我在汉堡大学工作,茨默先生突然来邮件说:“我最近看了一件文书,你回柏林时,请找时间来科学院一谈。”下个星期,我就去了科学院见他。他拿出两张打印的文书图片,已经用透明胶纸粘在一起,说:“我拼合了两个残片,你看一下。”我一看,是两个边缘很不规整的文书残片,出土状态不好,有“缺肉”,如果在分离的状态,不容易发现是可以缀合的。他说:“这是摩尼教的文书,我做了一个释读。”这个由东洋文库的梅村坦先生带队跟新疆合作的项目,成果要在中国、用中文发表。茨默先生建议我与他合写。他口授了几条要点,我做了记录,回家根据他的习惯文风整理成文,这就是《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三期,第1-7页)。

吐鲁番1981年出土柏孜克里克回鹘语摩尼教文书81TB10: 06-3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文书中的两个西域地名,按茨默先生原来的释读一来有点绕,二来距离有点远,不在从南疆到漠北的合理路线上。我又请他一起看地图,他看罢说:你说的对。这就确定了文书里提到的是“黑车子”(葛罗康里)和“曳咥河”。文章他请森安先生提意见,包括那两个地名在内,得到这位既是摩尼教、又是西域史地专家的学者的认可。后来2014年8月森安先生应邀到柏林讲学,题目是《东部回鹘摩尼教史的新发现》(New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Uighur Manichaeism),提到2009年这项重要发现时,他用了Zieme-Wang-Fragment(“茨默—王某残片”)这个词,恐怕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体现了他对这件文书在摩尼教史上的重要性的定位,至于对我的过奖,只是顺带鼓励一个学术后来人,我既感且愧。茨默先生当年建议这篇论文由他和我共同署名,我坚持只承担译者的责任,因为文书缀合、释读是茨默先生独力完成的。这篇论文的顺利发表也受到《敦煌学辑刊》的大力支持,特地安排版面,把这篇文章排为当期第一篇。责任编辑是老友冯培红教授,他不厌其烦,细心处理,让我读校样前后凡七次,最后把国内出版界一般不做特殊处理的音标字母和语音符号(diacritica)都按国际规范处理得完美无瑕,帮助我们圆满、按时完成了吐鲁番文物局与东洋文库的合作项目任务,留下美好的回忆。借此机会,再次向《敦煌学辑刊》表示感谢。
茨默先生在中国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不仅从事突厥语、回鹘语的同行学者奉他为泰山北斗,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也都注意阅读、吸收他多方面的成果。因为耿世民教授的邀约,茨默先生曾到中央民族大学讲学几个月,座中不仅有本硕博学生和青年教师,还有在京其他学术单位的资深学者。
2012-2017年我在中山大学任教,其间两次邀请茨默先生专程到广州讲学。第一次的题目是《摩尼教〈下部赞〉的回鹘文本》。第二次的契机是中大要筹备九十年校庆,举行“国际大师前沿讲座”,校办要求我出面邀请“(诺奖级别的)国际大师”来校讲演,计划的十二次当中,文科分得两三次。我不知文科学者中有诺奖获得者,只能请身任多重院士、德高望重的茨默教授出马支持。他选择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字与语言多样性——从无名氏到安藏:10至14世纪古回鹘语的例证》(Multiscriptality and multilingualism on the Silk Routes. From Anonymous to Anzang—Old Uyghur examples from the 10th to 14th centuries)。讲座在锡昌堂大讲学厅举办,那天欣蒙蔡鸿生先生莅临担任评议嘉宾,讨论精彩,校内外听众反响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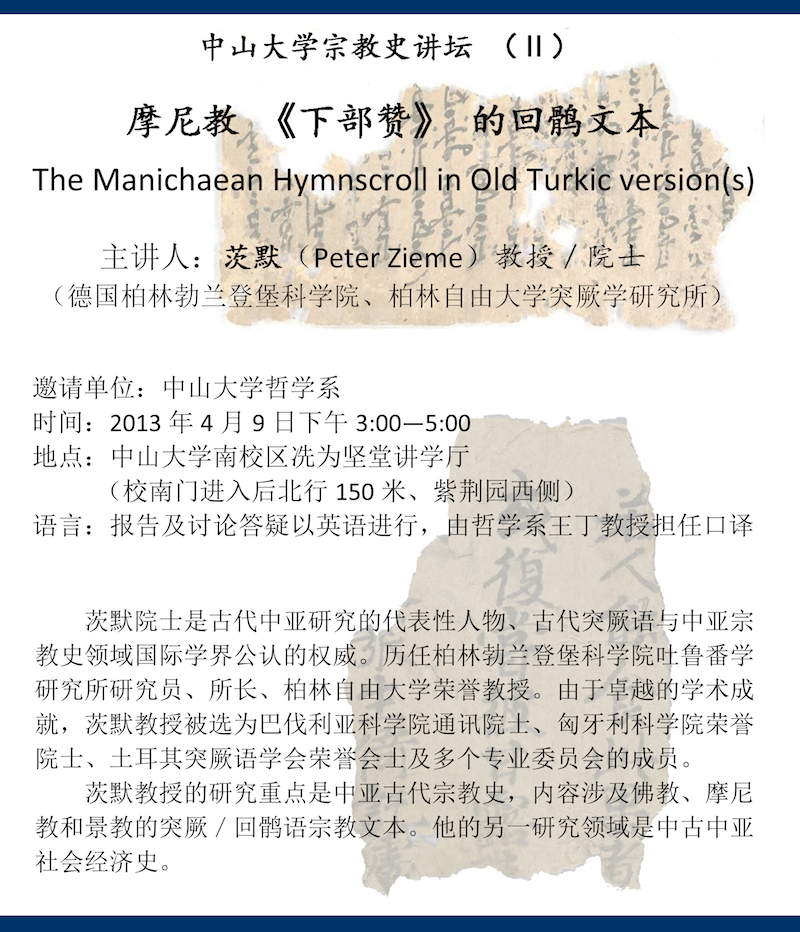
2013年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学宗教史讲坛”的讲座海报

蔡鸿生先生、茨默先生、张小贵教授
中国有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邀请过茨默教授去讲过学,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信息,形成一个完整的“茨默学术在中国的流传”表单。
由宗德曼教授与茨默教授于1995年共同创始的“高昌讲座”(Collegium Turfanicum,国内学界又译为“吐鲁番学讲座”),邀请国际专家前往柏林科学院交流、讲演,目前已举办了九十四届(http://turfan.bbaw.de/collegium-turfanicum-en),历年来受邀的中国学者有荣新江(12th,2001)、王丁(15th,2003;64th,2013)、段晴(33th,2008;84th,2016)、庆昭蓉(36th,2008;70th,2014)、王建新(38th,2009)、李肖(49th,2010;58th,2011)、罗新(77th,2015)、陈浩(81th,2016)、付马(83th,2016)等。最近公布的第九十五届讲座的主题是纪念老所长茨默教授八十寿庆,同行学者雅聚联欢,晚辈同人饮水思源,十分恰当。倘若届时国际交通恢复,可以想见一定会有很多远道的学者也去参与。

森安孝夫在德国柏林科学院第七十二届高昌讲座上,茨默教授主持,右起第三人起:Röhrborn、Sander、Schwartz、Raschmann、Wilkens等(2014年,http://turfan.bbaw.de/bilder/collegiumturfanicum2014)
茨默先生的学术贡献
茨默先生精通多种古代中亚语言,也通古汉语,这方面的能力帮助他解决了很多突厥回鹘语特别是佛教经典的困难问题。在世俗文书方面,他也有非常精彩的发现,如对来自汉地民间的“五更转”回鹘语译本的勘定。尤其令我钦服的是,他在一组很小尺幅的残片中发现有《管子》的回鹘语译文,这个难度非常大。
吐鲁番文书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宗教内容,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三大领域茨默先生都下足功夫,逐一攻坚。因为他博士论文做的是回鹘语的摩尼教文献,在1974年还出了一本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的合集,对这方面的上百件文书做了全面的搜集、鉴别与释读,书后附文书图版,成为学者必须参考的基本文献。佛教残篇是他下功夫最多的领域,著述也最多。景教材料相对较少,难度更高,在这方面,茨默先生是世界范围内对吐鲁番景教研究最多的学者,集大成之作为201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亚出土的古突厥语东方教会文献》(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eorgias Press, 2015)。
茨默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无法详举。有两个特点也许可以提出来,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详。一是他的著作具有科学性,一种具有可检验性的实证科学性。他的论证从来都单刀直入,不反复假设、迂回论证。我想这也许跟他最初选择化学作为专业有关,这种理科素养贯彻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结果只能是提高文科研究的精确性。这一点,是在我回头看当下很多文科著作时感触尤深的,森安孝夫教授也提出“理科史学”这样一个类型,可为实证派文科学者的纲领。二是他有发现而后作文,所以每篇文章要么是公布他作出解读的材料公布,要么是老问题的新解说。这其实也是自然科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没有求真务实的诚心实意,只是故作摇曳,纵有宏大叙事之势,无攻城拔寨之实,到底是不能在科学的专利局存下获得批准的发明的。
年齿愈尊,文章愈短,虽短而味深,小中却见大。这似乎是一条学术定律,在茨默先生身上也有体现。他治学六十载,全部吐鲁番回鹘语残片都印刻在脑海中,很多问题一直萦绕于心,真积力久,往往一朝宿疑顿解。我喜读这些精彩的短篇作品,做过一点翻译,如《古代突厥人的酒》(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突厥语Sart一词流变考》(Sart即“萨宝”;许全胜等主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古突厥语的纺织品名称》(尤小羽译,王丁校,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五辑,2020年),其他如《香炉考》《项链考》等名物考证诸篇均是,有必要一一译出,结集出版。
茨默老师
身为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茨默先生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写作、策划德国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合作项目。他也一直跟高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教课,这也是由洪堡倡导的科研与教学并举的传统,在大学一方应有志于研究,在科学院一方应联系教学实际,把最新的成熟成果传递出去,培养学术新人。1994年起,茨默兼任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段时间还代理过突厥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浩老师曾经从学于茨默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吐鲁番出土的数术文书整理研究,导师是冯孟德(Erling von Mende)教授,论文写作则是在科学院完成的,当时跟宗德曼先生听伊朗语的几门课,另外也为准备景教研究的基础,学了拉丁语和圣经希伯来语。茨默先生学术兴趣很广,他往往是先不耻下问,问我一些古汉语的问题或者我貌似熟悉一点的东西,其实他对那些问题已经有相当的研究、探索,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印证或更多的例证。久而久之,我跟他渐渐熟悉,到后来他甚至建议我不再称他Herr Zieme,直接指名不道姓,叫他Peter。这一点我至今都做不到,但不敢完全违命,所以采取折衷方式,先称Peter,之后说话、行文仍然用“您”(siezen),绝不敢说“你”,毕竟他是我从前敬畏、现在敬爱的师长。满族人、北京人在家里对长辈不也是都称“您”吗?
我的博士论文序言花了一些篇幅写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到过的新疆南北道各处遗址,这类在外人属于不太容易掌握的冷知识,地名之小无处查考,何况还是用拉丁字母转写。但在未刊的德国探险队档案里有很多相关材料,可以比勘确定。这些遗址体现在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早期整理者制定的“发现地编码”(Find-Sigel)中。写作这个部分,得到科学院吐鲁番所几位师友的大力帮助,其中以茨默先生、宗德曼先生赐教最多,毕竟他们对经手的所有文书都了若指掌。宗德曼先生的论文《以语言文献学的手段完善、补正考古工作:吐鲁番文书的个案研究》(Completion and Corr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Work by Philological Means: The Case of the Turfan Texts. In: Histoire et cult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P. Bernard, F. Grenet eds., Paris 1991, pp. 283-288)就是使用这类信息而写成的。茨默先生也经常以发现地编码作为参考,推证文书出土地与文书内容的关联。
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时常给茨默先生看一些部分,请他提意见,后来就成了习惯,让他都看,再后来他干脆说,你把写出来的尽早给我看,这样来得更快。我发现,他这样做,对学生最大的好处是:有错尽早改正,免得一路写下去,重复同样的错误,或者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包括德语表达错误,几百页非母语写作者的论文,改下来是占用了他很多宝贵时间的。偶尔有德国人对本人的德文德语予以谬奖,我心里知道,茨默先生也义务承担了语文老师的角色。
我的第一篇吐鲁番学习作《Ch 3586:契丹大字残篇考》也是在茨默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文书中夹行书写的回鹘字是由他协助释读的。当时在柏林科学院客座访问的卡拉(Kara György)先生也是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一起讨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笑话:我的契丹材料都存在电脑里了,到哪里都跟着我。也许哪一天梦里福至心灵,我突然就懂契丹语了。你的发现重要,继续努力,破解语言,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卡拉先生是李盖提教授的学生,也就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能够有机会在科学院、在茨默先生那里接触到东方学的正脉,我深感欣幸。
最近两次见到茨默先生,一次是2018年6月在日本,一次是2020年6月在德国。从2012年到18年,茨默先生因家人在日本工作,他也随同常住日本,展开了繁忙的退休后工作期,也是他的一个学术高产期。临近告别东京的时候,东洋文库梅村坦教授准备办一个送别活动,给我来邮件,建议我去给德国和中国同人代个表,顺便在东洋文库做一个讲演。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坐飞机去听茨默先生的Farewell Speech,会晤日本师友。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讲座那天,不仅有主人梅村教授热情主持,气贺泽保规教授也到场指教,老朋友松井太教授甚至特意多在东京停留两晚,等待这个活动举行。那次我讲的题目是《屏南文书的发现与摩尼教研究》,也在圆满完成这次讲座任务之后,迅速成文,将全部材料完整发表,以答关心这批新材料的国内国际同人。
2020年柏林再见茨默先生,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已身染重疫,德国也是半封闭状态。打电话的时候,我得知茨默夫人不甚愿意他出门,因为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注射疫苗。他执意要进城会面,遂骑自行车到轻铁站,乘车进城,会面地点是老地方:寿司店。餐后,他建议我们一起去科学院看看。他退休后仍然时常去研究所,还有门卡。我们从后门走进去,办公室走廊都是黑的,古老永动的Paternoster电梯也终于停歇不开了,我们从楼梯走上去,到了研究所,看到还在办公室坚持工作的Alisher Begmatov博士,握手寒暄,互道珍重。
茨默大师
前些年,在一次《上海书评》的访谈(《高田时雄谈敦煌学》,2009年2月22日)中,高田时雄先生对国际敦煌吐鲁番研究曾做过一次巡礼,以往百年早着先鞭的东西方各国情形不容乐观,“日本搞敦煌学的越来越少,应该是与日本汉学的衰落趋势有关。其他国家也差不多,英法就是,因为他们的敦煌学主要是为整理、编目的必要兴起的,这个工作做完了就没有了。欧洲几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还好”,德国似乎一枝独秀,所指的正是宗德曼、茨默两位大师开创的Turfanforschung盛业(在国际学界,敦煌学、吐鲁番学是不分家的,即使在只提敦煌学这个名目的情况下,吐鲁番研究也是包含在内的),不仅编辑出版目录(《德国藏东方写本注记目录》Verzeichnisse 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HD的伊朗语、突厥回鹘语等语种的吐鲁番写本系列)、专刊(《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erliner Turfan-Texte/BTT),还在柏林科学院设有专门的吐鲁番学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BBAW)以及挂靠德国几所高校或科学院的写本编目分支机构。由英国发起、多国参与的“国际敦煌学计划(IDP)”数字化项目,就完成程度而言,德藏部分最为完整,维护精良,得到好评。这是德国“工匠精神”的一个体现,“德意志彻底性”(季羡林先生对deutsche Gründlichkeit的译法)的实例。
茨默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成就之大,成果之既高产又卓越,不免令人有仰望宫墙之感。作为多年追随他读书问业的晚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他的勤奋有恒、下扎实功夫,是令我这个“年轻人”既佩且愧的。他已是欣开九秩的老人,每天依然抓紧做功课,任何事情都不在手头停留,尽早一次性完成,就一个问题,往往在一天之内数次邮件往返,不落实不止。发邮件给他,最迟是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复,除非碰上周末,他是基督徒,遵守风俗,周末一般略作安息停顿,所以仍然是有恒的。
茨默先生向我不止一次说过,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探访河西的萨里回鹘故地。这还有待实现。在民大讲学期间,他曾利用周末时间和意大利学者Pierre Borbone前往泉州参观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两位不谙汉语的外国教授在机场打车,几几乎没有一个司机知道摩尼教草庵所在,所幸最后出现了明白人,协助指点路径。此行来去匆匆,未能参访其他遗迹。近年闽东地区的民间写本中发现的大量摩尼教因素,也在第一时间引起他的兴趣,并于2013年命我在柏林科学院的“高昌讲座”(Collegium Turfanicum)做过一次介绍(Neues zum Manichäismus in China)。蒙元时期吸引了众多高昌回鹘人的东南地区还是茨默先生不甚熟悉的。我希望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封闭、阻隔状态快快解除,好让他能尽早重访中国,从泉南到天山,我陪他好好走一趟。
2022年4月19日是先生的八十华诞,诚愿仍骑二八横梁大自行车、仍然耳聪目明、仍然高产、仍然与时俱进频繁更新他在国际网络学术平台academia.com账户并在此首发论文的福乐智慧茨默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Sadu sadu qutlug bolzun!
附录:茨默教授简历
茨默(Peter Zieme),国际著名突厥学家,古代突厥语与中亚宗教史学者。1960年至196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主修伊朗学、突厥学,1965年至1969年在民主德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1969年获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留科学院东方所工作。1970年进入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学中央研究所古代东方室工作,1993年转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2001年至2007年间担任该所所长。1994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法国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土耳其突厥语学会荣誉会士、英国学术院院士及多个国际学术专业委员会成员。
研究重点是整理研究中亚发现的各种文字书写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文本,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主要是公元九世纪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时期)。另一研究领域为回鹘语社会经济文献与词汇学。主要著作有: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摩尼文字书写的回鹘语文献》,1975年);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密教回鹘译本残篇》,1976年);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回鹘佛教的押头韵诗》,1985年);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1992年);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回鹘文本〈金光明经〉序与第一卷》,1996年);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回鹘密宗文献》,2005年);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ählte Schriften(《回鹘佛教碎金——茨默论文集》,2009年);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亚出土古代东方教会回鹘景教文献》,2015年)等,数百篇用德文、英文、法文、日文、中文、土耳其文撰写的论文与大量书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