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桂丽:“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
1917年,李文糺在《读越缦叔<杏花香雪斋诗稿>感赋》中云:“天未丧斯文,或不成秘箓。”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2期,即围绕越缦堂主——李慈铭展开。
4月8日19点,读书班通过线上方式正式举行,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桂丽研究员受邀主讲,题目为《“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评议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研究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谢冬荣副馆长,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潘静如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主讲人发言整理稿,末附评议人发言稿。
张桂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出身,在辑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的过程中,略有一些感悟。今天就围绕着他的日记、交游、读书活动,与大家分享他作为学者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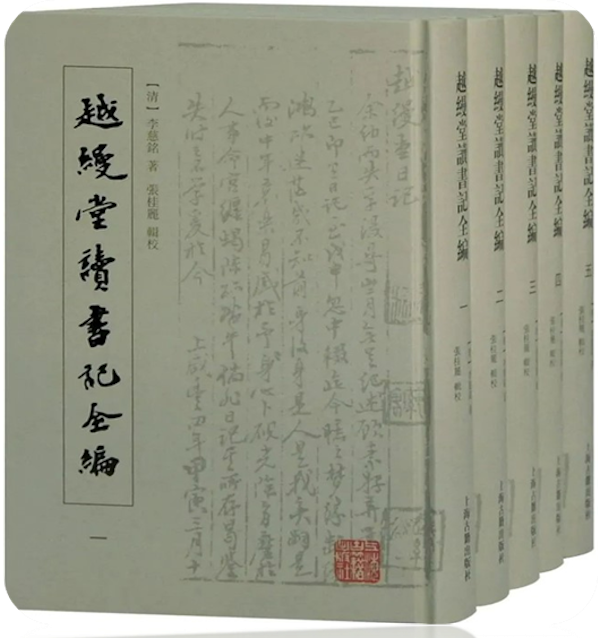
李慈铭著,张桂丽辑校:《越缦堂读书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一、李慈铭日记的传播与影响
今天讲座的题目“日记百年万口传”,出自曾朴《孽海花》。这部历史小说以实际人物为原型,塑造了一批晚清人物群像,前六回由金松岑撰写,对李治民的描述为:“赋诗填词,文章尔雅,会稽李治民纯客是一时之杰。”第七回后,均由曾朴撰写。曾氏在最终回写道:“现代的诗,除了李纯老的《白华绛趺阁》,由温、李而上溯杜陵,不愧为一代词宗。”首尾呼应,完满支撑了金松岑对李治民的人物形象设计。
曾朴因父亲、自己与李慈铭的交谊,写李氏有深刻的生活基础,也异常出彩。小说第二十回通过大笔墨描写李治民的生日宴会,地点在满族官员盛昱的“云卧园”。当时盛昱遍请京师名流,讨论学问,抽签联句:
云卧园中开琼筵(薆云),群仙来寿声极仙(怡云)。华山碑石垂千年(李文田),《周官》精椠北宋镌(汪鸣銮)。经幢千亿求之虔(叶昌炽),耕烟百幅飞云烟(张垲征)。《然脂》残稿留金荃(王懿荣),马湘画兰风骨妍(江标)。汉碑秦石罗我前(端方),绿毛龟伏玛瑙泉(缪荃孙)。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续南北史艺文篇(文廷式)。陈茂古碑我宝旃(沈曾植),影梅庵主来翩翩(盛昱)。黑头宰相命宫填(林旭),长图万里瓯脱坚(洪钧)。共祝我公寿乔佺(素云)。
这首即兴之作,即是要求诸人“炫宝”。琳琅满目,任何一件都价值不菲。李治民因贫病交加,只好吟一句写实的“日记百年万口传”,却也赢得了满堂喝彩。我想,这句话当源于曾朴对李慈铭及日记流传情况的一种理解。
《越缦堂日记》位列“晚清四大日记”之首,积四十年之力而成。李慈铭在二十四岁写作时就规定了日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国之大事、读书笔记、友朋交往、个人诗文作品等。民国间日记影印出版后,风靡一时,几乎成为与《孽海花》一样的畅销书。不过,日记并非获得一致好评。鲁迅先生对这位乡贤的日记颇不以为然,他说:
《越缦堂日记》近来已经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自以为一部著作”,正点出了李慈铭以日记为著述的特征。因为李慈铭打破了日记的私密性,写作时字斟句酌,难免有矫情做作之嫌。

李慈铭小像与《越缦堂日记》书影
郁达夫、周作人喜欢读日记中闲适、性灵的文字,胡适则认为这部书内容纪实,读书札记、时事价值很高,并为之题诗九首,其中二句云:“四十年前好人,后人切莫笑话”, 颇可以反映部分学人对李慈铭的态度。因李慈铭日记中会写如与歌郎厮混,与妓女假戏真做的内容,并暗戳朋友的阴私,骂不称职的官员,秉笔直书,毫无畏惧。
同时,有些读者认为日记有涂抹或隐匿的部分,难以称作信史。或称李慈铭与歌郎厮混,不注重学者形象。或批评他脾气大、爱骂人,对同时人出言刻薄,可谓毒舌。如果过度关注这些负面形象,自然对李慈铭日记及学问便不是那么的肯定。如钱钟书说道:“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张舜徽亦言:“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言辞过激,近乎攻击,已经不属于学术范畴内的讨论了。

周作人(1885-1967)和胡适(1891-1962)
现在距离日记出版,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李慈铭生前自诩的“日记百年万口传”,倒也真的实现了。然而这位百年前的名家、大家本人,并未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读其日记之人,不乏猎奇隐私者,或仅摘抄史料者。能持一份同情之理解,带点温情与敬意者,并不多见。台湾学者蔡长林在《长日将尽,典型夙昔——李慈铭学术批评中所见的乾嘉情怀及其意义》一文中,以充满同情与敬意的态度,深入探析了李慈铭的学术情怀与精神寄托,我认为很中肯、到位。
马忠文老师说过,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最好的方法。作为非历史专业的人,我对晚清历史的略微了解,也正是通过十多年来阅读、点校李慈铭日记积累起来的。
二、与张星鉴、桂文灿的交往、切磋
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名师名弟子一学数传及家学传承几代的繁荣景象,比比皆是。道光以后,世局多变,战争、天灾频仍,学者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挑战。经学衰败,但经师仍不乏其人,如著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邵懿辰在咸丰初年回乡,于杭州闭门著书。期间李慈铭曾两次至杭州省城考举人试,也曾去游玩,与这位学问、风节名于时的乡贤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因为他彼时志不在此。
咸丰四年(1854),李慈铭和越中文学青年成立言社,沉潜于歌咏美人香草,即便是与同龄、同城而居的学者平步青、傅以礼二人,也毫无往来。面对谭献的拜访,他仅以诗歌相切磋。咸丰九年(1859),因科举考试不顺,李慈铭出资捐京官。到北京后,他继续与言社的陈寿祺、周星誉、周星诒唱和诗词。后来因和周氏兄弟决裂,他便脱离了由乡情、文学活动维系的交际圈,转而投身钻研学问。
李慈铭对各地宿儒名师了解得并不真切,但只要友人官某地,他的关注点便触及到某处。他的考察方式,除了借接风、饯行之诗酒文会向以科考、述职等事入京的朋友们当面请教外,还与他们殷勤通信,询问当地的学林掌故、刻书编书、学术风气等讯息。
我最近辑录了李慈铭的书信集,大约八百余通,其中不少内容在长篇累牍地交流地方学风、访求宿儒著述。通信者如浙江学政瞿鸿禨、江苏学政王先谦、四川学政朱潮、湖南学政陶方琦、浙江书局校勘陈豪等等。这些书信不能简单地视作李慈铭维系社交的手段,了解学界动态,才是他意图所在。如平步青在江西任官,即将江西刻书如《明通鉴》《国朝文录》等书大批邮寄给他。因缪荃孙曾在成都张之洞幕府,关于川蜀藏书、刻书及学人情况,他也能随时咨询。又因门人吴澂夫在上海,上海新印书籍常能送到他手中。此外,李慈铭还通过贵州学者莫友芝了解了郑珍,通过王先谦了解了湖南学人邹汉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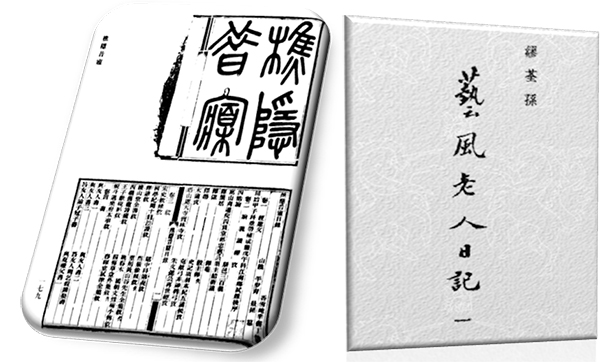
平步青:《樵隐昔寱》;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
对文献渊薮江苏、浙江两地,他更时时关注其间藏书楼、著名学人、名著稿本之流传、版刻之保存等情况。当太平军占据浙江时,他从江南友人处多方打听文澜阁《四库全书》、天一阁、振绮堂、八千卷楼等藏书的现状。当得知经师陈奂病卒于乱中,他不禁感叹到“江南经术尽矣”。而听闻顾河之在兵乱中去世,他亦为顾千里绝嗣而唏嘘良久。
李慈铭对域外古籍、学人十分关注。日本学者岡千仞来游中华,曾亲自拜访他数次,并以所著各国史书相赠。日本书籍如《难经疏证》《大唐六典》《古逸丛书》《日本新出玉篇糸部》等等,李慈铭也阅读评论过。他还向沈曾植借《蘐园随笔》,从许景澄处借日刻《大藏经音义》等书。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随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曾写信给李慈铭,详细告诉他汉文古籍在日本的流通情况。外交特使傅云龙自日本回,也以所著、所刻书相赠。同时,他与朝鲜学者也有交往。同治十一年(1872),张之洞与周寿昌、董文焕、吴大澂等人宴请朝鲜使臣闵致庠、朴凤彬,李慈铭向其询问国王李氏二十八世谥号、名字,藉此录成《朝鲜国王谥录》,并以《越三子集》回赠。
尽管彼时信息传达较为不便,但李慈铭凭借广阔的学术视野,强大的朋友圈,及时掌握了学林大事、学风动向。最为重要的是,他将自己所了解到的学术信息一一记录在日记里。在关注古籍的刊刻流传外,他也关注金石碑帖、器皿的收藏,学人存亡、学风动向,域外汉籍及学人。这些内容,在传统学术史的宏观叙述中被无意或有意忽略,反映的却是真实的细节,是认识、分析复杂学术场域的极有价值的史料。李慈铭与张星鉴、桂文灿的交往,也很好说明了这点。
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正式与张星鉴结识。张氏曾以《刘礼部集》相赠,并慨借各种书籍。二人年龄、经历、学术旨趣接近,故而能惺惺相惜。同治二年(1863),张星鉴丁父忧,李慈铭为其父写家传,张氏则赠以孔氏微波榭《国语音》《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而后张星鉴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以顾炎武为首,收录一百三十人。李慈铭亦着手编纂《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同样以顾炎武为卷首,总计收录一百六十五人。可以推测的是,他们在编纂二书的过程中,应该有过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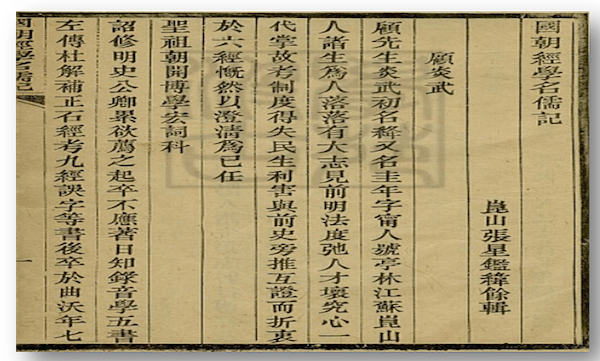
张星鉴:《国朝经学名儒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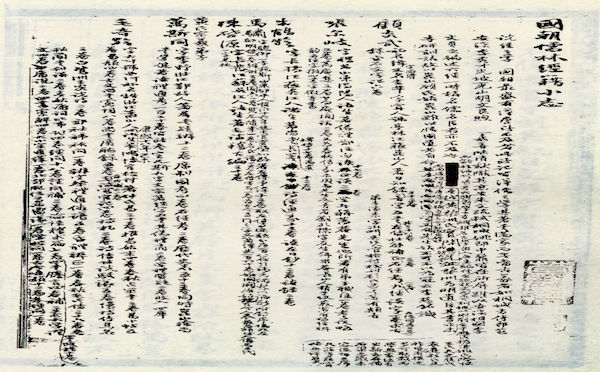
李慈铭:《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
张星鉴关注过桂文灿,藏有桂氏《诗笺礼注异义考》,并与李慈铭分享阅读。在桂文灿所著《经学丛书》进呈后,潘祖荫曾将《孝经集证》《群经补正》两种转请李慈铭评阅。李慈铭对此有知音之赏,称桂文灿“禀承汉学,著述褒然。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惜未值其时,恐终无当耳。”
当时李慈铭正坐馆于礼部尚书周祖培家。近水楼台,李慈铭对朝中风向、旨趣比较了解。同治初年,外有封疆大吏曾国藩、朝有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俱称理学名臣。学界内部有方东树、姚莹之攻击汉学。此时选择汉学,意味着逆流、孤立、落寞。故他断言桂文灿不能得到赏识,其后果然验证。可见,在同治初以乾嘉汉学之法治经,并不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褒扬。
同治二年二月,桂文灿入京应试来访。因神交已久,二人得以促膝长谈。遗憾的是,桂氏落第。回到广州后,他写信给李慈铭,寄到徐灏《通介堂经说》一书,并告诉好友《学海堂丛书》的刊刻情况。李慈铭在回信中回顾自己治学历程的同时,还表达了对桂氏、徐灏的崇敬,并请他留意乾嘉间粤中第一学者陈观楼的著述。这种广东、京师间的互动、交流,对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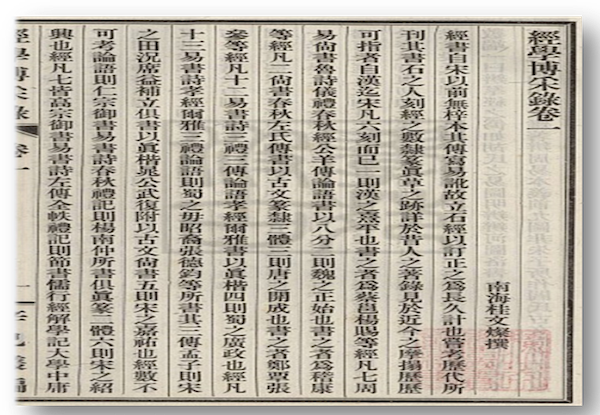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
早在咸丰五年(1855),桂文灿便编成了《经学博采录》一书,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经学名家,始于惠栋,终于顾千里、陈树华。我曾经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即从桂、张、李同时对本朝经学总结这一点切入,将《经学博采录》《国朝经学名儒记》与《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合为一编,并将三人于同治年间的交往、切磋资料作为附录。此外,赵之谦也撰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依江藩体例,专人专记。从学术史角度考虑,这四种为经师立传的书,可以视作对同治朝黜汉、尊宋经学政策的回应,对淡汉、反汉学风的反击。
三、阅读:由文士到学者
张星鉴师从陈奂。陈奂是段玉裁的高足,精通毛诗,著有《毛诗传疏》。桂文灿则师从南海陈澧(菊坡精舍山长)。陈澧主张汉宋兼采,撰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张、桂二人,因师承经学大师,较早树立了治学目标。相比之下,李慈铭并无师承。他早年读书,以博雅广识为中心,又好词章,不仅没有专研一经一史,在三十岁之前也没有读过《说文》《十三经注疏》,治学起步很晚。
捐官北上后,李慈铭见闻日广,常至琉璃厂阅书、访书,为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染。同时,他也接触到桂文灿的经学著作,又与平步青、张星鉴、黄以周商榷经史,开始专心治学。但这个选择充满了艰辛。
首先,在汉学衰败的情况下,仍用乾嘉汉儒的方法来研究经史,意味着逆流,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李慈铭也意识到:“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其次,李慈铭是在个人穷途末路之时展开治学的实践。在物质匮乏之际读书治学,尤其令人敬佩。同治四年正月初二日(1865年1月28日),他专心于考索《说文》,以至于不见来拜年的各位友朋,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天气温煦,如江南早春时,彻炉闭门,终日营营考订经义文字,颇有所得。献岁之际,车马如云,而作此生活,拙懒迂僻,京华软红尘当无第二人矣。”
张舜徽先生曾反复阅读李慈铭日记,认为其专心、努力的程度远未达到学者的标准,他在《清人笔记条辨》卷九云:
李氏少时偃蹇乡里,徒骋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卷轴,为日无多,故于朴学家坚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清史稿》置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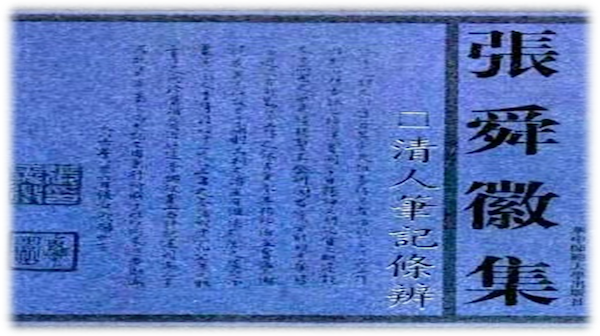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少时家居,以词章闻名,“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诸句,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放纵于酒色,不必为之讳言,但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而“亲迩卷轴,为日无多”一句,并不符合事实。张先生对李慈铭晚年读书曾予肯定:“知其晚年学进气平,持论乃迥异于昔矣。”不过大概没有看到李慈铭最后四年的日记,那时他的学术论见更为精当。总的看来,张先生对李慈铭的评论,肯定少、批评多。戴海斌老师之前深入剖析了先生对李慈铭学术的评价,客观允当,我个人深以为然。
综观清代学术史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在青年时代热衷于作诗作词,而后才专心治学。而学者往往,尤其是在乾隆朝开四库馆时,要比诗人获得更高的认可、更多的机会。虽较早确立了诗人的身份,但李慈铭有着强烈的自我预设。虽热衷于宦途,但读书治学是其立世的终极目标,谓“古今无学问外之人才,天下无读书外之事业”。又因中年后转行治学,他深知由文士到学者之甘苦,故不大喜欢姚鼐,曾批评到“姬传本文士,而妄思讲学”,也不喜欢文士兼学者的袁枚、翁方纲以及朋友谭献。不过,他对他们的批评,颇能深中其病。
李慈铭对向学之晚有切身之痛。实际上,对秉持“词章乃学人之游艺”的他来说,孜孜以求者在于经史,也更期望入儒林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绝对的自信。如他在《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曰:“是儒林耶?文苑耶?听后世之我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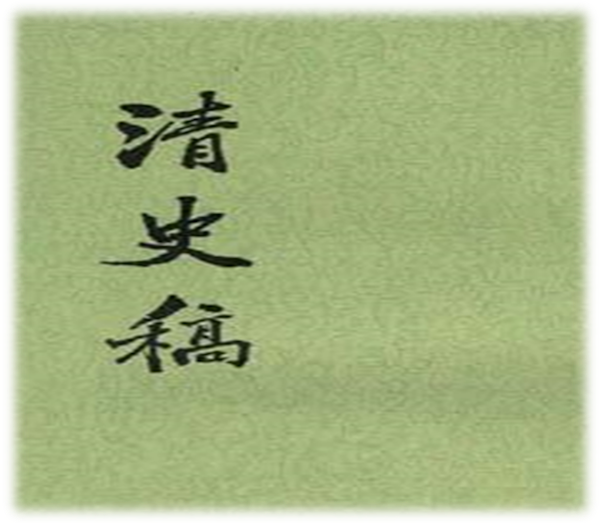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清史稿·文苑传》共收录354人,正传105人。李慈铭位于《文苑三》,传文出缪荃孙之手。能入文苑,本已难能可贵,但总让人意难平。因在重儒轻文的时代,入儒林要高等一些。同时,“文苑”并不能准确定位他们的实际身份,大概只表明各人在文学创作上更胜一筹而已。
李慈铭曾在《说文》上下功夫,但并未成书;也致力于史学,曾与王先谦就《汉书》往复探讨,对《宋史》《明史》也有论断。但他批校的读史札记散在数百册藏书上,并未经整理,直到后来才由王重民辑录成书。按照当日入选《儒林》的严格标准,他确实是不符合的。尽管如此,李慈铭的名气不可谓不大。在民国期间,由于日记的影印出版,读书笔记、读书札记的陆续出版,他始终都在学者的研究视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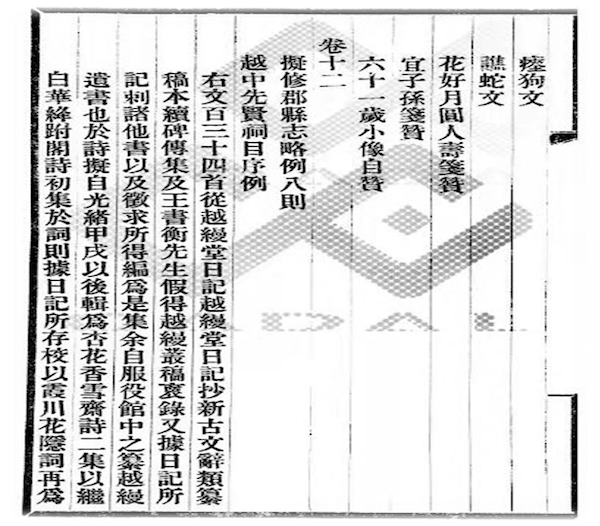
王重民:《书<越缦堂文集>目录后》
在认真、谨慎地考察李慈铭的治学过程、学术成绩后,我们可以说他实现了由文士到学者的学术追求。在评论历朝诸家学术时,他驾轻就熟,笔锋犀利,极为自信,所展示的不仅是阅读之勤、涉猎之广、识见之精,其批评天赋也超出时辈。在批评过程中,他注重版本、校勘、考证,秉承汉学家的旨趣。从他的品评持论来看,他极力维护汉学,但也能站在汉学传人的立场上,深刻检讨汉学流弊,批评汉学家好博,有别裁之短,且缺乏经世的追求。
这部《越缦堂读书记》,主要考察的是学者、专著之得失优劣及其当下意义,其内在理路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评论对象褒多贬少,能平情论之,肯定本朝的学术成绩。同时,李慈铭对学者文章才气的重视,反映出了他的文士本色。而能以一己之力完成对众多经史子集的评论,李慈铭实为不间出之学人。
另外,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李慈铭在对学者反复批评时,其实又不自觉地在某个侧面深受其影响。如姚鼐、章学诚,都是他深刻批评的对象。但姚鼐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一体的文章追求,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批评原则,又与他的治学旨趣甚为契合。这些影响,在读书笔记中也有体现。
在辑录李慈铭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我首先确立了编年体的体例。因为日记体的读书笔记带有印象性、即时性、原始性等特征,四部分类实在不能反映他的阅读历程。李慈铭的阅读是开放式的,随读随记。依其原始的日记体或者说编年体例,最能反映其阅读世界。同时,他的读书笔记有别于面对大量藏书而集中书写的评语,以及如馆臣那般撰写的提要。其次,经过历史的沉淀,当时不被作为学术笔记的内容,如记录的朋友们的著述,大多是稿本,或者只是单篇的诗文。虽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那么瞩目,但若被忽略,难免遗憾。再次,将札记、学林掌故、名物考证收入日记,这种日常的敏锐的积累,也是学术活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片段。在先前出版时,由于历史原因书里删去了对镇压太平军的官员学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著作的评论。在目前环境下,自然不能重蹈覆辙。
在考察学者理性学术评论的同时,我们也应了解他的感性世界。李慈铭读书有天分,这是毋容置疑的。他虽然多病,但精力充沛,又极为自律,处世真挚,古道热肠,是个老好人。受咸、同、光三朝内忧外患的影响,跌宕于世运中的文人,因为科场、官场的不得意、朋友的背叛,逐渐变得偏执、苛刻。这也是历史上清代浙东学人的精神特质,如毛奇龄、章学诚等,都有刻薄、爱骂人的一面。因而在李慈铭读书笔记中偶尔出现的目中无人的狂傲和品评失准,属于概率较小的失误,不应将之标签化。
总的说来,李慈铭距离我们并不太远。我们对他的理解也并不那么充分,容易流于掌故、猎奇的评价与认知,容易为既有成论左右,对其著述缺乏深入精读,未能在学术视野上有所拓宽,从而难以发掘出新的历史意义。因此,处于资源共享优越环境的今日,除了在历史文献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查、发掘,我们的学术视野、眼光也要与新文献、新热点匹配,努力去开展沉浸式的阅读,去捕捉更多的细节。我相信,以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将会更符合历史语境。

鉴湖边李慈铭塑像
评议人发言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老师今天这个报告非常全面、深刻,这与她十多年来投入的精力和花费的功夫有直接关系。我本人收获很大,这里主要想讲两点感想。一是怎么去判断和分析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二是对新版《读书记》的编排方式谈一点看法。
首先,这本日记跟一般、别的日记不同,李慈铭不仅仅把它当做日记来写,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有创意的作品来写。最关键的是,他从一开始或者在早期时候,就有意无意地把日记散布出去,让大家来传抄。这就有别于我们一般理解中日记私密性很强的印象。可以比较一下,像翁同龢、胡适这些人,可能都有将日记传世的想法,但在他们生前,大概很少把日记拿给外人特别是那些不熟悉的人看(胡适生前只是出版了《留学日记》)。李慈铭却恰好相反。
李慈铭这样做,与他个人经历和处境大有关系。他是以捐官形式进入京城的,沉浮郎曹,十分艰难。在北京不但要生活,还要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解决举人和进士这两道难关。所以,他比那些中了举人、进士,再到北京来做官的人负担更重、心理压力更大。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性格、生活都是有影响的,愤世嫉俗、狷介的性格由此形成。于是,他便借助日记中的臧否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日记中很少对他人有“恕辞”。
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李慈铭日记其实当时就参与和介入了现实生活。这种日记,成为研究的材料后,按照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的说法,可以称为“有意”史料。换句话说,李慈铭写日记,当年有很明确的目的。因此,如果我们想更完整、全面地了解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就不能把这个日记仅仅当做平面的、白纸黑字的文献,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立体的东西来看,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日记形成的过程。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常讲知人论世。所以在关注李慈铭日记的同时,也要关注他的生活,去看他的生活对日记的撰写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前张舜徽先生认为李慈铭读书做得不够深。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一种理解的态度来看。李慈铭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只是一个普通京官。和乾嘉时期那些脱离闹市、躲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不同,李慈铭虽然勤奋,也只是读书面非常广博而已,不宜用汉学家的要求来衡量他,何况,很大程度上李慈铭可能也有借此标榜和沽名的意思,毕竟他是一位名士。
众所周知,李慈铭骂人很厉害,大家都怕他。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做御史后,也参过孙毓汶这些权贵,词锋非常犀利。这让我联想到在光绪初年,李鸿章曾邀请他担任问津书院的山长。这件事给我一种感觉,可能李鸿章也不想或不敢得罪李慈铭,邀其掌教,也有借机笼络的目的(当然具体原因可以再详考)。再比如说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后来他把日记篡改了,将康有为换成了李慈铭,并写到“举世目为狂生”的评价。翁为什么不选他人而选李慈铭呢?恰恰说明在他的眼中,李慈铭狂傲是人人皆知,甚至代表了当朝显贵对李的基本评价。
说到李氏日记的史料价值,不仅要注意那些“有意”史料,也要关注当年李慈铭在不经意间写下的那些东西,因为无须加入自己的私人倾向,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史料。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同乡京官靠印结银生活的情况,和朋友们常去饮宴、听戏的饭馆、酒楼的名称、地址等,都是研究清末京城生活史的第一手绝佳材料。李慈铭是一个超级戏迷,他日记中留下来的大量的戏曲资料,对于现在研究京剧或者昆曲一些曲目的变化、剧目人物的角色,甚至是演员之间的代际流传等问题,都是大有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出版的《越缦堂读书记》的编排方式。我们知道最早的读书记,是由云龙先生是按类别来编辑的,他把对某一本书的所有记载汇在一起,每一条记载下面再补注读书日期,这样做不免淡化了日记的编年特点,其实是有缺憾的。日记按类分别编辑,不是从由云龙开始的。现在能够看到比较典型的是吴汝纶日记。他的刊本日记就是摘编的,没有时间,呈现出平面化的色彩,完全是资料汇编的形态。还有就是最近出版的《袁昶日记》,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根据类型分类的。这样编排,完全丧失或者脱离了日记材料最本质的编年特性,学者引用和分析时常常带来了很多不便。张老师这一次把读书记完全恢复成编年体的编排格式,采用文末附的索引来解决阅读书目同类检索。这种方式非常好,还原了李慈铭阅读某些书籍的先后时间与语境,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一些内在联系。这也是张老师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色。
谢冬荣(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关于后人对李慈铭的评价,张老师提到了多种说法,正面的、负面的等等。我这段时间在关注鲁迅弟弟周作人,发现他对李慈铭的评价非常高,说在众多乡贤中最推崇的就是他。那么,对同一个人,兄弟俩的看法并不一样,这也让人觉得李慈铭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较大的空间。
听完讲座后,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想法。一个是对于李慈铭日记,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原本。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当时大家经常一起抄,所以会产生多个版本。那我们在研究李慈铭本人日记的时候,还需留意抄本的情况。后者对李慈铭日记的研究也非常有帮助。因为李慈铭对日记的很多内容做了不少删改,特别是早期的日记。而可能有些朋友在删改之前,对日记已经有所抄录。从这一点来看,各种抄本有助于还原李慈铭日记的原貌,或者说是修改前的面貌。
第二个是民国时期,1928年的时候,北平图书馆购入了李慈铭的藏书。在李慈铭的书上,有很多的批校,包括藏书题记等。当时王重民先生对藏书题记、批校、读史札记等内容有过整理,撰写了专书和专文。后续对此比较关注的是王利器先生,著有《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及《续编》,记录李慈铭在谁的书上做了哪些批校等。这些其实能够反映李慈铭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但感觉关注的人不是特别多。或许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下一步的关注点,留意李慈铭对某本书的评价,他对这些书的批校、看法,或者说他对此做了哪些贡献等。
第三个方面是,之前有学者从阅读史的角度研究日记,讨论这些人读过哪些书,他为什么要读,他和当时人的读书观念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在张老师整理完读书记后,我们可以从阅读史的角度对李慈铭日记再做挖掘,关注李慈铭读过什么书,为什么读,然后评价是什么。
石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首先我对日记的感觉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跟它类似的物品有两个,一个是书札,另外一个跟版本学联系比较多,即写在古籍上的藏书题跋。
书札和题跋的情况跟日记相似。一种是作者在写的时候,不是太有兴趣,也不想示人。书信可能还有一个固定的收信人,而有时候写完的题跋,真的没有给人看的打算。另一种是有些书信和题跋,就是专门示人的。如一些作者在写完论学书札后,会马上找个刻工把它迅速弄出来,然后分发出去,这是常有的情况。至于题跋,古人有的时候喜欢晒书,或者找几个朋友来赏玩,那大家不免会看到书上的题跋,这也是一种传播形式。当然,可能其中有些内容是真话,有些是假话。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还有另一种题跋,就是请版本学专家或权威人物来执笔。背后目的很明显,或是为了增彩,或是为了营利等等。在书写的时候,他们大概对此也是心照不宣的。所以在利用史料时,如何去处理这么多种不同的情况,非常关键。
我的另外一个感受是,在厘清作者的意图外,对内容本身的梳理也很困难。比如李慈铭在日记中会提到看了什么书,又记过哪些书名。但那时候写日记、题跋或者写信,不像现在做古籍编目那样,遵循卷端、正题名之类的规范。大概写信只要对方能看懂,题跋只要自己能明白就行了。至于写日记,就更不用说了。
刚才好几位老师都讲到了阅读史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个人做版本学,就会去思考可以从日记中看出书的哪些特征或者版本信息,比如这段文字讲了哪些版本上的特征,可以供我们去判断。另外,有些书未必是当时写的,可能是前人的著作,最近被重新刻出,在朋友圈中流传。这样的记载对我们去了解各个版本的情况和流传速度,都是很有利的。
实际上,日记也是一个很好的校准工具。像我们有时候做编目,要写清道光三年某某刻本,好像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成书时间。那我们去看日记会发现,三年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因为前后拖了很久,或者标注的时间跟实际的时间有偏差。我以前看缪荃孙日记也有这样的感触。所以日记能够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当中去,让我们重新看到这些鲜活的细节。
最后,在使用日记时,也要特别小心。日记不像我们现在写的标准的学术论文,有完整的框架和清晰的论述。这就需要注意日记中那些没说、略过的话或者隐晦的言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仔细琢磨的。所以我觉得去研究日记、书信、题跋,真的会有不断的小发现以及好玩的点。
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整体的一个感觉是,李慈铭日记除了可用于他本人的研究外,可能还可以用于讨论近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清代学术史以及更早的文学史等。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也重新阅读了日记。最大的感触是,日记当中的“公”、“私”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首先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的论断,有一定知人论世的道理,这也是从“私”的方面来讲。同时我理解的“私”,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偏见和恩怨,还可以通向“公”的层面。就是说“私”虽然肯定有偏见,但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更关注这个点。因为一个公共事务,一个国家事务,它有无数个点。如果不处在这个位置上,你不会特意去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观察近代文学交流史的视角。
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李慈铭和赵之谦的恩怨,大概可以归结于私人是非。但有些私人事件,我认为还需放到近代史的公共层面上去讨论。以往在读某人的诗歌时,有条件的话,我们还会借助日记、书信之类的材料加以解释。那么反过来,把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和诗文对照使用,或许也能达到相得益彰的目的。我今天举的例子是关于晚清清流的,主要指前清流,即光绪初到光绪十年之间的这一波清流人物。从私人交游来看,李慈铭最熟悉或者比较早熟悉的前清流是张之洞。这一时期李慈铭日记的一则记载,反映了很多信息:
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病狂丧心,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看到这条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之前提到的李慈铭的个人经历。而结合郭则沄《十朝诗乘》中关于清流的记载可以发现,清流对当时官场生态有潜在的威慑,这也是李慈铭身处的一个大环境。我们如果只读日记这一条,当然可以认为李慈铭有某种功利心。但了解他立论的大背景后,便能明白这不仅是他和张之洞从交好到交恶的关系变化的反映,也体现了他对这种风气的不买账。
此外,李慈铭还有许多写于光绪初年的诗,如“方今时世重年少,弄姿搔首交称工”、“白面少年书累上,禁幄颇闻屡称赏”、“常僚骤擢跻公卿,或驰虎节莅百城”等,在我看来都指向同一波人,即前清流。当然诗歌语言,还比较玄乎,不能够一一去证实。但他的文章《暨艳论》则明确指向清流群体,其中言“昧者不察,汲汲以分别邪正为己任,无论其识之未必精,事之未必公也,即尽出于精与公,而惟恐世之不我知,悬一身以为众矢之的,而其祸不可胜言矣。”联系后来历史来看,李慈铭可谓是不幸而言中。
所以,将作为旁观者的李慈铭的日记、诗歌、文章结合阅读后可以发现,他对清流的看法,有“私”的一面,也有“公”的一面,呈现出交杂的状态。这对我们重新观察近代史上的公、私观念,或者晚清士大夫群体,是大有裨益的。反之也会促进我们去通过诗、文来升华他的日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