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石一枫:文学的精神就是反内卷(下)
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儿的“70后”作家,石一枫曾坦言自己深受老舍和王朔两代“京味”作家的影响。因为与王朔相似的成长背景和语言风格,在很多场合,他都会被问到有关王朔的问题。
但石一枫并不介意,也不焦虑。在他看来,大家都在书写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都通过北京,去感受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变化着的世道人心。后来人绕不过老舍与王朔,那是因为人家确实写得好,确实捕捉到了时代的“魂”。但是,王朔写不了老舍那个时代,老舍也写不了王朔那个时代,他自己也有身处其中的,有许多人和故事可讲的时代。
于是,在2018年的《借命而生》、2020年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之后,石一枫又在他的文学版图里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小说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专号2021年第五期,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漂洋过海来送你》讲述了三户人家“抱错骨灰盒”的故事。一户来自北京胡同,去世的那姓爷爷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一户身处上层社会,去世的老太太是个老革命,但她很会赚钱的儿子带着孙子去了美国;还有一户是一个海外劳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姓爷爷的孙子那豆和爷爷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无论如何也想换回爷爷的骨灰盒,于是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历经种种,听闻了另外两个骨灰盒背后的故事,也终于让逝去的人回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
石一枫虽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从没住过胡同,工作后才得以在日常时光走进胡同人的生活空间。这是他第一次写胡同里的北京人,写传统京味文学意义上的胡同生活。小说从2020年开始写,这一次,他脑海中先冒出来的不是人物,也不是情节,而是一种传统京味小说的叙述调子,或者说是一种情境与气氛。
“北京的作家基本上还是有一种情结,愿意写写最传统的老北京人,老舍时代的北京人。”近日,石一枫就新作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因篇幅关系,专访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他谈到了新作的由来与构想、京味小说的传统与延续、中国家庭价值观的“隔代遗传”;在下篇中,他从自身写作的变化谈起他对这个时代的感受与发现,以及他的小说方法与文学观。
此为下篇。

石一枫
在文学的世界里,体贴更多的人心
澎湃新闻:对这篇小说的叙事视角有什么考虑?似乎从《借命而生》开始,包括后来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漂洋过海来送你》都是用第三人称展开叙事,《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前作中常出现的那个带有石一枫特质的观察者消失了,这种写法会要求你对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人物更体贴吗?
石一枫:对。就我个人来说,我挺羡慕有的作家一上来就能写第三人称,而且写得挺鲜活的,这可能还真是一种天分。然后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通过“我”来叙事。我应该是属于写作时叙述者声音相对强的作家,然后有一个“我”之后,小说会比较顺畅,角度处理得也比较好。写《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的时候,我用的是“我”,甚至《漂洋过海来送你》之后我正在写的新东西,又开始用“我”。我用“我”能够写得比较真切,叙事也更从容。
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这个“我”——有点文化的、游手好闲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说实在的能够接触到的社会面不是特别广,如果老被这个人称限制住,那么有很多人物是写不了的,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是写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用第三人称,这对我个人来说还挺费劲的,就是说第三人称怎么去体贴,不需要一个“我”的视角就能体贴到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物,这个还真是功夫。对于有的作家是天分,但对我可能更是一种功夫,得训练,然后不断地去体贴,去揣摩,才能达到。我觉得我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三四十之后,能够体贴更多的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
当然,作家各有不同,你看王朔基本上没写过不是“我”的,都是“我”,但有的作家刚上来写就是第三人称,他的第三人称写得特别好,可你一看他这辈子没写过“我”,也就是说他写别人特别好,写自己反而有障碍。现在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我这两种都还行,能够切换,基本上写一个第一人称爽一把,然后再写一个第三人称的东西,接着又回到第一人称,跳着来。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澎湃新闻:虽然这个小说的主线是那豆一家,但我觉得黄耶鲁那一条线也写得很有意思,一方面是咱们前面说的“隔辈亲”耐人寻味,另一方面是我觉得黄耶鲁比李牧光可爱了。你的小说经常写到经济事件,黄耶鲁和《地球之眼》里的李牧光一样被家人强行送去美国,都有一个发着不义之财的父亲,但黄耶鲁比李牧光多了不少无辜与可爱之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否也意味着,你对黄耶鲁、李牧光这样的人,多了一些理解?
石一枫:对,他(指黄耶鲁)其实比较无辜。之前写完《地球之眼》我就反思了,有没有写得不够的地方?就是把李牧光写得有点简单,写成一个纯粹的反面人物了。那这个人物一定是纯反面的吗?他身上有没有更多的复杂性?我当时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就希望尽可能地体贴每一个人。不能说身处一个不道德的环境里就一定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有时候他只是处境不道德,但这和人道德与否要分开看。还有像黄耶鲁的爸爸,这个人物没实际出场,如果出场的话我现在也会尽量去理解他,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已经是“丛林法则”,那究竟是他这个人本身就坏,还是生存逻辑使他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觉得也是值得深究的。
至于黄耶鲁,我倒是觉得本质上就挺无辜。这种家里发过不义之财的小孩,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头脑比较简单,傻乎乎的,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太好了。而且大家也要理解黄耶鲁这种人,他有他的片面看法,比如他觉得美国不好中国好,是因为他在北京的物质生活超过了美国,但他只看到了北京奢华的那一面,只看到中国大城市奢华的那一面,他看不到别人的生活。所以从本质上说,他就是比较无辜,又目光短浅,是一个井底之蛙,只不过这个井底之蛙被扔到了美国而已。

《地球之眼》

《世间已无陈金芳》
澎湃新闻:从黄耶鲁这个名字也能感觉到他爸是一个很奉行“成功学”的人,你对“成功学”一直是有批判的?
石一枫:对,我坚决反对“成功学”,反内卷。文学的精神就得反内卷,都跟着内卷了还写作干嘛呢?
澎湃新闻:说到反内卷,你这次小说的主人公是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他们习惯的是很闲很慢的生活,那他们如何面对内卷?
石一枫:他们比较悲剧,因为在现在内卷的游戏里,他们基本上是失败了,被卷出去了。内卷的离心力把他们抛出去了。
澎湃新闻:从小说来看,那豆一家的职业都是酒店门童、司机、卖肉员这样的。
石一枫:对。如果我们用内卷的标准来看所谓胡同居民,或者说来看每一个中国城市里都有的老居民,会发现他们的悠闲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参加内卷的权利了。你要有资格,要受过高等教育,要有一技之长等等标准你才能跟别人去卷,但这些人都没有大文化,没有受过特别高的教育。这么说吧,他们除了在城市的核心地段有两间破平房之外,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一无所有。
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城市不断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人被抛出去,会被这个城市的主流生活给抛弃,那么这些人就是内卷的失败者,或者说没有参加内卷的资格。但是文学还会通过他们去看待世界,有时他们比内卷的成功者更能看到生活的意义。
澎湃新闻:这些人其实也令人心酸,好好生活着,也没干啥坏事,以前还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但突然间不是了。
石一枫:就是突然之间规则变了,标准变了。比如东北的工人是在一夜之间不再是主人,而北京的原住民也是这样,以前北京就是我们家,但现在我要在我们家门口领低保,就是你突然被生活抛弃了。这是城市发展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避免归不可避免,不等于说我们写作的时候就可以忽视他们。我觉得他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在写作的伦理里,恰恰是舞台的核心。
澎湃新闻:最近在看《人世间》,这部剧也是讲东北的工人故事。
石一枫:是,最早的时候讲“看完上海看东北”,就讲的是中国没有工业化的时候,只有两个地方工业发达,就上海和东北。现在如果你在东北说自己是一个工人,人家一定认为你失业了。
作家如果是明星,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也可疑
澎湃新闻:你在生活中有什么爱好吗?喜欢音乐吧?
石一枫:爱听点音乐,看个电影,游戏也玩,比如塞尔达。我属于那种什么都玩一点,但都不是特别精。比如我听音乐,没有像格非老师他们必须得用什么音响,然后音响还必须配个什么线,我没到那个份上,就觉得哪个好听多听听。看电影也是,咱也不懂镜头,就是看看热闹。反正是一般爱好者,只不过爱好多了点儿。
澎湃新闻:做文学编辑平日要看稿子,那工作之外的话,你会想看什么书呢?
石一枫:我是属于工作内外看的东西差不多,因为兴趣就在这儿,工作内是看小说,工作外也是看小说,就是看小说这事儿本身就是一兴趣。
澎湃新闻:那在小说的选择上呢?
石一枫:我比较喜欢看当下作家写的当下的小说,经典咱反正也得看吧,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得了,没必要非得一直追踪外国大师。比如英国作家,看看狄更斯,看看萧伯纳,法国作家看看巴尔扎克,就行了。更有意义的事是中国正在写作的,跟我差不多一个时代写作的这些作家,不管年纪大的还是年轻小的,都比较重要,因为你跟人家干的是一个活儿,你们处理的是一个问题,尽管大家的写作千奇百怪,差异很大,但是归根结底处理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写中国的当代,怎么写中国当下的社会和当下的国人。对于这个问题,国外的作家给你的借鉴不是直接的借鉴,直接的借鉴只能是你身边。所以我更愿意看现在中国的写作。
澎湃新闻:就你个人而言,你成长于1980—1990年代,经历了文学最热和文学开始落潮的年代,你认为文学在社会中理想的位置应该是怎样的?
石一枫:过去觉得当作家挺棒的,等你当了作家之后,发现作家啥也不是。但我觉得挺好。其实我们得相对冷静地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者说是社会的明星,我倒很怀疑在那种状态下作家能不能写出比较好的东西。
我们作家,尤其我这样的基本就是写普通人的写作,如果你迅速地成为不普通的人,那么这种写作真诚不真诚?有效不有效?还能不能完成?我都比较怀疑。所以我倒觉得现在挺好,而且说实话咱们国家对作家真是挺好的,虽说不会有那么多人看你,但是有相对的保证和辅助,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做得都好,有些地方还挺重视的。
在我的理解中,作家就是诸多职业的一种,一个很普通的职业,没有超越其他职业的意义,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职业做好。同时这个职业也有一些高要求,说得泛泛一点,比如传承人文精神,或者为人民鼓与呼,这也是这个职业应尽的义务。作家也好,记者也好,其实可能本质上都属于这一类职业。所以我倒觉得不要希望自己像1980年代的作家一样是全国人民的老师,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也不正常,当然可以说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但我真是觉得当时未见得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你在其中尽好职业的义务。
而且,如果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不普通的职业,这个职业很有可能会碰到危机。比如现在的网红,它不普通,它很可能会出现问题。经常是这样,朝阳产业充斥着骗子,夕阳产业反而是稳稳当当,踏踏实实。
澎湃新闻:你的作品在专业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中都有很好的评价,在写作的时候,你更多地考虑哪一种读者的眼光?
石一枫:作家的愿望是大家都喜欢,但我甚至觉得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可能批评家里是有一些专家比较喜欢我这样的写作路数,然后读者也是,但想做到和能做到的都是有落差的,我尽量弥补这个落差吧。我相信真是好的作品,应该是专家与普通读者都叫好,我们不要总是拿读者去反对专家,或者拿专家去反对读者,真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
澎湃新闻:你会有销量方面的焦虑吗?
石一枫:还行,焦虑可能也有,你看怎么比吧。比起真正的畅销书作家,或者说通过写作实现人生飞跃的作家,我肯定比不了,但是我还比较好的一点是基本靠写作能够正常地运转下去,靠写作支撑自己继续写作,这点就挺幸福了。而且咱们必须得承认,中国整个文学体制有一条比较好,虽然也有人说这不好那不好,但是它对于有写作能力的人总是能够给到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从这点来说我倒没有那么偏激。当然焦虑肯定也有,具体到经济方面的焦虑,都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就是有了游艇我还会想想飞机呢,就让人没辙了。

《借命而生》
澎湃新闻:你曾说王安忆像19世纪巴黎的“书记官”巴尔扎克,你是否也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做21世纪北京的“书记官”?
石一枫:那不一定,因为“书记官”这个概念指的是写到更多的社会层面,写到更多的社会人群。但是还有一点,你能不能在一个时代里提出一个新的或者独树一帜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应该说也是文学应尽的一个义务吧。
澎湃新闻:这是你追求的一个方向吗?
石一枫:写作的时候要考虑到。
澎湃新闻:很多人拿你跟王朔比,你对这个事儿是什么态度呢?在我自己的感觉里,你们俩有像的地方,比如贫嘴的时候,但我会觉得王朔是一个观念性很强的人,你有观念,但你会让感受大于观念,不知道这样的表述准不准确?
石一枫: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跟老舍一样,老舍就温和一点。王朔的战斗姿态非常强,老舍就相对温和一些。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欣赏王朔那样的战斗姿态,现在确实觉得要多体谅,然后多思考。跟王朔比的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为写北京生活的,你不可能绕开他,这说明人家了不起啊,是吧,你表现北京就不可能绕过老舍、王朔、刘恒他们这些人,一定会有人拿你跟他们比,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一点儿也不焦虑,因为这是文学本身的内在特质决定的,大家都是在写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王朔写不了老舍那个时代,老舍也写不了王朔那个时代,而我观察、写作、生活的这个时代,跟他们天生就会有不同,所以不太有那种叫模仿的焦虑。
澎湃新闻:“京味”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带有地域性的。你觉得带有地域性的“京味”和作为一般汉语的普遍性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石一枫: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语言审美,或者说是语言表述方面的地域不同。我们现代汉语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以北京话就是某种意义的普通话。我们北京的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不需要翻译的,直接就出来了。但是南方的作家需要翻译,我就听余华和苏童他们说过,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
哪个好?不好说。你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更自如一点儿,畅快一点儿,但你会发现往往经过翻译的语言更准确,更凝练。这个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多过了一遍脑子。还有一个,你把老舍和鲁迅做比较,你会发现北京作家的京味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表形,就是表述形态、描摹人物这方面特别好,写动作、神态会写得很好,但这样的语言在思辨的时候是吃亏的,而鲁迅用南方人的语言去表现思辨性的东西就会表现得特别好,各有优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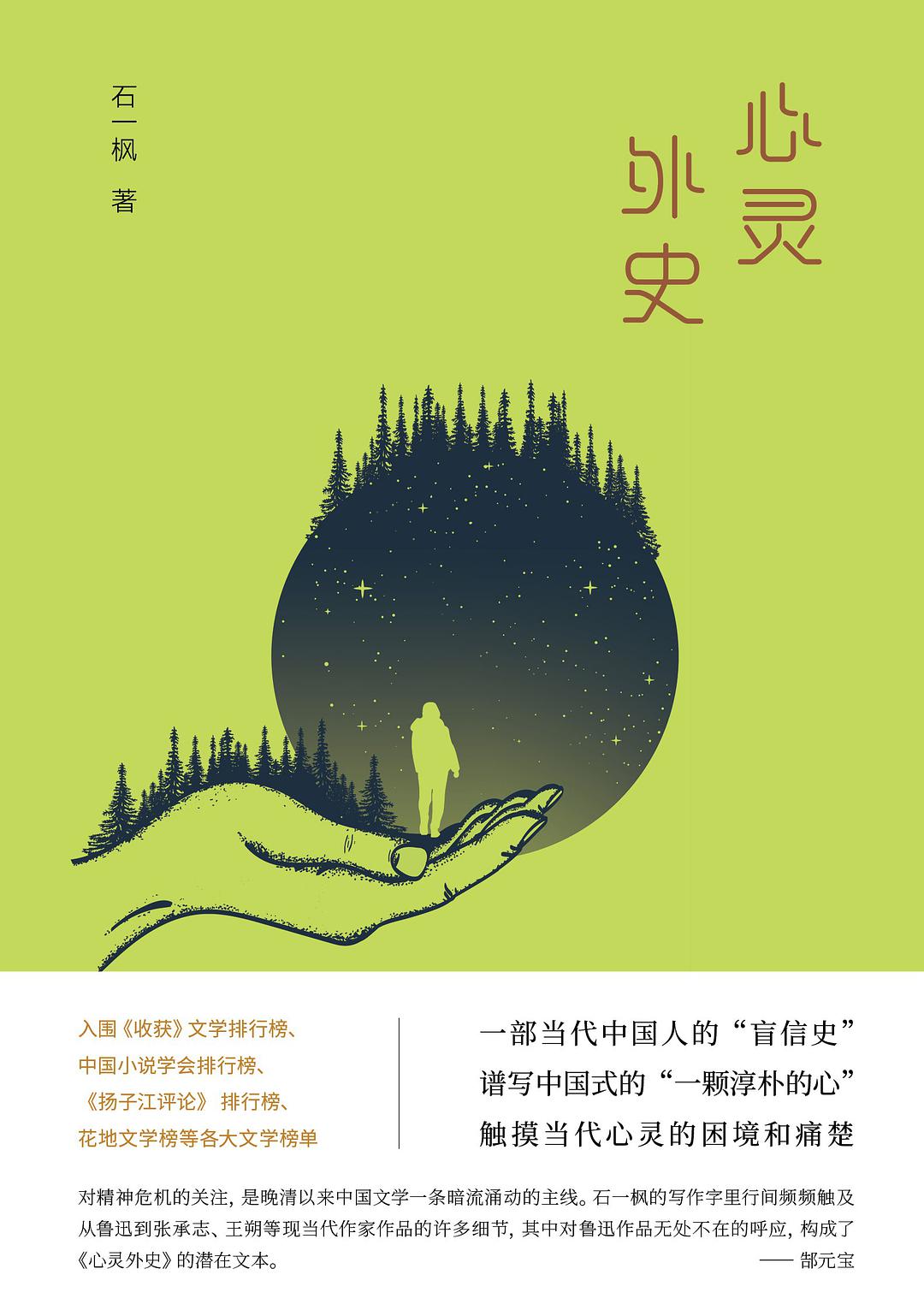
《心灵外史》
【后记】
在这篇当代京味小说里,我们会看到老舍时代的北京人走到今天,命运也在悄然改变。
上一次见到石一枫是在四川的文学期刊论坛,他讲到北京过去农村地方的一些乡民因为拆迁一跃成为中关村附近的有钱人,拥有了无数北清学子或许一生都望尘莫及的学区房。对于这样的乡民,有人不屑有人羡,但石一枫还看到了这些乡民正在经受的“精神虐待”:因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往往四处碰壁,甚至连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完成得相当吃力。当时石一枫说:“中国社会有政治等级、经济等级,也有文化等级。所以,同样看待拆迁,从不同的时间、地点、立场、视角去看,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显然,北京农村地方的乡民和这次《漂洋过海来送你》里写到的祖上“在旗”的胡同居民不一样,但他们在文化与教育程度上颇具共性,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都成为了今天所谓内卷时代的“失败者”。对于这样的“失败者”,石一枫有同情,有无奈,有反思,他坚定地反对内卷。
在我的感觉里,石一枫一方面是那种有自己观点的小说家,另一方面,他也打开自己的感受,甚至于让感受大于观点。最明显的一点是《漂洋过海来送你》又一次写到了通过非法集资谋取暴利的富人,他的形象类似于《世间已无陈金芳》里的b哥、《地球之眼》里的李牧光。尽管《漂洋过海来送你》里的这一人物最后没有实际出场,但我们能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石一枫对于这类人行为背后的生存逻辑有了更多的体会,对于个人与时代的角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