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贺喜、科大卫:天地会为什么要拜会?
但凡要了解一种活动,人们总是会问这样一些问题:这些人在做什么?做了有什么用?怎样做?怎样做才对?怎样做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有其他办法做这件事?
清政府的官员,参与天地会的群众,与研究天地会的学者,也基本上是在问类似的问题:拜会在干嘛?为什么要拜会?拜会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对此他们大概也有一些答案。他们知道绝大部分拜会的人不是因为要“谋叛”。清朝官员以为他们是受了敛钱惑众的传会人所欺骗的愚民,历史学者以为他们是中下层需要互相保护的民众,可能其中也有反清的感情在推动。乍一看,二者都有其道理。但是,敛钱或互助是不是一定需要秘密拜会?难道以一个既定的犯罪行为来组织敛钱或互助谋生比之于不触犯刑律的活动更具有吸引力吗?要解答这个谜一般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秘密拜会是怎么一回事。
边钱会
秘密拜会并非天地会所特有。嘉庆七年(1802)福建省破获一个被称为“担匪”的组织,其入会仪式就是秘密拜会。“担匪”这个名称,有可能来自方言,也可能指结会的成员都是以挑担为生的挑夫或抬轿子为生的轿夫。他们没有讲天地会的故事,但是有很多方面与天地会相似。
事件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萧烂脚的轿夫,宁都人。他在嘉庆十六年被捕,审判后,立即被以绞刑处死。从嘉庆六年到十五年,他参加了多次拜会。嘉庆十一年以前,他还只是一名跟随者。嘉庆六年,他跟随一个叫李次元的人在进贤县“拜把”,有二十三人参加。嘉庆七年,他跟随另一个“担匪”周(病字头+束)子在临川县“拜把”,有三十二人参加。周(病字头+束)子在当年被捕获。官员报告,周(病字头+束)子是个“无托足之地,是以身挑锅灶,在于古庙凉亭随地卧歇”的“担匪”。他“向各乡求乞,乘便掏摸攫窃,索钱取赎,聚散无常,每遇婚丧之家,强讨酒食钱米,稍不遂欲,即行吵闹。”报告特别写道,他“拜把”不是“拜会”,因为他“并未创立会名,亦无歃血焚表及另有不法情事”。可见这些人不是什么叛徒,而是身无财物不安本分的无赖。他们的结伙除了结拜也没有什么拜会仪式。
至嘉庆十年,萧烂脚在江西省临川县跟随了一个叫王瞎子的人,开始明白拜会是怎么一回事。王瞎子一伙,叫“边钱会”,共有四十四人。边钱会内,首领叫“头肩”,亦称“大老官”,最活跃的叫“老满头”。他们的规矩,“系用钱一文,分为两半,暗作记认,一边交为首之老大收藏,一边交老满头收执,为聚散通信凭证。”
具体怎样进行拜会呢?档案中说:“结拜之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一只,及钱一二百文,同买酒肉,写立关帝神位,传香跪拜。”
这个会不是平等的。“每年五月十三、八月十五两次作会,老大乘轿而至,众皆跪迎以示尊严。凡同伙之人,除老大为头肩外,其余分作二肩、三肩等名目。”档案文件也描述了边钱会的活动,“号令不许抢劫,不许放火杀人。若有违犯,老大问明责罚。其年力精壮者,平日肆劫勒赎,自定价值,不容事主较量。老弱残废者,结伴强讨,稍不遂欲,卧地诈伤图赖。其有弹钱赌博者,包揽护庇,抽头供奉老大。受害之人,或有具报到官,必公同设计报复。遇官府查拿,令善走者,名为老满头,探听消息,以便躲避。”他们的活动,就是“肆劫、勒赎、强讨、诈伤、包揽赌博”。最活跃的老满头打通官府,探听消息,方便会伙躲避政府捉捕。
“边钱”作为结会的符号比“拜把”有力,由此萧烂脚模仿王瞎子,建立了以他自己为首的边钱会。嘉庆十一年,他与三十九人,“在安仁县邓家埠地方(今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宰鸡取血滴酒,分饮结拜,一切边钱禁约,仿照王瞎子会规”。据同一份报告,接下来几年,萧烂脚起码还组织了两次拜会:嘉庆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参与者六十六人;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四十人。边钱会的参与人数比此前没有名目的拜把为多。在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拜会上,会内信物边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参与者分成一肩到十四肩的等级。边钱“添用五色丝线缠缚,外用红纸包裹,一边交老大存留,取名坐令,一边交三肩内之罗万(受)收执,取名行令”。我们可以想象五色线缠结的边钱包裹在红纸内,在仪式过程中,相当引人注目。档案中也提及了与会人行令的理由,是因为“如同伙犯约令罗万受一半边钱给老满头传到责罚”,而且“勒赎赃钱,除分给老大外,并给行令之人一股”。
可见,当人数增加以后,边钱会的权利系统也分成三层。萧烂脚还是老大,保存所有边钱的半边。以下有老满头和三肩。三肩大概是小头目,所谓保存边钱的另一半,即是其所统辖的小伙众结拜所用的边钱的另一半。伙友犯规,由老满头处置。为示边钱会结拜仪式的统一,小伙众的一半边钱将传回老满头认证。
“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答案,可能是在于仪式的力量可以引致组织的分化与统合。人数增加将引起分化的潜在危机,但是分享共通的象征却能够在形式上保持统合。有边钱比没有边钱的结拜更具象征性。那么,天地会的故事是否又比边钱更具有象征性呢?
天地会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福建永定县人卢三,又名破鼻花,到江西龙泉县(今遂川县)“结会传徒”。四月,寄居龙泉的广东兴宁人李魁升与上杭人蓝老四以卢三的徒弟上杭人陈纪传“交友甚广,拜其为师,可免外人欺负”为其介绍传徒。他还说,“如领红布花帖,即可传徒骗钱”。李魁升、陈纪传、蓝老四都在龙泉大汾墟开店,李魁升于四月二十七日拜陈纪传为师,送钱三千文。
档案很清楚地叙述了拜会的仪式,就是典型的天地会拜会。记录说:
陈纪传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米桶插五色纸旗五面,中插红纸旗一面,并用布搭桥,令李魁升 间过,陈纪传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并用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布花帖,以作传徒之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十一”口诀,发辫从左圈转,以便同会人关照,有事相帮而散。
拜会仪式后,李魁升开始传徒,每次人数十多人不等,各收六七百文。卢三还有不少徒弟,每人收一二千文。卢三其他徒弟也有传徒,也各收六七百。奏折说“该匪等入会以后,彼此联络,因李魁升、陈纪传师徒说话伶俐,又有勇力,推为大哥。”
嘉庆十六年,案件有了新发展。当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参与拜会的杨学贵母亲病故,无钱埋葬,有名为钟高才的人,建议他把母亲埋在当地徐姓与罗姓有争议的山地。当晚,杨学贵、钟高才一行人,向棺材店赊取了棺材,第二天抬到山上,在离徐姓祖坟前三丈的地方埋葬。徐姓人干涉,但是,“因畏会匪人众”,只要求杨学贵写立借据。杨答应,但是最终双方大打出手,双方各有损伤,钟高才的一个同伙死亡。
过了几天,七月二十九日,钟高才等与伤亡者的家属,跑到大汾墟向李魁升、陈纪传求救。李、陈应允“纠众复仇”,遂令钟高才等一方面向县告状,另一方面“写信九封”向会伙求援,“约定八月初四日,齐集大汾墟,拱抬尸首,赴徐陆传众殴毁泄忿。”徐家甚至大汾墟的人,为此甚为恐惧,巡检也不能弹压,但是乡民募集的乡丁把钟高才等五十余人制服,送到龙泉县审判,后因为案情严重,转到省。龙泉县在李魁升等家,“起出名簿、符书、花帖”。江西巡抚先福亲自审判,原先认为“起获刀头、小铁铳等件,均系民间常用之物,并非军械。即符书簿本,亦只练习拳棒俚语,尚无违碍不法。”
但是,随后在其中一家人家搜到了由陈纪传发出钟高才代笔的花帖,即如下文件,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
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都大平府太平寨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传下四字“阅、间、闽、闷”,再传授到广东惠州府高溪,兄弟议论,分开五房,共议传下四字:“云白连天”。兄弟各别,二房在高溪,三房在广东省。以后兄弟立业,分为五处,再传下四字:“木立斗世”。五房五兄商议,传下“顺天行道”四字。方大洪大哥三房在万山起义立业,众兄弟再传下四字:“顺天字号”为记。如今众兄弟万山传出帖,交与化兴弟子承领,日后若有查出不忠不义,割头示众。
在场:祖洪押、德标押。
保结:彦惠押、殿云□、邰周押、成珍祯押。
代笔:高材押。
非亲有义须当敬
是友无情切莫交
黄河自有澄清日
顺天结义合同心
天运元年辛月未日立传帖万山众兄弟承领帖,弟子化兴传出帖,交与承领帖弟子化茂、[化]思。
这张字条的发现非同小可。先福报告,它“载有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和尚万提喜,及传广东惠州高溪,分为五房,并方大洪等”,帖后写有“天运元年辛月未日”。先福认为这些字句证明“有谋为不轨情事”。
事关严重,先福盘问钟高才有关高溪的地点、方大洪的真实性。钟高才供,“帖内所写字样,都照陈纪传原帖誊写,曾向陈纪传查问,据说是会内流传,并不知有无其人其地。即帖后天运字样,因会中向有写顺天两字者,亦有写天运二字者,是陈纪传原帖如此。实在起自何人,伊并不知。”钟高才供出文件下款出帖人“化兴”就是陈纪传,承帖人也只是用了法名。好几个画押,是由钟高才代画。彭殿云(文件内的“殿云”)则供“伊不识字,系因陈纪传令其列名画圈,是以照画。并不知帖内是何字句。”先福接纳供词的内容,陈纪传没有被捉拿到案,李魁升、钟高才几名组织拜会的人照“谋叛”例斩首,其他人从轻发落。
以这个案件与“边钱会”比较,可以看出天地会的故事发挥的作用。铜钱作为结会符号不一定没有故事。但是,铜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的东西,即使把它分成两半,变成一个团体特有的符号;它也只是一个单一团体承认的符号。天地会的故事的仪式比边钱会丰富。天地会的故事联系到拜会人群以外的大历史。当一群人举行天地会的仪式的时候,他们建立起的不仅是拜会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与他们想象之中的其他拜会群体建立了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个网络式的关系到传会者所传授的口语、手势、花帖、甚至拜会的仪式得以在天地会的虚拟传统之下合理化。这就是传会人陈纪传“交友甚广,拜其为师,可免外人欺负”的意义。参与拜会者好像没有掌握到这个故事有“谋叛”的意味。他们“并不知有无(天地会人物的)其人其地”。甚至有不识字者,根本不知道“帖内是何字句”。归根到底,这些拜会的人,只求遇事时互相照应。天地会的虚拟网络让他们相信有获得照应的机会。所以,出事的时候,他们写信向外求救。当然,若求援无效,这个故事就会破产。不过,到了这一步,参与拜会者已经被政府甚至与他们对立的乡人认定为反清复明的集团。参与虚拟集团的后果并不虚拟,清政府的惩罚是非常实在的。
入会以保身家
若把参加拜会形容为受骗与互助,给人的印象则是参与是自主的行为。参与者之所以参与,是因为相信了骗局,或寻求互助。但是,时人也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曾在嘉庆十二年(1807)任泉州府知府的旗人金城,谈到当地的天地会,说:“久之,匪类多而势益强,虽善良殷实之户,恐被欺害,亦入会或交结供给之。”道光十年(1830)给事中牛鉴上了一个奏折,报告江西省赣州会匪猖獗的情况,也说:“江西省南赣会匪首犯凶横狭黠,遇有恒产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会者,非劫夺牛马,即蹂躏田禾,甚至抢掠子女,勒银取赎。小民被其淩逼,不入会则祸不旋踵,无以保其身家。入会不过敛给银钱,犹可免其荼毒。以是畏祸之心,甚于畏法。胁之者愈甚,从之者愈多。”
乾隆年间,禁止结拜的法令已经注意到被威胁入会的问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针对福建省“歃血、顶盟、焚表、结拜兄弟”的律例说:“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月。”嘉庆十七年的修订,再增加了两句:“如为从各犯内,审明实系良民被胁,勉从结拜,并无抗官拒捕等事者,应于为从各本罪上再减一等。仅止畏累出钱,未经随从结拜者,照违制律,杖一百。”
案发后,实际上很难判断谁是自愿参与,谁是被迫胁从。尽管如此,参考时人的意见,我们大概还是可以相信有些参与者是在被要挟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天地会的收费文本
天地会的案例,有一个常常发生的枝节,就是传会人藏有拜会参考的文本(叫“会簿”),以收费的代价让拜会者抄录。抄录者拿着这些文本,分头组织拜会。很明显,传抄这些文本就是天地会扩散的一种门路。但是,通过这种渠道的扩散,是天地会组织上的扩散,还是只是讯息上的扩散?收藏天地会文书的传会者,其实对天地会的认识有多少?天地会文书的收藏者之中,有多少实际的联系?道光十一年的一个案件,很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报告,捉到一个组织结拜“三合会”的人,名叫马绍汤,籍隶贵州开泰县。
嵩溥的报告说,当年正月,马绍汤从开泰去了广西怀远县,遇到广东船户吴老二。吴老二说及广东旧有添弟会,已改名为三合会。他有本“会本歌诀”的抄本,里面记载了防匪徒的问答和手势。他说:“如遇会匪抢劫,照依书内,开口不离本,起手不离三口号、手势行动。如遇人问姓,先说本姓某,易姓洪。匪徒知系同会之人,可以保全。”马绍汤付他二钱白银又七百文铜钱,向他借来抄。见到会书内“载有八角图形,四面几层俱有细字”。图内有马绍汤并不认识“彪(后四字为:虎字旁+寿、合、和、同)”五字,及长、二、三、四、五房内,有桃必达、吴天成等名字。吴老二告诉他广东属二房,名洪太宗,以红旗为号。其余各房,吴老二亦不知道。书内有一首五言诗,有“五房留下一首诗,身上洪英少人知,有人识得亲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等句。
马绍汤抄到的八角图形,是天地会(即三合会)的入会凭证,叫“腰凭”。我们可以拿其他地方出现的天地会文献做参考。可见,这个八角图形故作神秘。例如,“三、寿、合、和、同”五字,加上“虎”字旁,变成马绍汤“并不认识”的字。文件记录的五言诗,也不顺排,而是有系统地排在八角。诗句“身上洪英无人知”有双重的意思。“洪英”一方面可以代表归附到“洪”姓的参与者。所以,在附图的文件,“洪”字放在中间,虽然我们不知道马绍汤所见到的文件有没有这个部分。另一方面“洪英”就是这张“腰凭”,“身上洪英无人知”是因为“腰凭”放在身上就是一个会内的秘密。“腰凭”的字句排列,五字暗语旁加“虎”字,虽非常态,但是稍读过书的人大概都可以看懂。所以这个“秘密”其实只有增加了文件的故事性,它本身并没有保密的成分。

天地会的腰凭
马绍汤回到开泰,举行了拜会,参与者三十二人。他又把文件传给其他人。得到他传授的蒋倡华组织了两次拜会,又有三十七人参与。最后,马绍汤、蒋倡华均被捕获处决。
从这个案例显示有关天地会传播历史中的两件事。第一,马绍汤本人并没有经过拜会的仪式,他从船户吴老二处所得资料,全部来自文本或吴老二口传。但是,虽然他没有亲身经历拜会,回到家乡后他还是懂得怎样传授。这意味着拜会是民间所习惯的传统。在庙宇或神坛的祭祀中,“拜”与“会”都很普遍。“拜”是在神前烧香,“会”是集资做祭祀。拜祭神明后,做“会”的人集合享用祭品。在什么神前“拜”,谁“拜”,影响到“会”的性质,可以有地域、宗族、行业、官位品阶、甚至性别的分别。第二,尽管吴老二没有和马绍汤拜会,他很成功地传播了天地会的故事与仪式,因为天地会的核心资料已经浓缩为一张小字条。但是,字条所记录的事情,他们谁都没有经历过。吴老二也坦白地说他不知道广东以外四房的情况。对广东本房,他也只是知道属于二房,与以红旗为号。故事虽然以讹传讹,但是没有因此影响它的号召力。讯息的力量明显不在其真与假,而在其说服力。
清政府非常谨慎地看待天地会故事的说服力。清廷就马绍汤事件下了一道谕旨。谕旨的论点很能代表道光年间朝廷处理类似案件的办法与思路,所以值得一览全文:
前因御史冯赞勋奏,广东等省有三合会名目,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当经降旨,交各该督抚饬属严密访查。旋据各该督抚覆奏,俱称现无此项会匪。今贵州已拏获三合会匪徒多人,并据该犯马绍汤供称,广东船户吴老二,有细字图,所载长、二、三、四、五房内,有桃必达、吴天成等姓名。复告知广东系二房,名洪太宗,以红旗为号。是贵州会匪钞写逆词,系由广东传授,其余各省,亦必有传徒纠众之事。着李鸿宾等,各派妥员,认真查拏,将为首匪徒缉获,按律惩办,并散其党羽,以净根株。
谕旨的论点是这样的:在马绍汤案之前,已经有人报告天地会五房分布在福建、广东等五省。当时朝廷已经命令各督抚追查此事的真伪。督抚均回应没有会匪踪迹。但是,在贵州捕捉到的马绍汤供出来,他是从广东的船户处得到的字图传授,他还可以正确地说出五房的分布,由此证明了跨省授徒传教的事实。于是,朝廷不接纳先前督抚的奏报,坚持命令他们继续认真查办。
天地会拜会能够引发一个存在跨地域网络的想象,本身就是个很有利的传播条件。尽管吴老二对于其余各房,“亦未知悉”,但是,吴老二不知道不等同其余各房不存在。参与拜会的人,是参与一个实体的活动,只需要假设其他地方,其他人也在组织这种活动,参与者就可以认同天地会是一个超越地域的架构。政府在不同地方搜查到“腰凭”之类的文献,捕捉到参加过形式相似的拜会活动的参与者,发现他们有共用的口号,似乎又能为拜会背后跨越数省的人际网络提供证明。文本的流动,引发了跨地域网络暗流潜藏的错觉。
太平军起义时期广东的拜会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然后从广西进入湖广,屡败清军,咸丰三年,攻下南京,与清军展开拉锯战。当时紧张的气氛在长江以南各地蔓延开来。在广东的潮州、东莞、惠州、佛山等地,于咸丰四年先后有起义军攻打县城、对抗官军。虽然起义的队伍不一定打着“天地会”的旗旂,但是天地会的拜会在他们的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迹象。
广东在咸丰年间起义的群众,历史学者统称“洪兵”(少量资料可见的字眼,不见得当时普遍使用)。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把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带到英国(现存于大英档案馆),其中,保存了部分关于“洪兵”起义的详细材料,包括十多篇被捕的起义人士的口供。从这些生动的材料,可以窥见天地会拜会在起义群众之中的作用。以下挑选了三段为例:
许亚丽供:年三十四岁,花县朗溪村人,父亲已故,母亲黄氏,年六十八岁,并没兄弟,娶妻已故,未生子女,平日在里水做外科度日。咸丰四年七月十二日,在里水陈家祠拜会,共伙十余人,黎旦为老母,不知姓亚九为舅父,拜完各散。是月廿九日,投入佛岭市元帅甘先分扎冈头右营都督黄洸伙,派在第十旗黄亚应管带,同旗廿一人,闰七月初一,在金溪,初十日,在石门等处,与官兵打仗二次,均未伤人,后即散伙。至去年三月内,往香港卖生果。本年六月内,回来躲在家里。九月,到里水墟行外科,后推清远人陈亚方为首,纠同花县鸡枕山宋贵、(名字从略)及不识姓名的共伙百余人,约定俟鬼子闹,便乘机起事。
汤逢吉供:年三十五岁,花县石湖村人,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娶妻已故,生有一女,平日耕种度活。咸丰四年六月十二日,在本村汤家祠拜会,共伙六十余人。黄裔为老母,汤亚二为舅父。(其他经历类似许亚丽)
吕子桂即吕茂炤供:年五十二岁,鹤山县药迳司维墪乡人,父母俱故,并没兄弟,娶妻冯氏,未生子女,小的于道光十七年岁考,蒙李学宪取进第八名县学,咸丰元年岁考,蒙全学宪取准一等九名保廪,一向在家教读度日。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小的听从黄亚永邀,在本村义学拜会,同伙二百人,黄亚永为舅父,陈海为老母。拜时设立同义堂名,小的出银一元,枱上有斗,插五色旗,拜毕给还硃砂钱三文为记。即日小的投入鹤山县属药迳司维墪伪元帅吕雄杰贼巢,封小的为军帅……
从口供的资料可见,拜会与参与“洪兵”有点关系。许亚丽和吕子桂都先后拜会,然后参加起义。但是拜会也并非直接为起义军招兵买马,而是代表了某种立场。参与者在拜会后,可以参加不同的起义党伙。三个例子都表示主持拜会的有两个人,一位叫“老母”,另一位叫“舅父”,这两个名称在此前的报告中没有见到。例如,许亚丽拜会之时,在村子里的陈氏祠堂,主持人之中,黎旦为“老母”,“不知姓亚九”为“舅父”(“老母”“舅父”在拜会中的作用详见本书第四章),拜会后各散。但是,过了两周,许亚丽参加了甘先的起义,与军兵打仗后散伙,跑到了香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割让/租借给英国)。一个多月后,又回去参与了另一次起事,供词中,没有提到他是否需要参与另一次拜会。
这几个例子值得注意如下几点:其一,拜会的人数。许亚丽的拜会还只有十余人参与,汤逢吉的拜会有六十余人参与,吕子桂的拜会有两百人参与;其二,在洪兵起义的时候,拜会的活动已经比较公开;其三,拜会的形式也有所变化,关于拜会的变化在本书第三章与第五章还会进一步讨论。本处希望稍作提示,这些案例的形式与同治、光绪年间发现的拜会比较接近:仪式由两个人(“老母”和“舅父”)主持,包括一问一答的环节。比原先只在牌位前礼拜的仪式更为复杂。这一类的拜会仪式为天地会成熟阶段的仪式。
小结
为什么要拜会?从本章的例子看,拜会有很多理由,除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才发生的第五例,都与“谋叛”无关。乞丐与地方帮派有理由拜会结伙。招徒收费的人,惧怕帮派的人,不管帮派存在与否,也有理由拜会。归纳来说:有为认同天地会故事拜会,有传授天地会故事的人拜会,也有以“宁可信其有”的心态的人拜会。早期的拜会是个很灵活的活动,不一定需要任何道具,甚至不一定需要一本手册。后期的拜会则加入了比较复杂的仪式。
历史学者习惯于问历史背景怎样可以帮助解析历史事实的变化。他们追问:参与拜会的人是否来自社会的边缘?人们对民间宗教习惯性的接受是否帮助了天地会无缝地扩展?这些猜测都有可能,但是,若凭案犯的记录,似乎又都没有多少根据。从乾隆末年到咸丰初年天地会在地理上的扩散,倒是很清楚。一方面因为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甚至云南、贵州档案都存在确实的案例,另一方面从犯案的内容,也可以看到传会人不论是出于信念的理由,还是出于敛钱的目的,在多处组织拜会。“扩散”的背景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天地会的秘密是否从非常的状态进入了寻常的生活?
天地会的名称列入《大清律》其实是天地会寻常化的过程的头一步。拜天地会既然变成违法的行为,当然一方面增加镇压拜会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天地会”成了一个法律上的名词,也会更多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嘉庆十一年(1806),江西巡抚先福拟一张“用粗浅俗话”的告示,说明从林爽文起义后,办案所查出的天地会起源,俾民人“免致再为煽惑”。他的目的是证明“会匪假借捏说,希图哄骗银钱”。我们不知道这个告示有没有刊出,但是,假如有的话,当然也同时有扩散天地会讯息的作用。成功镇压天地会也变成官吏的政绩,记录在他们的传记中。久而久之,“天地会”成为一种行为的类型。例如,道光十六年(1836)两江总督陶澍《缕陈巡阅江西各境山水形势及私枭会匪各情附片》一折把匪徒分成三类:一为“真会匪”者,“宰鸡滴血,钻桥饮酒,传授口诀,散受花帖传徒者”;一为“虽会而不必真匪”者,“富民畏抢,庸懦被欺,胁从图保身家,与夫醵钱酬赛,如城隍、财神等会”;一为“游手凶徒俗名烂仔”者,这些人“遇事生风、执持刀械……纠党仇杀、掳掠畜产、拆毁房屋、捉人勒赎”无恶不作。“此则匪而不会,其情罪无殊于会匪,必应严惩。”更甚者,“拜天地会”变成寻常的犯罪,民间纠控时诬告对方为天地会分子,亦在在有之。嘉庆十八年(1813)广西平乐知府高廷瑶记录,当年查办附近武缘、荔浦县“天地会”案甚严,“两起凌迟,斩绞数十人,缘坐三百余口”,但是,“正乐于有事之际,趋风气者,讦告群兴……有一言不合,窃一草一木,即以会匪告。”
道光年间刻的《问俗录》解析“雪桥”条,也载:“据事直书呈式也。乃或二三人争闹,即控聚匪数十人,或至其家口角,即控聚匪数百人,掳抢一光。更有素无败行而指谓著名匪党,又或藉地方官访拿要犯指谓即其亲属交好,盖因上府迩来严缉会匪,故险其词以动目。俗名’架雪桥’”。
我们说“秘密在扩散”或“秘密在寻常化”的时候,应该同时怀疑这些说法有没有发生的可能。扩散了的秘密,不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寻常化的秘密,不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有没有都无所谓?没错,天地会的推广者面对着一个我们成为“秘密社会合理化”的结构性的问题:怎样在扩散,寻常化之中保持独有的地位?所以拜会一定需要变化,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复杂的过程才可以确认秘密的独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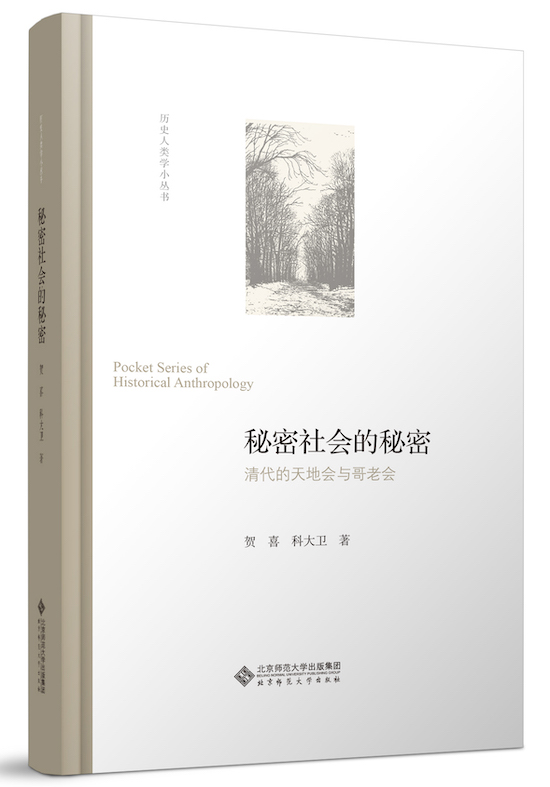
(本文摘自贺喜、科大卫著《秘密社会的秘密: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