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拍场一瞥︱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先生的生前身后
民国,毛笔,手稿,这些都是拍场上名人墨迹的卖点。最近现身一批拍品,正包含了这些要素。手稿为十行红栏稿纸装订而成,封面除标题、誊抄时间以外,还有“国立中央大学关防”红印以及“吴有训”蓝印,内页还有“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看来是来自原中央大学图书馆。内容以稀见出版物的抄件为主,钤有的一枚私印已有漫灭,仔细辨认为“李小缘”。

李小缘手稿内页
1962年10月16日,顾颉刚至胡厚宣处闲谈,两人民国时期在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共事,如今同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胡厚宣曾供职于中研院史语所,不知觉间聊到了南京的故人。回家后,顾先生日记如下:“到胡厚宣处,乃知解放以来,南京大学自杀者四人,欧阳翥、徐益棠、罗根泽、李小缘也。小缘一生循谨,孜孜矻矻于搜集资料,为南大积聚无数东方不易见到之书报,而五九年不知犯了何种错误,竟尔出此短见?闻其所写卡片,已归本所,倘能为之整理成书乎?”

这条日记谈到的几个学人,欧阳翥是生物系教授、前中央研究院院士,1954年投井;社会学系系主任、民族学家徐益棠1953年身亡;图书馆副馆长李小缘1959年过世;中文系教授罗根泽1960年跳楼。
身为前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小缘先生,久为世人淡忘。曾有位南大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生,在图书馆查阅民国期刊时,发现很多封面上都钤有“李小缘”藏书章。当时他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旧书店收来的。后来见到有相同藏书章的书很多,到网上去查,“才知道李先生原来是我们的老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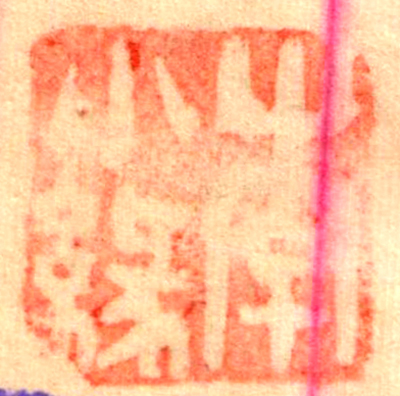
李小缘有遗稿《自传》,约写于1954年底或1955年初,写得很简略,也富于时代气息,可摘录叙述先生的一生。李小缘生于1897年,“幼读私塾,接受了很多封建影响”;后入“金陵中学附小,然后进中学,升入大学,十多年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回国后在金大图书馆负责西文图书编目工作,教授图书馆课程,不知道国家的形势,自己却陷入帝国主义的深渊”;最后总结说,“金大服务前后二十六年,再加上金大读书,美国留学,怎能不养成亲美崇美的观念?全国的解放是在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解放是在金大与金女大合并才开始的”。

《自传》来自《李小缘纪念文集》,此书源于1986年南大举办的“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这是1949年后图书馆学界正式出版的首部个人纪念文集,当时虽已“拨乱反正”,但编书者回忆,“在当年动议与实施之初,依然需要勇气与智慧”。南京大学有心,1988年初版后,2008年又出了增订版。其中有《李小缘年谱》,记录如下:“1959年12月26日,先生不幸谢世,享年六十二岁”,语焉不详;《李小缘纪念文集》广收回忆文章,叙述多有重复,虽是“纪念文集”的通病,但知名者如故交吕叔湘(并题写书名)、学生钱存训、同事王绳祖、弟子孙望、后辈徐雁等,均以回顾李先生早年经历为主,晚年提得不多,更无人言及逝世原因。

先生的大儿子李永泰,稍稍提了一下:“在去世那一天晚上,已九点多钟了,他还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学校图书馆里做最后一次查看。青年人遇到他,以为还是往常的查馆,谁知这是在向他心爱的图书馆,向他的事业,向人们告别。” 另有位朱正华,是李先生的内侄,他回忆姑父时写到:“我常想:我姑父这样的人,纵使那年不去,也定然逃不过后面的关,只是早走了几年……姑父啊!您为什么撒手去得这样猝然,这样毅然决然,叫您的子侄们至今茫然,惨然!”
从亲人的字里行间看,《顾颉刚日记》提供的信息更准确。前头提到的罗根泽教授也是如此,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罗根泽文存》,序文是这么说的:罗根泽“突患脑溢血,终因抢救无效,于3月30日晚逝世,终年60岁”。而顾颉刚1960年4月4日记载:“归来接罗雨亭凶报,渠已于三月卅一日在鼓楼医院逝世,朋从又弱一个,更加惆怅矣。” 1960年4月14日,死因得到确信:“得自珍信,悉罗雨亭以犯病太多,不堪其苦,医院已无法治疗,于上月底跳楼自杀。悲哉!”
李小缘先生于1959年12月26日逝世。1958年上半年,全国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李小缘当时也写了近百条“小字报”,内容极其丰富。先生态度诚恳,有话直说,表现了出朴实率真的本色。“小字报”部分存于南京大学档案馆中,《李小缘纪念文集》有收录,从中可读出先生生前点滴。
关于建国后的运动,首先李先生的表态就不合时宜,比如“运动接二连三的来,党的要求太高太急。应当让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而且牢骚不断,“既然应该让坏东西水远抛弃一刀两断,为什么又时常要我们挖掘,使已死之灰复燃呢”;“我对一位多年不通信的人说:现在是‘六亲不认’了”。对当时已经盖棺定论的名词,李先生不无微词,明显不悉世事,谈到地主,“有勤俭持家而来的,有封建恶霸的,应该有所区别的进行斗争,不应该让一般的地主来负责两千年的封建责任”;谈到右派,“反右斗争时我认为仅仅是言论上的问题,人民力量这样大我们不怕他的,给他们适当的批评够了,不必那样斗他,还是可以孤立他们来教育大家的”。偶尔的表态,要么是隔靴搔痒,如“反右不久,才认识到《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是适当的,及时的救了许多人,要没有这篇社论,右派分子更多了”;或者充满了滑稽感,如“当右派向党进攻非常明显的时候,不把大字报照下来,表示我们反对。但从资料的收集方面来考虑,不把大字报照下来,也不一定正确”。
谈及故友闻一多,两人年龄相仿,经历类似,可能留美期间就已结识。闻极为赏识李,曾先后两次相邀共事(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李小缘因早年在东北大学图书馆的经历,“观感不佳,官僚政治盘踞校中”,而“不愿在国立大学工作”,两次婉辞以谢。此后李小缘长期担任《金陵学报》主编,多次向闻一多约稿,1940年4月收到闻一多《说繇》一稿,刊登于当年《金陵学报》第十一卷。先生在“小字报”里是这么说的:“闻一多在昆明为特务所狙击,甚为愤恨,在成都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会中有很多挽联。热烈发言的甚多,甚至有许多人泣不成声。我虽和他是朋友,毫无表示,井且说这些人认不得他,何以哭得像百姓如丧考妣。”

而对已垮台的罗隆基,李小缘做了平实的回忆:“1925年3-4月间在纽约认得罗隆基,因为他知道我搞关于中国的书目,要我为他搞一个‘关于鸦片战争的书目’。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抄起来给他,在离纽约的前一天给他。这个‘书目’到底怎样,始终无下落。回国后始终未曾联系过。解放后看他在报纸上很活跃,认为他太神气。原想和他通信,但没曾通过信。在纽约的时候只知道他是小政客,也从未往来。这次反右斗争,他是一个大右派,幸而未和他联系过。”
人事关系上,对南大中文系“三老”之一、时任南大图书馆馆长的胡小石,李小缘充满了尊敬,“胡馆长做我们馆长,我从心里拥护的。他年长,学问渊博,这可以帮助我的浅薄。在金石方面,他有很深的研究。在国学方面,我还是有所请示的……总之是于我们图书馆有益的”。而对图书馆年轻人不明白,认为他不到馆就不应该挂名,“我认为这是很不正确的……不将引起胡馆长的反感,而后损失的还是图书馆”。

而对其他同事,李先生就不无微词了。同样出身于金陵大学的化学家李方训先生,1952年被任命为南大副校长。李方训专业素质极高,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但和李小缘相处不佳,“无论有什么事,我愿意找别的校长来解决,愿意迟一二天,等别的校长来解决,我不愿意访问李校长”;老同事万国鼎评价李小缘做事为人是方形的,看来不虚此言。两人似乎并无大的过节,大概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吧,比如李校长在动员金大金女大合并时说,新的学校比旧的学校要百倍好千倍好,但小粉桥(即南京大学南苑)的草坪没有了,原来有的花草没有了,李校长说话不算数,李小缘有些不乐意。

1954年,有位严仲仪同志受校党委委派,协助李小缘主持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严同志出身于华东军政大学政教系,虽然才三十出头,但已有近十年党龄了,曾担任过南京市的区委宣传部长。李先生与这位口中的“严秘书”关系比较微妙,李先生提到了自己“有职无权”的问题,并且把“要钱要不到,要人要不到,但是党员一要就要到”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且“自此以后,凡是人事关系问题、经费问题,全请严秘书负责”。不过严仲仪倒并非极左狂热之徒,李先生对两人关系做了定量分析,“我和严秘书的关系是:90%-95%是两下配合的好,其余5%-10%是由于联系不好的未结合好。经过时间是可以结合好的”。严先生后来也成为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了不少图书馆专业论文。
李小缘最看重的莫过于图书馆藏品。曾有一套馆藏的《天学初函》,他不单清楚地记得数目(二十一种三十二册),也道得出流传(由文化研究所购置,后转入大图书馆),而且为后事忿忿不平。原来1934年福开森向金陵大学捐赠个藏时,曾来函借此书,当时的校长陈裕光是研究有机化学的,头脑灵活,用“偷鸡也要一把米”好不容易说服了李先生将书外借,可惜一直未归还。按说福开森为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的创始人,又长期担任金大校董会的董事,而且已将个人收藏悉数捐赠,李先生在时隔二十四年后,在已改朝换代、校名更迭后,仍念念不忘这套书,确实可称得上老校长匡亚明对他“惜书如命,爱馆如家”的评价。

正在筹备校庆一百一十五年的南京师范大学,底子是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教育系。南师艺术系很想把南大图书馆的艺术书籍拿去,这可惹恼了李小缘,他说:“艺术书不借出馆外,是国际惯例。七八年来,如果(南师)专心一致的搜购,也不难补充。我们开辟了教师阅览室,欢迎来看,他们也不来。借而不还是个人主义;有阅览室不来看,还是个人主义;不订出计划采购,专门向别的人叫嚷,这又是什么作风!”李先生是真把校产当私产了,且生气起来不假颜色,乃至“在外面开会,坐在一处很不好处”。
南京博物院就更不卖帐了。1952年,曾昭燏院长向南大借展文物,并声明“这是柯庆施招呼的”,但一年多过去了,南博毫无归还之意,且“把借去的东西,照像的照像,仿造的仿造,全未向我馆提过”。李小缘坐不住了,正赶上院系调整,他把博物院借展之事提交到“建校文物图书整理委员会”,并反复电话催还,仍无效。1953年曾昭燏来南大图书馆,他又提出归还事宜。曾很强势,只说请“孙叔平(时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来要”。曾走后,李先生大为光火,说“这是强权,没有公理的”,“这是曾国藩思想作风”。但又能怎样呢?李先生所做的,只能是“从此我不再到博物馆去了”。曾再强势,也不过“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于1964年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

南唐画家王齐翰所绘《挑耳图》 (又名《勘书图》),由福开森捐赠,算得上是南大图书馆镇馆之宝,单单这件文物,李先生就写了四条“小字报”。有些还是陈年旧事了,比如在“三反运动”中,把《挑耳图》展出是否有必要?万一折坏,谁应负责?1958年,南京博物院携书画前往上海博物馆办展览,来南大借展《挑耳图》。有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书画的专家,懂得保管,李先生说我们派不出人去,未允。这位工作人员说,你所顾虑的,是不是怕它的“娇气”?如果你做不得主,他可与党委会联系。最后,在李先生的坚持下,《挑耳图》用照像放大的方法寄去。收到后,这位工作人员写了一封信,将复制件退给了校党委会。这位工作人员是谁?在“小字报”里未点名,不符合李先生的风格,可能是编辑隐去了。李先生最后评价他,“不愧为将门之子”,结合之前的言行,看来来头不小。 李先生深知,《挑耳图》的事让自己成了“招风的大树”,“现在是在刮四五级风,将来还要刮八级风,把名字弄到报纸上,一定是有可能”, 但《挑耳图》是国宝,是有“娇气”的,应该要照应好它,“才对得起六亿人民”。

李小缘逝世后,南京大学为先生举行了降重的追悼会,胡小石馆长致悼词,郭影秋校长出席并讲话,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南大于逝者倒也不薄。如前文所言欧阳翥教授自杀后,据南大王觉非回忆,出事后,校领导担心被上级斥为未能执行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以主动检讨,并且“声泪俱下,惊慌失措”,而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却大发脾气,有“死了活该”、“示威”、“应该加以批判”之语。校领导精神立时轻松,传达时说“这是对他自己不负责,对人民不负责的表现”。不过这近乎一家之言,欧阳翥身后并未被批判,还成立了有五十一位教授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并且出版了《追悼欧阳翥教授》的小册子。南大档案馆藏《华东局宣传部转发南京大学孙叔平、陈毅人两同志关于该校生物系教授欧阳翥自杀事件的报告》,措辞也很理性:“这一事件反映了某些老教授受旧社会思想影响甚深,感情甚为脆弱,致一旦遇到了某些意外事情,容易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希各高等学校今后特别加以警惕,加强对老教授的团结和政治思想教育,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多加以关心,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李小缘纪念文集》也影印了李先生的遗嘱,遗嘱写于过世前夜。除了交代家事、叮嘱子女以外,关于自己的书籍,先生做了以下安排:“图书全部赠送图书馆,其不要部分还给家中作为妻子生活之资”;“我编的稿子和西文论中国之目录,希望图书馆好好保管,如果有人能编可以扩大编制,把一切的一切捐献出给人民”。
后人忠实地完成了先生的遗愿。1960年1月,李永泰、李永徽将先父中外书刊近三万册捐赠南京大学图书馆;1961年2月,李永泰将十万余张西人论中国之卡片及卡片柜(共36匣)赠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顾颉刚日记提及的“闻其所写卡片,已归本所”即此;同年,李永徽将祖上所遗之折扇、碑帖、字帖赠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1963年李永泰将十余斤手稿捐赠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年11月2日的清晨,薛冰先生在南京南王府大街逛旧书摊,见到一本《李小缘先生赠送书刊简目》,薛先生“一瞥之下,即知系难得之资料,一旦错过断无复见之机会,遂急与议价”。此即南大图书馆接收李氏藏书时登记造册的原始目录,由施廷镛主持编制。《简目》不单列出了图书的种类、数量,而且著录了每一本书的书名、编著者、出版时间、出版者等信息,并注明了估价。《简目》还列出了一大类,就是“有待选定未曾列入目录者”,包括幻灯片,卡片目录,手稿(大部分是图书馆学讲稿),以及抄录稿。编制者认为这些资料“零散繁多,它的内容,究与图书馆业务学习和研究,有何参考价值,须详细检阅,不是仓促间所能确定”。而这些手稿和卡片,正是李小缘先生毕生未竟之事业,希望图书馆“好好保管”并“扩大编制”,没想到不到一年,连有没有参考价值,都成了问题。
李先生到底是什么模样?在晚辈眼中,从外表看,从未见他着过西装,解放前总是长衫、长袍,解放后是中山服,也从未听他讲过“YES"、“NO”。他留学回来,运回了大量卡片,但送给岳父岳母家的,只是一把在美国买的红漆中国筷子。他厌恶拉拉扯扯,亲友凡“求差”、“担保”、“做中人”一类的事,都不敢去找他,怕碰钉子。他有情绪,他面对“图书馆馆长三人,秘书一人(一国三公)”的配置,无所适从,异常苦闷;他熟悉的领域突然陌生起来,《采菲录》这样的民俗学资料,居然成了黄色书籍;他与外界隔阂,当思想改造时,他才第一次听到“统一战线”,“以为是一个军事机关,下午去开会,午饭时告诉家中,今晚可能不得回来”;对时髦口号“厚今薄古”,他说“其结果将数典忘祖”,并天真的设想“多数人厚今,少数人厚古,可以不可以呢”;1957年3月,领袖动议,《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扩大,他开始订阅,“却又弄得思想更混乱,赶快停止不阅了”;至于变幻莫测的苏联政治人物如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忽然一天看不见他的名字了”,他只能说“我不明白”。
但他仍有激情,仍愿意发出声音,1955年当选为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时,他提出“保护好南京城墙”、“保护南京栖霞山摩崖石刻”的议案;在当时“看图书馆工作,是无须要学识,任何人都可以行”的言论下,1956年在高教部举行的全国高校图书馆会议上,他仍反复声明“高校图书馆应该是学术性机构”,这是一位学问家的真知灼见。

这样一位朴素、端方、耿介的学人,后人尊其遗愿,骨灰撒入黄海。后来,其衣冠与妻朱淑贞的骨灰,合葬于南京南郊普觉寺“婺源馀庆堂李氏墓园”。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