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献祭、暴力与驱魔仪式
神圣的祭祀为何总与暴力相关?痛打“替罪羊”何以维护社会内部的稳定?法国当代思想家勒内·基拉尔认为,人类族群中普遍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杀死“替罪羊”可将对内的暴力隐患释放到族群之外,从而保全族群内部的和平稳定。因此,暴力的祭祀行为并非宗教自身的产物,而是族群化解内部矛盾的需求。
*文章节选自《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 ([法]勒内·基拉尔 著 周莽 译 三联书店2022-4)“第五章 狄俄尼索斯”

《权力的游戏》剧照
文 | [法]勒内·基拉尔
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有一些节日长久保留着仪式性。现代观察者尤其从中看到对禁忌的触犯。性的混杂得到宽容,有时甚至被要求如此。在某些社会中,性的混杂甚至可能发展到普遍的乱伦。应当将违犯禁忌纳入更广的差别普遍消失的框架:家庭与社会的等级暂时被取消或被反转。孩子不再服从父母,仆人不再服从主人,附庸不再服从领主。差别被消除或反转这一主题重现于节日的审美附属部分,不协调颜色的混搭,对两性易装的使用,穿着花里胡哨服装的愚人的到场以及他们永远驴唇不对马嘴的对答。节日期间,那些违犯天性的配对,最无可预料的相遇,暂时得到容忍和鼓励。
节庆中,差别的消除,如人们能料想到的,往往与暴力和冲突联系在一起:下级辱骂上级,社会的多元群体相互揭露彼此的可笑和邪恶,失序与争议当道。在许多情况下,敌对的主题仅仅以游戏、比赛、或多或少仪式化的体育竞技的形式出现。到处的工作都停下来,人们投入过度的消费,甚至集体浪费几个月里积累起来的物资。
我们毫不怀疑节日构成一种对祭祀危机的纪念。人们在欢乐中回忆一种如此可怖的经验,这可能显得古怪,但这一谜题容易解释。那些纯粹节日的元素,那些最让我们吃惊而最终主导节日的元素,甚至那些在演化中唯一存留下的元素,它们并非节日存在的理由。真正的节日仅仅是对献祭的准备,而献祭标志着节日的顶点与结局。罗杰·卡卢瓦(Roger Caillois)注意到,关于节日的理论应该与关于献祭的理论衔接。差别的危机与相互对等的暴力可能成为欢乐纪念的对象,那是因为它们是作为宣泄的解决的必需的前奏出现的,它们的结果是宣泄的解决。创始的暴力的集体一致的吉祥性倾向于向过去回溯,倾向于越来越渲染那场方向得到反转的危机的不祥侧面。暴力的无差别化要求有利的寓涵,最终让它成为我们称作节日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同类的一些诠释,这些诠释可以至少部分地被纳入节日框架。比如乱伦最终获得一种吉祥价值,看起来几乎独立于献祭。在某些社会中,贵族甚至工匠或多或少隐蔽地借助于乱伦,目的是让乱伦给他们“带来吉祥”,特别是对某个困难的事业进行准备。与非洲君主的即位和重获青春相关的仪式往往具有一些特性,让它们接近于节日。反过来说,在某些并不涉及真正的君主的节日中,我们仍看到一位临时的国王,有时是一位“愚人王”,他同样只是供献祭用的牺牲。在节日结束时,被祭杀的将是他或者他的代表。君权,不论真实还是虚构,不论持久还是短暂,总是来源于一种以替罪牺牲为中心的对创始暴力的诠释。
节日的功能与其他献祭仪式的功能并无不同。涂尔干(Durkheim)早已明白这一点,节日即通过重复原初经验,通过复制被看作所有活力与丰足的源头的起源,让文化秩序保持活力和获得更新:的确,那一时刻,族群的统一性最紧密,对重新堕入无休止的暴力的恐惧最强烈。
文化秩序被初民看作应该保有和加强的一种脆弱而宝贵的财富,绝不应该抛弃、改变甚至做出任何通融。在节日背后,对于“禁忌”,既没有怀疑,也没有反感,怀疑与怨恨是我们现代人自己的特征,我们把这些投映到初民的宗教思维之上。著名的压力释放说(release of tensions)、没完没了的放松说(relaxation),这些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俗套,仅仅不完整地把握了仪式行为的某些侧面,这些理解是出于一种与原始仪式的精神完全不同的精神。

酒神的狂欢,提香
节日依赖对暴力机制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设定在祭祀危机与危机解决之间存在的延续性。祭祀危机本身从此与危机的有利解决不可分割,危机本身变成人们享乐的素材。我们已经看到,以王室乱伦为例,对于危机与危机解决之间的关系,宗教的思考可能采取两条相反的路径:有时是延续性的路径,有时是非延续性的路径。这两种诠释都部分地真实,同时部分地错误。事实是在危机与创始的暴力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延续性和某种非延续性。宗教思维可能采用这两种解决方法中的一个,并紧紧抓住这一个,随后则是固执于此,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宗教思维差一点就转向了另一种解决。
我们几乎可以从理论上假设,后一种选择(非延续性)会是某些社会的选择。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节日的另一面,还应该存在一种反节日(anti-fête):献祭性的驱逐仪式之前并不是一个放纵期,驱逐仪式是要结束一个极端禁欲期,而禁欲期中人们对禁忌的遵守尤其严格。在禁欲期,族群会采取异常谨慎的措施,以避免重新堕入相互对等的暴力。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某些社会拥有一些仪式,它们既与节日非常类似——同样具有周期性,正常的社会活动被中断,当然,这是些献祭性的驱逐仪式——同时又与节日如此不同,它们在人类学诠释层面构成与王室乱伦的难题类似的谜题,有时候是人们要求的,而有时候则相反是被人拒绝的。在这些仪式中,文化禁忌远未临时得到解除,而是全部得到了加强。
斯威士兰的丰年祭仪式在多个方面都符合反节日的定义。在整个仪式期间,连最合法的性关系都受到禁止,甚至睡懒觉也被禁止。个人必须避免身体接触,甚至对自己身体的接触。他们不能盥洗、不能挠头等。不洁即暴力的传染的急迫威胁压迫着每个人。歌唱与喊叫被禁止。如果孩子玩耍时太吵,人们会训斥他们。
在《金枝》中,弗雷泽给出了一个绝佳的反节日的例子,即非洲黄金海岸地区海岸角(Cape Coast)的例子。在四个星期里,听不到任何鼓声和枪声。集会商议不被允许。如果出现不同意见,如果争吵起来,对立双方就一起去见酋长,酋长会不加区分地给双方施以严重处罚。为了避免因为丢失的牲畜而导致的纷争,无主的牲畜将属于任何发现它的人,真正的主人不能控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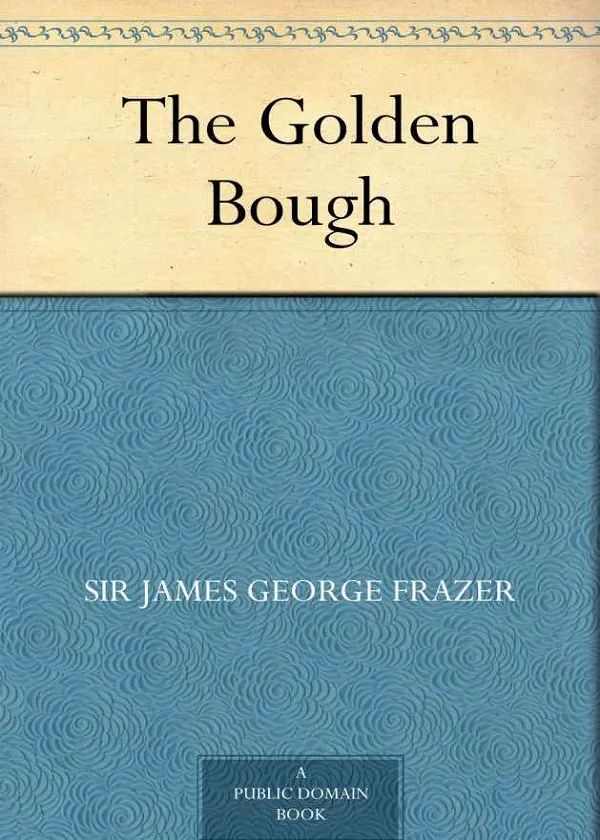
弗雷泽:《金枝》
事情很明白,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预防一种暴力冲突的威胁。弗雷泽没有做出解释,但他作为人类学家的直觉要比他的理论见解高,这促使他将这类现象与节日列在一起。反节日的逻辑与节日的逻辑同样显著。反节日是复制暴力的集体一致性的那些吉祥的侧面,同时避免暴力之前的那些可怖阶段,在反节日中这些可怖阶段是用否定的方式加以纪念的。不论两次净化仪式之间的间隔有多久,随着人们距离上一次仪式的时间越来越远而距离下一次仪式越来越近,暴力爆发的威胁显然与日俱增。不洁性积聚起来:在举行仪式之前紧邻的阶段,在这个与祭祀危机联系起来的阶段,人们的行为必须异常谨慎。族群将自身看作一个真正的弹药库。农神庆典式的放纵向反面转变,酒神节的放纵变成了斋戒期,但是仪式并未转变自己的目标。

酒神与阿丽亚德尼,提香
在节日与反节日的范围内,应当存在而且实际存在着一些“混合体”,它们符合对危机与建立秩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精细的诠释。这种诠释既考虑延续性又考虑非延续性。至少在某些情况中,节日与反节日的分歧也许构成一种后起的现象,与人们远离了本质性的暴力有关,与更加高级的神话得以建构有关。现代观察者采集到这种新近的分歧,因为分歧符合观察者自身的偏见,在某些情况中,观察者加大这种分歧,或者说他要对分歧完全负责。
我们错误地认识了节日的真正性质,是因为仪式之后的事件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真正的目的丧失了,附加物战胜了本质的东西。于是,仪式的统一性倾向解体为单一的和互相对立的视角。当宗教思维达到接近我们的无知的程度时,仪式便获得一种被我们看作本质和原始的特性,而其实这种特性是后起的和派生的。禁欲和苦行被我们看作与节日背道而驰,而它们却与节日具有相同的起源,在仪式仍然具有活力的地方,它们与节日常常处于“辩证的”平衡中。仪式越是偏离自己的真正功能,它们便越是彼此有区别,于是,仪式就越是倾向变成学术评论的对象,而学术评论旨在对它们进行越来越多区分。学术的描述必然会坚持走这条道路。
现代世界,特别是在弗雷泽之后,已经了解到某些节日曾经包含着用人类献祭。但我们远未怀疑人祭这一习俗的所有区别特征和它所包含的无数变体都直接或间接上溯到一次集体的和创始的暴力,一次具有释放意义的集体私刑。但是,要证明事情如此并不难,虽然所有献祭性的祭杀都已消失了。这种消失可能让其他一些仪式残留下来,很容易证明这些仪式的献祭性,那就是驱魔仪式。在许多情况下,驱魔仪式处在节日的高潮,同样也是节日的尾声。这意味着它们在节日中占据着与献祭相同的位置,虽然驱魔仪式与献祭没有直接关联,但我们很容易看出它们与献祭起着相同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它们代替了献祭。

《9号秘事:女巫审判》剧照
如何驱逐魔鬼或恶灵?人们发出喊叫声,愤怒地挥舞手臂,人们用武器或炊具制造很大的撞击声,人们对着虚空用棍棒击打。表面上看,用扫帚驱赶魔鬼,这再正常不过,再明显不过,只要足够愚蠢到相信魔鬼存在。现代的智者,被弗雷泽解放的人,看到迷信将恶灵等同于某种大野兽,如果能够惊吓到它,它便会逃走。理性主义对一些习俗不大提出问题,这些习俗显得再明白不过了,因为理性除了认为它们是可笑的,拒绝给予它们任何别的意义。
在当下的案例中,如同在许多其他案例中,志得意满的理解和“纯属自然”的东西有可能掩盖最有价值的东西。驱魔行为是一种在原则上向魔鬼或其协同者施加的暴力。在某些节日中,结尾时的这种暴力之前有一些对驱魔者之间的战斗的模拟。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与许多献祭仪式的序列类似的序列:祭杀之前有仪式性的争吵,施祭者之间的或多或少具有真实性的冲突或者模拟的冲突。在所有案例中,这一现象应该揭示出同一个解释类型。
在弗雷泽提到的一个例子中,村庄的年轻人一家一家进行驱魔仪式,但每家都独立进行。一轮仪式的开始是对于应该最先去哪一家的争吵。(作为合格的实证主义者,弗雷泽小心不遗漏细节,虽然这些细节是他的理论最不能解释的。单凭这一点,他就值得我们感谢。)作为前奏的争吵是在摹仿祭祀危机,争吵之后的献祭或驱魔摹仿集体一致的暴力,这种暴力的确是直接接在相互对等的暴力之后的,与相互对等的暴力的区别仅在于它的神奇后果。
一旦争吵结束,集体一致性便达成了,现在是替罪牺牲的时刻了,也就是仪式的时刻。争吵所争夺的东西就是仪式本身,换言之,他们争夺的是对必须加以驱除的牺牲者的选择。在危机期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就是通过战胜最直接的对手而战胜暴力,每个人都想给予对手具有决定性的一击,让这一击之后不再有还击,因此,这最后一击将会充当仪式的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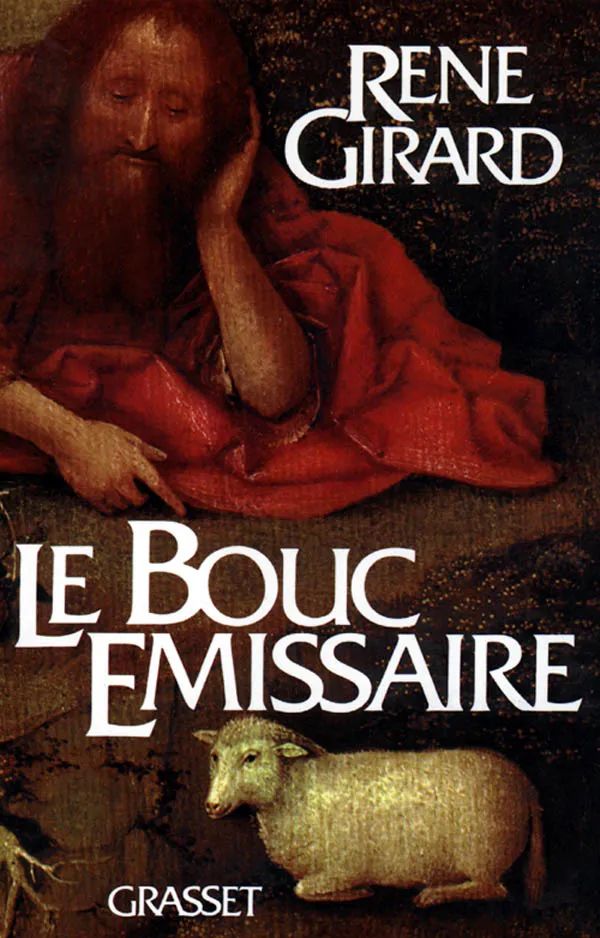
勒内·基拉尔:《替罪羊》
某些希腊文本模糊谈到一次——用人类——献祭,是某个族群、城邦、军队决定献给某个神的。相关者对于献祭原则达成一致,但他们对选择牺牲者却意见不一。要想理解其中涉及什么,诠释者必须将事件的顺序颠倒过来。暴力首先到来,它是无理由的。献祭的解释随之而来,这种解释真正是献祭性的,因为它掩盖了暴力的无理由,这是暴力的真正让人无法忍受的元素。献祭的解释来源于结尾时刻的暴力,来源于最终被揭示为具有献祭性的暴力,因为这暴力结束了争执。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神话建构。集体杀害恢复了秩序,反观性地对控制了群体全体成员的彼此相互杀戮的野蛮欲望给出了一种仪式框架。杀戮变成献祭,杀戮之前的混战变成关于最合适的牺牲者的仪式性的争吵,这个牺牲者要求信众的虔敬,或者要求神祇的偏爱。实际上,这便是回答“谁将祭杀谁?”这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应该驱魔的房屋的争吵,掩盖着某种类似的东西,即危机和危机的暴力解决的整个进程。驱魔仅仅是一条复仇链条中的最后一环。
投入相互对等的暴力之后,参与者一起向虚空打击。这里,一个真相显露出来,所有仪式的共同真相,但从未像在这种驱魔仪式中这么明显。仪式性的暴力不产生任何对手,它的面前不再有任何敌对者。只有他们大家一起进行打击,却没有人还手,那么驱魔者们便不会重新开始向彼此动手,至少不是“真正”动手。此处,仪式揭示出它的起源和功能。借助替罪牺牲机制而重新建立的集体一致性不应该被打破。族群想要针对“恶灵”保持统一,忠于自己的决定,不重新堕入无休止的敌对,仪式强调并加强这一决定。宗教思维不断回归到最为神奇的奇迹,回归对暴力的胜利,这胜利来得如此之迟,付出的代价如此高昂,在人们眼中这胜利常常被看作最值得被人们以千百种不同方式加以保存、回忆、纪念、重复和复苏的东西,目的是预防从超验的暴力重新堕入相互回应的暴力,堕入不再是“开玩笑”的暴力,堕入分裂性和毁灭性的暴力。
▼

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
[法]勒内·基拉尔 著 周莽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4
ISBN:9787108073044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内在经验》
[法]乔治·巴塔耶 著 程小牧 译
《文艺杂谈》
[法]保罗·瓦莱里 著 段映虹 译
《梦想的诗学》
[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刘自强 译
《成人之年》
[法]米歇尔·莱里斯 著 王彦慧 译
《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法]安托万·贝尔曼 著 章文 译
《罗兰·巴特论戏剧》2021新书
[法]罗兰·巴特 著 罗湉 译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2021新书
[法]勒内·基拉尔 著 罗芃 译
《1863,现代绘画的诞生》 2021新书
[法]加埃坦·皮康 著 周皓 译
《入眠之力:文学中的睡眠》
[法]皮埃尔·帕谢 著 苑宁 译
《祭牲与成神》
[法]勒内·基拉尔 著 周莽 译
《文学第三共和国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2022即出)
[法]安托万·贡巴尼翁 著 龚觅 译
《保罗·利科论翻译 附:本雅明<译者的任务>》(2022即出)
[法]保罗·利科 著 章文 译
《论国家:法兰西公学院课程1989—1992》 (2022即出)
[法]布尔迪厄 著 贾云 译
《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2022即出)
[法国]达尼埃尔·阿拉斯 著 马跃溪 译
《犹太精神的回归》(待出)
[法]伊丽莎白·卢迪奈斯库 著 张祖建 译
《人与神圣》(待出)
[法]罗杰·卡卢瓦 著 赵天舒 译
原标题:《献祭、暴力与驱魔仪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