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历史学家能从“非虚构写作”中学习什么?
【编者按】
“非虚构写作”目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一个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会怎样看待和反思这种写作方式呢?以严谨、求真、价值中立为要求的历史学家们,又能从汪洋恣肆的“非虚构写作”中,学习些什么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琳的文章,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2016年11月底,我应“丽泽书院”的邀请,为同学们主持了一次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沙龙,这篇文章就是从那次沙龙的讲稿整理而来。她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写作,是我个人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不吐不快的想法。坦白地说,我也不愿意把她写成一篇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因为她所聚焦的“非虚构写作”,本身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加自由、更具亲和力、表现力的叙述方式。毋庸讳言,“非虚构写作”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但也正是这种类似于青春期少年的叛逆、浪漫和不拘一格,才让她具有了直击人心的魅力。

一、什么是“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是时下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许多新的出版物都标榜自己属于非虚构写作,一些门户网站也开辟了非虚构写作专栏,比如“腾讯.谷雨”。2015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假如与我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这其实也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
可是如果我们犯了学者的职业病,必须要对“非虚构写作”下一个定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少有人对这个词有特别清晰又特别自信的理解。我曾经专门请教主持过“非虚构写作沙龙”的著名媒体人张丰先生,究竟什么才是他理解中的非虚构写作,但是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个问题重要吗?”这样的情况,与其说是因为人们少了一点学者的严谨和概念抽象的自觉,倒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写作形式现在仍然在不断的探索和试验之中。各种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写作手法的新作品令人眼花缭乱,也让习惯于学术思维的头脑感到深深的无力,甚至是一说即成错。但是为了给后面的讨论确立一个前提,我们还是要交代一下什么是“非虚构写作”?或者说在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中,什么是“非虚构写作”?
如果你在“百度”上输入“非虚构写作”这个词条,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定义就是:
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写作。又被称为“第四类写作”。
这个定义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对于理解我们所要谈论的这种“非虚构写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如果你接受了这个定义,那么你一定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区别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非虚构写作”和人们之前非常熟悉的纪实文学、传记、调查报告、游记、回忆录,甚至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学或社会学论文?表面上看,后面讲的这些也是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呀。但是我们谈到“非虚构写作”的时候,说的好像并不是这些。也就是说,现在被许多写作者实践着的,也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可的,其实是一种狭义的“非虚构写作”。根据我自己有限的阅读经验,一个高质量的非虚构作品,大概要具备以下几点特征(或者至少要具备以下一部分特征):
1、叙述历史或当下真正存在的人或事,简而言之就是“写实”。
2、用深度介入的方式挖掘真相,也就是“求真”。
3、用精心构建的叙事结构、写作技巧和语言来塑造作品的品质,或者可以说是“好好讲故事”。
4、用个人的视角进行独立的写作。
在我看来,最后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践行非虚构写作的人,要给他们自己写的东西重新起一个听起来相当拗口的名字。因为这种写作,她在价值观上是独立而且叛逆的,她其实是基于人们对传统文学和历史写作方式的不满,故而自立门户出来的一个部分。而且至少在今天的中国,连“非虚构写作”的载体也并不是那么主流。许多进行非虚构创作的人们,并没有开宗建派、著书立说,他们许多都是自由作者,依托新媒体、自媒体进行创作。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近乎“野生”的状态,使得非虚构写作能够在束缚和苛责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自由探索,专注表达,从而迸发出直击人心的魅力和生命力(笔者按:国外的非虚构写作情况非常不同,笔者了解不深,所以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而讨论)。
下面,我就从一个学院派历史研究者的视角,结合一些深深打动过我的非虚构作品,来谈一谈与“非虚构写作”相关的几个问题。我并不想说“如有不当,还请指正”之类的套话,因为这篇小文其实只相当于一个普及帖,肯定会有很多的“不当”,简直不值一驳。但是毋庸讳言,这篇文章中不免会有一些对前辈师长、年轻学友的苛责,然而这只是出于对现有历史叙述方式的反思,没有任何不敬之意。如有无意之中的冒犯,在此先行致歉!
二、非虚构写作如何“写实”?
说到“写实”这一点,历史学家大概是最有自信的。但是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其实很多写历史的学术或非学术作品,并不是特别尊重或者在意那个所谓的“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那部妇孺皆知、被许多人视为明史启蒙读物的《明朝那些事儿》。每年开“明清史专题”课程的时候,都有一些同学来问我:“老师,我的读书报告能不能写《明朝那些事儿》?”我的回答永远都是“Absolutely No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部书就好像把明朝的历史放在哈哈镜前去照一样。下面举几个例子:
急性子的夏言兴冲冲地跑去西苑了,他要表达自己的兴奋。而那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严嵩,却露出了笑容。
徐有贞终于成功了,他带着疲惫的身躯和长时间的笑容,独自站在大门前,挡住了上殿的道路。
被吓出了一身汗的李贤和王翱这才松了一口气,落到这么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手里,他们也只有认命了。
这样文字当然非常能够讨好读者,因为它生动,画面感很强,不仅有人物的唱念坐打,甚至还有他们的内心独白。那阅读体验,简直和看电视剧没啥区别。你想一想,如果换一种平淡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效果呢?“夏言独自走向西苑去了,严嵩独自坐在内阁值房”。“徐有贞站在大门前,挡住上殿的道路”;“最后,曹钦并没有杀李贤和王翱”。不用说,这两种叙述方式的表现力,简直就像是五粮液和白开水的差别。但是我要告诉你,根据我读明代史书的经验,后面一种表述可能是更接近史料的原文的。因为即便明代人的率真和表达欲远超中国古代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他们写下的大部分著作仍然没有那么丰富的细节。也就是说,在上面这三句话中,大约有一半的文字都属于作者添加上去的水分。不管是对于学术性的历史写作而言,还是对于非虚构性的历史写作而言,这都是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
你或许会说,这就是些细节而已,无伤大雅,用不着那么较真吧。但是如果在作者的头脑中,迎合读者的想法占了第一位。那么在细节上可以注水,在关键性的地方同样可以注水。所以我认为,《明朝那些事儿》更适合用来娱乐大众。如果一定要用“虚构”或“真实”来评判的话,那我会说它是一部“半虚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写现实的事情,注入一定的水份还好一些,因为你的读者或许比你了解得更多,或者至少都是有一定的亲身经验和常识的,能够分辨你写的东西里面哪些是实,哪些是虚。但是历史作品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几乎完全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你注入的水分很难被发觉。所以就会让人们认为,那些被注过水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历史。所以虽然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明朝那些事儿》,但我从不把他推荐给我课堂上的同学。
如果说非专业的历史作家出于各种原因臆造细节,那么专业的历史学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恰恰是无视细节。《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当然,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李中清先生是曾给予我很多教导的老师,,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口史领域最振聋发聩的作品,至今仍然未被超越。而且更令人叹服的是,两位作者对于中国“一胎政策”的评估和预言,居然被后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一一证实。但就是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到非常不适,那就是关于溺婴的论述。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听任人口恶性膨胀,而是有一些行之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溺婴就是其中的一个。书中的原文如下:
溺婴是一种理性决策的结果,根植于一种独特的生命观文化。中国的农民不会把杀死亲生子女看作是谋杀。中国人在传统上并不把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看作完全的人。实际上,有一句很有名而且经常被提到的话,说婴儿只是幼崽,到“两岁”生命才开始。因此中国的农民和贵族同样可能把溺婴看作是一种“产后流产”。
坦白地说,从我十年前第一次看这本书到现在,这句话始终令我充满质疑而且抵触。两位作者认为,溺婴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通常会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他。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再仔细去看他们引用的文献,都是《唐会要》中说怎样怎样,《周礼》中说怎样怎样,明朝的丘浚说怎样怎样。可是我想问的是,写《周礼》的人和写《唐会要》的人他们溺过婴吗?明朝的丘浚他溺过婴吗?为什么相信他们能够真实地表达父母溺婴时的内心状态?虽然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个时代的父母真的会完全按照另一种逻辑和感情模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吗?而且用溺婴来说明中国人口控制机制的有效性,进而证明清经济、社会并非那么不可救药,这实在是一个说不通的逻辑。如果一个时代的发展要一定程度上依赖那些被溺死的小小的亡魂,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还有什么正面评价的意义呢?所以,“传统的中国人怎样看待溺婴”,其实是一个被作者忽略,但实际上需要去证明的细节。
三、非虚构写作如何对待细节?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优秀的非虚构写作,是怎样对待细节的呢?
在谈论这一部分之前,请允许我首先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名为《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她源自于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The Nieman Foundation)每年举办的尼曼叙事新闻会议(the Nieman Conference on Narrative Journalism)。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非虚构叙事的艺术和技巧”,参与者包括全世界的新闻记者、编剧、编辑和作家。这本书汇集了51位会议发言人的91篇文章,从各个细微的环节告诉你成功的非虚构写作者究竟如何工作。即便你不想进行非虚构写作,此书也绝对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读物。

下面再回到我们正在谈论的“细节”问题。我个人的体会是,好的非虚构写作一定是关注细节的。在这本书中,普利策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展示了她的作品《尼古拉斯的男子汉生活,10》(The manful life of Nicholas, 10)中的一个细节:
孩子们排成一列,还有他们的围巾、外套和腿。男孩们低下头,这样母亲还能再为他们做一次梳理。虽然她自己上课要迟到了。丢失的手套引起一阵骚乱,接着母亲摇了摇一瓶喷罐,在孩子们的外套上、头上、摊开的小手上来回喷洒,以庇护孩子们上学这一路,因为他们要面对这疯狂而危险的世界中的黑帮招募和子弹。喷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闻起来像药房香精的宗教圣油。孩子们紧闭眼睛——为了他们能够在日落时分活着并安好地归来,安杰拉的喷雾,总是长足有力。
正是从这个颇具仪式感的细节中,伊莎贝尔瞬间理解了暴力对这些生活在芝加哥南部底层家庭的孩子而言,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在看到这个场景之前,她本来已经就“在暴力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的问题,与孩子的母亲聊了好几个小时,都已经准备结束采访开始写作了。但是这个场景的出现,让她改变了写作思路。后来,这段文字如一个特写镜头一般被放在文章的末尾,收获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表达效果。
但是另一方面,负责任的非虚构写作者也从不会为了讨好读者而去臆造细节。极其擅长非虚构写作的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曾经说过:
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一个读者告诉我,他尤其喜欢《八月炮火》中的一段,那一段写到英军在法国登陆的下午,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他以为是我艺术加工出了一种末世景象,但事实上那是真的。是我在一个英国军官的回忆中找到了这个细节。如果存在艺术加工,那也仅仅是我挑出了这个细节,最终用对了地方。

以前我常常认为,只有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撰写的历史论文,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严谨和真实。但事实上,“真实”或许只是一个价值目标,在达致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学术性写作方式和非虚构写作方式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与学院派的研究者相比,非虚构写作者要持守这样的信念,需要更多的诚实与自制。
为了如实地展现事情原本的样子,非虚构写作者有时甚至会面临伦理上的困境。美国记者索尼娅.纳扎里奥(Sonia Nazario)的作品《被天堂遗忘的孩子》(Enrique’s Journey: The Story of a Boy’s Dangerous Odyssey to Reunite with his Mother)曾经获奖无数。这本书讲的就是作者跟随一位名叫恩里克的洪都拉斯男孩,非法进入美国国境去寻找他在北卡罗莱纳州做保姆的妈妈。在这个过程中恩里克经历了很多危险,包括严寒、酷热、饥渴、响尾蛇、恶警、黑帮、强盗、湍急的河水、行驶的火车。然而除了危及生命的情况(如溺水),索尼娅一直没有出手帮助他。最后恩里克身上分文全无,一天只靠洗车挣一顿饭钱,他想要打电话给妈妈。可是虽然索尼娅身上有一部手机,但是她一直没有借给这个孩子。
依常理来说,这样的做法已经伤及人道。但是对于非虚构写作者来说,如果处处出手相助,必然会污染细节,进而导致整部作品的真实性流失,这违反了非虚构写作的工作纪律。而且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还怀抱着另一层意义上的“善”。下面就是她的一段自白:
任何报道这类故事的人都会见证到伤害。这是叙事性报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考量一名孩子所受到的伤害,也见证现实并有力地传递给读者的好处进行衡量。像《被天堂遗忘的孩子》这样的故事可以激励我们的读者更多地思考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作为叙事记者,我们必须努力写出最能打动人心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多了,至少我们不用面临这样进退两难的纠结。
在“明清史专题”的选修课上,我曾经出过一道“穿越题”:
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到1644年,你最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籍、居住地、民族、职业、性别、年龄等)?请试着描述那时TA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其实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训练。有的同学告诉我,他们答题的时候每写一句话都很难,因为不知道他笔下设定的这个人物究竟是不是做过这样的事情。一旦具体到细节,就觉得好像处处都需要去认真考证一番。其实有这种感觉就对了,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或者优秀的历史剧、历史小说)相对于学院派的历史写作更考究,也更难的地方。因为论文可以省去或回避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出色的叙事则必须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不仅要有关怀和情怀,还要在细微之处精雕细琢,任何细节的失真都会让读者瞬间出戏。近日,看到一则对演员王功松先生的专访,他讲到在扮演“荀彧”这个角色之前,他会去考证“荀彧作为文人身边应该带什么类型的香”,“他们吃饭用的碗碟究竟是什么样式”,甚至细到“碗底一定要有‘君幸食’三个字”等等。看到这里我只想说:“谁说只有历史学家才有‘求真’的本事?”
四、“深度介入”何以可能?
所谓的“深度介入”,简单说来就是与你的对象一起生活。
为了写一群来自墨西哥的挑蟹肉女工,美国记者安妮.赫尔(Anne Hull)曾经与她们一起工作。这份工作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外,但是当她真正站在工作台前开始劳作,她才发现这份工作极其辛苦而且艰难。因为每天要站10个小时,而且锐利的蟹壳和刀子随时可能划到手。有的时候,手已经因为疲劳而发抖,但却不可以停下来。这时,她才理解了这些女工的艰辛,以及国外劳工在美国的境遇。
一个更加疯狂的例子是美国作家特德.康诺弗(Ted Conover),为了展现惩戒制度,他把自己送进监狱工作了10个月。在这10个月中,他成功地申请了惩教官的工作,每天把犯人领进领出他们的囚室,和他们交涉,在工作间隙记下各种细节,然后还要时时担心自己的“卧底”身份暴露,被那些暴力的同事打晕在停车场。最后,他写出了影响极大的作品《新杰克》(Newjack: Guarding Sing Sing)。
这种写作方式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它与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非常接近。但不同的是,如果以非虚构写作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更强调的是突破空间上的距离。走到你研究的现场,与你的研究对象相接触。但事实上,心理的距离是更难突破的。在一些人类学作品中(尤其是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读者始终能感受到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心理上的疏离。当然,近年来所阅读到的一些人类学研究,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在关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中,“深度介入”的一个典范,我认为是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何伟在27岁的时候,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被派到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教书。《江城》这本书,记录了他在这个城市两年的生活。我个人觉得整本书最具魅力的部分,就是他对他的写作对象透出很多的理解和善意。比如让小孩到他的房间里面疯玩,和学生的亲密互动,在饭馆老板的家里共度春节。全城人都像看热闹一样看他晨跑,他只是说不习惯。甚至在大街上被人围观、谩骂,在他的笔下也是徐徐道来、云淡风清。我能够感觉得到,这种善意绝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非常丰满,作为一个在川东地区生长的人,我觉得我平日里见到的家乡也就是那个样子,他甚至还发掘出许多当地人都感受不到的东西。这说明,他的写作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对他卸下了心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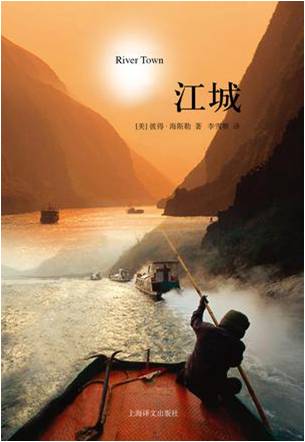
另一个触动我极深的例子,就是台湾学者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虽然是一部学院派的人类学著作,但是我认为已经具备了优秀非虚构写作的所有要素。也正是因为如此,此书的简体版在2016年甫一面世,就收获了许多赞誉。在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了自己“凉山遇鬼”的故事:
妈呀,果真,差不多七点左右,我眼睁睁地目睹一颗石头从那个角落射出,落在我跟前。“它真的想给我看?”我脑中冒出这个念头,惊愕不已。拉铁看着我说:“你看见了吗?”我点点头,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捡起石头仔细端详,然后问我:“你觉得这个石头被烧过吗?”他把石头递给我,棱角确像是烧黑了。“嗯,是被烧过了。”我边回答,边在手中把玩、端详着这颗小石子。拉铁又满脸严肃地蹦出一句:“火葬场有一堆像这样的石头。”我像被电到似到,立刻甩开石子。太恐怖了!
作者非常坦率地承认了“鬼”的存在,没有做任何的合理性解释。这样的“怪力乱神”出现在学术作品中,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正是因为这个故事,让读者看到作者与她的写作对象之间的相互接纳。在大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比如对于艾滋病的叙述,作者并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评价,而是从理解的视角展现出离家、吸毒、坐牢,其实类似于当地年轻人的一种成年仪式。因为在家乡没有出路,年轻人的心又向往着精彩的世界,所以才会出现许多令人悲伤的事情。“学问无非世道人心”,作者于此已然通透。

最令人动容的还是一部名为《没眼人》的作品,她的作者亚妮本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2002年她到山西拍摄纪录片,认识了一群被当地人称为“没眼人”的盲艺人。从此她中断了风生水起的主持人工作,在太行山深处与11个没眼人共同生活了8年,只为记录他们的人生。她与没眼人之间的厚重情谊,没眼人生活中那些细水长流的、嘻笑怒骂的、哀婉缠绵的、憾人心魄的故事,都绝非这篇小文所能绕舌。我只能说:“翻开这本书,你一定不会后悔!”

与非虚构写作者相比,历史学家有时倒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惊人的隔阂。研究一个城市历史的人有可能从未到过这个城市,甚至连这个城市的地图都没有仔细看过。讲授阳明心学的老师,背熟了“知行合一”、“心即是理”,却从未真正理解王阳明庭前格竹、龙场悟道时的心路历程(我其实是在说我自己啦)。然而,历史学家在今天为何还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一度被“贴标签”的思维所统治。历史学要真正贴近她的研究对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中,我也常常看到那些充斥着大话、套话的文章,好像除了这些就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这当然与一个时代的语言习惯有关,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膜,所以说不出来更加实在的、更加意义清晰的东西。我们太习惯于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或者书斋里构建自己的研究,反而把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弄丢了。
当然,历史面对的是不可重现的人与事,但是要用心体贴也绝非虚妄。去年读到李洁非先生研究明代人物的一系列著作(《龙床》、《黑洞》、《野哭》),虽然不是一板一眼的学院风格,也并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非虚构写作”,但是作者对于那些人和事的体悟真的是非常用心。他是作为一个人,去理解另一个人,虽然这个人生活在几百年前,虽然他只能通过文字来走近这个永远不能再开口说话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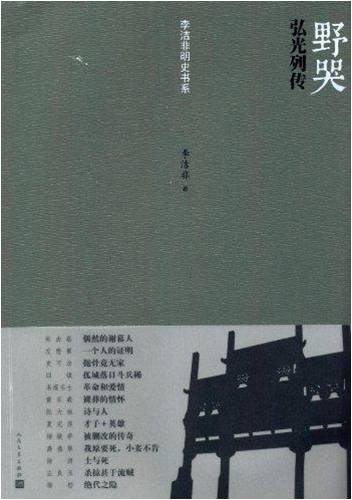
五、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在她的著作《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中谈到讲故事的重要性:
当你为大众写作,你就得写得清楚,写得有趣。
没有必要在准确和优美中二选其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不能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读者存在,作家的文字生于书页,也将死于书页。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
世间无穷事,但化为笔下的历史则需要表达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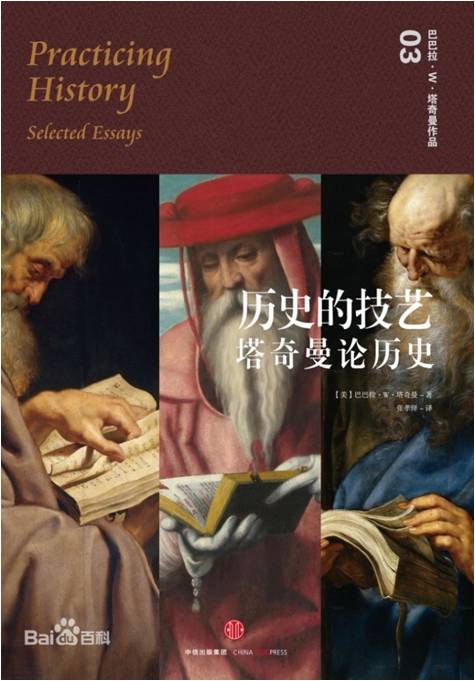
然而,学院派的历史教育普遍轻视讲故事的能力。许多学术水平很高的史学论著,却不太在意故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可悲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具有惊人的讲故事和吸引读者的天赋,这是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无法企及的能力。
在学术作品中,能否加入合理而又出彩的叙事呢?我想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方面堪称大师的史学家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的叙事巧妙而又多变,颇有非虚构写作的风格。不信请看:
朕于骑射,哨鹿、行猎之事,皆幼时习自侍卫阿舒默尔根:阿舒默尔根直言禀奏,无所隐讳,朕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共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鋓狲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意射获诸兽,不计其数矣。
这是《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一书中的一段。你能看出来这些事实都来自于某个史料,但是又表达得非常自然。而且用第一人称,瞬间就让读者和作者都直接面对康熙这个人。对于作者而言,这样做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因为如果你不能写出一些实在的、有深度的东西,这种第一人称的写作就完全写不下去。接着再看下面一段:
我们的这位胡先生,具体地说,胡若望先生,此时双脚站在接待厅门道内,伸长着脖子把头探进室内,两眼转个不停,向里张望了一阵。室内,几十个穿着教士长袍的神职人员占满了所有的长椅。室外,给胡若望套上外衣并将他从牢房押送到此的管理人员紧紧地夹住他的两侧,以防他因受到刺激而做出某种意外的激烈举动。胡若望本人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押到这里来,因为不但没人告诉他,而且也没人能有办法告诉他。胡若望不懂法语,根本不可能开口用法语询问任何问题,而将也押到此的人对中文也一窍不通。
这是《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的开篇,这段文字就好像是一个精彩的特写镜头,用倒叙的方式,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悬念。看了这一段之后,你就会迫不及待地想把这本书看完,看看这位来自中国的胡若望先生究竟在法国经历了什么,以及于落到那步田地。这就是让读者欲罢不能的技巧。本来历史是已经尘埃落定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作品中设置悬念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史景迁却成功地做到了。

然而最当得上“神来之笔”的,还数《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的结尾。史景迁运用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文学意象,为将死的王氏编织了一个瑰丽而又魔幻的梦境。那种时而飞翔时而坠落,前一秒是明丽后一秒是龌蹉的画面,正是那个时代妇女心中的憧憬、忧伤与恐惧。作者将现实与浪漫穿插使用,让人刻骨地感受到郯城那个小地方的小人物的挣扎、麻木、愚昧和死一样的沉寂。

当然,不是的有的学术写作都可以写成扣人心弦的故事。但是打磨文字,尽量使之精炼、优雅;站在读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好奇心和对个体经验的敏感,却是每个历史写作者都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希望我们所写的这些东西为别人所阅读和理解,所以讲好一个故事就显得特别特别重要,这一点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向非虚构写作学习。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