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丈夫去世1年,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我,在努力消解丧亲之痛
原创 小蒋 偶尔治愈

清明节,一个慎终追远的日子。
一年前,北方姑娘小蒋的丈夫意外去世。巨大的哀伤如同疾风厉雨,顷刻来袭,让她经历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度过「无法相信」的阶段后,小蒋开始散步、读书、游泳,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家人陪伴之下,她试着进行心理复原。
这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对抗、消解丧亲之痛,并试着与之共处的故事。以下是小蒋的讲述:
混乱
3 月 21 日下午,东方航空一架搭载 132 人的客机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毁。看到消息,我一阵揪心,一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也意外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这一天晚上,我彻夜难眠。
一年前的春天,一个阳光明媚到有些刺眼的早晨。我刚到单位不久,就接到丈夫同事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得很含糊:「肖某某受伤了,我们这会儿在某某医院。」
挂了电话,我便往医院赶。路上,我并没有不详的预感,以为丈夫是磕磕碰碰,受了点皮外伤。或是伤口深一些,缝几针就好,再严重点也许是骨折。
我到医院的时候,丈夫已经在急诊抢救。他的父母也赶来了,但是家属不让进,只能在外面等。我看到外面有很多人,他的亲戚、同事,以及关系要好的同学。
我问给我打电话的人,「伤到哪儿了」。他指了一下后背的位置。肖是在工作中受伤的,伤及动脉,出了很多血。
大家安慰我,说不会有什么大碍。但是我坐立不安,不时起身去抢救室门口张望,却什么也看不到。
传出来的消息是人昏迷了,但有生命体征,已经输上血。由于缺乏医学常识,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感觉整个人十分混乱。
上午 11 点,医生从抢救室里出来,喊「肖某某家属」。我和他的父母围上前去。医生说:「我跟你们讲啊,人不行了。」
冷冰冰的一句话,让我猝不及防,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形容自己的感受。
我双腿发软,几乎跪倒在地,记得是周围几个人把我架着,扶到了座位上。
「不可能,不可能。」我嘴里喃喃道。
我们央求医生再抢救一会,用上最好的药。当抢救室的门再次打开时,我冲了进去。十几张病床上,躺着各种各样的病人,我的丈夫躺在最里面那张病床上,毫无血色。护士在给他做电除颤,另一边还在输血。
我拉着他的手,想让他感受到我的温度,大声叫他的名字,不停和他说话。我轻吻他的手背,希望能有「医学奇迹」。
可是,一切终究是徒劳。
再后来的事,我只能记起两个片段——一旁坐着的病人家属冲我轻声说了句:「想哭就哭出来吧。」肖的母亲坐在我左手边,说了声,「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
离开医院的那一刻,我仰天长啸。那是一声哀嚎,仿佛悲鸣。
梦境
丈夫去世的那个晚上,我不敢闭眼睡觉。外面春雷滚滚,像是上天也在为他哀鸣。
最开始,我无法相信他已经离去。
他三十岁出头,一米八几的大高个,身材魁梧,爱打篮球,爱玩游戏,平日总是活力满满。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阳光、乐观、正直」。

小蒋保存的丈夫生前照片。
图源:受访者供图
丈夫是个朴素节俭的人。意外发生之前一周,他刚给自己配了一个眼镜,这还是因为之前的眼镜镜片磨损严重,否则,他都舍不得换。
由于工作性质,他经常往户外跑。去的地方常常是荒郊野岭或者大山,每次回家,鞋子、裤子上都沾满了泥巴。也因此,他的身体一向健朗,平时连医院都很少去。
我无法相信,这样鲜活的一个人已经离开我了。总觉得这是新闻、小说、电影,又或者是一个噩梦。
一旦有「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冒出来,我就会崩溃到大哭,使劲摇头,甚至用力拍打自己的脑袋。
那段时间,我很惧怕黑暗,睡觉都要开着台灯。直到现在,我的睡眠仍无法回到事发前的状态,有时难以入睡,有时半夜醒来,后面几个小时都睡不着。
我开始不分时间地点流泪,随时随地都能泪崩。眼泪在脸上干了一遍又一遍,留下一道道泪痕。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竟然会流那么多眼泪,止都止不住。
每天醒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世界不一样了,和他经历的一切皆成幻影。窗外阳光灿烂,可是想到爱人已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我就麻木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记得刚在一起时,有一回他掐着自己说:「这是真的吗?跟做梦似的。」到头来,他也用梦一样的方式走出我的生命,让这场梦短暂、甜蜜且哀伤。
「五七」那天凌晨,我又一次梦见他了。
梦里,我们分坐在家中两个沙发,他坐着,我躺着。我一直哭,他就坐到我这边,一把拉起我,抱着我。
梦里他穿了一件蓝色T恤,上面有个闪电图案。我也紧紧抱着他,哭着埋怨他不能开这种玩笑,说:「你知道吗?这一个月我做梦,梦见你不在了。」
这是他去世之后,我第一次清晰梦见他——俊朗的五官,坚实的臂膀,宽阔的胸膛。梦境清晰得如同真实发生。醒来之后我想,这也许是他来和我道别吧。
他去世的那家医院和他的单位,都在城市的西边。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城西。
睹物
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到父母家和他们同住,直到一个月后才回到我和丈夫的家。
家里还是出事前的那番布置。他的电脑和耳机还亮着灯,一闪一闪。洗漱台上,有被他束之高阁的眼霜和男士面膜,那是婚礼前他人来疯似买的,说要保养自己。
床头柜里,有一张七夕他送我花时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给最爱的 XX(我的小名), you are my lobster.」

小蒋丈夫生前送给她的花。
图源:受访者供图
斗柜上,有我和他的水杯,旁边还有半块不规则的铝箔纸。那阵子我每天早起空腹吃药,他都帮我倒好水。药吃了一半时,我将空了的一半铝箔纸剪掉,他看到了,把它剪成弧形,说「要不然太尖锐了,容易划着手」。
以前,我们坐在客厅看电视,他偶尔会用手指在我的胳膊或者手背上,写下 I 和 YOU,并画上心形图案。
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我趴在他常睡的那边床,抱着他的枕头哭了很久,努力寻找着他的味道。
每天,我都会给他发微信,想到什么都跟他说,一直发了三四个月。可是微信弹出的消息,再也不会是他发的,他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当一个朝夕相伴的人从日常生活消失时,当代科技、通讯有多发达,也就有多残忍。
我们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也留下我俩的很多回忆。睹物思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一个初冬夜晚。他在我家楼下等我,上车后,问我想吃什么。那两天我口腔溃疡,说别吃太辣的,于是他带我去了一家淮扬菜馆。吃饭的时候他问我有啥爱好,我说摄影。送我回家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地邀我第二天去拍银杏。
记得为了纪念相识六周年,我们又去过一次那家餐厅,那时它还在营业。可是他去世后,我有一次路过那家餐厅,发现它已经暂停营业了。
我俩也始终没有去拍过银杏。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总以为来日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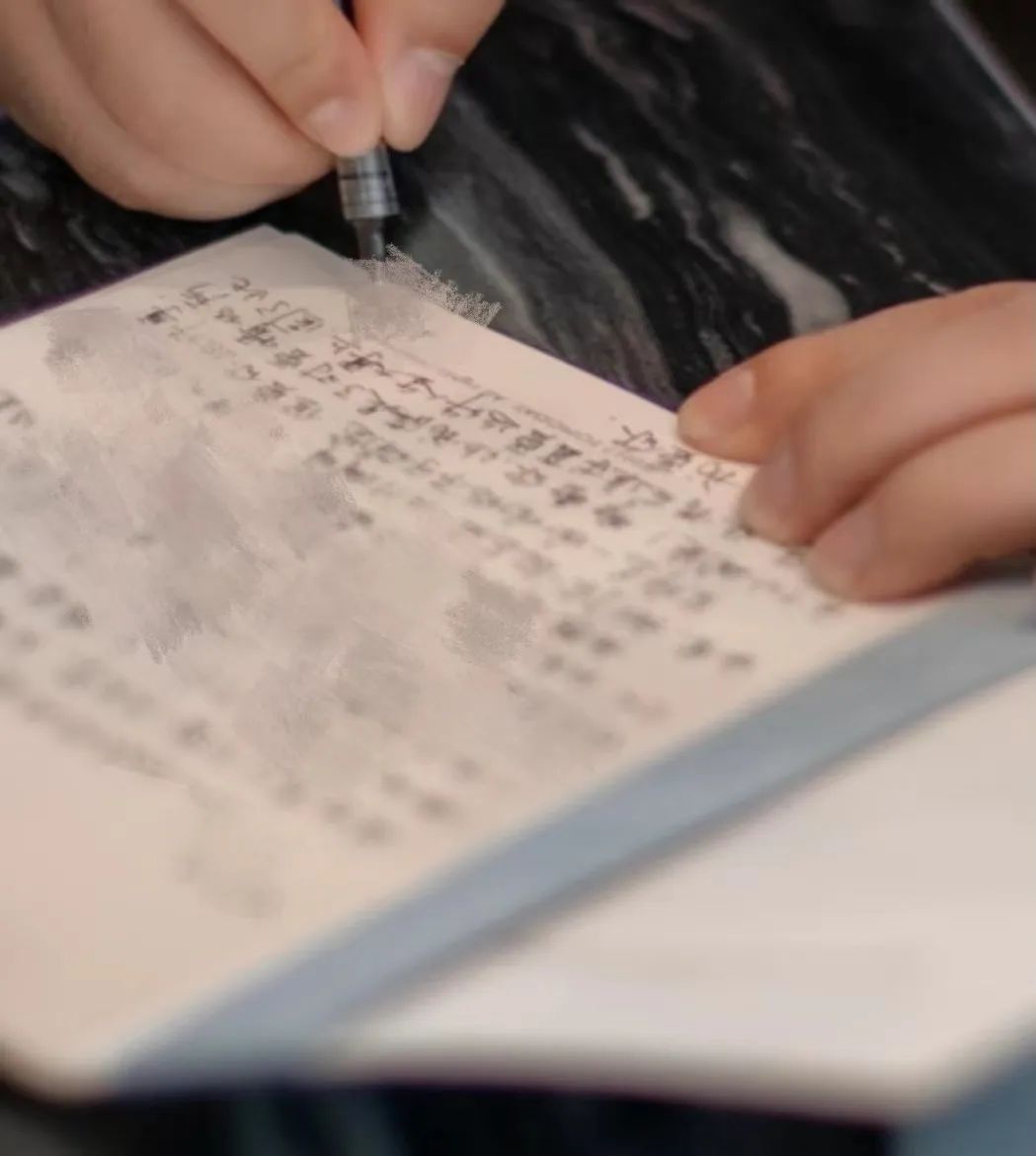
小蒋丈夫婚礼前写的誓言卡。
图源:受访者供图
事实
我的姥姥快 90 岁了,眼花了,听力也差,事发后好久我第一次回姥姥家,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他怎么没一起回来」。幸亏她眼睛不好,没看见我早已泪流满面。
后来每次回去,姥姥问起他,我都用「加班」「出差」等理由搪塞过去。有一回她过寿,全家人一起吃饭,我举杯祝她长命百岁,她却拉着我的手说:「你要保重。」我想,她也许早已知道发生了什么。
日常点滴最是伤人。在家休息了没多久,我就正常上班了。
上班前我心理压力很大,害怕出门,怕见人,怕去单位,怕坐在办公桌前。我变得愈发胆小,觉得外面的世界令人恐惧不安。因为上一次出现在这里时,一切完好,我还可以和别人谈笑风生,现在已是另一番光景。
丈夫去世的前三四个月,我每天都会哭一场。上班时,我经常坐在工位上哭。我们的办公条件很差,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没有格挡,我只能默默流泪。
有大半年的时间,我的眼睛一直肿着,没有了神采。我不再照相,两鬓也增添了白发。
旁人稀松平常的生活细节,都会让我羡慕。因为我觉得,自己平淡生活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
原先我最喜欢周五下午。在以前,我和他总在周五下班后去吃好吃的,有时甚至故意跑远一点,美其名曰更有过周末的感觉。但我知道,这一切不会再重现。

图源:站酷海洛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开始强迫自己阅读。
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探讨生死的书籍,每读一本都有强烈的融入感。我也读其他书,让自己完全沉浸于书中的情节,不去想自己的事。什么类型的书我都看,唯独不看情感类的书籍。
记得在看一本关于冰岛的书时,我想到疫情爆发前,我俩计划的蜜月旅行地之一就是冰岛,还做了很多攻略,看了很多照片。所以读到书里描述的冰岛种种,我突然之间就哭了。
为了化解悲伤,我喜欢上了游泳和走路。
游泳的时候,每一次将头埋进水里,我都尽量延长在水下的时间,让整个人被泳池里的水包裹住,好像这样,就能产生一种与「与世隔绝」之感。我喜欢一个人出门散步,仿佛走着走着,就能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再后来,他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即使照片和视频就在手机里,想起来却像是上辈子的人。就连意外发生之前的自己,我也有些陌生。
终于,我接受了他已经离开人世这个事实,不再幻想他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阴阳两隔就是这样?感觉很遥远,远到不论做什么,都倍感无力,连想念都使不上劲。
半年后,听闻他姥爷不在了,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平行时空的那一边,多了一个可以陪他的亲人。他不会那么孤单了。
恢复
春天如约而至。树叶在阳光下摇曳,可我就算晒着太阳,看到百花怒放,也愉悦不起来。
尽管已经接受了丈夫离开的事实,但伤痛依然尖锐,折磨着我。
我的脑海,时常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医院里的场景。看电视一看到流血,就极为痛苦。
我的记性也大不如前了,经常丢三落四,坐车回家竟然提早一站下了车。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觉得一切没有意义,好像连笑都不会了。人始终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不能放松下来。
我还变得暴躁易怒。听见跟他有关的、能联想起来的话题和词汇,就会紧张,甚至喘不上气,想立马逃离那个环境。
在这种状况下,我切断和他有关的一切联系,与我原来的朋友圈也断开了。尤其是关系要好的共同朋友,更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我是后来才知道我病了。而这些症状难以描述,也无法量化。于是,在挣扎了八个月之后,我鼓起勇气寻求医生的帮助。2021 年国庆节假期前夕,我来到北京,在一家心理救援机构接受医生的治疗。
这是我第一次做心理咨询,内心有些忐忑。医生是国内知名的心理救援、危机干预专家,坐在他面前,我发现他态度很和蔼。他很耐心地和我聊天,问我问题,详细记录我的情况。最终,他给出诊断,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但是医生说,因为我此前的生活经历和原生家庭都很健康,没有掺杂其他更复杂的内容,这就有益于后期的治疗和恢复。
也是通过这次机会,我发现,心理咨询并不完全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问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问清我的成长经历和原生家庭状况。
一个小时的咨询很快结束。最后,医生还给了我两点建议,「走路和写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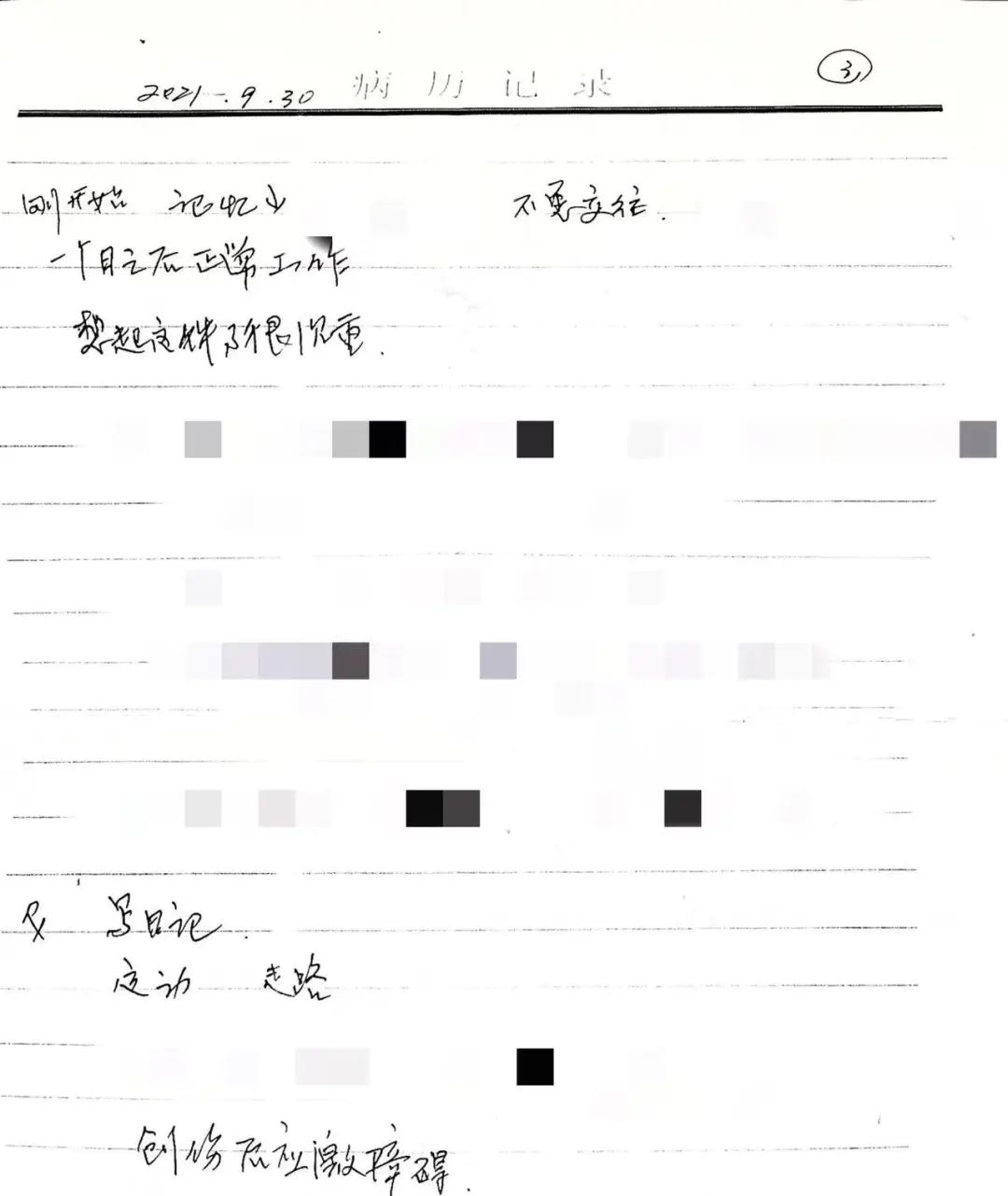
小蒋的病历本。
图源:受访者供图
除了医生,我的家人们也在帮助我。
我的父母年岁渐长,本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因我的遭遇,让他们一起承受了痛苦。这一年母亲因为担心我,生出了好多白发。
我记得去年国庆节前夕,在去北京的路上,高铁疾驰而过,窗外景物依然,我却高兴不起来。晚高峰,北京西站格外拥堵,在北京生活的表妹却坚持到车站接我。整个国庆假期,舅舅也处处考虑我,问我「想吃什么,想去哪里玩」。
我知道对我而言,失去丈夫的哀伤只能独自咀嚼消化,旁人能给的建议十分有限。更多时候,家人们是在陪伴、倾听,但这也是一种帮助,并且弥足珍贵。
我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我不知道。未来,我还需要数次的心理干预治疗。
回顾这段日子,我觉得至亲意外离世,心理干预必须越早越好。尽管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反应会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感到悲伤。如果刻意压抑悲伤,装作若无其事,反而容易酿就更大的问题。
我知道未来一段时间,我还会痛苦、低落,但我尝试把这件事看作人生的一个低谷。尽管若干年后,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也一定会是一道抹不掉的伤疤。
但我知道我能恢复过来。会有那么一天。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小蒋为化名。)
撰文:小蒋
监制:潘闻博
首图来源:站酷海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