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达伯霍瓦拉评《低级趣味》︱经受嘲笑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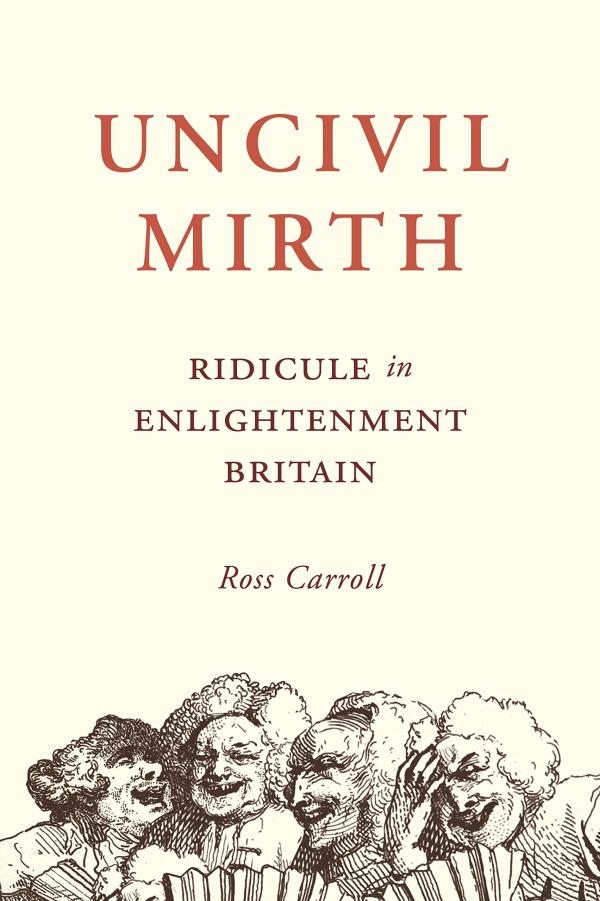
Uncivil Mirth: Ridicule in Enlightenment Britain, by Ross Carroll, Princeton, April 2021, 255pp
在一个基本上人人目不识丁的世界里,笑是一种与他人一起做的事情。幽默领域的早期理论家认为,幽默是言论而非写作的一种形式。而言论可以是高度危险的,就像《圣经》所警告的那样:“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箴言);“舌头是火,……是个不公义的世界”(雅各书)。在经文的其他地方,舌头还被比作利刃、剑、弓、箭——话语是致命的武器。《圣经》未曾为欢笑正名。例如,使徒保罗提醒以弗所人不要沉迷于“愚蠢的谈话或玩笑”。只有以利亚嘲弄那些代言巴力神的假先知的例子似乎表明,“滑稽的机智”有时是对“卑鄙的”事情的最好回应,正如十七世纪的神学家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所写的那样,“当直白的声明不能启迪人们……直率的论证无力穿透时,理性就会把它的地位放手让给机智,让其来承担指正和责难的工作”。
但是,如何在不冒犯他人的情况下进行娱乐?佛罗伦萨的礼仪权威乔万尼·德拉·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曾经在1558年如此解释:“有两种玩笑”,“一种是锐利而严苛的;另一种是无害而纯真的”。玩笑应该“像羔羊那样轻咬,而不是像狗一样啃噬”,否则就会成为“某种冒犯”。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德拉·卡萨认为笑声主要是蔑视的一种表达——“与对某人造成任何真正的伤害相比,对他施以嘲笑是一种更大的蔑视”。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笔下那样,“那些能让人欢笑的场景和让我们快乐的方法——是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滑稽、肮脏、畸形以及所有那些邪恶的行为”。在《忧郁的解剖》(1621年)中,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从受害者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一个苦涩的玩笑、一次诋毁、一句诽谤,能够比任何财物损失、危险经历、或者身体上的痛苦与伤害都更加深刻地刺痛一个人。”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为保全自己的名誉而反对这种口头上的轻薄。嘲讽引发了频繁的暴力争斗和无休止的诽谤诉讼。1638年,托马斯·霍布斯建议他的贵族门生查尔斯·卡文迪什:“避免一切攻击性的言论,不仅是公开的谩骂,也包括那种讽刺性的闲言碎语。”贵族年轻人常常将这类言语挂在嘴边,而这将为“许多两败俱伤的决斗”创造诱因。他警告说,嘲笑别人是傲气十足的自恋的表现。但作为一位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将社会生活视为某种竞争,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重视笑声:它是一种可怕的蔑视指数。他在《论公民》(1642年)中写道,所有“心灵的愉悦和欢乐”都包含在对他人的优越感中,所以“人们别无他法,必须通过笑声、语言或手势来表达相互之间的某些鄙薄和轻视”。
几十年后,约翰·洛克也“明言反对说笑”。“未经妥善管理的话”会造成“危险的后果”,他还敦促年轻人戒除说笑。他模仿别人颇有名气,也为自己的机智风趣感到自豪,但他认为笑话是有风险的,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冒犯:“面对着一个微小失误就可能破坏一切的情况,恰当管理如此美好而棘手的事务,并不是每个人的天赋。”与其同样恶劣的是在宗教问题上的“轻浮的论述”和“不合适的噱头”。在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洛克督导了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教育,此人后来成为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观念似乎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沙夫茨伯里于1698年在荷兰自我放逐期间,研究了斯多葛学派,并试图抑制自己谈笑风生的欲望。他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安全,也更难管理的了”;相反,人们在笑的时候应该“独自一人”,而且只在“严肃的时候”发笑。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他认为说笑是一种危险的反社会力量,并谴责“在宗教问题上说三道四”以及嘲讽虔诚的行为。
然而,不到十年后,沙夫茨伯里自己就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嘲讽的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为它赋予了一种更受认可的地位。他认为,宗教狂热主义是危险的,但与对其进行迫害相比,嘲讽是更好的回应。重要的是要宽容,至少对新教徒同伴要宽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尊重疯狂的想法,或让它们不受质疑地发展;相反,应该对它们进行攻击。这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证,也可以通过嘲讽——而这是吸引广大听众的最佳方式。能否经受“嘲讽的考验”将决定一种理论是否值得尊重:因为人们对真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真知灼见不会被嘲弄玷污。他在1709年的《常识:一篇关于机智与幽默之自由的论文》中写道,“只有扭曲才可笑”。
沙夫茨伯里对嘲讽的看法还有在其他方面的新颖之处。他认为,笑声主要来自对失调事物的共同欣赏,或对邪恶以及非自然事物的共同蔑视,而不是来自个人的不屑情绪。这并非是一种反社会的做法,而是一种鼓励讨论,并使人们感到“能够相互认同”的实践。他认为,学会相互嘲笑和被嘲笑是集体理性和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与启蒙运动时期后来许多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类自然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私的;文明的进步是通过集体礼节的完善来实现的;而教导人们如何礼貌交谈,对社会在道德上的进步至关重要。
在十八世纪初,公共论辩的状况是一个被特别关注的问题。1689年树立的对新教异见者的宗教宽容制度助长了宗教领域的攻讦,而英国实行的出版前审查制度在六年后的崩溃与印刷业管制的放松,导致了讽刺性写作和政治攻讦的繁荣。政党政治的出现,1694年引入的三年一度的选举制,以及1688年后主权在民理论的日益增长的吸引力,都使公众舆论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但同时也使人们对公众的易变性和善变性的担忧更加尖锐。在笛福、曼利、斯威夫特和蒲柏的时代,嘲讽的大潮是否应被视为未经审查的媒体所导致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个问题,沙夫茨伯里是最早一批对其进行思考的作家。
在这个问题上,沙夫茨伯里有不少追随者。弗朗西斯·赫奇逊(Francis Hutcheson)采纳了他关于文明礼仪和公共言论的论述,以及他关于嘲笑有助于社交的观点;赫奇逊的学生亚当·斯密也是如此。大卫·休谟尽管怀疑以嘲笑来解决有争议问题的成效,但还是经常以嘲笑来破坏虚伪或迷信,认为嘲笑可能揭示真相,但在同样程度上也可能歪曲事实。休谟在哲学上的一些对手如托马斯·里德和詹姆斯·比蒂认为嘲笑是对任何冒犯“常识”的自然反应——比如休谟自己的荒谬学说。来自爱丁堡的博学的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持不同观点:他在1762年写道,“对那些光鲜有礼的人来说”,嘲笑是一种“过于粗糙的娱乐”,并预测它将在恪守礼节的商业社会中逐渐消亡。它“在英国每天都在萎缩”,在法国已经被“逐出门外”。
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孟德斯鸠在当时刚刚运用讽刺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效果。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他嘲笑了那些通常用来为新世界的奴隶制辩护的论点:“欧洲人在灭绝了美洲(原住)人民之后,别无选择,只能让非洲人成为奴隶。”此外,如果没有奴隶劳工,“糖就太贵了”——而且“黑人”有“那么大的鼻子,所以他们几乎不值得同情”。在孟德斯鸠的启发下,苏格兰的废奴主义者们也创作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戏讽文字,以至于激进的天主教讽刺作家亚历山大·格迪斯(Alexander Geddes)的《为奴隶制辩护;或反对立即废除奴隶贸易的六个有力论据》于1792年出版时,颇有一些读者认为它是一份真诚的辩护。在随后的版本中,“讽刺”的字样被加入了书名中。
正如《低级趣味》(Uncivil Mirth)的作者罗斯·卡罗尔(Ross Carroll)所指出的,即使是那些与沙夫茨伯里同样认可嘲讽价值的写作者,也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问题。讽刺可以给人以启迪,但它同样可以迅速地使公共言论变得粗俗,尤其是当它未能落地的时候。随之而生的是一种尴尬的平衡。例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谴责她的对手的言论与文字包含轻蔑的同时,她自己也在嘲笑他们。她在《为人类权利辩护》(1790年)中抨击了埃德蒙·伯克的刻薄,同时也取笑他“幼稚的敏感”和脆弱的“神经系统”。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鄙视比自己低下的人是不对的,但“有尊严的”嘲弄可以揭开上层阶级的伪装。
1713年沙夫茨伯里去世后的几年内,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认为“嘲笑的适当对象”并非恶行本身,而是关于恶行的道德主张,他攻击沙夫茨伯里是个伪善者,认为沙夫茨伯里对自然社会性的幻想“只会滋生寄生虫”,“使一个人蠢到觉得僧侣生活也是享受”。亚当·斯密断言,在《常识》一书中,“没有哪一段话能让我们发笑”。沃斯通克拉夫特钦佩沙夫茨伯里的思想,但无法忍受“他做作的膨胀期”和“炫耀文字”。她怀疑沙夫茨伯里“在头脑里编织着那些狂想曲时,其实内心毫无波澜”。到了1800年,沙夫茨伯里关于嘲笑的理论已经无人提起。
《低级趣味》包含了很多有趣的观察和深思熟虑的阐释,但并无半分玩笑。对于将十八世纪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卡罗尔持谨慎态度,但沙夫茨伯里、休谟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面临的困境与我们这个属于新媒体、言论攻讦、以及成为商业化娱乐的政治的时代有明显相似之处。大多数十九世纪的观察家认为,民主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缺乏乐趣。托克维尔写道,在贵族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让自己在喧嚣的欢愉中爆发出来”。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偶尔会出现“疯狂的笑声”。但民主国家的公民总是很严肃,因为他们掌有权力。关于清醒的政治的优越之处,他可能是正确的。正如卡罗尔所指出,“小丑们开始爬上权力的阶梯”,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本文英文原文刊于2021年12月16日《伦敦书评》,获作者授权翻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