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北川到芦山:小事记
“5·12汶川地震,我跟着他去家访。他立马跪在失屋的两个老人面前。老人的子女和孙辈全部遇难。他抱着两个老人,听他们心里哀伤的事情。那个时候,给到人们的那种温暖,是无可比拟的。亲人不一定能给你那种感觉。”——文太科/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血意味着从天而降的灾难。人类聚居之处,地动山摇,难免流血流泪。
血也是志愿行为的起点。5·12汶川地震后,各大城市街上的采血车旁边,前来献血的人群排着长队,甚至一度堵塞交通。
那时,有很多人坐不住,前往灾区支援。绵阳人高思发与QQ上的网友们结伴,向北川灾区运送物资,在那儿帮着做点事。这支队伍当时叫做“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他打算暂时放下生意,做两个月志愿者。在任家坪,他给北川的孩子搭建了帐篷学校,免得他们到处跑不安全。
退役军医张小红也以志愿者身份,第一时间从成都进入灾区,进行医疗救助。
虽说,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年被称作“公益元年”,但高思发和张小红等人当时还想不到,自己会与伙伴一起,在公益道路上走到今天。
而绵阳师范学院社工专业大二学生文太科,也在老北川附近的安置点做志愿者。他接触到来自香港的社工,被安慰人的力量深深震撼,真正认同了自己的这个专业。
大灾来临时,血将众人变成亲人。也有社会组织因血而生,希望延续这种人与人的连接。
成都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刘飞,组织了公益剧社“爱有戏”,招募志愿者,用戏剧等方式讲述血与献血的故事。过了几年,爱有戏成为一家5A级社会组织,从事社区文化与社区互助的社会服务工作。比如开展让街坊讲古的活动,以及社区安全教育。爱有戏还借鉴传承古代“义仓”的内涵,建立现代义仓——社区居民捐物互助,也增强了社区的力量。
如今刘飞的机构有许多工作。她不再像在5·12汶川地震时,只是忙着组织市民献血。
二、巴拿恰
“受5·12直接影响的,已经非常少。虽然有心理的震动,隐藏在生活之中,但也要把标签撕掉。人会长大,会回归自己的生活。”——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领队、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巴拿恰是羌语中的“集市”。北川新县城的步行商业街以此命名,这里也是四川最大特色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仿古建筑颇为精美。到了周末,去巴拿恰逛逛街,也是一家人很不错的消遣。在异地重建的成果之上,老北川人的生活得以重新开始。
巴拿恰商业街还是一种分界。从老北川搬来的人,住在巴拿恰北边的安置社区;而本地农民的社区在巴拿恰南边。北边的生活气息相对浓一些。本地上楼的农民大多得了三四套房。有人出外打工,也有人忽然无事可做,难免不适应,甚至空虚无聊。
巴拿恰是北川新县城的标志物,可以代表这里完善的硬件和美丽的景观。援建的效率非常之高。但相比几年后的雅安灾后重建,在北川灾后重建时,很多人还没意识到,需要支持更多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
在2009年底,“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队长高思发,注册了北川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即如今的“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而2011年底,他们在这里第一次拿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针对北川新县城的安置社区,做社区的文化服务和综合发展。大概可以这样说,就是让这里的人对社区认同高一些,生活丰富一些。
陪伴北川九年的高思发早已不再做商业。在北川的帐篷学校,他认识了那些来到帐篷玩耍的孩子和他们受灾的家庭,还有那些帮忙照料孩子并乐意伸出援手的志愿者——从此,志愿者成为资助人,而孩子成为受助对象,高思发则走上助学之路。
如今,他所发起的大鱼公益,在接受更多资助人的捐赠,其助学对象也扩展到家庭贫困的孩子,而不再是受到地震伤害的孩子。作为专业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高思发要为资助人把钱用好。这是最常态化的公益,也是应对下一次灾难的准备。
虽然从志愿者转变为专业公益人,但他仍然被称作“高队”,这或许是某种不忘初心的意思。
三、成都4·20联合救援行动
“路上半夜两三点,讨论每个人的分工、每个机构的分工,谁负责交通运输,谁负责物资筹集,海哥负责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发布出来。南都基金会开始资助了两万元钱,第二天看到我们有序救灾,便紧急开会,专门针对我们的救援行动,资助提升到20万。”——张小红/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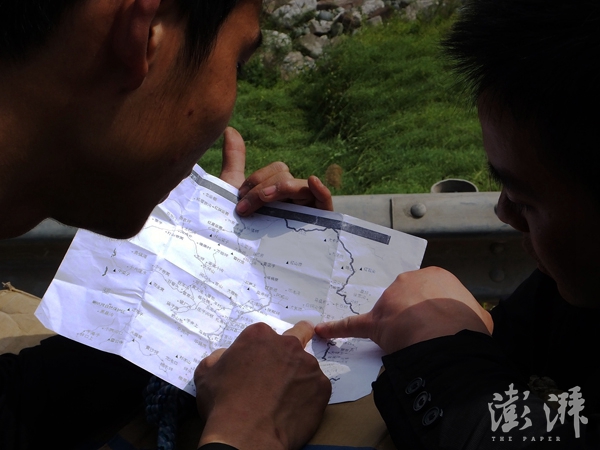
2013年4月20日早上,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的消息传来。当天下午,成都爱有戏原定在成都肖家河办义集,临时把主题改成“我们和雅安人民在一起”,接着开始募集物资。肖家河成为这场联合救援行动的大本营。
联合是有序的。大量救援物资涌向肖家河,共有八家社会组织参与。刘飞和丈夫杨海平开始担当协调工作。那些年,人们更加相信民间机构。爱有戏要根据前线信息反馈,及时精准定点派发物资。
4月21日凌晨,张小红、杨海平、高思发等六人押运物资,赶赴芦山。路上遇到封路,因为需保证救援车辆通行。张小红与另一位公益人,租了老百姓的摩托车,带了一些物资向前走,并及时发回需求信息。其他人分头去了其他受灾地点。
大家要在现场收集受灾信息,及时反馈情况,并安抚村民情绪。有受灾村民在路边帐篷里,眼看一车车物资从眼前经过,情绪激动。张小红便赶快向后方反馈,用摩托车先送一点物资上来,平复灾民心情。而物资也不能乱发,必须统计人数和需要。张小红发现,现场的米和油不够,就统计前面一个组的老人,尽量把他们先照顾到。
另外,社会组织发放物资,好处还在于,因为是第三方献的爱心,灾民不会挑三拣四,不会埋怨政府照顾不周。
在这场救灾行动中,社会组织各自努力,又相互协作。虽然起初出现问题——大本营的人员,押送物资到现场,又因灾区忙碌而无法返回,使得中心缺乏调度,但相关权责第二天就被明确下来。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组织也有了抱团发展的意识。
之所以能做到有序,不仅是参与者这些年间在各种行动中增长了经验——比如,张小红参与过玉树地震救援,还因身份已然不同。这些在2008年凭热情前往灾区的志愿者,此时已注册了社会组织。这个身份对应的是明确的责任和义务。
行动也成为一些社工扎根雅安的起点。因透明高效,行动得到了诸多基金会支持。比如,腾讯委托联合救援行动驻点,在村里建八个社工站。
实际上,安置工作对应的就是社区服务。比如帐篷里没有电,就要在安置点放电影;小孩没人管,就要有人手帮忙。救灾时,村民都是志愿者。因为这样的群众基础,自然而然地,各个机构分别选择在自己救灾的地方来建社工站——心家园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而爱有戏在飞仙村。这两个社会组织的社工,至今仍以不同方式,陪伴着当地的村民。
四、雅安群团中心
“雅安的本土社会组织是因4·20地震而产生。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中心跟你们都是同时出生的,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刘雪松/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

雅安群团中心,是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简称。早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一周,其前身“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就已在灾区运转工作,协调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的力量。
此事是官民良性互动的绝好范例。当时,雅安灾区还有大量外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缺乏信息沟通,也一度产生混乱。有学者看到“成都4·20救援行动”的有序,结合当时情况,撰写了报告。而报告得到正在灾区视察的副总理汪洋的批示。4月25日,四川省委救灾指挥部成立了社会管理组。4月28日,由团省委牵头,芦山成立了首个“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5月12日,省市共建的“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成立。对政府的救灾服务,与社会参与救援者的救灾行动,进行同步调控安排。2014年3月,随着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成立,其更名为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大家看到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在雅安的灾后重建规划中,社会管理服务成为一个专门的部分。而雅安群团中心的任务是,继续协调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让政府的相关规划与社会组织的项目能够对接。
实际上,在接纳外来社会组织的同时,人们也希望雅安本地能有自我服务的能力。孵化和培育本地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恢复重建,以及更长远的社会治理工作,成为雅安群团中心的重要使命。
从2015年开始、为期三年的灾后重建规划中,雅安群团中心共有9042万资金可用。这笔钱除了用于市县乡各级群团中心的体系建设,以及较为常规的关爱项目,就是进行本土社会组织的培育。
第一年,雅安群团中心已完成培养一百家社会组织和一千名社工人才的任务,但其成长发育还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得让本土的社会组织有项目做,能够真正按照公益的方式去实践。这两年,雅安群团中心设计了“我爱我家”项目——工作人员在全市找到100个项目,由49家本土社会组织承接。还引入南都基金会和壹基金的资金支持。而成都的爱有戏全程担当培训和项目督导的工作。
这只是雅安群团中心诸多具体工作之一。
雅安孵化本土组织着实不易。本土组织对撰写标书等程序大多陌生,财务方面也不够细致,就连申请项目的过程也是锻炼。因此,需要不断面对面地教。其中还得去粗取精,今年要选择扎根社区的十余家社会组织,进行重点培育。
雅安群团中心的创新意味是明确的。2016年7月,雅安市委市政府对灾后重建工作中有功单位和人员记功,雅安群团中心得到了二等功嘉奖。这无疑也是对灾后重建中社会组织工作的认可。
群团中心搭建平台,让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并孵化本地社会组织。“雅安模式”大概可以这样概括。但雅安群团中心的身份,终究有些尴尬。它是不登记的群团组织,而不是一个法人单位。另外,灾后重建规划是三年,三年后该怎么办,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胡焕庸线上的机制创新,又与民间社会的发育紧密相连。
五、上课
“2011年,我们第一次拿到基金会的项目。我折腾了三个月,才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那套项目财务体系搞清楚。现在我用那套东西,加一些小小的改良,已经给上百家的公益组织做过培训了。”——刘剑峰/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副领队、原点公益慈善中心主任

上课首先可以视为公益的入口。5·12地震救灾时,刘剑峰起初是以志愿者身份前去帐篷学校帮忙。而这一帮就是九年,并与高思发成了搭档。
高思发还把当年的帐篷学校,延伸为每个暑假的营会。每年有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来到北川,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学习与同龄人相处,过集体生活。这是心灵助学的一部分,高思发觉得,物质上的关心还不够。
上课也是社会组织交流和连接的重要契机。心家园的社工吕小英,自雅安地震之后,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驻点工作。他通过一次培训,结识了高思发。后来,吕小英学习了高思发的营会组织经验,也在雅安组织了一次中学生夏令营。
给村民上课,也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吕小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所做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本土人才培育项目,即培育本地村民成为社会工作者。也就是说,把方法教给村民,让村民自己来给自己做服务,最终发生改变。这些村民区别于专业社工,故称之为乡工。
上课也是“零八帮”发展壮大的证明。财务管理问题最让一般的公益组织头疼。刘剑峰自己是财务出身,也是研究许久才弄清楚。针对基金会的财务体系,他已经培训了上百家公益组织。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公益人,都在传递各自的经验。
上课最终关乎个人成长。史加利曾跟着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师,在雅安进行灾后重建的心理援助,如今也转为常态化的社区工作。作为雅安本地社工,这个生于1994年的姑娘,去过鲁甸支援,也去过缅甸的受灾地给当地教师做培训。她发现,这些受灾的地方真的需要专业心理手法,自己原来一直在成长。
六、扎根
“我们就想尽量把它落在实处。能有尽量多的人留在这个社区里面,从事社区服务,建设自己的社区。而不是拿到项目,就机械地按照项目来做。”——吕小英/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扎根就是与当地紧密连接。吕小英三年来很少离开大同村和仁加村,顶多去芦山县城办事。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项目点。那儿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家,空气里混合着孩子的尿味与饭菜的味道,噼噼啪啪的键盘声与来访乡工的谈笑声。
墙上贴着感谢信和锦旗,是心家园“4·20”在这里救灾的证明。张小红当时来的就是这个地方。
救灾是社会组织与村子的连结契机,但这也形成了认知惯性。村民对物资发放印象深刻,把社会组织当作“发东西的”。假若不发东西,村民就不来参加活动。于是,吕小英便设计出一些规则,通过发礼品来增加村民之间的互动——总比去其他地方听讲被骗钱好。
扎根意味着因地制宜。原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针对的是返乡青年和妇女,希望当地有人带动整个村子。但在仁加村和大同村,正值灾后重建,青壮劳力都在修自家房子或维持生计,余事无暇顾及。于是,吕小英与扶贫基金会沟通,重新定位了项目,以老人为主,来培育本土社工人才,即乡工。
乡工中也有两位年轻妇女。如今,她们已在各自村里成立了机构,自己成了法人。李传俊在仁加村主要做生计项目。罗静在大同村主要做社区服务。吕小英手把手地教她们写报告,申请项目,组织活动,为村民服务。
扎根是希望能够传递影响。要让本地人为自己服务,本地人受益以后,哪怕社会组织走了,精神还在。而心家园的这个项目明年就结束了。可能要在更远的未来,才能看出这个项目到底给这里带来了什么。
文太科也喜欢呆在山上的项目点,虽然他在新北川县城买了新房,并把松潘的家人接来,却并不时常回去。他更喜欢在山里接触土地,在村里接触牲口,在办公室坐久了,感觉全身都不好。
文太科认为,要注重与政府的关系。他有时发现,站在对方的职务上,去考虑全局,就可以防止自己犯方向性的错误。他随时会与政府部门沟通,说自己需要怎样的协助,以及对方可能需要自己做什么样的工作。
扎根也可理解为长期陪伴。在高思发看来,助学的孩子在长大,在发生变化,而家长和孩子与自己的情感也在产生。高思发发现,家长生命里的事情,可能不讲给亲人听,却讲给自己听。而他的目标是,要和孩子产生关系,培育孩子承担家庭的能力,进而影响社会。他希望,资助的两个孩子,未来有机会进入中国心,成为自己的同事。
高思发正在试点家长义工,希望能把资助人、家长和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进行连接,把助学的大家庭建立起来。
因为陪伴,中国心也有所延伸。最初,是从救灾开始做的助学,但发现,单方面经济资助无法改变现状,就从助学延伸出社区发展。高思发和刘剑峰曾想过,是否要集中一些,但哪一部分都无法割舍。于是,大鱼做助学,羌魂做社区发展,原点做灾害应对。正因逻辑上有需求,大家才做了这些事。
扎根是个主动行为。社工专业科班出身的吕小英,不喜欢那些“有救世主情结”、“讲大话”的社会组织老大,对来自江湖的高思发却是激赏有加。敏感的人总能体会到那种道德绑架与脚踏实地的差别。自我满足与渲染悲情往往意味着,并没有真正地扎根下来。
七、项目
“我老公都支持我的,随时都安慰我:你不要着急,接得到项目就做,尽量去争取,没接到就算了,休息一下,不要灰心。”——廖国香/雅安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村村民、爱有戏之家负责人

“项目”可能是个令公益人士又爱又恨的词。吕小英一家之所以能团聚,是因为2016年这里的某个项目,需要一位有儿童项目经验的社工专业人才,而人员配套经费每月只有1800元。吕小英意识到,这点薪酬难以吸引到合适的人,而妻子刚好符合条件。虽然钱不多,一家三口能在一起也很好。
但做项目时常身不由己。为使本土社工人才成长,吕小英给附近的五个村子,申请到以舞蹈队、民乐团等为载体的妇女互助项目,让村民自己去操办广场舞大赛等。为了跳舞的场地,一些村民还组织起来,休整了坝子;有的村民,趁着练舞休息,一起做饭,其乐融融。项目只有半年。而村民至今对这段快乐时光意犹未尽。
社会组织当然希望有项目做,否则无法生存——虽然管理费通常比较微薄,往往需要联络其他资助。但在高思发看来,项目持续时间更重要。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是要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今天购买服务,明天不买了,社会组织本身就无法对社工负责,不仅没尽到责任,还把社会秩序搞乱了。这也不利于自身机构的人员稳定。因此,时间少于三年的不做。
正在实施中的项目,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持。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中——通常是管理者忽然更迭,政策方向变动,一切得重新开始。另外,政府部门需要考虑更多面上的事,需要让事情看得见,更容易评估。比如,需要频繁举办活动,对应大量人力成本投入;但未必看得见被服务对象的改变。
相对而言,基金会比较倾向于小而美的工作,会与成熟的社会组织结成长期战略伙伴,但其要求也更加精细。初创的小型公益组织——如雅安本土的社会组织,往往达不到要求,申请不到基金会的项目。这样看,雅安群团中心的“我爱我家”项目,更大的意义是提供锻炼机会。
项目是向本地社会组织传导经验的载体,执行项目是成长过程。在雅安,外来的社会组织,多半会把本地的项目——多数是来自群团中心的项目,转包给自己孵化的本土社会组织去做。但后者也面临难以独立申请到项目的问题。
比如,在爱有戏的帮助下,飞仙村的廖国香等人成为社会工作者,成立了“爱有戏之家”,并执行了爱有戏转包的乡村摄影项目。并在村子里开展许多工作,比如上门帮助不便行动的老人,或组织歌舞表演。不过,虽然廖阿姨等人做过几个“我爱我家”的项目,还把机构的管理费——即自己的人力成本,也用在了活动里,相当于不计成本地工作,但她们不擅长写和说,要学习申请项目,与年轻的大学生竞争,并非易事。
即使是返乡的年轻人,学着写申请项目的标书,也不容易。在大同村,罗静开始独立申请公共空间的项目,吕小英在旁边反复指导,一个文档写了好几次。
八、乡工
“七八十岁的老人,儿童时代的玩具弄出来,她老公说她是乖乖,逗得别人看着笑得不行。给她一种平台。大家欢乐自己,是不容易的。”——石传敏/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

乡工的主体是老人。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许多乡工是当地的老年协会成员。
他们平日负责管理村里的活动室。值班有补贴,但更重要的是服务社区,比如陪伴来玩、来借书的留守儿童。
大家在一起众筹了重阳节的大型活动。有人买菜弄饭,有人照顾老人。坐了六百多人,共有八十桌。全村人都参加了这场活动。大家还组织茶会,有人分享受骗的经历,有人唱山歌,说起了夫妻的故事。她感觉,这其中包含着人的改变。要根深蒂固为社区做事,有为社区服务的美好的心。
乡工石传敏提到,谁会发月饼给他们吃?这就是无私地对他们好。她比较乐观,认为心家园把这个地方提升起来,未来也可以放心离开。
乡工年纪比较大,固然是个问题。但吕小英认为,老年乡工在这个地方,即便不做社工,也还是这个地方的人;大学生就不一样,更容易离开,留不下来。
乡工们也得到一些出外访问的机会,这无疑开阔了视野,也增强信心与认同感。
李传俊去过一次深圳慈展会,留下深刻印象。她觉得,的确可以帮助大家变得更好,也想在公益方面发展。
李传俊想到,地震过后,家家户户出去打工,许多老人需要照顾。但家庭中往往是,小孩是宝,老人是草。大家并不重视老人。“想为孤寡空巢老人,要一个长期固定的场地,中午有一顿餐,有一个老人兴趣班,长期感受到温暖。”但她觉得,目前似乎还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与已有项目的方向差别太大。
吕小英强调痕迹管理,需要随时写下来。但李传俊感觉,文字工作太累,时间大部分耗在了写东西上,宁愿多做点事情。毕竟,她当年高中没有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李传俊感觉,做公益好难,与村民相处,虽然有改变,但并不大。
吕小英在村子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他认为,在这儿不一定要追求改变什么,只是做一些事情。因为,社会组织在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过促进或陪伴就可以了,至于能否改变,那是自己的事情。
九、路
“从雅安地震,我就发现一个新的模式。和修房子一样,最基础的那一层永远最重要。先谈基建,我们把老百姓最关心的生活最着急的事情解决掉,然后再跟他们谈文化,大家就相互认识,相互理解。到了一定程度,然后开始谈发展。”——文太科/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路是救援的通路。这里地震泥石流多发,路上常有大块碎石。由于气候与地质条件,村里的路极易被损毁。
但修路也是参与的契机。在雅安地震灾后重建中,文太科做过一个修复村路的项目。针对一条老大难的路,村民反复协商,自己组成管理小组,共同捞石头填路基。虽然花了很长时间,反复做工作,但最终结果是,以最节省的办法,做了最多的事。既解决了实际问题,村民也凝聚为共同体。人的改变就此发生。
文太科感觉,这样的模式,真正切合社工里讲的自愿原则。与路相似的,还有用来办公共活动的房子,以及消防池等减防灾设施。
十、羊
“我申请项目时,有一项是可持续发展的,想等我们这个羊生了小羊,一户带动一户。结果看着去年价格降了,很多老百姓就说不愿意养了,就连把羊送给他们,都不愿意养。”——李传俊/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爱心家园负责人

羊不仅是羌族图腾,还是常见的扶贫生计项目。而在雅安灾后重建的地方,那些还有老房子的人才有条件养羊。并且,养羊的收益还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要看天吃饭。
李传俊申请了扶贫基金会的养羊项目。今年五月就满两年。她一共养了三十只羊,本来希望靠养羊来补贴其他项目的人员经费,但市场行情不好,收益无从指望。
好在,养羊的成本全由扶贫基金会负担,每户三万元。李传俊也没有额外的损失。
而吕小英认为,还是得让申请这类生计项目的人出一些钱,否则很难保证积极性。
鸡也是常见的扶贫生计项目。看似成本低,但也十分麻烦。2011年,文太科曾在映秀的村子做灾后项目,养了两年鸡。他不光募集贫困户,自己也学习养殖技术,还请了专家帮忙。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做饲料,鸡感冒了还要给打针、喂感冒药。还去学了鸡的宰杀和包装。
他总忘不了那个拼命拔毛和满地抓鸡的场面。有一次,文太科接到来自成都的订单,要一千只鸡。包括活的和杀好的。
杀好的要去毛去内脏,包装起来。村民人手不够,文太科带着实习生,一起杀了两天鸡——天气开始热起来,得在下午集中杀,拔毛拔到手软。随后,拔完毛的鸡与活鸡一起,装车运往成都。当时不知活的家禽晚上八点前不能进三环,车子被交警堵下来。但鸡关久会死,文太科和村民把活鸡放到郊区树林里圈着,八点后再捉起来,关进笼子,送进城去。
虽然文太科尽心尽力,抛开鸡苗和运输的补贴,这个养鸡项目,还是没有赚钱。
生计的确很重要。高思发正在尝试进行生计助学,用养猪或种豆子的项目,帮助贫困孩子的家庭。
小微生计项目实在复杂。吕小英打算,这类项目只投四位数的。因为,对社会组织来说,几万元简直就是大钱,别人给你捐了钱,就要把这个钱用好。
十一、女人
“能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又找到钱的话,比如搞编织等,是最好的。这种生活,她们最向往,还是勤劳朴实。”——石传敏/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

女人无疑是社区中的骨干力量。回到村里并能为当地社区出力的,绝大多数都是女人。因为顾家,她们也很可能继续留在村里。在雅安,外来社会组织所培育的本土社区工作骨干,也大多是女性。她们天然具有粘合社会的性质,比如能歌善舞。
而这些女性骨干总是强调,丈夫支持自己。也就是说,要不然,她们就很难开展这项社会服务的工作。
而在大同村和仁加村的乡工中,男人大多是之前老年协会的成员,女人则多是救灾时帮忙的志愿者。后者服务社区的动机似乎更为纯粹,对未来也更为乐观和积极。
高思发的生计助学,所帮助的对象,大多是家庭不幸的妈妈。高思发请她们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虽然家庭有种种变故,但她们富于韧性。高思发认为,她们是足以让孩子骄傲的母亲。
十二、“人道主义”
“( )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A人道主义 B科学发展观 C共产主义 D宗教思想”——乡工小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试题
“人道主义”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这是吕小英给乡工们出的试卷上的题目,上面全是选择题。之前培训了四次,这算是一次总结。但老人们看不清字,读题比较慢,再说本来也不太记得住。大部分人分数都不高,甚至有没答完的。
石传敏得了八十多分,已是高分。但她把这道题答错了,选成了科学发展观。她回顾这道题,反思到:“科学发展观,是在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开发。首先要做人道主义,要有人,人才能规划一切。”
还有一道题,是关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石传敏也答错了。她说:“我想到,先有爱,然后才有尊重。你爱都没有付出,谁尊重你呢?对不对,等于有种升华。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但一个前一个后。就是这两个之间徘徊。道理转过来,也是想得通的。我受人尊重了,也付出爱。看你从哪个角度进入,需要什么目标。”
她觉得,答这些题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她想起高中的毕业歌,唱完这首歌,她就去下乡劳动了,再后来去打工。而这些选择题,这些排除错误答案的过程,似乎把人拉回少女时期。也许,她不必知道人道主义的完整定义。因为她说:“争来争去有什么用,让一下多好。有能力的过得好点,能力不好的,又瞧不起人家,这不行。你不一定是全的。大家要和平相处。”
而在救灾的实践中,人道主义又化为具体可执行的标准。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老鬼——这位退伍军人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起,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多次抗震救灾,也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如今,他能把全球一百家机构根据以往经验汇编成的“人道主义核心标准”说得头头是道。一人一天要喝多少水,吃多少食物,都是救灾需要掌握的信息。还有性别视角,女性应该得到怎样的救助。
尊重恰好是人道主义的一项原则。比如,救灾要尊重所有人的生活习俗和习惯。“如果有人遇难,不可能扔在那里。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丧葬仪式,要尊重人家。但又不能让他在自己住的帐篷里做丧葬仪式。所以要专门选一个地方作为殡仪馆,也是为了安全。另外,还要了解当地灾民的饮食清单。”
老鬼认为,不是谁扛着旗子,穿着迷彩服就能进入灾区救灾的。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一定要标准化。
十三、减防灾
“应该让更多人来参与。但这个圈子里,能带动社会组织的人不多。社会组织的人个性很强。救灾指挥,你说话,人家得听。这些人是武夫的脾气。”——老鬼/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

减防灾在四川是个重要课题。这里灾害频发。但中小型灾害乏人关注。雅安地震后,壹基金找到中国心的原点公益,希望联合本地组织,发起应对中小型灾害的救灾网络。实际上,在救灾方面,本地组织能应对中小型灾害,才能在应对大灾害上起到作用。
这个覆盖四川19个市州的救灾网络,随时可以响应灾情。有意愿的救灾组织,被加入到网络中。原点公益为其做能力建设,也关注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通过一些项目提升其能力。而这些社会组织在遇到灾情时,就有义务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参与到救灾当中。
具体而言,减防灾是一门专业。
上海等地也有不少学校,请老鬼来做减防灾的培训。他会评估学校潜在的灾害风险,以及老师与孩子的能力,挑选自己准备好的课程——一些内容是自己研发的,因为中国建筑结构不同,不能照搬国外的东西。
研发课程也挺费钱。最笨的方式是做实验。比如,逃生要砸玻璃,要看砸哪块合适。老鬼找了个玻璃厂赞助。一共砸了两千块玻璃,各自记录在什么位置敲,破碎要花多长时间。这样综合算出,整块玻璃哪个位置可以最快最完整地砸碎。
而如果要研究生命三角区,就得盖假房子摇。老鬼认为,不是三角区就能救命,有些区域不找三角区反而安全。
老鬼定期去川大和港理工合办的灾后重建管理学院讲课,甚至给民政系统的官员培训,让官员能看懂灾害管理的报告是怎么来的。
老鬼说,高层政府的民间合作,找的还是2008年的志愿者。本来应该让更多人参与,但人们最信服的还是最老资格的这批人。
十四、行动研究
“行动了就是研究者,一定要研究自己的东西。不学习,很多时候被专家忽悠。人家谈专业,你弹不出来,就傻眼了。”——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领队、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行动研究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主的网络。其中,高思发学历最低,但经验最丰富,也有充分的学习愿望。他参与行动研究已有六年,如今成为里面的骨干力量。
行动研究意味着,自己研究自己。高思发认为,很多基金会不相信,一线工作的人还有做研究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事说清楚,才能让出资方认可自己,才能有尊严。否则,等着别人来研究,与自己的初衷不符,容易招致误解。
相对来说,大多数研究者不接地气,而能扎根下来的社会组织也并不多。因此,行动研究是学习与自我反思,也是自己为自己争取话语权。
高思发感觉,专家喜欢从理论上谈,要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在一线做服务,研究的是自己已经重建了什么样的东西。他打算写一篇关于家庭重建的文章,谈谈这些年来,重建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