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龚龑评《讽刺的解剖》|我们为何而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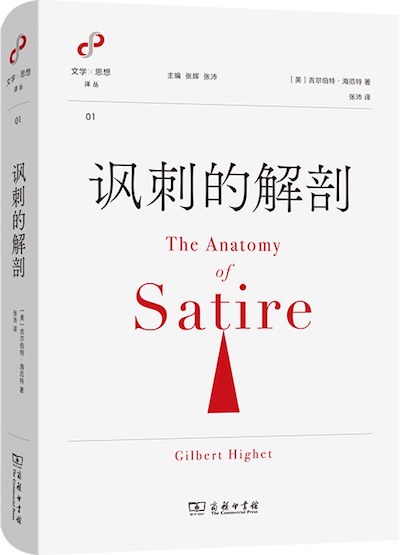
《讽刺的解剖》,[美]吉尔伯特·海厄特著,张沛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384页,85.00元

吉尔伯特·海厄特
阅读《讽刺的解剖》(1962),可以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个久违了的“新批评”年代。作者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是苏格兰裔美国古典学家、评论家、文学史家。他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49)、《荷马概论》(An Outline of Homer,1935)等。诚如作者所说,讽刺是最富创造力和挑战性的文学形式之一。
讽刺的多样形态与历史
海厄特将讽刺文学分为独白、戏仿与叙事三种类型,并以此为脉络,在西方文学中寻觅各种各样的范本。讽刺的多样形态,是这本书研究的重点。“讽刺”究竟是什么,不太容易界定,但围绕着它,有诸多相关联的概念,比如“戏仿”(parody,13页),“反讽”(irony,15页),“讥诮”(lampoon,28页),“攻讦”(diatribe,42页),“讥讽”(sarcasm,62页),“谩骂”(invective,175页)等等(本文提及的页码,均出自中译本《讽刺的解剖》)。作为文学形式,“讽刺”的“近亲”也不少,比如喜剧和闹剧,书中常常征引。
《讽刺的解剖》涉猎的,不仅仅是文学,还包括其他的艺术种类。比如,海厄特指出,米开朗基罗和提香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对《拉奥孔》雕像中某些人物的姿势,进行了“讽刺性的戏仿”(100页);同样,西方音乐中,也不乏经典的讽刺范例,比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仙女之吻》,就是对柴可夫斯基的戏仿。“讽刺”甚至超出了文学和艺术,还可以是“恶作剧”(hoax)。一伙布鲁姆斯伯里的艺术家(其中,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伍尔夫,居然女扮男装!)假冒埃塞俄比亚皇帝一行,并且骗过了英国皇家海军(107页)。作者还以惊险刺激的历史事件为例,说明对真实身份的戏仿,如1944年,一位英国中尉模仿蒙哥马利将军,前往直布罗陀执行任务,竟然迷惑了纳粹情报机构的谍报人员(105页)。广义的“讽刺”,已经不是修辞格或者艺术形式,而是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口号,我们都还依稀记得,“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可谁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二十世纪末,有人高喊“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二十一世纪初却见证了各种“原教旨主义”(不限于宗教派系)的涌现。
海厄特还简单地勾勒了“讽刺”的历史。比如独白型讽刺,它起源于古希腊,到了贺拉斯和朱文纳尔的手里,变得丰富多样,几乎可以和史诗、悲剧曾并驾齐驱。不妨说,这是它最辉煌的年代(43页)。后来,独白型讽刺逐渐衰落,作者指出,终结这一古典讽刺传统的,正是背教者尤立安皇帝。随着基督教的到来,“讽刺独白,几近销声匿迹”(46页)。修道院和教会神职人员,狂欢作乐,或者酗酒成风,早在十世纪,就被揶揄、嘲讽了,彼特拉克、伊拉斯谟等,也戏弄了此种行径。海厄特这里强调的,仅仅是“讽刺型独白”,而它的复兴,则要等到巴洛克时代,经典的作家,有法国的布瓦洛,在英国,则有蒲柏、斯威夫特(51页)。
就英国文学而言,这里有一个不必然的关联。蒲柏、斯威夫特等恰好属于英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奥古斯都”作家。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其统治时期,罗马不仅武力强大,文学上也鼎盛繁荣,贺拉斯和维吉尔就是最好的例证。蒲柏曾写诗献给乔治二世,把后者比作奥古斯都,这当然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后世的文学史家也用“奥古斯都风格”,来称呼十八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文学。蒲柏写过“仿贺拉斯诗札”多篇,约翰逊博士的《伦敦》,则是仿朱文纳尔的诗作,都是讽刺文学中的名篇。英雄双行体,是蒲柏诗歌的一大特点,《讽刺的解剖》中译本以散文体来翻译,也未加说明,这是一个遗憾(如第5页、18页等)。
讽刺的“兴起”与 “不从国教”
其实,讽刺(不只是“讽刺独白”)在英国的“兴起”,和宗教是有一点关系的。宗教改革以降,各教派之间相互攻击,少不了冷嘲热讽,这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尤甚尤烈,本文对此稍加解说,并指出相关讽刺背后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制度化的不公正”。
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恢复国教(圣公会)的法令,在国内实行宗教歧视政策。此时,相对于“国教徒”,产生了一个叫作“不从国教者”的群体,他们是“二等公民”,被剥夺了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权利。1661年颁布的《市镇机关法》,要求市镇供职人员必须采用国教的圣餐仪式,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要求不从国教者服从国教的教义。1673年的《誓证法》重申:一切官员必须按英国国教会的礼仪领受圣餐,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否认天主教教义中的“圣体转化说”。但这样的压迫政策,并不能贯彻到底,总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调整。光荣革命后,由于《宽容法》的颁布,强制不从国教者在星期天到国教教堂做礼拜,这完全不是政府或教会法庭控制得了的。领受圣餐者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更有甚者,在信奉三位一体说的不从国教教徒当中,还流行着“偶尔尊奉国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的做法,藉此,这些“二等公民”可以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等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有条件地”担任公职。当然,也有坚定的不从国教者,拒绝为此而宣誓,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在漫长的十八世纪(1660-1832),曾出现过各种努力,力争要取消《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但均未成功。有了这样的“制度化不公正”的背景,就可以理解国教徒和不从国教徒之间的唇枪舌剑了,不必说,后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讽刺的解剖》所提及的英国十八世纪的讽刺作品,可以说大多与此有关。
1663年,巴特勒的《胡迪布拉斯》面世,《堂吉诃德》和《乔装的维吉尔》是它的“前文本”,这首诗嘲讽的对象是清教徒,确切地说,是长老派教徒。海厄特的评价很精当:“塞万提斯有时拿不准是为力图改变和改善这个世界的堂吉诃德说话,还是为嘲笑堂吉诃德徒劳无功的世人说话。但是巴特勒始终知道谁在嘲笑谁,而且断无疯狂会比理智高贵的想法。”总之,塞万提斯会觉得,吉诃德是有些可爱的,而巴特勒心知肚明,胡迪布拉斯只有可笑的份。约翰逊博士也有类似的评论:塞万提斯对吉诃德,可谓“略有深情”,而巴特勒之于胡迪布拉斯,只是“无动于衷”。中译本在这部分,有一处翻译上的错误,原文如下:“它的主人公‘全无上校的样子(acolonelling)’闯荡江湖。”(135页)这句话出自《胡迪布拉斯》第一卷第十四行,原文是,And out he rode acolonelling。译者大概认为acolonelling中的前缀a,是用来表示“否定的”,其实这里的a在语法功能上主要是构成现在分词,并无语义上的变化。这句话的意思是,主人公“像上校一样,驾马而去”。《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对这首诗有简单的介绍,其中提到“acolonelling against the popular sport of bear baiting”,也就是说,“驾马而去”是为了阻止民众参与“逗熊”之类的娱乐。这是清教徒道德严苛的一个例证,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记中多有记载。
再来看德莱顿的《麦克·弗莱克诺》。这是一首滑稽史诗,诗歌标题的意思,是“弗莱克诺的儿子”。被嘲讽的“儿子”,指的是当时的诗人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此人日后接替了德莱顿,成为下一位“桂冠诗人”。德莱顿在诗歌中,硬是把这位“清教徒”死对头与天主教信徒(作者按:即弗莱克诺)挂上钩。当时的宗教斗争,总是和党派相关。1681年,德莱顿写了《押沙龙和亚希多弗》(Absalom and Achitophel),这是对“排斥法案”的回应。所谓“排斥”,就是不让信仰天主教的约克公爵(查理二世的弟弟,后来的詹姆士二世)继位。其实,英国的两党,就是围绕着“排斥法案”产生的。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指出,《押沙龙和亚希多弗》是“第一次将诗歌和政治结合起来”,颇受民众欢迎。在《旧约》里,大卫王爱子押沙龙造反,仰仗的一位谋士,叫作亚希多弗。德莱顿的这首诗,影射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谋反,而那位维护新教利益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恩主),就成了亚希多弗。德莱顿被沙德威尔唤作“托利”,作为回应,他称后者为“辉格”。此时的德莱顿,以国教徒自居,语气咄咄逼人。稍后,德莱顿写了《俗人的宗教》(Religio Laici; or, A Layman’s Faith),从中读者可以嗅出时代风气的微妙变化,国教徒不得不面对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的诸种攻击,而诗人要求国教徒“保持冷静”。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德莱顿干脆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他的诗歌《牝鹿与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Part 1)就是一个心迹的证明。这个当口,许多国教徒纷纷改宗,以迎合詹姆士二世。时人和后来的学者,都纷纷推测,德莱顿改宗,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约翰逊博士有言,“如果说德莱顿变节,那么,他是随着全国人而变节的”。所谓的变节,就是改宗。
最滑稽的是,在这样的“讽刺”大战中,有时会敌我不分。诚如作者所说,揶揄过于含而不露,甚至给人一种发自肺腑的印象的话,就有可能被误当作是冷静的评论者,或者真诚的赞美者。海厄特以《格列佛游记》为例,不太有代表性(15页)。这里不妨举两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1702年,笛福的时政文章《对待不从国教者的最简便办法》(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问世。在文中,笛福俨然一个托利党人,提出“整治”不同教派的最佳方案:将这些人赶出国门,或者,干脆将教士处以绞刑。文章发表之初,托利分子并不明白,这是讽刺他们自己的迫害行径,而辉格党人反倒义愤填膺,发毒誓要跟此文的作者算账。稍后,掌权的托利党人恍然大悟,二话不说就监禁了笛福,除了罚款,还让他戴着枷锁,在伦敦街头示众三天。
另一个例子,是柏克的《为自然社会辩护》(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1756)。此文刻意模仿博林布鲁克行文风格和思想原则。博林布鲁克是洛克的信徒,将怀疑论经验主义原则应用于宗教,否认任何基于神启的基督教,其中自然神论的倾向,可谓昭然若揭。柏克的模仿,惟妙惟肖,人们确信,这篇文章出自博林布鲁克或其忠实信徒之手。后来再版时,柏克不得不附上一篇前言,说明自己的讽刺意图,其实,他的矛头也指向伏尔泰和卢梭。顺便说一下,伏尔泰曾被霍安家族送进巴士底监狱,出狱后就逃亡英国,期间受到这位博林布鲁克的盛情款待,通过后者又进一步结识了蒲柏、斯威夫特等。比较而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讽刺较为明显,普通读者亦能觉察到。吉本十六岁时,信仰了天主教,他那位忠实于国教的父亲,为此大发雷霆,干脆送大逆不道的儿子去洛桑,在一个加尔文教士的家里反省。1757年,吉本恢复了国教信仰,但终生对宗教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本巨著的第十五和十六章,专门讨论基督教兴起和发展,多有嘲讽、挖苦,引起了时人的谴责。为了驳斥这些读者的偏见,吉本撰写了一篇题为“为15和16章中某些段落辩护”的文章,来澄清自己的意图。
斯威夫特是引述最多的英国作家

肖像画家查尔斯·杰瓦斯(Charles Jervas)绘制的斯威夫特肖像
《讽刺的解剖》全书引述最多的英国作家,是斯威夫特。1697年,在宗教讽刺寓言《一只木桶的故事》中,斯威夫特看似捍卫国教立场,抨击罗马天主教的反动和清教徒的偏激。就在光荣革命的前夕,少数不从国教者犹豫不决,拿不准是否要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宗教宽容”。斯威夫特对此耿耿于怀,似乎他们与天主教徒追求共同的目标。不过,这篇文章里还包含了大量对教会的尖锐批评,以及对神学观点的嘲弄,简直不像是出自一个教会人员的手笔。对斯威夫特的宗教立场,海厄特给出了耐人寻味的评价。斯威夫特虽然“表面上是一名基督徒,强烈地信仰原罪,但对超自然的力量毫无信心,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它的创始人中,都看不到任何救赎的希望”(183页)。这是针对《格列夫游记》而发的评论,断定作者的内心世界谈何容易,更不必说这位讽刺高手了。斯威夫特刚出道时就写过《书战》,对古典派作家和现代派著作都十分熟稔。《格列夫游记》常被当作“儿童文学读物”,实际上,它和《理想国》也很明显的精神契合。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最后都领悟到:灵魂不可能变得“纯洁”,或者说,不可能得到“净化”,除非它脱离了人的身体及其邪恶。《格列夫游记》可以看成是一部“变形记”,“原罪”说到底和我们的身体或者“形”有关。
斯威夫特对光荣革命的态度,更不太容易断定。受辉格党恩主坦普尔(也是他自己的远房亲戚)的影响,斯威夫特写过《威廉颂》,这是对光荣革命的肯定,但这场革命也威胁到了社会的基本秩序,此类担忧在1692年创作、但未曾发表的《桑克罗夫特颂》中隐约可见。桑克罗夫特指的是,刚去世的前坎特伯雷大主教,著名的“拒绝宣誓者”,拒绝向威廉国王宣誓效忠。斯威夫特的讽刺文章,一如蒲柏的诗歌,是最为复杂的,个人性情、政治、宗教和族裔等因素,往往交织一处。谁能说清楚,斯威夫特有几张面孔?他是托利,还是辉格?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他自称,政治上是辉格党人,宗教上属于国教中的高教派。但不要忘记,他还说过:“我们当中的辉格和托利,大多数不是都声称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吗:效忠女王,拒绝向僭越王宣誓,新教统治下的王位;接受光荣革命的最终解决,钟情于国教,以及对非国教徒的宽容。不,有时,他们还更进一步,转而拥护彼此的原则:辉格分子会成为国王特权的坚定拥护者;而托利则变成了(拥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党派 。”
斯威夫特常被当作爱尔兰的爱国者,“自由的捍卫者”(这是墓志铭中的原话),这主要得益于《布商的信》(1724)。实际上,他的写作动机极为复杂,与热爱自由相比,他更痛恨伦敦辉格党政权,尤甚仇视乔治一世和沃波尔首相。斯威夫特曾经紧紧追随辉格党,梦寐以求在英国国教内觅得一个显赫的神职。斯威夫特也不太不掩饰自己对爱尔兰人和爱尔兰政治的蔑视。可以说,爱尔兰最初只是他的流放之地。当安女王去世后,斯威夫特失望地回到爱尔兰,并下定决心不去干涉爱尔兰的政治。接下来的几年,他主要是为安女王的最后一届政府而辩护。那么,《布商的信》背后的愤怒,究竟是什么?汉诺威王朝登基后,托利党失宠,辉格党反攻倒算,弹劾斯威夫特的老朋友、托利党领袖(包括上面提到的博林布鲁克),最重要的是,此时的辉格党政府试图加强不从国教的地位。1718-1719年,辉格党内阁提出一系列法案,为不从国教者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提供了各种办法和措施。当然,国教徒是不会不加反击的。
在整个十八世纪,双方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歇。十八世纪末,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猛烈抨击普莱斯,指责他忘记了作为英国国民的义务。普莱斯是一名不从国教者派的牧师,在《爱国论》(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中,公开支持法国大革命主张的民事与宗教自由。激进的女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虽然是国教徒,却视普莱斯为精神之父,她的《权利辩》是最早答复柏克的文章之一。其中写到,“有人(作者按:此指不从国教者)反对我们的礼拜方式,但在国教教堂之外,他们又无处可以容身,如何祷告或布道,而又问心无愧呢?这位普莱斯博士无非说,他们(作者按:亦指不从国教者)不妨设立自己的礼拜方式,那些不必要的道歉就可一免,也不会招致国教徒的反对”。你瞧,还是那个老问题。
“讽刺”与女作家
在这本书的最后,海厄特花了不少篇幅来探究“讽刺”的动机。其中提到,许多讽刺作家是因痛感自卑、社会不公,或是被排除在某个利益集团之外,才投身写作的。海厄特所举的例子,主要涉及如下几个因素。阶级因素,比如贺拉斯,他的父亲是奴隶。族裔因素,比如斯威夫特和乔伊斯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拜伦和奥威尔是盎格鲁-苏格兰人。甚至有身体因素,如蒲柏身材矮小、畸形;布瓦洛神经过敏,身体多病;拜伦跛足等(275页)。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因素没有被提及。不仅如此,《讽刺的解剖》几乎没有认真讨论任何一部女作家的作品。涉及的女作家,屈指一算,不过三个。前面提到的伍尔夫,是个“恶作剧者”;蒙塔古夫人,只说了一句俏皮话(259页)。说来说去,只有玛丽·麦卡锡的小说《学园的树林》被提及,但一句话就打发掉了,这本小说的题材是“一名自由主义校长领导下的女子学院”(224页)。
一如阶级和族裔,性别也关乎制度化的权力关系。不平则鸣,谈何容易!有一些群体是不便于鸣,或者不敢鸣的。毕竟,并不是任何不满或者憎恶,都可以直接、真诚或者公开地表达出来。哈丁(D. W. Harding)是一位心理学教授,却因《有节制的憎恶》("Regulated Hatred")一文,而留名于奥斯丁批评史。该文起初是他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时所写的讲演稿,1940年在《细察》上,未加改动全文发表。文章开篇就指出,对奥斯丁的印象,经过批评家、文学史、大学讲坛和文学报道等层层过滤,“到了读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哈丁精心挑选了若干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段落进行分析,指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文字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奥斯丁对“井然有序、优雅体面的文明社会,从心底里怀有尊敬的感情”,同时,对其中存在的“粗俗和平庸,也十分敏感”。奥斯丁必须寻找一种隐蔽的手法,既能坚持己见,又不至于和亲戚朋友发生公开冲突。1952年,某一位美国的文学评论家(Marvin Mudrick)干脆说,奥斯丁的反讽是女人独有的心理反应,同时也是自我防护的有效武器。
男女在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的确是他们间真诚交流的一个障碍。反讽在伯尼、奥斯丁等女作家的手中,变得成熟丰盈,成了得心趁手的工具,这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分不开。法国大革命之前,洛克关于幸福、教育、自由和必要的权威等观点,得到各种立场作家的认可。传统派也好,时尚派也罢,他们的论辩中,往往包含着共同的词汇。“情感”是革新者所支持的高频词,但传统人士也希望在家庭中培养健康的“情感”。然而,随着反动风气日盛,这些词汇的含义,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快乐是道德的督促者,这是约翰逊博士的看法,无可厚非,到十八世纪末,却有宣扬纵欲之嫌;个人独立本来也值得鼓励,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却意味着藐视权威。同样,“情感”越来越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几乎是“滥情”的代名词。英法一旦开战,英国国内的社会舆论,在对抗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时,就更强调民族国家的建设了。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改革热情逐渐转向了宗教和社会领域,比如福音主义者和柏克等,大肆宣传审慎的举止,强调自我牺牲的精神。总之,“民族国家”的号角和宗教的热忱,成为那一时期谋求社会共识的有效工具,不仅被用来证明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也推进了文化改革和社会管理。
在整个十八世纪,报刊蓬勃发展,已经为女性话题的自由探讨敞开了大门。但在世纪之交,多数英国女作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何来进一步自由真诚地探讨女性话题,又不卷入革命与反动的政治表态之中;如何来批评父权社会,又不被怀疑传播“有毒的思想”。不难理解,审慎、谦逊、矜持等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品质,在行为指南和道德说教小说中,它们成为支配女性行为的主要原则。前面提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评柏克所谓的“骑士的殷勤”是一种虚假的礼貌。谦逊的确是重要的品质,但要区分真正的谦逊和虚假的谦逊。在沃氏看来,正是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虚假的谦逊和矜持(假正经),包括贞洁的观念,让女性陷入从属的地位,变得不真诚,甚至虚伪。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戈德温,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鼻祖,在同一时期写了《政治正义论》,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真诚”,而他的政治小说(Caleb Williams,1794)讨论的是贞洁观念对男性的毒害。

历史与肖像画家约翰·奥皮(John Opie)绘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肖像
在《对现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评》(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1799)中,针对日常对话中的得体举止,保守作家莫尔给女性提出了广泛的建议。谈话是一种“取悦他人的艺术”;淑女们要学会“倾听”,适当保持优雅的沉默,尽管内心不需要接受。原因很简单,许多男人并不一定欣赏理智的女人。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殷勤和求婚”,她的原话是:“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优雅的女性,存心想要作弄你,我是一个理智的人。”莫尔考虑的是,在不损害“美德”的情况下,将“骑士的殷勤”,或者矜持和谦逊,转化成为女性的优势。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如此的谦逊或者矜持是道德上的弱点,而对莫尔来说,这可是一套复杂的道德义务。考虑到当时的大背景,哪怕是激烈反对革命的女作家,也得细究其作品中暗含的社会批评,莫尔何尝没有意识到女性的边缘地位。
许多英国女性作家,未必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她们害怕被扣上“雅各宾派”的帽子。当然,她们也担心社会秩序的动摇,或对某些激进诉求,如对个人欲望的张扬等心怀戒惧,不得不来批判改革者的热情,同时,又谨慎地界定了保守和进步人士都认同的中间立场。她们吸收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某些因素,宣扬真正的谦逊和真诚的情感,并将这些作为社会稳定和家庭美德的保障。她们也借助矜持和审慎,巧妙地缩小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柏克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一系列暗度陈仓的手法,如反讽、矛盾修辞和双重情节等修辞技巧,就这样被发展出来,从而含蓄地表达社会批评。难怪在二十世纪晚期,“激进的奥斯丁”“后现代奥斯丁”,甚至“酷儿奥斯丁”等比较耸听的提法,不绝于耳。颠覆传统的奥斯丁批评,乃至传统奥斯丁的形象,曾一度成为英美学界的潮流。
这些看似矛盾的阐释,恰说明了讽刺(尤其是反讽)的鲜活力量,通过这些相互矫正的解读,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文学和社会,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解。诚如本书的译后记所说,“讽刺不仅是一种文学类型,更是一种内在于人类存在史、同时为之提供超越可能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现象”。反讽性的矫正一旦变成文化惯例,也许会缓解“制度化的不公正”,增强公民的宽容心和责任感,从而促成一个健康的社会。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