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遵循埃科的“生活指南”,离百科全书式作家更近一步 | 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我坚信写作仿讽文学不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责任之所在。”
在翁贝托·埃科的小说中,我们早已体验到什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公众场合与人交谈时,埃科也经常口出妙语:他说“上帝躲起来了,因为他不想上《VOGUE》杂志”;他说“现实比梦好:假如有东西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而不会怪罪于你”;他说“要建立不朽的声名,你首先需要宇宙性的无耻”……
如果觉得《玫瑰的名字》等代表作的知识点太过频密、难以进入,那么从埃科的短篇散文读起,无疑是接近这位作家的一种快捷方式。近期,收入多篇新篇、直译自意大利语的埃科散文集《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在这本“生活指南”中,埃科式的幽默无所不在:他告诉我们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如何避免谈论足球,如何在美国坐火车,如何谈论动物,甚至,如何成为马耳他骑士……
戏谑、挑衅、幽默,他将深刻与世俗形成了不可思议的结合。埃科以他顽童般的机智和天才般的玩世不恭,对那些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予以解答,又对习以为常的答案提出质疑,将一个个看似“无脑”的话题变得既有趣又深刻。他以“仿讽文学”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们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有些需要被遵守,也有不少正在等人们用机敏和睿智去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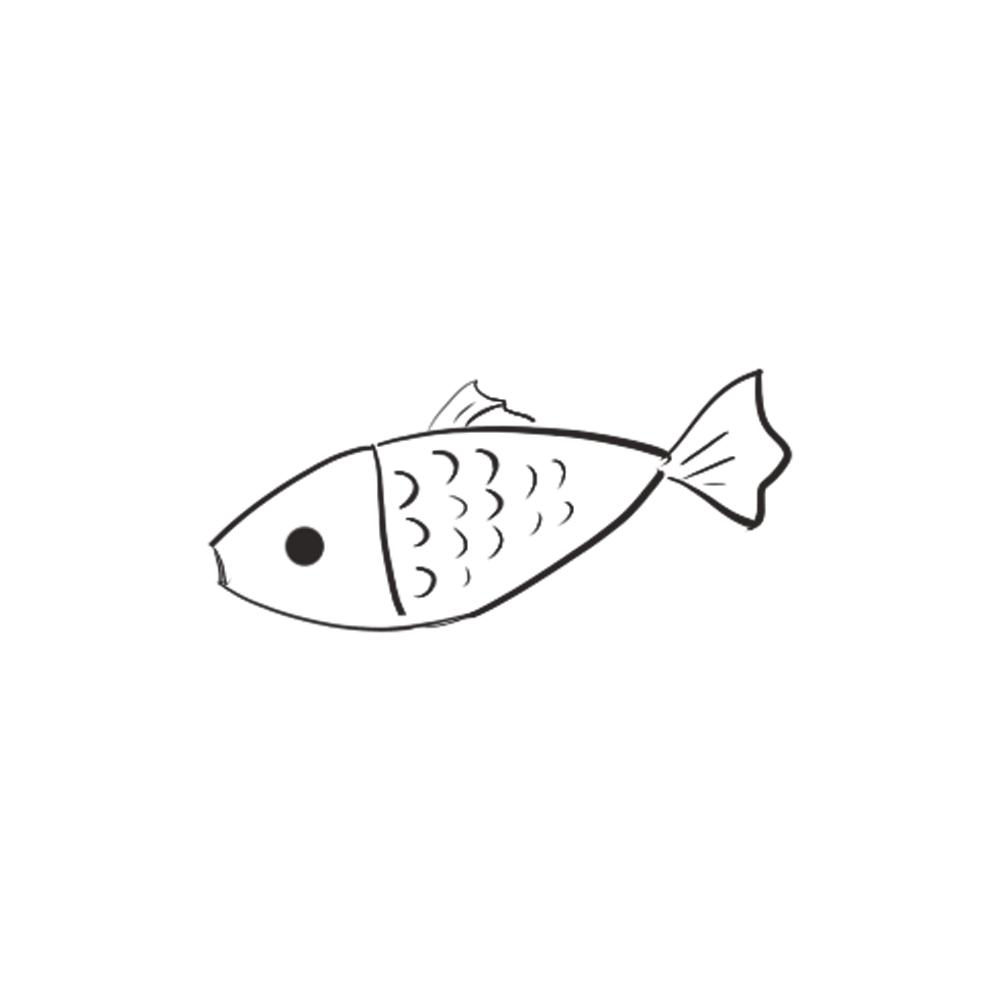
如何避免谈论足球

我对足球没什么偏见。我不去球场,就跟我不去米兰火车站地下通道过夜,或者晚上六点后不会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的理由一样。但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兴致勃勃地在电视上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承认,这种高贵的运动挺值得欣赏。总之,我不讨厌足球,但我讨厌球迷!
我不希望造成什么误解。我对球迷的感情和伦巴第联盟对第三世界移民的情感一样:“要是他们都待在自己家里,我也不是种族主义者。”我说的“家”,其实就是球迷通常聚集的地方:酒吧、自己家、俱乐部和体育场,他们在这些地方做什么我都不在乎。假如利物浦球迷来了,我还能在报纸上看看热闹,因为从流的血来看,简直是还原古代斗兽场了。
我不喜欢球迷,因为他们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他们会这样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是球迷。他们坚持认为你应该也是球迷。我可以举例说明我想表达的意思。我的爱好是吹竖笛,虽然吹得越来越糟糕了,卢恰诺·贝里奥就是这么公开评价的,但被大师悉心指导也是一种非凡的享受。我们假定,我现在坐在一辆火车上,我和坐在对面的先生搭讪,问他:“您听弗兰斯·布鲁根最新出的唱片了吗?”
“您说什么?”
“我说的是《泪的帕凡舞曲》,我觉得刚开始节奏太慢了。”
“对不起,我不明白。”
“我是说凡·艾克,您不知道吗?巴洛克竖笛。”
“您看,我真不懂……是用弓拉的吗?”
“啊,我明白了,原来您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真有意思。但您知道吗?定做一根手工Coolsma竖笛,需要等三年的时间。所以Moeck的黑檀木笛子更好些,可以说是市面上最好的。塞韦里诺·加泽罗尼也这么跟我说。听我说,您有没有听到第五变奏。”
“老实说,我到帕尔玛就下车了。”
“哦!我明白了!您喜欢F大调,我就知道您不喜欢C大调。不过F大调在某种情况下是蛮让人愉快的。告诉您吧,最近我发现了一首罗埃莱特的奏鸣曲……”
“罗埃什么,这谁啊?”
“我真希望他能演奏一下泰勒曼幻想曲。他应该可以吧?您用的该不会是德国指法吧?”
“您看,德国人有宝马,我觉得很不错,最近他们……”
“我明白了,您用的是巴洛克指法,这很对。您看,圣马丁室内乐团那帮人……”
就是这个聊法,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假如这时候,我不幸的旅伴忽然拉响了警铃,你们一定会赞同他的做法。面对球迷就是这么个情况,要是碰上的是个开出租车的球迷,那就更惨了。
“您看到维亚利了吗?”
“没有,可能我当时错过了。”
“那您今天晚上会看球赛吗?”
“不看,我要研究《形而上学》第六卷,您知道吧,就是亚里士多德写的。”
“好吧,您看了之后再跟我说,我觉得范巴斯滕就是年轻的马拉多纳,您觉得呢?但我还是会关注哈吉。”
他就这样一边开车一边说,就好像对牛弹琴。他并不是看不出我不感兴趣。问题在于,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足球一点都不感兴趣。就算我长着三只眼睛,脖子绿色的鳞片上伸出两根触角,他也不会明白:我和他不同。在这个大千世界,他没有差异感,他不知道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我举的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例子,但同样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在某个集团总裁身上。就好像溃疡,穷人会得,富人也会得。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球迷一方面坚定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一样,都应该热爱足球,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打破邻省球迷的头,这种极端沙文主义真让我赞叹不已。就好像伦巴第联盟的人说:“让那些非洲人来吧,看我们怎么暴揍他们。”
如何解释私人藏书

从小时候开始,因为我姓氏“埃科”的意思是“回声”,大家都喜欢用这两句话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别人说啥都会回应啊?”或者“你是不是山谷来的啊?”整个童年我都觉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遇到一些笨蛋。后来长大了,我不得不相信,所有人都无法避开两个定律:一下子想到的东西总是最显而易见的,但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一下子想到的东西别人之前也想过。
我收集了一些评论文章的标题,包括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都是和我相关的,很多在拿我的名字做文章,比如说《埃科的回音》或者《一本产生回音的书》。此外,我怀疑这也不是编辑一下子想到的,可能整个团队一起开会,讨论了二十多个标题,最后主编灵光一闪,说:“伙计们,我想到一个极好的标题!”他的几个下属会齐声说:“头儿,您真是个天才,您是怎么想到的?”“神来之笔。”他可能会这样回答。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想说人们很平庸,没有创造力,把显而易见的东西当作灵感迸发、前所未有的发明。这同样展示出一种精神的敏锐,对无法预见的生活的热情,对思想——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敬慕。我总是会想到我第一次和伟大的欧文·戈夫曼见面的情形:我喜欢他的才气,崇拜他的深度和洞察力,他能入木三分地刻画社会行为的微妙之处,揭示迄今为止还没人谈论过的一些行为特点。当时我们俩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大街上的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觉得城市里的汽车太多了。”可能他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脑子里全是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忽然灵感一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呢,当时深受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影响,是个势利鬼,尽管我也这么想,但从没说出口。
还有一种庸俗的震撼,很多跟我一样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的人都会遇到。进到我家里,一眼就能看到书架,因为家里除了书也没有别的了。于是客人一进门就会说:“好多书啊!您都读过吗?”刚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些不怎么接触书籍的人说的,他们只习惯于看到摆着五本侦探小说、一套儿童版百科全书的书架。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话,一些我确信很有文化的人也会说出来。可以说,这些人对书架的看法和我不一样,他们觉得,书架是放看过的书的地方,而不是用于工作的资料库。我觉得,面对这么多书,任何人都会充满求知欲,所以难免会提出这个问题,这表达了他们的焦灼和懊悔。
问题是,当有人拿我的名字开涮时,我顶多一笑了之,客气的话还可以说句:“好有趣!”但关于书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尽管这时你面部肌肉僵硬,冷汗沿着脊椎骨流下来。我有一次用轻蔑的语气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些书我都没看过,要不然把它们摆在这里干什么?”但这个回答很危险,会引发一系列自然的反应:“那你看过的书都放哪儿呢?”罗伯托·雷迪的回答要好一些:“先生,我看过的书比这多多了,简直放不下。”这会让提问的人呆若木鸡,对你肃然起敬。但我觉得这个回答太残忍了,也会让人不安。于是我换了一种说法:“这是我下个月之内要看的,其他书我都放在学校。”这个回答一方面暗示你阅读量极大,另一方面会让来客提前告辞。
如何提防遗孀

亲爱的作家,无论你是男是女,你可能根本就不在意子孙后代会如何,但我认为此事不可疏忽。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在十六岁时写了一首关于风吹过树林的诗歌,或者记了一辈子流水账,就算只写过“今天我去看牙医”,都希望后人能视若珍宝。即便真的有作家渴望被人们遗忘,如今的出版社总是会全力挖掘出那些被遗忘的小作家,尽管有时候这些作家一行字都没有写过。
要知道,后人是来者不拒的。为了能写出点儿什么,逮住什么是什么,前人写的东西更是拿来就用。因此作为作家,你可要当心后代如何使用你留下的文字。自然了,最理想的是在有生之年只留下那些你决定要出版的作品,把其他东西定时销毁,哪怕是一部作品的三校稿。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留下一些笔记,因为死亡经常来得很突然。
在这种情况下,身后最大的风险就是生前的笔记被爆料,让人觉得你简直就是个十足的白痴。如果每个人都回过头去读读自己前一天晚上记在本子上的东西,就会发觉风险太大了,因为任何文字脱离背景都显得很傻。
假如没有笔记,第二大风险是在你死后像一阵风一样掀起关于你作品的研讨会。每个作家都希望有人写学术论文、毕业论文、作品的评注版来纪念自己,但这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事儿。死后马上举办研讨会,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会让一堆朋友、评论家和渴望成名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写下评论文章,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下只能炒剩饭,把之前人家说的再说一遍。就这样,过上一阵子读者可能会对作家本人失去兴趣,觉得他不过尔尔。
第三大风险是私人信件公布于众。作家也是凡人,写的信和凡夫俗子没什么两样,除非他像大诗人福斯科洛一样,通过书信来写小说。作家可能在信中会留下这样的句子:“给我寄一些治便秘的药。”或者:“我疯狂地爱着你,感谢你降临人间,我的天使!”自然了,后人去查看这些资料也很正常,他们会得出结论,大作家也是人啊!那还能怎么样,难道他会是一只火烈鸟吗?
如何避免这些身后的事故?对于那些写作时记的笔记,我建议你们藏在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同时在抽屉里放一份类似于寻宝图的文件,说明存在这些笔记,但要用一种别人无法破解的语言记录文件的具体位置。这会产生双重效果,一则隐藏了手稿,二则会催生很多学术论文来讨论这张地图的谜底。
针对研讨会,可以在遗嘱中写清楚,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在你死后十年内举办的研讨会必须捐赠两百亿里拉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搞那么多钱绝非易事,但要违背你的遗嘱,那也得脸皮够厚才行。
情书的问题比较棘手。还没来得及写的情书,建议用电脑完成,好让那帮笔迹学家无从下手,签名时要用昵称(“你的小猫咪、小狗子、小兔兔等等”),每换一个情人就换一个称呼,到时要都算到你头上也很难。情书可以写得热情如火,但建议留下些让收件人觉得尴尬的细节(比如说“我也爱你的臭屁连天”),这样对方可能就此放弃公布的念头。
但那些已经写好的信,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写的,就无法挽回了。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找到收信人,再写封信给他们,心平气和地追忆往昔的难忘岁月,再三强调那段记忆不会褪色,即使你死后,也会经常探望故人,重温旧梦。这一招不见得管用,但再怎么说,鬼魂可是鬼魂啊,那人公布了你的信,也会睡不安生。
你还可以写一本假日记,在里面要暗示你的朋友们有弄虚作假的爱好:“真是一个爱说谎的女人,我可爱的阿德莱德!”或者:“今天瓜尔提耶罗给我看了一封佩索阿的书信,那是一封伪造的信,但差点儿让我信以为真!”

《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
[意] 翁贝托·埃科/著
陈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标题:《遵循埃科的“生活指南”,离百科全书式作家更近一步 | 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