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黎︱微物之神的国度
在南印度、尤其是西南角那一带旅行,常会产生错觉,以为时空倒流,回到多年前的南台湾:香蕉树、木瓜树、榕树、椰子树、槟榔树(是的,当地人也嚼槟榔),还有那些熟悉的花:牵牛花、美人蕉、扶桑……还有水边的白鹭鸶——那里几乎处处有水,多半是从阿拉伯海流进来的平静的“回水”,肥沃的河海沼泽地,养成了一块风土与印度其他地方大不相似的鱼米之乡。

热闹大神庙
位于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与其他地方一眼就看得出的最大不同,就是宗教。同是南印度,东南方常见的巍峨壮观的印度教大神庙,到这里就极少见了。车行在喀拉拉邦的路上,无论是市镇还是乡间,每隔不多久就会出现尖顶上有十字架的教堂。原来早在十六世纪,随着葡萄牙航海探险家达伽马“发现”绕过好望角的印度洋航线之后,就有源源不绝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这里。在滨海大城科钦的圣法兰西斯教堂里,原先就葬着病故在此的达伽马;虽然十五年后他的遗体被送回了里斯本,但教堂至今还保留着那块原址。还有一个极其特别的“景观”就是处处常见的招展红旗,上面清楚显示着斧头镰刀的标志——共产党在这里不仅合法,而且经常是民选出来的执政党。

为了感受这片鱼米之乡,我们一行五人先是在“回水”乘船——带着当地的新鲜水产请船上的厨师烹煮,在船上度过悠闲的一天一夜,还靠岸顺道拜访一个岸边人家。夫妻子女加上老人和长兄六口,住在三房两厅的平房里,男主人打渔贩鱼,女主人开一间小杂货店,也像极了台湾的“柑仔店”,最大差别是这家店的顾客多半是乘船来的。

上岸后的一个清晨,我们去当地的鸟类自然保护区,领我们观鸟的向导是一位退休的英语教员。保护区也在水边,他来到一处傍水的树丛停下指着对岸说:“听过《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这本书吗?隔着水就是Ayemenem村,作者罗伊的家就在对岸。”我听了感到一阵惊喜,就像这个陌生人竟然读出萦绕在我心头,却一直没有问出的话。

来南印度,尤其是喀拉拉邦,有一个对我很强烈的召唤,就是《微物之神》这本书。因为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也是作者罗伊(Arundhati Roy)的家乡。书中对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和现场景象无不描述得历历如绘,二十年前读到时就非常喜欢,书中的人物和场景常常萦绕心头难以忘怀。二十年后再度细读,就是准备到这里旅行,寻访故事场景了。

虽然是获得英国布克奖的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在国外却鲜少听到印度人提及这位世界知名的同胞作家。不仅如此,这本书出版不久就在家乡喀拉拉邦被禁了,罪名是“腐蚀公众道德” 。赢得大奖后成了国际瞩目的作品,竟然在家乡成为“禁书”,作者当然不服上诉,令得科钦高等法院的法官左右为难,判也不是不判也不是,案子拖了几年,最后换了法官才撤销禁令。虽然“腐蚀公众道德”这项罪名,看起来指的是书中一段炽烈而优美的性爱描述,但实际上触怒“公众”的,恐怕是书中对亲人和乡民,甚至政党和整个社会种姓制度残忍无情、不公不义的描绘和揭露。所以触犯众怒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倒是这位向导的下一句话使我惊喜:“我们都以这位作者为荣!”
这本小说1997年一出版就赢得英国布克奖,同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最佳五部书之一。我读的是原文,中译据我所知有两本,不久之前我找到现今流传较广的一本。可惜作者使用的语言太奇特,不仅用字遣词生僻刁钻,还有许多西方和印度的典故、双关语,更伤脑筋的是夹杂不少她的母语——当地的Malayalam语,再加上多音节的人名和暱称,以致于翻译难度极大,初读译本时不免会觉得有些晦涩难读。
我知道小说是虚构,但我也从作者的自叙和受访中得知,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对应历史事件的时间点都是精准的:时间是1969年,作者八岁,正是书中贯穿主线、几乎是半个叙事者角色的小女孩“瑞海”的年龄;二十多年后长大了的瑞海回溯当年情景,也正是罗伊开始写这本书的年纪。场景地点是南印度喀拉拉邦,也是作者的家乡,一个并非虚构的名叫Ayemenem的村子;甚至于若干主要人物的身分背景,也颇有雷同之处,包括罗伊本人跟瑞海同样在大学是学建筑的,后来也去到美国……所以我才稍稍违背了“不在虚构小说中寻找真人真事”的原则,来到“微物之神”的发源地。
什么是“微物之神”呢?
印度教是多神的,还不只是一般的多——印度教的神是数以百万计的,简直是满天神佛。希腊神话里那些跟凡人纠缠不清的男女众神,比起多如天上繁星的印度神来,就显得寥寥无几了。就算是最荒凉贫瘠的印度乡下,也不乏缤纷灿丽的色彩,这就多半要归功于那些无所不在的、姿容丰润美丽的众神,和那些神庙、神殿、雕塑、彩绘、庆典……从北到南从东至西几趟印度之旅下来,参观了数不清的壮丽精美的庙宇圣殿宫廷洞窟,对几位主要的印度大神大致耳熟能详了:大梵天(Brahma)、妙毗天(毗湿奴,Vishnu)、大自在天(湿婆,Shiva),各司创造、保护、毁灭之大任,暗合了佛教“成、住、坏、空”的宇宙观。不过人气最旺的还要数胖墩墩的象头神迦内什,护佑子民趋福避祸;还有中国人不可不知的风神之子、飞将军神猴哈奴曼——大名鼎鼎的孙悟空的原型。

南印度神庙
神兽雕塑
白色大神庙
可是在这些威力无穷的大神之外,也会有更多不计其数的小神,司掌着无足轻重的人间小事吧?罗伊就在她的小说中创造了一名“微物之神”——祂是最渺小、最卑微的事物的神,祂的子民是如此渺小卑微,有时连神也无法庇佑他们,甚至藐视、厌弃他们。这就是“微物”的悲剧。当然,这部小说“微物之神” 说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里面的小人物,不仅被人、也被他们的神离弃了。
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阿慕”——也就是瑞海和她双生兄弟的妈妈——出身望族,家族里几代信奉的,就是喀拉拉邦特有的叙利亚基督教。阿慕的父亲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可是这个备受尊敬的男人在家中却是动辄毒打妻女的暴君。阿慕为了脱离家暴而早早远走他乡嫁了人,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女。阿慕匆促婚嫁的对象是个没有责任担当的男人,嗜酒如命险些丢掉工作之际,竟然想把妻子“献”给对阿慕垂涎的英国上司。阿慕当然不能忍受,带着一双小儿女回到娘家。可是作为一个“泼出去的水”的女子,阿慕在娘家过的是仰人(母亲和哥哥)鼻息的隐忍日子;虽然暴虐的父亲已经去世,但同样可怕的是家中还有一个心地偏狭、阴险自私的姑母,总是在窥探挑拨,唯恐天下不乱。
依然年轻美丽的阿慕,重逢了家中自小一起长大的长工维鲁沙,一个黝黑健美、温柔正直的木匠,两人相爱了——却是致命的、禁忌的爱。阿慕虽是遭受歧视的失婚妇人,但她的阶级身份是“高贵”的,而维鲁沙,和他的世世代代,很不幸的,属于印度种姓制度里最低贱的“不可接触”(Untouchable)的贱民。这个制度之森严,不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不同阶级的男女胆敢相爱,他们触犯与违反的,是整个家庭、社会、文化的最大禁忌与律法,是十恶不赦、天地不容的行为。当维鲁沙的父亲发现儿子与主人家小姐的私情时,竟然痛哭流涕地到主人家告自己儿子的状,痛责儿子不守本分胆大妄为而誓言要“宰了他”。奴才尚且如此,主人家的反应当可想象,阿慕立即遭到禁闭。
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同时,也显现了男女两性的极度不平等:同样是离了婚的哥哥“恰可”回到家中不仅不受歧视,还掌管了母亲的果酱工厂;作为老板,他常跟女工们行苟且之事,对象无论是已婚妇人还是贱民,家人却视若无睹,溺爱他的母亲还暗中资助他。
更有甚者,这场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由于一桩突发的意外而成为一场涉及其他人的大灾难:恰可的英国前妻与女儿来作客,女儿却意外溺水,出了人命就牵连到那对带着她涉水的双胞胎兄妹——瑞海兄妹因为妈妈忽然被关而仓皇离家出走,渡河去到“历史之屋”避难,来自英国的小表姐跟着他们却不慎落水溺毙。不巧小兄妹的好友维鲁沙也在那里,阿慕的姑妈便乘机罗织,指控维鲁沙心怀不轨,绑架了小孩而导致命案。
身为“贱民”,维鲁沙的逾越行为不仅冒犯了牢不可摧的种姓制度,甚至也涉及工人权益和政治斗争——号称同为劳工兄弟的公会同事其实不齿与“贱民”平起平坐;号称为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当地共产党书记其实不把维鲁沙当同志;以致于维鲁沙的下场可谓世间之至惨:他遭受至亲、好友、上司、同事和政党同志无心的或有计划的出卖与背叛,最后连他的神也弃他于不顾 ——只除了他的恋人阿慕。但阿慕完全无能为力拯救他,她连自身和两个孩子都保不住,被逐出家门之后不久也抱恨郁郁以终。
至于这对双生小兄妹——这一切事件的关键人物,在邪恶的姑婆精心诱骗下,懵懂无知地顺从了大人的指控,背叛出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好友维鲁沙。目睹维鲁沙的惨死,造成他们一辈子的罪疚与创伤,永难平复。男孩变成一个不再开口说话、人们眼中与世隔绝的“怪物”;女孩瑞海则在孤僻与叛逆中挣扎成长,结婚离婚、浪迹异邦,最后决定回到家乡她的手足身边,面对过去,和那抛弃了她的微物之神。
作者其实志不在述说一则老套的爱情故事,而是描绘一个地方志、建构一段国族史。故事的重心其实都只发生在1969年底的两个星期里,多半是从小瑞海的眼中看出去,但迂回曲折的反覆倒叙、二十四年后成长到了他们母亲去世年纪的双生兄妹的回顾、穿插过去的历史和当时当地的种种风土习俗,交织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漩涡,宛转回溯,越转越回旋越深,虽然书的一开头就显示了结局,但要直到小说的最后才终于一切真相大白。事情发生的当下,孩子是无知的、懵懂的,虽然有着天赋的直觉与敏锐,却还是要等到二十几年后,也就是书中的“现在”(作者书写的年纪),长大成人的瑞海才有勇气面对不堪回首的过去,回到家乡回顾、寻找、疗伤、和解。
除了家族居住的村子Ayemenem,书中人物的活动范围也涉及近旁的市镇Kotayam(他们都是搭乘公交车来去),甚至两小时车程外、有飞机场的大城科钦(一家人由恰可开车去机场,迎接来访的恰可的英国前妻和女儿)。我们的行程就以这几处为重点,最后从科钦机场离开印度。我们先是在“回水”乘船,贴近感受水乡——书中“水”是重要象征,孕育了爱情也导致了死亡。然后来到Kotayam,车子竟然经过一间警察局,立即想到书中警察对维鲁沙暴虐施刑、阴险的姑母在那里哄骗小兄妹陷害维鲁沙、阿慕带着她的儿女来到这里要为维鲁沙申冤,却遭到警长不堪的羞辱……差一点我就要下车“凭吊遗址”了。
我们下榻的酒店在回水的另一边,面向大海。我一到那里放下行李,就抱着试探的心情问大堂经理知不知道这本书?他理所当然地说知道啊,我很高兴,立即向他打听怎么去Ayemenem House——小说中阿慕家族的宅邸。经理说这是书中主角的家,“但很有可能就是作者本人的故居”。二十年了,还有对这本书内容这么熟悉的人!他很快查出地址,并且替我们雇一辆出租车载我们过去。至于小说里用了不少笔墨提到的那栋她称为“黑暗之心”的“历史之屋”建筑,曾是这对悲剧情侣的爱巢;作者言之确凿地说是一位印度共产党领袖的故居(那位“领袖”倒是确有其人),他那栋荒废的河边屋宅,书里说多年后变成了观光酒店,我却怎样也查不到那家酒店的下落。问这位所知甚多的酒店经理,他却说不曾听过那栋“历史之屋”或者其后改建成的观光酒店的事,我只好把这栋屋子搁下,专程去看“阿慕的家”。
出租车在小路上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就到了Ayemenem。说是村落,其实是个还算齐整的小镇。司机显然对这里不熟悉,几度掉头、打转、问路,我都几乎要放弃了,最后车子开进一条窄巷子,一眼看去竟是几栋气派不凡的洋房,跟外面街上的房子大不相同。而巷子尽头,在浓密的、充满南国风情的树丛后面,赫然出现一栋南欧式的红瓦白墙楼宅——我终于找到它了,阿慕的家!

那条巷子里的几栋庭院深深的楼房,在印度乡间确实少见,而尽头的那栋特别有气派,是真的可以称之为豪宅了。大门是双扇铁栏栅,不遮挡视线,前院和建筑本身从外面看进去一目了然。院子很宽濶,花草稀疏;主屋建得高,上正门得走好几级台阶——果然有台阶,记得书中提到有九级,我怎么数只有八级——也许四五十年下来,最下面一级被草和土湮没了?远处有个工人模样的人,也许是守门的,我向他呼叫,他朝我们摇摇手表示闲人莫入。

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只好隔着栅栏拍了照,然后失望的转身,想退而求其次,从屋子旁边绕到后面寻找那条河……可是两侧都是封死的墙,除了退出巷子,根本没有继续往后走的出路。正想不甘心地退出,却见右首边一栋小洋房,从大门上方看得见阳台上有一位老先生正在看报。我们抱着姑且一试的心隔着门喊话,问他说不说英语?他竟然放下报纸慢慢走过来。透过门上方的空格,我向他简单说明来意——不无夸张地告诉他:我们万里迢迢从美国来看罗伊的故居,可惜进不去,我们想看看近旁的河,怎样才能过去?
我自说自话一阵之后,忽然想到说不定人家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于是试探地问他:“你知道《微物之神》这本书吗?”老先生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当然知道。我是作者的舅舅!”我的惊喜神色大概感动了他,老先生打开大门,迎我们进去。我回身拍下大门旁墙上气派的金色名牌,记下了主人家的全名。
进门后就在花木扶疏的前院里,我们礼貌地向主人作简单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老先生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位退休的骨科医生。估计他有八十出头了,是一位气质温雅的老绅士 。

老医生很友善,他说巷底那栋大宅是他们家族的产业,罗伊小时候常在那里玩,等于是在那里长大的;房子现在空着,雇族人看管。他指指正对面比较小些的一栋房子说:“那栋是罗伊的家,她住在德里,回来时就住这里。现在也空着。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妹妹,住在Kotayam城里。她母亲退休之前是位开办学校的教育家。”办学校?那不是苦命的阿慕未曾实现的梦想吗?罗伊现实人生里的母亲竟然做到了!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隔壁竟然住着罗伊的舅舅,而且听到这许多“内幕”。记得罗伊在一篇访问中自己“对号入座”,说她在Ayemenem长大,离了婚的妈妈带着她和另一个手足回来这里(就跟阿慕和两兄妹一样),外婆开了家果酱工厂(也跟阿慕的母亲、瑞海的外婆一样)。老先生既然是罗伊的舅舅,我不禁脱口而出:“那么你就是恰可(阿慕的哥哥)了?”说完就后悔不迭, 书中的恰可虽然是留学牛津的罗德学者,却是个肥胖、没气质、没担当的男人,最后还把妹妹逐出家门……眼前的老先生温文儒雅,和善可亲,怎会是恰可?好在老先生不但不以为杵,还微微一笑说:“我不是恰可,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兄弟正是罗德学者。”我打蛇随棍上:“那他的太太是英国人?离婚了?”(唉我真八卦!)他又微笑了:“不是英国人,是瑞典人,是离婚了,现在这个太太是印度人,他们现在住在美国。”
我们越聊越高兴,最后他竟然说:“我妹妹(罗伊的妈妈)住在Kotayam,妳在这里待几天?我可以安排带妳去见她。”我几乎为之心动,但想想未免太冒昧了,也太违反我读虚构小说的原则了。老先生固然热心友善,但罗伊的母亲很可能并不想见人,尤其是万里迢迢来到的陌生人;更何况罗伊本人要是知道了,说不定会怪她的舅舅多事,甚至迁怒我这唐突的“粉丝”……还是到此为止吧,这已经是很意外的奇遇了。我们很开心地与“舅舅”合影,然后由衷地谢了他,礼貌挥别。

我还没有忘记那条河。虽然河边绝对不会有维鲁沙的小茅屋,也不会有那艘承载过他俩而最后翻覆了的小船,而我终究还是没有找到河对岸的“历史之屋”,但在渐渐降临的黄昏,我们还是循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来到了屋后的那条河畔——双生兄妹在那里戏水,他们的小表姐在那里溺毙,维鲁沙在那里涉水来与情人阿慕相会,他们乘一艘小独木舟过河去到“历史之屋”,历史的必然和命运的偶然在那里将他们残酷地吞噬……许多年过去,悲剧的帷幕始终不落下,直到成长的孩子回来面对、埋葬。

戏台化妆
最后一晚我们看了印度西南最有名的卡塔卡利地方戏,以浓厚的脸部彩妆和鲜艳夸张的服饰留给人深刻的印象。 绿脸红唇和大蓬裙,正是这戏独一无二的特色。演员全是男性,但扮出的女角却极为妩媚。演的都是民俗传说故事,一般要演上一整夜,但为了将就观光客,表演只有不到两个小时,其中还有一半时间是演员在舞台上化妆给观众看,剩下的时间一半解说舞蹈的眼神动作,最后以一场短剧作结。罗伊在书里用大篇幅详细描述了这个地方戏——二十多年后迈入中年的瑞海,在自我流放多年后回到家乡,有一晚跟她的双生兄弟不约而同来到小剧场,看了一夜的戏,演员与观者都精疲力竭,却像一个净化仪式,那些痛苦的记忆,都在这个历史文化不绝如缕的地方戏里叩问,凝固,升华。
罗伊在访谈中说:“实际的经历到哪里为止、想象从哪里开始,是很难说的。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实的故事,但里面的感觉都是真的。”正如木心说的:“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好的小说一定是这样的。
第一本小说就获得那么高的成就,罗伊却没有如众所期待那样接着写下一本小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她成为一名实际行动家,投身政治和社会运动,倡导人权和环保。她关注、查访、报导的议题包括:妇女和弱势族裔的权益;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尚有无数生活在贫穷线下的百姓的印度政府却要发展核武;政府兴建大水坝对环境的影响和对居民造成的迫迁流离(她捐出《微物之神》的版税收入来支持反对建坝的行动);支持克什米尔独立(因而被控以“煽动叛乱”罪)……她以文字呼吁和纪录,出版了五本散文和评论集。然而大家还是在殷殷期待她的下一本小说。
终于,整整二十年之后,她的第二本小说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我将之暂译为“极乐使命”)将在2017年6月出版。我期待这本新书,同时期待着我的下一次印度之旅 ——当然,很可能又是追寻她的文字足迹,去到另一个她的时空,另一个神祇的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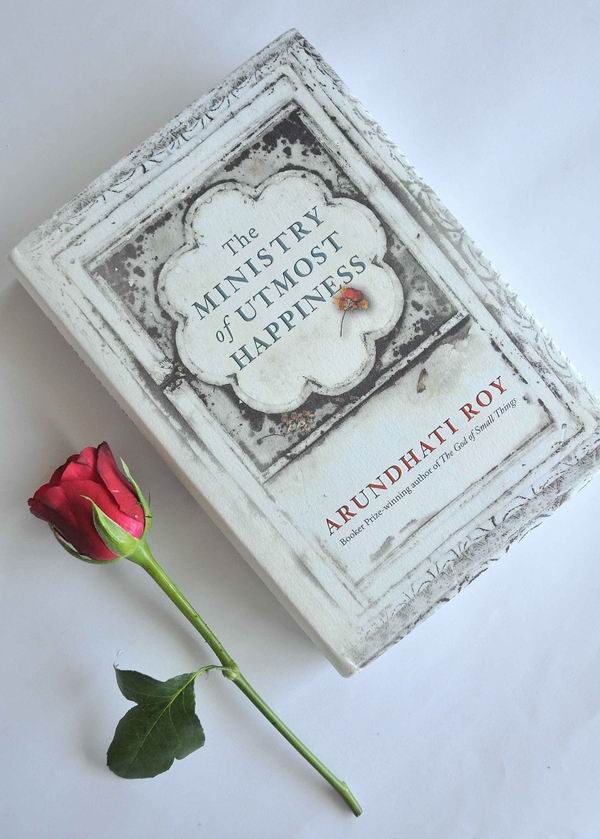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