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木心追求的“文化焊接”和“文本再生”,是否等同于“抄袭”?|文化观察
原创 姜玉琴 文学报
最近开始不断有人围绕着木心的创作,发表了一些批评的意见。委婉含蓄的说法是,木心的很多创作都有一个原文本,甚至有的篇章还不止一个原文本。木心本人的创作过程就是对这些原文本进行“较小程度”的改写过程,并把这种靠通过“较小程度”改写而成的新文本命名为“文本再生”;不客气的则直接斥责木心的这种创作方式就是一种对他人的抄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读这种与他人文本互有关联的文学现象?

1
辨析互文性与独创性
推敲起来,木心的部分作品里是有其他作家、诗人,包括哲学家、理论家的影子,甚至在某些片段中会有着一些明显地改变字词和次序的现象。从表层来看,这种对别人东西的改写或演绎应该算是一种抄袭的行为。但对木心而言,这个过程的发生有着特定的意义:他对别人文本的改写或演绎,在多半情况下并不是因为那些名家说得好、写得好才予以改写和演绎,相反他是认为这些人说得不够到位或不够全面详尽,没有点明事物的本质,所以不得不予以重新的改写和演绎。
“人在悲哀之中,才像个人。”(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先生啊,也有在悲哀中也不像人的人呀!”(木心)
“智者即是对一切事物都发生惊奇的人。”(纪德)
“致纪德:智者,乃是对一切事都发生讶异而不大惊小怪的人。”(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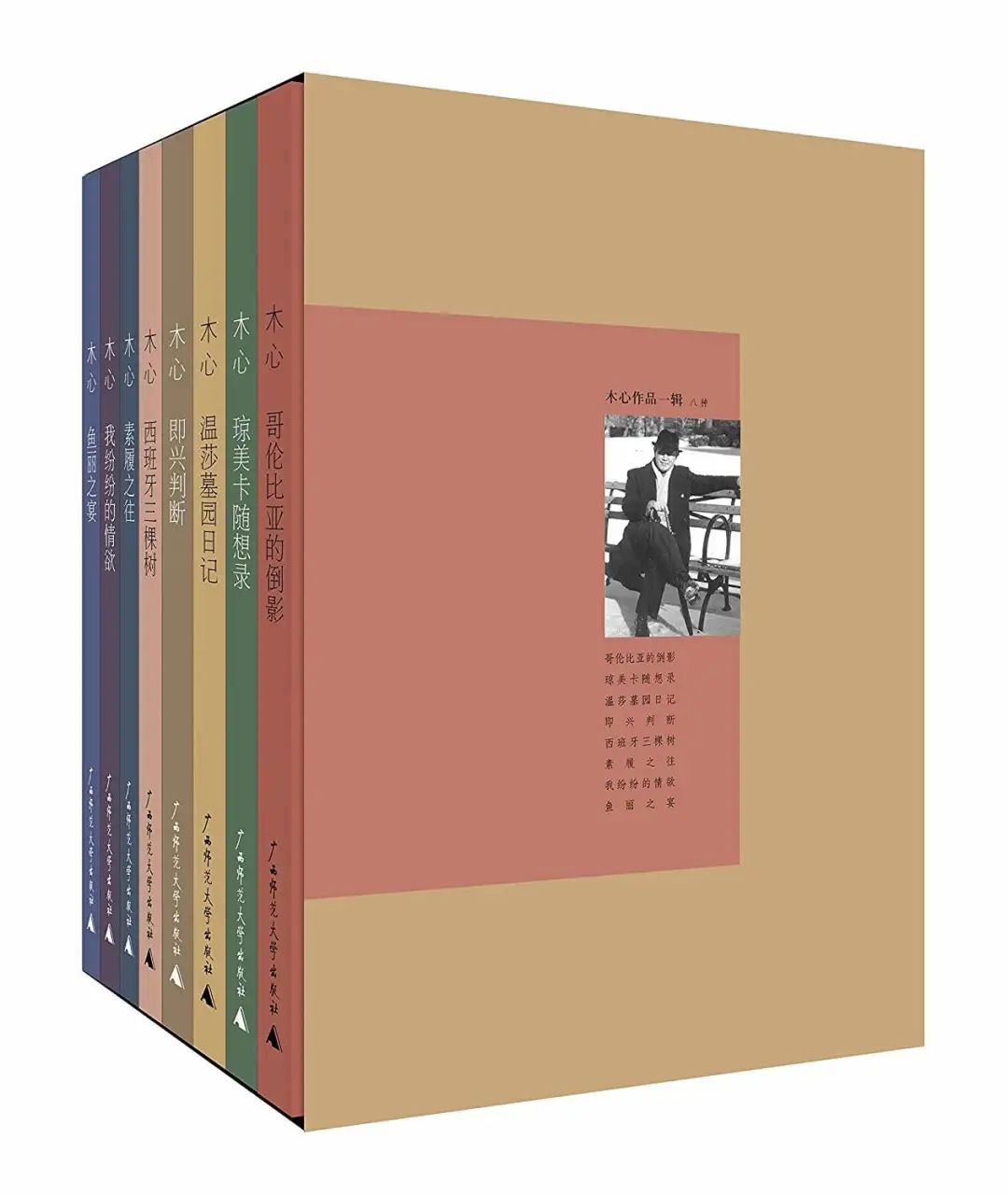
有两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孟德斯鸠说:“人在悲哀之中,才像个人。”木心在自己的文本中把这句话演绎成了,“孟德斯鸠先生啊,也有在悲哀中也不像人的人呀!”纪德有一句名言是“智者即是对一切事物都发生惊奇的人。”木心则将其改写为“致纪德:智者,乃是对一切事都发生讶异而不大惊小怪的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木心的这两段文字分别与孟德斯鸠和纪德有关系,可以说是木心的“原文本”。换句话说,木心就是在这两个“原文本”基础上改写成自己所谓的“再生”文本,但是这种“再生”的文本非但不是抄袭,也不是“较少程度”的改写,相反他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即用对方所提供的文字资料又推翻了对方的说法——用对方的“矛”打了对方的“盾”,给予了一个更高明、更有张力和更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界定。如果非要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改写”的话,那也是一种完全不同含义的改写,这种改写中不但蕴含着思想的真知灼见,也蕴含着文体上的独创性。
显然,此处与其说木心是在抄袭孟德斯鸠和纪德,不如说木心是在用自己特殊的创作手法来与这些伟大的人物、有趣的灵魂展开心灵的对话。正如他说:“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阅读木心的书会发现,木心是有把古今中外的作家都视之为“朋友”的习惯,正如他在《地下室手记》中所写:“我有朋友的,古今的艺术家和我同在,艺术对我的教养此时就是生命意志,是我的宽慰。”该处的“朋友”,就是指“古今的艺术家”。每个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创作习惯和策略,木心的习惯与策略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与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优秀作品保持一种互文性,即通过与他们交流心得、对话技艺的方式,汲取与完善前辈作家的优秀成果,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自己创作的一次飞跃。

理想国近期推出的第一批《木心遗稿》
我为什么要强调木心的这种创作方法是汲取与完善前辈作品的优秀成果,而并非是抄袭,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与前辈们有关系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与止于前辈,而是把前辈成果的终点当作他创作的起点,即木心之所以要借助这些外力,其目的就是要实现自己的那一跳。面对前辈和前辈们的作品,木心的内心其实是极为从容与骄傲的,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常常会不自觉地留露出心理和智商上的优越感——“我”的思想见识、美学见识可是比你们要高出一截。正如他曾借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来表达自己对国人所写书的不满。正常逻辑,木心应该对这部“吸引我读,读着读着,浸润在幸乐之中”的书,拥有一种敬佩之情——没有这种情感的产生,也就没有必要借这本书来说事,但是木心的内心活动却是:“我举布克哈特这本书,是借来骂我们这边,而且要站得比布克哈特高。”木心并没把布克哈特视为一个高不可攀的人物,相反他认为自己看问题的“点”,要强于布克哈特。
这种“沾沾自喜”并非是夜郎自大,从木心所改写或演绎的那些具体文本来看,凡是经他之手改过的东西,不论在语言上还是境界上都更上了一个层次,衍生出了新的且富有现实的意义。
2
历史远景与理想远景

雪天木心照片
或许有人会说,木心为何总喜欢拿着别人的东西下手,他就不能撇开别人,自己造自己的东西吗?首先,这应该与他的性格有关。木心是一位有精神洁癖和美学洁癖的人,被他所能看上眼的东西并不多;即便是看上了,还是觉得有瑕疵,不够完美,所以就禁不住地要把这件艺术品变得更加艺术化。
其实,这种创作手法并不陌生,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就具有这种特性。我在一篇名为《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一文中,就曾谈到过盛唐边塞诗人为了突破时空之局限,便有意识地通过引用和改写的方式,把其创作融合到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中去的现象。这当然不是盛唐边塞诗人所独有的创作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一就是一个相互引用、改写和创作的过程。如一句“诗言志”,都是你说、我说、大家都说,没有谁特意注明过其出处和发展,对其来龙去脉感兴趣的都是现代人。而对古人而言,这一切都是公共资源,一个大的文化场域,谁都可以接着说,区别在于谁说得更好,谁说得更妙。还有中国古代的变文,其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引用和改写的文体,即借用中国民间故事,并用中国不同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来对固有的佛经教义、佛经故事进行改编,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佛理能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到民间百姓中去。
最后一点,这也与木心本人的艺术追求有关。木心曾认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缺乏或丧失了两种远景:历史远景,理想远景。为了把这两种“远景”还原到现代社会中来,他便把历史上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为一种背景知识引用到其作品中来,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历史参照,即以此手段使作品获得一种应有的纵深度。
3
追求文化之间的“疤痕”


木心画作,他表示绘画深受林风眠影响
我们再来谈谈木心的“仿”。不可否认,木心是喜欢“仿”,他有一种强烈的“仿旧”情结,但他的“仿”不是一般意义上模仿的“仿”,而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仿”。他的这种“仿”,有时或许多少有点西方学者所说的“戏仿”,但更多是一种让旧的生命“再生”的意思。只不过,这种“再生”不是某些人所指的抄袭,而是一种注入了新鲜血液、具有了新的体悟和精神,使之焕发出新生命光辉的意思。其实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美国小说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就是“续写”了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对此行为,西方的评论界也是众说纷纭,先是有人用抄袭、剽窃等来抨击这部作品,后又有评论家用“重述”、“改写”或“模仿作”等来进行解读与辩护,最终这部作品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先后获得了普利策奖和国际笔会福克纳奖。而且,该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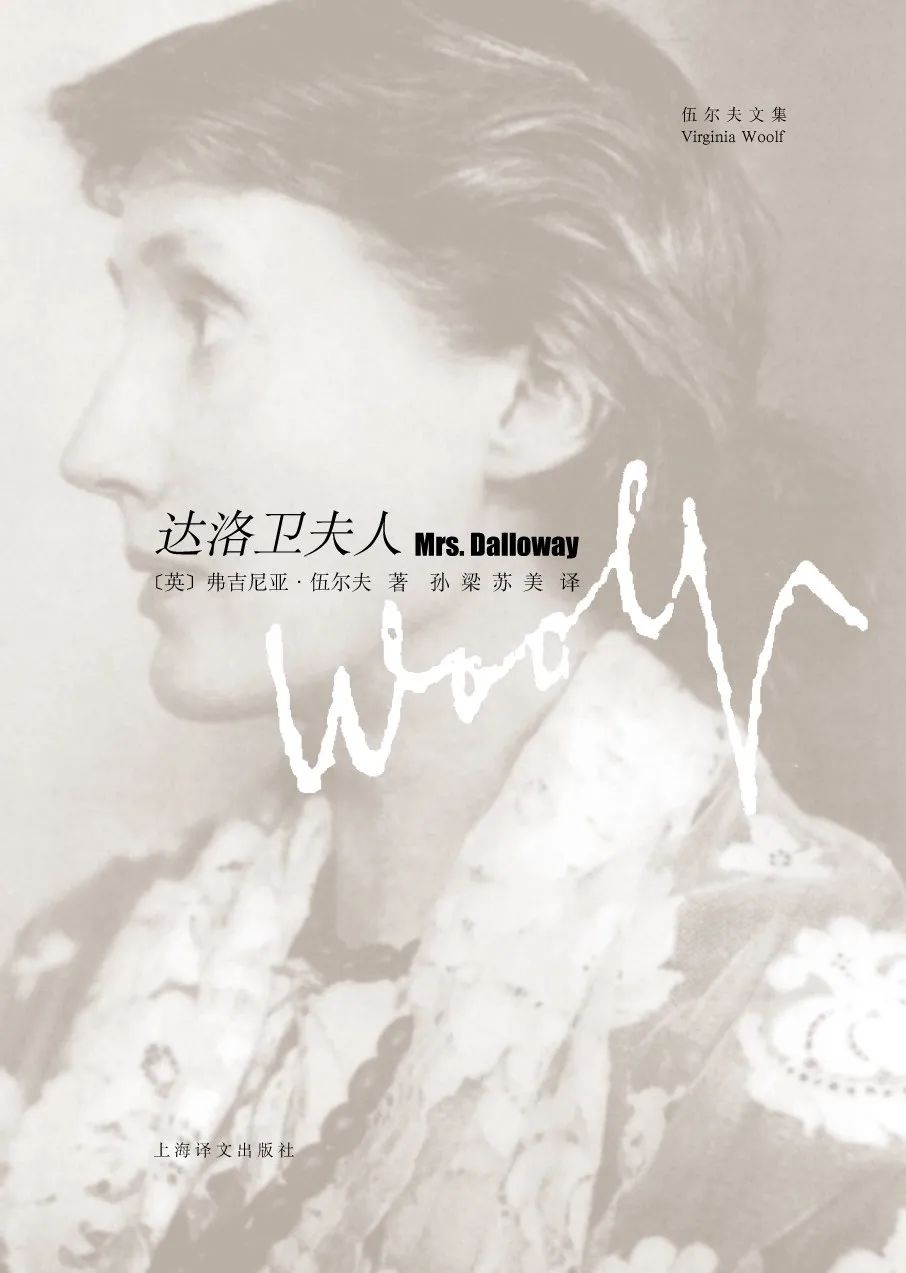
什么叫文学原创?文学原创有多种,一种文学原创是把从未有过的东西创造出来;还有一种文学原创,是把看上去还不错的东西重新进行改装、塑造,使已经静止的东西迸发出新的活力——是属于一种让“好”变得“更好”的文学创作行为。
有人说木心不交代改写、演绎的出处,就是一种有意识地掩盖其抄袭行为。其实不然。木心对于这种文学创作行为,在文章中有过多次申明,诸如他说:“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拿了你的东西,叫你拜倒。世界上只有这种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拿了你的东西”不错,但“拿了”以后,被拿的人不但不恼火,反而愿意对拿的人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这既是木心对“原文本”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对所谓“文本再生”的一个回答。
事实上,木心的《诗经演》也罢,《伪所罗门书》也罢,这些作品的题目本身就早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而且,木心不但不掩饰自己与其他文学文本的关系,还会洋洋自得地向弟子们炫耀他的“最杀手的拳”,即“写作的秘密”。我们知道,木心在美国时,曾经给陈丹青等一批留美画家讲述了长达5年的“世界文学史”。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曾以自己的作品为例,给他的这些弟子们传授一般“老师不教”的创作秘籍。他是以自己的《即兴判断》的“代序”为例的。他就像老师给学生剖析实例一样,把“代序”中话,一句句地讲给弟子们听,并指出其中每一句话的来历,譬如“代序”中的“谓我何求,谓我心忧”,是来自于“《诗经》的典故,简化了”;“代序”中的“岂予好辩哉”则是“孟子的话”。他之所以在该处要取用孟子的这句话,是为了把前面的那句“‘肆意妄言’解了”;而“代序”中的“鲜有良朋,贶也咏叹”这句话是“取《诗经》”等,反正短短的三行话,几乎句句都是有来历、有典故的。

《即兴判断》代序:
丁卯春寒,雪夕远客见访,酬答问,不觉肆意妄言——谓我何求,谓我心忧,岂予好辩哉。鲜有良朋,贶也永叹,悠悠缪斯,微神之躬,胡为乎泥中。
通过他的这番自我解析,不难发现木心在创作中非常喜欢用典、化典,追求古人的那种句句有来历的文风。对此,他还专门给这种创作手法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搭架子”。而他之所以要搭这个架子,也是有目的的,即是“搭给人家看。懂事的人知道,‘来者不善’,不好对付”。当然,除此之外,他的这种“搭架子”还是与他的美学思想关联在一起的,正如他说:“今文,古文,把它焊接起来,那疤痕是很好看的。”追求的就是古旧之间的那种“疤痕”的微妙。同样,木心之所以喜欢把西方作家的作品“焊接”到自己所创作的中国文学中来,也是出于中西文化交界处的那个“疤痕”好看的考虑。
生活中的木心是一个无比讲究的人,讲究到什么样的大衣必须要配什么样的帽子和什么样的鞋子,就连裤子缝隙的走向都不能乱来;创作中的木心也是一个无比讲究的人,讲究到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哪个句子扣哪个句子,什么时候要“破题”、什么时候要把“钉子敲下去”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同样,他在作品中要引用谁、改写谁、演绎谁,为何要这样做都是有着起承转合的考虑,绝非是把别人的东西随便一抄就完事。套用今天的一个批评术语,木心是一个非常注重修辞的人,追求语言、形式和思想最大程度的戏剧化。面对写作,他就像一个导演,精心勾画、步步为营。

乌镇木心美术馆 图
说到底,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木心是一位有着更多旧文学趣味的文人。这与他的年龄无关,比他大的有牛汉和郑敏,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木心的这些“毛病”。木心很复杂,身上既有我们所没有的那种世界大同意识,也有我们所没有的那种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木心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可效仿和复制的。他的经历、学识、教养、趣味以及独特的个性特征,都决定了他不是我们中的“那一个”。
对待像木心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需要带有审视的目光,但同时更需要进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与创作轨迹中去。他的创作自成一派,放到中国新文学中也是独具特色,不可取代的,与其说是抄袭,不如说这就是他的写法。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跳舞、画画很痛苦,那你的跳法、画法大有问题。”他在创作时之所以要操持这套“写法”,就是因为这样做能令他觉得快乐,能满足有学问的心理。对待木心这样一个处处讲究雅致、格调、教养以及处处都要有意识地打破人们既定期待,即一个充满戏剧精神的人,我们需要有理解与敬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木心追求的“文化焊接”和“文本再生”,是否等同于“抄袭”?|文化观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