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 +115
鲍文欣︱“进步儒学”:含义模糊的标签?
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教授是近年来十分活跃的美国儒家学者,迄今出版有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 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2)等著作。其中的最后一本著作已译成中文,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安靖如:《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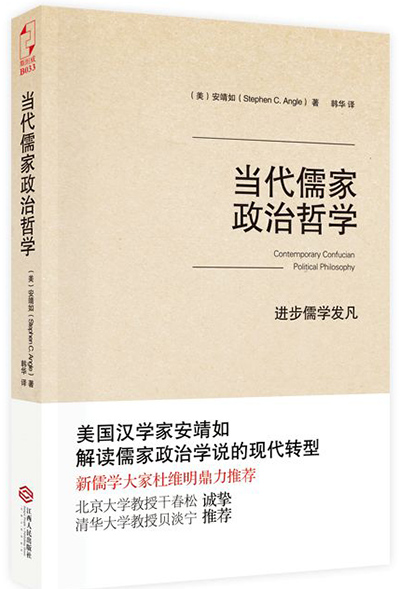
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儒家思潮中,政治哲学问题始终是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些年来随着大陆的儒学复兴,政治哲学问题更是有上升为中心议题的趋势。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来看,现代儒学百年来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有两个端点,一端探寻什么是“好的”,另一端则探寻什么是“中国的”。因此也就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心态,一种认为“因为是好的,所以是中国的”,另一种则认为“因为是中国的,所以是好的”。百年儒学的流变,似乎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依笔者浅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并不必然地、悲剧性地与对现代价值的否定联系在一起;但在当代儒学讨论中,一种即使还称不上主流、但的确十分响亮的声音,似乎对这条偏狭的思路青睐有加。
在这个语境下,类似于安靖如教授这样的讨论者的加入便具有独特的意义。安教授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同时又认同于“儒者”这一身份,与大部分当代中国儒者不同,他天然地就没有对于“文化自信”问题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现代儒家百年来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这种跨文化身份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从反面来说,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微妙特点是西方学者难以体会的。例如安教授几乎不加批判地赞同马克斯·韦伯关于“祛魅”的观点,并自称是“无神论者”。但在西方基督教语境和中国儒家语境中,所谓“神”的意义差别极大,表达两种不同的宇宙感觉。“生生之谓易”的背后当然没有基督教式的上帝,而与此同时,大化流行又并非价值无涉的客观过程。在私下的交流中,我发现安教授对“无神论”有更为复杂的理解,但同时也不难察觉,作为基督教反题的“无神论”如何限定着他一些临场的、更为即时的反应。
正面地看,跨文化的身份使得安教授具备了更为开放的态度。由此他的焦点便不在于维持或证明“文化自信”,而是在于建立一种“有根基的全球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它“意味着在一种特定的有生命的哲学传统中进行哲学研究,因此它是有根基的,但同时对来自其他哲学传统的刺激与深刻见解,采取一种开放的方式,所以它又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第16页)。与部分大陆新儒家对政治激进主义或明或暗、有时是不由自主的亲近不同,安教授明确地将另一种他所熟悉的传统——自由主义——作为参照:“在政治哲学领域,本书旨在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同时也会论及儒学与现存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制度体系的持续性差异”(同上)。另外,英美哲学的训练背景使得他习惯于对当今在世的同行学者进行坦率的评论,也十分善于用细密的方式讨论问题。可以相信,安教授清新的理智,谦和的态度和开放的胸怀,将为当代的儒学讨论带来更多自由的空气。
在《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中,安教授所提出的最具刺激性的论题,也许是重新启用牟宗三先生的“自我坎陷”说,将之作为其政治哲学推理的基本方法。但笔者见识尚浅,无法对此提供更进一步的观察。在这里只限于就一个更表层(但并非不重要的)的问题做些评论。
安教授将自己的儒学主张称为“进步儒学”。对于所谓“进步”,他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界定,首先,它用以描述“针对个人和集体道德进步的儒家思想核心”,其次,“该词也代表着一种通往我将自始至终在本书中提倡的研究儒家政治哲学路径的特定标签”(同上,第4页)。然而,由于“进步”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复杂性、变化性和超强的渗透力,它能否成为一张表意清晰的标签是大可疑问的。

安教授认为,“英文的‘progressive’一词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内涵。而中文的‘进步’主要指的是经济上的发展”(同上,中文版序,第2页)。这就把中文中的“进步”理解为一个太过削薄的观念了。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发展中,现代“进步”观念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厚度。业师高瑞泉先生曾指出中国现代“进步”观念的四层含义,第一,指“社会向善论”;第二,指“主体德性的提高和完善”;第三,指“相信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知识和科学技术将不断增长”;第四,指“对力量的追求,相信人类能够不断扩大自身的权能,以征服自然界”(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48-50页)。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宾塞、海克尔等人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以及诸如冯友兰的“无极而太极”、熊十力的“翕辟成变”、甚至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特点的话,也许我们还可以增加“进步”的第五层含义:它不仅指“人事”,还可以指“天道”。因此,安教授可能需要明确的是,他大体上是在第一和第二层含义上使用了“进步”观念。
其次,当安教授将“个人和集体道德进步”视为“儒家思想核心”时,给人的印象是他基本忽略了“进步”观念的古今之变。的确,个人的道德进步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主题,在宋明新儒家那里,甚至已经有直接用“进步”来描述个人修养进展的用例。例如朱子曾说,“主忠信是劄脚处,徙义是进步处。渐渐进去,则德自崇矣”(朱熹:《朱子语类》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6页)。王阳明也曾说,“自今当与诸君努力鞭策,誓死进步”(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但在“集体道德进步”的层面上,传统儒家的态度则较为悲观。用高先生的上述区分来说,传统儒家致力于“主体德性的提高和完善”,但这并没有导致“社会向善论”,传统中占主流的历史观仍然是衰退论和循环论。因此,安教授所辨识出的“儒家思想核心”,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家思想与现代“进步”观念相交涉所形成的产物。笔者指出这一点的意图,当然不是要宣布安教授的儒学不“正宗”,而正是赞同他的观点:儒家是一个活着的传统。但正因为儒家的活力与多变,我们才更需要哲学史和观念史的追溯,来确认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所处的历史方位。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哲学史和观念史的追溯,我们能够了解到,在现代中国思想中,不单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在各个层面上有不同侧重地接受“进步”观念。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性观念,“进步”是处于各种思想势力争夺之中的公共话语资源,换言之,各种主义之间所争论的是并非进步与否,而是进步意义的强弱、何种进步、谁更先进等问题。在这些争夺中,“进步”逐渐获得了包括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宇宙论、现实社会政治安排等多方面的含义,并最终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占有。例如,在当代语境下,“要求进步”这样的用法最有可能出现在入党申请书或政审报告上,而不会是在哪本儒学研究著作中。因此,当中文读者看到“进步儒学”这样的名目时的确会感到费解,但这种费解的原因也许并不是将儒学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而是难以判断,这里所谓的“进步”究竟是何种类型的。进一步地看,安教授曾提出过“广义的进步儒学”的概念,将康有为、牟宗三等人的儒学主张囊括其中。然而,这个概念难以将当代的另一些儒学主张排除在外。记得读本科时,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课堂上,黄玉顺老师经常面带微笑地说,“儒家没有新的,然而儒学是常新的”,这种“常新”便是一种弱意义上的进步。再比如被安教授称为“复兴主义者”的蒋庆,他虽然明确反对强意义上的、相信“人类历史必然进化”的进步观,但同时又“相信人类历史有其希望”(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第249页),并且把他的“政治儒学”视为儒学的“发展”,因此实际上仍持有较弱意义上的“进步”观。
总之,安教授将“进步”与“儒学”联系起来,的确有助于破除以儒学为一律“保守”的成见。但是,由于上述困难,我们实际上难以仅仅通过“进步”这一含义模糊的标签,将他的儒学主张有效地辨识出来。因此,也许安教授需要对他所使用的“进步”做出更详细的说明。当然,这一辨识标签上的困难,不会妨碍我们去承认“进步儒学”在当代儒学讨论中的独特意义。

- 大秀肌肉
- 国家卫健委驳美炒作病毒溯源
- 明日出征!航天员详细信息来了

- 河南郑州拟调整公积金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延长到68岁,女性延长到63岁
-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特斯拉涨约7%

- 约每76年环绕太阳一周的彗星,是人类首颗有记录的周期彗星
- 一部国产经典动画片,主人公是一只当警官的黑猫

- 19何竹康同志逝世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