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保罗·索鲁新书《深南》:是陈词滥调还是奇情异想?
文|杰克·希特;编译|Deanna
【编者按】旅行文学界的老面孔保罗·索鲁,今年年初入围斯坦福·杜曼旅行文学奖的新书《深南》(Deep South),惜败于一本由美国新人作家朱利安·萨耶尔(Julian Sayarer)撰写、同样是以美国为目的地的《洲际公路》(Interstate)。
《深南》讲述的是美国南部的黑人之路,对于生于美国、大学毕业即投身旅行并接受和平团教职,先后在意大利、马拉维、乌干达、新加坡、英国等地生活的保罗·索鲁而言,这实际上他第一次真正以一本书的体量审视自己的祖国。尽管在此前的五十年里,他曾经出版过关于中国、印度、俄罗斯、太平洋群岛等一系列被奉为圭臬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保罗·索鲁抱着无比接近故乡的念头投入写作,而一路所见的贫穷与倒退,却令他得出了自己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像一个游客,美国南部实际上也远比自己以往去到的所有地方更像外国的矛盾结论。
本文作者杰克·希特(Jack Hitt)为《业余艺术家:寻找美国特性》一书的作者。在这篇书评文字里,他以略嫌尖锐的措辞直指索鲁的叙事矛盾,以及隐藏在《深南》里的核心问题——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姿态,和戴着文化偏光镜的写作方式。其中一些观点或许会激怒相当大一票索鲁粉,但或许多少也道出了这位当代著名旅行家在天马行空的笔力与冷面笑匠式幽默背后的束手无策。

在保罗·索鲁的新书《深南》中,各种关于美国南部的浅薄、刻板的印象一股脑登台亮相了。书中第一幕,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县,是个“炎热的周日上午”,他写到了耍蛇表演和口音浓重的交谈、贫穷、五旬节派教堂、黑人理发店、枪友会、校队橄榄球,还有福克纳那句必不可少的名言——“过去并没有死”,甚至还出现了一位时髦的黑女人。这时我们甚至连第一页都没读完。
书中描述的种种关于美国南部的过去,既像陈词滥调,也像社会学一年级水平的文字:“南部的教堂是社区搏动的心脏,是社交中心,是信仰的港湾,是灯塔,是音乐的舞台,是聚会之所,提供希望、劝诫、福祉、温暖、陪伴、旋律、和谐与小吃。”看吧,这是个因奴隶制和种族而格外复杂的地方。我们过往生活的真相是史诗般的残忍,而历史则将之变成史诗般的神话。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奴隶制,如今,仍然有许多黑人和白人依然挣扎于荒蛮的贫困中,自从种植园经济被军队合法摧毁之后,这样的贫困就折磨着整片地区。多种形式的种族仇恨使得经济复苏推迟了一百五十年之久。
任何与深南部有一面之缘的人都会知道,以上所述均属事实,而非什么新发现。这些事实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居然有人——且这个人还是重量级旅行作家索鲁,《暗星萨伐旅》、《骑乘铁公鸡》等书的作者——愿意浪费几千字、白烧许多加仑汽油,去体验这么多面目全非的旧时光重现,不由得感到费解。

显然索鲁在上路前读了相当多关于南部的经典著作,也正是这些作品令他笔下的故事更显老迈,比如詹姆斯·阿吉的《让我们开始赞美名人》,威廉·福克纳的故事,玛格丽特·伯克-怀特的摄影作品,以及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而且,作者似乎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对于其余则漠不关心。他总在向老年黑人询问60年代的种族歧视情况,问起几代人之前的学校隔离和3K党暴力活动;与白人打交道时,他最关注当地人,想找到像电影《生死狂澜》中的角色那样的多余人;造访查尔斯顿时,他告诉我们他觉得古老的漂亮建筑很无聊,乔·莱利市长在任40年间的杰出城市规划也没什么意思,而人口与跨种族关系中的巨大迁移带来的烹饪复兴更加不值一提。相反,他直奔枪友会而去,毫无悬念地与一群反政府偏执狂、阴谋理论家和纳粹纪念品收藏爱好者展开了亲切的交谈。
究竟作者为何要给自己戴上这么一副密密实实的文化偏光镜,他也曾给我们一点提示:“没错,我去过巴塔哥尼亚、刚果和锡金”,但“我还没有在深南部旅行过”。大量冗词长句的铺陈,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他的深度阅读覆盖了美国南部以及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对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理查德·怀特、佐拉·尼尔·赫斯顿、查尔斯·波蒂斯,托马斯·沃尔夫、威廉·斯泰伦、杜鲁门·卡波特、卡森·麦卡勒斯、爱丽丝·沃克和德里克·沃尔科特等人的作品很有研究。我数了一下,这份耀眼的名单中足足包含35位名作家,作者可能出于任何原因顺手掉个书袋,哪怕遇到一群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人,他也会觉得“这些人是契诃夫式的人物。”

他也阅读伟大的经典作品,比如乔叟;发现内地的乡下人上大学时并不会选择中世纪英语课程时,他觉得很好笑。有一次,他与一位黑人牧师交谈,对方自我介绍为帕默主教。索鲁问,“‘帕默’就是朝圣者的意思吧,那些从圣地带棕榈叶做的十字架回来的朝圣者,乔叟不是那么写的吗?”帕默主教感到很困惑,于是索鲁解释道:“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朝圣者愿云游陌生的海滨。’”此时,索鲁忍不住对读者私语:“他的笑容就好像听见了特别晦涩的言论、或者听见狗发出了奇怪的叫声。”帕默主教主持的礼拜仪式包括整整一下午的唱歌、讲道,还有分发的午餐;出席礼拜后,我们这位在旅途中的北方佬写道,“真让人感动,《圣经》的些许严肃教诲能够提升人们的灵魂。”
一页又一页,索鲁都维持着这种屈尊纡贵的姿态。他约见了欧陶县一位非常忙碌的黑人女士,奇怪的是,这位女士的身份和会面意图他从未解释过;他去晚了,因此被这个“满头螺旋状卷发的、瞪着眼的老女人”责骂了一顿。几行乏善可陈的文字之后,他又重复道:“野蛮的螺旋状卷发让她看起来像是戈耳工。”她解释说,他理应打个电话过来、却没打,还补充道:“我会称之为‘白种人特权’。”于是索鲁立刻用自己的比克笔威胁对方:“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小笔记本,咔哒一声拔开钢笔帽。‘白种人特权,’我一边说,一边慢慢地记下来,‘喔……。’”
“当她说她是黑人的时候,”索鲁对读者坦露道:“她就已经完全不是黑人了。她可能是混血,她可能是西西里人,她也可能是——而且很可能就是——切罗基人或者巧克陶人。”
喔……

说起他的伟大发现:深南的贫困地区真是穷得令人心碎。这当然是真的,不过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环游阿帕拉契地区时早已发现了这一点,沃克·伊万斯的摄影作品曾表现了这种贫困,国家非常时期对策委员会于1938年发布的《南部经济状况报告》中、甚至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回忆录《矮棕榈叶》中也以各自的方式使得大众注意到了南部乡村的困苦生活。于是,索鲁加入围观者的队伍,带着恐惧,更多是怜悯,看者他们在困苦中激烈挣扎的身影。
上述这些书的每一本,都出现了关于文化退步的描述,关于枯井、无知和脏地板的隐喻。在索鲁看来,这简直就是非洲。一段关于为极贫人口建造房屋的对话中使用了“官僚主义的黑话”,索鲁认为“这种话我在非洲听到过”。南卡州的阿伦代尔“像是津巴布韦的一个小镇”,虽然几页之后,这个镇子就变成了“让人想起肯尼亚内陆的农业小镇,现在只有狗住在那里。”不过,200页之后,他又把话说了回来,他确定了自己的隐喻:阿伦代尔放在津巴布韦也绝不违和。
回到塔斯卡卢萨县,索鲁遇见了疯狂的红潮队球迷(Crimson Tide football);他把头盔滑至眼下,看见“大写的斜体A字母,代表阿拉巴马,画在车上和衣服上,还常常用鲜红的颜色刺在皮肤上。”球迷的庆祝是“暴乱般的部落仪式”,其中有些男人把‘A’字纹在脖子上,有些女人纹在肩膀上。可你猜猜塔斯卡卢萨让他联想起了什么?是“住在丛林中的勇士用野猪牙和鼻骨把自己全副武装”,还有“苏丹丁卡人那样的面部疤痕。”

阿拉巴马州格林斯伯勒镇的一个女人讲述,她的儿子去了赞比亚,成为社区发展的志愿者,此时索鲁拼命“忍住一阵讥刺的大笑”,因为“这里与我见过的赞比亚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并且,更好笑的是,索鲁约谈的某人迟到了,于是他对读者悄悄说:“如果这是在津巴布韦——这里确实很像津巴布韦,我可能会事先说好:事情紧急!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从非洲回来。”
最终,作者笔下的美国南部的也就沦为一种奇情异想。他把其他人的观察都塞进了自己的脑袋,并急不可耐地忽视了所有可能挑战他的先入之见的材料,令整本书读来就像是堂吉诃德的一连串长矛,刺向詹姆斯·阿吉的风车。最后一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或许道出了事实真相,他这样解释道,“因为最根本的矛盾在于,尽管我走了这么远——比我在非洲或中国走得还要远得多——我却从未离开家乡。”看来,保罗·索鲁还应该多出去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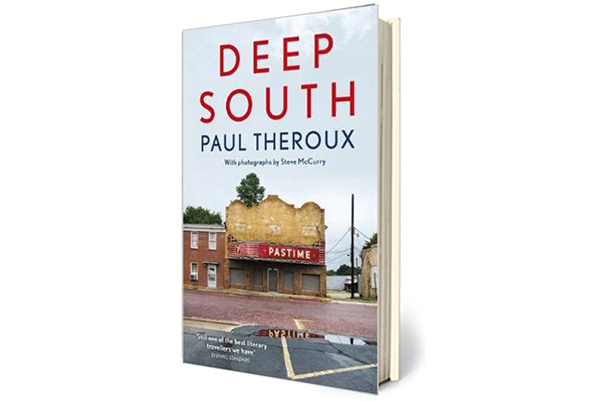
来源《华盛顿邮报》
更多前沿旅行内容和互动,请关注本栏目微信公众号Travelplus_China,或者搜索“私家地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