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火车、时刻表与陌生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现代性想象
火车是晚清时期“舶来”中国的新事物。清光绪二年(1876)吴淞铁路正式通车,一时间“观者摩肩夹道,欲买票登车者,麇集云屯,拥挤不开”(陈定山《春申旧闻》),吴淞铁路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关于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另有1865年北京宣武门外的“模型铁路”和1881年唐胥铁路两种说法)。二十年后,一八九六年上海《时务报》上首次刊出张坤德翻译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此后,西方侦探小说便进入到中国,并在中国掀起了一波翻译和创作侦探小说的热潮。
火车与罪案及侦探小说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火车也是中外侦探小说作家们格外偏爱的罪案发生空间。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西村京太郎的“铁路旅情”系列侦探小说,以及希区柯克的犯罪悬疑电影《火车怪客》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可能是由于漫长的火车旅途实在太过无聊,于是这些侦探小说作家们便开始展开各自的文学书写,想象着一桩又一桩和火车有关的谋杀案。

《轮下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着“民国侦探小说第一人”之称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作者程小青的代表作《轮下血》,可以视为无聊的火车旅途与刺激的谋杀案件之间关系的某种隐喻。在小说里,作为侦探助手的包朗就不断感叹火车旅途的寂寞无聊,“虽然只有数小时的途程,却还不免要发生烦躁不耐的感觉”,似乎总要发生点什么“新鲜的刺激可以来调剂一下”,才能打破这种火车上的沉闷。果然,小说里几分钟后就出现了一起火车轧死人的案件。侦探霍桑敏锐地注意到死者生前曾购买过人寿保险,并由此联想到了死者家属通过伪造火车交通事故来进行杀人骗保的犯罪可能性,最终竟至破获了一个专门制造“杀夫骗保”连环事件的“十姊妹党”犯罪团伙。
作为“速度巨兽”的火车
除了打发旅途中的无聊时间外,火车与侦探小说之间更深层次的内在关联还在于作为现代文明器物的火车给前现代人群所带来的冲击与恐惧之感。这种恐惧感往往内化为某种心理焦虑,并通过文学罪案想象的方式来予以表达。前现代人群对于火车最为直观的恐惧感受首先是其速度、浓烟与轰鸣声所带来的不安,即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在《铁道之旅》中所说的“对于熟悉的自然被一种自身拥有内在力量源的、喷着火焰的机器所取代的恐惧”。
在清末民初,传统中国人对于作为新事物的火车也有着类似的焦虑和不适感受,陈建华在《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中对此有过如下一番描绘:“眼睁睁看着黑压压庞然大物一往无前阻我者亡地在神州大地上横冲直撞,心头就不大好受。震耳欲聋的呼啸,飞驰而过的速度,对于一向崇奉牧歌美学的中国人来说,神经真的受不了。”再加之当时中国人对于破坏风水的担忧,以及火车所普遍隐喻的西方殖民之手对中国广大铁路沿线地区的深入和掠夺,火车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人而言,其所带来的现代威胁感受可谓有着切身之痛,且一言难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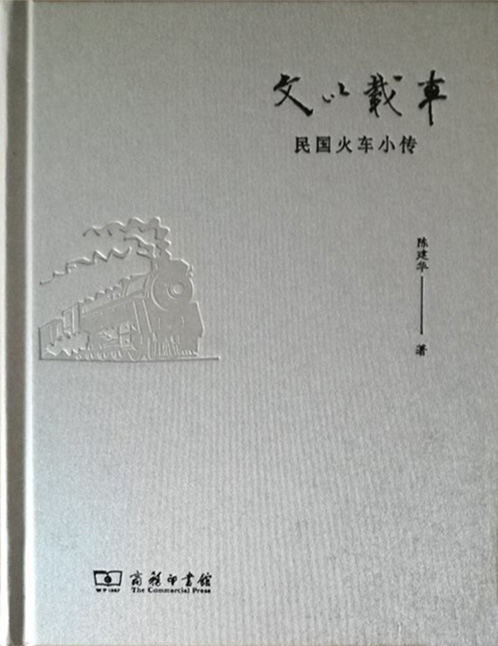
《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
相应地,晚清时期的报纸及画报上出现了不少关于《毙于车下》《火车伤人》的图像或文字新闻。在相关图像新闻中,火车或者是以其巨大的车头插入到画面之中,和画中人物身体的大小比例颇不协调,进而构成一种“巨兽”般的突兀惊恐与视觉冲击;或者是以横亘的车身直接将整幅画面一切为二,似乎暗示着其对原本画面整体感、和谐感的撕裂与破坏。而在相关文字新闻中,也不乏“火车从人身上滚过,当即碾为四段”“碾伤之皮肉已如齑粉,腰间肚肠均皆流出”等相当恐怖的记录。这些图像与文字或可以作为当时社会新闻与真实事件来看待,同时也更象征性地表达出了火车作为现代性力量所“引起的暴力和潜在的破坏感”。
火车速度不仅为身处火车之外的路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焦虑,也给车厢内的乘客以紧张和眩晕的感受。特别随着火车速度的不断提升,“看向”窗外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引起一种“眩晕”与“休克”的效果。对于这种现代“眩晕”感受,西方学者有着相当丰富且精彩的研究。比如希弗尔布施指出铁道旅行连通了出发地与目的地,同时也消灭了作为中间物的“旅行空间”,更使得慢慢欣赏沿途风景变得不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特劳斯视铁路为将“景观空间”转变为“地理空间”的关键性动力。铁路直接并置起点与终点而跳过中间过程所带来的视觉及心理感受,又和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具有了某种同构性,因此“都市人流”“电影画面”与“火车视景”共同成了本雅明所说的形成现代“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的典型代表。这种火车速度对乘客所引发的“眩晕效果”往往会导向另一种小说类型的产生,即哥特小说,或悬疑、恐怖小说。比如施蛰存在谈到自己小说《夜叉》的灵感来源时曾明确指出:“一天,在从松江到上海的火车上,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在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联想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梅雨之夕〉后记》)
坐着火车去查案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被视为“速度巨兽”的火车同时也是人们“收缩空间”和“节省时间”所必要的交通工具。简而言之,正是因为火车的发明、普及与不断提速,人们才有了更为方便和日常化的抵达新空间的可能性。而这种交通工具的进步无疑也增强了侦探行动的便利,拓展了侦探查案的范围。早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里,福尔摩斯与华生就经常搭乘火车离开伦敦去英国其他郡县或乡村查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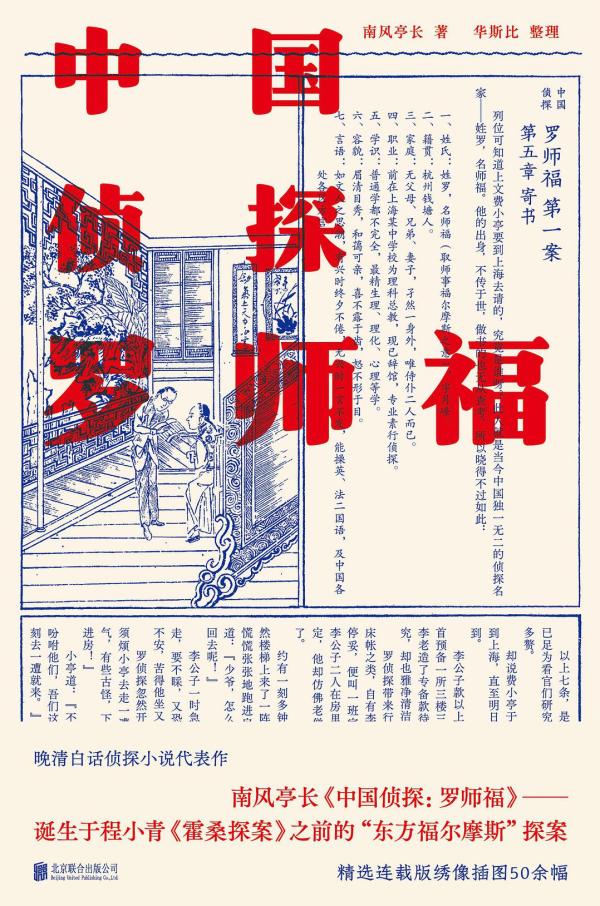
《中国侦探:罗师福》
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中,也经常出现侦探居住在上海,而案件发生于江浙市镇(特别是苏州)的小说情节模式。在这些小说中,侦探想要查清案件,就必须搭乘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才能保证及时赶到案发现场。比如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1909-1910)开篇,在“苏州省城的中区”小巷北底的房间内发生了一起毒杀案,而后当地的警察、巡官、县令、师爷等一众人物纷纷登场,但依旧对这起案件束手无策。终于,“受了学校的教育”的青年费小亭提出“吾一个人,决不能担此重任,吾想还是到上海请他去”,然后“费小亭于十六日傍晚,趁火车到上海,直至明日午后,方把罗侦探请到”,这才最终开启了后来整个罗师福(侦探的名字已经暗示“其师从福尔摩斯”)侦探破案的故事。小说中发生于苏州的凶案最后必须依靠于来自上海的侦探罗师福才有可能获得解决,这既是源自于在当时的上海由警察、侦探、法医、律师等所构成的现代侦破与司法体制相对更加完善,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也普遍更强的现实境况;同时又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城市隐喻”和地域现代性想象。当然,在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来自在当时被认为是更为“现代”的上海的侦探罗师福之所以能及时赶到苏州查案,正是因为其借助了现代火车交通的便利。而具体对应到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小说情节得以成立的前提之一,即是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工具连通了苏沪两地,所以才会有侦探从上海到苏州隔日往返的现实可能性。
火车时刻表犯罪
火车及其速度不仅压缩了现代时间与空间,改变了起点、终点与途中的关系,更是强化了主体对现代时间的精确感受。具体来说,即火车时刻表较为集中和突出地体现了现代生活中人们对于时间准确性与可控性的追求。在俞天愤的侦探小说《箧中人》(1916)一开头,即对火车发车时间的分秒不差予以了先声夺人的强调:“三等车出入之玻璃门訇然而闭,站长左手执绿旗,缓步而来,右手在衣袋中探其银笛,作势欲吹,盖距开车时仅三分钟耳。”之后随着火车沿途各列车站的储物箱相继发生了连环盗窃案,侦探韦诗滕需要借助火车时刻表来进行案情推演,所谓“有轨可循,有时可定,君之行车表,已语我下手法矣”。小说对韦诗滕在出发办案之前先“取火车表细检之”的过程和分析结论,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展现:
余既检火车表,复检日报,第三站之案,发现于上午八点三分以后,第九站发现在八点五十三分以后,第十八站发现在九点七分以后。总而言之,其窃取之时必于夜中,不越于第一班车之时间。例如第三站之末班车,在下午六时必至,次晨六点四十一分乃有第一班车,试问此十二时中,何事不可为?又如第十八站之末班车为下午五点五十一分必至,夜一点乃有向东之车,此六时内之光阴,又何事不可为?故余于此案着手之处不外时地二字,今时已研究明白,则更进言夫地。
侦探韦诗滕借助于对火车时刻表的分析和推理,弄清了犯罪者的犯罪时间与行动路径,进一步锁定了犯罪者的犯罪方式并最终成功将其一网打尽。而小说中侦探“于此案着手之处不外时地二字”,根本上来说是得益于火车时刻表对于现代时空的准确切割,《箧中人》也因此堪称是民国时期展现火车时刻表在侦探小说中所起到功能的最全面且深入的代表性作品。
在后来的侦探小说史上,甚至还发展出了一种专门的“时刻表推理小说”,即犯罪分子利用“火车时刻表”来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原本是侦探用于确定时间具体性与精准性的火车时刻表最终却成了凶手破坏认知准确性的犯罪道具,人们追求对于现代性时间的极致把握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毁灭了现代人似乎可以把握一切的虚假幻象,比如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代表作《点与线》(1957)就堪称其中典范。当然,这种对于火车时刻表的理解与运用方式还不能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们所想象和掌握。
车厢内的“陌生人”
与前文所述望向车窗之外所引发的“眩晕感”一体两面的是身处于车厢内的孤独、警惕与紧张。较长时间与一群陌生人共处在同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内,“陌生的他者”所具备的“匿名性”又构成了现代性焦虑的另一重要表征—我们不知道同车旅客的真实身份,又要被迫和其长期、近距离相处,随着火车到站大家又会各自分散,甚至永不再见。这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性体验与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指出的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矜持”“是一种拘谨和排斥”的关系和感受高度一致。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本雅明才会对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予以高度评价。在本雅明看来,侦探小说中侦探的主要职责就是找出藏匿于人群之中的犯罪分子,而“人群中的人”恰好是侦探小说中一切神秘犯罪者的人物原型和形象隐喻,即侦探小说本质上就是在讲述一个寻找“人群中的人”的故事,后世很多侦探小说研究者也因此将这篇小说看成是世界侦探小说的“雏形”之作。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将“火车上的人”视为“人群中的人”的另一种“变形”或者“典型”。
对此,民国侦探小说作者们也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张庆霖的侦探小说《无名飞盗》(1924)开篇就描绘了一个火车进站时的混乱场面,“火车渐渐走得慢了,嘈杂的声音从窗口送将进来,闹得人头脑发昏”。朋友曙生还特别提醒“我”小心窃贼浑水摸鱼、趁乱作案,即暗示了在嘈杂的车站人群之中可能隐藏着作为“人群中的人”的犯罪分子。李冉的《车厢惨案》(1942)进一步设计了一段车厢内意外熄灯、歹徒趁黑行窃、乘客戒指被盗的情节,小说中熄灯所引发的黑暗正是对火车上陌生人身份的又一层掩盖或者说强化。
此外,在当时的一些非侦探小说中,也有不少对火车车厢内罪案题材的书写,比如张恨水的小说《平沪通车》(1935)就着力刻画了一起发生在铁路旅行中的艳遇与骗局,银行家胡子云在火车上偶遇摩登女郎柳絮春,他一方面难掩内心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时时警惕着这个陌生女人。但最终胡子云仍然不幸“中招”,他忍不住将柳絮春请到自己的头等包厢中休息,而柳絮春中途在苏州悄悄下车,顺便偷走了胡子云皮箱里的十二万巨款。对于这篇小说,学者陈建华、周蕾与李思逸等皆有过相当精彩的论述,比如对小说现实故事原型的考察、对神秘且危险的女性他者的解读,以及对现代社会陌生人信任的建立与困难的分析,等等。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魔道》(1933)则更加在象征的层面上表达出了火车上的“陌生人焦虑”。小说写“我”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到朋友郊外的别墅中度周末,在车厢里看见了一个老妇人,开篇即是“我是正在车厢里怀疑着一个对座的老妇人—说是怀疑,还不如说恐怖较为适当些”。由此,“一个老妇人的黑影”就一直如影随形,不仅引发了“我”对各种黑色事物的恐怖联想,更是如鬼魅般附着在“我”的心头和梦境之中。以往对这篇小说的解读通常偏向于从现代都市人心理焦虑及施蛰存小说中受显克微支与爱伦·坡影响等角度出发。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小说里“我”遇到老妇人的具体空间是在火车车厢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火车车厢所带来的现代紧张感受才构成了“我”后来一系列无法摆脱的梦魇的源头之一。
铁路无疑是一个现代以来的科技产物与文学意象。按照《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中的精辟概括:“在十九世纪,除了铁路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作为现代性更生动、更引人注目的标志了。”一方面,铁路与火车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表征,“科学家和政客与资本家们携起手来,推动机车成为‘进步’的引擎,作为对一种即将来临之乌托邦的许诺”;另一方面,该书作者希弗尔布施也明确指出,“事实上从一开始,铁路就未能免于威胁之论调与恐惧之潜流”。我们可以说,铁路本身就内蕴了现代性进步与危机并存的一体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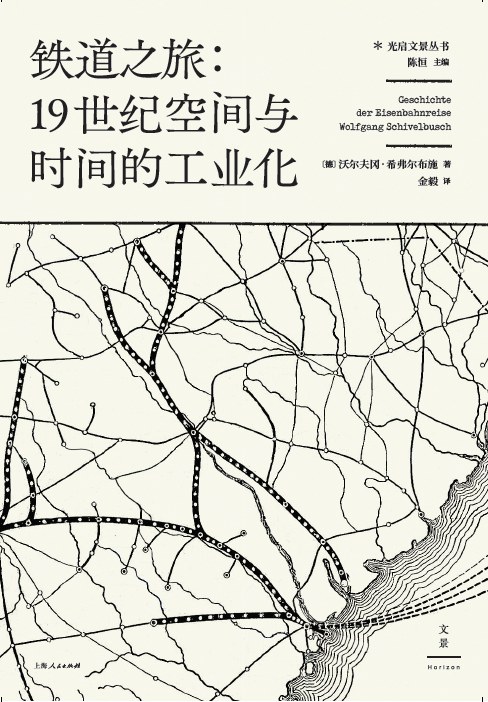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
具体到火车与侦探小说之间的关系来说,二者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与表征,共同形塑了现代社会人群的心理体验和感觉结构。火车作为“速度怪兽”所引发的恐惧感,同时也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如洪水猛兽般袭来时在内心所产生的惊恐和焦虑;火车对现代时间的强力宰制更是在侦探小说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以至于最终衍生出了一种特殊的侦探小说子类型;火车所形成的车窗外“视景”的“惊颤体验”与车厢内的“陌生人空间”,也和侦探小说产生所依赖的现代都市感受具有高度同构性。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侦探小说作家都偏爱火车罪案题材,其中固然有封闭空间、有限人群所带来的情节展开上的便利,但更为根本的心理根源或许在于,火车所包含的现代性危机感受,正是作为一种现代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在本质上所意图捕捉或表达的深层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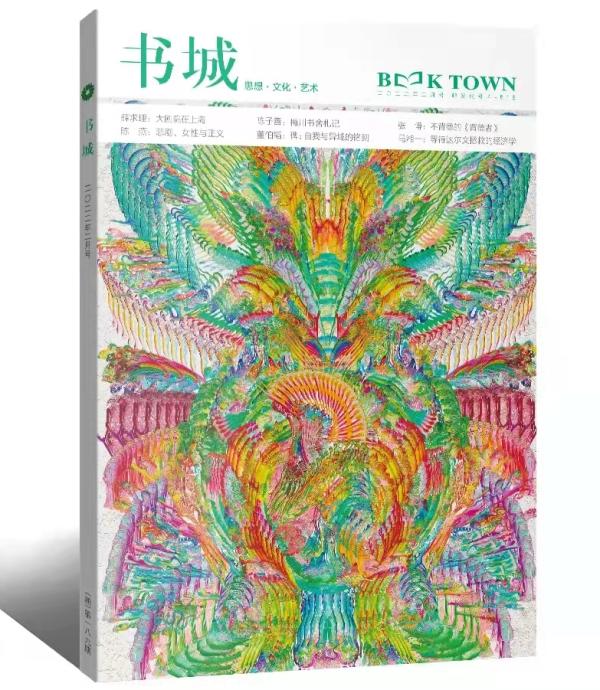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2年2月号),澎湃新闻经《书城》授权刊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