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日本帝国梦之中的身体奴役与……死亡政治
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 1945》(朱新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2月,原版杜克大学出版社,2010年)无疑与日本历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从大的方面来看是运用后殖民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分析理论研究劳动转化,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史的特殊性;而从深层角度来看,以身体叙事为核心的现代性研究视角与方法渗透在对帝国梦崛起的批判性研究中,在对生命与政治、中心与边缘、欲望与异化等核心概念的运用和研究之中,提炼出一种极富想象力和挑战性的资本—帝国暴力叙事,从中让人们看到资本、帝国、文化在帝国梦急欲崛起中的邪恶合谋以及普遍性的反人类罪恐怖深渊。的确如杰拉尔德·菲加尔的推荐语所言,其勇敢和挑衅挣脱了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论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使人感到被直截了当地扔进日本现代性的泥沼里,不管那里多么肮脏、多么兽性。

这是历史阅读中相当少有的双重体验:首先,在来自档案文献、新闻纪录、当事人供词、文艺文本等等实证史料与马克思理论、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研究等分析武器的精准配合之下,从被遮蔽的边缘叙事向历史叙事的中心挺进的学术勇气与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历史思考视野;其次,深刻并且锋利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资本主义与帝国战争践踏人性的罪行,并且提升为对以暴力奴役生命、以专制消灭自由的普遍性质的反人类罪的控诉。如果说前一种体验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研究的思考乐趣的话,后者则更应该唤醒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激情。
想起之前读过的美国日本思想史专家哈利·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的《日本的“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虽然该文的切入角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思想与文学中的知识倾向和理论特点,但仍然提到了在“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中一直被遮盖的边缘地区问题,认为正是在这些边缘地区凸显了既不可化约又无法摆脱的资本主义普遍逻辑;后发性与地方性仍然遮掩无法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的必然展开。这也是马克弟的“绝对欲望”中的核心议题,虽然看起来它不像身体政治议题那么突出、鲜明。马克弟十分强调殖民主义如何通过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暴力掠夺以获取超额利润、喂养帝国巨兽,他认为罗莎·卢森堡说“暴力是资本的永恒武器”一语道破资本主义的伪自然化面目,正呼应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话:“一面是财富的积累……一面是惨剧的积累,劳动、奴役、残暴和道德堕落。”因此他在研究中一再引用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隐匿真理:它只能通过暴力产生,他不断强调这正是对资本隐匿的本质与逻辑的深刻揭露。从暴力、奴役、扭曲人性等核心议题来说,在日本帝国梦的崛起中并没有什么在本质上是独特的、只此一家的“日本经验”。相反,从对闯关东的劳工剥削(包括以包工头为招揽与管理体制的方式,以及1860年马克思以“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到奴役性的强迫劳动,从通过走私毒品而中饱私囊的日本权贵到侵华军队及特务机关在掠夺财富中的特殊利益与垄断特权,从打着禁毒牌子的官方机构本身就是毒品贸易最大获利者到以狂热的军国主义宣传毒化本国人民心灵,最后回到“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中国苦力的劳动和可怜的‘中国工资’,没有日本性工作者和皮条客寄回本土的汇款,没有对劳动主体的隐形剩余价值的剥削,没有发展到对死亡生命的无情压榨,日本帝国梦的崛起根本无法实现。所有这些都折射出贪婪的权贵集团与资本家在帝国主义生长史上的共同特性。如果深入到马克弟在书中论述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种种剥削与奴役的细节,可以更明显地认识到暴力剥夺与奴役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普遍性本质。
马克弟自述:“在本书中,产生于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而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因为生命和劳动的具体存在物是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中国苦力、在中国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输送能量与劳动剩余价值给日本帝国主义。”(序言)与劳动、欲望、死去的身体相对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三个阶段: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无辜身体的牺牲是日本帝国梦崛起的基本垫脚石。在日本史学界,1970年代受法国学界影响而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也开始关注对“身体人”的研究,从学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二宫宏之教授反对在史学研究中仅仅把人看作是“政治人”、“经济人”、“思想人”,认为首先要退回到人作为“身体”和“心灵”的存在来重新把握历史,否则政治史、经济史最后也会成为“表层的历史”。如果放在日本帝国掠夺与侵略战争的研究语境中,离开了马克弟所揭示的身体奴役与牺牲史,更加会成为冷漠的“表层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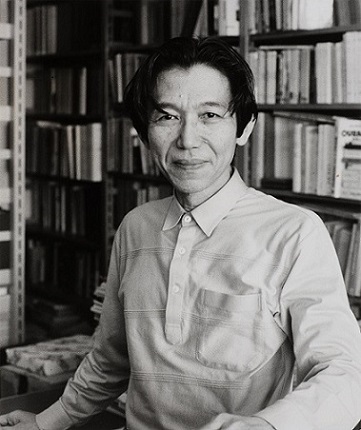
然而,正如马克弟所指出的,“日本现代研究由于受数十年冷战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误导,长期以来忽视了日本资本家在这场帝国主义飨宴中吞噬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劳动果实的事实。研究者们……把眼光局限在日本历史的‘光明面’,要么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同上)关于鸦片问题,在日本有山田豪一的专著《满洲国的鸦片专卖》(2002年),总括地探讨“满洲国”的鸦片政策、生产等议题。华裔日本籍教授伊原泽周在《抗战期中日军的对华烟毒政策》一文(《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1月)中则指出中国史学界对于日军的烟毒政策甚少给予具体而充实的研究与批判,他认为日军的烟毒政策的目的是:充实日军侵华的机密费、维持傀儡政权的财政、搅乱中国的战时金融、麻醉中国人使其身心败坏。(506——507页)并且揭露烟毒政策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主其事,他们贩卖、制造烟毒,一攫千金,以此暴利作为对华的种种策划工作。(521页)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有不少中国学者撰文研究日本对中国的鸦片侵略,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对台湾、东北、华北等地区的鸦片毒品政策与毒化行为,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具体研究成果仍然无法成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与侵华罪行的核心叙事,无法在资本掠夺与战争罪行的核心关系中占据应有的重要位置。马克弟在“序言”中说第七章“中国人民的鸦片”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期间对毒品生意的依赖,“毒品作为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成为日本从中国人民的死亡和补充生活能量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伪满大约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的利润来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为止,伪满统治下的四千万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二十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令人感到有点奇怪的是,这样明显的罪恶竟然没有使一直对鸦片战争那么重视的中国史学界在抗战史的主流叙事中给予应有的重视。
关于闯关东,国内学界过去一般认为九一八事变前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事变后则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关内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实际上这是很笼统并且不准确的说法,李秉刚、高嵩峰、权芳敏三位作者撰写的《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以大量中国国内保存的档案文献、数据统计、幸存者法庭口述等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调查,全面而具体地揭示了日本骗招、强征和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真实历史,遗憾的是马克弟未能采纳该书提供的资料与调查成果。
在马克弟的研究中,有些我们原来比较熟悉的人物显示出他们的复杂性。例如日本思想史上的福泽渝吉,他曾“公开鼓励贫苦的日本女性移民到亚洲各个通商口岸做妓女,……坚持认为女人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没什么用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挣外汇……。”(82页)与他相同的是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他认为日本妓女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色情蛊惑力表明这些男性顾客会很快被“日本化”,然后会购买日本商品,进而认为自己参与买卖日本妇女是“爱国责任”的表现,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亚洲的日本进程。(83页)而那位在佐藤忠男笔下尚有几分正面形象的“满映”董事长甘粕正彦,在马克弟的聚光灯下被还原为帝国特务头子和毒品王。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