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良廷、刘文澜夫妇谈外国文学翻译
陈良廷,1929年出生,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后进入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任宣传助理,编辑电影刊物《水银灯》。解放后,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六十年代任职于上海市编译所,“文革”期间系上海市“五·七”干校编译组成员,改革开放后,与妻子刘文澜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文学作品。
陈良廷与刘文澜的合译作品包括《马耳他黑鹰》《教父》《儿子与情人》《萨马拉约会》《考德威尔中短篇小说选》《奥德茨剧作选》《纳尼亚传奇》。此外,陈良廷还翻译了阿瑟·米勒的《都是我的儿子》、田纳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并与人合译了《汤姆·莎耶出国记》《乱世佳人》《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

光华实验中学和《辛报》
汤惟杰:陈先生,您是哪一年进光华大学的?
陈良廷: 1947年,我十八岁。在光华读过一学期工商管理专业,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徐燕谋的英文课。
汤惟杰:这之前您在哪里读中学?
陈良廷:光华实验中学。这个中学全是光华大学的校友做老师,校长叫傅敦厚,研究生物学。光实的国文老师都好得一塌糊涂,有王芝九、吴竞寸、廖康民(光华大学教育家廖世承之子)、谭惟翰。谭惟翰很有名,写过小说、散文,后来研究评弹。他会把自己的书送给他看得中的学生,我总算都有。
汤惟杰:我1988年读大学,他那个时候还在华师大。他好像会唱京剧的。
陈良廷:他梅派青衣唱得特别好。我在光实中学才慢慢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之前在教会学校,我是老牌留级生。那时因为家庭环境与抗战的缘故,觉得读出来没意思,前途茫茫。初中读了两年,开除了。我姐夫是光华大学的校友,就把我塞进光实,仍旧读初三。光实特别注重文学教育,我进去不久就做壁报编辑,和同学打成一片。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投稿。

汤惟杰:对,我查到您好像读中学的时候就向报纸投稿了。
陈良廷:这也是受到谭惟翰先生的启发。当时有份《新晚报》,由女作家潘柳黛编副刊。她叫谭惟翰组稿,谭先生叫我写,我便学着谭先生的样子写散文,结果就登出来了。我自己投稿是翻译两段幽默,给《辛报》——从成都路的学校把稿子送到山东路编辑部。另外在《辛报周刊》《前线日报》《大晚报》《时事新报》《中华时报》(青年党的党报)上也发表过文章。大多是瞎写的,骗铜钱的。
我在《辛报》上写得最多,当时用了不少笔名,笔名有时候是编辑朋友随便起的。当时和我熟悉的编辑有编《辛报》第三版的董鼎山——董乐山的哥哥。董乐山起初也是影评家,笔名麦耶,我们都叫他麦耶。

汤惟杰:我看您那个时候的文章,一是对文学感兴趣,您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的短文,写她住的常德公寓,还有您好像比较喜欢翻译电影方面的东西。
陈良廷:我就是靠电影起家的。
华纳公司和《水银灯》
汤惟杰:您读中学的时候去哪里看电影?
陈良廷:说来也有趣。我影评写得多了,影院经理、八大影片公司宣传部的人就差不多都认识了,他们会叫我去看试片。这期间认识了在四十年代已经博得文名的马博良。他觉得我太苦,靠笔杆子养老娘,就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华纳的宣传部主任朱曾汶(笔名麦黛玲)。这样,我进了华纳,成了朱曾汶的助手,两人共用一间办公室。
汤惟杰:您哪一年进去的?
陈良廷:1948年。进去后,几个朋友编了一本《水银灯》,出了九期。

汤惟杰:这是你们当兴趣办的?
陈良廷:对,顺便帮华纳宣传。我们两个人假公济私,把华纳办公室当编辑部。朱曾汶和马博良(后去香港,编过《侦探世界》)各出一千块,徐汝椿出一千块,朱定(后来成了新疆作家)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出一千,一共四千块办这本杂志。

汤惟杰:您在华纳的薪水如何?
陈良廷:我和朱曾汶翻译电影字幕,回读者来信,我一个月两百多块,朱曾汶还要构思电影片名,一个月六百多块。华纳总共十几个人。还有个负责进口片子报关的老头,一个月有近千块。
刚解放,影片公司要搞工会了,打倒美国佬。我们就把自己的公司打倒了,解散了。当时,洋大班已经把所有的美钞放在大旅行箱里,坐轮船逃到香港去了。但八大西片公司都有自己的银行小金库,数目不大,留下的中国大班把钱拿出来分了。我拿到了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
汤惟杰:华纳出来以后这段时间,您怎么办?
陈良廷:我是西片发行公司失业救济委员会的一个小头头(工会安排的),负责组织下岗工人——不光是电影公司的,还有越剧、江北戏班子的人学习文件,帮他们介绍工作。其实我自己也找不到工作。像电影院卖票,我也轮不到的。
刘文澜:当时长宁区造了一个长宁电影院,徐家汇造了一个衡山电影院。但它们不要他。
汤惟杰:刘先生,您那个时候在哪里工作?
刘文澜:我在美商电话公司。解放后,中国人暂时没接管它,仍旧是外国人的。他失业了,我是有工作的。
陈良廷:后来,我就又写起稿子了,为《文汇报》《新民晚报》《亦报》写副刊,写苏联电影。我找来苏联的资料,学俄文。朱曾汶学得好,他给《新民晚报》和《亦报》译过不少俄国小品、儿童文学,还翻译了些苏联短篇小说集和苏联戏剧。他笔头很快。
文化工作社和平明出版社
汤惟杰:陈先生,您怎么会变成专职翻译的?
陈良廷:1951年,我见到了吴劳。
我和吴劳早就认识。《水银灯》发过一篇他的文章(笔名奥斯嘉)。这篇文章本来是为圣约翰大学的电影壁报写的,但没有登。他写了四个美国电影女明星眼波的特色,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很吸引人的名头,叫‘Look·Look·Look·Look!’(中文《眼波·眼波·眼波·眼波!》)。

吴劳解放后考上了北京外语学校,他、朱定、叶麟鎏,还有复旦的王科一被派到了专门训练精通外语的特殊外交人才的劳动大学。但他们在北京心不在焉,想到将来要做的工作不理想,先后都溜了出来。王科一回来后在复旦大学继续读,他文笔好,一边读一边翻译了很多苏联小说,后来就到文光书店做编辑了。
王科一对吴劳说,你搞翻译,这倒是一个新的出路。他还介绍方平(当时在译莎士比亚)给吴劳认识。方平和王永年(圣约翰毕业)、汤匡时(汤真,后来支内成了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周访渔(方予)当时是文化工作社的。吴劳平时最爱淘西书店,碰巧买到了巴西亚马多的《无边的土地》。经王科一的介绍,吴劳有工作了,译《无边的土地》——后来果然一炮而红(文化工作社,1953年3月版)。
吴劳遇到我很高兴,让我也来试试。当时文化工作社要出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从英文本译),里面有两篇没人翻,叫我翻。我说我没翻过这种。吴劳说他来帮我校订。我译完交稿后,书一个月就出版了,稿费也马上有了。这就是我第一部翻译作品——普里希文的《北极蜜》(《北极蜜》,普里希文等著,陈良廷、张景桂、姚永彩合译,文化工作社,1953年4月版)。

与此同时,我还在翻译保加利亚短篇小说。这是保加利亚大使馆送的宣传品,英文版,比较简单。我译了十多篇,选了八篇,交给了汤匡时(《乡村故事——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保]达斯卡洛夫等著,陈良廷译,大华出版社,1953年版)。
汤惟杰:刘先生,您什么时候和陈先生一起翻译的?
刘文澜:我和他1951年结婚,当时他正好失业。他在翻苏联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好玩,比如他翻到一半,吃饭了,我来看看,在翻点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英文版的苏联小说不难,我也可以加两句。
陈良廷:她十几岁在西安的时候,就帮她爸爸翻译过《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的文章,登在西安的报纸上。

汤惟杰:陈先生,我记得您那个时候还翻译过美国共产党法斯特的书。
陈良廷:我和徐汝椿一道翻译了五六本。
徐汝椿到朝鲜去过,做俘虏的翻译。他在朝鲜的时候,开头我们经常通信。那时候年纪轻,也不知道什么是机密,他同我讲战场的事情,公安局还特地为此找过我。徐汝椿到底是大少爷,吃不起苦头,后来借故回来了。回来后,他看见几个老朋友都在搞翻译,眼红了。吴劳说你去搞吧,旧书店有本法斯特的书,你去买来看。其实徐汝椿过去从来没译过,他虽然是《水银灯》的编辑,但朱曾汶看不起他写的文章,让他跑印刷厂、制版厂,所以他在《水银灯》没写过文章,但他在圣约翰倒是编电影壁报的。
徐汝椿对我说,你出过几本书了,帮我加加工。于是,他译一点,我译一点,凑在一起,吴劳再帮我们加工。交稿的时候,因为徐汝椿没出过书,就把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投给平明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由巴金和他的弟弟李采臣(后来打成右派,去了宁夏)主事。巴金特别好,自己看稿子,还请语言专家看。这样先出了第一本《都会一角》(平明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然后第二本《孩子》(平明出版社,1954年3月版),第三本短篇《海盗与将军》(平明出版社,1954年4月版),第四本《公民汤姆·潘恩》(平明出版社,1954年11月版)。第五本The Proud and the Free——《自豪与自由的人》,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稿,准备出了,碰到法斯特宣布脱党,出版社打招呼说这本书出不了了,但稿费照给,寄一本清样作为纪念。其实我认为这本是法斯特写得最好的,完全用独白。

《公民汤姆·潘恩》
汤惟杰:您对出版社的编辑印象深吗?
陈良廷:有几个人印象很深。
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吴钧陶。五十年代初,大家听无线电学俄语,课后就去他家(富民路口的别墅)开辅导学习小组会。吴钧陶半残废,自学成才,俄文非常好。他当时已经通过他父亲朋友的帮忙,在太平洋出版社出了三本小书(如《高玉宝传》,太平洋出版社,1952年版)。他知道我在平明出版社译书,也有兴趣,就通过父亲的路子去平明做了编辑。
不过我们的书都不是他编辑的,我们的编辑是祝庆英(《简·爱》译者)。她也是圣约翰毕业的,一辈子没结婚,帮吴劳校过《铁蹄》。她做编辑像吴劳一样认真,能捉出你细小的错误,还会试译两句,提议这句句子似乎可以这样译。她自己翻译也做得很好。她有个哥哥叫祝文光,是文史馆馆员,他们合译了《爱玛》。祝庆英后来译过法租界档案——法租界里抓过许多共产党,所有关于迫害我们党的档案都要译出。“文革”期间,祝庆英也没进干校,去编《法汉词典》了。当时编《法汉词典》的还有方平和李孟安。李孟安的爱人成钰亭(《巨人传》译者)是平明的法文编辑,早先在现在淮海路三联书店的地方开了一家国英书店,专卖法文、英文旧书。
平明出版社还有一个编辑叫陆清源(笔名海岑)。他父亲是二十年代有名的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作家陆士谔。陆清源精通英文、俄文,他和叶麟鎏、王科一、王永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在新文艺出版社,号称“新文艺四大才子”。反右的时候,他们因为之前讲过两句话,都打成右派。
叶麟鎏多亏总编辑孙家晋(吴岩)帮忙,把他调到了青海博物馆,他又学会了针灸,当起了赤脚医生。改革开放后,他回来了,起先也没什么工作,我把他的情况反映给了社里,社里欢迎他,这样他就进了译文。因为吃过苦头,提拔得快一点,开头在汤永宽手下编《外国文艺》,后来升上去了,做主编,然后再升上去做总编。
王科一运气好点,剪辫子,没事了。王永年去了北京新华社,做西班牙文翻译,还翻译过医学方面的东西。我去北京看他,说你应该继续翻译文学,后来他欧·亨利继续翻了下去,也翻了博尔赫斯,再后来的《在路上》也反响很好。当然译笔上,王科一比他更活。
陆清源很作孽,下乡吃了很多苦头。三年自然灾害,饿得没办法,到田里捉老鼠吃。“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小集团,精神也有点失常了,回上海不久就过世了。
汤惟杰:当时翻译的稿费多吗?
陈良廷:五十年代的稿费很多。王科一译了《傲慢与偏见》,一炮而红,以后就专门翻译文学名著,他的稿费一个月要接近一千块了。所以公寓搬来搬去,都是好房子,生活好得不得了。当时宝大的罗宋大餐一块钱一客,一汤一菜一只面包(按:即所谓公司大菜,相当于现在的套餐),我们经常去吃。巴金开的稿费很高,我们当时第一本书《都会一角》,定价一万零四百块,折合成新的人民币一块零四分,定价的百分之十二给我们,这样一算,印三万本书就有三千六七百块。这等于就是版税,当时叫千字千册。

历史研究所、编译所和“五·七”干校
汤惟杰: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公家的单位?
陈良廷:差不多六十年代初。
我是民盟的成员。民盟里有个经济学家叫寿进文,人民出版社约他译经济书,寿进文让我替他分担几章。但徐汝椿不开心,他说你去帮他译经济书做什么,我们又不是搞经济的,我便作罢。后来民盟千方百计帮我们介绍工作,介绍到历史研究所,翻译一批清末小刀会、《字林西报》的资料。我一看那么多资料,一个人不行,就介绍同是民盟成员的朱曾汶等人一起译,后来徐汝椿也勉强来了,一共四个人。
翻译这些东西不容易。很多英文我们从来没碰到过,还要译成清末《北华捷报》那样的文笔,比如法院要叫公廨,还有清朝的官职都很麻烦。我们下了一番功夫。我到徐家汇藏书楼去看那时候的材料,笔记就做了好多本。
历史研究所给的稿费不少,一个月一百二十块。拿了三个月,徐汝椿闹翻了。他说自己是专业翻译文学的,不愿意干这个,就退出了。这样我们待着的人也尴尬了,只好一道出来。又没饭吃了。

汤惟杰:从历史研究所出来以后呢?
陈良廷:开始先待在家里。正巧市委要组织一批翻译力量,办一个编译所。宣传部的石西民、白彦和出版局的丁景唐牵头,草婴具体筹备。先摸底:全市大概有一百多个搞翻译的。再挑选:出版社有哪些基本的文学译者,政治方面好一点,文字方面好一点,出过书的。再问生活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这样筛选了四五批,选了十三人。
草婴做编译所的头,张满涛(张可的哥哥,王元化的大舅子,俄文、法文都好,曾打成胡风分子,此时落实政策)和罗稷南(译过高尔基)有政协头衔:这三个人第一档,一个月一百二十块。
韩侍桁(《雪国》《红字》译者,鲁迅骂过他是狗,“文革”时因此被揪),李俍民(《牛虻》译者),陈梦海(时代出版社编辑,译儿童文学),冯鹤龄(时代出版社译者)都是作家协会外文组的:这四个人第二档, 一个月八十块。
我、徐汝椿、蔡慧是英文的,吕翼仁(左海,吕思勉之女)是俄文的,李孟安是法文的:我们第三档,一个月六十块。还有丰一吟(丰子恺的女儿),一个月四十块。
过了几个月又吸收了第二批五个人,包括荣如德、吴力生、侯浚吉(美国回来,会英文、德文,原先搞航空管理的)。白彦在香港认识中国银行的经理程慕灏(程乃珊的祖父),他说有一个女儿叫程萣华,震旦大学毕业的,从香港回来了,但没翻译过书,白彦也把她吸收进来。后面还有个叶群(笔名叶冬心)。一共十九人。
我们的办公室在后来译文出版社的地方,延安中路967号。这里本来是中国银行俱乐部,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办公室,让了两层给我们。办公室里有五个人坐班,包括党支书记傅禹华(老干部,女的),周朴之(译过两本俄文书,做党的工作),郭振宗(普通职员,曾把草婴作榜样,笔名学婴,后来用了冯春的笔名,取义枯木逢春,是《普希金文集》译者)。
我们不上班的人就两个礼拜去开一次会,政治学习。当时市里面很重视,和我们开会、讲话的都是领导:金仲华、白彦、杨永直都来讲过话。行政上,我们属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兼管,因此蒯斯曛、包文棣、孙家晋都经常来一道学习。
汤惟杰:您在编译所翻译过什么?
陈良廷:他们通过外文书店订了很多刊物,主要是进步杂志,我们看了,把一些消息翻译出来,供领导内部参考,比如美国又出了什么新的畅销小说,谁得了诺贝尔奖。
当时,毛主席接见了一个叫杜波依斯的美国黑人领袖。我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赶译他的“黑色火焰”三部曲。第一部《孟沙的考验》蔡慧译,第二部《孟沙办学校》我和徐汝椿分工赶译,一人一半,然后再帮蔡慧译第一部剩下的几章,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交给主万。这书一出来(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6年3月版),正巧“文革”来了,不能够发行,印了两百本,送了几套到北京,其余都没进过新华书店。开头我们也没有样书,后来工宣队开后门,给了我们一套,最后这些书都流到上海旧书店去了。译这套书是进编译所后唯一一件要紧工作,译了一年多。

汤惟杰:“文革”开始后,您的工资减少过吗?
陈良廷:我没打倒,工资仍旧六十块。草婴、张满涛打倒了,就三十六块的生活费,但后来,他们工资都稍许加了一点。
汤惟杰:之后你进了“五·七”干校?
陈良廷:我在奉贤的干校,和电影的在一起,所以经常会看见王丹凤、黄宗英。

《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
干校搞了编译组,我们接任务,集体编译了很多内部书。比如尼克松要来了,翻译《尼克松其人其事》(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大家一人分一章,后面《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美]C. R. 阿什曼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也是大家各译一章。都是限你们两个星期赶出来,出版社印刷组也搞突击,一下子就送到北京去了。国务院给了我们几次好评,周总理表扬过《尼克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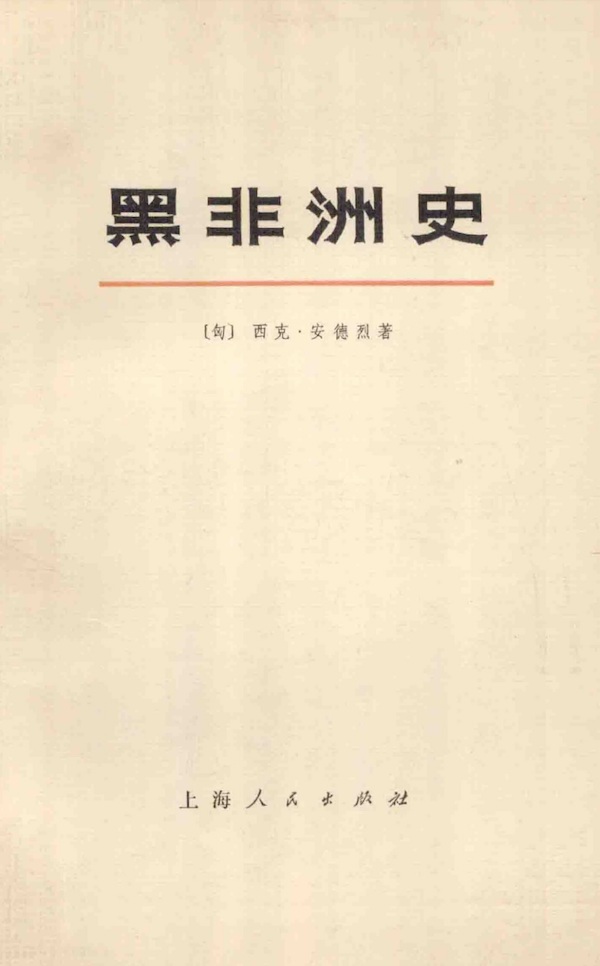
《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
另外还赶译过《黑非洲史》([匈]西克·安德烈著,西蒙·山多尔英译,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73年8月版,第二卷,1974年4月版)和《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美]詹姆斯·理查德·卡特著,陈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版,按:“文革”时的一些集体翻译会署一个共同的笔名,但陈先生又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上海文史馆馆员陈绛所译,他参与编校,此地存疑)。市委写作组的戴厚英还布置我们翻译内部小说。最出名的是《阿维马事件》([美]内德·卡尔默著,钟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我带头组织,一共四个人译了近二十万字。就拿到过一本样书,没有稿费。

当时翻译的环境比较差,把干校一大间废弃的女厕所填掉,改成办公室,晚上蚊子很多。后来宽松了,会放我们回上海的图书馆看一些外文杂志,能接触到《新闻周刊》(Newsweek),我们通过组织关系借回来。
汤惟杰:后来从干校回上海了?
陈良廷:对。回上海后,我对翻译这一行也没什么打算。像荣如德就眼光远了,他读过英文系,也是徐燕谋的学生,回到上海后就翻译了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化身博士》放着。李俍民和任溶溶也是眼光远大的,他们在牛棚的时候就学日文和西班牙文,名正言顺地把《毛主席语录》的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日本版对照,硬读。虽然语法不懂,但也硬啃了下来。后来就慢慢能做这些外文的翻译。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翻译
汤惟杰:“文革”结束后您又开始翻译文学了?
陈良廷:我们回到了延安中路967号,仍旧一个月六十块,再后来让我们选择,要不要进编制,进编制一个月八十块。

一开始,他们让我组织一批人突击译《大屠杀》,由我统稿。这本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参考消息》登过一段,需要全部翻出来参考。书出版后(《大屠杀》,[美]杰拉德·格林著,方平、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版),总算提了译者的名字,销路特别好,初版印了三十七万。自此之后,译文觉得我统稿统出经验了,几本书都要我这么搞,直到九十年代前,《乱世佳人》([美]玛格丽特·米切尔,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5月)还叫我这么弄,再后来《蝴蝶梦》我就不上了。统稿要花很多时间,统稿费却一次付清,只有千字三块钱。我不是快手,也不想粗制滥造。

“文革”后,吴劳也进了译文。他做事情卖力得要命,尤其喜欢帮人忙。凡他看不惯的稿子,都要帮你加工到底。李文俊、王永年都有过被他改得差点哭出来的经历。他心是好的,义务帮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组稿译《战争与回忆》([美]赫尔曼·沃克著,第七章至第九章,方平译,第十章至第二十章,陈良廷译,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鹿金译,第二十八章至三十二章,吴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鹿金即叶麟鎏),我找了吴劳和叶麟鎏,我们分组分头译。吴劳虽然和叶麟鎏一组互校,但他说我的稿子也由他来校,我说最好了,你是我的老牌加工师了。

汤惟杰:我看到1981年的时候,您和刘先生在云南人民出了一本《马耳他黑鹰》([美]达希尔·哈梅特著,陈良廷、刘文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良廷:《马耳他黑鹰》是我解放前在上海的旧书店偶然买到的一本袖珍本(pocket book),觉得好玩,随便看看。后来发现它三次被翻拍成电影,华纳就拍过《马耳他之鹰》。不过这本书一直没人译,我有空就译着玩,也没想出版,那时她(刘先生)已经从电话局退休回来了,也一起译。后来云南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辑室主任梁友璋来上海组稿,问我有什么现成的稿子。我说只有《马耳他黑鹰》,他见有现成的稿子很高兴,马上就出版了——译文当时不敢出,胆子小。

梁友璋说他在北京拿到劳伦斯的一本书,叫《儿子与情人》,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我们觉得挺好,就开始翻。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翻译《教父》。《教父》我最早是从《参考消息》上知道的。当时我女儿陈茂先在外语学院英文系,“文革”后,一些美国人组织来中国的学校,学太极拳,类似旅游团,他们随身带了很多袖珍书,茂先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教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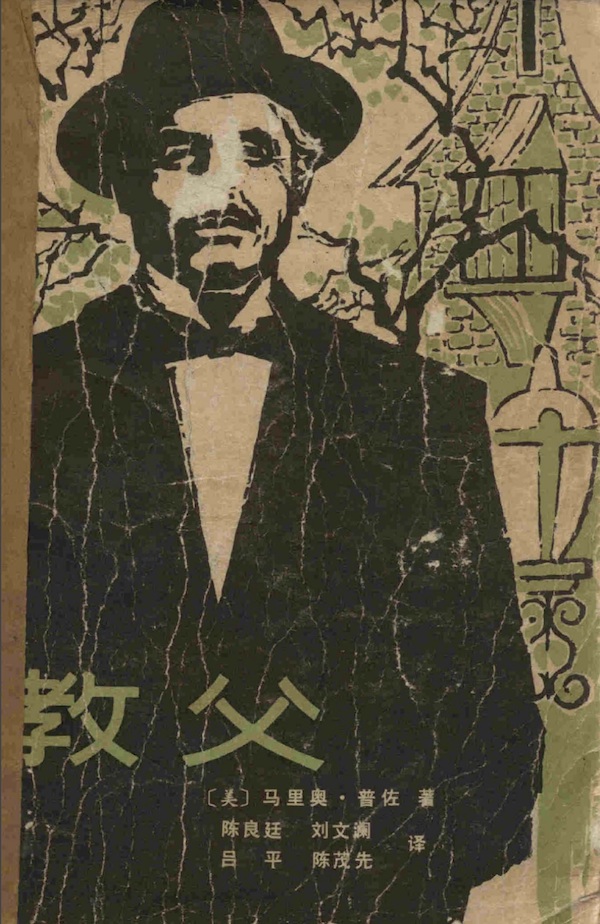
刘文澜:我觉得《教父》的故事性蛮强的,就在家里译,也让茂先去译一点试试看。译完后,问云南人民,有没有兴趣出,他们起先也有点胆小。不过梁友璋后来去北京开会,一些出版社的领导一听说他可能要出《教父》,每个人都找他预定了几本,让这书变得很热门。《教父》里有个别地方比较露骨,我们建议他,如果胆子小,就不要公开发行。他果然听了我们话的,内部发行([美]马里奥·普佐著,陈良廷、刘文澜、吕平、陈茂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
陈良廷:我们译《教父》也算有经验了。太露骨的色情场面我们坚决不译,晓得这点抓得很紧的。出版社说,你译出来给我们参考。我不干。万一你放进去了呢,那我倒霉了。不过,虽然内部发行,云南人民最终还是因为出《教父》吃批评了。那时我们《儿子与情人》也译好了,稿子交齐给他们,但因为反对精神污染,云南人民不敢出了。《儿子与情人》尽管也有点这方面的描写,但比较诗意、隐晦,有人把它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就问云南人民把稿子要回来。几年后我去北京,碰到人民文学外文室的一个搞俄文的领导,叫秦顺新,他对我说现在环境两样了,稿子交给我们吧。于是书很快就出版了(《儿子与情人》,[美]劳伦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按:外国文学出版社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这两本书都是她(刘先生)译得比较多,我主要统稿,那时候我们住在愚谷邨的亭子间,条件比较差。

汤惟杰:1982年出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徐汝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我印象很深,第一版就印了四万本,封面是张守义设计的,也设计得非常好。据说出版社在“文革”前就约稿了?
陈良廷:对的。这个选题最早是人民文学定的。我和徐汝椿译好,交稿,但那时徐汝椿想离开历史研究所,就借了修改爱伦·坡译稿的理由,我们只好把稿子拿回来,分头修改。改好后寄回出版社,出版社又不敢出了,因为爱伦·坡这个作家争议挺大,出版风险蛮大的。这样就经过了一个“文革”,“文革”后稿子从仓库里找出来了,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又不放心了,再把稿子要回来重新再加工。所以这本小说我和徐汝椿做得苦透苦透,一直推倒重来,反复互校。书出版的时候,徐汝椿已经在美国了。

其实爱伦·坡中国人很早就译了。但老实说,没一个人译得看得懂的。最早伍光建用文言文译过,因为伍光建本身不懂英文,别人讲给他听,所以问题很多。后来焦菊隐译过,也译得异常难懂。还有很多人,我们都找来参考,译文都读不懂。因为我学过点俄文,碰巧还买到了俄文本的爱伦·坡,不懂的时候就去俄文里查。幸亏在初译的时候吴劳也在,有很多问题问吴劳的。翻这本书等于翻十本书了,特别花时间。
汤惟杰:《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陈良廷、郑启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9月版)也是您牵头的?

陈良廷:这是当时孙家晋说要出译文丛书,让我们选了几篇译。曼斯菲尔德我们蛮喜欢的,很细致,尤其看了吴钧陶提供的徐志摩的译本,觉得确实配徐志摩的味道,背景气氛让人身临其境。
吴钧陶的父亲是老板,钱多,他家的藏书非常多,有近两万本。我们翻译的很多书都是他提供的。译《乱世佳人》,译文社只有一本书不够分,就从他家里再拿出一本书,拆开来。李俍民译的《牛虻》也是他提供的,后来蔡慧要重译,他说他还有一本,提供给了蔡慧。淘旧书方面,他和吴劳一样,老资格了,当然他比吴劳钱多。
汤惟杰:海明威的英文是不是也不好译?
陈良廷:蛮难译的,海明威就是短句子,你不好自说自话,为了让中文好懂,就把句子加长,加长就不像海明威了。所以我们尽量译得简洁。
译海明威是因为译文社想出全集,狄更斯全集出过了,接下来就是海明威。吴劳牵头。吴劳本来让我们译长篇,但我们身体已经不大好了,长篇吃不消,就短篇译了几十篇,吴劳也帮忙加工(《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的下册主要是蔡慧译的。蔡慧没结过婚,时间比较多,最早他和他的同学李文俊搭档(译了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但后来李文俊到北京去了,成了《世界文学》的主编。
汤惟杰:《纳尼亚传奇》是你们在休息之前翻译的最后一套书(《纳尼亚王国奇遇记(上)》,[英] 克·斯·刘易斯,刘文澜、吴力新、徐海燕、陈良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刘文澜:好像是的。这本书的来历也和《教父》一样,是我女儿从留学生那里拿来的。她拿回来也不看,我一看,觉得蛮好玩的,就开始翻第一册。现在这套书的版权给译林抢去了。译林的封面比译文做得好,所以生意很好。
汤惟杰:你们后面还翻过什么吗?
陈良廷:给黄昱宁编的《译文》杂志翻过。大本的后来不翻了。
汤惟杰:陈先生您做了那么多翻译,有什么心得吗?
陈良廷:翻译理论我讲不出什么。我的方针是,要译得中国人能看懂。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读傅雷、朱雯、巴金、萧乾这种译笔,看得蛮舒服的。像萧乾的《好兵帅克》译得多好。还有张友松(“文革”时笔名常健)、施蛰存、杨绛、杨必,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我反复看他们的译文,尽量找原文对照,受益匪浅。我力求学到点名家的皮毛就最好了。

我年轻的时候,在旧书摊淘到过一本林汉达编的英汉翻译教程,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按:书名为《高级英文翻译法》,世界书局1947年初版,商务印书馆1951年再版)。里面有四个范本是他自己翻译的,中英对照,还有很多例句,告诉你碰到这种句子应该怎么译。他这本翻译教程对我帮助蛮大,我在翻译俄文小说之前,读过很多遍。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先生为此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