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楯︱《牡丹亭》述说的是性而非爱情

问:去年秋天你在国家图书馆讲《牡丹亭·寻梦》时说,汤显祖在四百年前于《牡丹亭》中所书写的是性、人、生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为什么?
答:爱情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发生在具体人身上,它是在两人之间的,如相恋,最起码,是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的,如单恋、暗恋。而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并没有恋着一个人,甚至连一个想象中的人都没有(用今天的话说:心中的“白马王子”),杜丽娘只是做了一个春梦,“男人”出现的第一镜象就是在她梦中的性交合。没有话(“好处相逢无一言”),只是性交合。
视《牡丹亭》为淫的人可以攻击这一点,而喜爱和肯定《牡丹亭》的人中许多人却掩饰这一点。
问:为什么?
答:因为人有许多不能或不敢正视的事。
人类认识自己比认知外部世界就要难得多,而性正是人生命过程中的本质所在,是最一般的,最质朴的,却是很难清楚认知的。
人类与其他有生命的物种不同——最起码,与绝大多数的物种不同,人是生存于自己的社会之中的,有行为规范,有意识形态,这些,都影响着人的认知,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
而正是这种人不能正视,或不敢正视的性,在《牡丹亭》中却有了相对充分的展现。
问:《牡丹亭》中对性是怎样描写的?
答:《牡丹亭》是一个过程,汤显祖的书写,四百年的舞台演绎(原著与传世本是有不同的)——四百年来,文学剧本的读者,曲子的唱者、听者,戏的演者、观者,共同型塑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牡丹亭》。
《牡丹亭》的精华所在是《惊梦》(包含今天舞台上的《游园》)和《寻梦》。我以为无论是看五十五折的《牡丹亭》,还是看汤显祖的“四梦”,最了不起的就在这两折,其他,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就其艺术性而言,更是这样。在这两折中,汤显祖通过性,把人,把生命写到了极致,把因性而生的情(爱情),也写到了无限美好的境界。

我们来看:
——梦前:杜丽娘作为一个少女,清晨与侍女游园,自然是万物萌生的春天,人是渐近成熟的少女,回到房间后,慵懒而眠,入梦前已觉 “春情难遣”,由是得梦。
——梦中:戏从“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直接写到“逗得个日下胭脂雨上鲜”。很美的词句,也是今日非经解说,文化断裂后不懂古汉语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按“日”训:内;入。是全句应解释为:当两性交合时,阳具初进,遂使少女见红。
梦境是“……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在大自然之中;正是大自然提供了条件,决定了这一切。
而对性事的进一步描摹,出自梦境中的男性(一个并不存在的人)是:“……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于是,“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结果“逗得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性交合后“……红松翠偏”(发髻散乱,致簪环移位)。
出自梦者(女性)的追忆是:“敢迤逗这香闺去沁园”,“恰恰生生抱咱去眠”。“他捏这(着)眼,奈烦也天,咱噷这(着)口,待酬言”。“他倚太湖石,立着咱玉婵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捱过雕栏,转过秋千,掯着裙花展,敢席着地,怕天瞧见。好一会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
“他兴心儿紧咽咽,呜着咱香肩;俺可也慢掂掂,做意(着意)儿周旋”。“等闲间,把一个照人儿昏善,这般形现,那般软绵,忒一片撒花心的红影儿吊将来半天。敢是咱梦魂儿厮缠”?
回想的感受是“……好不动人春意也”。
至于在梦外的神仙(花神)眼中则是:“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扇,一般儿娇凝翠绽的魂儿颤”。“……云缠雨绵;……红翻翠妍”。“梦酣春透”;“一个精神特展,一个欢娱恨浅,两下里万种恩情”,“勾引得香魂乱”。
——梦后:女性自觉“……泼新鲜,我的冷汗粘煎,闪的俺心悠步軃,意软鬟偏”。希望“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

问:通过《惊梦》和《寻梦》中这样细致的描写,你看到了什么?
答:汤显祖和在他之后那么多戏文的读者、曲子的唱者、听者、戏的演者、观者于无意识中共同构建的一种对性和生命(生死)的感知。或者说是假杜丽娘而构建的一种对性和生命(生死)的感知。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有的两种感知:自己梦中性伴的感知与自己的感知——杜丽娘在《寻梦》中说“强我欢会”。如果杜丽娘是“被动”的,谁是“主动”?作为梦中性伴的柳梦梅并无其人,否则,《牡丹亭》就成了轻松的神话故事,而不是悲喜剧了。《牡丹亭》不是《白雪公主》,《牡丹亭》是有浓厚深重的悲剧色彩的,它的悲剧部分远胜于“大团圆”结局。因此,我以为:“被动”的是人世间(社会中)的杜丽娘,“主动”的是蕴含在杜丽娘体内自然的生命力。
在戏的演者和观者互动中渐成的戏台上花神眼中的性与性交合(按:这是汤显祖笔下没有的,是由众多在今天我们已不知其名的演者和观者创造的),及四百年传唱中听者、观者所感知的性与性交合,都是非常美,或说是极其美的,以至在剧中人所表现出的难以压抑的性冲动面前(“春情难遣”,已到了“淹煎”——如在水中、火中——的地步),听者、观者心灵所感知的却是纠缠在一起的浓烈的美与深度的悲伤,这一切,正源于对性,对人生,对生死和生命的体味和感悟。

问:怎么说呢?
答:性是生命的过程。相当多的生物是取有性繁殖的。从同花的雌、雄蕊,到异花、异株,到鱼类体外的精、卵结合,到其他动物的雌雄交合,到上天给了人类丰富的性感受,使性与生殖分离,使情感可以离开肉体的交合而独立存在,使人类可以在性的交合和基于性的爱恋中升华,或是堕落。
《牡丹亭》中,杜丽娘自言“我一生爱好是天然”。“好”,在这里读“上声”,“爱好”是动宾结构。全句释为:我一生热爱那美好的事物是天性使然。
性,表现出人类最激情、最深刻、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是如颠似狂,物我两忘,浴火重生。
性,是生命的本质,人的本质。从中可见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于是,有说:性,可作为研究人类的切入点。
性,又可见生命的过程,生命的短暂,转瞬即逝。
由是,《牡丹亭》写“性”,写人,写生命的最根本处;写“性”的力量,“性”的美好,也写“性”的无奈。当那美好释放已尽(得与不得都在其次),就是死,一切不复存在,或说原本就不存在,但它却能顽强地再生出来。于是,《牡丹亭》写到《离魂》时说:“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又说是:“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杜丽娘终于在月圆时,于泠泠细雨,朦朦月色中离去。杜丽娘死的那么美,那么惨烈,惊天动地,《牡丹亭》成千古绝唱。
因性而情,致由生而死,复由死而生。这就是汤显祖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汤显祖甚至说“死而不可复生者,非情之至也”。
问:你所说的在《牡丹亭》中作为人的根本,作为生命的根本的“性”的美好,表现在哪里?
答:我们看,对杜丽娘来说,性是美好的,于是:梦毕时,“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寻梦时,回味性的交合“美满幽香不可言”。
《寻梦》的点题在[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是睡荼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杜丽娘有两次惊觉、警醒:第一,对“美好”的义无反顾的追求,表现在[江儿水]中的“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第二是表现在对生死的感悟——“偶然间,心似缱”——心像是被牵住了:从大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悟到了生命周期。——“我杜丽娘死后得葬于此,幸也。”
我觉得《寻梦》比《惊梦》更令人震撼。《惊梦》中梦前的“春情难遣”,梦后的“冷汗粘煎”、“心悠步軃”,对应《寻梦》的“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问:有多少人能有你说的那种对“美好”的体味和感知呢?
答:不多。有这些感觉的人应是有的。感知和认知有区别,体味和感知有层次。感知敏锐的人,愉悦和悲伤都会比不那么敏锐的人多些。情思细腻,感知敏锐,会有很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伤痛。我们看《红楼梦》中的黛玉就是在听到《牡丹亭》的曲文后,从“不觉心动神摇”,到“如醉如痴”,到“心痛神驰”,而她所听到的正是《牡丹亭·惊梦》中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由此深感自己“在幽闺自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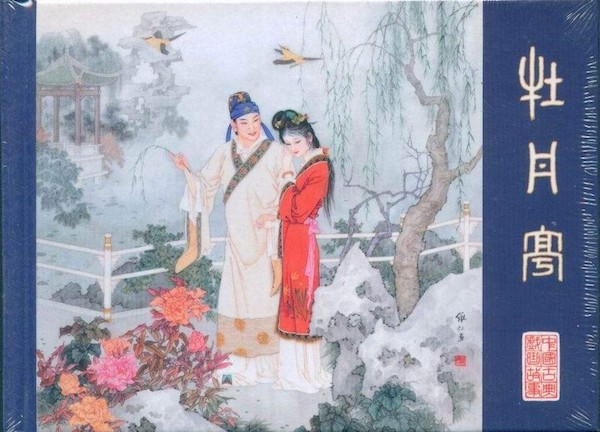
问:人们是因为没有感知,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对《牡丹亭》另做讲解呢?
答:我想不只是感知问题,把《牡丹亭》解说做“追求爱情”和“反封建”而避讳性的,恐怕另有原因。
回避杜丽娘作梦到底“梦到了什么”和寻梦到底“寻什么”,在特定的时期成为阐释、解说《牡丹亭》的一种“主导”倾向。我前面讲了《牡丹亭》与《白雪公主》不同,在这里还要说《牡丹亭》和写爱情的《西厢记》《玉簪记》不同。《白雪公主》纯情而不涉性,《西厢记》《玉簪记》基于情而涉性,而《牡丹亭》则写因性生情,致由生而死,复由死而生。极力想否定这一点的人的做法有二,一是解释,见于已出版和发表的诸多书籍、文章。二是改词和表演,俞振飞先生曾把《惊梦》两支[山桃红]中的涉性之词全部改掉(把“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改作“我和你手相携,行并肩”,把直接描写性事中插入见红的“逗得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改作谁也不明白的“逗得个柳眼梅心别样妍”)。梅兰芳先生则改了表演,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他说:
……杜小姐就是属于内心有“难言之隐”的一种。……剧中人既有了这样的心情,于是老派的身段,不论南北,就都要在这一方面着重形容。……唱到“则为俺生小婵娟”一句,她才慢慢地站起来,边唱边做的走出了桌子,这以后就要用身段来加强她的“春困”心情了。等唱到“和春光暗流转”一句,就要把身子靠在桌子边上,从小边转到当中,慢慢往下蹲,蹲了起来,再蹲下去。这样的蹲上两三次,可以说是刻画得最尖锐的一个身段了。这是南北相同的一个老身段,我从前也是照样做的。后来我对它有了改动的企图,……我觉得也太过火一点吧。……杜丽娘的身份是,十足是一位旧社会里的闺阁千金。……到底她是受旧礼教束缚的少女,而这一切又正是一个少女的生理上的自然的要求。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杜丽娘的一种幻想,绝不是荡妇淫娃非礼的举动。这是少女的“春困”,跟少妇的“思春”是有着相当距离的。似乎不一定要那样露骨地描摹。所以我最后决定,是保留表情部分,冲淡身段部分。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社会学家又称之为“无性”的年代。我们看今日的发展,有报告称:中国人的性行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段中,以及在不同类的人际关系中,较过去的那个年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关系人的幸福感的性行为品相,较过去的那个年代也已有了日渐提升的表现。
问:问题是那个时代已过,甚至是人们的行为在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什么对文学或戏曲的解说却依旧?或是说,对与性相关话题的述说,在居主导地位的话语空间中却仍然缺失?
答:依旧避讳,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中相当多的人缺乏看到问题和找寻答案的兴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性事只做、不说、不思寻——在本应是最亲近的性伴侣间,既缺乏于性交合中多种方式的交流互动,又缺乏日常的沟通、讨论;人多不了解自己的性伴侣的需求和感受,甚至没有想到应该了解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性伴侣的需求,反之,对自己与性相关的事,也不甚了解——对人而言,性不是本能,是需要学习的。
想一想,存在于《牡丹亭》中的性事,有“温存”,有深吻,有吻身体的其他部位,有着意“周旋”的行为表现,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愿景,是不是比在今天相当数量人的性事只是单调而少技能、情感的“插入”,在品相上要差了层次?我们是否会感到虽经四百年,我们的性事及与之相关的认识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问:您怎么看汤显祖?
答:我个人认为:汤显祖的其他著述(包括其他剧作)绝难与《牡丹亭》相比,中国自南宋以降至今的戏曲,也绝难有可与《牡丹亭》相比的。《牡丹亭》中的《惊梦》《寻梦》,在中国的戏曲演唱史中,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中,在思想史中,绝无仅有。
问:你怎么看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并提呢?
答:汤显祖除与莎士比亚同为四百年前人外,在其他方面,我以为是不可比的。汤显祖何以能写出《牡丹亭》的《惊梦》《寻梦》,也不是可以清楚地讲明缘由的。一般人看《牡丹亭》的《惊梦》《寻梦》可能和看《西厢记》《玉簪记》差不多(都是生、旦戏),而在我看来,则认为大不相同,就在于它无论是从艺术上看,还是从对性和生死、生命的认知、感悟上看,都是千古绝唱。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