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大男神杨立华教授B站开讲,在这里彻底读懂《庄子》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月1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在b站开课,第一个视频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期待与热议。杨老师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学识、气质与人格而广受北大学生的欢迎,在校外也收获了大量粉丝。

很多上过他课程的人都评价他为一名现代社会的儒者,然而这次杨老师在b站选择开设的却是庄子课程。为什么是庄子?杨老师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首先,《庄子》属于经典,而经典之为经典,首先在于它所涉问题之普遍性,凡是经典所讨论的问题、所做的思考,对一切时代来说,都有它的同时代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部伟大的经典、每一个伟大的经典性的哲学家他的思考都与我们今天有同时代性。而正确地阅读经典是把经典转化为我们同时代的思想。
阅读经典,深入地、专精地读一部或者几部经典,一个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凝聚精神。因为真正坚硬的、坚深的、经典的阅读,必须调动起你自己最高的主动性,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深入进去。所以,经典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是有持恒的重要性。尤其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变化越来越剧烈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经典的恒久的力量,来给我们支撑。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不仅是中国最伟大哲学家系列当中的人物,而且他还影响了庄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哲学家。庄子像一个中国文明里的巨大的漩涡 ,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对他的某种程度的欣赏和迷恋当中,但是我们都只能在漩涡的核心环绕。似乎在不断地触及它,但又似乎永远接近不了。
杨老师也回忆了他本科时期的经历,选择了不适合的专业令他一度迷茫痛苦,而大二偶然对《庄子》的阅读改变了他的一生,使得他转向了哲学,并走出了“无法忍受的穷极无聊,懈怠,没有方向,迷茫”。
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过类似的感受,如何对抗生活的无意义感,或许阅读经典能够提供力量。然而,这种阅读显然不都是愉快的阅读,它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避免“贴标签”式的理解与阅读。我们对庄子的理解,如果只是停留在“听说”的层面,那么就永远无法领会我们的往圣先贤们达到的高度,也无法具体地产生对中华文明内在的自信与自豪感。

今天,小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杨老师在《庄子哲学研究》中对庄子哲学思辨内在脉络的梳理。如果你对《庄子》内篇有所了解,在此基础潜心阅读,一定能够大有收获。
01
真知之路:逍遥的视野
哲学以真知为目标,那么,何为真知呢?对这个问题的领会,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路径。在庄子哲学里,何为真知的问题是以否定的方式解答的。只有明确了什么样的知不是真知,才有可能确立真知的标准,进而敞开抵达真知的道路。
这一否定式探索的开端是一个根本的质疑:怎么知道我们所说的知不是不知呢?怎么知道我们所说的不知不是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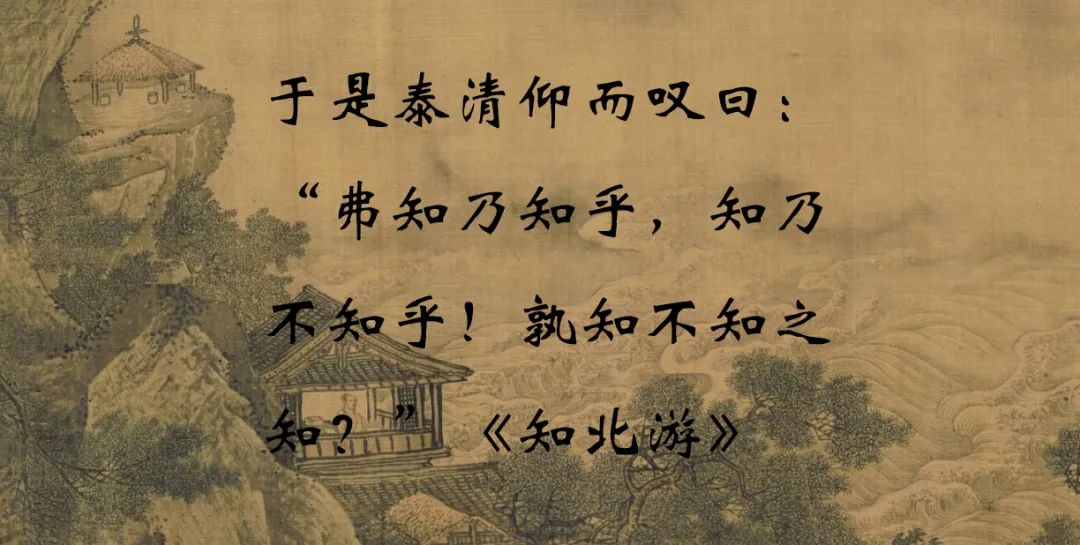
在庄子那里,没有确定性的知不可能是真知。也就是说,确定性是真知的首要标准。而由于知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有所待,有确定性的真知必定是无所待的。无所待的确定的知,是无条件的。换言之,真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成立的,因此是普遍的。
但这样的知有可能存在吗?如果普遍、绝对、确定的真知有可能实现,那岂不意味着可以有某种人格性的万物的主宰者?而如果这种真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庄子以真知为追求的哲学思考岂不成了不折不扣的徒劳?
而且,既然真知是普遍的、绝对的、确定的,那么,它应该遍在于一切个体的心灵。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意味着可以有不认同真知的心灵,那么,真知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确定性又从何谈起呢?
真知遍在于一切个体的心灵,只是在大多数人那里,它都被遮盖了。对真知的遮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来源于真知本身。而之所以有揭开这遮盖的可能,也同样是以真知为根源的。
去除了遮挡的无尽辽远的视野是真知得以揭示的前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逍遥”本作“消摇”。“消”是消除义,“摇”是摇动、挣脱。两者都是否定性的,指向对大知视野的遮挡的去除。
那么,究竟什么遮挡了呈露真知的视野呢?知和用是《逍遥游》全篇贯通性的概念。而与用相关联的知总是有所待的。因此,要想达到绝对的、确定的知,就要超越用的关联的遮挡。
一旦被纳入到用的关联的整体当中,人就在用物的同时为物所用了。作为用具的使用者,人使得用具的有用性得到了实现。“窅然丧其天下”之前的尧,是为天下所用的。许由不受尧让,表面上说的是“予无所用天下为”,同时也等于说“予不欲为天下用”。具体的用的关联总是从属性的、局于一域的。在宋人那儿必不可少的章甫,到了“断发文身”的越地成了无处可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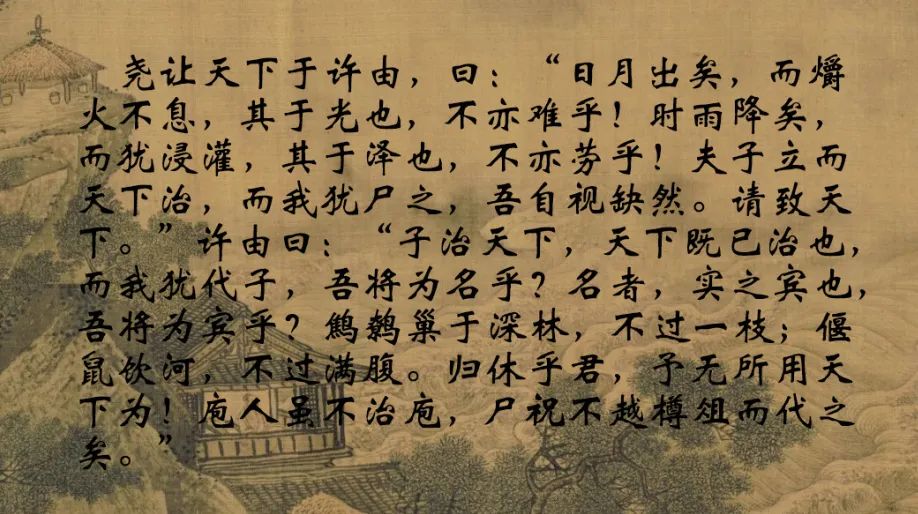
由于用的相对性,与用相关联的知当然也就是相对的。从根本上讲,人类的知识领域的展开还是以用为核心的。即使是最远离实际功用的学科,其产生和发展也没有办法与用的关联的整体完全割裂开来。
庄子对不测的偶然的强调,提示出了他对这一并不在其论域中的问题的可能的回答。以用为核心的知遮挡了确定、普遍的真知,仿佛光芒吞没其晦暗的来源。
02
“真宰”与“是非”:两条线索
“真宰”和“是非”是《齐物论》两条交织的主线,最后收结于“罔两问景”章的“待”和“梦蝶”章的“物化”。由“消摇”敞开的大知的视野,为存有的基本问题的展开提供了可能。个别存有的存在及其形态从何而来?以何者为根据呢?有“使之者”吗?
真宰
《齐物论》首章一个隐蔽的关键词——“使”被完全忽略了。而这个词正是后文引出“真宰”概念的关键:“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这一段文字里涵藏了庄子思辨结构的核心。

华祖立《玄门十子图》
庄子之所以被误解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恰恰是因为他的哲学质疑和追问的深度。对于一种拒绝接受任何成见的哲学来说,确定无疑的思考的起点是回避不开的问题。庄子是从人的存有的直接性出发的,同时涉及心与身两个方面。
庄子没有在入手处便去探讨纷纭繁复的心灵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是体察到所有情感念虑都与“此”相关联并且似乎都根源于这个“此”。这些似乎由“此”而来的短暂易逝的心灵显像是不由自主的,由此可以推知,其关联的另一端有一个无法把握的“彼”。
若心灵的种种显像完全来源于“此”或“我”,那么就应该是可知的、可以掌握的,但深入的体察将会发现它们的产生、变化和消失都有无从认识和无法掌控的方面,所以,只能从与“此”相对的“彼”来理解。“此”或“我”不仅不知道心灵显像的产生、变化和消失,也不知道自己的所由来、所去往和存有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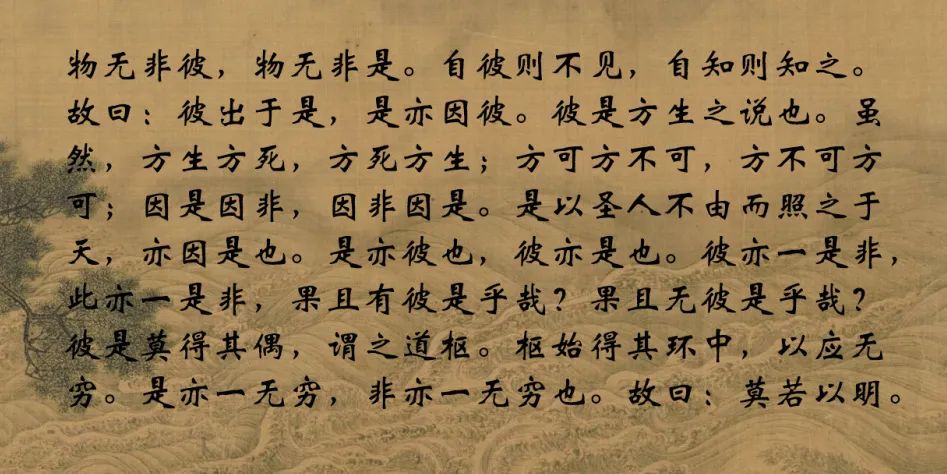
反思中对自己的根源的追问,充分暴露出了“此”或“我”的非根源性。因此说“非彼无我”。这一“彼”“我”之间的必然关联又是为何者所“使”的呢?由此似乎可以推出“真宰”来。但既无眹迹可寻,又似乎找不到确证的方法。
由于身体在人的存有的直接性中也是切近的,庄子也做了相应的考察。庄子没有对身心关系给出正面的讨论,但从他的种种相关论述看,身与心是可以相互作用的并行的实有。心灵可以对身体施加影响,但“百骸”“九窍”“六藏”之间的有序运行并不是心能够支配的。由此似可推出“其有真君存焉”的结论。
而且无论是否能“求得其情”,换言之,无论对其知还是不知,都无法影响“真君”之“真”。对人的心和身的体察,可以推论出“真宰”或“真君”的存在。但这种体察并不意味着哲学上的证明。
是非
以真知为追求的目标,则“是非”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由相对立的认识的存在,可以推知一切声称其具有普遍性的知其实都是相对的。麻烦的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是又道出了一个普遍的论断吗?这一普遍性的论断至少是可以被质疑和反对的——这并不困难,那岂不是又陷入是非之争了吗?

由此开启的是一个无尽的循环。事实上,只要涉及是非的问题,这样的循环就是避免不了的。当我们说分辨是非不对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出了自以为正确的东西。是非的循环是根源于认识的实际还是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庄子清楚地看到了语言的从属性——“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真正的至德者都是无言的。关于道的言说在庄子之书里都出自闻道者或知道者之口。而且这一类的言说也都是“尝言之”“尝试言之”和“妄言之”。对道的言说,也会落入无尽的循环。当我们说道不可言说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出了关于道的某种理解。于是,只能再用一层否定来消解刚刚说出的东西。这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过程。
是非的无尽循环虽然不能说与语言的局限性无关,但并不根源于此。之所以会有是非之争以及由试图消解是非之争而来的无尽循环,是因为个别存有根基处的此和彼的分别。
一切个别存有都有其“此”,只不过有的是自在的、盲目的,有的则是自觉的。对于不能自觉其“此”的存有,“此”是其维持自体之一的倾向的体现,而“彼”则是从瓦解的方向呈显的。
正因为有无限多“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的自觉其“此”的存有,才导致“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人与人之间根本上的不能相知,也是人的无法消除的主动性的保障。
然而,真的有“彼”“此”的分别吗?还是根本就没有呢?说有或说无都会落入知的范畴,根源性的怀疑则是真正的不知。这一不知指向了对“彼”“此”对待的超越——“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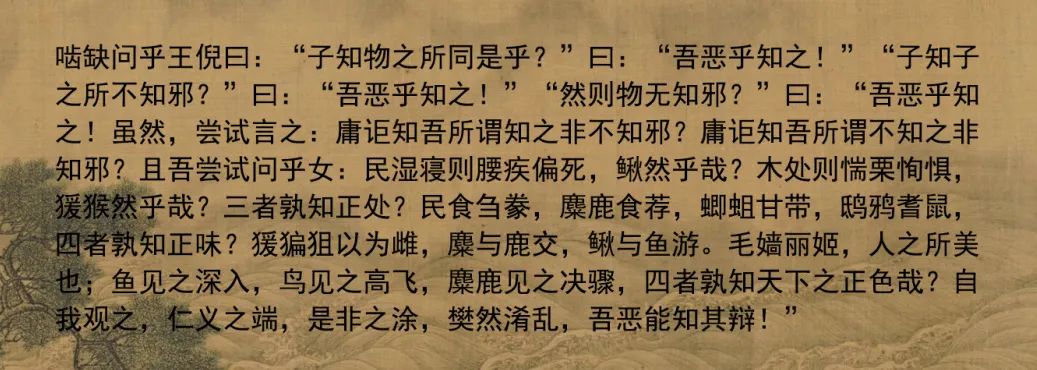
然而,吊诡的是:不知也是知,换言之,是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自觉其“此”的个别存有除自知以外,还知道自己的不知。深藏在自知的根基处的不知,呈露出根源性的他者——“非彼无我”的“彼”。这个“彼”与“此”不构成偶对的关系,是“此”的根源。作为“此”的根源的“彼”就是庄子所说的“真宰”或“真君”。
“真宰”或“真君”在不知中呈露。由于不知是自知的根基,所以,一切以自知为基础的知在本质上也都是不知。这样一来,对待中的“彼”“此”以及由之而来的“樊然殽乱”的“仁义之端,是非之涂”也就失去了声张自己的普遍性的基础。
至此,《齐物论》的两条线索在不知这个关键环节上结合起来了。
《齐物论》最后一章梦的寓言以最坚硬的方式引出了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无法证明自己是否活在梦里,是一个根本的哲学困境。除了真正的“大觉”者,甚至都没有人能“知此其大梦也”。“大觉”者的所见不进入言说,只能通过闻道者的思考和体证略见仿佛。“梦蝶”章思辨的关键环节也是不知。

刘贯道《梦蝶图》
对于觉与梦的分辨,庄子没有做任何徒劳的努力。在梦中又如何呢?难道不是同样在不由自主的变化当中吗?既然都在变化的不可掌控当中,不恰恰证明了无论在觉还是在梦,都有与“此”相对待的“彼”的客境存在吗?
03
“物之化”与“命之行”
何谓客境?凡不在自主掌控范围的,皆可归诸客境。客境既然是实有的,那该如何理解庄子将“有以为未始有物”看作知的极至呢?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庄子说的是“未始有物”,而不是“无物”。从《庄子》内篇里“未始”的用例看,这个表达是有否定意味的怀疑语。疑其未必有,亦不能必其无,则入于不知之域。以古之至人之“以为未始有物”,只能证明在庄子那里至人之知即是不知,而不能由此认为庄子否定物境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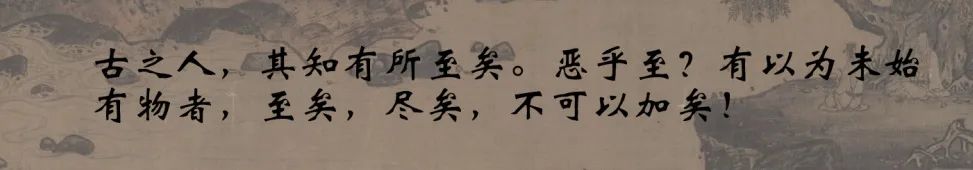
物境的存在是由自觉其“此”的存有的自知所体察到的变化的经验来证实的。由于有觉性的存有的自知只是对自身同一性的觉知,是始终不变的,所以,不可能是变化的经验的来源。当然,这里所说的对自身同一性的觉知并不意味着个体存有的自体之一的实现,而只是持续变化中不变的倾向。
既然变化的经验的根源不在有觉性的存有的自知当中,那就只能归诸客境了。不因变化的经验而改变的对自身同一性的觉知,是有自主性的主体的明证;而变化的经验不为自主的主体所掌控,则呈显出客境的本质。
具体的知总是试图把握各种变化,并藉以操纵它们——延缓、阻止、触发和增进。然而,无论是感官经验的认知还是知性的认知,都有无法确定的部分和要素。感官经验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超越的局限性是显见的。知性所认识的各种规律则容易被误解为普遍必然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的错觉。

由于无限在根本上无法认知,也就是无法主宰和支配的。这也就构成了客境之为“客”的本质。换言之,不测的偶然才是客体的真正内涵。变化的客境的“不得已”和“不可奈何”,在庄子哲学里被揭示为“物之化”“命之行”。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变化的偶然与不测的一面,则会陷落为完全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虽然一切变化都有不可测知的偶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变化的过程是完全没有确定性的。知的根源就在于自觉其自体之一的主体试图将不测的变化纳入到某种同一性秩序中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知其实都是主体主观化客境的结果。
尽管具体的知不可能是普遍必然的,但仍然可以对实际的变化过程产生影响。能自觉其“此”的存有始终有对自身同一性的觉知,这一觉知在根本上是一切变化的经验都无法消解的。在无尽的变化中自持,有陷落并迷失于不测的同一与差异的纽结的可能。
沉溺于某种感官快乐的人,汩没在偶然的客境的一与异的流转中,部分地失去了返归自体之一的自知和自主。故庄子说:“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能在变化中自持、自主者,其自身同一的觉知在根本上必定表达为否定性的“不”。否定性的“不”对于有觉性的存有而言,是普遍的和本质的可能。
这样的自主不在任何被动的束缚里,是人的最高主动性的体现。人的自主和自持却能够反过来通过具体的知对实际的变化过程产生影响。自身不受影响却能够给他者带来影响和改变,是主宰者的作用的表现。当然,由于有觉性的个体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个体的自知以及由之而来的各种具体的知的主宰作用也并非普遍的。
04
不知之知
自觉其“此”的存有的自知以及各种具体的知都是有限的,其根基处都是不知。不知之知才是确定、普遍和绝对的。换言之,只有不知之知才是确定无疑的真知。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真知是遍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敞开真知的可能。其所以如此,恰在于对于真知的遮盖源自真知本身。
对于迷失在无止境的逐物当中的人来说,不知之知是一种需要克服的缺陷,而不是有敬畏的人生的地基。部分醒觉者深刻地知道其根本上的不知,然而,对自己的不知的知道仍然是有分别的、知解意义上的。
对于能自觉其“此”的存有,无法掌控的偶然和不测整体性地呈显为“命”。面对整体上隐身于彻底的晦暗中的不可奈何,唯有“安之”而已。将“安之若命”理解为消极的随顺,理解为衰朽者不可救药的油滑,是对庄子哲学精神的根本背离。
“事之变,命之行”既不可测知,即使想要随顺又从何随顺起呢?“安之”其实只是置之度外、不为所动而已。有觉性的个体存有始终有对其自身同一倾向的觉知,并以此为基础持续地自我设定——庄子所说的“吾之”。尽管在实存的层面,这一自我设定的边界并不确定,但有了明确的内外的限隔,也就有了自身同一的范围。
试图在被设定为“自”或“我”的范围内维持其自体之一,也就有了“说生而恶死”的倾向。然而在无尽的变化中,有限的个体自我设定的自体之一的范围终归是无法维持的。自我设定的基础在于以自身为对象的自知,而自知的根基又恰恰是作为根本知的不知之知。
自我设定的自体之一的消解——死,从根本上讲是自知向不知之知的返归。在这个意义上,死从来都不是外在的,而就在生的根基处。“死生存亡之一体”,就内蕴在自身同一倾向的自我觉知当中。
##20220216
本期活动
你最喜欢庄子的哪些思想?欢迎在留言区聊一聊,小北将挑选2位幸运读者,送出本期主题图书《庄子哲学研究》以及B站课程一份!
原标题:《北大男神杨立华教授B站开讲,在这里彻底读懂《庄子》》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